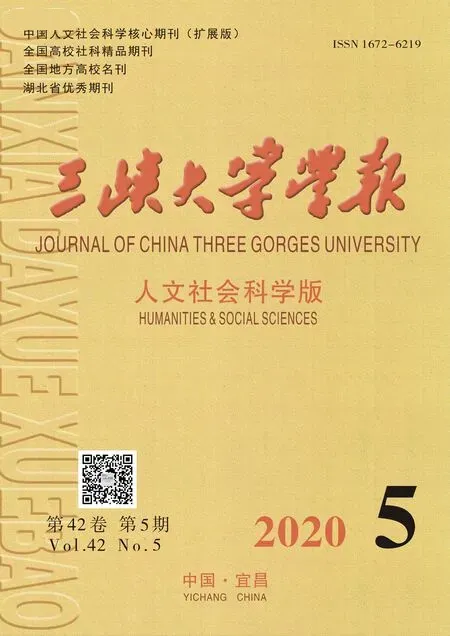论胡适对《独立评论》历史的篡改
李文才, 张卫东
(1.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2.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7)
《黎昔非与〈独立评论〉》[1]于2002年出版以来,《独立评论》的经理人黎昔非及其对《独立评论》的重大贡献,渐为世人所知,由此所衍生出来的相关问题,诸如黎昔非与《独立评论》、黎昔非与胡适的关系等,随之成为学界关注的“学术热点”,相关研究论著也相继公开发表。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独立评论》的认知,大致停留在这样的层面:只知存在一个以胡适为核心的编辑部,而以黎昔非为首的社务部则基本不为人知。作为《独立评论》的实际经理人,黎昔非不是被长期掩蔽,就是被人为地褫夺经理的功劳,甚而将其辛勤付出张冠李戴于他人。而追溯这一状况的形成原因,则又缘于胡适对《独立评论》历史所进行的刻意掩盖、歪曲、伪造和篡改。然则,胡适为何要篡改和伪造《独立评论》的历史?他又是如何篡改和伪造《独立评论》的历史?凡此诸般疑问,皆值得深入讨论。
黎昔非与胡适,因为《独立评论》而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笔者曾综合学术界十余年来的相关研究,先后撰写《胡适的戕害与黎昔非的悲剧性人生——黎昔非与胡适关系探秘》《胡适戕害黎昔非原因试析——兼论黎昔非与胡适关系之真相》,全面论述胡适对黎昔非施加的种种戕害,及其对黎昔非人生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对中国近代文化学术的消极作用,并深入分析了胡适戕害黎昔非的原因。不宁唯是,胡适利用创办《独立评论》之机,剥夺了黎昔非研究生学业和学术研究的条件与可能,将他从人生的上升阶段推入下降阶段,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甚至连黎昔非付出了巨大个人牺牲而为《独立评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也企图加以剥夺,将其从《独立评论》的历史中彻底清除。故今特撰此文,对胡适篡改《独立评论》历史的手法、原因、背景等稍加剖析,以期最大程度地还原《独立评论》的历史真相。
一、胡适是如何篡改《独立评论》历史的?
胡适一向把创办《独立评论》看作其人生的得意之笔,他总是乐此不疲地在各种场合和著述中言及该刊的创办情况,晚年更是在所撰《丁文江的传记》中专辟一章,对《独立评论》的创办历史进行回顾。然而在具体评述的过程中,胡适对于《独立评论》社务部门及其负责人黎昔非,不唯有意识地予以回避,甚而篡改和伪造相关史实,人为地制造了种种迷惘与混乱。
对于《独立评论》创办过程中的问题,胡适从不回避,有些甚至谈得十分详细而具体,唯独关于《独立评论》社务部门及其负责人黎昔非始终三缄其口,讳莫如深。例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胡适大谈特谈自己及其团伙成员丁文江等人如何如何,而说到《独立评论》社务工作的时候,仅以寥寥数语匆匆带过,略云:“当时排字工价不贵,纸价不贵,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所以开销很省。”[2]502在这里全然不见1935年5月胡适在纪念《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时谆谆告诫世人所说的——“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黎昔非,以及“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的“发行所”!而当年在表彰黎昔非时被附带提及的章希吕,在此处却取代了黎昔非的位置,并被说成是“开销很省”的关键!这里只剩下“校对”和“写文字的人”,而当年胡适曾高度赞许的“发行”“印刷”“杂务”以及由黎昔非“一个人支持”的“发行所”,竟如人间蒸发,了然无痕!很明显,胡适在这里是想告诉世人:《独立评论》社不存在社务部门,《独立评论》的社务工作只是“校对”任务,由住在他家里的“朋友”章希吕来承担。
胡适作为《独立评论》的主编,加上他煊赫的地位和名声,故后来学者在研究《独立评论》及其相关问题时,全盘接受了胡适的这些说法,将胡适的话当成权威的历史资料。为了让世人坚信他的这些说法,胡适还以其一贯的手法,大力宣扬他在撰写《丁文江的传记》时如何广泛搜集第一手资料。他说:“一九五五年的冬月里,我把Columbia Univ.所存的《独立评论》全份,及《科学与人生观》等等,全借在我寓里,细细读一遍。又把我的日记细细翻查一遍。”[3]1299-1300此外,胡适还特别强调了他写作态度的认真和严谨,云:“我检查了我手里的材料,我决定用严格的方法:完全用原料,非万不得已,不用second hand sources.这是材料的限制……其实这是我平生自己期许的工作方法,就是‘述学’的工作做法。”[3]1299-13001960年《丁文江的传记》再版,胡适又对此书作了细致校勘,他说:“我借这个重印的机会,仔细校勘一遍。新校出的错误,都在重印本上改正了。”[2]548胡适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他撰写的《丁文江的传记》是一部极其“严谨”“严肃”、经得起事实和时间检验的“信史”。
正是在胡适长期的、有意识的误导下,关于《独立评论》的种种曲解和违背历史真实的奇谈怪论,长期以来弥漫于史学界和舆论界。诸如:“那时候一切也比较简单,几个读书人,只要将自己月收入5%拿出,就可撑起一份杂志来。而杂志一经出版,往往很快成为一个公众舞台。《独立评论》正是如此。”[4]45依此说法,则办刊时间长达五年多、发行量大而影响甚巨的《独立评论》,竟然无需社务部门,仅靠主编胡适随便召集几个文人、筹措些许银两,再请一两个朋友到家中顺带做做,便可办得风生水起、长盛不衰。办刊之容易果如斯乎?或曰:《独立评论》的“编辑杂务及校对等事由胡适本人,罗尔纲、章希吕义务效劳。”[5]246或曰:“他们一切从俭,只请了一个职员负责发行事务,其他事务多由朋友帮忙,如校对等文字工作就由当时在胡适家住的章希吕负责。”[6]332诸如此类,不烦一一列出。将上述诸般说法综合起来,那就是:《独立评论》即便有社务工作,也是胡适亲力而为,有时或请朋友如章希吕、罗尔纲等人帮帮忙即可完成。台湾学者就对《独立评论》的办刊“奇迹”表示过质疑,如赖光临就说:“文人办报或杂志,最大难关,在维持不易……《独立评论》依凭四千多元能按期出版,如非抗日军兴还不至于停刊,确然是一项奇迹。”[7]660可惜赖氏对于“奇迹”产生原因的分析,仍基本沿用或重复那些被胡适刻意歪曲了的说法,未能窥得历史的本相。
历史的真相是,《独立评论》实为主编胡适和经理人黎昔非通力合作的产物。黎、胡二人之于《独立评论》,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而不可。已有学者对此有所认识了,如邵铭煌论述《独立评论》社的组织构架,就是把黎昔非作为“发行”人,而与主编胡适比肩并排[8]27;赖光临排列《独立评论》社的组织构成,也是“总编辑”胡适、“发行”黎昔非并置[7]660。完全有理由相信,《独立评论》若是没有黎昔非这样出色的经理人主持日常社务,则能否顺利办刊,都将是未知数,更遑论办得如此成功而持久了。兹举一例以言,黎昔非曾在一封致胡适的信函中写道:“寄报的封袋,据沙滩一个铺子说,那种大的每万份二五元,小的二四元。现在打算明天到前门去问问看看如何。”[1]14所言之事虽小,却直接体现了黎昔非作为《独立评论》的经理人,在经营时的用心良苦,因为以彼时北平的物价水平,如果不是黎昔非如此持筹握算、精密部划,则《独立评论》断难长久维持,更不用说逐年扩大发行量了。中国近代著名报人戈公振曾说过,报馆的经理人作为“一馆之领袖”,需要具有“编辑、营业、印刷”等多方面的综合才能,方可胜任[9]245。因此,经理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是否尽职尽责于社务,直接决定着报刊经营的好坏,其作用是无可替代和至关重要的。黎昔非作为《独立评论》的经理人,全力以赴、竭忠尽智地投入社务工作,《独立评论》无论校对、出版,还是发行、邮寄,每个细节都从未出现过失误,不仅为刊物争取到了一批固定订户,而且发行量逐年递增,最高时达到一万五千册,这些成绩的取得,实皆建基于黎昔非一丝不苟的坚持。要知道,此前晚清风行一时的《时务报》,最高发行量也只有一万四千份,而这个销量的取得,是建立在全国范围内202个代售处的共同努力,以及说服地方大吏官购报纸、让利派发等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另外《时务报》维持日常经营发行的团队成员有15人之多[10]66-78。反观《独立评论》办刊五年,整个社务工作全由黎昔非独力操持,刊物发行量却一路攀升,从创刊第一期“两千本”到第二期“三千本”。仅用一年时间,发行量就飙升至“八千本”,两年之内达到了“一万五千本”,可见其发行效率远超《时务报》[11]145。再如,当时《北平晨报》《世界日报》等大报每日发行约三四千份,《京报》《益世报》等小报每日只有两千左右[12]65。因此,《独立评论》作为一份内容比较枯燥的政论性周刊,能够维持良性运作和发行信誉,并且取得傲视群侪的发行量,主要就是取决于黎昔非出色的经营和发行能力。整个《独立评论》的社务工作,只有黎昔非一人承担,绝对称得上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一个奇迹,对此有学者指出:“当时维持一个报刊机构的运作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尽管有些报刊在发行之初会因‘无利可图’而压缩员工规模,会出现一人兼任主笔、经理人、访员,负责招揽广告,发行报纸的个别情况,但一旦报纸销路渐开,大多会延揽人才,增置设备,扩大经营规模。《独立评论》作为学人自办‘同人杂志’,显然缺乏扩大市场的商业野心,在其发行的五年多时间里,始终只有黎昔非一人身兼经理人、发行人,该社营业部、服务部均由其独力支撑。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报刊史实不多见。”[13]57此说允为公道。然而,对于这样一位为他创造了“奇迹”的经理人,胡适每月只为黎昔非提供三四十元的微薄工资,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一书中,对诸般账目都有精心算计,却单单故意回避黎昔非为《独立评论》所付出的这笔账,他提供给黎昔非的低廉薪资,远远不能同黎昔非极度超负荷的工作任务相匹配。由此可见,所谓“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纯属胡适虚构的伪历史,事实上《独立评论》的“奇迹”完全是建立在对于黎昔非超限压榨的基础上。
在篡改和伪造《独立评论》历史的过程中,除胡适本人带头造假之外,还有不少胡适的乡亲、友好,也先后加入造假的队伍,从而成为胡适篡改和伪造《独立评论》历史的“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在所有协同胡适造假者当中,石原皋可谓“杰出”代表,他在《闲话胡适》一书中言及《独立评论》,云:“无人代他照料排印、发行,乃请他的老友章希吕到北平,住在他家,主持发行事情。章原来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编辑,搞这些事是内行。”[14]142与胡适完全否认或掩蔽《独立评论》存在社务工作的说法有所不同,石原皋倒是承认《独立评论》社是有社务工作的,只不过他说这个社务工作是在胡适家中进行,并将社务工作负责人说成是胡适的“老友”章希吕,则是彻底的虚假不实。石原皋何许人?“石原皋是胡适的亲戚和同乡,并常有交往,熟悉胡适的生活和家世,对其学术思想也有所研究。”[14〗(再版后记)213石原皋作为胡适的“亲戚和同乡”,与胡适一家关系亲密,因此他关于《独立评论》社务工作的说法,便不会是向壁虚构或空穴来风,而极有可能来源于胡适或家人的日常言谈。由于石原皋是胡适的亲戚兼同乡,又曾一度住在胡家,身份比较特殊,因此,石原皋的相关说法,很容易被世人误解为历史见证人的“实录”。
蒋廷黻关于《独立评论》历史的一些信口开河之说,也可视为胡适篡改和伪造《独立评论》历史的组成部分。蒋廷黻在回忆《独立评论》时曾说:“终《独立评论》时期,社中只用一个小职员,负责发行事务,月薪六十元。”这里至少存在三处错误:其一,“终《独立评论》时期,社中只用一个小职员”,这句话明显不符合事实,因为《独立评论》社除经理人黎昔非外,后期1935年至1937年经胡适批准正式添聘了一位职员——会计陈晋祺[1]72-75;其二,黎昔非并非“小职员”而是“经理人”;其三,黎昔非的月薪不是60元而是40元。短短几句话,就存在三处明显有悖于史实的错误,这一方面反映了蒋廷黻蔑视乃至无视《独立评论》社务部门的直接体现。征诸史实,1932年《独立评论》初创时,蒋廷黻曾因“找不到合适的经理人”而“发愁”,当得知有黎昔非这样“合适的经理人”之后立刻表现出“很高兴”,然后就是急不可耐地“即刻”要“征求昔非同意”,然而若干年后却将这些全然“忘记了”,并摆出一副蔑视与无礼的态度。胡适、蒋廷黻等人企图通过把经理人篡改为“小职员”的办法,以否定《独立评论》社务部门的存在和经理人黎昔非的重要作用。历史真相是,黎昔非作为《独立评论》的经理人,是与主编胡适地位相当的《独立评论》社两位主要负责人之一。蒋廷黻不仅把《独立评论》“经理人”贬为“职员”,而且特意在“职员”前面加上了“小”字,不仅刻意贬低社务部门的重要性,而且素常可能就是以贬义性的语调来谈论“经理人”黎昔非的。
如果说1956年《丁文江的传记》出版时胡适是因一时“疏忽”,1960年再版时,胡适又对此书做了细致校勘,却依然不见黎昔非的踪影。胡适如此“认真”对待、“严格”撰写和“反复”推敲磨勘的《丁文江的传记》,经过两个版次仍然“忘记了”黎昔非及其主持的“发行所”,这就进一步表明:胡适是刻意隐瞒和掩蔽黎昔非参与《独立评论》工作及其突出贡献的事实。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胡适对于《独立评论》历史的掩盖、歪曲、篡改和伪造,并不是从《丁文江的传记》一书出版的1956年才开始的,而是肇端于《独立评论》办刊期间。不仅如此,胡适刻意掩蔽的对象也并不限于黎昔非,他还同时设法掩蔽了《独立评论》社务部门中的另一成员——陈晋祺。
1935年5月19日《独立评论》创办三周年,胡适才在第151期的纪念特大号上第一次公开了黎昔非同《独立评论》的关系。而此前的三年时间里,无论是《独立评论》的封面、封底、扉页,还是《编后记》或其它任何场合中,都没有关于经理人黎昔非的任何信息,可谓了然无痕。需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只要是公开出版的报纸刊物,都一定会在适当场合公开经理人的个人信息,然而黎昔非作为《独立评论》的经理人,竟然没有关于他个人方面的任何介绍。实际上,若不是黎昔非本人此前曾一再向胡适提出辞职,并且最后一次还是带有“最后通牒”式的请求,胡适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公开黎昔非的个人信息,恐怕都将是打上问号的。
陈晋祺作为《独立评论》“发行部”的一名工作人员,长期以来默默无闻,无人知晓,也是根源于胡适有意识地掩蔽。《独立评论》经理人黎昔非,自然是胡适刻意掩蔽的对象,而为了达到掩蔽的目的,胡适还同时掩蔽了陈晋祺,因为陈晋祺不仅是黎昔非的同乡,而且加入《独立评论》也是出于黎昔非的介绍[1]44。陈晋祺的自述之词,得到了林钧南及黎昔非夫人等人的证实。林钧南1932—1937年求学北平期间,曾亲眼目睹了同乡黎昔非经理《独立评论》的全部过程,1998年8月11日,林钧南在致黎昔非次子黎虎的信中,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他说:黎昔非“是总其成的,包括财务、校对、发行等在内。
1933年后,(陈)晋祺到北平,才由昔非提出让晋祺任财务人员,经胡(适)同意才到社的。”[1]58黎昔非的夫人、黎虎母亲也曾对黎虎说:他(陈晋祺)有时也“协助您爸爸处理独立评论的发行事宜”[1]54。可见,陈晋祺是经由黎昔非介绍,并经胡适批准,而成为《独立评论》社的正式职员。陈晋祺的具体职务是会计,但平时除了负责社中财务之外,也协助黎昔非进行文字校对、刊物发行等事宜。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陈晋祺前往贵州投奔叔父陈侃[1]44-45。陈晋祺从1935年春加入《独立评论》社,到1937年四月离职,在《独立评论》社工作了两年,对于《独立评论》也是有贡献的。然而在1935年5月19日《独立评论》三周年纪念特大号中,胡适对陈晋祺只字未提,反而表彰了章希吕,需知章希吕参与《独立评论》“末校”始于1935年初夏,时间在陈晋祺之后;另外,陈晋祺是《独立评论》社正式职员,章希吕只是住在胡适家中的私人朋友。胡适如此处事待人,不公不允于此可见一斑。1936年,胡适在《独立评论的四周年》中继续无视陈晋祺,却将并非《独立评论》正式职员、“住在他家中”的章希吕与黎昔非相提并论。陈晋祺、黎昔非和章希吕相比较,他们在胡适那里的待遇,何以有霄壤之别?原因无他,因为章希吕是胡适的同乡和“朋友”,他不仅住在胡适家中担任其“秘书”,还同时协助胡适做《独立评论》“末校”工作。显然,在胡适的心中,《独立评论》社的工作乃是公私有别、内外分明的。章希吕、罗尔纲皆为亲信,在胡适的心中都是他“朋友圈”中的人,属于“自己人”;至于黎昔非及其所主持的“发行所”,或者其他成员如陈晋祺等,则无一例外地是“朋友圈”外的“公家”人,属于“外人”。由此可见,在胡适的心中,“圈内”“圈外”是有着严格区分的,对于“圈内”的朋友,提携不遗余力,对于“圈外”的别人,则尽力掩蔽乃至打击戕害。胡适于1935年5月第一次被迫公开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关系的同时,就“顺便”表彰一下刚刚开始协助他做“末校”的、并非《独立评论》社正式职员的章希吕,而对于早就参加《独立评论》社并被聘为全职、正式职员的陈晋祺,却只字不提。时至1956年《丁文江的传记》公开出版,胡适在书中完全抹杀黎昔非及其所主持“发行所”,而一切代之以其同乡、朋友章希吕,也就无足为怪了。
二、胡适篡改伪造《独立评论》历史探因
胡适煞费苦心、处心积虑地篡改和伪造《独立评论》的历史,在《丁文江的传记》中更是千方百计隐瞒和掩蔽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关系,企图将黎昔非为《独立评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付出的巨大个人牺牲从历史中抹去,其中必定有其需要隐瞒、需要篡改的“难言之隐”。胡适的“难言之隐”,窃意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胡适为维护个人声誉和独享《独立评论》经办之功,不敢也不愿公开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关系。在黎昔非参加《独立评论》之前的1931年,胡适的日记中曾经两次记述过他的名字[15]85,109,1932年参与《独立评论》之后,黎昔非就从胡适的日记和其他文字中彻底消失,只在《独立评论》三周年、四周年的纪念号中出现过两次,且没有任何的说明。
1931年胡适在日记中两次记述了黎昔非的来访,其因何在?这是因为彼时的黎昔非凭着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生,其身份是独立的、自由的、自主的。彼时黎昔非作为中国公学出身的本科生而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生,令曾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感到与有荣焉。然而,当1932年黎昔非进入《独立评论》之后,胡适便感到与黎昔非的关系已经不同往昔了,因为黎昔非此时已经成为黄节的弟子。众所周知,黄节与胡适的人品、性格、学术,皆是大相径庭,黄节的刚直正派、愤世嫉俗与胡适的圆滑世故、趋炎附势,迥然不同;黄节学术上的务实、深刻,与胡适的飘浮、浅薄,也较然有别。是以两人共事20多年,矛盾日益加深。对于黎昔非成为黄节的弟子,1931年的胡适虽然心中不爽,却是无如之何。1932年黎昔非进入《独立评论》,黎昔非由北京大学研究生转变为胡适的雇员,胡适对于黎昔非的心态遂逐渐发生变化,他很快就发现,将黎昔非操控于股掌,对黄节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既满足了自己的私利,成就自己的大事;又断了黄节的学术薪火,令其后继乏人。胡适对于同样是中国公学出身的三位学生,其爱憎可谓冰火两重天,对另外两位学生罗尔纲、吴晗倍加关怀,极力提携推进;对黎昔非则经济上困苦之,学术上扼杀之。他一再不许黎昔非辞职,控制长达五年有余。通过这五年多的努力,胡适终于达到了目的:在他的全力栽培之下,罗尔纲、吴晗均在各自研究领域崭露头角,进入研究员、教授行列,为他们日后成为历史学家铺平了道路;而另一位同样来自中国公学的学生黎昔非,则活生生地剥夺了他已经到手的研究生资格和本来光明的研究前景和人生途程,而从人生的上升阶段跌入下降阶段。
胡适深知此事若处理不好,对其名望声誉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为了满足自己的既得利益并保持清名,胡适采取将黎昔非彻底屏蔽和掩蔽起来的做法。于是,通过掩蔽黎昔非以篡改和伪造《独立评论》历史,对胡适来说,就成为必须和必然的选择。自1932年之后,黎昔非的名字就从胡适的所有文字中消失,在《独立评论》创刊三、四周年时不得不提到黎昔非的名字时,则采取“空心”战术,完全隐瞒黎昔非的身世和来龙去脉,令人摸不着头脑,个中奥秘即在于此。“住在”胡适家中的章希吕附庸风雅,也效法胡适写日记,尽管1935年以后他部分介入《独立评论》的工作,可是在章希吕的日记中也没有只字片言提到黎昔非。这一诡异现象,以及前文所言石原皋在书中公然作伪,皆非偶然,都是胡适篡改和伪造《独立评论》历史的“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在绞尽脑汁之后,胡适终于发明了上述“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的妙语神言,藉此以彻底隐去黎昔非及其所负责的“发行所”在《独立评论》历史中的存在和地位,从而用经过他篡改和伪造的《独立评论》历史取代了真实的历史,既确保了他独占《独立评论》的创办之功,又抹去了他戕害黎昔非的历史,可谓一举两得。
胡适不愿意让黎昔非与他“瓜分”《独立评论》的创办之功,因此他只要把黎昔非的事情瞒住,就可以继续独占办理《独立评论》的功劳。《独立评论》的成功大大出乎胡适的预料,胡适及其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通过《独立评论》得以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1]88,他们不仅成为当时舆论界的明星人物,掌握着舆论资源,而且在政治上纷纷在国民政府任职,掌控高等学校、研究部门的要津,从而形成了以胡适为首的新的权势集团,而胡适则俨然登上了无冕之王的宝座[16]85。欧阳健对于胡适进入北大以后,从最初为了站稳脚跟,到后来操控文学院乃至校务所耍弄的一系列计谋,以及胡适利用出版报刊、挟洋自重等“善假于物”的手段,终于实现其“横扫文坛,争夺霸权”目标等情况,皆有精致详实的述论[17]111-129。正是在胡适刻意掩蔽之下,黎昔非及其主持的“发行所”悄然消失了,《独立评论》创办的功劳也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一股脑儿地加诸胡适的身上。面对这等“特殊荣誉”,一向奉行实用主义的胡适,自然也乐得顺风扯旗,又何必劳心费神,去改变这个既成事实呢?
第二,种种侥幸心理驱使胡适篡改和伪造历史。首先,黎昔非在研究生二年级时便被胡适拉进《独立评论》,其时还未能真正踏入当时的学术圈,在胡适看来,黎昔非乃“时人未之识”的无名之辈,因此掩蔽他和《独立评论》的关系比较容易。长期以来,世人所理解的《独立评论》,大致停留在这是由胡适主办的一个政论性周刊,论其功则归诸胡适及其成员(如蒋廷黻等),却从来不知道《独立评论》还有“经理人”和“发行所”,更不知道黎昔非何许人也,经办《独立评论》的功劳和荣誉早已被胡适尽收囊中了。及至胡适撰写《丁文江的传记》,谈及《独立评论》仍然立足于对自己的吹嘘,并继续为此而篡改史实,比如他说:“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最大的节省是我们写文字的人……都不取稿费。”胡适所总结的“开销很省”的原因,可归纳为二:一是章希吕负责“校对”,而章又是住在他的家里,因为世人皆知章希吕的工钱是由胡适支付的,所以胡适这样说,言外之意就是我替公家节省了开销;二是写文字的人都不取稿费,这一点确是事实,无需否认。蒋廷黻在总结《独立评论》的办刊历史时,所持角度与胡适略有不同,蒋廷黻曾回忆说:“半年后,已经无需继续捐助,可以自力更生了……终《独立评论》时期,社中只用一个小职员,负责发行事务”,蒋廷黻同时还承认:“办一个刊物需要花费很多人的力量”[11]20-27。我们注意到,蒋廷黻强调《独立评论》本身自力更生的同时,认为“开销很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只用一个小职员”,蒋廷黻此处所说的“小职员”,即是指黎昔非。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蒋廷黻在这里将黎昔非说成“小职员”,并将其月薪误记为60元,证明他对于黎昔非知之不多,对工作情况及重要性更是没有什么了解,从而大大贬低了黎昔非为《独立评论》的巨大付出和重要贡献。此事又从另一侧面表明:胡适一直在设法掩蔽黎昔非,就连蒋廷黻这样的《独立评论》社核心成员对于黎昔非及其工作情况都不甚了了,甚至于蒋廷黻竟然忘记了黎昔非的名字而称之为“小职员”,这样的结果不正是胡适刻意掩蔽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关系所造成的吗?
其次,胡适以为既然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关系一直不为世人所关注,那么顺水推舟、因利成便自然也就成为他无二的选择。素以名誉为先的胡适,为了维护自己的盛名和维持“既成事实”,也必然选择继续隐瞒下去,而且当时的历史形势也非常有利于胡适继续隐瞒和掩蔽历史真相。20世纪50~70年代海峡两岸人员和信息方面的交流几乎完全断绝,当时大陆地区胡适正作为“反动文人”的代表和骨干而受到广泛、深入、持续的揭批,无论《独立评论》还是胡适的著作,都不可能公开流通,这就为胡适继续隐瞒、掩蔽黎昔非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再从胡适的立场来说,此前他已经将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关系掩蔽了二十多年,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功,已然令世人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了。即便是到了现在,不少研究者包括胡适和《独立评论》问题研究专家在内,仍然深深地感觉到,有关黎昔非的历史资料还是太少了,关于黎昔非在“在《独立评论》的工作和事迹,仍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记载。”[18]78何以然?窃意胡适长期隐瞒和掩蔽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关系,应当是造成这一状况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三,篡改和伪造《独立评论》历史,是胡适“为我主义”人生观的必然逻辑。胡适曾经极力批判“野心的投机主义”,并将之视为“‘少年中国’的仇敌”之一,他批评这种人“虽不退缩,但为完全自己的私利起见,所以他们不惜利用他人,作他们自己的器具,不惜牺牲别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紧要关头,不惜作伪,不惜作恶……”[19]562然则,胡适所批判的这种“野心的投机主义”者,恰恰是他本人的自我写照。“不惜利用他人,作他们自己的器具”“不惜牺牲别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来满足自己的野心”,用来表述胡适对待黎昔非的态度和行为,可谓贴切之极。胡适还曾经公开主张:“‘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20]486况诸胡适一生,“为我主义”可谓其终身的行动指南。在胡适心中,只有他所做的事情才是为“公家”的,只有他的学术研究才是为国家社会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因此,胡适从来都不愿意因事务性工作而影响自己的学术研究,把所有那些与学术研究无关的事务性工作交由别人去做。如果他担任不符合自己愿望的工作,则“不能不说是国家社会的一大损失,故有所不忍,亦有所不敢。”[3]1125胡适还曾说过:“学术的工作有‘为人’与‘为己’两方面”,并引王安石《杨墨》说:“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3]903胡适的以上说法有其正确的一面,学术成果最终当然是要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但是胡适在这里却偷梁换柱,将学术研究工作所包含的社会公益性当成他“为我主义”的护身符,并以此作为其损人利己的挡箭牌和剥夺他人学术研究权利的遁词。胡适经常洋洋自得于当年办理《独立评论》时的“无为政治”,然究其实质,胡适不过是把影响他本人学术研究的事情转嫁给了别人,至于别人是否也需要这种“为国家社会”而进行学术研究的权利,胡适向来都是漠不关心的。因此,胡适为一己之私,而不惜牺牲黎昔非的学术研究和人生前途,正是其“为我主义”的必然逻辑。
第四,篡改和伪造《独立评论》历史,是胡适实用主义思想在历史书写上的运用和必然。综观胡适一生,可谓实用主义的忠诚践行者,表现在他篡改和伪造《独立评论》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几幅截然不同的场景:一是胡适在日记、书信等文字中,对于黎昔非及其在《独立评论》中的作用和贡献,极尽隐瞒掩蔽之能事,企图将黎昔非从《独立评论》中完全抹除;二是胡适又利用日记、书信等文字,极力宣扬和突出他本人在《独立评论》中的作用,企图贪天功而归诸己;三是胡适还利用日记、书信等文字顺带表彰一下“朋友”或“兄弟”,让他们也感受到雨露的“润泽”,而对章希吕的再三褒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对于胡适的“提携栽培”之情,章希吕也是投桃报李,看到胡适在日记、书信中表扬自己,章希吕也依样画葫芦,在日记中高调颂扬胡适。就这样,通过相互之间的歌颂表彰,章希吕居然也成为了坊间“名人”,以至于有些胡适问题的研究者谈起他来,竟然也是口若悬河。众所周知,作为一种记录个人心路历程的私密性文字,日记通常情况下是秘不示人的,因为写日记的初衷只是为了记述个人的日常行事或思想感悟,这样的日记,里面才可能讲真话。如果一个人写日记,主要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看,而是想着让别人看,甚至是为了将来能够公开发表,那就不大会讲真话。胡适一生写了大量的日记和信件,其实是怀有明确动机的,那就是为了给别人看,为了将来能够发表,例如他在撰写《丁文江的传记》时,就曾“把我的日记细细翻查一遍”,便可证明这一点。这就是说,胡适写日记、信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将来某一天树碑立传能够用到,胡适毕生都在为此而布局谋划。
经过胡适的精心伪造,以及胡、章等人在日记、书信中的彼此唱和,《独立评论》的历史被彻底改写了,此后世人言及《独立评论》,胡适之外的最大功臣便非章希吕莫属,至于《独立评论》的实际经理人和真正的功臣黎昔非,则被他们完全掩蔽而不为人知,黎昔非所辛劳操持的一切事务,全部被移花接木而变成了章希吕的功劳。于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出版时间长、发行量大、影响力甚巨的《独立评论》,就这样由胡适等几个撰稿人写上几篇文章,再加上一两个住在其家中的朋友随意帮忙“校对”一下,就坚持下来了——这就是胡适等人所“装扮”“涂抹”出来的《独立评论》的历史!长期以来又由于某些学者迷信胡适的权威,特别是将胡适的日记和信件等文字视为“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因而这个被严重歪曲了的《独立评论》的历史,竟变成了“信史”和“正史”。
中国素以悠久的史学传统独步于世,其中“直书”与“曲笔”的矛盾争执乃是贯穿古今的主线之一,“史之不直,代有其书”[21〗卷7,197“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21〗卷7,196《魏书》的作者魏收明目张胆地借修史以逞其好恶,“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他曾经“得阳休之助,因谢休之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22〗卷37,488故其书曾被斥为“秽史”。胡适篡改和伪造《独立评论》历史的行为,与魏收等并无二致。
三、历史的审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黎昔非,胡适一方面利用自己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之职将一名研究生转变为自己的雇佣,控制长达五年有余,不但导致北京大学无端失去了一名研究生,而且也剥夺了黎昔非的研究生身份,严重影响了他的一生;另一方面胡适又将黎昔非付出五年有余的黄金岁月而为《独立评论》做出的巨大付出和贡献也予以抹煞,篡改和伪造《独立评论》历史,独吞《独立评论》之功,将黎昔非彻底排除于《独立评论》历史之外。
联系当前正在进行的高校及学术领域乱象与腐败的治理工作,“教师随意役使学生为自己服务”一条赫然列入其中,更不必说役使在读研究生为自己服务长达五年有余而令其丧失研究生学业,沦为社会上的“待业”人员这么严重的案例了。如果今天发生像当年胡适那样以院长、系主任身份而剥夺其管辖之下的研究生学业,导致该校莫名其妙地缺失了在籍学生那样的事件,相信一定会成为网上热点而引起上级部门的关注,进而派遣巡视组进驻该校,成立专项调查组进行查处,查实之后将其涉罪问题移送司法部门绳之以法。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案件已经过去80余年,超过了法律追究的时限,更不能因为胡适是名人而不是普通民众,就可以不必追究其罪责。
黎昔非之功被抹煞的冤案公之于世的十几年来,学术界人士已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胡适戕害黎昔非和篡改《独立评论》历史的罪行进行了谴责和清算。
有的学者指出:“《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揭示了《独立评论》后面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从而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和值得探究的问题,其中胡适究竟何如人?就是需重新探讨的问题之一。”[23]63有的学者指出:黎昔非“与胡适的关系又让我们看到胡适性格的另一面。”“从1933年开始黎昔非多次提出卸任,要求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业当中去,都遭到胡适的拒绝。迫于压力,黎昔非提了几次之后,终于不敢再提了,以致放弃自己的研究生学业。黎昔非为《独立评论》付出了沉重代价,这对于他是非常不公的!如果相比较于胡适的另两个学生,这种不公就让人感到不解而终于心里也打抱不平了。”[24]48-49学术界的共识是:“黎昔非为《独立评论》而牺牲了自己的毕生。”[25]140学者纷纷挺身而出抱打不平,发出对于胡适“如此摧残人才、扼杀人才的行径是不能不受到谴责的”[26]101呼喊。
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近代史专家,安徽大学教授王天根在深入研究黎昔非案件之后,指出:“黎昔非一事,不说是千古奇冤,恐怕也是百年不遇的了。为数不多的北大研究生黎昔非被埋没,反映了中国近代自由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借助《独立评论》而声誉鹊起的背后,有部分知识分子在默默无闻中作奉献,甚至是牺牲。”“黎昔非在社会阶层中地位的变动及事业追求中进取与被迫撤退,折射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及胡适、蒋廷黻等社会精英成功在某种程度建构在榨取那些(由普通民众走向社会中间阶层)知识分子艰辛的劳作,甚至是被迫默默无闻的‘奉献’基础上的。”王天根进而认为,黎昔非案件“为全面、深刻考察处在动荡的社会嬗变历程中的近代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群像成功的背后不被人注意的(甚至有意被掩盖的)丑恶的一面提供独特视角。”[27]87-91虽然作者是以学者惯有的文风而进行委婉的表述,但所指出的问题的实质却是尖锐而明确的:一则指出将黎昔非被迫“转变”身份的操刀手就是胡适,在胡适的亲自操作下,黎昔非被剥夺了研究生学业而转变了身份,付出了人生最宝贵的7年黄金岁月,却仍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担任中学教师。二则指出《独立评论》的成功是建立在胡适等人对黎昔非的压榨和掠夺基础上的。三则指出胡适等人采取“丑恶的”手段欺压黎昔非,在压榨和掠夺黎昔非的同时却“有意掩盖”黎昔非。王天根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术界的普遍看法。
现在,经过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胡适戕害黎昔非及其篡改和伪造《独立评论》历史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清算胡适这一罪行的条件已经具备。兹作出严肃的历史审判:
第一,胡适对黎昔非的戕害应当加以清算。具体包括如下二个方面:一是胡适将通过考试,被北京大学正式录取并正式注册的在读研究生控制、禁锢五年有余,导致北京大学无端丧失一名研究生,属于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二是胡适剥夺黎昔非北京大学研究生学业的机会,擅自将其转变为自己的雇佣,并对其进行长期役使,对于黎昔非造成了严重的、长远的伤害,胡适必须承担这一罪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第二,推倒胡适-蒋廷黻等人所篡改、伪造的《独立评论》历史,还《独立评论》历史的本来面目。具体包括如下三点:一是《独立评论》是主笔胡适与经理人黎昔非合作的产物,黎昔非享有对《独立评论》的合法权利和地位,应当予以恢复并得到尊重,胡适独占《独立评论》权利地位的假象应当予以推倒。黎昔非对于《独立评论》所享有的权利地位,不是仅仅把胡适以章希吕忽悠世人所造成的误解予以纠正和消除,而是还黎昔非对于《独立评论》所应享有的全部的、完整的权利和地位。二是陈晋祺作为《独立评论》的正式职员,其合法权利也应当予以恢复并得到尊重。三是章希吕并非《独立评论》正式员工,而是胡适的私人雇佣,他在《独立评论》后期代替胡适进行的“末校”工作,属于胡适作为《独立评论》主笔的职责范围,不能视为《独立评论》正式员工,故不享有对于《独立评论》的权利。
世人将继续以历史的判决,以检验胡适生前关于《独立评论》的种种相关言行以及后世关于胡适相关问题评判的是非曲直,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世人以天理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