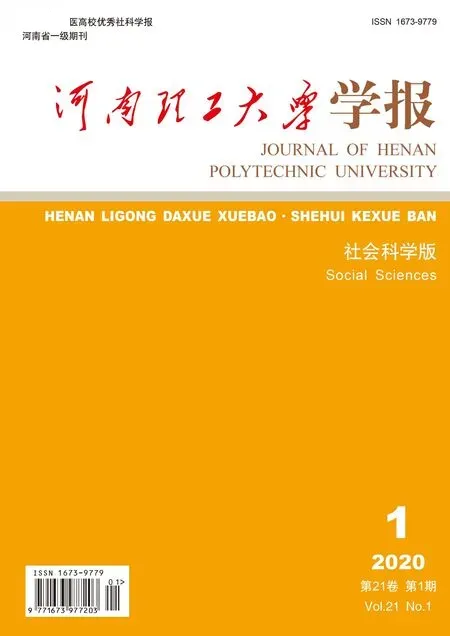分裂与聚合
——从《金色笔记》看五十年代英美左翼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
张 慧,陈义海
(1.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2.盐城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0)
作为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的代表作,《金色笔记》自问世之日便备受关注。我国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针对其迷宫般的结构、包罗万象的主题、形式与主题的融合而进行了叙事、结构、主题等方面的研究。在主题研究这一部分,学界的研究重心又多集中在女性意识、精神心理、宗教哲学、两性关系、作家的多元文化背景与文本主体之间的深层关联这几点,但真正关注左翼知识分子及其生存境遇的并不多见。本文以《金色笔记》中的三位左翼知识分子——女作家安娜·沃尔夫、流亡政客索尔·格林和青年学生汤姆·波特曼为研究对象,通过剖析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挣扎、迷惘和矛盾,揭示特定时局下特定群体的生存挑战以及他们为走出困境所做的艰苦努力,同时展现20世纪中叶复杂而独特的社会时局,以期为客观认识那个特殊年代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对“左翼知识分子”的理解建立在对“左翼”理解的基础之上。关于“左翼”,尽管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总归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如其与“右翼”相对立,通常指代那些支持社会变革、寻求社会公平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词典》则将其定义为:对承认、宣扬和信奉左派思想或纲领的个人、团体或政党的一般称呼。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政治层面的“左翼”虽可追溯至200多年前的大革命时期①(1)①在大革命胜利后召开的一次国民会议中,第一、二等级的代表,即国王的拥护者坐在了会议主席的右边,代表第三等级的革命派则坐在了会议主席的左边。两派争锋相对、互不相让。此后,这种左与右对立的政治意义及称谓传遍各国并沿用至今,“左”与“右”因而逐步成为政治派系分野的标志。,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左翼古已有之”[1]。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无一不是左翼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左翼内部分枝众多、各有侧重,同一个体完全可能受到不同左翼派别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完全可能随时间流逝而发生变化。因此,由“左翼”衍生而来的“左翼知识分子”,首先,是对社会变革报以支持态度的知识分子的一般性称谓,并不一定与具体的政治履历挂钩。有些左翼知识分子既未真正涉足左翼政治,又并非现实意义的共产党员。其次,“左翼知识分子”是对那些在整体上“承认、宣扬和信奉左派思想或纲领”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阶段性称谓,曾经的左翼知识分子并非永远的左翼知识分子。从这一层面讲,作品中的安娜、索尔和汤姆都属于左翼知识分子这一范畴。
一、安娜:分裂—聚合的自由女性
主人公安娜·沃尔夫是一位独自抚养女儿的单身女性,也是一名小有成就的自由作家,供职于伦敦的一家二流杂志,因一部畅销作品的丰厚稿酬安然度日。但其生活并非像表面那般平静:安娜渴望爱情但遭无情抛弃,身为作家却患上写作障碍症,追寻完美但却日趋分裂,甚至一度想到自杀。种种不安源自她的精神危机,而精神危机则源自她“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幻灭”[2]。
安娜的左翼历程相对复杂。早在20世纪30年代,她滞留中非时期就加入了当地的左翼团体,但因殖民身份而遭受排挤。到了50年代,回国定居的她则将目光投向了英国左翼政党,四年后又黯然退党。退党以后,她依旧密切关注左翼动向,终因悲剧现实再次离开。历经三进三出,安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彻底放弃左翼信仰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濒临精神崩溃。她坦言,“我就是这么个自相矛盾的人物”[3]343“我觉得我离疯并不远了”[3]47“我,安娜,正走向崩溃”[3]470。
党内生活是引发安娜精神困境的导火索。安娜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正式入党,目的是纾解因美苏冷战、朝鲜战争等产生惶惑不安的心境、借助理性和谐的党内气氛找回内心的平静统一。然而,党内生活非但没能平复她的精神紧张,反而使其逐步走向分裂。这是因为加入英共不久,她很快就察觉到其中的诸多弊病,如官僚做派严重、不作为之风盛行、民主机制徒有其表、党员间普遍缺失信任等等。碍于正式党员的身份,安娜由此陷入一种奇怪处境:出于捍卫左翼事业的共同心理,她迫使自己咽下心中的疑惑,并选择像其他党员一样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由于始终怀抱赤子之心,她无法说服自己忽略英共内部显而易见的缺陷并继续若无其事地装傻充愣。就这样,进退维谷的她表现出了鲜明的矛盾对立性特征。比如,虽对英共运行机制和僵化现状嗤之以鼻,还是以“我仍在党内”为由竭力维护该组织在党外人士面前的正面形象;就算对斯大林暴政有所耳闻,但在确凿证据面前依旧抑制不住为其开脱辩解的冲动;一方面乐此不疲地为卢森堡夫妇②(2)②卢森堡夫妇,即美国犹太裔共产党员朱利叶斯·卢森堡与埃塞尔·卢森堡。他们于1951年3月6日在纽约被判处死刑,罪名是向苏联泄露原子弹的制造机密。此举在国际上引发广泛抗议浪潮,尽管萨特、爱因斯坦等人皆为卢森堡夫妇请命,但二人仍在1953年被处决于纽约“辛辛监狱”,此案当年轰动一时。积极请愿,另一方面却对布拉格审判中的受害者无动于衷;入党不久就已经萌生脱党之意,却在党内蹉跎至4年后才正式离开;明明在1954年就已经正式退党,但在1955年重又回到“充满激情、目标明确”[3]440的左翼团体。如果说4年的党内生活初步毁灭了安娜的左翼梦想并促使她下决心离开英国共产党,那么真正摧毁安娜生活根基并将她推向崩溃深渊的则是1956年接连爆发的两场左翼地震。
其一是苏共二十大。确切地讲,是赫鲁晓夫在会上(1956年2月24日晚至25日凌晨)作出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篇直斥斯大林本人及其诸多暴行①(3)①秘密报告揭开了许多斯大林的政治污点,包括开展大清洗运动和反犹运动、制造医生阴谋案以及大肆屠戮老一辈布尔什维克党人等等。且只在有限范围内②(4)②一开始,“秘密报告”的知情者仅限于与会的苏共中央委员和波匈两国的党组织代表,同时报告现场严禁记录。但纸包不住火,报告的副本很快就被他国获悉并在欧美各国广泛传阅。传阅的报告中,斯大林转瞬由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领袖成了不亚于希特勒的独裁者和杀人犯。对安娜这样视斯大林及苏联神话为偶像的左翼知识分子而言,这份报告无异于打在后脑上的一记闷棍。因为尽管早已获悉由斯大林政策造成的部分错误③(5)③早在1952年,安娜通过同居恋人迈克尔得知他的三个朋友因苏联方面在东欧各国发起的新一轮大清洗运动而在布拉格被绞死。此外,在1954年正式退党前,安娜通过摩莉得知那些据说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丛林派队友其实已被强制关押了三年。,但由于斯大林本人早已成为社会主义无限潜质的毫无疑问的象征,在这场政治地震波及英国之前,就算偶有关于斯大林的负面消息,安娜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塑造他的形象”[3]162,并继续将其视作指路明灯。“然而攻击却来自莫斯科本身。这个事件无法不叫人正眼看待,却又另忠贞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不知应如何自处”[4]275。就这样,安娜精神世界的“承重结构”[5]瞬间倒塌。一时间,她变得手足无措,不知应该继续支持斯大林还是索性转投赫鲁晓夫。
其二是英共1956年危机。危机缘起英共未能有效处理苏共二十大在党内掀起的道德和政治上的危机。因为直至当年6月10日,英国《观察者》《曼彻斯特卫报》全文刊发“秘密报告”,众多基层党员业已“怀着十分痛苦的心情,不得不承认有关苏联的真相”[3]475同时强烈要求英共当局“站出来承认并作出解释”[3]474,英共高层非但没有及时反思二十大暴露出来的现实问题,反而忽略甚至刻意阻挠围绕上述问题的公开讨论并试图用“不惜一切代价,和苏联团结一致”[3]474的老套说辞敷衍了事。这些不作为之举再加上来自英共执行委员会的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的公开声明最终引发大规模退党热潮,并使1956年成为英共“自建党以来所面临最严重和最危急的时刻”[4]276,不仅损失了诸如“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④(6)④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是英共全国文化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小组成员大都身兼历史学家和共产党员的双重身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展历史研究。在苏共二十大之前,历史学家小组主要致力于调和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矛盾;1956年后,该组织则成为最早最积极要求英共就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的机构。等“相当数量且有影响力”[6]的左翼党员,而且彻底浇灭了安娜这类虽已退党但仍对英共抱有希望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丝热情。最后,安娜与左翼政治走向决裂。
离开左翼对安娜是一个相当痛苦的体验,在政治上彻底沦为无家可归者的她继而开始了一段异常艰难的自囚生活。那段时间,她意志消沉、极少出门、常常忘记吃饭、睡得很少、噩梦频频、逐步丧失时间感并做出种种让人费解之举,比如大量阅读、裁剪新闻、满墙钉简报,不仅同时浏览多种报纸期刊,而且在公寓卧室的“四面墙上,凡她能够得到的地方,全钉满了剪报”[3]642。此外,安娜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那些像自己一样在“信仰的起伏波折中受到伤害”[7]的人,濒临崩溃的她因得以反观自我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如若继续自囚自闭,那她本人也将成为战战兢兢、精明冷漠、漂泊无依的空心人。为避免悲剧重演,她决心走出狭小公寓、回归日常生活。
事实上,“爱”“善”“自由”才是安娜走近左翼的真正原因。虽曾以赤子之心追随左翼,但当其意识到英共已积重难返,而苏联则逐步偏离社会主义本质且愈发鲜明地表现出霸权主义和寡头政治倾向的时候,安娜最终与之划清界限、重拾自由知识分子的人道立场。最后,她不仅凭借顽强意志走完分裂—聚合的道路,而且自愿成为婚姻福利中心的咨询师兼少年犯教师,期待能够用实际行动为社会带来一些实际的改变。
二、索尔:逃离—回归的流亡政客
索尔·格林是流亡英国的美国共产党员。同为左翼党员,他与安娜间的差别可谓泾渭分明:前者如履薄冰,鲜少提及自己在祖国的不幸过往;后者随性坦荡,从不避讳自己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这种反差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英国相对宽松的政治格局和美国谈共色变的整体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得以窥视20世纪50年代以麦卡锡主义为首的反共大潮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
“麦卡锡主义”缘起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一般而言,狭义的“麦卡锡主义”指在1950—1954年间,他主导并发起的一系列针对共产党员的指控、调查、逮捕活动以及由此引发的深刻社会影响;广义则指一种20世纪中期的政治态度,以及反对那些被认定为具有颠覆性质的因素为目标,使用包括人身攻击在内的各种手段,尤其是在未对提出的指控进行证实的情况下,四处散布任意做出的判断和结论(《韦氏词典》)。事实上,麦卡锡主义及由其引发的后续悲剧其实是“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脱轨’情况”[8]67,它“不再只是麦卡锡一个人的疯狂表演,而是整个美国社会的挣扎”[8]73,其中有着鲜明的时代因素和深厚的社会基础。然而,在这场全美范围的猎巫运动中,“美国的左翼力量受到空前的打击,原本就处于弱势的美共更是受到致命打击”[9]。与此同时,反共呼声一路高涨,最终波及文化、教育、国防在内的其他领域。在人人自危的大环境中,多数左翼知识分子为免受“颠覆分子”的指控纷纷倒戈,另有坚持左翼立场的少数人则受官方驱逐而流亡他国。
毫无疑问,索尔就属于坚持立场的少数派。他曾以戏谑态度对安娜提及自己因“‘过早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随后因自己“是赤色分子而在好莱坞被列入了黑名单”[3] 555、最终因拒绝与左翼政治划清界限而被好莱坞辞退①(7)①受反共风波影响,众多演员、编剧、导演继“好莱坞十人”之后被列入黑名单。此外,美国电影业主要制片商和企业主在1947年11月24日联合发布“华道夫声明”(the Waldorf Statement),表示各电影公司将不再雇用任何一名共产党员或者颠覆分子。通过索尔自述,可知他曾因此遭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人生经历。与那些集体右转、如今安稳度日的昔日队友相比,即使在英国过着“挣钱只够糊口,只能不时审慎地小口抿点儿上等的苏格兰威士忌”[3]617的困窘生活,索尔的左翼热情依旧不减,不仅对社会主义勾画的“美丽的难以实施的行动计划”[3]629坚信不疑,而且牢记自己“唤醒他们(人民),振奋他们,推动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3]618的政治使命,甚至因未能去古巴投奔卡斯特罗而感到惋惜。然而,即使政治立场坚定如索尔,终究没能躲过麦卡锡主义制造的恐怖的侵袭。
侵袭一开始得以直接呈现。他因左翼立场而遭国内右翼势力驱逐出境,成为“游荡在欧洲的美国人”[3]539。以致他即使身处相对安全的环境,他仍习惯性地以高度警觉的状态面对周围环境,甚至“在酣睡中,也是一副防卫的姿势”[3]557。为了避免在异国卷入是非,他自觉地成了冷漠自怜又毫无感情的人。虽游走于欧洲各国,但不相信任何人、不愿付出自我感情、更无法感知他人关怀,最终物化成了“沉甸甸、冷冰冰的一团”[3]558,散发出一阵阵彻骨寒气。
侵袭最终得以间接显现。具体而言,呈现为索尔身上的多重人格性。或如安娜所言,索尔常“表现得像几个不同的人一样”[3]568。比如,他有时是对人民一片赤诚、以拯救劳苦大众为己任、无私利他的模范党员;有时则是以强硬姿态表达“我,我,我”的绝对中心主义者;有时是拒绝向右翼势力妥协、拥有虔敬社会主义信仰的工人阶级少年;有时则是敏感多疑、惯于施展欺骗伎俩的谎话精,既可以是将安娜从崩溃边缘解救出来、了解安娜的温柔多情的美国房客,又可以是周旋于各色女性之间、以伤害女性为乐事的浪荡公子,前一秒是明哲保身、工于心计的利己主义者,转瞬间就成了不畏艰险、心思单纯的理想主义政客。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相差甚远、甚至趋于对立的身份却在索尔身上和谐共生。更让人意外的是,索尔既可身兼多重身份又可实现不同角色的瞬时转换,以致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安娜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同时应付“五六个不同的人”[3]567。
事实上,多重人格性一方面是索尔分裂内心的无意识流露,更是他应对50年代美国国内指鹿为马、黑白颠倒社会环境的自我保护机制,是如丛林动物保护色一样的存在。可以说,索尔是一位对社会主义怀有深厚感情却又被20世纪50年代反共浪潮灼伤的左翼青年。逃离美国后,索尔逐渐成为冷漠善变、具有多重人格气质的流亡政客。幸运的是,相似际遇促使他逐步放下对安娜的戒心并与之倾心相交。借助安娜客观冷静的剖析,他最终明白以往聚集在街角畅谈理想的日子已成为历史,自怨自艾、伤害他人或自我放逐都将无济于事,唯有继续战斗才有机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改变。至此,索尔这位逃离美国的左翼知识分子走完了自己的回归之路。
三、汤姆:虚无—理性的迷途少年
汤姆·波特曼是安娜好友的儿子。母亲摩莉活泼好动、积极乐观,是一名精力旺盛的舞台剧演员;父亲理查精明世故、擅于理财,是一名颇有权势的商人。夫妇关系剑拔弩张,终至不欢而散。随后,父亲再婚,汤姆跟随母亲生活。与安娜等人最大的不同在于,汤姆从小①(8)①根据文本线索,1958年,汤姆举枪自尽时年仅21岁。由此可知,汤姆大致在1937年前后出生。安娜在195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那么摩莉入党的时间必定更早。据此推算,汤姆接触到左翼知识分子的年龄不会晚于13岁。关于左翼对汤姆影响之深,其父理查曾戏言汤姆其实“就是在光荣的、美好的、自由的苏维埃祖国长大的”。就与左翼知识分子一起生活,他是在左翼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
母亲最早在汤姆心中埋下左翼的种子。摩莉厌恶英国呆板僵化的社会氛围,总觉得生活中少了一点乐趣。一次偶然的机会,摩莉加入英国党组织。成为党员后,她总是忙进忙出地组织活动、参加会议或安排展览,甚至因“在空余时间里不去组织点什么事”[3]52而感到自责。耳濡目染,汤姆逐渐形成自己的左翼信仰,像母亲一样同父亲理查保持距离:不仅拒绝他提供的工作,而且否定其“牛津”或“伊顿”式的资产阶级晋升道路,打算继续无所事事地过上一段时间。如果时局安稳,汤姆或许会如摩莉那样加入英共,成为正式党员。然而,一个小插曲——1954年,得知英共为无条件支持苏共霸权,而导致左翼队友蒙冤入狱3年的真相后,摩莉愤而退党——使上述设想成为泡影。
母亲退党是汤姆信仰的转折点。对汤姆这样一个未经世事的少年而言,摩莉在英共的一举一动都极富示范性,他也从未隐藏这种来自母亲的深刻影响。那么,当摩莉一反常态地骤然退党并不遗余力地嘲弄英共的尴尬处境时,汤姆内心必定疑窦丛生,他由此开始逡巡不决。相应地,政治失利加上生活不顺,遂使得摩莉作为榜样的人设彻底崩坍,不再视母亲为人生导师的汤姆,转而重新审视自己的双亲:父亲理查庸俗势利,奉行利益至上原则,对左翼政治百般厌恶;母亲摩莉天真理想并关心时事,反对唯利是图的资本体制,富有人道主义情怀。然而,保守老派的父亲却成了金融大亨,在资本主义世界风生水起;激进多变的母亲则如跳来跳出的女人,在现实社会屡屡受挫。两者对比,汤姆内心的天平开始发生倾斜,以往占据绝对优势的左翼不再被他当作唯一出路。就这样,“左”“右”之争由最初的态势明朗走向不确定并演变成双方的持续拉锯,汤姆置身其中但难以取舍,甚至羡慕起只有一条出路可走的牛奶工的儿子②(9)②汤姆嫉妒牛奶工儿子莱奇·盖茨的不利条件。因为他要么像父亲那样送一辈子牛奶,要么努力获得奖学金、进入知名大学、成为中产阶级。如汤姆所言,“他(指莱奇)根本没有任何选择”。。正因此,他一出场就显示出明显的“哈姆雷特”气质,耽于思考、郁郁寡欢、无所适从。而这一状态刚好折射出了汤姆分裂的内心世界。
首先,分裂体现在对双亲的矛盾态度上。对于母亲,汤姆既敬重她优越的精神品格,又忍不住讽刺其糟糕的现实生活;既感激她的养育之恩,又不满因她而来的不安定因素。他曾明确表示:“我的心智是分裂的——这都是你(指安娜)和我母亲的影响造成的。”[3] 258对于父亲,汤姆明知他是一个自以为是、行为不检的自大狂,但依旧不忘在安娜和母亲那里为其争取更多的尊重;虽然打心眼鄙视他那套世故的处世哲学,但仍禁不住钦佩他在商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功,甚至因自己“未能由父亲抚养成人而感遗憾”[3]258。
其次,分裂还体现在对左翼政治的矛盾态度上。即使洞悉同龄人大多是在对共产主义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偶然闯入左翼阵营的事实,但还是与他们一道跑来跑去地贴标语、呼口号;就算见证了母亲和安娜因左翼政治心力交瘁,仍未停下阅读报刊、议论时局、幻想未来的脚步;明知自己不可能真正有助于非洲民族事务的解决,但在行动不便的情况下坚持参加关于非洲某国独立的政治会议,加入声援该国的游行示威活动。
最后,分裂给汤姆带来了重重困扰,他终因不堪思想重负而举枪自尽。虽侥幸活命,却失去视力。失明以后,汤姆与左翼渡过了短暂的蜜月期,先是与继母一道没日没夜地讨论左翼政局,而后想方设法地为黑人和穷人争取利益,狂热程度远超退党前的摩莉。事后,汤姆坦言这样做是为了帮助马莉恩消除婚姻危机引发的负面情绪,为了使她“关心自身以外的事”[3] 394。其实,汤姆更是为了自救,为了结束自己的精神困境,所以,他外出当天,身为盲人却没有带上标志其残障身份的白手杖。在被集会人群告知“往前走”的时候,他却站在原地不动。或许可作此设想,汤姆有意促成自己被捕的局面,进而亲手将自己从对左翼政治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中拉出来,他在拯救马莉恩的同时,同时也拯救了自己。
简言之,作为在左翼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汤姆身上既有左翼青年的共性特征又有其个性一面。共性在于他仰慕左翼但却因残酷现实而最终止步,个性在于他得以近距离同时接触到以母亲和父亲为代表的“左”和“右”的思潮。独特的成长背景使得他“知道什么东西是我不想要的,只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3] 258,因而在母亲退党后长期徘徊于“左”与“右”之间。这一方面加剧了汤姆的分裂进程,也推进了他的重生。尤其是,失明后与左翼团体“擦边球”式的短暂接触和50年代中后期母亲摩莉失败的政治体验,汤姆终于领悟到英国左翼政治难以为继的可悲现实,随后做出了更加理性实际的人生选择——进入家族企业、接管父亲事业。
四、结 语
综上可知,20世纪50年代,夹杂着左翼内讧和“左”“右”之争的扰攘时局,对英美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深刻且多维的,不仅扰乱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打破了他们的精神宁静,使得以安娜、索尔、汤姆为代表的英美左翼知识分子普遍承受着矛盾、迷惘和分裂的精神创伤。他们驻足在信仰的十字路口,起初因不知该往何处去而几近崩溃,继而在互为观照的过程中完成痛苦的“精神的超越与突围”[10],最终在复归完整之际做出了迥异的人生选择,或如安娜那样悻悻离场、重拾人道主义的自由立场,或如索尔那样不忘初心、坚守社会主义阵线,抑或如汤姆那样左右冲突、拼搏无效后走向资本主义的现行机制。
也因此,多丽丝·莱辛从正反两面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外部的混乱无序,从而引发内部的矛盾分裂以及内部的四分五裂如何折射外部的动荡不安,而这一特征恰巧标识了《金色笔记》的价值所在,首先,真实具现了20世纪50年代诡谲政局施于英美左翼知识分子的集体性精神创伤以及他们重拾生活信心——由“分裂”至“聚合”——的艰苦历程;其次,完整勾勒出20世纪中叶“整个世界的道德风貌和政治气候”[11]。与此同时,它使得《金色笔记》达到了历史小说——“它应该在过去的历史中辨认出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的成因,也应该描绘出这些成因缓慢变化发展并产生其结果的过程”[12]的高度,散发出一股深厚的人文关怀、责任意识和历史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