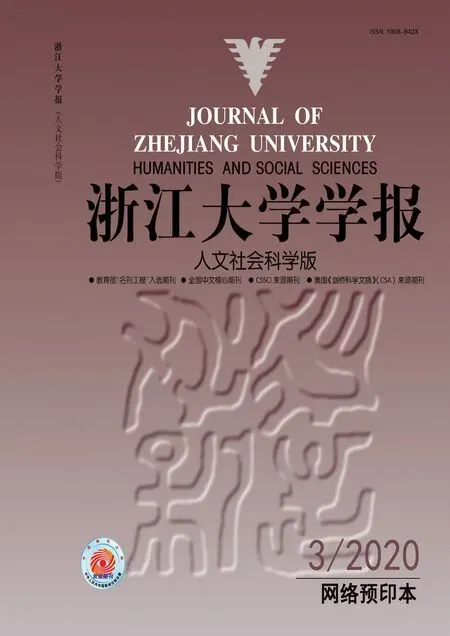京味文学英译研究的多维文化再现
吴庆军
(外交学院 英语系, 北京100037)
一、 京味文学的发展及其英译研究管窥
京味文学是以北京的百姓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具有显著的地方文学和城市文学特征。京味文学主要包括小说、话剧和诗歌等,随着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京味文学还涉及电视剧、电影以及新媒体文学等。京味文学特征集中体现在“京城”和“京事”上,可以概括为“地、事、风、话、性”[1]10,即运用北京方言叙事,展现北京的市井生活和风土人情。京味文学萌芽于清末民初的京味小说,其代表人物有蔡友梅、尹箴明等,早期的京味小说如蔡友梅的《连环套》、徐剑胆的《新黄粱梦》以及尹箴明的《西太后外传》等,主要叙述清末民初皇城根儿下的世俗百姓故事。随着北京城白话报纸的传播,早期京味小说的读者群不断扩大[2]253-256。但早期的京味小说由于主题较为陈旧、缺乏五四运动以来的社会批判精神,真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见,对现当代文坛的影响力不大,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但其显著的北京方言特征为京味文学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语言基础,并培养了早期的读者群。
京味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至40年代形成了以老舍为代表的第一代京味文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阅读白话小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京味文学的发展。第一代京味文学主要叙述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下层平民的生活,重点书写胡同视角中的城市、风俗传承中的京味文化,“在语言、形象和风格等方面都奠定了现代京味文学的初创形态”[1]21。老舍作为京味文学的先驱,其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及话剧《茶馆》等具有现代民族意识和批判意识,人物事件更具平民性和普遍性,展现出小人物的生存现状。第一代京味文学沿承了早期京味小说的京味语言,故事内容更贴近市井生活,思想内容上更具现代意识。这一时期,京味文学作为一个流派日臻成熟。
20世纪中叶至80年代中期,京味文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坛重要的文学流派,此期间逐渐形成了以林斤澜、汪曾祺、邓友梅、韩少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京味文学。这一时期的京味文学主要讲述发生在京城街道及胡同中的百姓故事,代表作有邓友梅的《那五》和汪曾祺的《饭后的故事》等。第二代京味文学重点展现了当代京城小人物的“处世哲学”。
第三代京味文学主要展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北京人的“精气神儿”。这一时期的作品不仅仅停留在小说和话剧的样态,而且出现了电视剧、电影以及网络文学等不同表现形式。在内容上,还出现了大院文化、办公室文化以及具有后现代文化特点的京味文学新样态。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有王朔、王小波和刘震云等,代表作有王朔的《顽主》和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90年代后还涌现出一批反映北京老百姓生活的京味影视剧,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这是京味文学的新发展。
京味文学英译将以京味文化为核心的京地、京人、京事和京韵通过文学翻译呈现给西方读者,为西方了解京味文学打开了一扇窗户。京味文学英译同时成就了一批文学翻译家,如施晓菁、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等。他们的译本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素材,而且丰富了文学翻译研究方法及翻译策略。现阶段京味文学的英译研究零散且单薄,其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拓展。一方面,京味文学体裁广泛,涉及小说、话剧以及影视作品等,同时涉及多达几十位的京味文学作家。目前翻译成英文的京味文学作品已达几百部之多,但当前的京味文学英译研究主要集中于老舍及其单部作品,且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而关于第二、三代京味文学作家如邓友梅、汪曾祺、王朔、王小波和刘震云等的作品的英译研究还未见到。另一方面,目前的京味文学英译研究总体上仍处于语言和翻译策略的研究层面,深度的文化翻译研究及综合研究鲜见。截至目前,对京味文学整体流派的英译研究还未见到,更未形成综合的研究体系。
文学翻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重要的文化转向,文化学派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指出文学翻译并不是两种语言的简单转换,而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多维度转换,即“翻译研究已经开始了‘文化转向’”[3]3。文学翻译中最重要的文化就是民族文化和受众文化,这两种文化间的转换是当代翻译研究的核心内容,而这都是目前英译研究中常被忽略的方面。京味文学叙述了北京城近百年的历史和文化变迁,蕴含丰富的京味文化、城市书写和民族认同等要素,这些社会文化要素在英译本中的再现方式和再现效果是英译研究的焦点。目前京味文学英译中的受众文化、城市再现和民族认同是研究的薄弱之处,需要对其做深入的探讨。
二、 京味文学英译的受众研究
受众是翻译作品的最终接受者,赋予京味文学在英语世界中的第二次生命。受众是决定译本是否成功的关键要素,“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力在没有受众积极参与的情况下是无法想象的,文学作品只有通过受众作为媒介,才可以进入不断变化的视野”[4]19。一方面,受众的文学传统与阅读习惯不仅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也是评判译本质量的关键指标。另一方面,文体与叙事契合研究是超越文字表层的话语分析,是文学翻译受众研究的深层探究,应成为京味文学英译受众研究的核心。
(一) 受众的文学传统研究
受众的文学传统是文学翻译的重要文化契合要素,也是京味文学英译研究的重要评价指标。英语文化中的文学传统主要包括英语小说的创作传统和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是读者期待视野的核心要素。如果译者忽视了这两点,文学翻译就会无的放矢,译本仅仅表现为语言层面的对等,而文化层面的脱节致使英语读者“见木不见林”,造成文化误读。在文学翻译中,“目标文本的读者作为翻译的受众,在翻译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5]22。译者应充分认识到受众文化的文学传统和阅读习惯的重要性,尽力将“原作中的优点完全渗透到另一种语言中,使该语言所属国家的读者能够像源语言读者一样切实、清晰地感受到原文的优点”[6]209。可见受众文化契合是文学翻译研究首先要考虑的内容,因此京味文学英译研究应关注英语小说的创作传统和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提高当代译者的受众意识。在此以小说译名为例进行分析。
京味文学的英译名作为带给英语读者的第一印象,与受众文化的契合尤为重要,译名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英语读者是否愿意继续阅读,因此作品名称翻译要遵循受众的文学传统和语言特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使译名向受众文化靠拢,避免造成文化误读。早期的英国小说受到欧洲大陆流浪汉小说的影响,作者希望展现给读者一个“真实的”故事,因此小说多以主人公、故事或事件为标题,如18世纪的《鲁滨孙漂流记》及19世纪的《匹克威克外传》等,这也形成了英语小说以主人公或故事内容为标题的传统。英国文学史上的绝大部分小说都符合这一特征,读者乐于从题目中管窥故事情节和内容。此外,在英语文学传统中,小说标题通常不会以祈使句的形式出现。即使是贝克特的后现代经典戏剧《等待戈多》,也仅仅使用动名词短语“WaitingforGodot”作为书名。
作为英语受众,读者更容易接受与英语文学传统一脉相承的译名。京味文学的译者倘若忽视受众文学传统的这一特点,译名会显得非常蹩脚,从而造成英语读者的困惑。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葛浩文译为“PleaseDon’tCallMeHuman”,采取了异化的翻译风格,更符合少数研究型受众,也可能是为了凸显原作的后现代风格,但此译名却会使普通英语读者困惑不解。如果将其译为“AmIHuman?”,则既具有后现代内涵,又符合英语受众的文学传统和阅读习惯,此译名风格类似于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骆驼祥子》不同的英译名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其中“RickshawBoy”或“Rickshaw”充分考虑并顺应了受众文化传统,没有拘泥于原作标题,符合英语小说的传统和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受众文化契合,提高了小说的吸引力。而英译名“CamelXiangzi”虽然在形式上是小说主人公名字,但这种“洋泾浜”式的英译名会让英语读者困惑不解。由此可见,译者在小说名字的翻译中,倘若忽视了受众的文学传统和阅读习惯,将无法实现“入乡随俗”,从而影响受众的阅读感受。此外,京味文学英译的受众研究可拓展小说情节、诗歌意象等要素在文化传统中的契合研究,也可拓展从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样态的差异等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
(二) 文体和叙事的话语契合研究
文体和叙事的话语契合也是受众研究的焦点。京味文学中的“京味”多体现在独特的文体和叙事中,但当前京味文学英译研究对词汇和句法在译入语的对等方面关注较多,对文体和叙事的话语契合关注较少。翻译的“唯一法则乃是任何语言都必须以受众为转移,要使其自然”[7]25。广义上的语言不仅包括词汇和句法,还包括话语层面的文体和叙事。京味文学的译本最终都要面向受众,其文体和叙事层面的“京味”是否自然顺畅地转换为英文,是京味文学英译的难点,也是京味文学英译研究的核心内容。因此,京味文学英译研究更需要重视文体和叙事中“京味”的再现效果,这既是翻译自身的需要,也是译者受众意识的体现。
文体是原文和译文中重要的话语方式。译者应首先关注原文的文体,通过词汇和句法的变化在译文中实现文体的话语契合。“文学翻译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文体翻译,因为文体传递的不仅是信息,还有作者风格。”[8]112英语的文体不同于汉语,具有受众意识的译者会充分考虑再现原文的文体特征。对受众话语方式的考量有助于译者在译本中实现话语契合,而非文字表面的词汇契合,从而本真再现“京味”,并被英语读者自然接受。在《骆驼祥子》中,刘四爷怒怼虎妞时说的“不用揣着明白的,说胡涂的”[9]127,简·詹姆斯(Jean James)译为“There is no point in beating around the bush”[10]135。译者准确理解了原文的话语方式,运用英语中的习语对应京味俗语,无论是内容还是文体风格,都做到了准确自然,译文非常贴切。这说明译者很好地把握了受众文化与京味文化的文体互文性,使受众文化的文体与京味习语自然契合,使原文文体得以顺畅再现。
京味俗语中常会带有对仗特征,比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9]130,这就要求英译研究在关注词汇和句法层面对等的同时,必须注重对仗在译文中的体现,实现文体对等。这里通过对不同译文即“a grown man should marry and a grown woman should be married”[10]137(译文一)和“a full-grown man takes a wife and a full-grown woman wants a husband — that’s only natural”[11]232(译文二)的比较,分析文体对等在京味文学英译中本真再现的意义。显然,译文一中的平行句式不仅实现了内容的对等,而且借助英语中适当的文体对等艺术再现了京味语言中的“诙谐对仗、雅俗共赏”,通过话语契合实现了“京味”本真再现。译文二虽然也运用了平行句式,但“that’s only natural”显然是画蛇添足,破坏了文体间的对等。
另一方面,译本叙事连贯的准确再现也是受众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决定了中国传统叙事同西方叙事存在一定区别,“没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作品就很难求得一个共同的‘叙事法则’”[12]1。因此,中英文学作品中的叙事差异是译者不可忽略的方面,在英译中实现叙事效果的对等成为译本成功的一个因素。这就决定了京味文学英译研究需要关注源语言文化同受众文化之间如何实现叙事连贯的对等。在叙事学视野下,一部文学作品通常由两部分组成,即故事和话语。故事指小说内容,话语指的是叙事,叙事通常包括叙述者、聚焦、视角等要素。对京味文学的叙事特征,译者需要运用英语中对应的叙事技巧进行对等处理,实现叙事效果对等。如汪曾祺在《晚饭后的故事》中采用了第三人称故事外叙述:“郭庆春只有两条路可走:当底包龙套,或是改行。郭庆春坐科学戏是在敌伪时期,到他该出科时已经是抗战胜利。”[13]20这段文字具有强烈的京味气息,体现了京味文学重要的“接地气”叙事特征,犹如一位京城平民坐在身边娓娓道来,体现了顺畅的叙事连贯。而译文“What should he do next now? Play minor roles or change his profession? There were no other alternatives.”[14]248,尽管故事内容与原文基本相同,但在这短短的三句话中,叙述者从故事外走到了故事内,然后又跳出故事,这种叙事视角的不断跳跃切断了叙事连贯性,读来更像是意识流小说。译本同后面的“Guo Qingchun had begun his apprenticeship in 1940 and finished it five years later.”[14]248在叙事人称和视角上更是无法实现连贯,显得尤为突兀。这说明译者在翻译中仅仅关注了词汇层面,却忽略了原文在译入语中的叙事连贯。在译文中,小说原本的第三人称故事外叙事转换成破碎的故事外叙述和意识流叙事的杂糅,无法实现话语契合,难以实现原文中“娓娓道来般”的京味叙事。可见,文体和叙事契合也是受众研究拓展范式的主要内容。
京味文学作为叙事作品,其所包含的两部分即故事和话语在英译本中应得到相同的本真再现,在一定程度上,话语即叙事策略及视角层面的对等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体现“京味”的重要方式。因此,京味文学翻译中的话语契合是京味叙事本真再现的重要翻译策略和手段,也是文学翻译评判的标准之一,在翻译实践中愈发重要。
(三) 受众文化与源文化的融合研究
文学翻译是受众文化与源文化的融合互动过程。英语文化的基石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伴随着英美两国称雄世界,英语文化在20世纪依然保持强劲态势,京味文学英译在长达近80年的翻译和传播过程中见证了这一文化态势。20世纪上半叶的京味文学翻译中,大部分译者特别是英语本土译者都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比如伊万·金(Evan King)和简·詹姆斯等的译本强调词汇、句法和文化层面对英语文化习惯的顺应。而一些同中国文化有着亲密接触的译者,比如施晓菁和葛浩文等的译本中,异化的翻译策略比较常见,他们会采用一些接近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这充分展现了京味文学翻译过程中受众文化与源文化间的交锋和互动。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愈加频繁,受众文化不仅影响文学翻译,对京味文学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京味文学作家曾与西方文化有过长期接触,到西方国家求学或工作的中国作家不断增多,在英语国家长期的生活和工作中,英语文化对中国作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些京味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英语文化的痕迹。老舍曾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加入基督教,并于1924年至192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汉语。由于同英语文化较长时间的“亲密接触”,老舍在此期间及回国后创作的作品中存在众多“英语化”语句。如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写道:“他几乎要承认钱少爷的摔死一车日本兵,和孙子瑞全的逃走,都是合理的举动了。”[15]69这句话严格来讲是病句,句中“的”与“和”显然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这句话如果按照汉语习惯应该是“钱少爷摔死了一车日本兵,瑞全也逃走了,他不得不承认这一切都是合理的”。老舍的这句话显然受到了英语中名词所有格的影响,即“Master Qian’s killing of Japanese soldiers”(钱少爷的摔死一车日本兵)和“Ruiquan’s escape”(瑞全的逃走)。同时也受到了英语连词“and”的影响,汉语中的“和”常常连接词语,如“我和你”“天和地”,很少连接句子,而英语中的“and”常常用来连接句子,实现句法层面的连贯。再比如,“俗气凡庸,可是能用常识杀死浪漫,和把几条被浪漫毒火烧着的生命救回”[16]75。这些在中文读者眼中非常另类的表达方式,显然是受到了英文“and”的影响。这种“英语化”语句在老舍其他众多作品中也屡见不鲜。因此,受众文化对京味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典型的文化互动过程,这一现象为受众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当代译者要逐渐适应源文化与受众文化的融合发展,翻译批评也需要在新的受众语境下调整翻译研究的思路和视角。一方面,需要译者准确把握文化融合的“度”,在文学翻译中找到源文化与受众文化结合的黄金点,既能准确表达源文化,又能使英语读者易于接受。比如,一些典型的京味词语可以应用“以中为核,以西为形”的原则来翻译,如“糖瓜”可以通过凸显中国文化中的“瓜状的糖果”作为英译的核心,同时通过英语易接受的“合成形容词+名词”的形式,译作“melon-shaped sweet”。这样既在形式上契合了英语语言特征,也在表义上顺畅地表达了文化专有项中的“京味”。
另一方面,英语语言的发展长期吸收其他语言和文化,如吸收了拉丁语、法语等,也吸收了少量的汉语外来语。在文学翻译中,对英语中汉语外来语的接受程度的研究,有助于译者选择恰当的方式再现“京味”,进而契合英语受众。英语近年来也吸收了许多中文词,比如taiji(太极)、tofu (豆腐)和fengshui(风水)等,最新资料显示“add oil(加油)”已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17]。同样,越来越多的译者采用贴近中文习惯的外来语方式翻译“胡同”(hutong/hu-t’ung)和“饺子”(jiaozi)等“京味”语言,更贴切地再现了“京味”,并逐渐被受众文化接受。比如林海音《城南旧事》第一章中的介绍“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 ’……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长班老王’”[18]4-7,译者殷张兰熙(Nancy C.Ing)和齐邦媛运用拼音式外来语加注释的方式,将“胡同”译作“hu-t’ung”,“老王”译作“Lao Wang”。“I said ‘Hui-an Hostel’ like the other children in our hu-t’ung...Everyone called the girl’s father, Lao Wang.”[19]2-5。伴随着源文化同受众文化融合的发展,京味文学翻译策略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使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京味文学。
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源文化与受众文化的融合成了时代特征,随着英语受众对中华文化的接受程度逐步加深,京味文学在受众文化中的传播和翻译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一些典型的中华文化专有项和京味文化专有项不再完全依赖归化的翻译策略,译者可以采用已被受众文化接纳的汉语外来语,以及符合英文语法习惯的自造词。受众研究可以通过两种文化的互动,分析不同译文中受众文化与源文化的融合效果与困境,发现既能有效传播京味文化,又易于被受众文化接受的翻译策略,更好地为京味文学翻译实践服务,拓展英语受众的研究范式。
三、 京味文学英译的空间再现研究
空间书写是文学作品中各种景观和场所呈现方式的总称。城市中的各种空间留下了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烙印。比如北京的紫禁城无声地叙述了王朝的变迁,铭刻着几千年来的中国儒家文化思想。文本中的城市空间是社会文化记忆功能和文字符号功能的统一,是“对现实城市蕴含的社会文化的再现”[20]193。京味文学作家在创作中运用叙述视角的转换以及空间书写的连贯等技巧,将城市的历史沧桑、市井生活和风土文化悄然融入空间书写中,形成了文本中的“京味”。这些城市书写策略是京味文学英译本中“京味”本真再现的关键,译者需要运用相应的策略本真再现原文空间书写中的“京味”效果。因此,充分认识京味文学的空间书写特征,既是“京味”本真再现的关键,也是英译研究的重点拓展方向。
(一) 空间书写中的叙述视角
京味文学中的叙述视角是译本“京味”准确再现的焦点。中西方叙事在空间书写上的区别是对译者空间再现能力的一种考验,译者可以通过一些叙事策略实现空间书写效果的对等。京味文学经常以小市民的视角叙述故事,构建城市空间中的各种场所和景观,呈现独特的京味城市。比如老舍《骆驼祥子》中阜成门附近的街道、《四世同堂》中的小羊圈胡同以及邓友梅《那五》中的天桥市场这些明显具有京味特征的城市空间,常常以某位小市民的视角呈现给读者,特别是在一些庙会、集市和市井生活的场景中,叙述者时常放弃故事外的全知视角,转而以小市民亲历的视角对城市空间进行淋漓尽致的展现,从而生动地呈现京城百姓生活,使“北京甚至可能比之乡土更像乡土”[21]43。这里的乡土就是地地道道的“京味”:
这清音茶社在天桥三角市场的西南方,距离天桥中心有一箭之路。穿过那些撂地的卖艺场,矮板凳大布棚的饮食摊,绕过宝三带耍中幡的摔跤场,这里显得稍冷清了一点。两旁也挤满了摊子。有修脚的、点痦子的、拿猴子的、代写书信、细批八字、圆梦看相、拔牙补牙、戏装照相的。膏药铺门口摆着锅,一个学徒耍着两根棒槌似的东西在搅锅里的膏药,喊着:“专治五淋白浊,五痨七伤。”[22]204
《那五》中的这段空间书写以故事外的全知视角展开,叙述者带着读者“穿过……绕过……”,使读者感受到了身临其境的庙会场景。作者巧妙借助一个虚拟小市民的穿梭引领,生动展现了众多的人物和繁华的市井,使得空间叙事声景交融,人城一体,一个具有浓厚京味的天桥市场跃然纸上。接着,景观中的“一个学徒耍着两根棒槌似的东西”将空间书写的叙述视角由故事外全知视角转移到了小市民身上,全知的叙述者应该知道“两个棒槌似的东西”是什么物件,但叙述者暂时以一位“非全知”小市民的视角“佯作”不知,带着读者穿过了市场。这一视角显然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的空间距离,再加上作品中像“秫秸墙”这类方言词语的衬托,生动再现了具有乡土味的京味京韵,娴熟地展现出空间的京味特征。然而在英译本中,原作中小市民穿梭于市场的“京味”叙述效果却未能再现:
Qingyin Teahouse was off the beaten track in the southwest of Triangle Market, a bowshot from the centre of Tianqiao. To reach it he had to pass the amusement stalls and refreshment booths with low stools and canvas awnings. Then he skirted round a wrestling ground both sides of which were packed with more stalls run by chiropodists, professional letter-writers, fortune-tellers, dentists and oculists. There you could also find cures for ache, watch performing monkeys, or have your photograph taken in opera costume. In front of one shop was a cauldron in which an apprentice was pounding up a plaster, calling out, “A guaranteed cure-all!”[23]177-178
这段译文摒弃了原文故事中的小市民视角,从头至尾一直是故事外视角,这一视角变换使原作带给读者的身临其境的体验不复存在。与此同时,译文中“he”和“you”人称的突兀变化明显破坏了原文空间书写的连贯性,展现给读者的只是景观的白描叙述,空间书写中的“京味”乡土气息荡然无存。可见,空间书写中的“京味”并非仅仅通过词汇呈现,叙事视角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要做到本真再现原文空间书写,不仅需要关注所指的对等,即各种场所本身,更要关注空间书写层面能指的对等,这是空间书写方式的对等,也是“京味”再现的重要手段。简言之,京味文学的城市书写中,不仅景观自身具有“京味”,其空间书写的叙事技巧也具有“京味”,这就需要在英译中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两个“京味”要素。英译本城市再现研究不仅可以促进译者重视空间再现对传递“京味”的重要作用,同时可以推动空间书写成为当代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客体。
(二) 空间书写的连贯再现
由于中英文在空间书写中的差异,空间书写中的连贯特征是京味文学英译本中城市空间准确再现的核心要素。在中文语境中,京味文学常常将人物置于空间书写的主导地位,以人物为空间的主体,在人物与空间景观之间形成某种特殊的空间关系,在空间中渗透“京味”。中文语境中的空间书写连贯注重 “意合”,即无论空间书写中的人物在景观中的位置发生怎样的变化,其“形散而神不散”的空间连贯不变。如王朔在《玩的就是心跳》中通过主人公的双眼展现京城夜景,描写自然流畅,景物以人物为中心进行镜头推移,人物始终贯穿其中。城市空间中的“我”、店铺和人流依次展开,由远及近,多主语、短句相连,形式上达到空间连贯:
我再次来到大街上,天已经完全黑了,一些商店的霓虹灯远远近近地闪烁,更多的商店关了门。下班的人潮已过,街上很冷清。我步行到东单路口,这儿热闹些,长安街上灯火通明,数条车龙相对川流。[24]5
在这段城市书写中,简单的句法和儿化韵词语“这儿”实际上体现了小市民的身份特征,是空间书写的小市民京味身份印记。尽管“我”是这个空间中的一个客体,但同时也是这段城市书写的叙述者,控制着这段场景的开始和结束,居于这段城市书写的主体地位。英文空间书写讲究“形合”,强调通过句法连贯实现整体空间连贯。英译本将人物作为空间书写中的客体,将主体让位于空间自身,所以在英译本中,原文空间中人物的主体地位会被削弱或转换,人物“I(我)”成为空间中的一个客体,通过空间中主客体关系的转换,实现空间书写效果的连贯。英译文如果完全遵循汉语的语法习惯,主客体关系与原文相同,以“I”为中心,就会破坏空间书写的连贯性。葛浩文的译文就处理得非常得体,空间书写拿捏得准确到位:
It was dark when I walked back outside. Up and down the street neon signs were winking, although by then most shops were closed for the day. The evening commune was over, [and] the streets were cold and uninviting. I headed toward Dongdan, where it was livelier; Chang’an Street was bright with trams shuttling back and forth.[25]6
在译文的段首,葛浩文运用“It was dark when I walked back outside”,与下一句的“Up and down the street...”实现了连贯顺畅,空间整体效果达到对等。在英语译文中,虽然“I(我)”依然是叙述者,但其主体地位被“it”所取代。译文以非人称代词“it”作为叙事主体展开空间书写,将中文以“我”为空间书写的主体转换为英文以景观为中心的叙事,构成了空间再现的句法连贯,空间书写一气呵成、自然流畅。译文中空间主客体关系的反转顺应了英语句法习惯。这种主客体关系的变化分别顺应了各自的“意合”与“形合”,同时,译文简单的词汇和句法结构也顺应了原文小市民的叙事特征,充分实现了空间书写上的连贯。
京味文学英译中空间书写的再现实际上是空间自我指涉在两种文化和语言中的效果对等。列斐伏尔曾指出,“[空间]可以从语言学的概念,如能指、所指、指涉关系和意义层面解读”[26]114。京味文学的空间书写是所指和能指相得益彰的指涉系统,所指是北京城的空间、人物和事件,能指则是描写这些城市空间的话语方式,即上述的叙述视角、空间书写连贯等。叙事的空间连贯并非简单的所指连贯,也需要能指的功能连贯,才能实现译文中“京味”城市空间再现的整体对等。总之,二者相辅相成是京味文学英译中城市书写“京味”再现的关键,这一研究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四、 京味文学英译的民族认同研究
民族认同指的是具有相同历史、文化和族群特征的集体身份认同,是“对具有独特民族特性的价值观念、象征体系、记忆图谱、神话原型和传统模式的不断复制和重新诠释,是个体成员对民族文化要素的认同”[27]20。京味文学记录了中国社会百年来的风雨历程,见证了北京城的世纪沧桑,拥有丰富的中华民族认同印记。文学叙事与民族认同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民族像叙事一样,将其本源散落在时代的神话之中”[28]1。京味文学在叙事中将民族文化、民族记忆和民族创伤等认同要素融入一个世纪的作品中,这既是京味文学创作自身的需要,也是民族认同存在于文学叙事中的方式。如《四世同堂》中老舍笔下一家四代在日寇统治下的北京城生活,恰恰反映了列强侵略下的中华民族创伤,皇城荣辱变迁中的京城百姓故事正是民族认同的呈现。“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29]295
京味文学翻译中的民族认同研究旨在探究译者是否本真再现了作品中的中华民族认同,做到了民族文化的本真传播,注重分析译者是否“借助翻译加强自身的霸权,在被殖民者身上、族群或种族原型中烙印上殖民者的想象”[30]166。京味文学英译研究以本真再现民族认同为己任,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避免西方殖民话语的影响,致力于民族文化在英语世界的本真再现。
(一) 民族认同的建构和去殖民化
京味文学中的民族认同内涵非常广泛,京味文学中寻常百姓以及胡同院落具有鲜明的民族时代特征。这些颇具“京味”特色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在英译本中的再现效果已经成为译本是否成功的关键影响因素。英译的民族认同研究旨在对译者在选词、造句和文体等层面的京味再现做深入分析,探究译本是否存在文化误译以及隐含殖民话语。《骆驼祥子》对大杂院中老人及小孩的描述中写道:“春已有了消息,树枝上的鳞苞已显得红肥……春到了人间,在这大杂院里只增多了困难。长老了的虱子——特别的厉害——有时爬到老人或小孩的棉花疙疸外,领略一点春光!”[9]152仔细品味这段描写,老舍将京味民族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院子里的男女老幼纷纷走出家门,艰苦环境中老人悠闲的生活节奏恰恰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京味”。英译文需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原文中的这一民族文化特征,下面两段译文对原文中“虱子”的处理就有所不同,再现效果也明显有别:
译文一:...old lice, the worst kind of all, some times hopped out the cotton wadding in the ole people’s and children’s clothes or gained the experience of a little sunshine.[10]162
译文二:...Lice that had survived the winter — most vicious, these — sometimes crawled out of the padded clothes of the children and old people to enjoy the spring sunshine too.[11]256
身上有虱子在中国旧社会的穷人中并非什么骇人听闻之事,因此在翻译中需要注意用词的“度”。译文一将“特别厉害的虱子”译为“worst of all”,既表现了虱子难以对付,同时又有一种京味幽默在其中,此处的描写将人们的生活困苦、老人的悠闲、虱子的“强壮”和作品的诙谐幽默融为一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相比较而言,译文二的选词“vicious”显然不妥,因为“vicious”含有恶毒、邪恶之义,这一译文展现在英语读者面前的是一群荒蛮甚至令人作呕的京城老人形象,原作中所表现出的老人们的悠闲自得荡然无存,不知不觉中迎合了东方主义视野下的民族形象,未能本真地再现作品中的民族认同。与此同时,原文中的京味幽默在译文二中也没有再现,造成西方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华民族形象的误读。另一方面,“vicious”的拉丁词根也无法再现原文“接地气”的京味文体,一词之差会造成人物形象及其背后民族认同的强烈反差。相对于上述译文,笔者认为原文可以译作“lice having survived the last winter were the sharpest...”sharp既有“强壮、难对付”之意,同时也有“狡猾”之意,得以全面展现原文表现的生活困苦与老舍文笔的诙谐幽默,使京城旧社会的民族文化准确再现于西方读者面前。京味文学英译研究要针对译本中隐含的殖民话语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民族认同的误读与误译,探究本真再现民族认同的翻译策略,拓展文学翻译研究视角。
(二) 民族创伤的本真再现
京味文学叙述了北京城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国所经历的列强入侵、民族危亡和经济凋敝都被文学家悄无声息地书写在了京味文学中,展现了重要的民族认同要素,即民族创伤。民族创伤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民族情绪在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宣泄。京味文学塑造了一批鲜活的小人物,他们的言谈举止表达宣泄了不同的民族情绪,是民族认同研究的重要内容。多数京味文学作家并没有强烈的英雄情结,而是将故事聚焦于命运多舛的小人物身上,这些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小人物身上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创伤。老舍笔下的刘麻子、唐铁嘴、马五爷、“密探”等一系列反面人物,祥子、小福子、康六等一批谋生者,往往命运多舛,或者人性堕落,或者悲慎而亡,这一人物集合正是病态社会的反映,是当时社会中民族创伤的文学再现。《茶馆》中的刘麻子就是畸形社会病态小市民的集中体现,作品通过刘麻子对常四爷和康六不同的说话语气,将一个阴险奸诈、趋炎附势、崇洋媚外的病态小市民形象细致入微地刻画出来。但在一些译本中,刘麻子这种病态形象未能准确再现,因而其背后的民族创伤也未能深刻展现:
您二位真早班儿!(掏出鼻烟壶,倒烟)您试试这个!刚装来的,地道英国造,又细又纯!……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耽误了事别怨我!快去快来![31]18-22
前面一句是刘麻子对常四爷和茶馆掌柜王利发的应酬,后面一句是其对贫苦农民康六的呵斥。英若诚先生的译文是:“You gentlemen are early today. (Takes out a snuff-box and measures out a little.) You must try this! I just got it, genuine thing from England! So fine and pure...I’m telling you, you won’t find out another chance like this. If you lose it, don’t blame me! You’d better get a move on.”[31]19-22。译文显然没有表现出势利霸道的人物特点,刘麻子在对常四爷和茶馆掌柜的应酬中说“您尝尝这个”,充满了奉承巴结的味道,但译文“You must try this”却带有明显的命令口气;而原文中刘麻子对康六不耐烦的呵斥,译者却译成了带有商量和建议口气的“you won’t...”和“you’d better...”。在这段译文中,刘麻子趋炎附势、专横霸道的形象荡然无存,一个崇洋媚外的小地痞身上呈现的病态的民族创伤在译文中没有充分体现。
京味文学中的民族创伤并不关注气势磅礴的革命运动,而是将这一要素潜移默化地渗透在了小市民的市井生活中,京味文学英译研究需关注小人物的身体、精神和心理创伤描写在英译本中的本真再现。由此可见,京味文学英译中民族创伤的再现研究是民族认同研究的有益探索,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三) 京味文学翻译研究与文化自觉
长期以来,西方译者潜移默化的东方主义思维“最热衷的策略非‘归化’莫属,因为归化致力于鼓励殖民大国将外国的文本译成本国话语,进而消除文化差异”[32]109,这导致一些译者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致使京味文学英译本中存在大量的殖民话语,客观上造成西方读者对京味文学存在一些误读现象。京味文学英译中的文化自觉是文学翻译、翻译研究和民族认同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深度融合,同时也是一种翻译研究范式的拓展。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自觉研究注重探究民族文化本真再现的策略和思想,促进译者和翻译批评者的民族认同意识,在文学翻译中本真再现京味文化,进而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民族自信。
文化自觉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30]67。翻译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翻译研究是文化研究的延伸,也是全球化时代跨学科的融合。京味文学翻译研究应突破语言研究范式的束缚,在研究中自觉融入文化研究的视角,借鉴文化研究理论,提升文学翻译研究厚度,拓宽翻译研究视野。京味文学经常出现的歇后语彰显了京味文化诙谐幽默的特点,歇后语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重要的中华文化认同要素。在《千万别把我当人》中,当谈及抗击外国殖民者时,王朔接连用了三句歇后语,其中一句为“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33]92。葛浩文的译文“You have to be an idiot to sleep on a cold brick bed, since it’s built to have a fire underneath”[34]121曲解了原文本意。原文中的“傻小子”在这里是“老实憨厚、身体强壮、有蛮力气”之意,而葛浩文却翻译成了“idiot(白痴)”。原文不惧强敌、大无畏的故事语境在译文中消失殆尽,原文中人物形象及其背后蕴含的文化认同也被误读,可见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向来不是孤立的。当代文学翻译研究不断吸收借鉴文化研究中的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播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多维文化研究视域下的文学翻译研究,建构了文学翻译研究范式。
另一方面,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自觉旨在提高译者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进而强化本真再现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实现文化认同的本真传播。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京味文学作为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需要走向世界并丰富世界文学之林,其作品的广泛英译既是这一流派发展的需求,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京味文学译者和翻译研究学者都应将本真再现民族文化认同看作自己的责任担当。老舍的短篇小说《抱孙》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前,描写了北京老百姓的市井生活。书中字里行间都京味十足,民族文化认同的再现是其英译成功的关键。“现在,王少奶奶又有了喜,肚子大得惊人,看着颇像轧马路的石碾。”[35]341译文为:“Now young Mrs.Wang was again blessed.The size of her belly was astonishing,like stone rollers that road gangs use.”[36]47-48。译者王际真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留学美国,随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文。他是最早将京味文学作品译介到美国的译者之一,他的跨文化身份使他能够顺畅地本真再现中国文化。在这段译文中,译者既没有简单地将“有喜”翻译为“happy”,也没有译为“be pregnant(怀孕)”,而是采用了“be blessed”。“be blessed”在英文中指被上帝所青睐,译文将添丁视为“天赐之喜”,这既符合英语受众的语法和文化,又准确地表达了中华文化中“有喜”的文化内涵,凸显了中华文化对人丁兴旺的期盼,实现了译文与原文在句法和文化认同上的相得益彰。
文化自觉和民族认同是当今学界常探讨的核心关键词,二者与文学翻译的融合研究是京味文学英译研究的有益拓展。京味文学中的“京味”是一种浓厚的民族认同,京味文学翻译中的民族认同研究更多关注译本中的西方话语霸权以及去殖民化意识,为再现“京味”探究适宜的翻译策略和思想。其中人物形象的去殖民化研究、民族创伤的再现研究以及译者的文化自觉研究,都有助于译者放下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抑制翻译中种族主义的暴力”[37]20,在京味文学翻译中更好地本真再现中华民族认同。
综上所述,京味文学英译研究将文学翻译置于一个更为宏观的语境中进行考量,将多维度的文化研究纳入视野,是“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学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的有效尝试, 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对翻译学这一新兴的尚不成熟的边缘学科的理论建构”[38]6,提升翻译研究的厚度。在文化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京味文学翻译研究日益走向跨学科、多维度和深层次研究。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译者在多维翻译思想、翻译理论和文化背景下,源源不断地创造出风格迥异的京味文学英译本,丰富了文学翻译的宝库。京味文学翻译研究在语言和翻译技巧研究的基础上,需要与时俱进,深入探索文化、叙事、城市和民族认同等多维度研究方法,融合当代文化研究理论,为文学翻译研究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本真传播中华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