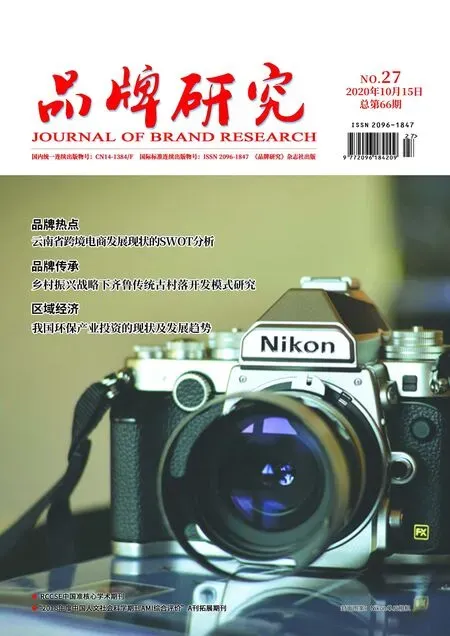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研究综述
文/任雅静(浙江师范大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和基础,可以赋予乡村生活以价值感、幸福感和快乐感,激发起人们在乡村生活的意愿、努力振兴乡村的活力和动力;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村民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全面提升村民思想道德素质,助推乡风文明的实现。当前,国内关于文化治理、乡村文化治理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此对其作出梳理和分析,以探究未来的研究趋势。
一、文化治理概念的研究
已有研究主要持三种观点:①文化是治理的工具。文化治理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利用文化的功能解决国家发展中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社会共治活动(胡慧琳2012),其本质就是透过文化和以文化为场域达到治理(王志弘2010);②文化是治理的对象。文化治理是指矫正社会文化趣味、对社会低劣情趣进行治理(何满子1994),强调的是运用相关治理理论对文化及其发展进行干预、治理,以达到国家预先设定的发展目标(廖世璋2002,景小勇2016);③文化既是治理的工具,又是治理的对象。文化治理不只体现为借助文化来进行治理或者对文化进行治理,更主要体现为对文化的治理与借助文化而治两者的结合(廖胜华2015);文化治理是多元主体合作共同治理文化,并利用文化的功能来达成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重治理目标的过程(吴理财2019)。
二、乡村文化治理功能研究
一些学者将文化治理与乡村场域相结合,形成了对乡村文化治理方面的研究,认为诸多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深层次的伦理文化,始终支撑着乡村社会秩序,并且在权力结构的运作中自然呈现。韩庆龄和宣朝庆(2015)从文化的显在功能与潜在功能两个方面对文化的社会功能进行了阐述,认为文化的显在功能是促进当地村民的道德教化,文化的潜在功能是治理社会失序,通过教化和德治达成社区治理。金萍(2017)对孟子后裔古村落的文化治理考察中,提出运用当地的儒家传统文化可以为当地社区形塑优秀的家风文化。周静(2019)认为乡村礼仪、乡村记忆馆、村晚等集体参与项目在活跃乡村文化生活中,对于引发村民公共意识、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的问题研究
(1)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缺失。乡村文化治理中存在着严重的主体缺失,具体表现为文化传承的主体缺失、政府的失灵、社会组织的缺位、村民的文化治理意识淡薄(朱菲菲、包先康2016)。在压力型体制的影响下,乡村文化治理未能充分调动基层文化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忽视了农民的参与,难以在村庄内部有效构建公共文化行动的基础(陈楚洁2011,刘建2020)。而主体缺失、“行政主导”治理模式的程式化、项目化、任务化突出导致文化活动载体与价值意义断裂,使自身陷入功利性、封闭性和技术性治理之中,带来了供需割裂问题,难以满足村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这已经成为乡村文化发展中的难点所在(韩鹏云,张钟杰,2017)。(2)优秀乡土文化的缺位。乡村文化治理中存在着优秀乡土文化的缺位,这具体表现在乡土文化在乡村场域逐渐式微、优秀传统文化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以发挥其社会治理功效。由于青年这一主要行动主体的流失,许多乡村民俗仪式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也几乎不复存在(庄孔韶2004);将文化等同于活动、文化建设等同于项目建设、文化产业等同于经济利益的功利性治理,使得乡村文化的教化性内涵开始逐渐丧失(韩鹏云、张钟杰2017)。
四、乡村文化治理的对策研究
乡村文化建设问题的根源在于缺少群众参与性的文化组织及其动员机制,培育这种组织与动员机制是乡村文化重建的核心内涵(谭同学2006)。要改变现有问题,需要加强农村文化供给侧改革,提高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形成健全的供给体系,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加注重文化供给的可接受性,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文化领域健康可持续发展(徐勇2018)。
(1)构建“协同治理”模式。构建“协同治理”模式(韩鹏云2017)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为其他主体提供资源和服务,鼓励社会组织和村民积极参与,形成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机制,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朱菲菲、包先康2016)。20世纪上半叶,梁漱溟先生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衰败深感忧虑。为此他提出乡村建设,基本任务就是依靠乡村自治,创造一种以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团体组织,由此推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进步。(2)激活乡土文化。乡村文化治理不能忽视乡村既有的传统美德和乡土情谊,需要借助蕴含着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民间文化资源,运用文化治理的方式,逐渐培育起体现新时代文化特征的新型村落文化形态。文化供给最终要为消费者所接受,只有文化产品和活动能够为民众所接受,才能发挥最大效益。而乡土文化具有自然生长的原生性特征,值得重点关注和进一步扶持;需要发现并激活乡村民众和乡村社区所蕴含的巨大文化潜力,探讨“如何传承乡村的文化传统,如何实现乡村文化的创新发展”(徐勇2018)。
五、结语
总的来说,目前学界研究都肯定文化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认为可以通过文化治理来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并且从不同方面加以论证;在参与治理的主体上,学者都主张多元主体,并且更加强调社会的参与力量。在乡村文化治理所面临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目前我国乡村文化治理存在严重的主体缺失、传统文化缺失;针对所存在的问题,认为需要激发内生动力及活力,这包括激发内生主体的治理活力、挖掘内生文化的治理动力,即强调突出村民、大众的治理主体地位,强调重视“乡土文化”。但是根据以上梳理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内容虽然明确了文化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但只是停留在多元主体共治价值或意义上的讨论,各个主体所扮演的角色还是宏观方面的论述,对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各主体在文化治理中的协作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显著,未来应该在乡村文化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多元主体合作机制方面做出进一步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