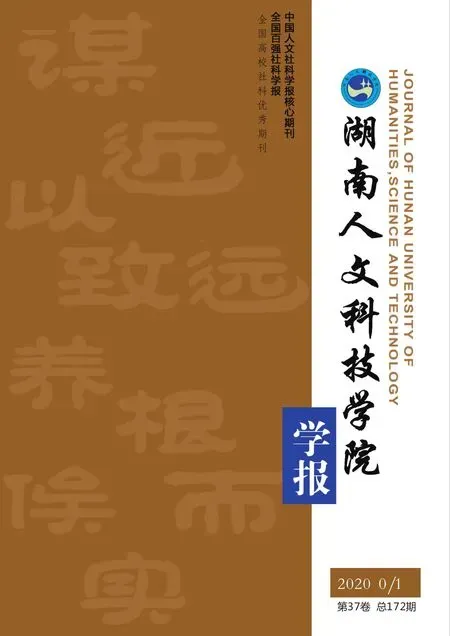东晋南朝浙西航线的文学生产与传播
沈 琪,李德辉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411021)
跨学科研究成为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趋向,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对文学进行关照。从交通的角度谈文学,以创作主题的日常生活,特别是行旅生活为考察对象,文人的每一次漫游、旅宦和迁徙都可能会成为创作的动机,情发于中,文形于外,通过文学作品将内心的情感进行抒发,因此可以说交通为文学的生产提供了条件。此外发达的交通为文学传播提供了途径,邮递、便寄、遣使等方式有助于加速文学作品的传播和作家影响的扩大。朱睦卿最早提出开发浙西“唐诗之路”,其后的研究者也多将精力放在浙西的唐诗上。本文借助地理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考察东晋南朝地域、交通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探究东晋南朝时期浙西航线对东晋南朝文学生产和文学传播的一些基本特点和作用,并就浙西航线和东晋南朝文学之间的关系与存在意义加以论证。
一、东晋南朝浙西航线的概念内涵
古人对地域的划分,以河流为界,面对河流的发源地,左手边为江左,右手边为江右;面对河流的入海口,左手边为江西,右手边为江东。按照这类划分依据,浙西航线就是地处浙西,自西向东,接新安江,流经建德、淳安、富阳、桐庐等地,从杭州湾延伸至东海的一条连贯的水上航线,也是东晋南朝文人行旅的一条重要交通之路。
首先浙西航线作为东晋南朝文人的交通圈,具有鲜明的“点—线—面”的空间布局和结构特征。以浙西航线沿途新安、建德、淳安、富阳、桐庐等十多个重要城市为点,以将这些城市连接起来的浙西水陆交通道路为线,通过航线与若干条驿路将浙西与都城建康联接起来构成的广大区域为面,构成了一个巨型交通网。若对其加以简述,则是以从新安江发源向东注入杭州湾的浙西航线为枢纽,以新安、杭州作为枢纽的两端,以歙县、新安、建德、富阳、桐庐、钱塘、杭州等区域城市作为伸向四翼的轴端,通过这个交通构架来对国家的辖区施行有效的管理。《晋书·潘岳传》载:“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1]。这展现了当时交通之便捷,道路纵横,行旅颇盛,逆旅众多,无论冬夏旅人都会有休息、歇脚之地。《富阳县志》载:“富阳为水陆通衢,置邮传命,兴德之流行并速,则小民均食服矣。”可见当时富春江航线津口逆旅遍布,来往人员众多,便利交通给富阳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这些例子都从旁佐证了浙西航线的巨大的交通功能。
再将文人作为主体进行研究,将浙西航线构成的巨大交通网与文人活动进行重合,又构成了一条界限大体明确、架构基本稳定的文人活动路线。北上文人的漫游、南下文人应举以及官员中央与地方任职迁转等,不同身份的人赋予了浙西航线着不同的功能。但因为文人行经浙西航线,沿途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作品,从而促进了东晋南朝的文学生产与传播。
二、东晋南朝浙西航线与文学传播的关系
文人的文学作品一般是沿着交通路线传递的,文学传播路线与交通路线基本一致,交通繁忙的要道同时也是文学流播的主要路线。浙西航线以其水上交通的便捷分别从纬度与经度两个方向推动了浙西文学与文化的传播。
纬度即是指在东晋南朝期间,浙西文学与文化在这一时期的传播。当时,都城建康做为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诏徵入朝、投亲访友、参师问学等一系列活动都会吸纳文人群体从四面八方聚集建康。建康以南的吴越文人就通过浙西航线这条交通动脉,从外邑流向都城,从边缘流向中心。人是文学传播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员来往为文学传播创造了很多机会。文人会选择浙西航线,与浙西航线水陆兼备,以水运为主的便利条件分不开。东晋南朝受战争影响,马匹多被征用为军马,常人出行或货运采用牛车、驴骡车甚至肩舆。但畜力及人力车在速度及载重量上都有限制,且遇到畜疫或者道路问题,路上交通就会产生诸多不便。而水上交通不需车马,可避免道路的颠簸,规避山野强盗,而且速度较快,是当时最便捷的出行方式。因此大量的文人赴任、贬谪、行旅、漫游都会选择走水路。浙西航线的上段新安江发源于安徽黄山,流经建德、淳安,向东汇入富春江,流经富阳、桐庐两县,下接杭州西湖,最后经杭州湾注入东海。叶浅予《富春江游览志》云:“(富春江)在浙水之上游,离杭州水程只四十里,在海运未通前,为闽、广、徽、籍往来通道……时至今日,行旅虽趋捷径,要亦未失,浙江上游交通枢纽也。”[2]可见浙西航线连接了浙西、浙东、浙南以致福建,是皖、闽、赣三省的水上动脉,在古代倚重水路交通的情况下,尤受重视。
除了向政权中心的集聚效应,浙西航线还具有将文人从都城派遣至四方,产生文学的扩散效应。政治中心的南移以及人口的迁徙推进了南北交通的开辟。西晋末开始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东晋南朝都在南方发展,使南方人口在三世纪中叶首次达到了与北方大致相等的数量。李凭《华夏文明与江南文明的融合》指出:“东汉末年至三国西晋之间,在中原发生一系列战乱……动荡不安的政局引起频繁的移民,大量中原人民从长安、洛阳等地流散到河北、河西和更远的江南”[3]“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4]。左思《吴都赋》这样描绘江南地区:“其四野则珍啄畷无数,膏腴兼倍。”当时江南甚至流传着“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的俗语。连年的天灾人祸使北方人民对南方产生了向往。晋朝迁都至远离战火的建康,建立了东晋政权,建康成为东晋南朝都城。政权中心的南移往往伴随着人民的强制性迁移,各阶层都被要求随都城的转移而迁移。据《晋书·地理志下》载,吴郡户数为25 000,到《宋书·州郡志》时增长到50 488,增长了25 488 户。刘宋时期户口隐漏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户口的大幅度增长只能说明实际人口增长的幅度更大,这种增长的合理解释就是得益于外来移民[5]。他们的南迁将北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带入南方,带动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南方的开发。对南方地区交通线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政策支持,促进了南北文学的交流与传播。
文学重心伴随着都城南迁至建康也开始发生南移。西晋时期吴郡著名文人有9 人,到了东晋时期,吴郡著名文人有26 人,南北朝时期更是跃升为88 人。钱塘县东晋时期著名文人3 人,南朝时期上升为8 人,浙江地区的著名文人数量排名从东晋时期开始一直位于第一或第二。琅琊王氏、陈郡周氏、庐江何氏等世家大族的迁入,带动了南方地区的文学水平,培养出更多著名文人。除了世家大族的迁入,也有被流放或贬谪的世家大族。浙西因为离都城建康不远,容易监视,但又比浙东偏远有惩罚的目的,所以选择浙西有利于监管有罪的宗室、官员及其家属。浙西处于建康的南方,这些被流放的人员会对政权中心建康产生一种仰视心理,此外他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经济实力,这些文人来到这里,和当地文学结缘,对本土文学产生影响,也被本土文学所影响,甚至部分文人反客为主成为当地文学的主力军。
他们的文学活动与文化创作既促进了文学传播,又对迁入地经济文化大发展起到较大作用。
经度就是指以时间为经线,看浙西航线在时空中对浙西文学与文化的传播。到了唐宋,伴随着第二次、三次人口南迁,江南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大量文士的迁入为浙西航线的文学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无论是自由浪漫的李白、辞句质朴的白居易、山水田园诗派的“王孟”、清新活泼的杨万里、豪爽旷放的苏轼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都在浙西航线上留下佳句。从他们的创作中都可以发现到东晋南朝浙西文人的影子。东汉严子陵、南朝名士戴颙等隐者给浙西航线增添的隐逸文化的魅力,吸引了后世大量慕名而来隐居、求仙之人。特别是易代之际的遗民诗人,效法前人选择浙西隐居,并经常结社唱和,形成了浙西遗民作家群,其中以南宋方逢辰和何梦桂为代表的严州遗民群创作了大量描写浙西的诗文。
浙西航线的开辟与发展,一方面使来往行人数量增长,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东晋南朝浙西文学生产与文化的不断传播。
三、东晋南朝浙西航线与文学生产的关系
伴随着东晋南朝政治斗争的不断激烈,朝代更迭频繁的大背景,在这条繁忙的交通航线上,每年都会有大量官员离京赴任、入京做官或被贬流放,还有往来穿梭的使客,再加上一些想要效仿东方朔入京自荐,谋取功名的文人,他们在浙西航线上南来北往,消耗了大量时间。浙西航线以其奇特的自然景观、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给士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往来文人在这条交通线路上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可以说浙西航线对浙西文学生产力的解放、作家创作能量的释放提供了支持。
浙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的地域风气。文人生活于此,为此方风土所浸染,形成了六朝文学独特的温清秀润之气。浙西航线沿途拥有江南地区所独有的秀丽明媚景色以及富有历史文化内涵且密集的人文景点。途径这里的文人感于浙西山川风貌,“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6](《文心雕龙·物色》),从而创作出与其他朝代和地区气质不同的秀润之作,也不会有西北黄土地孕育出的悲凉厚朴混茫之气。
浙西航线沿途自然景色奇特,外地文人赴任、远调经过浙西航线沿途定会被它天下独绝的奇山异水所吸引,所慑服,感悟江山风貌、追忆名人将相,往往都会留下动人的诗篇或文章。谢灵运永初三年遭到徐羡之等人的排挤,出任永嘉太守。赴任途中,他沿着浙西航线欣赏了浙西的美景,写下了《富春渚》《七里濑》《初往新安至桐庐口》《夜发石关亭》等多首作品,实为最早的东晋南朝的山川纪行组诗,谢氏也因此而成为吟咏浙西山水的第一人。梁代文学家吴均《与朱元思书》:“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沈约《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洞澈随清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万丈见游鳞。”都是描写浙西山水的同类作品。沈约等诗人在诗中多次描写的浙西风景,要说与浙西航线沿途独特的风景和布局走向无关是不合理的。《晋书》卷九九《殷仲文传》及《世说新语·假谲》载,殷仲文迁为东阳太守,意甚不平。临当之郡,游宴弥日。行至富阳,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孙伯符”[7]。自古人们都喜欢将地理环境与人物成长联系起来,殷仲文虽没直接赞美富阳,但他认为这里是能出孙策这样人才的地方,也就是从侧面赞美了富阳这里的自然环境。此外,浙西自古以来的隐逸文化吸引大量慕名而来的游人。上古时期采药求道结庐东山的桐君、东汉高士严子陵、南朝名士戴颙等隐士都给浙西奠定了隐逸文化的渊源。魏晋文人爱好游仙、采药,浙西航线作为他们游览吴越的主要路线,吸引了后世大量慕名而来隐居、求仙之人,他们沿着浙西航线凭吊赏玩,贡献了大量隐逸、山水诗。浙西的隐逸思想和独特山水景色成为抚慰诗人心灵的重要媒介,对山水景色的审美享受可以使文人忘记行旅的舟车劳顿,从浙西隐逸文化延生出的玄佛义理能安慰文人漂泊困顿的心灵,这都说明文人在浙西的游历能够影响到诗的题材内容和意境风格。
官员在浙西航线上的迁转也赋予了浙西文学不同的魅力。何逊《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诗》:“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归……故乡千余里,兹夕寒无衣。”任昉《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涿令行春返,冠盖溢川坻。……叠嶂易成响,重以夜猿悲。”《入东经诸暨县下浙江作诗》:“疲身不自量,温腹无恒拟。未能守封植,何能固廉耻。”把这种远离故土,离京远调时的复杂心境生动的述说出来。丘迟天监三年出任永嘉太守,途径浙西,写下《旦发渔浦潭》。任昉天监六年出任新安太守,写下《严陵濑》《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成为第一位从外地到浙西做官并留下诗作的浙西地方官。何逊出任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写下了《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诗》《入东经诸暨县下浙江作》《西州直示同员》。这些作品,都是浙西航线促进浙西文学生产的明确证据。
外地作家纷纷南来,将不同地域的文坛风气带到这里,促进了本土作家的成长、水平提高与数量增加。通过命官、出使、贬官或其他客游,无论何种行旅都是文化交流的方式,都能影响到当地文学。本地文人在流寓作家与浙西山水的共同沁润下,他们的创作也深刻地打上了浙西独特的烙印。浙西本地文人孙惠所撰《百枝灯赋》《楠榴枕赋》《繀车赋》等赋体文学作品,字句简丽,题材也扩大,将浙西生活风物做了生动再现。特别是《繀车赋》:“工巧是嘉,或口绵组,或匹绫罗。舒皓腕于轻轮兮,拟景乎镜华。丝成妙于指端兮,号推幽而相和。”再现了西晋浙西精湛的纺织技艺,对后世了解西晋浙西地区的社会生活有重要意义。《谏齐王囧》《诡称南岳逸士秦秘之以书干东海王越》《与淮南内史朱诞书》等文再现了西晋末浙西地区战争与祭祀的场面。孙拯与陆云唱和的诗文《赠陆士龙十章》语言典雅、富含哲理,体现了传统赠答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虽然陆云写给孙拯的诗未流传下来,但是也可根据孙拯的赠诗管窥浙西本地文人之间相互赠答唱和的活动。
浙西航线是对现代地理航线概念的借用,是一个功能地域概念,交通成为文学的表现形式,在这条航线上的自然与人文都成为文人的创作素材,文人既创作出赞美沿途风景、酬赠送别类的诗文,也有抒发个人羁旅愁思的佳作,更有展现政治战争问题的作品,文学作品有一定深度和广度,是空间与情感的高度契合。总之,东晋南朝的浙西航线走向明确、景点密集,文人途径及创作较多。从东晋南朝浙西航线文化遗存以及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上看,东晋南朝浙西航线都是不可忽视的,可称得上东晋南朝文学生产、传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