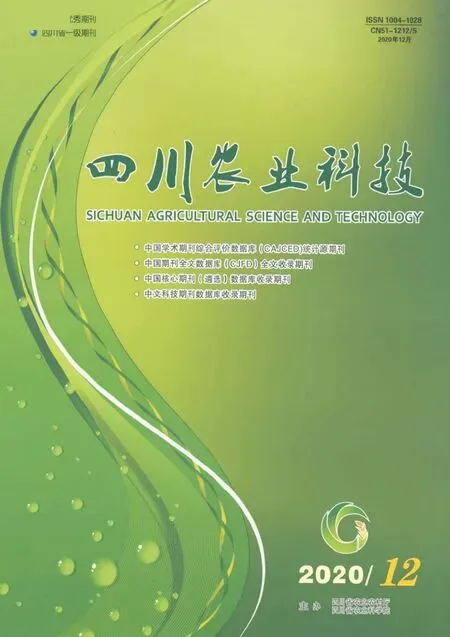科技扶贫项目对贫困户增收与农业增效双重促进效果研究
——基于四川545个科技扶贫项目实地调研
杨 柳,李 镜,杨 宇,姚凌云,陈 兵,张秀琼,谢士娟,王敬东*
(1.四川省农村科技发展中心,四川 成都 610041;2.四川省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41;3.成都理工大学,四川 成都 610059)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脱贫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科技扶贫是我国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点,是实现精准扶贫脱贫的重要举措,是助力产业扶贫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1-2]。科技扶贫产业项目(以下简称科技扶贫专项)作为四川省22个专项之一,其实施现状和效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科技扶贫专项是以政府为主导、科技为依托、农业产业链为载体、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协同共生系统,在推动产业扶贫、切实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和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四川省科技厅以产业科技扶贫和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两大重要抓手和创新举措来推进科技扶贫产业项目。为了深入落实这一抓手,四川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与实践“互联网+科技扶贫服务平台”模式[3],建立“四川科技扶贫在线”来实施科技扶贫产业项目,有效整合区域科技扶贫资源,采用大数据手段扩大科技扶贫服务平台对贫困县乡村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换。
为了准确摸清项目实施现状及其效果,项目组展开了科学的实地调研。2019年7月,课题组依托“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通过发放电子版问卷与实地纸质问卷调研方式对四川省插花贫困区、乌蒙山区、秦巴山区、凉山彝区及高原藏区五个贫困片区实施的科技扶贫产业项目展开了广泛调研。问卷调查覆盖18个地级市(州)104个县的545份有效样本,调查内容包括项目主持单位、项目开始结束时间、项目覆盖产业领域、项目投入经费、项目覆盖的贫困村和人口、项目带动的贫困人口和直接增收、项目的培训次数及项目形成的产值等8个方面。调研共收集到545份有效样本。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对“项目的实施现状情况怎样?项目实施的效果如何?存在问题有哪些?”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以期为农民稳定脱贫和农业产业持续增效提供政策依据。
1 科技扶贫产业项目的实施现状
1.1 从区域上看,科技扶贫产业项目的投入布局突显了瞄准
在调研的545个科技扶贫产业项目(项目支持经费30146万元)中,贫困面广的秦巴山区、贫困程度深的凉山彝区和高原藏区项目数和经费分别占总项目的86%和87%。其中,40万元以下项目、40~60万元项目、60~100万元项目及100万元以上项目数和项目经费占到总项目的85%以上。这说明了我省科技产业扶贫项目在区域上投入上有靶向。然而,调研发现40万元以下的项目占到总项目数的54%,对于周期长和风险较高的农业而言,这种“碎片化”或“撒胡椒面”资助方式并不利于发挥或增强项目的规模效应和持续效应。
1.2 从贫困群体上看,科技扶贫专项的投入布局显现出精准性特征
545个调研项目总覆盖1309个贫困村和近16万贫困人口,平均覆盖2.5个贫困村和281个贫困人口。对于贫困程度相对较轻的插花贫困区和乌蒙山贫困区而言,项目平均覆盖3.2个贫困村和472贫困人口;而就处于深度贫困区的凉山彝区和高原藏区而言,仅仅覆盖了2.1个贫困村和150个贫困人口。40万元以下、40~60万元、60~100万元及100万元以上这4个类型的科技扶贫专项在凉山彝区和高原藏区覆盖贫困村和人口数相对于其他片区更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贫困程度越深,项目平均覆盖面越少和投入越精准,体现了科技扶贫专项在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在贫困村和人口的布局上发挥项目投入的精准性。
1.3 从资源禀赋上看,科技扶贫专项的投入布局体现了产业特色
545个调研项目以扶贫需求为导向和农业特色资源带动为主线,覆盖了粮油、中药材、果树、林产、园艺、养殖、农产品加工及循环立体等四川的8个特色产业,有利于推动“一乡一产”和“一村一品”产业布局。项目覆盖范围集中在养殖和林业等产业链相对较短的产业内,占总项目数的76%和总项目经费的77%。然而,对于产业链长和附加值高的农产品加工和循环立体产业,仅占项目数的18%和项目经费的18%。这表明了科技扶贫专项旨在深度挖掘当地农业特色资源、促进农户与产业深度融合,从而支撑帮扶地区产业发展和脱贫增收,培育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然而,要确保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增强稳定脱贫效果,还需进一步在产业链长、附加值高的农产品加工和循环立体农业上增加投入。
1.4 从主持项目的主体上看,科技扶贫专项项目的投入布局呈多元化态势
贫困地区农民由于其组织化程度较低,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缺乏利益纽带,单凭个体力量难以实现脱贫,这就迫切需要在产业化中协同发展起来的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及科研机构将分散的贫困户组织起来,进行现代化生产。在所调查项目中,合作社或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县级技术推广及高校或科研院所负责的项目数分别占总数的32%、52%、6%和10%,金额分别占28%、54%、8%和10%。这表明科技扶贫产业项目有助于构建“企业、科研单位、合作社+贫困户”等有效带动模式,动员和整合多种力量投入到脱贫工作中,激活贫困户和贫困村发展内生动力和打赢脱贫攻坚战。
1.5 从项目投入时间跨度看,科技扶贫产业项目的投入推进表现了有序
2015~2018年,调查的科技扶贫产业项目投入呈现从递增再到递减的趋势:投入数目从2015年9个增加到2016年164个和2017年210个项目,再从2017年210个减少到2018年162个;投入金额从2015年630万元增加到2016年9340万元、2017年10450万元,再从2017年10450万元减少到2018年9726万元。对于深度贫困地区的凉山彝区和高原藏区而言,投入保持持续增强的态势:投入数目从2015年2个增加到2016年52个和2017年56个项目,再增加到2018年63个;投入金额投入数目从2015年120万元增加到2016年2820万元和2017年2650万元,再增加到2018年4728万元。表明科技扶贫产业项目的推进体现了普适与重点:总体上脱贫区域逐渐缩减而投入减少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性而持续增加投入。
2 四川科技扶贫产业项目的双重效果
科技扶贫产业项目旨在充分挖掘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和契合市场需求,既能增强贫困全体内生发展动力和促进脱贫致富,又能发展壮大特色支柱产业和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由此,从上述2个方面评估2015~2018年4年科技扶贫产业项目的效果。
2.1 减贫成效
2.1.1 从脱贫的经济效应来看,样本项目的效应在执行期间持续增强和区域差异显著 从总体来看,项目直接带动贫困户20943户和贫困人口约59948人,每个项目平均带动了38户和108人。项目直接带动的贫困人口人均收入从2015年419元增加到2016年1062元、2017年2466元,再增加到2018年3704元,分别增加了1.5倍、4.9倍及7.8倍。充分表明项目的效应持续增强。从区域来看,凉山彝区和高原藏区2个深度贫困片区项目的效应相比于其他贫困片区要弱,例如,2个片区在2017年项目直接带动的贫困人口人均收入是1913元和1625元,2018年收入分别是3027元和2427元,均比总体样本在2017年2466元和2018年3704元要低。
2.1.2 从产业领域来看,项目效应呈显著差异 从样本了解到,有关果树、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的产业项目平均直接带动贫困户效应更为明显,分别带动61户、42户及42户,其次是园艺、林产及粮油产业项目,效果较为差的是循环立体和中药材产业。另外,项目直接带动贫困人口人均收入较高的产业是农产品加工、园艺、果树产业。2018年,3个产业项目带动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分别达到4874、4252和4246元。其他产业项目带动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在2018年也达到了3000元以上。揭示项目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有效集合各种科技资源,促进产业创新发展与贫困户脱贫紧密结合,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的特色之路。
2.1.3 从项目主持主体来看,项目的效应也出现明显差异 作为农户直接参与的合作社或家庭农场所主持的科技扶贫产业项目平均直接带动52户贫困户和120个贫困人口,其次是以公司、县级技术推广站为项目主持单位,较差的是高校或科研单位,平均仅仅带动了24户。然而,高校或科研单位所主持项目直接带动的贫困人口人均收入相比于其他主持主体表现强劲,2017、2018年分别达到了2853元、4216元,均显著高于2017年的平均值2466元和2018年的平均值3704元。这说明尽管以高校或科研单位主持的产学研项目更能增强农户的收入效应,但是农户参与度低。
2.1.4 从社会效应来看,样本项目在执行期间不断增强内生动力和提高吸纳就业水平 从调研数据了解到545个项目共组织培训次数达到8216次,贫困户参加项目培训达到137182人次,吸纳贫困人口就业达到了50337人;平均培训次数15次,252人次参加培训项目,吸纳贫困人口92人就业。这些培训旨在使农户掌握农村实用技能和使农户对新技术、新品种有具体科学的了解,在主观上消除风险。不仅为贫困户提供切实有效的脱贫技能培训服务力,而且提高了贫困户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创业和就业能力。
2.1.5 项目的社会效应由于区域、产业及项目主持主体不同体现出明显差异 作为深度贫困片区的凉山彝区和高原藏区覆盖的项目产生的社会效应相比于其他3个贫困片区要弱。2个片区项目平均培训次数分别是9次和8次,培训贫困人口160人次和148人次,吸纳就业46和52人,都显著低于这5个片区的平均值。从产业来看,培训次数、参加培训项目人次及直接带动就业人数较高的项目主要集中在粮油、果树、林产及养殖等产业项目,而对于产业链长和附加值高的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在这三方面的社会效应要低。从主持项目主体来看,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和公司平均每次培训分别是23和13人次,直接带动就业分别是73人和126人,而县级技术推广站和高校或科研单位每次培训达到30人次以上,直接带动就业均在20人左右。
2.2 增强农业产业能力
2.2.1 科技扶贫产业项目有助于撬动经营主体扩大生产规模的投入 项目主持主体在确保扶贫任务前提下,积极主动地把产业扶贫项目与主体自己的发展项目相结合来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强科技投入。从调研中发现,省级科技扶贫产业项目经费(78.8%)平均撬动项目主持主体自筹经费投入达到21.0%。其中,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和龙头企业自筹经费分别占18.9%和占28.2%,而高校或科研单位或者县级技术推广站可能以技术支撑或入股显得自筹经费占比非常少,分别占2.6%和0.2%。农产品加工和园艺产业的科技扶贫产业项目撬动自筹经济比例较高,分别占28%和26%,其他产业自筹经费比例均在20%左右。
2.2.2 科技扶贫产业项目有益于新技术推广和研发及培育新品牌 调研发现,545个项目在执行期间共研发示范新品种1075个(平均1.9个),推广新技术1260项(平均2.3项),研发新产品485个(平均0.9个),培育新品牌188个(平均0.3个)。从项目主持主体来看,龙头企业和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分别培育了118个和59个新品牌,分别占总63%和31%,其他2个主体仅仅占6%。然而,高校或科研单位和县级技术推广站所主持项目平均研发示范新品种分别达到了2.6个和2.8个,而龙头企业和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平均研发新品种分别仅达到1.7和1.9个。这表明科技扶贫产业项目的确有助于新技术推广和研发及培育新品牌,但是科研单位与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在研发与转化还未达到有效衔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生产力。
2.2.3 科技扶贫产业项目有利于逐渐增强农业产业产值 从总体来说,项目平均形成农业产值从2016年267万元增长到2017年549万元,再增长到810万元,分别增长106%和203%。作为深度贫困片区,凉山彝区和高原藏区的农业产值分别也从2016年177和33万元,增长到2017年305和112万元,再增长到2018年487和167万元,但相对于其他贫困片区,产值增效差异明显。其次,以农业龙头企业主持项目形成农业产业产值远远高于其他主体,从2016年453万元增长到2017年933万元,再增长到2018年1351万元,增长了107%和198%。具有农业产业链长或农产品附加值高的农产品加工和循环立体产业的农业产值增长量高于其他产业,分别增长到了2018年1107和2657万元。揭示项目在形成以龙头企业为主导和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导的产业链的基础上,实现农业产业经营的同时对接农业产业链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效农业产值。
3 经验启示与建议
尽管当前四川省科技扶贫产业项目的实施体现了精准、特色与多元,在减贫上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在推广农业产业新技术和培育特色产品品牌方面上延长产业链和形成了产业产值。不过,项目的实施也出现了亟需解决的问题。另外,伴随着从解决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方向转移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项目的实施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4-6]。基于此,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丰富与拓展。
3.1 科技扶贫产业项目的实施进一步突出凉山彝区和高原藏区导向
作为深度贫困片区,凉山彝区和高原藏区存在处于民族地区、贫困持续的时间长,贫困程度深,致贫因素复杂,农业产业基础差等问题[7]。这些问题使2个片区的项目在实施进度、减贫成效、增强农业产业力等方面的效果和难度相比于其他3个片区要弱和大。从任务紧迫性来看,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剩余的攻坚任务都是贫中之贫、坚中之坚。由此,继续重点加大对凉山彝区和高原藏区两个深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加快产业项目扶贫支出进度和项目实施进度,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期目标。
3.2 科技扶贫产业项目的实施进一步突出产业融合发展导向
调研样本表明,作为产业链长和农产品附加值高的农产品深度加工产业和循环立体产业项目在直接带动贫困户增收和增强产业值上取得的成效明显好于其他产业的项目。然而,2个产业项目和金额仅占总数的18%,不利于农民持续增收和稳定脱贫,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和延长产业链。由此,科技扶贫产业项目以提质增效为重点,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溢出效应,提升农业技术水平,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辐射带动农业农村发展,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和稳定脱贫,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3.3 科技扶贫产业项目的实施进一步突出利益联结机制导向
尽管样本数据反应项目平均培训次数15次,252人次参加培训项目,吸纳贫困人口92人就业。但是,实地调研发现一些项目培训仅停留在表面任务和应付交差上以及贫困户就业也不稳定,不利于贫困人口持续增收和稳定脱贫,反而使扶贫资源被新型经营主体获得,通过“渗漏效应”到达贫困人口手中的资源不足以带动他们稳定脱贫。由此,建立可以既从数量上也从质量上考核产业扶贫项目涉及的“龙头企业+贫困户、合作社+贫困户、家庭农产+贫困户”等模式的长效利益联结机制。
3.4 科技扶贫产业项目的实施进一步突出产学研融合导向
要延长农业产业链和做强主导产业,需集聚科技资源,促进农业科技成果集成转化,培育农业高科技产业,通过试验示范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走农户稳定增收和农业持续增效之路。然而,样本数据发现龙头企业和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分别培育了118个和59个新品牌,分别占总63%和31%,其他两个主体仅仅占6%。然而,高校或科研单位和县级技术推广站所主持项目平均研发示范新品种分别达到了2.6个和2.8个,而龙头企业和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平均研发新品种分别仅达到1.7和1.9个。表明产学研还未更有效结合,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还有很大的空间,未完全突破农村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瓶颈。由此,项目需加强科研单位与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在研发与转化的有效衔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