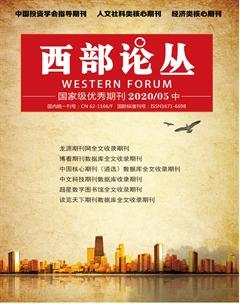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绩效的行为特征及其测度
陈潇潇
摘 要: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研究和高科技前沿领域原始性创新的主要来源。由于目前我国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还未建立,研究型大学担负起了科技创新主力军的角色。在研究型大学建设的过程中,国家和地方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结合国内外研究文献讨论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在科技创新绩效涵义阐述的基础上,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和学校建设投入的角度分析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活动的特征和科技创新绩效的测度。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绩效;测度
创新是国家繁荣发达的助推器,是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体现。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世界各个国家都在抢占创新竞争的制高点,纷纷提出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而这其中科技创新能力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能否产生科技创新绩效已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在未来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力量,是人类进行基础研究、探索未知世界的主要阵地,是高科技领域内原始性创新的主要来源,也是培养创新性人才的主要基地。近年来,为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需要,我国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一、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国外关于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作用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Wolszczak和Parteka利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德国56所大学七个不同科研学科领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德尔菲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探讨了研究型大学中不同学科领域中论文的引用率与其研发经费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科研经费的增长速度与论文的增长率和论文引用率的增长速度之间是近似相等的,而科学研究发展所获得的收益在选取的每一件案例中几乎都是成规模报酬递减的。Johnson W.分析了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溢出效应,得出的结果是研究型大学的科技研发活动对于创新知识的溢出具有推动作用。Lee Y.S.和Leydesdorff L.应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研究型大学的创新效率,并得出研究型大學与其所处的区域创新环境之间具有正向的相关关系,并且相互促进创新,能有效的改善区域创新环境。McQueen D.H.和Wallmark J.T.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对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生产和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出进行测量,选取专利申请数量和成果获得国家级的奖项这两个评价指标,运用的测量方法为后续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关于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Etzkowitz和Leytesdorff提出了“三重螺旋”理论。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指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紧密联系,相互合作,共同促进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三螺旋理论”理论的观点是,知识创新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模式,在该模式中,各创新主体,即大学、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相互之间的交叉互动日益增强,功能相互重叠,政府、企业和大学在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市场经济作用下,交互合作,呈螺旋状上升,促进整体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该理论并未刻意强调在政府、产业界和大学这三种力量谁是创新主体,而是重在指明三者的协同合作关系,彼此互惠互利,推动国家创新系统螺旋上升,为它们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创造新的价值,在区域内发挥更强的技术创新辐射作用,是创新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尝试、新范式。
国内对于国家创新体系中研究型大学所起作用的研究成果也是颇为丰富的。马瑞敏和张欣在构建中观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成果评价的基础上,对中国778所本科高校的创新型人才和成果进行了评价研究,着重从“平台”、“区域”和“类型”三个方面对中国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和成果分布情况行进了整体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和成果在“平台”、“区域”和“类型”三方面均呈现分布不均匀的情况[1]。赵蓉英和陈必坤在RCC发布的“2012年中国高校创新指数”的基础上,选择其原始数据对中国大学的综合创新能力进行深入分析,在对大学类型和省份分布划分的前提下,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和创新投入和产出、创新效益的排名[2]。李丽莉和张富国探讨了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创新性人先所起的关键作用。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总结出当前我国大学创新型人才流动的趋势与特点,分析了大学创新型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阻力和流动成本,进而从政策层面、单位层面、个人层面提出促进大学创新型人才合理流动的对策建议[3]。刘军探讨了创新型经济下大学的创新行为,认为科学、合理、准备地把握大学在创新型经济尤其是在协同创新中角色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创新型经济下大学的创新模式主要有:大学参与协同创新存在的利益分配、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利用和孵化、机制和体制建设等。而针对“三螺旋理论”,我国学者近年来也进行的较多研究[4]。佟林杰和孟卫东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三螺旋创新系统的内容,分析发达国家在三螺旋系统构建中存在的风险和误区,对发展中国家构建和改进三螺旋创新系统提出了参考建议[5]。叶柏青、贾雪和黄金鑫基于2009-2013年我国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的检索数据对官产学三螺旋的关系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在三主体合作方面,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均形成了稳定的三螺旋关系,发明专利的自组织性更高,三重螺旋关系更加紧密[6]。
二、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活动的特征
(一)科技创新绩效的涵义
“创新”一词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的《经济发展理论》,其创新概念包含的范围很广,涉及到技术性变化的创新及非技术性变化的组织创新。而经济发展至今,创新赋予了新的内涵,它是指无效资产和有形资产从研究开发到投入生产、到现实产品的应用,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社会经济生产能力的大幅上升的过程。
科技活动本身无法直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它必须通过创新活动才能产生经济社会价值。因此,从国家创新系统的角度来看,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创新活动是指以大学的自由科技研究人员为研发主体,整合来自政府、企业的物质资金和信息资源,进而科技知识的创新、技术的研发,并通过市场作用,借助合约等媒介手段进行市场交易,通过建立大学科技企业、大学科技园等渠道,实现科研成果(如申请的专利)的产业化和商品化,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具体的科研活动包括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科研研究与试验发展;科研成果应用于转化;建立校企联合产业、经验大学科技园等。而衡量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创新绩效可以从科研投入产出比例,以及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效率两方面进行考察。
(二)科技创新活动的特征
目前对大学可以按照其职能属性划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以及教学型。通常研究型大学更加注重与基础的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并且作为国家的知识库,为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世界一流的高校作为科研创新任务的主要承担者,肩负着探究未知领域和解决未知世界的任务,因此需要掌握高端知识的创新型人才,并将成为优秀科研人员和创新成果的聚集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型大学就不重视科研教学活动。恰恰相反,研究型大学由于其创新认为的艰巨性,更需要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强调教学相长,强调培养和挖掘学生的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需要师生在教学中相互启发,不断推动学校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出。此外,研究型大学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良好的创新氛围,加之社会认可度的不断提升,在创新网络里有着其他主体无可比拟的科研优势。
在学校建设投入上,研究型大学由于其历史定位问题,能够获得相对较多的政府研究项目和政策支持,同时还能获得社会机构、校友会等多方的力量援助,进而拥有较高的科研发展平台,形成资金和科研实践的良性互动机制。其次,研究型优秀的学术环境吸引的世界各地顶尖的创新人才和专家学者,而这些创新人才积累的学术声誉和再创的科研成果又为研究型大学提升了在国家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度,在更大程度上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与科研主力的加盟,客观上促进了研究型大学创新成果的诞生。另一方面,优秀的人才带来高质量的科研项目以及更多的资金支持,不断提升研究型大学的创新环境。
三、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绩效的测度
国外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创新多是以绩效的评定为主。其中,英国的大学科研评价体系(Th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就是欧洲最先进的大学科研创新评价体系之一。该体系主要是以大学的科研水平和研究型的教育质量作为衡量标准,并且与研究型大学获得的科研资金直接挂钩。而美国的大学科技创新评测系统中,最著名的是弗罗里达大学的“全美最佳研究型大学年度评价报告”,自2000年起,每年由该校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颁布。该评价系统共包含九项指标,具体分为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获得科研经费总额、用于国家院士的数量、联邦科研经费数、国家级奖项获得情况等,是全国公认的权威评价机构,具有半官方性质。除此之外,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如英国的RAE那样的机构或颁布创新绩效评价指标,并将评价结果与政府对高校的科研与教学拨款进行直接挂钩,以促进公平竞争,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大学创新能力和教学质量的目的。
目前,对于大学科技創新绩效的评价方法多以定量的计量分析为主。1962年和1963年,被称为美国“科学计量学之父”的科学家普赖斯先后发表两部著作,《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和《小科学,大科学》,开创了科学定量分析之先河。文献计量分析的依据以专利、专利的引用和发表论文和论文的引用为主。在创新能力的分析上,多是以申请的专利数、创新产品生产的数量为依据。在评价模型的研究方面,首推的是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它是由美国匹兹堡大学运筹学家T.L.Saaty教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用于多目标决策的研究方法,该评价方法一经发表,迅速在实践中获得了推广和应用。在此基础上,美国运筹学家查姆斯教授和库珀教授发明了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用于评价具有多投入和多产出属性的研究对象的绩效水平。
国内学者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较为丰富。而针对于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绩效的评定的探索与研究开始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第一次提出要评估高校的办学水平。1997年12月,《中国高等教育评估》杂志上列出了中国最佳大学30所,这是国内第一次大学综合排名;2000年至今,网大科技有限公司连续在国内发表了大学排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单位也相继开展了大学评价工作。大学是一个复杂的知识系统,涵盖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培养创新人才以及服务社会等的职能,因此对于其创新绩效的评测是创新评价领域的一个研究难点,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创新绩效。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创新绩效展开评价的指标系统,现有的评价对象都是整体高校,而且评价的内容是高校的综合实力。迄今为止,关于高校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约有十余种,但是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围绕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指标评价大学的科研能力;从科研投入、科研生产过程以及科研产生综合评价高校创新绩效;以及分析大学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这三个方面。如刘志迎、单洁含选取了13所大学及与之协同创新的191个企业为样本,用大学——企业联合申请的发明专利数作为测度两者协同创新绩效的指标,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技术距离、地理距离对中国大学——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距离对大学——企业协同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理距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正效应大于负效应[7]。李栋华等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企业创新知识生产函数进行评测,发现企业从大学等研究机构获取的知识存在严重浪费的现象[8]。但是这些方法只是考察的在特定情形下,大学创新绩效的一个方面,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降低了评价结果的信服力。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关于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绩效方面的研究文献比较全面的介绍了研究型大学整体创新水平或者是某一特定方面的创新绩效,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提升大学创新绩效的发展方向。但是,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改进。
第一,从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看,研究型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最高级别,但是其发展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较多的研究文献是关注大学整体状况,研究型大学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已有的不多关于研究型大学创新绩效的成果中并没有对创新绩效评价指标的选取达成共识。已有的大学绩效排名更多的是考虑综合水平,较少关注科技创新绩效。此外,在理论上,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绩效的理论研究还很欠缺,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机理和模式的研究,国内大学如何因应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实现科技经济一体化,如何促进知识产业化、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等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二,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国内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绩效评测方法种类较多,但各有利弊。主要采用的是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但运用的较为传统,没有对于DEA有效的大学作出进一步的对比分析。
第三,针对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绩效的提升策略研究,也不够全面,较少有文献探讨影响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效率值变动的原因,没有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绩效值变动的机理。作为对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绩效研究的延伸,需要在绩效排名的基础上,探讨现状的不足,明确影响因素,为提高我国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 马瑞敏、张欣、彭茜,中国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与成果分类分层研究,科研管理,2019(1):88-95.
[2] 赵蓉英、陈必坤,2012年中国高校创新指数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0):67-74.
[3] 李丽莉、张富国,高校创新型人才流动问题及对策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1(2):77-80.
[4] 刘军,创新型经济下的高校创新行为与创新模式,开发研究,2019(5):19-24.
[5] 佟林杰、孟卫东,发展中国家三螺旋创新系统构建探论,理论导刊,2020(5):61-69.
[6] 叶柏青、贾雪、黄金鑫,我国官产学三螺旋关系测度研究,商业研究,2016(10):33-39.
[7] 刘志迎、单洁含,技术距离、地理距离与大学—企业协同创新效应——基于联合专利数据的研究,科学学研究,2015(9):200-213.
[8] 李栋华、顾晓敏、任爱莲,知识来源于企业创新:基于DEA的研究,科研管理,2020(2):27-38.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视角的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绩效研究”(项目编号:2018SJA093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