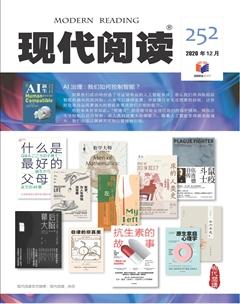粮票故事
粮票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中国最早实行的票证种类是粮票、食用油票、布票等。粮票作为一种实际应用的有价证券,在中国使用达40多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粮票,从我记事时开始,就是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从古到今,不论中外,都有粮票一说,不知道那是物质匮乏的产物。
上大学以前,但凡与粮食沾边的,都要粮票,光有钞票,恐怕就得饿死。那时有粮站,专司粮食供应,从那里面出来的,当然得要粮票,过年时才供应的赤豆、绿豆也要。没粮票下馆子是不成的,又有一些加工过又非即食的食物,像饼干、蛋糕之类,在副食品商店里卖的,没粮票也不行。
粮票还有高下之分,全国粮票可以走遍中国,地方粮票则只在某个地区管用,江苏粮票到了上海就无效。各个地方粮票的单位还不一样,比如江苏粮票,最小的单位是一两,上海则还有五钱、二两五的粮票。由全国、地方之分,衍生出一系列的比喻,比如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就分别被比为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按粮油证领来的似乎都是地方粮票,我父亲算部队的人,部队里发的则是全国粮票。
亲身体会到二者的高下,已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地方”“全国”无关的,是不同身份的人,粮食各有定量。学生较工人要低,每个月28斤,班上有位从工厂考来的,原先的定量近40斤,此时肚皮并未因体力劳动转为脑力劳动而见收缩,遂大闹饥荒。另一方面,只要同一身份,粮食定量又是不论性别都一样的(这应该算是男女“同工同酬”政策的延伸吧):那男生是不够,一般女生则粮票决计用不掉。这方面并无什么宏观调控之举,只能是私下互通有无,那男生便以目测饭量特小的女生为对象,实行赎买政策,被选中的女生便有意外之喜,因额外来了零花钱。
事实上,这时候粮油管制已渐渐开始松动,有些地方,买吃的没有粮票也可以通融,通常是多出两分钱,就可免一两粮票,好多人粮票都有富余了。就有农民拿农产品进城换粮票。没城镇户口的人没粮票,这我知道,农民换粮票做何用,我却不知道。只知道最常见的是拿鸡蛋换。下午、傍晚,学校宿舍区里农民弄一筐鸡蛋挨着宿舍问有无粮票换是当时校园宿舍的一景,自由贸易,小有讨价还价,最终的结局总是“双赢”吧。
后来可换的东西就多了,钢精锅、塑料盆、脸盆架、痰盂、毛巾等等。通常是在路边摆一地摊,规模大的品种多,摆开一大片,甚至并非路过的人也会专程跑来换东西。照这情形,粮票已是有价证券,这样的交易却不叫“买”,还称“换”。有次在离家不远处碰上这样的摊子,看到一塑料小书架想买下。索价二百多斤糧票,我是路过,身上哪有这么多?便问可否用现钱买,摊主不干,一定要用粮票换,害我骑车飞奔回家去取。
其时还有一教师模样的中年人在和摊主讲价,而书架只有一个。待我取了粮票回来,那中年人的讲价还在继续,不过价码显然已升了。小贩见我当真携了粮票回来,态度立马强硬。听起来颇像是竞拍的雏形了,其实不是,小贩一见我手上是全国粮票,立马宣布东西归我了,其实那中年人出的价还高些。我庆幸自己干脆反而占了便宜,我的竞争对手却说道:“你亏了!你那可是全国粮票!应该多算好几十斤哩!”
记得有一阵,疯传粮票要取消了,粮票换东西的小摊子似乎越发轰轰烈烈起来,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过一段时间,没什么动静,我们家的老保姆很肯定地辟谣说,没粮票还得了?那不跟建国前一样了?——这可能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过不用粮票的时候。
但是老保姆的经验主义这次没管用,忽一日,悄无声息地,粮票当真取消了。可能是有了很长的铺垫吧,记得此前的一段时间,一些私人开的小饭馆已开始拒收粮票,只认钞票了。而过去每家每户视同命根的粮证早就失去了重要性,小时时常被大人差遣去粮站买米兼领一月的粮油票,渐渐地好像根本没这回事了,买米居然可以不去粮站!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去今未远》 作者: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