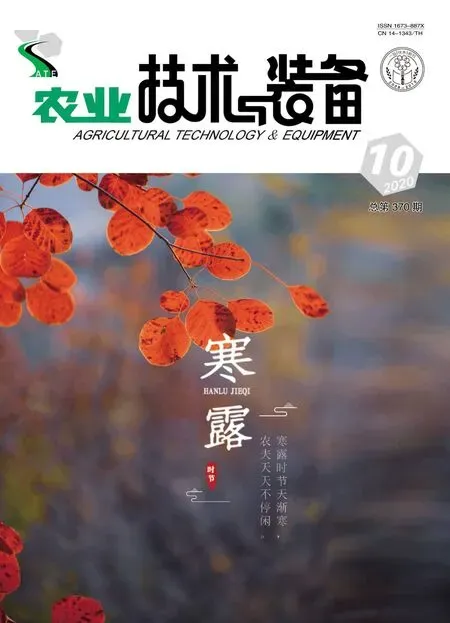食源性克罗诺杆菌污染防治策略的研究进展
梁安莉,温桂珍,谢 斯
(广西民族大学 相思湖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8)
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母乳是婴儿的最佳食品。然而,无法得到母乳喂养的婴儿和新生儿则需要使用重组婴儿配方奶粉(配方奶粉)替代母乳。配方奶粉需要满足“婴幼儿配方奶粉卫生规范”(CAC/RCP 66-2008)的国际微生物标准。据报道,尽管配方奶粉是一种脱水产品,其水活度(aw)为0.25~0.35,不利于大多数微生物生长,但仍有一些案例表明,受污染的重组配方奶粉与婴儿和新生儿的克罗诺杆菌感染有关[1]。
克罗诺杆菌被认为是导致新生儿和婴儿脑膜炎、败血症和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的致病病原。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克罗诺杆菌引起的感染致死率为27%。存活下来的婴儿经常出现神经系统后遗症,如四肢瘫痪、脑积水和神经发育迟缓。自1961 年两例由克罗诺杆菌引起的新生儿感染病例被报告以来,到目前为止,全球新生儿和幼儿中约有120~150 例克罗诺杆菌感染病例[2]。配方奶粉的克罗诺杆菌污染可能来源于原料和生产过程,有报道指出克罗诺杆菌来源于植物,如蔬菜、药草和香料等[2]。除此以外在许多非生物来源中也分离到克罗诺杆菌的存在,包括食品加工生产环境、生产设备,冲调奶粉的器皿等。研究报道指出,克罗诺杆菌可以耐受高温和干燥,这是由于克罗诺杆菌具有形成生物膜的能力[3],这为细菌在不同环境存活提供了物理上的阻隔和保护,同时也使其很难用传统的防控防治方法进行完全灭活,例如食品加工中常用的热处理、渗透压、饥饿、清洁剂、抗生素、消毒剂和消毒剂等[3]。
国际食品微生物学规范委员会(ICMSF)也将克罗诺杆菌描述为“能够对受限制人群造成严重危害、威胁其生命或导致长期严重的慢性后遗症的致病菌”。由于克罗诺杆菌感染的严重性,有必要根据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制定的指导方针和建议,制定严格的防控措施,以降低食品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风险[4]。
研究控制食源性病原体的生物防治措施已成为热点。迄今为止,针对克罗诺杆菌生物防治的研究方法较多,诸如使用植物源性化合物、益生菌、噬菌体和具有拮抗作用的代谢产物等生物保护剂。因此,本文主要综述各种克罗诺杆菌防治方法,为控制食品中克罗诺杆菌,确保食品安全提供参考[5]。
1 食源性克罗诺杆菌污染防治策略
1.1 益生菌和益生元
一些分析说明乳酸菌(LAB)组的益生菌可以作为控制克罗诺杆菌的生物控制剂,在体外和体内模型中,发现了益生菌或其废培养基可有效抑制克罗诺杆菌生长。有研究报告了在克罗诺杆菌定殖之前,益生菌菌株会先在人体肠道黏液层定殖从而降低了克罗诺杆菌的黏附能力。在与发酵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和酸乳杆菌共培5 min 后,克罗诺杆菌活细胞计数减少了50%。尽管益生菌细菌素(GRAS)被普遍认为是安全的,但这些蛋白质的不耐热性质不适用于脱水配方奶粉的生产。而据最新研究,从嗜酸乳杆菌Er2 317/402 株(一种从新生婴儿粪便中分离出来的菌株)培养滤液中提取的有机酸能够抑制克罗诺杆菌的滋生。这是由于未解离的酸分子迅速进入克罗诺杆菌细胞,导致细菌细胞质膜解体[4、6]。
除了益生菌或其上清液的纯培养物能抑制克罗诺杆菌的滋生,混合培养物也可以抑制病原体。研究表明Kefir(发酵乳制品含有未定义的微生物群)上清液具有抑制克罗诺杆菌的活性。据报道,在复原乳配方奶粉中,当浓度为30%~50%时,Kefir上清液可完全抑制克罗诺杆菌的生长。另外一项研究报道了含有多个LAB 和双歧杆菌菌株的Kefir 奶制品和酸奶可抑制克罗诺杆菌的活性。在所测试的产品中,Kefir 型奶制品(pH 值为4.5 的温和型和pH 值为3.6 的强型) 比酸奶型(含有LAB 或LAB 双歧杆菌的组合)对抑制克罗诺杆菌更有效,在4℃下储存1~5 d 内持续抑制病原体。这些研究中的抑制作用可归因于几种生物活性化合物,如产品中存在的微生物(活的或死的)、来自食品基质的分解产物(肽)和微生物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代谢物,如有机酸、多糖、细菌素等等[7]。
近年来,益生元被描述为一种可食用食品添加剂,通过影响细菌对胃肠道(GIT)的黏附性,来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此外,有研究认为益生元可能对克罗诺杆菌的肠道黏附有抑制作用,因此益生元可防止和降低克罗诺杆菌的感染。益生元,特别是聚葡萄糖(PDX)和低聚半乳糖(GOS)已被报道单独或联合使用对克罗诺杆菌产生抗黏附作用,并在最初感染阶段直接降低该病原体对Hep-2 细胞系的黏附。16 mg/mL 的GOS 显著降低了克罗诺杆菌对上皮细胞壁的黏附。GOS-PDX(8 mg/mL)的混合物可使病原体黏附性降低48%。乳聚糖是另一种潜在的益生元来源,它能够通过乳低聚糖(OS)与宿主细胞表面的碳水化合物配体(作为细菌粘附的受体位点)的结构相似性来干扰致病细菌对肠道上皮细胞的附着[8]。
1.2 生物活性肽及乳制品衍生成分
不同来源的哺乳动物乳以及乳的衍生物成分包括糖脂、糖蛋白(如乳铁蛋白、黏蛋白、免疫球蛋白等)、乳过氧化物酶系统和低聚糖,除了具有营养作用外,还具有其他几种促进健康的特性。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化合物对克罗诺杆菌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据报道,牛初乳含有许多生物活性成分,如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 和II(IGF-I 和IGF-II)、溶菌酶、乳过氧化物酶、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在HEp-2 细胞中评估了牛初乳组分及其超滤(UF;<10 000 Da)、纳米过滤(NF;<1 000 Da)液和纳米过滤滞留物(1 000-10 000 Da)对克罗诺杆菌的黏附抑制作用[9]。该研究报告了牛初乳组分在最低浓度为10~20 mg/mL 的UF和40 mg/mL 的NF 保留液时,对克罗诺杆菌的黏附抑制率为99%,NF 保留物对克罗诺杆菌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除牛乳外,生骆驼奶和巴氏杀菌骆驼奶在25℃条件下,可使克罗诺杆菌的生长降低0.6%和4.6%,在37℃下则分别降低5.1%和10.5%[10]。高水平的热稳定抗菌成分可能是抗克罗诺杆菌活性的重要因素,加工过程中的热处理可导致蛋白质的特定去折叠,其可能与细菌表面相互作用,形成抗菌脂肪球随后与美拉德反应代谢物反应,从而导致细菌细胞膜损伤[11]。
1.3 噬菌体
食源性病原体中抗菌药物耐药性个体的出现推动了噬菌体(感染细菌的病毒) 的应用。从第一个基于噬菌体的产品(LiestShiedTM)获得批准后,2006 年为了解决肉禽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的污染问题,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了一批噬菌体产品[12]。一些报告描述了噬菌体作为生物控制剂在食品加工单位和后加工过程中控制克罗诺杆菌污染的潜力[13]。一项研究表明在高浓度(109 pfu/mL)的克罗诺杆菌污染的配方奶粉中使用特异性噬菌体实现了对克罗诺杆菌属菌种的完全抑制。另外,在食品中用作生物防治添加剂的噬菌体必须是完全可溶解的(非温带噬菌体),且不含编码细菌毒性因子的基因。因此,在将噬菌体应用于食品之前,需要考虑大规模量产噬菌体作为食品添加剂的方法和噬菌体应用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2 结语
尽管现在食品加工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从食品中彻底消除食源性病原体仍是当前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目前,消费者对安全、优质、理化加工少的食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促使食品科技人员寻找替代生物方法来控制病原体。本文综述益生菌和益生元、生物活性肽及乳制品衍生成分以及噬菌体在抗食品克罗诺杆菌污染中的应用和研究进展。然而至今为止没有一种单一的方法能够实现在食品中对克罗诺杆菌的完全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