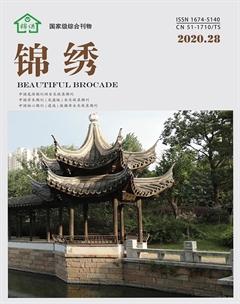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意义
摘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十条,马克思写道:“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市民社会是以原子式的个人为前提,由于个人私利无法消除,致使彼此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与斗争,黑格尔甚至直言不讳地宣称市民社会的本质就是“个人私利的战场”。作为以市民社会为载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所流露出来的缺陷可以说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虚幻的共同体”,并具有极强的愚惑性和伪装性,成为贫富分歧、宗教冲突以及社会动荡的滥觞。因此,马克思提出建立“人类社会”的构想,以全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起“真正的共同体”。而目前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活动则正是响应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的举措,为实现从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之间的转换,解决当前世界治理危机提供了最佳方案。
关键词:市民社会;人类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以市民社会为载体的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种种问题,从发展不平衡到地区动荡,从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到全球生态危机,从宣扬全球普世到独权霸政,全球问题呈现集中爆发的态势。资本主义主宰的“虚幻的共同体”不仅难以解决这些问题,甚至是这些问题的创造者,成为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阻碍。这一时代所衍生的更深层次的问题给了我们一个严峻挑战,那就是人类如何共同生活?如何在一个新的高度,没有暴露当前问题的新世界共同生活?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经验同目前全球面临的危机挑战进行考虑,创造性的提出了符合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思想的倡议活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复杂多变的全球社会形势与人类的共同命运结合起来,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对人类发展美好未来的理念和立场,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市民社会:虚幻的共同体
“市民社会”理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名著《政治学》,是指由民众组成的城邦国家,不过在那时,市民社会与城邦国家是并为一谈的。直到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摧毁了这种混合的政治发展模式,致使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分裂,才出现了现代社会基础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理念。马克思在其一生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及到市民社会,那么什么是“市民社会”?早期,马克思对这一理念的认识源自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细致地论说了“市民社会”的具体内容,他写道“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黑格尔指出,在市民社会阶段,独立的人们为了得以生存不得不结成一定的关系,但是在这一关系中,每个人都以利己为目的,存在着欲望和需求,黑格尔将这种关系看作是“私人需要的体系”。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下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与黑格尔表达的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马克思专心研究“市民社会”理论是因为在报社工作时对现实遇到的问题的不解,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入手的,一方面对黑格尔在书中阐释的思想给予了认可,另一方面又批判其对这一思想的错误认知。黑格尔在书中认为当市民社会出现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国家来充当其管理机制的补充,所以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国家是决定市民社会的,但是由于当时马克思所处的历史环境,普鲁士政府的作为让他怀疑黑格尔对于这两者的决定关系,并对此理论进行了颠覆,认为市民社会应该决定国家。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原动力、国家的前提,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能存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是站在哲学与现实的角度上展开的。随后,马克思写作《论犹太人问题》时,进一步认识了市民社会思想,他寫道:“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从这可以看出来,他对“市民社会”的理解认为个人对他人进行欺压,国家对个人进行掌控,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并且这一时期对该社会形态的认知已经向“资产阶级社会”靠近。随着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逐渐形成,对“市民社会”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认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在这里他开始运用经济学来解读市民社会的内在逻辑和本质现象,使其内涵具有双重性的新的解释:一是书中所提及的抽象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用这两方面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界定市民社会;二是具体的“市民社会”,即将这一社会形态看成是“资产阶级社会”。
根据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思想的阐述,可以得知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处处勾心斗角,以私利为目的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且与市民社会相对立的政治国家也用一套虚假的理论实践来控制社会,对其产生负面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以市民社会为利益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就是一个纯粹的、十足的“虚幻共同体”。资产阶级吹嘘自己是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的,并把这种行为美化为“普世价值”来“普惠”天下,但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只会成为贫富分歧、宗教冲突以及社会动荡的滥觞。所从,市民社会仅仅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而非普遍的人类利益的代表。马克思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这种以虚假性为本质的市民社会,提出建立“人类社会”的构想,以促成社会的全面解放为最终目标,建立起“真正的共同体”。
二、虚幻的共同体转向真正的共同体:人类社会的构想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六条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原始时代开始,人就是群居生活在一起生活的动物,人是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人的存在意义只有在社会环境中即在共同体中才能得以表现出来,没有共同体也就没有“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深入推进和分工的持续扩大,人与自然构成的关系即“人的依赖关系”被打破,代而取之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以商品交换的形式来满足自身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成物与物交换的间接形式,人的本质被物所奴役的社会,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认为这种被物所奴役的社会不仅对人的本质进行了亵渎,同时也对社会的全面发展造成了妨碍,这就需要一种能够超越当前社会形态并且能体现人的本质的共同体来取而代之。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通过政治解放使单一的政治国家生活分离开来,但是不彻底,政治解放仅仅让人们获得了政治层面的虚假的自由,市民社会中的人仍然受制于他人,受制于物。而只有站在人类立场上的解放才能从根本上抹去人与物、人与社会之间的对抗,人的本质才能最全面、最大化的彰显出来。并且这次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解放所要建构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预示了未来人类解放后所要建立的人类社会的面貌,他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正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社会,是“真正的共同体”。
关于“真正的共同体”,未来的人类社会是什么样子的,马克思对此并没有作出详细的描绘,而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对人类社会进行宏观上的展望。他认为未来的人类社会应具备以下基本特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对于这样的描绘,我们可以看出未来的人类社会在经济上为了使消费资料按需分配,不仅在生产力上要得到极大发展,而且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实行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同占有的制度,由此便可以克服市民社会中生产者与其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异化性和社会的异己性。而公有、共同占有是人类社会的实质和核心,人类社会就是在公有制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人们共同生产的结果。其次,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本质可以最好地呈现出来,人们不再受制于金钱、欲望的存在物,可以摆脱被物的奴役状态,让自由自主的活动成为人存在的全部意义。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有工具性,取而代之的关系是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关系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马克思所构想的“真正的共同体”就是未来的人类社会。
今天的世界离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社会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思想正在逐步由理论走向实践,其最为直接的继承与发展就是当代中国正在推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活动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哲学上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类社会”“社会的人类”概念,正是基于这一哲学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市民社会为载体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最大公约数建立一种“真正的共同体”,为走向人类社会指明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连接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桥梁
针对目前市民社会所显现的种种问题,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这种社会形态并不适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他认为应有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来替代,提出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即人类社会,在这个人类社会中,人可以得到最大化的发展,社会能够获得极大的进步,人类最终走向以人的存在意义为出发点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而中国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活动就是从“市民社会”走向“人类社会”的现实出路。
2012年11月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大会议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意识不仅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思想,而且结合时代要求对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作出了凝聚东方智慧的中国判断。
习总书记指出:“以规则为基础加强全球治理是实现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进步,强行将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纳入到资本统领的霸权版图以便于形成单一的世界格局,但出于西方国家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构成的资产阶级社会,必然擁有着市民社会所固有的诟病,因而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联合体”也就必然是“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要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唯有这样才能克服“虚幻的共同体”所带来的社会动荡、独权霸政等全球危机。而为了全面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颠覆以往的社会形态,重新建构一种全新的共同体即马克思所提出的构建“人类社会”。当今的世界格局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共同主导的,并且在这其中存在着多种价值观的冲突与碰撞,所以走向马克思所描绘的“人类社会”还需要面临数不胜数的挑战和困难。因此,要想实现人类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达到马克思所言的“人类社会”,需要在“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中间建立一条连接两端的纽带,这条纽带就是中国提议推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人类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命运前途,其所提出的目标和愿景是团结全球人类,努力营造各国交往过程中的友好关系,共同为建立美好和平的“地球村”而奋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发展目标是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活动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思想,它源自于马克思,又超越了马克思,不仅在思想上发展了新的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也真正的实现了现实的行动。作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运用中国智慧促成世界和平与稳定是一种责任和担当,中国应倡导各国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人类社会”。
参考文献
[1]刘长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市民社会”解读的探讨[J].社科纵横,2010,(11):119.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7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0、17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
[5]习近平.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8-11-18(001).
作者简介:王长安,男,1996.12,汉族,江苏徐州,法学硕士,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