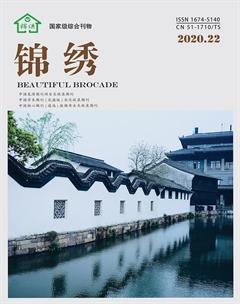人工智能对传统法律关系的挑战
彭立茹
摘要:1936年图灵提出“图灵机”设想使之成为“人工智能”之父,而后在1956年的Dartmouth学术会议上约翰·麦卡锡最早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2017年沙特授予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这是首次对智能体的区别对待。随着俄罗斯的机器人 Ostagram1基于Deep Dream 算法来生成绘画作品、机器人歌手 Deep Beat2写出一首完整的歌曲等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出现,人工智能创作物可版权性相关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人工智能社会形态的变革中版权制度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关键词:人工智能;著作权;主体;作品;权利归属
就知识产权法律而言,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问题一直是学界中争论性的话题。其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肯定说主张,人工智能创作物是遵循的设计者意志的产物,可以构成作品。否定说主要从两个角度作为切入点,认为人工智能创作物不是作品。一个角度以创作主体作为切入点,另一个角度以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作为切入点。肯定说与否定说最大的分歧点在于,肯定说认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创作主体仍旧是人;否定说认为创作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是人工智能,而非人类。因此,只有先解决主体资格这个普遍问题,后续的各个特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人工智能创作物对现有版权制度的挑战主要有三个:一是主体的认定,即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主体资格;二是客体的认定,即人工智能的创作物是否可以被列为作品;三是权利归属问题,即人工智能创作物权利归属于谁。
一、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保护的困境
(一)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的主体障碍
按照实定法,人工智能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那么是否能够通过法律拟制手段賦予其法律主体地位呢? 有学者认为法律主体在类型与范围上都具备开放性,人类之外的物体在法学构成上成为可能。法人可以拟制,为何不能通过法律拟制手段也赋予人工智能权利义务主体资格? 但人工智能与法人本质上还是有所区别的,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的主体在法学理论上以及伦理上面临着诸多障碍。
(二)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的客体阻碍
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客体属性的争议主要在于其是否属于作品。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作品的构成要素包括两点,即独创性与能以有形形式进行复制。人工智能创作物满足以有形形式进行复制条件并无争议。讨论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属于作品应当从独创性进行判断,即是否是人工智能独立生成的具有创造性的成果。
二、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保护之分析
(一)人工智能不可作为著作权法上的主体
人工智能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但是其本身独特的性质又于其他作为一般工具的物相区分。那人工智能到底是“物”还是非传统意义上的“人”呢?目前知识产权学界中对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认定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同法人一样被赋予法律主体地位,作为“有限人格”以“类人主体”的方式出现。二是认为人工智能尚不足以被拟制为法律主体。法律主体是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人工智能无论以何种方式承担责任,最终责任的承担者都是人。
笔者认为,就目前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水平而言,人工智能尚不具备上述法律主体资格要件,不能拟制为法律主体。一是人工智能不具备人类独立自主的意识能力与情感能力。二是人工智能不具备享受权利、履行义务与承担责任的能力。人工智能无法拥有和行使权利,人工智能不具备独立的财产,难以履行义务和承担法律责任。三是人工智能并未认同人类社会的秩序价值和法律规范。社会秩序是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逐渐建立起来的,法律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二)人工智能创作物可作为著作权法上的客体
(1)对独创性认定的理论与实践
人工智能的创作物是否可被称为著作权法上的客体,也就是作品?王迁教授认为,人工智能能生成的内容,在生成过程中没有给人工智能留下其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不具个性特征,因此该内容不符合创造性要求,不构成作品3。而且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著作法所称的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智力活动之创作的核心,人工智能是算法系统,无法体现其智力的御用,也无法在其意向性中体现作品的内核价值。
而熊琦教授则认为,如今大量事实表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人类创作的作品相比,在没有明确表明来源的情况下已经很难区别。北京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联盟秘书长马德刚律师认为,保护著作权是手段,鼓励更多的创作才是目的。如果我们承认人工智能的创作物可以成为作品,哪也会鼓励更多的人工智能区创作作品,并且从客观上看人工智能的作品与人类的作品本身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只要具有创造性和独立性,并且可固定的载体,即可以构成作品。
在结果意义上讲,人工智能成果完全可以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类或非人类的类似成果的独特性,以至于专业人士也不能区分出成果完成者的真实身份。“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目前的弱人工智能的成果既然已经初步做到,未来的强人工智能下更是毫无疑问。但是如果不仅从结果意义上讲,而是考虑现有著作权法理论中基于传统而对“独创性”画地为牢似的限定,人工智能成果难以符合独创性要求。
(2)对可复制性认定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2 条对“作品”所下的定义是:“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人工智能的基本程序或者说算法本就是人类社会的程序员采用特别的信息处理方式来进行信息的重组与再现,并创设出新算法用以模拟人类大脑和神经网络。我们可以说,人工智能成果是计算机在程序员的设定下,运用特定符号和仿人类的神经网络层(初级比较机械,高级超级更加智能)进行“脑力活动”所产生的与成果,而此种成果在人工智能发展到较高程度后与人类通过脑力活动所创作的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在形式上的差异会逐步减小甚至消失。从更深层次的知识产权法客体(保护对象)理论看,人工智能成果也完全符合知识产权客体的权威定义。
三、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归属
(一)人工智能创作物权利归属的模式
(1)归属于智力投入者——创造者
当然,如果承认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在机器人不具备主体资格的情况下也能确认著作权归属问题。可以认为,机器人作品享有著作权,但机器人并不能像自然人作者或法人作者那样去行使权利,换言之,该项著作权应归属于机器人的创造人。这是因为,机器人是机器而不是“人”,它是依靠数据和算法而完成写作,该机器人以及其写作的技术路径无一不是人类创制。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可以通过保护机器人作品以达到保护机器人的创造人和所有人的目的。具言之,照著作权法关于职务作品或雇佣作品的规定,由创制或投资机器作品生成软件的“人”而不是机器人本身去享有和行使权利。
(2)归属于资金投入者——投资者
在人工智能创作物中,投资者只是提供资金,其作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主体是否适合?首先,人工智能创作物等这些十分依赖巨额投资和相当长时间劳动才能完成的作品的创作,某种程度更加依赖于投资方的资金保障和组织工作而非依赖于个人的独立创作、智力创作或者创新。其次,投资者享有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具备可行性。一方面,从我国现行法律条文来看,我国《著作权法》第 9 条规定著作权人即可以是作者,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组织。我国《著作权法》第 11 条规定,作者既可以是创作者,也可以是法人。这些制度为投资人享有著作权提供了法条支撑和参考依据。赋予投资人享有著作权资格的做法,可以鼓励投资者源源不断地投资,有助于作品的创作与传播。
(二)人工智能权利归属的制度设计
(1)以作品生成方式为依据划分权利归属
笔者认为讨论人工智能作品权利归属问题,要把人工智能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算法辅助人类生存的作品,第二类是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的作品。第一类作品虽然是由人工智能生成,但其算法和内部系统语句均由人类设计,该类作品人工智能的定位智能是辅助人类创作的工具,著作权人是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的人类。第二类是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的作品,该类作品笔者认为采用推定的方法认定其权利主体比较妥当。首先,人工智能并不具有法律主体的资格,它并不能成为由自己创作的作品的权利主体,由享受著作权所带来的收益主体作为该作品的著作权人既能保障版权制度的实施,又符合知识产权的激励理念。其次,人工智能的算法属于知识产权而载体属于物权,在人工智能转让时转让的物权而非知识产权,而进行作品创作的是人工智能的算法,若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的所有者,则该归属于用于人工智能载体物权的法人还是用用人工智能算法的研究开发者呢?最后,在权利归属主体难以确定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确定享受权利带来的利益主体来完成权利主体的推定。若人工智能创作物带来的利益由法人享受,则创作物的权利归属于法人,若人工智能创作物带来的利益由研究开发者享受,则研究开发者是该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主体。
(2)权利归属与创作物的必要安排者
笔者认为,无论是程序投资者、开发者抑或是使用者,都对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产生有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对于人工智能生成成果权利的归属以“对成果产生进行必要安排”为判断标准更为客观。“必要”表明不能免除,“安排”是指对人工智能自动写作进行具体的规划和劳动。英国版权法也将计算机作品的权利归属于“必要安排者”。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必要安排者的确定主要综合以下因素来考虑:一是有设计人工智能成果形式的行为。二是有构建人工智能逻辑体系的行为。三是有实现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商业利用的行为。
四、总结
目前,围绕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知识产权的发展提供了无法想象的资源和素材,新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不少学者以强人工智能与超人工智能为研究对象,认为人工智能拥有独立的自主意识,具备独立的辨认与控制能力,已对“以人为中心”与“人作为主体”的理论提出挑战,人工智能可取代人类精神劳动,对著作权制度造成颠覆性的冲击。这种设想脱离人工智能仍处于弱人工智能的现实,缺失独立意志的人工智能仍是人类创作的辅助工具,处于从属地位,而非独立的主体。本文是在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工具理论的基础上,再依据著作权法制度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与权利归属进行合理界定和安排。
参考文献
[1]王果.论计算机“创作作品”的著作权保护[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01).
[2]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J].知识产权.2017(03).
[3]曹源.人工智能创作物获得版权保护的合理性[J].科技与法律.2016(03).
[4]熊琦.著作权法中投资者视为作者的制度安排[J].法学.2010(09).
[5]姚志伟,沈燚.论人工智能创造物的著作权归属[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
[6]刘强,彭南勇.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问题研究[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
[7]张春艳,任霄.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及权利归属[J].时代法学.2018(04).
[8]雷悦.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法律问题探析[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
[9]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05).
[10]乔丽春.“独立创作”作为“独创性”内涵的证伪[J].知识产权.2011(07).
[11]陈艺芳.著作权法视域下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法律保护[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
[12]https://www.ostagram.ru,该官网上由更多机器人生成的“画作”.
[13]据 MIT Technology Review 報道,来自芬兰的 Aalto 大学的 Eric Malmi 决定让计算机学会写歌,还是酷炫的说唱歌曲。第一阶段,机器歌手 Deep Beat 在一首混杂了随机词句的歌词里挑出了82% 的“外来者”;第二阶段,Deep Beat 写出了一首歌.
[14]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35(05):148-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