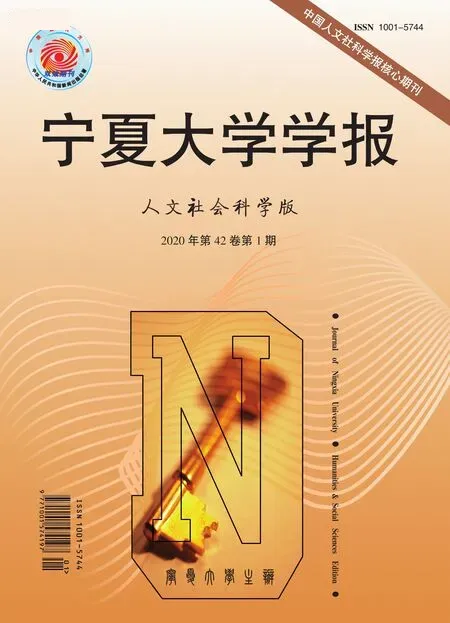李白诗词英译中的暴力阐释
吴雨轩,乔 幪
(1.华北理工大学 国际教育中心,河北 唐山 063210;2.宁夏大学 外国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首先把翻译比作“暴力”的是迈斯奈(Meissner)[1],但韦努蒂(Venuti)对“翻译暴力”进行了系统论述[2],两人皆认为暴力是在翻译中进行的不当变更或歪曲变形。孙艺风以“我族中心主义归化翻译暴力”概念为核心,总结归纳翻译暴力的性质、类型,借此分析暴力对翻译行为的影响。暴力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克服语言或者文化不可译问题的柔性暴力,而另一种则属于为改变目的或改变形式而进行的操纵性改写[3]。曹明伦指出正常的翻译中不存在暴力,界内对“暴力”的诸多讨论皆源于对韦努蒂“violence”一词的误读,认为翻译暴力的流行是翻译研究的倒退[4]。同年,张景华就曹的观点发表独到见解,再次使“翻译暴力”上升至学理层,肯定了violence 一词译为“暴力”的合理性,同时点明“翻译暴力”的术语化不是翻译研究的倒退,它反映了全球化语境下文化思想交流的地缘政治和时代特征[5]。
一 翻译暴力——随风潜入夜
学界对“翻译暴力”一说的研究自21 世纪初就存在,近两年,国内学界关于“翻译暴力”的讨论仍此起彼伏,屡见不鲜。刘满芸认为翻译暴力曲解了翻译的性质[6],侯国金则认为施暴观的提出并不能说明翻译学研究的倒退,“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对翻译暴力的分析研究将对提高翻译和跨文化交际质量和效度有新的贡献[7]。近二十年来国内翻译界对“翻译暴力”不同角度和维度的解读恰恰说明我国翻译界对国外翻译理论的批判性思考。综合分析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翻译暴力的解读,暴力在翻译中的确存在,因为语言在跨文化传递中虽然具有可理解性、可接受性,但一旦在表达和运用中涉及文化因素时便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可译性,即人们常说的“语塞”。这时,要想破解源语言编码,首先要克服文化障碍,在目的语重构输出的过程中必然会与源语存在一定偏差,这种偏差便是“翻译暴力”的结果。说起文化和语言,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的古诗词,古老的中华大地物产丰富,人杰地灵,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更是滋养了一代代文人骚客,他们或吟诗怀古,或游历山水,千万种思绪凝练成数十个词语,这便是汉字的魅力所在,而且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研究呈现出宽视野、多维度、跨学科的态势[8]。
在文化走出去的今天,国内学者应注意到“当今英美读者已经比较客观、全面地对唐代诗人李白有一定了解,在21 世纪的英语世界李白诗歌逐步巩固了它的经典地位”[9],究其原因,汉学家和中国译者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马会娟曾对全球图书馆收录的主要英译李白诗歌选集进行汇总,按被收录的图书馆数量排名前五名中,前四位均为外国译者,第五位为中国本土译者许渊冲[10]。就当前国内经典文化典籍或中华文化外译工作的具体操作者而言,国内高校学者和翻译爱好者占相当大的比重,相比之下从事该工作的汉学家数量屈指可数。另外,在翻译过程中许渊冲兼顾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注重对文本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阐释与转换。在许渊冲看来,文学翻译中英美译者只求达意,而中国译者不仅要“传情”,还要创造意义[11]。鉴于此,尝试以学界提出的“翻译暴力”为切入点,从柔性暴力和强制暴力两方面分析许渊冲先生英译“诗仙”李白诗词,一方面看许老如何巧妙英译诗词,根据自己的文化立场和翻译语言观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原诗的意境,另一方面试图向学界说明翻译暴力在古诗词翻译中的可行性。
二 柔性暴力——译者的妥协
根据翻译的目的和产生的效果,翻译暴力可分为两大类,软暴力主要是为了克服不同语言文化引起的不可译问题。它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仍然不能否认它对翻译主体和客体施加的暴力行为[12]。软暴力又称为柔性暴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实现意义的忠实,必然会对形式不忠,就这一点而言柔性暴力在翻译中几乎不可避免,因此为追求意义的忠实而破坏原文的形式,实属译者不得已而为之。译者借助词汇选择、句式变形及运用厚度翻译等方式,通过柔性暴力保证原诗信息向译入语读者的传递,实现翻译目的。
(一)词汇选择
由于存在文化差异,中西方哲学思考模式亦相去甚远,西方哲学思维重分析性和逻辑性,中国传统哲学则重整体性和宏观性。受此影响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上自然有所差异,在诗词翻译上更应注意到这一点。
《静夜思》是李白创作的一首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唐诗。李白时年26 岁,秋日某个夜晚,诗人寄宿扬州于屋内抬头见皓月当空,思乡之情涌上心头。诗人运用比喻、衬托等技巧,“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举”“低”之间委婉表达自己的客居思乡之情。许老译为“Eyes raised/I see the moon so bright/Head bent/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13],译文每小句8 个音节,对仗工整,“raised”与“bent”两个动词采用过去分词形式和“举”与“低”相对应,“思”乡直接,但情感却委婉地通过“drowned”缓缓流露出来。
诗歌翻译中,意美的传递关乎整个译诗与原诗对等效果的实现[14]。细读上述诗句,译文仍存在端倪,英译后诗人“举”的不是“head”,而是“eyes”,似乎和原文有些出入,柔性暴力就此产生,但恰是这样的译文更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尽量减少单词的重复使用。若前半句改成“head raised”看似做到了与原文形神俱合,但与后半句“head bent”成句则语感稍差。此处,许老借“望”翻译出诗人直接抬起的是“eyes”恰好符合当时的情景。可见柔性暴力下,虽然译者改变了源语文本主体我“举”起的客体,但意义却达到了忠实可接受。
再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与李白以往的送别诗不同,诗中没有“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的痛心惋惜,没有“正当今夕断肠处,黄鹂愁绝不忍听”的肝肠寸断,而是满目春光的人间好时节。此次李白送别的是自己心中“风流天下闻”的孟夫子,其要去的不是荒蛮之地,而是烟花烂漫春色满眼的广陵,自然是喜上眉梢。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开篇直接点明时间、地点、人物和故事背景,许老译为“My friend has left the west where towers Yellow Crane/For River Town when willow-down and flowers reign”[15],意义上与原文最大的不同要属“River Town”对“扬州”的翻译。从题目看,孟夫子“之”的是“广陵”,而诗中却说“下”了“扬州”,原因是唐朝时期广陵是扬州的一部分,当时的州相当于现在的省一级行政单位,因此古扬州地域范围远大于现在扬州的行政范围。由此看来,若是译为“Yangzhou”目的语读者读来恐怕会把现在的扬州和当时的扬州混为一谈;而且,当时的扬州位于长江下游,土壤肥沃富裕辽阔,地理位置和人文风貌也和今天的江南水乡相差不大,因此翻译为“River Town”是可接受的。但不能否认如此一来,译文和原文必然存在差别,这种差别便是柔性暴力的结果。译者为满足文化传播需求,考虑到译入语读者信息提取能力而有意改“扬州”为“River Town”,这种柔性暴力确实存在,但却保证了原文信息在译文中的有效传递。
本句中的“烟花三月”本是偏正结构,根据现代汉语可理解为“烟花灿烂的三月”。“烟花”说明暮春时节的繁花似锦,而在英译本中却未见“March”。“when”一词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替代了原文的偏正短语,源语中的具体时间在译入语中模糊化了,此处似乎是未能最大化传递源语信息,由此可说明译文存在翻译暴力。但是这种暴力也未影响全诗内容的传递和审美的判断,无论是从纬度还是从海拔,三月的扬州和同时期的译入语国家必然风格迥异,因此“三月”并不能使译入语读者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译者只有妥协而为之,将时间模糊化,景色具体化,便有了“willow-down and flowers reign”。
(二)句式变形
诗歌的形式是其精髓,如汉语诗歌的格律,包括诗韵和平仄、平仄的变格、对仗以及五言、七言等题材[16]。汉语古诗和英诗最大的不同在体裁和韵律上,汉语古诗在体裁上多分为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在韵律上讲究平仄、对仗等,英诗则不然,其没有固定的体裁,却有节奏变体和抑扬格。因此许老在英译李白古诗时多以抑扬代平仄,在句式上尽量追求译文和原诗的匹配。
李白一生狂放不羁,喜游历山水饮酒放歌,《登金陵凤凰台》是其为数不多的七言律诗之一。相传当年李白曾登上黄鹤楼欲泼墨吟诗,不想崔颢已作《登黄鹤楼》,遗憾地感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现终有机会来到金陵登上历史遗迹凤凰台,诗人借景抒情怀古咏今,最后回归“使人愁”的长安城,上升至家国情怀。该诗的首联和颈联很是精彩,首联连用三个“凤”字,却不显重复节奏明快,暗示朝代兴衰。颈联则凭吊历史,一副衰败没落的“吴宫”图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
原诗节选: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译文:
On Phoenix Terrace once phoenixes came to sing,The birds are gone bur still roll on the river’s waves.
The ruined palace’s buried’neath the weeds in spring;The ancient sages in caps and gowns all lie in graves.[17]
英译文首先在排版时特意将每一节的第二小句首行缩进两个字符,形式上更像英诗,给译入语读者视觉冲击效果更为强烈,这种形式上较源语的变化可看作翻译暴力存在的结果。宏观来看,原诗首联两句的“游”和“流”及颈联的第二小句“丘”皆押尾韵ou,读来琅琅上口。英译本则不然,一改汉语的尾音AABA 押韵形式为英语的ABAB 交韵形式,颇有英诗风范。押韵形式的变化引起了句式的变形,这种变形也使得译诗较原诗在译者有意或无意施加的柔性暴力作用下存在一定差别,但译诗又可以为译入语读者以译入语文化中的审美视角所轻易接受和理解,说明这种翻译暴力并未破坏原诗语义和美感的传达。
在《将进酒》中,李白豪饮高歌借酒消愁,感叹怀才不遇,人生应及时行乐。全诗似酒后落笔,一气呵成,首句两组排比长句气势恢宏。
原诗节选: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译文:
Do you not see the Yellow River come from the sky,Rushing into the sea and ne’er come back?
Do you not see the mirrors bright in chambers high Grieve o’er your snow-white hair though once it was silk-back?[18]
第一句从空间范畴感叹“逝者如斯”,黄河自发源地奔流不息,流经之地虽土壤肥沃,但上中下游落差极大,素有“九曲黄河”之称。上半句写出黄河之水浩浩荡荡自西向东奔流的汹涌壮阔,下半句写大河逝去,沿河道入海的不可回头。第二句则从时间范畴感叹人生短暂不过朝暮。开篇气势恢宏,汉语读者读来不禁黯然感伤。英译文中许老在沿用押尾韵的基础上毫不犹豫改陈述为反问,开篇连续两个反问句不仅迅速抓住译入语读者的眼球,直接带入源语语境,同时使其陷入和源语读者一样对人生的深入思考。虽然英译本达到了预期效果,但不可否认用反问句表达之后对源语的肯定句式进行了“伤筋动骨”的手术,这种暴力形式也是译者为实现翻译目的而进行的折中。
(三)厚度翻译
厚度翻译又称补偿,“很多传统文化内涵在英语中是缺省的”[19]。若在翻译过程中涉及文化差异而不可译时,译者往往通过添加注释或阐释主题内涵的方式尽可能为目的语读者提供更多的有效信息,以帮助其理解原文意义和内涵。
李白著有《春思》一诗,描摹深闺中的妇人见“春风”吹进“罗帏”,对戍边丈夫的深深思念之情。这首诗题目翻译颇为有趣:A Faithful Wife Longing for Her Husband in Spring[20],从字数上来讲,原文本中的“春思”两个汉字被译为英文的9 个单词,汉英字数译制比例高达1∶4.5,说明译者在竭力向目的语读者解释原诗题目的深层意义,这种有意识的操作也可以看作暴力作用的结果。中国古诗之美较大程度与其所指的含混有关,换言之,一个能指可能会有多个所指。就这句诗而言,首先“春思”中的“春”在此处有两层意义,第一是自然现象春天交代了叙事时间,进而在下文中才有“燕草”和“秦桑”;第二,“春”在汉语文化中还指代男女之间的美好情愫。对目的语读者,“春”的第一层意思很容易理解,因此许老在翻译时直接翻译为时间状语“in spring”,但第二层意思目的语读者因缺乏知识和文化背景理解存在困难,这时译者勉为其难只能将题目中的两个字顺势解释,直接把全诗的内容呈现给目的语读者。“faithful”和“longing for”两组词既歌颂了中国古代深闺女性的忠贞不渝,也将一个独守春闺,渴望战争结束丈夫早日回乡的女性形象讲述给目的语读者。暴力作用下产生的这种厚度翻译,正是说明了文化差异下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别,英语形合多介词和分词短语,汉语意合其背后隐含的需要读者揣摩的内容就更多。必须看到,“春思”译成英文后,虽有效避免英文读者困惑不解,但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却大大缩小。因此,翻译暴力运用程度强弱仍应进行综合考量。
三 强制暴力——暴力的合法
柔性暴力多集中于词语的选择、句式的变形以及通过厚度翻译等方式用译入语对源文本的形式进行加工调整,以最大程度忠于原文。“从本质上看,翻译的目的论……都强调为达到某种翻译目的,用什么手段并不那么重要。”[21]暴力作为译者为达到翻译目的而有意或者无意采取的一种手段,有时会出现“用力过猛”的迹象,这种现象多发生在一些文化负载词上。译者从宏观角度出发,照顾全文的翻译效果有意为之,但这种情况下译文内容的传递和审美效果的传达并未受到实质性影响,反而会让读者豁然开朗。
(一)强行归化
在古诗词英译中,有时译者会面对巨大的文化差异鸿沟,单独依靠直译或是字词、句式的变化已经难以弥合,故不得不采取较柔性暴力更为强硬的手段以操控全诗所传达的情感。
李白在金陵逗留的大半年里创作三十余首古诗,且几乎每篇题目中均含“金陵”二字,给后人研究金陵与李白的诗词文化留下了丰富可取的材料。《金陵酒肆留别》中诗人即将离开金陵奔赴扬州,微风吹拂着柳絮,倒酒的侍女唤客把酒言欢,朋友们纷纷跑来为自己送行,自己却迟迟不肯离去,只能迷失在酒桌上,沉醉于觥筹交错之间。全诗的点睛之笔在尾联,实际存在的“东流水”和抽象的“别意”同时置于一个维度相比较,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诗人却借此吟唱自己绵延不绝的伤感别离之情。
原诗节选: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译文:
O,ask the river flowing to the east,I pray,Whether his parting grief or mine will longer stay![22]
原诗诗人用肯定句强烈地表达出自己的不舍和难过,但在译文中却换成感叹句,“O”的出现立刻把目的语读者带入目的语语境,因但凡对英诗有所了解的读者都知道“O”是英诗的常客,正如Ode to the West Wind 中雪莱开篇便借“O”点出西风的秉性和存在,罗伯特·彭斯在A Red,Red Rose中则借“O”引出“my luve’s like a red,red rose”,把自己的爱人比作红红的玫瑰。“O”的出现,注定译者要把原肯定句改为感叹句,相对于源语读者,目的语读者不用细细揣摩便可直接体会到此处作者的无奈。“O”不过是作者的感叹,意义上相当于汉语的“啊”“哦”等,但在汉语古诗词中却鲜少看到诗人采用“啊”“哦”等汉字直接抒情,暴力自此产生,但此作用下“O”却使译成的英诗更像本土的英诗。
接下来,译者又插入主语“I”,把原诗中隐含的主角“我”拉到读者眼前,这与传统的英诗毫无二致,约翰·邓恩写有Flea 一诗,通过写一只同时吸了男女血的跳蚤表达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爱慕之情,“Oh stay/three lives in one flea spare/Where we almost…”,该句作者同样把当事人“we”直接写给读者。此外,流水的“别意”化为“his parting grief”,河水被拟人化了,直接参与了在座各位好友的情感交流,此处无情胜有情。如果把整句英诗进行回译,很难再从中看到原诗的影子,可见许老对这一句诗的翻译经过了细致思考,决定采取强行归化的方法,这样翻译无疑产生了暴力,使译文在意义和表达上与原文有所偏差,但这种暴力没有对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形成伤害,译者运用这种暴力方式使译文尽力贴近目的语文化,兼顾目的语读者的感受,体现出东方宏观哲学思维下的人文关怀,这样看来公然的暴力没有引起反感,反而合法了。
(二)过度文化适应
一般而言,文化在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必然存在高低强弱之分,译者往往在进行翻译时就高不就低,就强不就弱,因此文化的隔阂和疏离会造成原语和译语在转化时呈现出语言上的不平等,也便产生了暴力,“翻译突显的是‘双向’脆弱,造成交互暴力:如欲减轻对译文的暴力,可能造成对原文的另一种暴力,反之亦然”[23]。因此,知悉原语和译语双方文化强弱也十分重要。
李白袭用乐府旧题作《蜀道难》,诗人就蜀之险展开丰富想象,勾勒出秦蜀道路上一道道奇丽惊险的山川谷道,气势磅礴。该诗的题目许老译为Hard Is the Road to Shu[24]同时在“Shu”下做脚注“present-day Sichuan province”,因普通目的语读者可能对中国的行政区划不甚了解,对“Shu”更是前所未闻,此处是译者做的补偿翻译,补充目的语读者缺失的文化背景。全诗围绕崎岖艰险,坎坷蜿蜒的“蜀道”展开,因此译者不得不译出“蜀”这一点名山道地理位置的词。若直接译为“road in Sichuan”,一方面忽视了蜀作为四川简称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忽视了原诗中“蜀”的出现频率,直译加注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全诗英译的质量。为了更好地促进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尽量将文学作品当中的文化内容保存下来[25]。
也应看到,即便许老对译文题目做如此调整,一部分目的语读者对“Sichuan province“和“蜀”各自的意义仍因缺乏背景知识而无法理解,这里存在对读者的暴力。译者通过加注的方式尽量满足了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诉求,但加注一方面可能会打断其阅读思路,影响阅读兴趣,另一方面对那些对中国地理不甚了解的目的语读者而言,“Sichuan province”的翻译可能反而增加了其阅读和理解负担。此处要讲的文化适应,便是译入语读者对原文本文化的适应,这一点在提倡文化走出去的今天尤为适用。翻译暴力需要合法,就像现在中国的“饺子”已经为越来越多的西方朋友接受为“jiaozi”而非“dumpling”,来华留学生愿意称“老师”为“laoshi”而非“teacher”。在建立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凭借中华文化的强大力量应该更加有信心把优秀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在世界逐渐推广开来。
四 结语——润物细无声
“翻译暴力”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在我国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其实暴力主要表现在译者对原文或目的语读者的“施暴”。许渊冲在英译李白诗词过程中,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寻求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对原诗的忠实,另一方面又要照顾目的语读者,为其提供更多的文化背景信息弥补文化缺省,避免文化阉割和食人翻译现象的出现,取舍之间便是暴力滋生的根本原因。
但是也应注意到,不管是为实现跨文化交流目的而进行的缓和暴力还是译者自身对原文大刀阔斧地改写甚至改编,均未影响中华诗词在目的语读者中的接受和认可。“中华诗词的外译,我们既要促进东西跨文化交流……又要维护民族文学的异质性”[26]。值得一提的是,许老在翻译过程中巧妙运用翻译技巧,淡化了暴力对原诗和目的语读者的冲击,甚至暴力作用下译诗还能最大限度传达原诗的风格和意境,这便是暴力之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