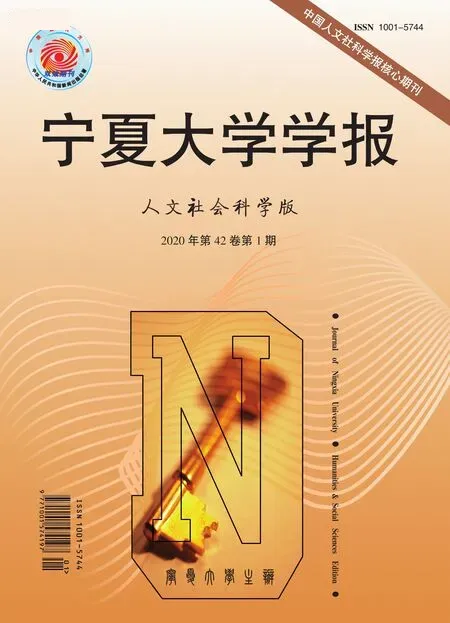史学素养与蔡邕的碑文创作成就谫论
袁亚铮,崔严之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蔡邕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大家, 其在经学、文学、史学和艺术等领域皆有很深的造诣,但笔者发现近年来学界对蔡邕的研究多侧重于经学和文学方面,对于其史学成就却鲜有论及[1]。而据史书记载蔡邕最重要的身份是史学家,并且其史学才能对文学创作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蔡邕的创作成就以碑文为主, 而碑文的创作即和史学有极大联系,所以古今学者一致认为创作碑文须具史才,如近人冉德昭云:“为一碑文家, 除了文人应备之条件外,须具有史才”[2]。而据笔者研究蔡邕在碑文创作上之所以取得很高的成就和其深厚的史学素养有密切的关系,而目前学界对此点的研究却付之阙如,鉴于此,笔者将就蔡邕的史学素养对其碑文创作成就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论述,并就教于诸位方家。
一 续修汉史是蔡邕毕生的宏愿
蔡邕字伯喈,东汉晚期陈留圉县人。 蔡氏虽是陈留的望族,然蔡邕却早丧二亲,失祜后蔡邕在叔父蔡质的庇护下生活,其在《与人书》中云:“邕薄祜,早丧二亲,年逾三十,鬓发二色,叔父亲之,犹若幼童。居则侍坐,食则比豆。”[3]蔡质在灵帝时官至尚书,其不仅是位官员,还是一位学者,曾撰《汉官典职仪式》一书(蔡质《汉官典职仪式》一书已亡佚,清孙星衍辑有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 见 《平津馆丛书》)。 在叔父的影响下,少年的蔡邕就对史学产生了兴趣,《蔡邕别传》载“时在弱冠,始共读《左氏传》”[4],其后,蔡邕又师事胡广,胡广不仅是六朝元老,更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史书载其“谦虚温雅,博物洽闻,探赜穷理,《六经》典奥,旧章宪式,无所不览”[5]。著有《汉制度》一书,还曾为王隆所作的《汉官解诂》作注。 在此期间,胡广认为蔡邕具备史学家的潜质, 将自己积累多年的文献资料全部交付于蔡邕,蔡邕在其《戍边上章》中云:“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世祖以来,唯有纪传,无续志者。 臣所师事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6]。然而修史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为此蔡邕“积累惟思二十余年”[7],并结合朝廷现行的礼仪制度,凡有所知,必加以钩稽整理,以备后用。 蔡邕为修史前后花二十年的时间准备,其对于修史的看重由此可知。
建宁三年(170),蔡邕应司徒桥玄之辟出仕,后“出补河平长。 召拜郎中,校书东观”[8]。 东观是东汉中后期宫廷的藏书中心, 任职其中的多为名儒硕学,谓之东观著作,而东观著作的职责之一即是撰修史书。 据《通典·职官八》载:“汉东京图书悉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入直东观,撰述国史,谓之著作东观。 ”[9]蔡邕在东观前后九年,这期间的主要工作是“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10],此即著名的《东观汉记》。 《东观汉记》是暨《汉书》之后,对后汉历史的官方整理,其发轫于班固;安帝时在刘珍等人的手中初具规模;桓帝时曾命崔寔接续刘珍等人的修史工作;到灵帝、献帝时期,续修汉记之事再起,“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11]。 蔡邕作《灵纪》“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12],不仅续作纪传,蔡邕还独自撰写史志“别作《朝会》、《车服》二志”[13]。 其后又陆续撰成“十志”。 “修史之难,无出于志”[14],这是古代史家的共识,本次修史活动蔡邕是主导“在这项史学工程中(《东观汉记》的撰写),蔡邕不是以一般的执笔者侧身其役, 而是充当了这项工程的主要构筑者。 他对于书中的纪、传都曾继踵前人,有所开拓。但最值得令人推重的,是他撰写的十志”[15]。 然史书编纂未竟,蔡邕却因事髡徙朔方。 在被贬边地期间,他仍以修史为念,在《戍边上章》中上奏云:“臣初被考逮,妻子迸窜,亡失文书,无所按请……被沥愚情,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诏明国体。 章闻之后,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 ”[16]被贬边地却仍以修史为念,对此胡三省评论道:“初,邕徙朔方,自徙中上书,乞续《汉书》诸志,盖其所学所志者在此”[17]。蔡邕终生之志趣可见。除奏章外,随此次上奏的还有“十志”“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十志),分别首目,连置章左。 ”[18]关于蔡邕所撰“十志”的篇名,吴树平先生认为可考的有七篇,分别是《律历志》《礼乐志》《郊祀志》《天文志》《地理志》《车服志》《朝会志》[19]。蔡邕所撰述的“十志”虽因汉末动乱有所遗失,但部分仍保留在司马彪的《续汉书》和谢沈的《后汉书》中,梁刘昭的《注补续汉书八志序》中云:“至乎永平,执简东观,纪传虽显,书志未闻……自蔡邕大弘鸣条,实多绍宣……于是应(劭)谯(周)缵其业,董巴袭其轨。 司马(彪)续(汉)书,总为八志,《律》历之篇,仍乎(刘)洪(蔡)邕所构,《车服》之本,即依董(巴)蔡(邕)所立。 ”[20]可见蔡邕的十志在后世亦有流传。
从边地被赦后,蔡邕又因触怒权贵,流亡吴中12 年。后因董卓征召,勉强出仕拜左中郎将,及董卓被诛后, 蔡邕因同情董卓而被司徒王允收捕下狱。在狱中蔡邕“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21]。 死前仍以续修汉史为念,太尉马日磾恳请王允惜其才云:“伯喈旷世逸才, 多识汉事, 当续成后史, 为一代大典。 ”[22]王允不允,遂死狱中。 马日磾对蔡邕才学的评论说明其史学家的身份早已得到当时士人的肯定。 其死时“缙绅诸儒莫不流泣。 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23]。 郑玄对蔡邕之死的痛惜,说明其时蔡邕续修汉史是众望所归。
二 蔡邕用创作史传的方法来撰写碑文
碑文是一种记述碑主生平功德、彰显立碑者哀悼之情的文体,由“序”(碑志)和“文”(碑铭)两部分组成,“序”用于记事,多为散体,“文”用于颂赞,多为韵文。 “序”一般先叙述碑主名讳、世系等,再叙述碑主的懿德景行、仕宦经历,最后写明碑主的卒葬之事、以及树碑之义等事项。 由于其是对碑主整个生平经历的记载,颇似史书的人物传记,所以古人认为碑文的撰写者应具史才,如刘勰云:“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24]刘勰认为散体之碑“序”即为史传,押韵之碑“文”则是铭,虽其观点值得商榷, 但亦反映碑文和史传确有相似性。碑文与史传相似,加之蔡邕的史才“伯喈既专门史学,又长于辞赋,故论碑者,咸推其为巨擘焉。 ”[25]蔡邕的史学素养对其碑文创作上影响极大,其表现如下。
其一, 蔡邕将史传的叙事手法运用到碑文中。碑文和史传虽有相似性,但并非完全等同。 史传以叙事为主,且注重叙事的真实与全面,所谓的“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26],而碑文却不以纯粹的叙事为主, 更不追求叙事的全面,“盖碑序所叙生平,以形容为主,不宜据事直书,琐屑毕陈”[27]。 碑文应以描写为主,须突出碑主的功德,所谓“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28]。 虽碑文和史传各有侧重,但作为史学家的蔡邕在创作碑文时不时流露出其长于叙事的史学创作习惯,用碑文来叙述碑主的全部生平事迹,且力求真实。 如《故太尉乔公庙碑》一文总共叙述了乔玄一生十多事, 其详细程度则远超正史,如对于其荒年开仓赈济,监视桓帝同产渤海王刘悝等的记载可以补正史之阙。 而其中揭发陈国相羊昌贪污;耻于为梁不疑所辱而弃官;收考上邽令皇甫祯;奏免盖升等四事更是与《后汉书》本传吻合。 由此看出, 蔡邕是以撰写史传的方法来撰写碑文,力求叙事的全面和真实。 史传叙事除了要全面、真实外,还要选取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特征的材料作为重点的描绘,而蔡邕碑文亦体现了此点,如《胡公碑》。文中蔡邕历叙胡广的家世、仕宦经历;最后则写胡广“于时春秋高矣。 继亲在堂,朝夕定省,不违子道。旁无几杖,言不称老”[29]。 文中将对胡广的描写落在至孝上,胡广的蒸蒸至孝则大略可知。 此则材料后来被范晔抄录入《后汉书·胡广传》,史家直接将蔡邕碑文中碑主的事迹录入正史,则其碑文的真实性立显。 总之,作为史学家,蔡邕撰写的部分碑文明显带有史传的叙事意味, 且其叙事注重全面和真实,蔡邕碑文的叙事性正如刘师培先生所云:“综观伯喈之碑文,有全叙事实者,如《胡广碑》;有就大节立言者,如《范丹碑》;有叙古人之事者,如《王子乔碑》”[30]。
其二,史学家的眼光使得蔡邕在创作碑文时善于谋篇和剪裁。 蔡邕所作的碑文,往往一人数篇,比如胡广、陈寔碑等,如何既尊重事实又避免雷同,则布局谋篇显得尤为重要。 考察蔡邕的此类创作,虽一人数碑,却各有侧重。 如《陈太丘碑》共有两篇,两篇虽同叙事实,但一详生前(《陈太丘碑》(一)),一详死后(《陈太丘碑》(二)),同写一人而内容全然不同,这是蔡邕善于谋篇的体现。 另碑序是对碑主生平事迹的记述,虽要求完备,但亦无须琐屑毕陈。 蔡邕作为史学家,善于剪裁,其在撰写碑文时“往往借鉴史传的写法,截取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来突出碑主的品行”[31]。 比如乔玄一生值得称述之事颇多,但蔡邕在《故太尉乔公庙碑》一文略写他事,却选取最能体现乔玄品格的奏免盖升一事作详细描写。 乔玄不顾盖升与灵帝有旧,接连上表奏免盖升,为将盖升绳之以法不惜触犯天威,则其不畏强权的品格跃然纸上。
其三, 蔡邕借用史传的手法来塑造碑主的形象。 人物形象多见诸史传或文学作品中,用细节来刻画人物更是史传创作的重要手法。 而“碑铭所追求的是庄重典雅,原本没有描写人物真实形象的余地”[32]。 但蔡邕作为撰写“《灵帝纪》及列传四十二篇”[33]的史学家深谙人物传记的创作方法,并将此用之于碑铭创作,以至于其在碑文中刻画了许多生动的碑主形象。 在刻画碑主形象上,蔡邕善于选取最能体现碑主性格特征的细节加以描绘,来塑造人物。 如在《故太尉乔公庙碑》一文为表现乔玄“达于事情、剖断不疑”的品质,蔡邕记述了乔玄在凉州太守任上的一事,“又值馑荒,诸郡饥馁,公开仓廪以贷救其命。 主者以旧典宜先请,公曰:‘若先请,民已死。 ’讫乃上之”[34]。 寥寥数笔,而乔玄忧心民瘼、权变于事的形象呼之欲出。 再如《陈留太守胡公碑》中描写胡硕“是年遭疾,屡上印绶,诏书听许,以侍中养疾。 其年七月,被尚书召,不任应命。 诏使谒者刘悝赍印绶,即拜陈留太守。 君闻使者至,加朝服拖绅,使者致诏,君以手自系,陈辞谢恩。 ”[35]晚年胡硕以侍中之职居家养病,平时燕服,听闻使者至,即使有疾不便但仍然“加朝服拖绅”以示恭敬,此处的细节描写,凸显了碑主温恭笃礼的形象。
其四,蔡邕多采用史书的“互见法”和“春秋笔法”来撰述碑主的事迹。 “互见法”和“春秋笔法”是史书常用的创作手法,作为史学家的蔡邕亦时常将此种手法运用到碑文的创作中。 古代碑刻名目繁多,“更因立碑之地不同,而名称亦随之而异……故蔡邕为碑文,常一人数篇,殆以此也”[36]。 在一人数碑的情况下, 蔡邕的碑文却每篇侧重一个方面,将其生平经历和功劳德行分配到不同的篇章中,如此每篇看似独立,却又统为一体。 如蔡邕的恩师胡广就有三碑, 一碑详在叙述其生平经历, 偏重叙事(《胡公碑》);一碑重在述其德行,侧重描写(《胡太傅碑》);一碑重其德行学问,叙议相间(《太傅安乐乡文恭侯胡公碑》)。 三碑各有侧重,看似独立,却互为表里,分可以单独成篇,合则可以相互补充,颇存史传“互见”之法,体现出史学家构思的匠心。 另外,蔡邕的碑文时有运用“春秋笔法”,如其在《故太尉乔公庙碑》记载了乔玄奏免盖升一事,盖升在郡受取数亿以上, 乔玄上奏盖升“‘贪放狼藉, 不顾天网’……连表上不纳,而升迁为侍中”[37]。 盖升为汉灵帝的故交,贪赃受贿数亿以上,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升为侍中,这里仅“连表上不纳,而升迁为侍中”一句,“作者在称赞乔玄的刚直的同时,借势加以揭露,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像这一类的‘春秋笔法’在蔡邕所作的碑铭中并不少见”[38]。
三 受其史学素养的影响蔡邕的碑文呈现出用典和简要的特点
蔡邕的史学素养体现在其碑文的诸多方面,具体来说, 就内容而言体现在其碑文的叙事性上,就形式而言,则体现在其对材料和语言的驾驭上。
其一,史学家的博通特质使得蔡邕在创作碑文时多用典故。 东汉的文人多兼学者的身份,所以其在创作时引经据典已经成为一种时代风气,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云:“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 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39]。 刘勰指出从扬雄、刘歆开始博采经书中的典故,到了班固、蔡邕等人更是将引用的范围扩大到史书,究其原因则是班固、蔡邕的史学家身份,史学家在修史时须博览群书,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认为“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40],其在创作碑文时,亦受史家博通的影响,多用典故。 如蔡邕的《琅琊王傅蔡朗碑》在叙述蔡朗的闲居生活时云:“以《鲁诗》教授,生徒云集,莫不自远并至。 栖迟不易其志,单食曲肱,不改其乐,心栖清虚之域,行在玉石之间。 ”[41]这里的“栖迟不易其志”句,邓安生先生认为“栖迟”下脱去“衡门”二字[42],其原句应为“栖迟衡门,不易其志;单食曲肱,不改其乐”,而“栖迟衡门”即化用了《诗经·陈风·衡门》中的“衡门之下,可以栖迟”的典故;“单食曲肱,不改其乐”即化用了《论语·雍也》中的“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和《论语·述而》中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典故。 这三个典故都形象地表现了蔡朗安贫乐道的形象。 再如《陈太丘碑》(一)写陈寔在乡里的为人时云:“于乡党则恂恂焉,彬彬焉,善诱善导,仁而爱人,使夫少长咸安怀之”[43]。 “于乡党则恂恂焉”化用了《论语·乡党》中的“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 似不能言者”。 突出陈寔在乡里的恭敬之貌;“使夫少长咸安怀之” 出自 《论语·公冶长》“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表现了陈寔在乡里的威望。 论及碑铭的风格,陆机的《文赋》以为“碑披文以相质”“铭博约而温润”[44],强调其语言应文质相半,典雅温润,蔡邕的碑文就体现了这种质实典雅的文风, 究其原因则是蔡邕作为史学家熟读经典博采百家的缘故。 又因为蔡邕所用典故多出自《尚书》《诗经》和《左传》,所以钱基博先生认为蔡邕的文章“大抵以《书》之端凝植其骨,以《诗》之安和植其节,以《左氏》之整暇调其机”[45]。其见解尤为深刻。
其二,史书力求简要的撰写准则使得蔡邕的碑文叙事简要。 史书的撰写要求简要,所谓“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 ”[46]蔡邕作为史学家深谙简要之道,并将其运用到碑文的创作中, 其碑文的简要主要体现在叙事精练上,具体来说是概括笔法的运用上。 如《陈太丘碑》(一)中蔡邕将陈寔的一生经历概括为 “四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将军,宰闻喜半岁,太丘一年……会遭党事,禁固二十年,乐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谄上,爱不黩下,见机而作,不俟终日”[47]。其中“四为”“五辟”“六辟”“半岁”“一年”,极为简要地概括了陈寔的仕宦经历;接着概括其在党锢之祸中的遭遇及态度,寥寥数语就叙尽陈寔一生。 再如《太傅安乐乡文恭侯胡广碑》言胡广:“五蹈九列,七统三事,谅暗之际,三据冢宰。 和神人于宗伯,治水土于下台,训五品于司徒,耀三辰于上阶,光弼六世,历载三十。 自汉兴以来,鼎臣元辅,耄耋老成,勋被万方,与禄终始,未有若公者焉。 ”[48]此数句将胡广仕宦经历包举无余,用笔何等简括。 又辅以议论,尤为精允。 蔡邕作为史学家其碑文多简要之作,正如刘勰所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 才锋所断,莫高蔡邕……其叙事也该而要, 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矣”[49]。 此处的“其叙事也该而要”即称赞蔡邕的碑文叙事全面又简练,詹解释云:“碑文不如史传详尽,但也不能遗漏太多,因此必须精要”[50]。 近代学者冉德昭评论蔡邕的碑文之间简洁云:“伯喈最善叙事,遣词与命意俱能烦省合度,锤炼工整,所谓‘文约而事丰’者也”[51]。
蔡邕一生虽在诸多领域皆有建树,但综观蔡邕的仕途履历和人生追求,其更是一名史学家。 作为史学家,随着东汉末年碑文创作的兴起,蔡邕亦参与到创作碑文的热潮中,虽然碑文文辞的典雅要求其作者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但碑序与史传相似的文体特征则需其创作者具有史学素养,蔡邕则兼文学家和史学家于一身,而史学家长于人物传记的创作习惯使得蔡邕在创作碑文时仍以叙事和刻画人物形象为长;史学家善于剪裁的素养使其所作碑文善于选材;史学家秉笔直书的史学的原则使得其笔下碑主的行迹多合于正史;史学家常用的“互见法”和“春秋笔法”亦被蔡邕用来撰述碑主的事迹。 而史书对语言的要求又使得其碑文叙事简要语言简洁,总之,蔡邕的碑文之所以能取得极高的成就即得益于其史学素养。 黄侃先生在《中国文学概谈》一文中极力称赏蔡邕的碑文,认为“《史记》《汉书》,尚未纯粹。 质言之,班较胜马。 至《汉书》以下之文,陈陈相因,四字一句,此种体裁,实出自议碑。 而议碑则以蔡邕为主,其后范蔚宗以碑为史,韩退之以史为碑,盖范受蔡之碑版影响也”[52]。 黄侃先生认为其后范晔的《后汉书》以碑为史和韩愈的以史为碑皆源自蔡邕,亦反映出蔡邕碑文以史为碑的特点,而蔡邕碑文以史为碑的特点正是源于其史学家身份的影响,并且蔡邕以史为碑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唐代韩愈的碑文亦呈现以史为碑的倾向, 考其滥觞所出,则起于蔡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