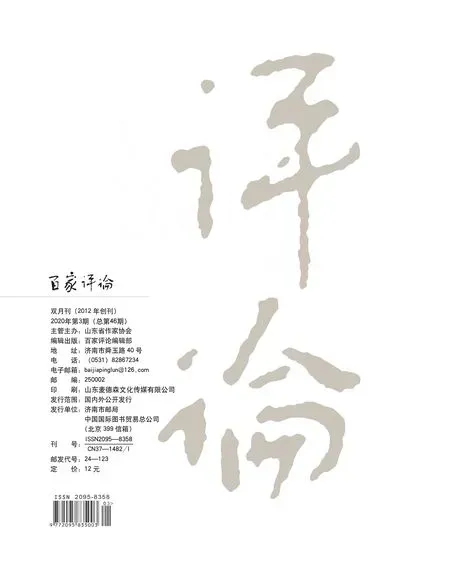小说意象世界的建构与探索
——评房伟长篇新作《血色莫扎特》
内容提要:《血色莫扎特》是房伟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该小说是房伟在现实主义创作路径上进行的个性化探索。在突出故事性叙事特征的同时,小说运用“音乐”“刀子”与“蛇”三个意象对主题话语进行丰富和深化,并产生了强烈的艺术冲击力。“音乐”意象构成人物情感发展的媒介,主导了小说叙事的情感基调。“刀子”意象指向深刻的时代困惑,有效呈现和表现了时代的某种症候。“蛇”意象成为当下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注脚,为小说主题话语增加了惩罚和救赎的复杂元素。三个意象的内涵层层深入,具有鲜明的意象审美特征,并显示出独特的创新品格。
房伟的小说创作愈来愈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关注。继短篇小说集《猎舌师》后,房伟推出长篇新作《血色莫扎特》。从批评家向小说家的“转换”中,房伟的每一次创作总能给读者带来新阅读体验。《血色莫扎特》也是如此。房伟这次是想在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径上进行个性化探索。《血色莫扎特》写了一个谋杀案的故事,很像惯常的“悬疑小说”。故事发生在一座北方小城,从“凶手还乡”开始叙事。小说采用了多视角叙述的结构,五个好朋友,除去“一死一逃亡”以外,剩下的三人轮流讲述,追索真凶的叙述时间中交织着故事时间,叙述线索中散落着无数回忆碎片。小说中每个人都有诉说机会,每个人都有难以启齿的秘密,这对“悬疑”氛围的营造恰到好处。但房伟显然没有把小说叙事停留在故事和结构的浅表层面。小说中,房伟注重“虚实相生”叙事效果,在清晰的叙事表征之中赋予主题话语更多复杂性,从而形成了宏阔的艺术境界,正如宗白华所说:“化实景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①这个过程中,意象具有了独特艺术作用。对其中意象的理解就成为走近该小说世界的重要通道。在《血色莫扎特》的情节推进过程中,“音乐”“刀子”与“蛇”三个意象让人印象深刻,它们支配着整个小说的叙事基调,意象内涵层层深入,形成了强烈的艺术冲击力。我们就从这三个意象开始,讨论《血色莫扎特》的意象特征,从而走进其丰富的小说世界。
一、音乐:情感的基调和媒介
首先是“音乐”意象。从小说命名中的“莫扎特”一词,读者就可以感受出来“音乐”意象的某种特征。从小说的整体叙事来看,“音乐”意象贯穿始终,并蕴含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无论是人物之间的联系,还是人物命运的发展,音乐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要素,对故事氛围的形成和人物情感的联结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是“音乐”意象决定了小说叙事情感的基调。小说题目中的“莫扎特”,一方面指美妙的音乐,另一方面成为一种隐喻——即“莫扎特”这一伟大音乐家人生遭遇的隐喻,如小说最后所注“莫扎特之死,是音乐史上的谜团”,指出有研究者认为莫扎特死于谋杀,其死亡与婚外情和音乐都脱不开关系。这显然为小说定下了悲剧的基调。小说正是在这个基调中形成了整体的叙事情感,并在其中推进故事的发展。这个情感基调,我们从主人公葛春风的叙述语气中就能明显感受出来,比如他认为:“‘明亮耀眼’的东西,都是害人的。比如,音乐,舞蹈,友谊,爱情,刀子。”葛春风将“明亮耀眼”和“害人的东西”画上等号,这近乎是一种病态的倾诉,呈现出某种压抑的悲伤语调。葛春风正是以这样的语调进行叙述,回忆曾经的庄严歌剧和优雅的钢琴曲,再从幻想中的维也纳金色大厅回到现实中的“苗苗的客厅”,从而形成小说的伤感叙事氛围。
如果说夏冰和韩苗苗的情感叙事是这种基调中主要展开的对象,那么夏冰和女学生冯露的遭遇则形成了叙事情感中最低沉的部分。情窦初开的少女恋慕年轻有才华的钢琴老师,尽管这位老师是有妇之夫,她还是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音乐引导着两个人彼此靠近,迸发出道德之外的情感。这种爱情也是音乐的刽子手,冯露葬送了夏冰的“音乐生涯”:“他的手在粪池里,他的头脑中却响彻着庄严的音乐剧。”这种相遇打击了一个“钢琴王子”的自尊心,并因此摧毁了他的音乐世界。正是在这一刻,那些音乐大师一个个从夏冰的头脑中“告别”式地掠过,这宣告着夏冰音乐梦想的终结。从此,夏冰认为自己无法再用这双“肮脏”的手抚摸琴键了,他不愿再去“亵渎”大师的作品。冯露用这段畸形的爱情毁掉了夏冰充满浪漫想象的音乐世界,同时也使她失去了自己的“音乐梦”。在这里,音乐不仅形成一种“事件”,而且也使人物的心理和观念形象化,形成了“音乐”意象,从而强化了故事的悲剧氛围。
二是“音乐”意象构成人物情感发展的媒介。“艺术的生命不是‘物’,而是内蕴着情意的象(意象世界)。”②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情感发展正是通过“音乐”媒介来完成的。大学时代,葛春风因为好奇结识了“钢琴王子”夏冰,继而认识了韩苗苗。青春时代的单纯美好就像一首悠扬的钢琴曲,音乐也成为青春、自由和激情的象征。韩苗苗是只“高贵的天鹅”,然而她的舞蹈也离不开“麋鹿”夏冰的音乐配合,音乐成就了这对校园里的“金童玉女”,而悲剧也从这里开始。值得注意的是,几次大型的文艺演出不仅推进了小说的情节,而且也是人物情感建立和发展的支点。在故事情节中,人物往往在充满音乐的场景中相聚,譬如,在毕业后的演出现场几个主要人物的相逢,等等。人物的每次相聚都会出现不同往昔的情感交流,产生新的情感况味,形成新的情感线索,而此时音乐不仅是情感发展的媒介,也是人物精神世界的某种象征,形成显著的审美意象特征。
“苗苗的客厅”是小说中突出描写的场所。这个场所实际上是一个家庭聚会的地方。几个好朋友在闲暇之余,相约在韩苗苗的客厅组织音乐沙龙,音乐是失意青年们的情感寄托。走出象牙塔之后的夏冰和韩苗苗,也只能在自己的客厅“施展才华”。他们在这里放纵歌舞,诉说或者倾听对方未曾实现的梦想,在音乐中进行嘲笑和自嘲,安放理想或释放欲望。在这个“乌托邦”的世界里,他们分享着不同风格的音乐,用音乐的在场来淹没和实现一切。在这个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真实与荒诞、欲望与情感、物质与精神在狭小的空间中混杂、融合,这个空间就是这些青年的精神王国。房伟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苗苗的客厅”,在叙事中显得自然顺畅,同时又呈现出别具匠心的艺术效果。“苗苗的客厅”是边缘的和压抑的,也是放纵的和自由的,它与外部的环境相望和对峙,并以音乐混响的形式与环境对抗,从而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音乐已经被“抽象化”,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时代精神象征。
人物情感的终结甚至是死亡也都有“音乐”意象的在场。譬如,小说最后对夏雨的死亡描写。夏雨选择和母亲韩苗苗一样,决定在音乐剧的旋律中了结所有的情感,走向生命的终结。死亡是一种抗争,“在文学的视野里,死亡本身不再是只具有社会认识价值而变得毫无意义,死亡本身还是另一种方式的抗争,是世界的另一种真实”。③房伟对其死亡方式的安排也充满了更多的意味。夏雨在音乐中生,也在音乐中死,音乐在其生死之中形成一种尖锐而又沉闷的力量,生成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在这里“音乐”意象已不再停留在某种观念的具象化,而是上升到审美层面,有效参与了小说主题话语和艺术内蕴的建构。
当然,“音乐”意象也并没有失去对“美”的一种象征。它在小说的叙事中也指代了美好的青春、梦想与追求,对葛春风、韩苗苗、夏冰等人物的精神世界也涂抹了一层绚烂的浪漫色彩。这种色彩与灰暗的现实色调调和在一起,共同形成了“音乐”意象的复杂内涵。在这个基础上,小说对“音乐”意象包裹着的世界进行了深入的探寻,探寻的结果则是“刀子”意象所指涉的对象。
二、刀子:命运和时代症候的一种指涉
“刀子”意象在《血色莫扎特》中呈现出独特艺术内涵。与“音乐”意象一样,“刀子”意象同样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同时,“刀子”意象指向更深入的时代困惑。“刀子”意象首先以“实物之形”——作为“凶器”,推动了小说的情节发展。刀子作为凶手的作案工具,是追捕真凶的一个重要线索。吕鹏通过对刀子多次仔细的观察,逐渐辨别真凶,找到了“案中案”的突破口,查到真凶,还原了真实的夏冰。实际上,小说中不只是一把刀子,而是出现了多把刀子,并逐渐形成了对人物某种“意念”的象征。韩苗苗被杀现场里第一把“刀子”是冯露拿起来伤害自己的,在夏冰、韩苗苗和冯露三个人的激烈争吵中,夏冰失手用刀割伤了韩苗苗。刀子是冯露拿的,她也割伤了自己的脖子。
这里还有一把刀子,在暗处等候、伺机行凶的郝大志手中。在凶杀案之后,“刀子”留在了冯露的心中。在以后的生活中,心中的“刀子”成为冯露重要的精神支撑,她甚至感谢凶手郝大志“帮助”自己杀死了韩苗苗:“等我醒过来,警察已经站满了我的家。我没看到那个郝大志。但是,他做了我想做,可是没做成的事。我要感谢他。”“刀子”的意念支配了她所有的行动,推动她帮助夏雨复仇。冯露以“忿怒莲师”的名义“伸张正义”,“让所有‘不义’的人都下地狱”,也向葛春风寄发了“死亡请柬”。此时冯露所有的欲望都由心中的“刀子”发出,这种极端的意念已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刀子”还是人物命运和生命的象征。小说中主要的女性形象如韩苗苗、冯露、邹红玉都具有“刀子”般锋利、刚硬的性格特征。小说尤其突出了对韩苗苗的塑造,指出她是一个像“清水里的刀子”的女人,葛春风、薛畅、吕鹏在各自的叙述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特征,从而把刀子这个物体与韩苗苗的性格、命运和生命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刀子也因此具有了显著的意象特征。
从阅读感受来看,“刀子”意象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它指向更深刻的时代困惑,这是这个意象最重要的审美内涵。我们看到,《血色莫扎特》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是快乐的,葛春风、薛畅、吕鹏、夏冰、韩苗苗、冯露、夏雨等都充满了忧虑,这种忧虑来自于不同的方面。小说在此基础上只是建构了“刀子”意象,而把对这种普遍忧虑的追问留给了读者——这也是“刀子”意象内涵的一种延伸。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这种精神状况称为时代的忧惧,并指出它无处不在:“忧惧与每件事都摆脱不了关系。所有的犹豫不定都沾染上了忧惧的成分,除非我们能忘掉忧惧。牵挂使我们无法适当地保护自己的生命。”④《血色莫扎特》中表现的情况甚至超过了这种忧惧,而是时代的“伤痕”。
小说中“伤痕”是普遍的,每个人都伤痕累累——肉体或精神上的。譬如,葛春风在麓城的失意和愧意地离开,以及最后面临死亡的选择;夏冰“音乐之梦”的破灭,生活所迫和尊严的丧失,以至“负罪”逃亡,最后成为枯井下一个“伤心至死的灵魂”;韩苗苗家庭的困顿,被诱受辱以至被杀;薛畅经营仕途负罪累累,最后也死于复仇之刀;吕鹏生活在案件的血腥和世情变幻中,内心的伤害也使他暗自伤神、感喟不已。正是种种“有形之刀”和“无形之刀”使每个人留下伤痕甚至失去生命,几乎没有人能够刀俎余生。更可怕的是,这些“刀子”可以传递下去,继续给人带来新伤痕。譬如,作为下一代的夏雨和冯露就接过了这些“刀子”,并且让它们变得更加锋利,上演着诡异、残酷的凶杀剧目。从这个意义上看,“刀子”的意象就具有了更加“形而上”的意味,具有更加抽象的审美特征,指向了“世界的本质”,即“伤害”是世界的本质。
从“刀子”的意象不难看出房伟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房伟的思考并没有从现实的“挤压”和人生的“窘迫”这样的角度展开,而是在“伤害”和“毁灭”的维度上把握和表达对世界的认知,并以“刀子”的意象来呈现这种反思和理念,这大大拓展了小说的思想深度。而且,“刀子”的意象是对“音乐”意象的一种递进,这增强了小说叙事的节奏感和丰富性。“音乐”意象营造了叙事的整体氛围,铺垫了情感的基调,也预示了曲终人散的结局。而“刀子”意象则指向这个氛围中的世界深处,指出这个世界某种“伤害性”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刀子”意象也集中体现出房伟现实主义的创作诉求,并呈现出房伟独特的审美旨趣。在喧嚣斑驳的世界中,“刀子”意象以一种犀利的力量有效击中时代的症候,形成小说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房伟的思考远没有结束。在“伤害”本质的世界中,人又如何存在?如何安放自己的精神?房伟把“救赎”作为答案的一个选项,并运用“蛇”的意象来表达这种思考。
三、蛇:时代背景中欲望和救赎表达
“蛇”的意象对于《血色莫扎特》主题话语和艺术魅力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小说中关于“蛇”的叙写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吕鹏所说的“贪食蛇”游戏,一处是夏雨叙述中内心深处复仇的“大蛇”。这两处的“蛇”,显然都具有象征意义。重要的是,这种象征意义契合了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和命运的发展,成为人物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复杂注脚,表达了时代背景中的欲望和罪恶,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批判力量。同时,小说中“忿怒莲师”的咒语“愿狼口蛇心者地狱永不超生”,这使得“蛇”意象具有了一种神秘的色彩,也使得小说主题话语中具有了惩罚和救赎等复杂的元素。
小说中作为刑警队长的吕鹏,既是凶杀案件的侦办者,又是葛春风、夏冰、韩苗苗、薛畅等人物的朋友,他洞察着案件进展的一切,也感受着案件中人的欲望和罪恶。他感概人们都是“贪食蛇”游戏中的大蛇,不停地吃东西,不停地长大,最后咬掉自己的尾巴。吕鹏的那句“我们都是那条贪心的大蛇”,实际上指涉了每个人欲望化的精神世界,以及不择手段贪婪攫取的罪恶。譬如,葛春风、夏冰、韩苗苗贪心于“三人爱情”,夏冰、冯露贪心于不属于自己的情感,薛畅贪恋于仕途的经营,邹红玉、陈副市长在自己的贪欲中不断地膨胀等等,他们最后都如同“贪食蛇”咬掉了自己的尾巴,宣告了“人生游戏”的结束。可以看出,“蛇”的意义在故事的推进中就是一种观念,它指向对时代精神中某种病症的表现和诘问,它的意象审美性也从中产生。
“蛇”意象的意义还不仅仅如此。贪欲的膨胀带来不断的伤害和毁灭,由此又埋下复仇的种子,产生连环的伤害效应,这使得“蛇”意象的内涵不断扩大和深化。小说中的夏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复仇者”,正如他的自述:“一个人心里,有了一个致命秘密,就如同养大了一条蛇。”夏雨还不到九岁时,就开始养大这条“蛇”。他装作患有自闭症,默记母亲在日记本中留下的秘密,与冯露共同实施复仇计划,并早就预料这条让他痛苦多年的“蛇”早晚会与自己同归于尽。夏雨的人生是一个“杀手”的成长和毁灭过程,是什么造就了他的一生,这是小说留给读者的问题,也是“蛇”意象的深层内涵。
小说中葛春风的精神世界也是“蛇”意象中的重要内涵。葛春风是小说中最为复杂的人物形象,他有热情和良知,同时也怯懦和冷漠,考到省城做记者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逃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能不断地反思和自省,并处于长期精神的压抑和痛苦之中。葛春风回到麓城是看望生病的母亲,但显然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返乡旅程。从整个小说的叙事来看,葛春风的这次返乡更像生命的最后一次释放,是一种终结也是一种开始,正如小说题记所说:“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致命的秘密’。它藏在心灵深处,等待着唯一,也是最后的危险绽放。”小说结尾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阳光下,我举起手掌,托着那药片,好似托着一个即将诞生的奇迹。”冯露准备的这几粒毒药无论葛春风是否吃下,这一刻都成为他新的开始。葛春风被抑郁症折磨多年,他正期待着这样一个新生——心中的“蛇”将走向灭亡。或者相反,葛春风拒绝死亡救赎,怯懦逃离,这也将是另一个新的开始。因此,“蛇”的意象就具有了原罪与救赎的丰富内蕴。
在“蛇”的意象中,小说完成了葛春风“救赎”的意义表达,提供了现代人心灵安放的一个路径。当然,葛春风的“救赎”行为是极端的,是以生命的可能终结作为代价的。房伟正是在生存的这一悖论中展开反思,拓展了对于现代知识分子心灵的表现空间。小说并没有给葛春风更多的选择方式,一开始就安排他踏上返乡之路,最后也没有让他走出麓城,这个安排是耐人寻味的。进一步说,葛春风的省城“逃离”并不能开始“新生”,他必须“折返”,在自己的历史中找到真正的自己,并付出相应的代价才能获得灵魂的安宁。显然,房伟对当代知识分子的认识是清醒的,情感是复杂的。在欲望化的时代中,即使知识分子的灵魂发生了扭曲,但房伟依然努力发现他们内心深处不曾泯灭的良知,让读者在其生死之间看到了人性的些许光辉。从这个意义上说,葛春风是当下时代背景中新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对其返乡的叙写也是知识分子一种新的“返乡模式”。
可以看出,“音乐”“刀子”与“蛇”三种意象都具有心理意象特征,是在作家现实体验基础上形成的感性形象。这些意象呈现出房伟对现实社会的复杂感知,如此“立意于象”也体现出独特艺术悟性和艺术表现力。同时,三种意象在不同人物叙述中形成,因而也是人物自己的观念意象。黑格尔指出:“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因此,我们在象征里应该分出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⑤作为“意义表现”的“音乐”“刀子”和“蛇”,融入小说叙事,给读者以哲理性思考,产生了强烈艺术冲击力。当然,象征性也是现代小说重要艺术品格,如杰姆逊所说:“现代主义的必然趋势是象征性。”⑥值得注意的是,房伟并没有把《血色莫扎特》写成处处隐藏着隐喻、象征的具有现代或后现代特征的文本,而是突显了小说故事性,这并没有削弱小说的象征性品格。上述分析可看出,这与房伟对意象的独特处理密切相关。“音乐”“刀子”与“蛇”三种意象无疑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它们形成的过程也是意象审美的过程,“表现力是经验赋予任何一个形象来唤起心中另一些形象的一种能力;这种表现力就成为一种审美价值。”⑦
作为一位“70 后”作家,房伟的写作呈现了这一代作家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感知:“强悍的现实、无序的情感、鲜活的欲望,总是以各种难以回避的方式,与一个个卑微的个体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形成了种种错位、分裂乃至荒诞的生存景象。”⑧房伟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一直在追求艺术的创新——正像他在《血色莫扎特》中对意象世界的探索一样,这将使其在创作之路上走得更远。
注释:
①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59 页。
②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45 页。
③冉小平,刘志华:《死亡意识:文学创作徘徊不去的结》,《求索》2003 年01 期。
④[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黄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年版,第59 页。
⑤[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10 页。
⑥[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154 页。
⑦[美]乔治·桑塔耶纳:《美感》,缪灵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132 页。
⑧洪治纲:《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18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