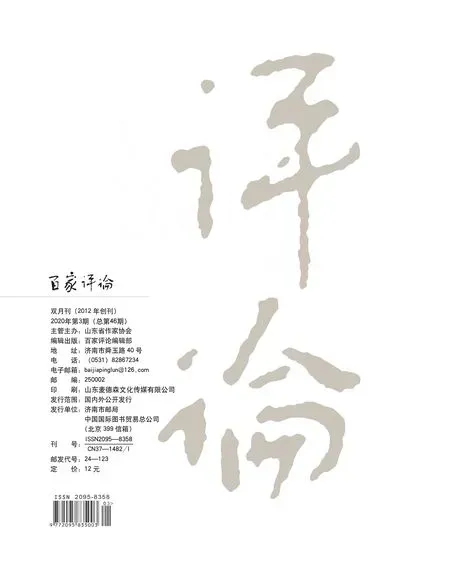时间哲学,或教育现象学
——读常芳小说集《蝴蝶飞舞》
内容提要:在常芳小说集《蝴蝶飞舞》中,她选择童年往事作为题材,以怀旧的笔调刻摹往昔的美好,在少男少女们的情窦上,施展着时间哲学的种种。同样地,也以发人深省的方式,触及儿童教育的问题。巧妙的是,她使用“儿童与成年的换位法”,成功地将儿童题材置换入纯文学的范畴,来映照成人世界中的种种悲哀不幸与命运多舛,实现了对题材的突破和新变。
初读常芳小说的人,可能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以女性的细腻体物至深,一俟这种体察延及到人物身上,则是贴着人物灵魂的爱;这种爱显示出一种人间的大爱格局,它以温润、宽容、慈悲作为基调,以理解、同情、怜悯作为方式,在给予人物以体贴入微的勘察之后,深入到生活的各方面,来发现围绕着人物所构成的环境,既有自然环境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有社会环境之世事洞明皆学问,更有人与人之间的世态炎凉之人情练达即文章。她笔下的小说,并不凸显任何一个人物,却在人物描写的细致入微上,营造出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里传达她的“人间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写法称之为“人物情境法”,即以人物作为小说发展的情境,人物与人物之间互相构成背景,从而并不凸显核心或主要人物,却把所有出现于小说中的他们的音容笑貌、命运浮沉给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既得益于常芳的“体物至深”的写作原理,更得益于这种“人间大爱”的散播与流布,或者说这构成了常芳文字的“播撒”。
一、时间哲学,或童年记忆的温情
书写记忆,或者以记忆作为描绘对象,是作家所常愿嘱笔的选择,其中皇皇巨著者莫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也许是对世间体悟过深,其所经历亦能足以撑起这记忆的一方天地,常芳在《蝴蝶飞舞》中诸多篇什都指涉记忆,挖掘那些沉淀在时间隧道中的美好与欢欣。但只需细细品味,这被时间所尘封了的记忆之所以充满了美好与欢饮,盖源于其“儿时属性”:从孩子们的眼睛看过来,世界充满了阳光与希望、温馨与乐趣,即便是不能懂得人世,也能在自然的萌发中悄然领悟纯粹的人情世故、父母恩情与关爱,而对饥饿、穷困、艰辛并不特别属意。常芳善于在岁月的深处打捞“时间哲学”的思想碎片,但所有这些时间哲学的思想碎片又全部沾染着人间的情怀,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是在一个个少年的身上所闪耀出来的,带着审美的趣味,读来令人喟叹、欷歔。
《四季歌》是一篇写得很美的小说。小说之所以美,在于常芳用了诗意的笔触描摹四季的景观,更在于她用了自己的笔去探求一个少女心中那些奇思妙想。在这些文字中,常芳似乎为这个少女营造了一个安全、可以信赖的避风港,即便外在的世界多么疯狂、多么混乱,她也能在这一片少女的心思天地里,获得纯美的感受。大饥荒的年代,树木枯死,人也不久殒命,这位少女在父母的爱护与关怀下,体悟大自然的美景,甚至于对母亲的刺绣产生天然的景观想象。但常芳并不着笔于少女的饥饿感,反而让让在食物中也领悟到一种极致的美,仿若在这种食物中看到了渴盼已久的景致。也许是她那位饱读诗书的父亲给了她以文学想象的功能,让她在严酷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审美的眼光与心思。饥荒严重,一家人只能选择远走他乡,即便背井离乡的路上,每到一处,少女仍然瞩目于那些美景。等他们到达百花村,一场意外的客栈大火夺取了父母的性命,当她一个人孤独无依的时候,一条狗不但救了她的命也成了陪伴她的朋友。更有甚者,她周围的一切也都美妙起来,对她和蔼可亲——渡口的白胡子老爷爷还能给她算命,终于和她走到一起的少年也成为纯美的人间乐事。常芳其实时时刻刻处处,都像是在维护着少女,不给她以艰辛与困苦,让她在自己的年龄中体悟岁月的精髓,感受时间哲学的思想碎片。这却恰好,符合着少女的心思。
不啻此,《少年法海》看上去是重述一个中国民间的传说故事,但实则是以这个作为由头,来去摸索少年的爱情心思,或者说去研究少年们的“爱情心理学”。少年法海作为大户人家的子弟,饱读诗书,自从两年前听说家里人要给他提亲白家小姐白小素之后,便陷入一种对于情思的美妙绝伦的想象里。他甚至产生了如同《洛丽塔》中亨伯特对于小女孩的几乎陷入疯狂的爱恋,着迷于白小姐的名字、倩影,更为了能够与之相遇而不断跑向西湖周边浪荡,仿佛能从人群中一眼就看出梦中情人来。不单于此,他甚至觉得白小姐身边的丫鬟小青都是绝美的存在,能够令他产生无边的遐想。但不巧的是,身边的书童和寺庙的和尚总提醒他,白小姐是一条大蟒蛇,恋爱不得。少年法海却明知故爱,还给这一份爱加上更为纯美的想象,以至于显得唯一、独特又圣洁。世界也许污浊不堪,人间也许肮脏淫邪,只是在少年的心思中,一切都如此美好。直到少年法海碰到许公子并且知道他与白小姐的婚配,也似乎仍在抱着这样的美好遐想,不愿意承认这是假的。梦中醒来,知晓白小姐已经悬梁自尽、香消玉陨,他依旧怀抱着这一份美好,去寻觅梦中女神的芳踪。古老的民间传说,被常芳拿来演绎少年的爱情心思,可谓是冒险之举。但在她写来却如此适恰,又如此贴切,笔触都在少年法海的身上缠绕,把周围的花草树木、人来人往、房间住宅等都搅动起来,却真真俱是少年的眼光,在在雕刻着少年的心魂。
深藏于常芳小说中的“时间哲学”其实常常撑破了“儿童文学”的外表,而径直走进了对成长的反思、对人世的唏嘘以及对命运的慨叹。小说中,常出现的“这都是命”的感叹与判断,不单单指向了不通文墨的村人野夫,而是要通由他们来传达一种带着宿命论悲观色彩的人生之喟叹。《桃花水母》是一篇很耐咀嚼的小说,写得诗意盎然又缠绵悱恻,把埋藏于时间哲学中的少女怀春、时间的摧残、命运、流水一般的日子等,都容纳在一篇“诗化小说”中。河流、对岸的油菜花、磨坊、诗与哲学、水流的声音……这些外在的铺垫,全都为了烘托少女春来的心思。但对于春来而言,时间一去不返,再也无法重回少年的她,空怀着对少年史小普深深的爱,而不得不接受成为村主任儿媳妇的现实。当时间流逝,促成命运的诞生,且一旦命运来临,绚烂美好的童年时光就被映照为童话般的世界:纯净、美好,充满善意和温馨,带着难以言述的贴心贴肺的爱。如果说《四季歌》、《少年法海》还不舍得让少年们看到成年后的世界,看到时间带来的残忍与恶狠狠,那么《桃花水母》则硬要把这一份现实摆置在眼前,从而形成了一种对位和映衬,愈发显示出那个值得守护的童年世界是多么的美妙。
从选材上来看,常芳确实多选择困境中的少年,然而却不愿意让人间的丑恶、艰辛来给纯美的岁月、年纪蒙上沉重的灰尘,反而举重若轻地聚焦于少年们的心思,看出世间的美好,看出自然的景致,更看出人情世故的协和。这既是久远年代的故事,却也是记忆的力量,更是独属于常芳的“时间哲学”。
二、教育现象学,或可怜天下父母心
不仅聚焦于记忆、历史与岁月深处的“时间哲学”的思想碎片,常芳在这部小说集中,还兼顾当下现实,使得这部小说集在时间的线索上拥有完整的结构。在处理记忆、历史的题材之时,常芳尽可能地以诗意的笔触来进行描绘,可谓每一篇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作。但涉及当下的题材之时,常芳则换了一种笔调,把现实生活中的琐碎用了别样的文字进行呈现。初看上去,这些文字好像未经修饰,呈现出一种泼洒的状态。细细品味,却是常芳提供的关于当下少年儿童们的独特观察视角,因为围绕着他们的周遭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琐碎的世界,精神生活显得疲惫而枯燥,那些诗意的东西也远离了他们,被还原为一个个家长的“教育心经”。需要知晓的是,这里的“教育现象学”并不是要依傍“哲学的现象学”,而是要指明常芳在小说创作中,提供了一种对于当下教育乱象的几乎是“现象学直观”一样的研究,不啻于提供了一部全新的“教育现象学”的力作。
《一只乌鸦口渴了》,可谓是直击当下泛滥的“亲子教育心经”,揭示当下“教育现象学”的种种弊端和病痛。对世界毫不知情的林林带着少儿的目光观看一切事物,并将之当作景观之时,却因为一些行为被家长视为是患病。焦心的父母怀揣着望子成龙的心态,四处求医,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教育观念的讨论。这其实已经触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应该让孩子如何成长——大人们以自己的成年世界作为标准,以他们看到的一切作为要求,让孩子成长为是他们心目中的模样,却不知道如此其实是戕害了孩子们的天性。父母构成的家庭环境如何进行言传身教,社会环境如何影响到了孩子,甚至是如何保护孩子的自尊心,让他们自由、自然或者说随着自己的天性来成长,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林林的父母辗转给孩子看病之后,医生却建议要适当给孩子减少压力——这种教育中经常出现的“父母的焦虑”或者“家长的担忧”,实际上给孩子带去的伤害可谓是触目惊心,尤其是出于攀比和虚荣的心态而来的那种强势父母。
同样是探讨孩子教育问题的另一篇,《蝴蝶飞舞》则关注于一个患了“孤独症”的孩子。但常芳写得非常聪明,她并未停留在对孩子的描述上,而是让孩子提供给一个聚焦,来反映其周边家长们的焦虑与担忧。这种行文思路与《一只乌鸦口渴了》是一直的,孩子的存在提供了一个中心点,甚至是成为一种话题,而围绕在他周围的一切才是常芳要烛照出来的各种社会人生。因为“孩子的病症”,身体上的疾病、精神上的孤独、智力上的欠佳、心理上的缺憾等等,都成为家长们慌乱的原因。夏茫作为一个处于焦点的孩子,却在孤独症的围困下欣赏这个世界的风景,尤其是一再出现的蝴蝶。父亲因为患病的孩子,意志消沉,更因为愧对妻子而无法平息婆媳之间的矛盾;婆婆以头胎孩子聪明的老经验主张生下孩子,仿佛获得了自己的原罪,始终与夏茫被置入同样的境地;母亲由于生下患病的孩子,且再也不能生养而逐渐沉沦下去……一个孩子几乎毁了一个家庭。当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陷入自己的焦虑、痛苦与悲伤之中的时候,有谁去关注一个被疾病围困的孩子呢?常芳无疑提出了一个令所有家长都警醒的问题。
此外,《白色蝌蚪》关注的是儿童被拐。但这个事情同样是作为一个聚焦点,常芳要表现的是大人们的恐慌、焦虑与畏惧。生养一个孩子不容易,尤其是担心他们的成长,还要操心他们不要被拐跑,消失于自己的生活。孩子们却保有他们自己的世界,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建构自己的世界,他们坚信那个丢失的孩子躲在生活的某一个地方,并执著去寻找,却根本没有担忧到自己有可能会变为被拐的对象。
也许,所有书写儿童文学的作家,都会构建儿童的天真世界,去摹写他们的友谊、爱和青春,用美好来去指引他们的成长。但是常芳却以此作为题材,去透视人间万象,去揭露、批判甚至是抗争什么。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儿童文学常识性所构建的世界,只是她并不愿意去为之,反而另辟蹊径,却写出了值得反思的小说。
三、作为外围的内在:儿童、少年心思与他们的世界
常芳的另辟蹊径,就是他在作品中把儿童世界作为一个核心焦点,使之成为一种“作为外围的内在”的存在,从而在互相交织出的背景中,让他们彼此成为背景、反衬,当这些背景与反衬成为一种不能忽略的存在之时,所有的背景都走向前台成为主角,所有的反衬都开始言说自己的心声。这种置主角为背景、推背景为主角的“换位法”,说来确实并不常见,能使其完美交融、互相呈现,更是少见。在这一点上,常芳可谓是独树一帜。这尤其体现在《青黄》一篇中。
小说的取材背景是新中国的灾荒时期,正是神州大地上老百姓吃不饱的集体制时代,小农之家更是难以糊口。妙的是,常芳仍旧秉持着她儿童的纯美笔调,对人间惨相、饿殍满地等都不触及,甚至都不提及,满眼看去都是孩子二青目光中的诗意春色——院落中,杏花开放,对色泽的品鉴可谓得春光之妙;田野里,百草争荣,却在挖野草果腹中透露出春天的盎然生机;豌豆花开,充饥的描写中孩子眼睛里绽放的豌豆花一样的光彩又冲淡了许多哀愁与惨淡。甚至写到工作组成员到贫苦户家吃派饭,也并不展现贫困户的贫瘠、家徒四壁,甚至并不言语到吃食上来,而一任笔墨淌在家长里短、三婶八叔等日常琐事上。直到二青领着妹妹去集体食堂吃粉条,一个孩子的肚皮装下六大碗粉条的奇迹,终于把饥饿、悲惨与不幸揭示出来。不过常芳却并不去忙着写孩子的吃,反而去描摹家长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二青的爹因为尽孝、为了尽人父之责,而去偷生产队的大麦,不巧被工作组的组长看到,为了不至于身败名裂、深陷批斗的漩涡,他竟然用镰刀砍死了工作组长。最绝妙的是,常芳在侦破案件上下足了功夫——没有线索查找凶手,最终只从井里捞出了一把杀人凶器镰刀。为了找出凶手,他们想出了让孩子辨认家里的生产工具的方式,二青作为一个孩子,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很自豪地辨认出了自家的镰刀,那份来自于孩子的天真无邪与成年人的世故老练的对比,实在是令人读后有一种戕害幼小心灵的震撼与悲戚。孩子的善良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孩子的幼稚也是所有家长的软肋,二青的父亲正是在这个软肋上被成年人的狡诈奸猾给利用。
在这篇小说中,二青作为一个孩子,是常芳用心经营的,他顾家、有责任心,也天真无邪,还有孩子独有的那份自豪与虚荣心,尤其是当这种孩子的天真无邪被世故的成年人世界所利用时,一种产生于无奈无助的悲怆之情,油然而生。世故老练与天真无邪的对比,让《青黄》另开蹊径,达到了既定的书写效果。然而如果仅仅是停留于此,常芳的“作为外围的内在”的“换位法”书写方式,就有被漠视的风险。一方面,“作为外围的内在”所指就是孩子的世界,是儿童文学的世界,在对比中更能看出二青的天真无邪与纯美之思。另一方面,“作为外围的内在”还意指着成人的世界,这样二青就变成了一个话题或者一个转轴,围绕着他的大人们,父母亲、工作组组长、村民,乃至于整个历史时期的合作化、大食堂时代,都在孩子的世界映衬下,显得残忍、狡诈、虚伪又带着人祸的悲哀。正是得益于这种“换位法”的写作方式,在映衬儿童世界的同时,它们也被反射得越发鲜亮。
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本来就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常芳用了“换位法”将之调换观察的视角,从而实现“作为外围的内在”的效果,使之区别于一般的儿童文学,又让它获得了与其它纯文学写作的不同特质。不管是书写时间哲学,还是对准教育现象学,可怜天下父母心也好,豆蔻年华易相思也罢,常芳是用儿童文学来书写纯文学,也是在用纯文学来书写儿童文学,话头既是孩子,也同样是大人,但不变的是充满了爱、怜悯与慈悲的灵魂,在这一灵魂的烛照下,在记忆中的童年岁月充满了诗意,在天真无邪的纯美境界中是一颗颗少年的心。不管世界如何改变,人性多么复杂,给予其以淳朴与纯净,是可以排除一切污浊的尝试。从这一点来说,常芳在小说中重新勘定了人类的本性,一种返璞归真的小说哲学也于焉呼之欲出!
同样可用这种“换位法”来理解的,还有《桃花水母》。只不过这里的“换位法”使用了两层的“作为外围的内在”——其一,是春来的“时间置换法”。对于春来而言,她所有的哀愁都来自于美妙的少女时期懵懂的爱情,而这爱情种子一旦种下就根深蒂固,使她再也无法摆脱。从而,“童年”经由“少年”和“成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对于她而言毋宁说是一种“时间的换位法”,让她在“成年”的时间里领略“童年”的美好,如诗般宁静的爱情只能成为油菜花依然烂漫、河流依旧无声流淌,人却已经沧海桑田,一转而为“命运的悲剧”。其二,是“两代人的换位法”,或者说是属于女性的“二重命运设定”。春来在情窦初开时暗恋着史小普,长大后不得不与另一个同村青年订婚,她在真爱与生活之间所做的抉择,早在史小普的母亲身上已经上演,以至于一个能把花绣活的乡村女性选择自杀,而她所深爱的人疯癫而后死去。显然,常芳在这里已经溢出了“时间哲学”的范畴,而使用了“换位法”的方式,来探讨女性、时间与命运的诸多问题,而作为话题的“儿童文学”一转又成为别一种“作为外围的内在”。儿童是外围的存在,却又无处不在成年的世界里,并成为他们的内在,决定着他们的现实生活与命运安排。春来最终只能在惆怅中看见史小普与另一个姑娘肩并肩前行的背影,无奈中黯然神伤,用一场哭泣来埋葬自己的童年和青春,祭奠自己的豆蔻年华和少女心怀,凭吊已逝的时间和注定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