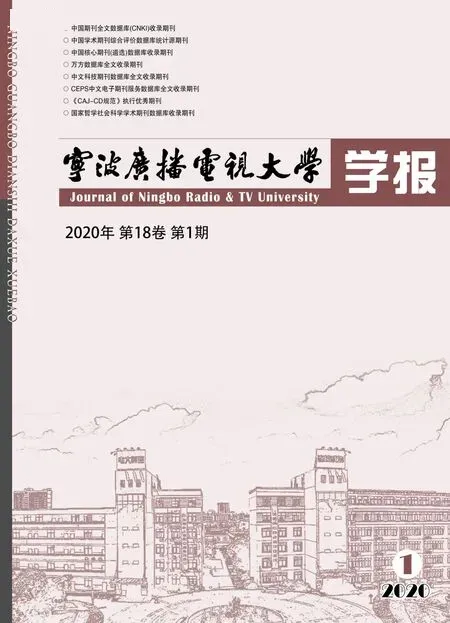浅论东晋郗超忠君问题
王昊哲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魏晋南北朝的人物及思想的研究,是史学界的研究热门。就忠君问题而言,前有先贤的奠基,如钱穆先生的“二重君主观”、[1]唐长孺先生的“先父后君论”、[2]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王朝禅代问题中对于忠节意义的探讨[3]等。后又有众多时彦对于魏晋南北朝忠孝关系的进一步探索,如对嵇康、[4]王祥[5]等个性人物思想的解析和归纳。而尽管如此,对于东晋人物的忠君观问题,我们依旧存在许多盲区与误解。
首先,史学界对此的研究侧重于将魏晋南北朝作为整体进行研究,难以分析出东晋特殊政治背景下忠君观的特殊性。其次,研究始终偏向以忠孝关系为核心。如关于“忠孝观倒错”问题、[6]关于“忠孝论的转变”问题、[7]关于“忠孝分途”问题[5]等等。忠孝关系逐渐对立,并出现了以思想现象论述思想现象的趋势。最后,在浅析人物时,前代学者容易出现以单一的忠奸观评价历史人物的现象。这主要体现在宋代以后文人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上,导致今天以“不忠”之名埋没了大量历史人物。
本文以东晋名士郗超为例,结合东晋的时代背景,以郗超的性格和思想为视角,剖析东晋人物的忠君观,以此试析东晋人物的忠君问题,亦正郗超之名。
一、郗超不忠之名的由来
郗超是东晋时期的一位名士。纵观其一生,奇闻逸事众多,备受当世之人的称赞。赞美郗超的言语,今易查之。如东晋时期的名僧竺法汰、支道林等人就以“一时之俊”赞誉郗超。而民间流传王坦之与郗超二人齐名的歌谣,翻阅史料,竟共有三种不同的记载。谓王坦之者皆为“扬州独步”,但赞郗超之语却有“后来出人”,[8]227“盛德日新”,[9]314“盛德绝伦”[10]1964三种记法,从其逐次递进的现象,不难推测:郗超年岁虽比王坦之小,然随着年龄的成长,才智渐高,以至超越,终被以“绝伦”相称。史书中除了有众多表现郗超才智甚高的记载外,亦有许多表现其品性的记载。比如其人广结贤良,慷慨以助。郗超每次听说有高尚贤达的人退隐,都花费巨资为其置办宅邸以为结交,见《世说新语·棲逸第十八》记载:
“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8]354
郗超贤达至此,深受当世名士赞许。所以郗超壮年而终更受当世名流叹惋,在《晋书·郗超传》记载:
“及死之日,贵贱操笔而为诔者四十余人,其为众所宗贵如此。”[10]1804
此等盛况,就连当时的宗亲贵族也不过如此。而对于郗超才智与品性的赞许与佳论,更有力的记载就是,连他的政治对手,名闻天下的谢安都对他的死惋惜不已。《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记:
“谢公云:‘贤圣去人,其间亦迩。’子侄未之许,公叹曰:‘若郗超闻此语,必不至河汉。’”[8]29
谢安乃当世高门,其评价足显郗超当世名望。
从以上几则史料可见,郗超于东晋乃至南朝之时多受世人嘉许崇拜,是为当世楷模。以至于盛唐之时的儿童读物《蒙求》都将其形象著录其中,以为儿童所晓。然,为何后世其名却逐渐暗淡,乃至于今世之人对其知之甚少呢?追根溯源,因其与桓温密谋废立一事深受后人不解。《晋书·郗超传》对郗超之死有这样一则记载:
“初,超虽实党桓氏,以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将亡,出一箱书,付门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伤愍为弊。我亡后,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不尔,便烧之。’愔后果哀悼成疾,门生依旨呈之,则悉与温往反密计。愔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复哭。”[10]1804
郗超密札解父一事,后人揣摩、议论,无法解释为何此才智出众,受宠于世的名士会作出如此违背纲常伦理之事?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既与桓温皆为密谋,又为何自损名节,将密信公之于众?最终,在宋明理学之下,后世文人以不忠之名冠以郗超,宋代以后的名家操笔者,皆不扬其人,贬抑其为温谋废立之举。郗超也从此被以“不忠”定性,不为今人熟知。
但抱着疑古思辨的态度细思此事,郗超在东晋南朝,乃至隋唐之时的评价都颇为佳绝,而宋明以后却近乎完全负面,这就让历史的本来面貌愈发模糊,引发人们对于郗超言行以及心理的一番思考与查证。在对待“皇帝”,所谓忠君观的问题上,因为郗超的行径违背了后世士人的准则。于是今观诸论:苏轼有“小人之孝”、[11]冯梦龙有“勿为超之智”、[12]李慈铭有“奸谄”[13]等等。但郗超与桓温密谋废立绝非单一的历史事件,驱使此事的价值观是解释郗超其人矛盾之因的根本。故笔者以为后世诸家因受所处时代价值观的影响,忽视了历史人物的时代背景,这些评价缺乏客观性。
二、郗超忠君问题的考量
(一)郗超废立行径的探究
世人皆知东晋以门阀立足于江左,与高门“共天下”。然皇族与门阀之间却纷争不止。前有王敦居功之叛,后有桓温废立之举。世族高门一旦权倾一时,便会威胁到皇权。通常情况下,皇族必寻其他门阀以为盟友,制衡之。故东晋虽为半壁江山,然其内部却多方纷争,瞬息万变。倘若欲立足于东晋朝野,无琅琊王氏扶立之功,又无庾氏外戚之利,那如何在此格局之下长久生存必是诸门首要考虑的要务。
门阀制度之下,士人出仕皆靠门第,先贤时彦们所探讨的“忠孝观念倒错”表现出的正是家门利益与国家利益顺序先后的变化。“侍君”而不“侍家”的行为在东晋是很难出现的。故笔者认为分析东晋士人必须将人物与其家族利益联系起来,方能分析到位。
郗氏之望集于京口,未入中枢,始终没有如王谢之门的大权。其族想在东晋时期站稳脚跟力求不倒确是难题。而就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所言,京口扼建康咽喉,实则为以外治内,凌驾建康的佳处。[14]所以就算郗鉴一生致力于奇谋异策,调和门阀政治的平衡,但因其门望立于京口,郗氏势力就必定成为当时各方野心家的争夺对象。与郗鉴身份相同的中层贵族如苏峻、祖约诸流民帅,皆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中兵败身死,其家门也多惨淡而亡。郗鉴死后,郗氏一门何去何从便需及时规划。
门族之盛依赖人才,而人才之源一是门丁自生,二是于世招募。观郗氏一族,郗鉴两子,长子郗愔,次子郗昙。二人并无大智,亦不善为官。姐妹郗璿与琅琊王氏联姻,为王羲之之妻,兄弟郗昙之女亦嫁入王氏门中,尚可称之为郗门所倚赖的政治资本。但王羲之弃官退出中枢之后,琅琊王氏的政治影响已不及东晋之初。[10]2098简文帝时更是逼迫王献之休弃发妻,断了王郗之盟。故郗氏虽掌京口兵权,但随着郗鉴及老一辈幕僚的离去,中枢势力薄弱,实则极不稳定。时至桓温权盛,京口之权早已非郗氏可控矣。
郗超作为郗门世子,维护家门地位是历史赋予其的重担。如若郗超效仿其父,入观炼丹,修道不闻,郗族之陨在朝势复杂的东晋,必是朝夕之事。因此,郗氏需要一位强权人物的出现以依附生存。但因为强权人物和司马皇室天生的利益摩擦,也就必然导致郗氏利益与皇室利益的冲突。今虽见郗超计谋算尽,未得天年,然郗氏结局却不似与其相当的流民帅集团苏、祖诸门的惨淡下场,可见郗超对其家门的贡献之巨。
太和四年桓温欲夺郗愔京口之兵,见《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记:
“(太和四年)春,三月,大司马温请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初,愔在北府,温常云:‘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于事机,乃遗温笺,欲共奖王室,请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为温参军,取视,寸寸毁裂,乃更作愔笺,自陈非将帅才,不堪军旅,老病,乞闲地自养,劝温并领己所统。温得笺大喜,即转愔冠军将军、会稽内史,温自领徐、兖二州刺史。”[15]3213
故郗氏此时虽然掌握京口之兵,但面对权势熏天的桓温,根本无力抵抗他的吞并。郗超选择将京口家底投资于桓温身上,欲求得郗氏保全,更进一等。太和四年起,郗家与桓温的命运已经绑定在一起。
了解郗超出仕所面临的问题后,再将郗超献策桓温废立之谋分为两点加以探讨。这便是为何废司马奕又为何立司马昱?两位皇帝的身份以及和郗超、桓温的关系即是切入的关键点。
桓温枋头之败,直接导致郗超的投资面临破产。此时郗氏不再直接掌控京口兵权,可依仗者仅为桓温。晋废帝司马奕无为怕事,不理朝政,受重臣摆布。桓温败北归朝面临的是朝中敌对势力的重创。如若桓温政治受挫,郗氏则亦遭所累。为了保住投资,降低损失,同时也是为桓温立威,加强此时唯一的政治保障,故郗超在此时提出了废立的谏言。而郗超为何谏言拥立司马昱,其实可以从郗氏与司马昱的关系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有关郗氏和简文帝司马昱的关系可以在如下几则史料加以推论。
郗超早早就被其父置于司马昱府为官。见《资治通鉴·晋纪十九》记载:
“(永和元年正月)壬戌,以会稽王昱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昱清虚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刘惔、王濛及颍川韩伯为谈客,又辟郗超为抚军掾,谢万为从事中郎。”[15]3047
以郗超出生年份,公元 336年计,郗超九岁便已入仕为官。而此时郗愔却在修道隐居。见《晋书·郗愔传》记载:
“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后以疾去职,乃筑宅章安,有终焉之志。十许年间,人事顿绝。”[10]1802
可以推测,郗愔无心官场,很早就将儿子郗超置于会稽王司马昱府邸为掾。那么此时九岁郗超的见闻应是:第一,会稽王司马昱把持中枢。第二,父亲郗愔隐居山林,不问政事,却实际服务于司马昱。第三,在不久之后,司马昱外部所扶持的桓温又因北伐之故,以“复国”“还都”的旗号,名声大噪。故笔者以为,司马昱在郗超心中为侍主,桓温在郗超心中是楷模,也是一同服务于司马昱的同僚。
至于日后郗超逐渐与桓温相近,成为桓温党羽,但却并无与司马昱交恶的记载。相反,桓温行废立,与司马昱的矛盾正式激化之后,简文帝却多次“以事咨超”,欲从郗超处探听桓温所谋。如《晋书·简文帝本纪》记载:
“及帝登阼,荧惑又入太微,帝甚恶焉。时中书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谓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计,故当无复近日事邪!’”[10]223
可见,司马昱即位后都十分信任郗超。司马昱对于郗超应是存在情感的。
而郗超对司马昱的感情其实更为明显。根据《晋书·郗超传》记载:
“转司徒左长史,母丧去职。常谓其父名公之子,位遇因在谢安右,而安入掌机权,愔优游而已,恒怀愤愤,发言慷慨,由是与谢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阙,除散骑常侍,不起。以为临海太守,加宣威将军,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10]1805
郗超始终认为司马昱会在桓温死后重用父亲郗愔,如果郗超与司马昱交恶,定不会存在此种幻想。
虽今已无从知晓司马昱上位是否存在其和桓温及郗超之间的交易,但可以肯定的是,直至桓温之死,郗超对司马昱都存有侍主之情,也因此错以为司马昱对郗家同样保存有相应的信任。故无论桓温本心如何,郗超的废立之谏,绝不仅仅是保护桓温权倾朝野而已。这其中维护郗家的政治投资,以及对司马昱的情感和幻想可能是其中更深层次的动因。
郗超因为郗愔的无心政治,早早就担负起保门之责。其侍会稽王司马昱,投入政治纷争是保门之举;交出京口兵权,投入桓温势力是保门之举;献废立之策,扶少侍之主继位亦是保门之举。由此可见,保门之举是郗超行事的原则所在,而非单纯地为桓温服务。故后世因桓温有篡谋之心,而冠郗超的“不忠”之名,实则有待商榷。
(二)郗超忠君观念的分析
分析了郗超废立之策的动因后,其实郗超其人的价值观念也就渐渐明了——郗超是一个以郗门利益为原则的家族保卫者。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根据郗超与司马昱、桓温、谢安三人关系的史料中探查出郗超忠君观上的一些问题。
第一,司马昱与郗超的关系问题上,二人为旧属关系,无嫌隙可究。郗超性至孝,以家门利益为重,故帮助桓温行废立后,面对司马昱的顾忌和询问,是以其家门百口为担保的。见《晋书·简文帝本纪》记载:
“超曰:‘大司马臣温方内固社稷,外恢经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10]223
观郗超在此之言,结合郗超行事动因,如若非出自本心,郗超焉能以家族百口保之?笔者以为,就算郗超为桓温心腹,此时担任桓温在朝中监视简文帝的角色,也绝不可能发此毒誓。郗超此时必定是权衡了桓温的欲想,认定桓温此时并没有威胁司马氏政权的想法,方敢以此担保。魏晋时期,投身霸府,却曲线救国的事例其实很多。汉之荀彧助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然其忠于汉室,为曹操谋实则匡扶汉室天下。而更有意思的是,郗超祖上之郗虑亦有和郗超类似的行事与经历。曹操位居丞相之时,任命郗虑为御史大夫,监察百官的同时亦有监视汉献帝的任务。而之后在清除伏后的事件中,一直被视为曹氏党羽的郗虑却变身为汉室的拥护者。故不得不怀疑,郗超亦有此曲线救国的可能。
第二,桓温与郗超的关系问题上,除却上文所述桓温为郗超少年时心中楷模和日后政治投资对象两者外,还有其他值得探索之处。随着桓温权力日盛,逐步脱离司马昱的掌控,君臣矛盾日渐激化的同时,朝中的势力又重新划以派别。郗超此时成为仅次于桓温的实权人物。根据《晋书·郗超传》的记载:
“谢安尝与王文度共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邪!’”[10]1804
而上文分析可见,郗超与谢安交恶是在桓温死后而非此时。故可推断,郗超此时虽有帮桓温清除王谢之权,而未有侵犯王谢利益之实。郗超也就绝对不是一个痴忠于桓温的谋士而已。这也就给了郗超在忠君问题上更多的商讨空间。
第三,谢安与郗超关系的问题上而言,尽管郗超与谢安因桓温死后,司马昱疏离郗愔之事而交恶,但在面临北面强敌入侵时,郗超选择的是毅然抛弃私恨,力挺谢氏。见《晋书·谢玄传》记载:
“中书郎郗超虽素与玄不善,闻而叹之,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时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所以知之。’”[10]2080
此可说明,郗超绝非是受私人恩怨控制的不理智之人。即使此时郗氏已不复有京口之权,然则影响威望多少还有余温,谢玄若想镇京口操训府兵,得到郗氏的肯定是必要的。郗超对于谢氏的肯定以及文章开头所举谢安在郗超死后对其正面的高度评价来看。谢安与郗超的价值观应是极其相似的。至少在忠奸与否的问题上,笔者以为谢安定不会以“不忠”评价郗超。
除此之外,我们亦可在郗超自身的文学作品中,对郗超的价值观念加以分析和推测。近年来,为桓温正名的学者逐渐增多。桓温究竟有无篡晋之心,情况甚为复杂,在此无法断言。但单看郗超而言,笔者以为郗超作为桓温幕僚,在保门之则和所谓“二重君主观”下,每一步的决定都是十分困难的。在其佛学著作《奉法要》中论及“因果报应”之说时,郗超曾有此一段:
“《正斋经》云:‘但得说人百善,不得说人一恶。’说人之善,善心便生,说人之恶,便起忿意。意始虽微,渐相资积。是以一善生巨亿万善,一恶生巨亿万恶。古人云:‘兵家之兴,不过三世。’陈平亦云:‘我多阴谋,子孙不昌。’引以为教,诚足以有弘。”[16]
郗超在文中力图改变传统世人所认为的:阴谋家的子孙将会有所报应的观点。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性至孝的郗超却并无子嗣。根据《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记载:
“郗嘉宾丧,妇兄弟欲迎妹还,终不肯归。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8]362
郗超与妻周氏伉俪恩爱,两人都为信奉佛学。故不生子嗣的原因,笔者推测:谙通佛学的郗超夫妇深信“因果报应”,郗超因为桓温阴谋废立,将自己与陈平相较,定为“多阴谋”者。郗超深怕子孙家门因此不昌,故极力在《奉法要》中想扭转世人传统的认识。郗超作为孝子,却不惜承受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巨大压力。故大概郗超侍奉桓温,献废立之策,终究是极为煎熬的。
而众所周知,桓温北伐前燕之时,史料中对于郗超予以桓温的计策是有明确记载的。《晋书·郗超传》记载:
“太和中,温将伐慕容氏于临漳,超谏以道远,汴水又浅,运道不通。温不从,遂引军自济入河,超又进策于温曰:‘清水入河,无通运理。若寇不战,运道又难,因资无所,实为深虑也。今盛夏,悉力径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阵而走,退还幽朔矣。若能决战,呼吸可定。设欲城鄴,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但恐此计轻决,公必务其持重耳。若此计不从,便当顿兵河济,控引粮运,令资储充备,足及来夏,虽如赊迟,终亦济克。若舍此二策而连军西进,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阂,非惟无食而已。’温不从,果有枋头之败,温深惭之。”[10]1803
今细究之,不管桓温北伐目的为何,郗超之谋确是助桓温胜仗良策,多少有灭燕收复失地的目的。这也可以印证郗超从小视桓温为民族英雄,怀有收复北地之心的推测。否则,如若郗超仅想替桓温行立威篡晋之举,何必等桓温战败势衰后,再予献策。故综合几方因素,桓温南归后的废立是否在郗超原先的预期和计划之中,实在有待商榷。
结合上述的三宗关系和两点推测,笔者想要说明的是,郗超的忠君观不应该用宋明理学下的忠君理论分析。我们应该看到东晋时代背景下,郗超面对家国利益、二主利益时所作出的权衡和所受的煎熬。相较于“不忠”二字,恐怕还有更合适的评价。
(三)对郗超评价的纠正
从东晋时代的大背景下,以思想文化的角度观之,郗超其人致孝于东晋,在这点之上无人予以否认。《世说新语·俭啬第二十九》记载:
“郗公大聚敛,有钱千万。嘉宾意甚不同,常朝旦问讯。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语移时,遂及财货事。郗公曰:‘汝正当欲得吾钱耳!’乃开库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谓损数百万许,嘉宾遂一日乞与亲友、周旋略尽。郗公闻之,惊怪不能已已。”[8]465
郗超散财以助郗愔修好家族名声,又以开篇所举交好士林名士,以提升家族口碑,使当时名士皆因郗超而对郗愔等人敬重有加。见《晋书·郗超传》记载:
“王献之兄弟,自超未亡,见愔,常蹑履问讯,甚修舅甥之礼。及超死,见愔慢怠,屐而候之,命席便迁延辞避。愔每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子敢尔邪!’”[10]1804
皆因郗超在世时为家门作出的贡献,故郗超死后,郗愔才会有反差之感。同时,郗超对其父之孝更表现在其绝伦的才智上。如《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记载:
“郗司空拜北府,王黄门诣郗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之不已。郗仓谓嘉宾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8]417
可见郗超以绝妙的才智和口才,抬高父亲郗愔。加之上文所举,郗超换父书信,依附桓温,避免其父为温所惮,都可以看出虽然郗超与父郗愔性格迥异,然其才智过人,事事为父着想,无论是散财之举、褒父之言亦或是避温之惮,都在力求保护父亲郗愔,孝之深切显而易见。故以孝论之,郗超其人实乃东晋大孝,称颂于南朝隋唐也就不足为怪了。《蒙求》中的“郗超髯参”所想表达的绝非是简简单单的一位古人样貌,郗超少年出仕,品智双绝,保门斡旋的英才形象恐怕才是李翰真正想要传达给后世孩童的吧。
结语
本文寥寥数千字,仅能对郗超的言行举止加以列举,思想价值加以推测,很难用此一例归纳总结东晋时期士人在忠君问题上的共性。但也许正是东晋时期背景形势的复杂,促使东晋人物的忠君问题并不会有简而单之的归结,往往需要通过我们对各类人物的分析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