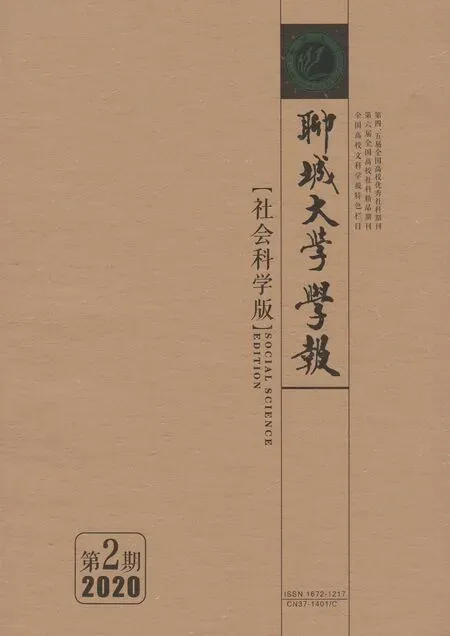西王赏功:大西政权以币制调解军功的策略及其困境
王泽萱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一、问题的提出
西王赏功币,是张献忠在建立大西政权之后,用以对有功之臣进行封赏的特制钱币。钱币的种类按照军功的大小分为金、银、铜三种。此种封赏制度与明王朝实行的赏功币、赏功牌,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虽不完全属于张献忠的首创,却是同期农民起义军中所独有。
根据《古钱大辞典》中的记载,张献忠入蜀后所铸钱币,有“大顺通宝”、“西王赏功”与“西王之宝”三种。关于西王赏功币,其出土实物“最早见于清代光绪末年的四川成都,至民国时期,已相继见有金、银、铜三种质地,并被数位泉家所收藏。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西王赏功钱大多捐赠或出售给各级国有博物馆,一些泉谱著录有拓本。”
由于受到赏功币十分罕见、传世量极少的限制,已有的学术研究自然也就存在着诸多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王赏功钱考》一文中,总述了截至该文发表时学界对西王赏功币出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王赏功币的铸造时间、铸造品种及其与大西政权常用货币大顺通宝的异同点的比较。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王赏功钱考》,《中国钱币》2011年第4期。《大西政权铸币考》一文中,则更加细致地专门论述了西王赏功币作为钱币的特点,以及其具体作用。②《大西政权铸币考》,《四川金融》1998年第2期。总之,传统观点认为,西王赏功币在大西政权中不仅承担了政治性的封赏,也同样作为货币的一部分流通于经济市场中,同时,大西政权本身并没有建立起有效和系统的货币系统。这也就导致了原本只被赋予了政治意义的纪念币被强行与市场情况挂钩,因此其价值的浮动也受到了市场效应的影响,在大西政权的财政系统中成为了不可被忽略的一部分。
2017年初,经过前期的一系列勘测、调研与讨论,正式开始了对被认为是民谣传说与历史记载中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的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大量的西王赏功币与大顺通宝币在内的大量金银文物相继出土。然而,此后刊发的学术研究成果仍存有诸多遗憾之处。《从“江口古战场遗址”等面世实物探张献忠铸币》①《中国文物信息网》,2018年8月23日。一文中,论述了大西政权本身以及江口沉银事件与西王赏功币之间,有可能存在的关系。《张献忠江口千船沉银新揭秘》②《品谋图书馆》,2019年1月24日。则梳理了江口沉银考古结果,更侧重于对张献忠沉银事件本身的研究。
本文以张献忠在货币制度和经济制度采取的举措为切入点,探求大西政权崩溃迅速的原因。笔者认为,张献忠作为农民起义军首领,重视军功的奖赏。西王赏功币初期主要是作为对部属军功的一种封赏,大西政权建立后,开始被纳入到币制体系,以币值和币质来核算军功。但随着局势恶化,钱币稀缺,军功无法正常封赏。而大西政权作为一个以军事起家的农民起义政权,军功封赏制度的被破坏,将会动摇大西政权的根本,并成为导致其迅速覆亡的诱因。由此可见,西王赏功币在大西政权中具有双重作用,初期起到了稳定军心、平衡经济并达到了稳定政权的目的;后期则导致了大西政权的骤兴骤亡。因此,西王赏功币的纪念性质决定了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
二、张献忠起义前期的封赏形式及其弊端
(一)张献忠起义前期的军功封赏
张献忠的起义军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攻陷夔州,后进占成都,自封为大西国王,改元大顺。在这个过程中,张献忠率军经历了湖北、四川等多地的转战。在转战过程中,张献忠在明代军功封赏的影响之下,制定了属于大西政权的关于军功的分级标准和封赏标准。这一标准被记载在了《蜀警录》中:“发安西将军巡嘉眉,方洪二都督分历川南各州县。尽勒绅士入城军民入村,凡居山扎寨者攻之,擒之,斩首剁手无算。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掌一双准一功。凡有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而成都城内人掌,则更几于假山之万叠千峰矣。尝见一札付,自副将升总兵。其札头空白处用朱笔细字备注功级算手掌一千七百有零。”③[清]欧阳直:《蜀警录》,收入《张献忠剿四川实录》,第189页。人的手掌堆积如山,这也许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由此也可知,大西政权建立后,对将士军功多寡的计数,直接取决于杀人的多少。而对杀人多少的统计,则是以手掌的数目多少作为最直接的统计标准。
在这样的统计标准之下,对军功的封赏主要以钱币的形式完成,“西王赏功”币也就应运而生。而这种以金、银、铜三种不同质地的钱币,对军功进行封赏的做法,并不属于张献忠原创,极有可能是受到了明朝固有的三等赏功制度的影响。但有所不同的是,明代的三级赏功制度中除赏功钱以外,另有赏功牌,但从文献和出土文物来看,大西政权都是以不同币质和币值的赏功钱直接对军功进行封赏的。
(二)“赏功币”的历史源流
对军功进行封赏是稳定军心最有效的手段,也即所谓“论功行赏”。这种封赏,在不同朝代中,处理方法并不相同,但从中也能够看出一些传承性。
唐代贞观年间,李世民用以封赏功臣有“官爵奖励、物质奖励、精神奖励三种,以及三种奖励混合并举的方法”④张婵、徐晓利:《论李世民的赏功之道与当代之鉴》,《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11月,第30卷第11期,第10-12页。。这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式的封赏,虽然简单粗暴,但是直观直接,在刺激军队战斗力和提高凝聚力方面很高效。
发展至元代,象征身份的“合符”开始在军功封赏中占据一席之地。“元代的符牌除了用于节制兵马、表明官阶、公文通报、信息传递、交通乘驿、城卫镇戌等诸多管理领域外,其赏功的功能是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的”①李晓菲:《浅议元代赏功符牌的政治功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第23-25页,第23-25页。,元代的赏功符牌主要有“赏朝觐者以远播国威”、“赏军功以鼓舞斗志”、“赏降将以巩固政权”、“赏工匠以强国富民”这样四个功用。符牌赏功的记载,以其在元代的大量出现,成为一个朝代特色,但可惜“这种符牌赏功只是作为维护统治的一种政治手段而随皇心所欲,终元一代基本上没有形成定制”②李晓菲:《浅议元代赏功符牌的政治功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第23-25页,第23-25页。。
到了明代,赏功制度“主要包括查驳功册、拟定赏格”③杨耀田:《明代军功监察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同时在不断的完善中变得复杂。明初时由兵部进行查驳功册,礼部进行封赏商讨,到正统之后则改为全权由兵部负责。而明代军功的判定以“计首论功”为基础原则,如“哨马生擒虏贼一人来者,赏银三十两;斩虏贼首级一颗来者,赏银二十两”④张剑:《明代军功制度初探》,《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12月第4期,第18-22页。。
(三)封赏形式存在的弊端
大西政权的军功封赏制度,将军功完全系于不同币质和币值的钱币,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论功行赏能够公平公正地推行,有利于巩固政权。但是也正由于军功的封赏完全被捆绑于货币之上,直接与货币制度和经济情况挂钩,一旦出现经济危机,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本来的货币面值将不适于继续作为封赏,使论功行赏出现不必要的困难。甚至,当货币出现大规模丧失(如本文的关注核心:江口沉银事件)或损坏时,军功将无法得到赏赐。而由于大西政权以行伍起家,对军功尤为重视,一旦有功而不能赏,对其内部的军心和政权的稳定性都会造成破坏和打击。
三、“西王赏功”币的铸造及其用意
(一)“西王赏功”币的铸造
“西王赏功”顾名思义,出现于张献忠在湖北自封西王,也即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之后。而已知目前为止出土的“西王赏功”币仅见于当时四川,并未曾出现于湖北。根据上文可知,张献忠逗留湖北的时间并不长,称西王的一年后即已入蜀。同时,通过“大顺通宝铜钱、铜印、铜镜、金戒指等大顺遗物,可以看出明末成都有着较为发达的铸造业,为铸造金、银、铜三种质地的西王赏功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⑤霍宏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王赏功钱考》,《中国钱币》2011年第4期,第24-37页,第24-37页。另外,从实物上来分析,“西王赏功”币与同为大西政权钱币的“大顺通宝”币在形制和材质上都有诸多相似性:“两者的内外郭均较宽,背面较之正面内外郭更加宽阔,背部方穿横平竖直,四隅棱角分明。在钱文上,两者皆为楷体,……,稳健而踏实。在钱币质地与铸造上,国博馆藏的西王赏功铜钱与大顺通宝铜钱均为黄铜,铜质精纯,铸造精良。西王赏功与大顺通宝在形制、文字和质地等方面如此相似,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两者有可能铸造于相同时期,甚至可能是同一批工匠所铸。”⑥霍宏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王赏功钱考》,《中国钱币》2011年第4期,第24-37页,第24-37页。根据这些情况,可以大致推算,“西王赏功”币的出现,应在张献忠起义军进入蜀中,于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并开始铸造钱币之时。
而关于铸造地点,学界的说法也很多,“主要有两种:一种据《明史•流寇传》等文献资料记载,认为钱铸于武昌;另一种观点也是据《明史•流寇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认为是张献忠占领四川,建大西国后于四川铸造,有学者并细化到铸造时间大约在入川以后至称帝以前。”⑦王俪阎:《从“江口古战场遗址”等面世实物探张献忠铸币》,《中国文物报》2018 年8 月21 日,第 006 版。而根据“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中出土的西王赏功钱范、钱币等文物判断,西王赏功币的铸造时间很短,而且铸造量并不大,是一种张献忠在武昌和入蜀之后称帝之前分别铸造的,用于赏赐功臣作为恩赏的带有纪念币性质的钱币。
(二)“西王赏功”币的用意和特点
“西王赏功”币,根据其名即可看出其作用,即“西王张献忠用以赏赐有功之臣”的钱币。“就其狭义而言,性质为奖励军功的纪念章,是明代赏功内容与钱币形式相结合的产物,亦属于广义上的钱币范畴。”①霍宏伟:《四川彭山江口遗址出水西王赏功金银币探讨》,第31-46页。而分为三种币制,又有数量多寡之差,反应了大西政权内部军功等级和查验制度的严格。而这种与正常货币同批铸造,形制相似的做法,将用于赏赐军功的纪念币纳入正常的货币体系中,在维持政权和军心稳定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
“西王赏功”铜币与“大顺通宝”币在材质和形制上都颇为相似,但“西王赏功”币为了区别不同层级的军功,除了铜币这种材质之外,还有金、银,这两种不同的质地。根据出土的数量,铜质最多,银质其次,金币仅有数枚现世。甚至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通过上海文管会,自泉家蒋伯埙先生处购得一枚之前,“西王赏功”金币一直处于“金质者,则闻而未见”②罗伯昭:《谭西王赏功钱》,原载《晶报》民国廿四年一月廿八日,收入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下册,第2209、2210页。的状态。从不同币值“西王赏功”币的数量来看,也符合对于军功分层赏赐的实际情况。
四、币制推行与大西政权的覆灭
(一)大西政权的币制及其竞争性意义推行
通过对江口沉银的发掘,“西王赏功”币实物大量出现,对比其实物与流通货币在诸多特征上明显的相似性,使大西政权的币制变得复杂。根据笔者考察,如今出土的大西政权钱币有“大顺通宝”与“西王赏功”两款,其他出现于各种书面记载的大西政权钱币,如“大顺铁钱”、“赏功至宝”、“西王之宝”等,至今并无实物传世,且缺乏足够书面史料佐证,无法证明其是否真实存在。基于此,暂时将大西政权的币制解读为正常货币与纪念币性质的赏功币同时发行并流通的一种币制体系。
关于钱币的流通,“旧钱谱所云‘疑为折二’或‘应是当二钱’、或‘似是小钱,非当二钱之磨也者’等,或因时铸币为前后两期,或因由于地方铸行,或本当时就铸有小平或折二两种,”③刘敏:《大西政权钱币考》,《四川金融•钱币园地》1998年第2期,第53-54页。由此可知,“大顺通宝”的铸造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中存在一些不同规格的钱币。而这些规格不统一的钱币,与纪念币性质的“西王赏功”币一样,也同样在大西政权的财政体系中流通。
货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不仅是经济意义。时至今日,铸造货币仍是绝对的国家行为,币权收归中央,“仍是历代封建王朝所坚持的主流原则。”④沈佳音:《中国古代货币发展中的财政因素》,《财智 FINACE WISDOM》,第88-89页。而发行和铸造货币并将其流通,则代表着这一政权的成熟与被承认。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末清初的起义军急于为政权铸造属于自己的钱币,除了确立经济和政治制度,更是给自己的政权一个符合传统社会认知定义的合法地位,并借此与同时存在的其他势力进行抗争。
(二)币制漏洞与大西政权的覆灭
从上文中不难看出,张献忠在进占蜀中,建立起大西政权之后,并没有相应地、迅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完整系统的财政体系,导致政权内部的经济体系中存在着多种钱币同时流通的混乱局面。而又因为入蜀以后,张献忠虽然建立了属于自己政权,但是“大西政权不能建立财政税收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坚实的财政基础;打粮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恢复社会经济发展,更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⑤万明:《张献忠为什么会有大量白银沉于江口》,《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尤其是在正常货币之外混入纪念币性质的“西王赏功”币,让因为“大顺通宝”自身的币制不统一而已经出现了混乱的大西政权财政管理变得更加困难。
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至顺治三年(1646年)去世,期间战乱频仍,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给张献忠整合一个正处在诞生期的新政权,因此在财政上便出现了首先表现在货币流通方面的问题。这样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让本就仓促建立的大西政权的内部更加堪忧。而同时,将用以奖励军功的“西王赏功”币纳入财政体系中的做法,使得对外的军功与对内的财政产生了直接的联系,即:“西王赏功”币在市面上流通,使得对军功的封赏具有了除纪念币之外的现实意义,在政权建立初期起到了稳定人心和军心的作用;但从江口沉银中出现的大量赏功币、普通钱币、白银、金银发簪等文物可以看出,大西政权在张献忠领导期间,曾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从而导致了沉银这一事件的发生。沉银事件的具体原因尚未可知,但作为目前为止“西王赏功”币最大规模的一次出土,也就说明了这是军功纪念币的一次大规模丧失。起家于军事的农民起义政权,丧失了用以封赏军功的凭证,赏功币本来稳定政权的作用便不复存在,代之以军功无法有效赏赐和兑现之下的军心散乱,进一步动摇作为财政系统根本的经济基础,成为了大西政权迅速消亡道路上的重要助推力。
五、结语
通过本文可知,“西王赏功”币在其铸造前期,确实起到了稳定军心与民心的作用,在大西政权建立初期,协助张献忠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政权。但随着政权的运行开始走上正轨,以及“西王赏功”币逐渐被纳入大西政权的财政体系,其本身的纪念币属性便造成了币制内部和整个财政体系的混乱,导致本就处在战乱中的大西政权内部出现紊乱。张献忠江口沉银,大量“西王赏功”币因此而丧失,直接导致了依赖于此币的军功封赏无法进行,更令大西政权雪上加霜,成为大西政权迅速崩盘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财政稳定和币制清晰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性,以及币制与军事直接挂钩存在的诸多危险性。而这样的危险,不仅存在于大西政权,也同样可能存在于任何一个政权的内部体系。因此,当制定财政制度与军事制度时,不可草率而为,否则便将会为此而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