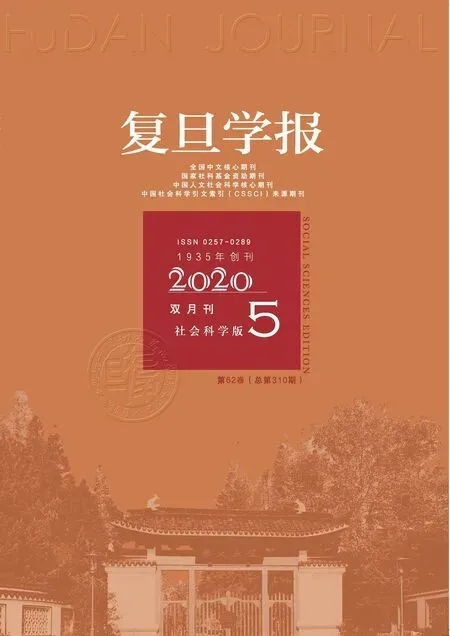现代意识复活中国文学传统
——欧阳黔森中短篇小说论
刘 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评论》编辑部,北京 100732)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全面、积极学习西方的潮流。就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德、赛两先生”的推崇一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一度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认为是在现代中国诸问题和诸价值中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和重要性。与此相类,“五四”新文学也全面开启了中国文学积极向西方文学学习的潮流。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当代小说还是当代文学批评,都被目为是处于自己的“黄金时代”。程光炜说:“最近三十年来的当代小说,真是精彩纷呈,群星灿烂,作家们各显神通,共同创造了百余年来中国小说创作所少见的一个黄金年代。”(1)程光炜:《小说九家·前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前言页。陈晓明也认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谓的“批评的黄金时代”,也是批评话语自成体系、龙飞凤舞的时代,“理论批评摆脱了文本的束缚,终于获得了无边的自由,理论批评的想象力空前激发”,“从七八十年代到21世纪初,理论批评沿着一条自我激发、自我生成的道路高歌猛进”(2)陈晓明:《理论批评:回归汉语文学本体》,《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外国文学理论和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思潮被大量译介进入中国,从视野到方法等各方面,都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产生了内在的和深远的影响,而且其与文学创作的态势和发展,其实是合拍乃至协调一致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先锋派文学,就是向西方学习的文学思潮影响之下产生的。2018年4月20日,贾平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时,谈及自己40多年的创作历程时说:“我们那代人在写作上起步晚,一开始是自己慢慢摸索,那时候是‘独特’的。渐渐地,我开始去拥抱世界、接纳西方文学,学习人家对人性和世界的看法,走向了‘普遍’。到了现在,又开始沉淀出自己‘独特’的东西。我几十年的写作生涯,就处于这样的探索和矫正过程中。”在他看来,外来文化影响中国作家的创作,就如同河水与河床的关系。河水(外来文化)一边冲刷、制约着河床(中国作家的创作),同时又改善和塑造了河床(作家的创作)。基于这种认知,贾平凹强调作家一定要有全球视野,把外来文化和本土意识两相结合,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欧阳黔森能够在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当中,以现代意识复活中国自古代、现代、当代以来的文学传统,形成独具黔地特色的文学书写,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可以给当代小说写作,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以有益的启示。
一、 地域性特征与地质知识性叙事的融入
有研究者认为,欧阳黔森“激活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博物’叙事传统,而且他还着意发掘和捕捉贵州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异人奇事,塑造出形态各异的贵州人物艺术典型,以此激活中国古代小说中以史传或纪传为中心的‘传奇’叙事传统。”(3)李遇春:《 博物、传奇与黔地方志小说谱系——论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而且研究者又认为:唐传奇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小说中一种典型的文体类型,而如若以唐传奇为界,“此前的汉魏六朝‘古小说’如志怪、志人之类”,似可被称作“前传奇”;而此后的宋元明清话本小说(章回小说亦多可归入此类),或可“并入‘后传奇’范畴”。野史杂传的特性,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的一个典型特征,其中,史传性与抒情性、哲理性兼备,而以传记性主人公为题,似也成为古代传奇小说的一个习惯。或者以“传”为名,像《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等唐传奇作品。或者以“记”为题,像《古镜记》《离魂记》《枕中记》《秦梦记》之类皆是。“至于鼎鼎大名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甚至其原始题目就叫做《传奇》,由此可见传奇与史传之文体血缘。”(4)李遇春:《“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欧阳黔森在他的中短篇小说当中,有着对中国古代史传、传奇文学传统的自觉承继,表现于他的小说写作在有意无意当中,体现出了为有着黔地特色的民间人物别立野史杂传的兴趣。众所周知,中国古典小说的史传传统是由来已久的,而为民间人物立传,恐怕亦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传传统里的重要一支。较之史学性更胜的史传,为民间人物立传的“野史杂传”其实也是由史学性的史传衍生出来的,但较之史学性更胜的史传,“野史杂传”更多文学性。亦可被目为中国小说传统精华的一个组成部分。野史杂传“主要致力于捕捉和打捞遗失在民间世界里的野生人物的灵魂”,这种“野史杂传”的古典叙事传统,被认为即使是在现代、当代的中国小说创作中,也绵延不绝、一直承续发展,与西方近现代小说叙事技艺彼此取镜,而不断加以承传和拓新。(5)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61~262页。欧阳黔森的中篇小说《八棵苞谷》,写的是房前就是石山的三崽一家的故事,是作家为贵州的乌蒙山区所作的文学书写。乌蒙山区是富有贵州地域性特色的、呈现喀斯特地貌的地区,欧阳黔森曾在其长篇小说《绝地逢生》的扉页写下这样的文字:美丽,但极度贫困,这是喀斯特严重石漠化地貌的典型特征,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划分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而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作品《报得三春晖》(《人民文学》2018年第3期),作家提到的那个自己曾写进《八棵苞谷》的故事:当年实行包产到户,有一户人家一共分到了大大小小十八块地,但谁能想到呢?不到三分大的地已经是其中最大的一块了,其余皆零零碎碎散落在沟沟湾湾之间。在当地,土地就是人的命,一家人当然要把自家的地仔仔细细扒拉清楚,但是全家人数来数去只找到了十七块地,正当全家困惑不已时,儿子无意间捡起了爸爸的草帽,露出了草帽下石旮旯中碗大的一块地——不承想父亲高兴地说:找到了,找到了。别看这块地小,在庄稼人的眼中,那也是可以种一棵苞谷的……《八棵苞谷》里,白鹰村这一方的石头山太多,三崽在一个小山头山上种上了八棵苞谷。三崽一家所居住的白鹰村美丽而贫瘠,三崽家只能用三崽大妹(大妹本来钟情的是杨家二崽)去嫁给一直喜欢大妹的田家四崽,换来田家妹崽嫁给三崽。小说结尾,新媳妇过门第二天清早,婆婆拿了十六棒苞谷进了媳妇的屋里,那苞谷棒每八棒一组用苞衣结捆起,婆婆要媳妇把两组苞谷棒挂在门梁上。媳妇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做?经三崽口才知,原来是三崽前一年在石头山上种了八棵苞谷,秋后收了这十六棒苞谷。三崽、三崽爹、田家老爹等人物形象,都是欧阳黔森为富有黔地乌蒙山地域特色的民间野生人物别立野史杂传,所写的“乌蒙山传奇”和“乌蒙山人物传奇”。
《村长唐三草》,可视为作家为当过村长的唐三草(本名唐万财)这样一个民间人物所写的野史杂传。唐三草本是桃花村的民办教师,妻子离家出山打工,把婚离了。唐三草颇有乡村生活和工作的智慧,在既当爹又当妈的个人生活处境中,处境艰而不觉艰,还肩负起了村主任的重任,帮助全村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唐三草富有智慧并运用乡间依然存续的传统伦理价值和乡情人情,解决计划生育难题和有人诬告他的事情,是一个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乡间野生人物。《丁香》《梨花》《白莲》和《兰草》等都有中国古代史传传奇小说的因素,可视为都是为民间人物作传的小说。正如有的研究者已经发现的,欧阳黔森的很多小说,都有受到中国式传奇小说文体的影响。短篇小说《敲狗》和《断河》中,就颇受中国古典小说“传奇”的文体影响。《敲狗》对黔地花江镇喜食狗肉民俗的描摹,对“敲狗”这样一种异常残酷的民间绝技的记录,对残酷中仍然有着人性温情(徒弟偷偷放走了师傅打算敲掉的大黄狗)的描写……欧阳黔森能够以不俗的叙事艺术,写下这样一段散佚在民间的故事,“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篇当代的拍案惊奇之作”。(6)李遇春:《 博物、传奇与黔地方志小说谱系——论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小说对花江镇人喜食狗肉的描绘:临街的店门都开狗肉馆,人一爱吃什么就会琢磨出好做法来,所以花江人不止会烹制狗肉,更会特殊的杀狗技法——杀狗不用刀杀,而是“敲狗”。那段小说叙事——厨子用包了布头的铁锤猛击狗鼻梁而致狗毙命的文字书写,真是惊心动魄,让人心中顿生有如亲眼目睹般的不忍。
富有民间传奇色彩的“敲狗”技艺的细节化叙述,可能会是文学史中仅见的一个类似的民间技艺的文学书写,富有黔地色彩和传奇性。要被敲掉的狗被绑缚了之后,任凭狗怎样挣扎,都没用。不仅无法挣脱,反而是越挣扎,脖子上绳索就会越紧。越来越紧的绳索,会让狗憋气,憋到在地上翻滚。瞅准时机,厨子拉动绳子把狗吊了起来。被吊起的狗彻底离地之后,狗会四蹄并用挣扎不已。这时,“敲狗”绝技开始了:厨子用一把包了布头的铁锤猛击狗鼻梁(敲击的力道大小,恐怕也属于一种民间秘技),被敲的狗扭曲了身子,被绳子紧勒的喉咙里发出像奶娃哭泣的声音。敲狗的玄秘就在于,在这猛击中,无论多威风的狗,只能坚持几分钟,便悄无声息了。被“敲狗”技艺敲掉的狗,样子既可怜又吓人——眼睛圆瞪着,舌头夸张地伸出嘴巴,还会有两行泪水流过脸庞。而让人特别不可思议的恐怕是:敲狗的厨子,样子却挺得意,狗的可怜,可能是他习以为常的了。厨子的得意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厨子丢锤子的劲头上,敲完最后一锤,厨子便“把锤子往地上一摔”,而那“锤子便连翻了几个跟头”。厨子不会把狗的可怜放在心上——这与后面所写厨子习惯徒手从烫水里取狗蹄子,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对死去的狗有一定的赎罪的心理,形成反差。厨子关心的是狗鼻梁有没有碰烂皮,所以厨子着急的事是,赶紧用手去摸狗鼻梁,好确定有没有碰烂皮。也许是因为些许的不忍,厨子顺手摸合不瞑目的狗的双眼,厨子的手湿湿的并不是因为有汗,而是因为沾了狗的眼泪。厨子最后还不忘训导徒弟:“看明白了,就这样打。狗鼻子最脆弱,要敲而不破才好。”(7)欧阳黔森:《莽昆仑·敲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284页。
这一带人家从古到今一直坚持着不卖狗的祖规,有了花江镇一条街的狗肉馆后,却慢慢发生了变化。有人继续坚持不卖狗,有人忍不住卖了狗,这就有了中年汉子送来了自家的黄狗,约定过后来赎,厨子却看上了黄狗的皮毛,不肯再赎给他,还想引自己的派出所的朋友来解决问题。看此计不成,厨子最后耍赖坐地涨价。淳厚的中年汉子答应了、又去筹钱时,厨子想失信杀狗,徒弟后半夜悄悄放走了狗,厨子扣了徒弟的工资想抵狗的钱,徒弟并没有如他愿留下来,而是离他而去。中年汉子却守信,给厨子送来了二百块钱,他误以为是厨子信任他,提前将狗放回了家。淳朴的中年汉子表示感谢的方式也很淳朴,他送了几斤自家种的花生给厨子。但实际情形却是(小说结尾),晚上厨子油炸了花生,一个人喝闷酒。因为厨子的徒弟三天前已离去,离去的原因,尽在不言之中……厨子面临着再到哪里招个徒弟的问题。这样的结尾,有些出人意料,又有点令人唏嘘不已。短篇小说《断河》,是一则不折不扣的“黔地传奇”。通过老刀和老狼的恩怨情仇,从晚清写到民国再到1949年之后,直至小说结尾的跨越到新世纪,在短篇小说的篇幅内,写出了一篇“断河的传奇”,是“一个贵州山寨百年间的历史浮沉和恩怨沧桑,是名副其实的山寨传奇”。(8)李遇春:《 博物、传奇与黔地方志小说谱系——论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曾说:“沈先生很注意开头,尤其注意结尾。” 对于《边城》结尾,汪曾祺说:“汤显祖评董解元《西厢记》,论及戏曲的收尾,说‘尾’有两种,一种是‘度尾’,一种是‘煞尾’。‘度尾’如画舫笙歌,从远地来,过近地,又向远处去;‘煞尾’如骏马收缰,忽然停住,寸步不移。他说得很好。收尾不外这两种。《边城》各章的收尾,两种兼见。”(9)汪曾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邓九平编:《汪曾祺全集·卷三(散文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2~163页。像欧阳黔森短篇小说《敲狗》一篇的结尾,就有些“两种兼见”的味道,煞尾的因素更为浓厚。欧阳黔森多篇中短篇小说,都在结尾上有着来自古代、现代文学传统的影响。“平淡中包含几许惨恻,悠然不尽”的小说结尾,或是“须要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清庙三叹而有余音,方为妙手”的“结尾有余法”,在欧阳黔森的中短篇小说结尾处都可见。欧阳黔森中短篇小说体现出的这些特质,与他受的文学影响——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以来的黔地包括湘西文学传统对他的影响有关。在欧阳黔森这里,有来自他的贵州前辈作家蹇先艾、何士光的现实主义文学书写的传统。但实际上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还深受沈从文、受湘西文学传统的影响。这与贵州的地理位置很有关系,许多贵州作家的家乡都是接近、毗邻湘西,或者原本就是在区划上属于湘西。欧阳黔森的家乡在贵州铜仁,铜仁与湘西其实都同属沅陵郡(明代以前),差不多是到明末,铜仁改区划归属入黔地,就连原属湘西的武陵山主峰梵净山一起,全部被划归贵州所辖。这一行政区划的变化,并不会让这里的物事人情发生割裂和遽变,要知道文化传统的作用是巨大的,不会随着区划的调整而遽然发生改变。欧阳黔森家乡的水土风物和文化传统等方面,依然可见楚文化传统的遗留和影响,欧阳黔森与湘西和沈从文之间有着不可言传的血脉关联,和对于湘西以及沈从文文学传统的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传承。欧阳黔森与沈从文的故乡,据考证是两相比邻的(不到60公里)。欧阳黔森在自己的散文随笔里也提到过这一点,他自己“深深地明白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基本文化背景,而且是自己所处地域特有的”。的确如欧阳黔森所说,世界上伟大的作家(一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如此)所写的作品,即使不出其所处地域周围方圆百里,哪怕就是写围绕他的出生地不出十里的范围,并不会因为只写了这么小一个范围的地域性特征的文学书写,而妨碍其成为世界文化的经典——独有的文化背景非常重要。在欧阳黔森看来,沈从文老先生写好了湘西,不就差一点成为华人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奖的作家吗?(10)欧阳黔森:《故乡情结》,《水的眼泪——欧阳黔森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5页。对于全世界的作家而言,写好一张邮票大小的地方,写好一个乡(高密东北乡)、一条街(香椿树街)等,都可以成就一名优秀甚至是伟大的作家。的确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对于贵州的创作实绩而言,从蹇先艾到何士光这些贵州作家的黔地小说创作“都属于典型的现代地域性叙事形态”,而欧阳黔森没有再执著于对黔地文化传统作现代启蒙思想和人性论等角度的发掘,也不再把黔地文化作为落后和愚昧的符号和符码来表现,而是注重凸显黔地的地方性知识,以更大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来反观黔地,“努力发掘黔地本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有效资源,致力于黔地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11)李遇春:《 博物、传奇与黔地方志小说谱系——论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欧阳黔森中短篇小说中,亦可清晰见出他是如何发掘黔地本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而对自古代、现代直至当代以来的黔地文化传统予以创造性地转化。但如果说是“欧阳黔森的黔地方志小说实现了对现代地域性叙事模式的反拨”,似还不很确切,实际上是欧阳黔森建构了新一种、别一种富有黔地地域性特征的小说叙事,从中可发掘出或者说可见黔地的文化传统。这或许可以说,欧阳黔森是在以一种现代意识,重新复活了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以来的文学传统。
欧阳黔森的中短篇小说,有着对中国古代史传、传奇文学传统的自觉承继,并自觉对其加以改造和创新。欧阳黔森小时候喜欢听母亲讲聊斋故事,少时喜读《聊斋志异》,具备“传奇”文体特征的《聊斋志异》和其他中国古典小说,都对欧阳黔森的阅读和写作发生着深远的影响。清人冯镇峦曾说《聊斋志异》是“史家列传体”、“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古典文学研究者石昌渝则认为冯镇峦其实是意指“蒲松龄用传奇小说的方法写笔记小说”,并且进一步修正为“与其说《聊斋志异》用传奇小说的方法,不如说是用笔记小说文体写传奇小说”。不管他们言其是用传奇小说方法写笔记体小说,还是言其是用笔记体的文体来写作传奇小说,都无法否认《聊斋志异》与唐传奇的文体血缘。(12)李遇春:《 博物、传奇与黔地方志小说谱系——论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唐五代小说,借鉴史传形式的同时,有意识地进行虚构,已经表明小说文体的发展趋于成熟,但仍有程式化特点。“开头及正文标注年号,以证人物、事件之真实。小说结尾注明故事来源、出处,同时模仿史传论赞的形式,阐发个人对作品人物所作所为的看法甚至发表对社会、人生的见解,《任氏传》、《柳毅传》、《李娃传》、《长恨歌传》、《南柯太守传》、《冯燕传》等都是这样。”(13)程国赋:《中国古典小说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8、60~61页。单篇小说会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有的小说集也如此对待——在文末作者往往会现身,交待故事所由来和发表议论。欧阳黔森在作民间人物野史杂传和黔地传奇的书写时,是把一些时间的标志或者迹象,自然嵌入小说当中的。他的中短篇小说,并不对时间等故意作模糊化处理,故事发生的地方,常常就是实存的贵州山与水等实实在在的地方,时间也在叙事脉络中被自然嵌入和隐现。欧阳黔森的中短篇小说,有时候用很隐讳的表达方式,或者以具体的物象隐喻的方法来呈现故事发生的时间,这种表现手法在《断河》等小说中就很典型。中篇小说《莽昆仑》《白多黑少》《水晶山谷》《非逃时间》《村长唐三草》等,都可以读出故事发生的地点、时间,地域性特征和现实感都很强。短篇小说,像《敲狗》《断河》《五分硬币》《丁香》《梨花》《白莲》《兰草》《血花》等,也都是可以看到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尤其是短篇小说《断河》,作者不动声色地书写了自晚清、近代、现代、当代直至当下的,一部关于断河传奇、黔地传奇的“传奇史”故事。
中国古典史传传奇小说,常常设置“小说之眼”。何谓“小说之眼”呢?古典小说作者为串起情节、推动情节发展以及方便处理小说结构,小说叙述中会出现各种“物件”,赋予其特殊的意义或者象征意蕴,有时还会成为线索,贯穿全文始终。比如,唐五代小说作家就在小说叙事结构上重视设置“小说之眼”。都是些什么样的“小说之眼”呢?男女定情或者订婚的信物,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小说之眼,像玉杵臼、玉指环、暖金合和梧桐叶等,而其他的东西有时也会拿来作此用,如谜语、词、曲等。它们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第一,具有象征意义。第二,是小说结构里起衔接作用的重要环扣,令情节与情节彼此相衔,贯穿前后文,情节发展有时也由其来推动。(14)程国赋:《中国古典小说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8、60~61页。欧阳黔森的中短篇小说,多设有“小说之眼”。像《八棵苞谷》里的苞谷,《五分硬币》里的那枚陌生姑娘所与、而“我”一直没有舍得花掉的“五分硬币”。像《丁香》《梨花》《白莲》《兰草》,小说标题既是人物名字,又是小说叙事结构上的“小说之眼”。欧阳黔森的中短篇小说,多有地质知识性叙事的融入,有些小说,就是写的地质队员地质工作和生活当中发生的故事,像《莽昆仑》《水晶山谷》《有人醒在我梦中》《远方月皎洁》《丁香》《兰草》《血花》等。黔地的地质、地域知识,被认为除了提供基本的主线索的叙事动力,还形成一种“地质知识话语”,并且提供辅助性的叙事动力的作用,由此欧阳黔森的小说也被认为呈现明显的、新奇的博物色彩,平添了一种所谓的奇异的博物元素。这甚至被研究者理解为系“欧阳黔森小说创作中现代地质博物体叙事的泛化”,而其小说中所有与地质学有关的知识性叙事,也被认为是“欧阳黔森小说艺术的一个典型符码”。(15)李遇春:《 博物、传奇与黔地方志小说谱系——论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地质知识性叙事的融入,也是符合黔地地域性特征的文学书写特质的。有关地质队员生活、故事以及它们所隐现的曾经的一段历史——文学的历史,都丰富了当代小说写作尤其是黔地文学书写和艺术长廊。
二、 “土”与“狠”的美学之上的人性辉光
陈晓明曾以“土”与“狠”的美学,来概括贾平凹叙述历史的方法。陈晓明认为:贾平凹在其代表作之一的《废都》之后,创作是以一种更为朴拙的手法,再次回到乡土——他的小说越写越 “土”,却不是原来写乡土的那种文化风情以及像“商州系列”小说所呈现的美好诗情那样,贾平凹更将笔力倾注于描写乡土生活的原生状态。在陈晓明看来,近二十年贾平凹在小说叙述手法上表现得愈来愈“狠”,乡村从前现代到进入现代所经历的激烈冲突通过这样的叙述手法来表现。“土”与“狠”构成美学关联,成为贾平凹新世纪创作的重要美学特征。“狠”的手法,既寄寓了贾平凹处理历史的方法,也体现了作家小说艺术的干脆利落……其中似乎也涵蕴作家对激进现代性的一种反思。(16)陈晓明:《“土”与“狠”的美学——论贾平凹叙述历史的方法》,《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这里所要说的欧阳黔森中短篇小说中所呈现的“土”与“狠”的美学,不完全同于陈晓明对于贾平凹创作的梳理、概括和总结。
陈晓明强调贾平凹在《废都》之后,创作越来越呈现一种“土”和“狠”的叙事美学特征。“土”是贾平凹贴近乡土生活、和土同泥的创作状态。“狠”是指:贾平凹后期的创作,颇为关注世道人心当中那些使狠斗强所造成的伤痕累累。为了表现乡村的自然和物的世界,在陈晓明看来,贾平凹小说笔法也用力愈来愈“狠”——贾平凹尤为关注 20 世纪的历史剧变和乡土中国艰难进入现代的那些痛楚时刻,“狠”是一种小说笔法和力道(包括用浓重的笔墨描写暴力冲突的现场),“让这些生命向死的行动直接碎裂在干涩的土地上,让他们共同归于物的自然史”(17)陈晓明:《“土”与“狠”的美学——论贾平凹叙述历史的方法》,《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其中短篇小说当中,也呈现明显的“土”的美学特征——当然,这个“土”不完全是贾平凹笔下的《古炉》中的“狗尿苔”式彻底落地、卑贱视角的“土”的美学意蕴,不是《古炉》等作品中那种“动物性”——《古炉》中,作家强调人的“动物性”,以及乡村世界的自然属性,乡村里人的行为和整个的乡村故事,都被作家“赋予了朴实粗鄙、原生自然的属性”(18)陈晓明:《“土”与“狠”的美学——论贾平凹叙述历史的方法》,《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欧阳黔森中短篇小说中的“土”,更加贴近黔地的山、水、乡土和自然,贴近这里的乌蒙山区、喀斯特地貌的地区,或者说是如实描写、贴近具体的像十八块地、三个鸡村、梨花村、白鹰村、汞都、万山,等等。这些地方,真切自然地实现了对黔地的文学书写——具有地方特色和地域性特征的“土”味美学的文学书写。不止有《八棵苞谷》里那样,种下八棵苞谷只收获了十六棵苞谷棒的高度贴近现实和写实的情况,也有《扬起你的笑脸》当中,对着贵州山谷里的不乏诗意的文学书写,对乌江沿岸、梨花寨和人物山鬼这样的乌江沿岸娃崽的惟妙惟肖的书写。
欧阳黔森中短篇小说中“土”的美学意蕴的呈现,一方面体现在贴近黔地乡土山水自然民生的书写,一方面体现在与黔地地域特色相关的地质知识性叙事的融入上。围绕地质队员的工作、生活以及情感等方面的故事,构成了其小说“土”的美学意蕴的一个重要维度。前面已经讲过,有研究者认为,欧阳黔森笔下的地质知识话语,除了提供小说基本的、主线索的叙事动力,即使是仅仅仅提供一种辅助性的叙事动力,依旧可以让欧阳黔森的小说呈现新奇的“博物”色彩,或者为其小说提供一种奇异的“博物”元素。中篇小说《莽昆仑》《水晶山谷》等,如果没有地质知识性叙事的融入,小说叙事将无法展开。全部的人物和故事,都要围绕地质知识话语、地质队员工作和生活或者与地质方面有关的物事来展开。地质性知识话语和地质知识性叙事的融入,构成了欧阳黔森中短篇小说“土”味美学维度的重要一翼。贾平凹曾经在《古炉》里说道:“最容易的其实是最难的,最朴素的其实是最豪华的。什么叫写活了逼真了才能活,逼真就得写实,写实就是写日常,写伦理。脚蹬地才能跃起,任何现代主义的艺术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写实功力之上的。”(19)贾平凹:《古炉·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607页。欧阳黔森是具备这样的脚蹬地的扎实的写实功力的,所以他才能在小说中辗转腾挪出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主义哲学意蕴的一些东西。《断河》,是一个很像新版民间武侠故事、颇似“断河传奇”的文学书写,写得那么“土”、日常和逼真,其实就是蕴含着“最容易的其实是最难的,最朴素的其实是最豪华的”这个道理。老刀、老狼作为刀客仇家,他们的快意恩仇令人印象深刻。儿子辈的龙老大和麻老九,一个阴骘,一个懦弱,龙老大对麻老九,似斗实护了一辈子。竟然在一个小小的短篇小说里,小说叙事时间横跨超越百年。小说结尾却转向了这里因发现了丹砂而成了汞都,而十年后跨世纪的一天里,被誉为汞都的特区却因为汞矿石枯竭而宣布汞矿破产。《梨花》一篇,以无大事、无来自现实的震惊体验,单单以日常生活的书写,就活脱脱写出了一个生动感人的三个鸡村的才女梨花的故事。梨花嫂麻姑也被写得栩栩如生、形象生动,贴地,自然,而土味十足。
陈晓明认为,借由“狠”的艺术手法,贾平凹实现回到历史中去的写作目的。在陈晓明看来,贾平凹可能是要通过“狠”,来抓住 20 世纪历史的一种根本特质。贾平凹在“狠”的道路上一路前行,他《山本》后记里解释他的创作念想和过程:“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地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20)贾平凹:《山本·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523页。欧阳黔森小说中的“狠”,不是暴力叙事以及战乱硝烟魍魉魑魅,但他的中短篇小说也常常展现“狠”的一面。《水晶山谷》以发生在1990年秋的七色谷在开矿爆破时,活埋了田茂林的事件开篇,小说采用倒叙的手法,写了围绕地质叙事展开的小说故事——是乡村的青年田茂林为了攒钱娶媳妇,而倒卖三叶虫化石,后来他又参加开矿,而终于遭遇不幸的故事。田茂林之死,其实是小说叙事所展现的“狠”的一面。《敲狗》所体现的花江狗肉馆一条街的故事,花江人嗜狗肉和独特的“敲”杀狗的技艺,都是体现出“狠”的美学意蕴。《丁香》中的丁香在抢修路基中,山体滑坡埋住了她,这是小说所呈现的“狠”。《血花》中,其实写了一桩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车祸血案。好心的司机老杨大年三十送久居深山的地质队员们回家团聚,为了车不致摔下万丈深渊,他毅然朝山壁撞去而身亡……“狠”是贾平凹回到历史中去的方式,而“狠”对于欧阳黔森来说,是折射人性辉光的重要元素或者说是反衬因素。
《水晶山谷》写的是田茂林被开矿爆破造成的坍塌活埋的惨剧,但只是在小说开头和结尾才稍作点染、接续和呈现出这是一个惨剧。小说展现的是田茂林这个不失青春气息的乡村青年,通过开掘三叶虫化石想攒钱娶白梨花的故事。小说动人之处在于小说叙事时时隐现和散发着人性温暖和人性辉光。小说的后记写道:“据说那坍塌的地方总有一个女人每年去烧香,总像愚公一样搬移那些石头。”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作不止一种维度的解读。《敲狗》在看似残酷和凶狠的“敲狗”(杀狗)技艺中,中年汉子的守信——带钱回来赎狗,充满人情温暖。中年汉子走后,厨子失信坚持要杀狗,厨子的徒弟偷偷放走黄狗,并且被要求以自己的工资抵扣、承担了狗的价钱。中年汉子在狗回家之后依然按约定给厨子送来了几乎是被厨子讹诈、涨价而成的二百元,还送上了自家种的花生作为答谢——小说在“敲狗”的“狠”与残酷当中,独蕴人性温暖和人性辉光。《断河》中龙老大对他同母异父兄弟麻老九的迫害——逼他终生守护在断河边为他捕鱼,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保护,可以保护懦弱的兄弟躲过时代的艰虞……底子里仍然是兄弟手足温暖情愫的充盈(至少是一种遗留)。尽管龙老大后来又送了一个女人来,却是替代不了麻老九对于自己那死去的女人的感情的。麻老九对被龙老大捆住投下断河的心爱的女人,是充满着感情的——麻老九宁愿一直住在断河的乌篷船上,这样就可以常常半夜梦见女人从水里湿漉漉地爬上船头。这梦这感情,无不感人且令人为之伤怀。《丁香》《血花》等小说,也莫不若是——在“狠”的小说结局和小说叙事当中,展现无尽的人性温暖和人性的辉光。
三、 “轻”与“慢”的文体特征
欧阳黔森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呈现受中国古代史传传奇小说影响的因素,也有受沈从文、蹇先艾、何士光等现代、当代小说家影响并对他们加以自觉承继的方面。但他的小说较少受古典章回体小说情节性强、小说内部有着缜密的叙事逻辑这些方面的影响。毕飞宇在《小说课》中分析《水浒传》中林冲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梁山的小说内部的逻辑,这个逻辑极其紧密、严密。毕飞宇认为《水浒传》有着严密的内部逻辑——林冲的“走”,就是按小说内部逻辑,一步步自己“走”到梁山上去了——由白虎堂、野猪林,再到牢城营、草料场等,林冲是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一步步按照小说的内部逻辑,自己“走”到梁山上去了(笔者注:毕飞宇认为林冲不是一堆偶然因素造成的“落草”)。毕飞宇将之称为作家根本说不上话的“莎士比亚化”。(21)毕飞宇:《小说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36页。这其实是中国古典小说讲求情节性、讲求“快”的内部逻辑和叙事节奏的一个典型特征。中国古典小说往往要通过很强的情节性和曲折复杂的情节,来吸引住读者或者说听众。在论述这个内部逻辑性时,毕飞宇也分析了《红楼梦》的“走”所体现的反逻辑——王熙凤离开秦可卿的三次“走”的描写,就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反逻辑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制造的大量的“飞白”有关且互相关联、发生作用。阅读欧阳黔森的中短篇小说就会发现,他受古典小说中讲究缜密叙事逻辑那类文体的影响,相对较小(像《敲狗》中有此方面的承继和影响),而受《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很注意在情节性之外,貌似反逻辑,实际上是非常重视作“飞白”和留白——这些方面的影响较大。
小说“轻”与“慢”的文体特征,似乎更多是自现代以来小说所具有的一个文体特征,是小说既传承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比如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影响,又受西方文学中讲求生命存在和生命哲学意蕴的小说或者是文学观影响的结果。欧阳黔森看重的湘西文学前辈沈从文,就以小说的散文化和抒情性特征著称,其中,是来自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影响的因素居多。而西方文学中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最容易与小说的“轻”与“慢”发生关联,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如迟子建等作家,以其小说的散文化和抒情性特征,表现了小说“轻”与“慢”的艺术哲学。小说的“轻”与“慢”,不仅仅是作家所具有的一种叙事技巧,同时也代表作者的一种面对生活的心理趋向。当“轻”与“慢”的叙事技巧与作者“轻”与“慢”的心理趋向吻合时,便会转化为作家进行小说创作的一种艺术哲学。所以,几乎可以说,小说的“轻”与“慢”,它们既是技巧的,也是哲学的。
“轻”与“慢”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样式的设计中。欧阳黔森不重视去捕捉生活中那搏战或者惨烈的一面,也不是那种向生活取走向和解、求得轻薄乐境姿态的作家。他在山谷、溪涧、竹篱笆等一切他可以将之揽过的黔地自然的元素当中,捕捉遗漏在日常生活裂隙当中的那些人情、人性、人的生命样态和情感的真实动人之处。《莽昆仑》《白多黑少》等中篇小说中,在一种轻轻掠过的、生活的日常性的文学书写中,把人的心理、情感和作家对于生命的感悟一一揭示。人生如浩渺的夜空,悠远而不可见其涯际,如果人活成以一种情感作为人生的全部或者结束,便会不幸坠落为一个悲剧的符号……消逝的生命,带来的是大悲痛,但也应该是丰富的,而不是单一的。生者看待逝者,逝者在生者心里和记忆当中,会留下什么样的折痕、印痕、形迹?或者我们对于尘封在历史和生活的记忆里那些曾经承载了我们真挚情感的人物,该投去什么样的目光?是忘却?是凭吊?是省思?还是纪念和追怀?欧阳黔森的小说中,对此着墨甚多。那几部几乎是以人物的名字来作为“小说之眼”、作为小说题目的小说,都似乎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写出的,小说也因此而呈现“轻”与“慢”的文体特征。《丁香》《梨花》《白莲》《兰草》等篇,都是设置和呈现了这样的一些女性人物形象。《梨花》一篇让人印象尤深。三个鸡村的梨花在麻姑阿嫂的帮助下,读了书,做了“梨花老师”,后来又做了“梨花校长”。围绕她所发生的乡村日常叙事生动感人,但她拒绝了来支教的李老师的追求,做了“梨花副县长”。李老师至今未婚,多情出诗人,李老师写了《这是那夜月的错》发表在省报,但换来的是梨花看了诗,几次拿起电话又放下。“最后,她还是打电话给公鹅乡中学的副校长李老师了。”似乎是断绝了未来情感叙事的可能和走向,但却又似乎并不尽然是如此。这正是小说“轻”与“慢”的叙事结构、叙事节奏的表现,令小说呈现出“轻”与“慢”的艺术哲学和文体特征。
有研究者认为,“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叙事节奏,当然也可以在叙事理论中,将“慢”视为隐含作者和叙述人通过叙述时间、距离调适所制造的效果。欧阳黔森的中短篇小说所形成的“慢”的叙事节奏,是他以现代意识复活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结果。他的小说,不讲求情节的繁富、复杂,不追求叙事的跌宕起伏和大起大落。在一种 “最容易的其实是最难的,最朴素的其实是最豪华的”(贾平凹语)文学书写当中,欧阳黔森的中短篇小说,写实,写日常,写伦理,写情感写人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既便是现代主义的艺术,也都要建立在扎实的写实功力之上。只有脚蹬着现实的土地,作品和文学性才能最终腾跃而起——欧阳黔森切切实实以他的小说创作,以现代意识复活着中国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