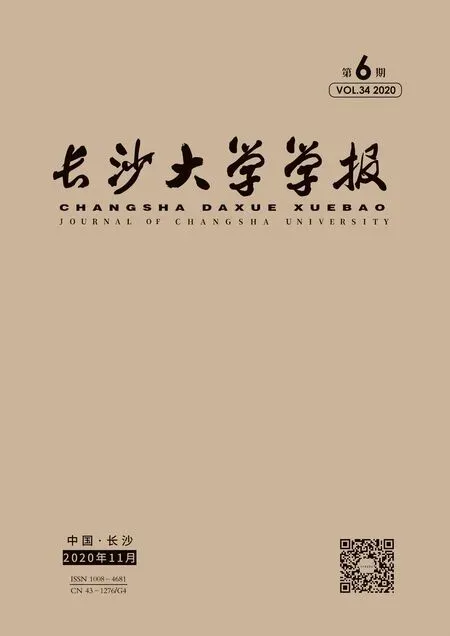文化想象与身份认同:现代中国旅行书写中的异国情调
林 铁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4102051;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旅行作为与中国知识分子相关的现代性事件,可以追溯至晚清以降知识分子的海外旅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旅行书写,成为世界观念在中国传播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五四”以降,现代中国的作家,大多数都有旅外的人生经历。文学史家们发现:“‘五四’运动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第一个十年中,打头的是海内外的旅行记和游记。”[1]10对“异国”的知识生产俨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跨越传统的必经之路。他们的旅行书写既是一次个体的体验,更代表着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一种源自民族共同命运观照下的社会建构行为;既能在风格各异的异国旅途中呈现作家的个体品性,也可以说是一次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想象世界、确认文化身份的集体书写,从而使得知识分子旅行书写中的异国情调,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一 世界与他者:异国情调的现代性意涵
旅行是一种与“异”相关联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异”的前往、发现、重塑和回应。“异”的魅力正是旅行的特殊魅力。读者可以借助旅行的视野,抵达一个陌生而辽远的世界,惊异于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现象。在顾彬看来,存在两个层面意义上的“异”。“异”的概念,具体可以翻译为“异地”“异情”,表示“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与‘异’相对的乃是自己”。其次,“异”表达的也是一种价值,意味着“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人、事、地点等……陌生并不是指一件东西、一个国家……陌生感代表着一种态度”[2]1。概言之,一是实录意义上的异国见闻,二是意识层面的超越本国和既有存在方式的经验价值,这两点都构成了旅行书写中异国情调的内涵。
西方现代性的展开离不开旅行的社会实践。以笛福《鲁滨逊漂流记》为标志,西方现代性伴随着全球地理大发现和欧洲殖民扩张而不断展开。旅行书写中“出于某种行动需要的异国情调具体表现在对探索、冒险和发现的嗜好”[3]139,这成为西方现代性拓展的文学镜像。西方文学中的旅行书写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主体的成长史、空间的建构史。旅行书写对于世界空间的跨文化想象,既呈现为现代性的后果,也是现代性力量的标志。在《关于“异”的研究》一文中,顾彬在谈论“异国情调”时指向旅行书写的政治功能和社会价值。他引述了19世纪末德国著名的游记作家保尔·林登贝格的作品,认为文中对中、日、泰等东方社会文学描述的目的就是激发和提升德国人的爱国主义意识,鼓动德国民众积极参与到世界商业和自然资源等的掠夺与瓜分中来,并通过强化德意志民族的世界政治和殖民地意识,建立起强有力的帝国主体地位。“东方”作为西方文学异国情调的重要素材源泉,几乎成为异国情调的代名词。异国情调的现代性意涵在西方语境下,实际上预设了西方中心、东方边缘的所指。
中国现代性的展开方式极为特殊。晚清以降,中国封闭的国门被欧风美雨冲破,接踵而至的军事失败和丧权辱国条约带来的政治无能,直接促使了清朝的统治者不再用一种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天朝中心”观念看待世界。统治阶层中率先清醒过来的贵族精英走出国门,探知世界,以王韬、郭嵩焘、曾纪泽、张德彝、何如璋、薛福成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官派知识分子出使欧美日等列强诸国。以《乘槎笔记》《扶桑游记》《使西纪程》《欧游随笔》等为代表,他们留下十分丰富和详实的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考察笔记、日记和研究资料。正如列文森所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4]87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列强的炮火和异国的旅途中逐渐明白,以万邦来朝的“天朝”姿态居高临下地看待其他民族(以“夷”“狄”“戎”“蛮”等命名)是虚妄的,中国作为一个朝代国家已经在衰落,如何真正地以一个国家的姿态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中,以本国的方式看待世界中的他国,这关系现代中国的存亡之道。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潮的洗礼下,走出封闭的国门,以各种方式流向世界的各个口岸,在异国他乡感受新鲜的气息,一时之间,旅俄、旅美、旅法、旅英、旅日的游记以通讯、日志以及小品文等多种形式见诸报端。他们的旅行书写,不只是游踪或行踪的记录,更是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民族和国家新的理解,他们在“如是我闻如是我见”的书写中,输入的是启蒙、是革命、是面向未来的价值,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出现在现代旅行书写中的各国景点或其他途径的地点,不仅仅是一种被记录和描述的物理空间,而是被作者赋予、被时代召唤的某种价值符号。
同时,在艺术上,与晚清知识分子那种充满怨羡和批判的海外笔记、政治评论、社会调研不一样的是,“五四”以降的旅行书写,在主题视域上更为多元开阔,既有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等流亡革命家的思想记述,也有周氏兄弟、胡适、汤用彤、吴宓、宗白华、闻一多们的文化感悟;既有瞿秋白、张闻天、巴金们的革命激情,还有冰心、林语堂、徐志摩们的闲情逸致。在风格和形式上更为丰富与疏朗,更注重生活化的细节体验,更强调地理场景和空间情韵的铺设,作品中的异国情调,也从异地考察的实录式研究转向异域风情的审美化想象。郭沫若的博多湾,孙伏园的丽芒湖,冰心的慰冰湖,徐志摩的康桥、翡冷翠等等,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令人难忘的异域记忆和审美意象。
台湾学者廖炳惠在其旅行文化的研究中认为,关于旅行的书写必然会存在一种差异书写,“在差异的比较过程之中,就会产生对本土政治、经济、社会种种文化现象有着批评的距离、不同的观点,也就是文化批判的位置,了解到优越感、自我中心、封闭性乃是闭塞无知的结果。所以旅行会发展出‘比较国际观’”[5]187。正是这一种比较视野中的文化观和国际观,影响着旅行书写对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启蒙与观照。异国的风景、地理以及人文风情等等,它们的出现和存在,与现代中国的价值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纳入知识分子理解世界和自我、传统与现代的思想结构中,服务于中国现代性的知识生产。
二 原乡与异乡:异国风景的命名方式
异国风景是异国情调的基本元素之一。萧乾在描述其海外旅行的心态时说:“在洋山洋水面前不会忘记老家,只会更加依恋。漫步日内瓦霄梦湖畔,心儿却不禁飞到自古丁冬的九溪十八涧。”[6]1这一方面表达出作者去国怀乡的思念之情,另一方面其实也传达着一种对西方风景的中国式的观看方式,即,使用观看中国风景的经验模式看待西方的山与水,在西方的山水与中国的山水之间建立一种互文关系。
异国情调的书写意味着跨文化维度的介入,在风景的叙事上分为两种视域,一是本国风景的异国视域,二是异国风景的本国视域。将异国情调纳入本国风景的视觉生产,将对本国的记忆与经验纳入异国风景的视觉描述中,在原乡与异乡之间完成现代风景的文化设置,背后的动力机制正是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美学建构。
基于异国视域的本国风景书写以郁达夫为代表。郁达夫(1896—1945年)的旅行书写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就是,他更愿意使用西方的地理、风景以及艺术名家名作的名称来表述他所见到的国内风景。比如在《钓台的春昼》里,作者游历浙江名胜严子陵钓鱼台,细致描写了东西两台和周边自然之境貌:“东西两石垒,高各有二三百尺,离江面约两里来远,东西台相去,只有一二百步,但其间却夹着一条深谷。立在东台,可以看得出罗芷的人家,回头展望来路,风景似乎散漫一点,而一上谢氏的西台,向西望去,则幽谷里的清景,却绝对的不像是在人间了。”作者在此刻已经沉浸于钓台幽景的美感中,却突然文笔一转,介入一个西方视角:“我虽则没有到过瑞士,但到了西台,朝西一看,立时就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见过的威廉退儿的祠堂。这四山的幽静,这江水的青蓝,简直同在画片上的珂罗版色彩,一色也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就是在这儿的变化更多一点,周围的环境更芜杂不整齐一点而已,但这却是好处,这正是足以代表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在此,瑞士的风光(来自作者对西方绘画的经验记忆)与眼前的钓台风光基于一种感伤的格调发生了视域融合。郁达夫在旅行中抒发的感伤情怀常以西方颓废美学的方式被再度建构,这显示出他者视域不仅参与了本土风景的表述,更参与了作者现代情感结构的建构。郁达夫对祖国山河的爱与怨,对个人命运浮沉的痛与悲,对未来的期待与失望、颓废与热望、逍遥与飘零,互相交织在一起,完成了他对浙江风景的书写。郁达夫始将西方风景(西方的知识体系)纳入祖国风景的描述中,显示出西方现代性的文化强势对现代中国文化建构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为中国风景的观看设置了一个西方的在场,且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读者。但这个来自异国的读者并非统摄和压制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他会成为一个有力的反思者。
基于本国风景视域的异国风景书写,以蒋彝为代表。蒋彝(1903—1977年),1933年开始游历伦敦、牛津、爱丁堡、都柏林、纽约、巴黎等地,运用诗、文、史、画相结合的媒介形式介绍欧美各地的历史沿革、地理风俗、生活人情,足迹遍及全球五大洲80多个国家,自称“徐霞客第二”。他的文书画结合的旅行书写在欧美热销近半个世纪,被誉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在他的西方游历中,中国本土风景的记忆(包括历史记忆)经常介入到对异国风景的描述中。
比如在《瓦斯特湖》中,记录了1936年7月31日对欧洲名胜瓦斯特湖的游览经历,在这篇长长的游记中,作者一方面用古典格律诗的形式,转译了克里斯托弗·诺斯的诗句“湖育风雨未知实,闲静难降山狂吼。文人犹恐赋新词,敬神沉醉游太虚。永暗隆响沛掩湖,扬波风云扰飞瀑。叹天地神能行异,欢笑骤临悲憾事”;另一方面,又穿插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绘画的区别:“中国画旨在表现画家的主观感受,而不设严格的规则要求重视当地景物。我希望读者不致因传统的风景画而有所偏见……中国画很少以色彩来令画面生动,多以留白点出水和天空。”并在游记中,根据瓦斯特湖的旅程所见,绘制了一幅中国画作品《大陡岩山对面云雾缭绕的岩坡》。这种将中国元素十分突出地引入游记中的做法比比皆是,这样一种本土文化的视域,在对异国景观的观看中直接映射出来,“我继续前行,走进中央荒山(Middle Fell)的双峰,刹那间心头涌起一种熟悉的感觉,那模样神似我祖国庐山的双剑崖,此刻我已有些怀念故乡。未几,一片云岫从山谷徐徐飘近,眼前尽是雾气,凭着对这幅景色的印象,我以米友仁(北宋书画家米芾长子)的画风完成此图。”
在旅游人类学的学者们看来,对于风景的观看实际上意味着游客与东道主(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文化交往,“‘地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关系构造:它既是一种具体的、有形的‘物化构造’——旅游目的地是将游客与东道主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物质的、可计量的存在;也是一种抽象的、无形的‘意化构造’——旅游活动将游客和东道主之间各种难以计量的、肉眼看不见的问题,诸如文化交流、社会意识、族群认同、社会关系、权力话语、文化霸权等,都拿到‘地方’这一舞台上展示和展演。”[7]69在朱自清、蒋彝等人游历西方的书写中,我们看到的并非只是对异国风景的惊奇与震撼,而是一种对本土文化、历史和风景的强烈守持。这是一种根系于本土的文化身份在面对异国文化时所做出的认同回应。
三 想象与凝视:异国情调中的文化身份
现代旅行书写中的相互命名行为,一方面显示出当时中国破碎的民族状况与社会处境中文化身份的游离感:他者的存在,让精神归属与身份确认的问题显得更为迫切;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对世界文化的开放性和融合性:他者的存在,又丰富了文化身份的建构内蕴。旅行“是一种文化身份的主动证实过程。借助时空的转移,借助旅游地的场景和当地人的凝视,旅游者证实自己具有某种文化身份”[8]70。旅行书写中的异国风情实际上也是文化身份的建构内容之一,如何描述看到的风景、如何表达对异域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的认知,实际上也是自我身份的一种主动求证,建构的并非风景,而是知识分子自我的文化立场乃至政治立场。
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对于西方现代性往往怀抱一个爱恨交织的心态,一方面,西方是我们的敌对者和侵略者,对于西方的反抗,是建立民族话语的一个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又是完成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难以绕开的命题。无论在器物层面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旅行书写,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将西方现代性作为文学想象对象的维度。旅行书写中的异国情调,被赋予了乌托邦的价值色彩,充斥着对西方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赞赏与感叹。比如林语堂在旅美的游记中这样表达对西方自由平等精神的赞赏:“德谟克拉西,必自由平等,自由平等,必无佣人老妈。既已平等,何必老妈?”美国民众的生活简单,个性独立,洗衣做饭擦鞋,一切自理,自由自在,不仰人鼻息。这样一种自由独立的生活方式,延伸出的是人人平等和互相尊重,无贵贱等级。在另一个层面上,现代中国旅行书写中的异国情调尽管没有表达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崇拜和学习姿态,却也呈现为“将异国社会文化中的某些特质作为一种理想生活方式”。比如方令孺对日本简易生活方式的叙述:“日本人酷爱自然,崇尚简易,不惯居住在高楼大厦里。那里离自然太远,住在里面心会不安,会烦躁,所以后来他们的房屋又渐渐缩小,返本归真合乎自然去了。”在旅行者方令孺看来,作为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符合人性,贴近自然,不必雕梁画栋,不必喧哗热闹,才是真谛。如果说,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投身于旅苏、旅美、旅日、旅英、旅法的实践中,为寻求未来中国民族崛起的出路而不懈努力,那么他们对这些西方国家文化的看待、选择和改造,实际上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于危机语境中现代中国的民族意识的需要。通过旅行书写,他们最终生产出来的是他们期待中的中国与世界的形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旅游学者尤瑞使用了“旅行凝视”这个概念,来解释旅行过程中旅行者与旅行对象之间的文化权力运作方式。他认为,“离开”是旅游活动的核心概念,换言之,旅游的本质在于“从模式化的日常生活惯性中出离开来,有限度有节制地,同时让自己寻觅并享受一种区别于惯常生活模式的新鲜刺激体验中。通过考虑典型的旅游凝视的客体,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客体去理解那些与它们形成反差的更为广阔的社会中的种种要素。”[9]3旅游凝视显示的就是旅行者与旅行对象、自身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矛盾交织的复杂关系。
正因如此,出于启蒙理想的需要,现代知识分子眼中、笔下的欧洲形象、日本形象以及苏俄形象都是形态各异甚至矛盾对立的。如朱自清、刘海粟笔下的欧美,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和谐、静美、浪漫而充满艺术情趣的气质,比如朱自清笔下的威尼斯:“远处是水天相接,一片茫茫。这里没有什么煤烟,天空干干净净;在温和的日光中,一切都像透明的。中国人到此,仿佛在江南的水乡。”而王统照、郑振铎等人笔下的欧洲则充满了苦难、破败和腐朽。比如王统照笔下的法国并非自由平等的,而是存在等级歧视的,马赛港海关检查官对其他各国游客自由放行,对中国人却要加盖特别印章,提示内容是“宣言到法国后,不靠做工的薪水为生活”。旅途中知识分子的内心充满了文化的碰撞,然而他们正是通过这种碰撞来确认自我的文化身份。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笔下的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形象与郑振铎、邹韬奋等人笔下的欧洲国家形象有巨大的差别,而鲁迅、周作人、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和庐隐等人笔下的日本形象也是千差万别,瞿秋白、徐志摩、茅盾笔下的苏俄形象更是无法相类甚至完全相反。正是因为在跨文化语境下,在异域旅行的过程中对于他者文化的认知存在一个“文化过滤”的现象,所以促使不同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出于个人社会理想的追求的差异还是内心情怀的差异)在面对异国风景和风情时,采取了不同的吸收和改造的方式。
由此,基于旅行者主体的文化意识的差异,知识分子在与异国文化的交流之间,进行了不相一致的转移和借用。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审视世界,认知异域异国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风土人情等方面呈现出来的文化心态是不同的,既有浓厚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古典情怀,又有积极强烈的现代意识;既出于一种对西方世界的崇仰心态,也有一种基于国耻国恨的民族主义情绪。现代中国的“游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传统与现代思想相互撞击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复杂性”[10]。
结语
在跨文化研究者看来,“所有对自身身份依据进行思考的文学,甚至通过虚构作品来思考的文学,都传播了一个或多个他者的形象,以便进行自我结构和自我言说:对他者的思辨就变成了自我思辨”[11]179。旅行书写是典型的本土(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对话的文本。从本土到他者,由他者再返回本土,这一循环而交织的认知模式说明了现代性语境下,异国形象创造的本质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书写对象与范围的扩大和延伸,也并非意味着在强大的西方现代性面前的文化臣服。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异国情调的引入、异国形象的书写以及异国视域的叙事介入,最终是要完成对本土文化的反思、清理和重构。在这样一种跨文化的文学实践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超离与缅怀、对西方文化的倾慕与反思,就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张力,显示出现代中国东西方文化碰撞过程中吸纳与排斥、融合与竞争的矛盾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