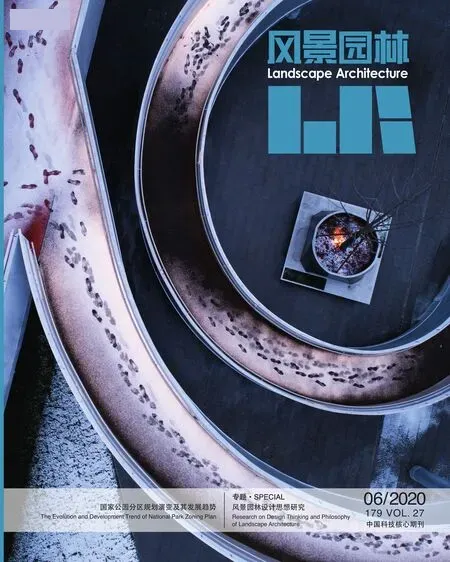以意造园,复以园造意:从《红楼梦》第十七回看文人园林
李溪
如果说《红楼梦》一书的写作乃环绕着贾府和大观园这“两个世界”[1]40,那么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无疑是整部书展露大观园此一文人之梦想世界的开端。大观园的结构之精巧,前人已有很多评述。顾平旦、曾保泉先生很早就指出曹雪芹堪称一位高明的造园理论家,他们认为,第十七回不同于文徵明《拙政园图册》等以一图绘一景的册页,这犹如观中国画的一幅长卷,“既含总揽全园之意,又有曲径通幽之妙”[2]298-299。其实这里不止有画卷,还有“题跋”和“评论”,它们共同显现出文人园林是经由经验、沉思、反省而逐渐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
在这一章中,依各人的视角,主要描写了对园林的3种态度。1)众清客的视角。观察通篇可知,这是具有基本的文人修养,但才识上较为平庸的视角,不过,清客们虽然才华有限,却亦可以判断才学和境界的高下。2)贾宝玉的视角。此乃作者心中理想文人的视角,代表着对道禅哲学和园林思想的精深理解。宝玉既自拟自评,以说明其观念之高明,也评论他人,指出其不足之处。3)贾政的视角。贾政在这一篇中并没有一处拟名或题联,而是作为一个“评判者”出现的。虽其自认缺少题咏之才,但从贾政对清客所拟之名的评论以及对宝玉“沁芳”之名的欣赏,可知其对文人园林的趣味也有很深的认识,但又出于儒家的倾向,偏爱“稻香村”这样的景观。
这样多人物视角的描述,正是《红楼梦》小说的文本性所在。这一文本性或许是一座园林更“真实”的体现—园林的面貌并不是一贯的、固有的,而是呈现于每个人的思想世界和生命境界之中。倘若只看现存园林而加以总结,难免会不加分辨地认为其都是“优秀的传统”,而在小说文本中,贾政和宝玉的评论以及彼此之间的对话和论辩,可以清晰地了解曹雪芹对文人园林在精神和艺术上的最高旨趣的认识。这一认识在文中其以一种公论的形式得到了确认,当然,最终是由读者的内心做出评判。
1 题名之重
这一回的主要事件,并非是单纯的访园和评鉴,众人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题匾对。在开头贾政便说:“这匾对倒是一件难事。论礼该请贵妃赐题才是,然贵妃若不亲观其景,亦难悬拟。若直待贵妃游幸时再行请题,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3]347短短两句话便道出了当时园林命名在“文化界”有共识的3个问题。1)匾对应该专门由“贵重之人”拟之,不可随意拟题。2)题名必须“亲观其景”,若无亲临的经验,任何人也难拟得合宜。3)匾对本身对园林而言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匾对便是园林的命名与立意,它们并非只是园林“组成部分”,亦非如山水画中之人物的“点景”,那是赋予物质形态生趣与意义的“重点所在”。
晚明张岱在给祁彪佳的信中便言:“造园亭之难,难于结构,更难于命名。盖命名俗则不佳,文又不妙。名园诸景,自辋川之外,无与并美。……寓山诸景,其所得名者,至四十九处,无一字入俗。到此地步太难。”[4]105在张岱看来,园林命名的难度更胜结构。文人园林之正源辋川别业,其物质形式早在明代不存,而由王维亲题的辋川十二景之命名得以百世流芳。不过,唐代文人园林,北有王维之辋川别业,南有白居易的庐山草堂,皆是以其“地”命名。而随着艺术哲理化的发展,在宋代以后,多是以“意”命名的园林,且文人多会撰文来说明命名之“意”,如欧阳修之醉翁亭,司马光之独乐园等。张岱在此文中所极为推崇,认为可与辋川媲美的“寓园”也是如此:园主祁彪佳曾亲著《寓山注》,序言总说“寓园”其意,后分说四十九“分胜”,处处也都点到“寓园”之意。譬如“宛转环”一处,乃是“层层旷朗,面目忽换”,于是祁彪佳感叹云:“夫梦诚幻也,然何者是真?吾山之寓,寓于觉,亦寓于梦。能解梦觉皆寓,安知梦非觉,觉非梦也?环,可也;不必环,可也”[5]。“宛转环”乃一梦幻之寓也。此一层层迷幻之境,正是透过这对人生存世于梦的理解而营建,又在营建之后书写出了更为深幽之意旨。他的友人胡恒旁注:“移步换景,非静观玄对,那得见此,是盖以意造园,而复以园造意者。”[5]此景之营,正是“以意造园”,而其名又是“复以园造意”。从此一例,已可以体会张岱说这一“取意”达到“雅”的程度为何相当不易,这不是基于文藻的堆叠,而是本自对生命存世之意义的至深领会。
无疑,《红楼梦》第十七回,也是出于对这一传统的继承。比起文人的诗文、笔记,此回则透过对众人经验的入微描写,以及对匾对之题的评论,更清楚地展现出园林之名如何在一种细致的审思、讨论以及体悟之中诞生,而在此之中,“名”如何“移境”便可窥一斑了。
2 雅俗之辨
园林命名之最高标准,张岱已明言“无有一字入俗”,这也是园林命名同现代的“主题园”(subject garden)或是“点景题名”的区别。后两者仅仅指出命名是表达景致的某一主题思想[6]39,而园林命名的关键却不只在于“主题”,更在于雅俗。有人认为使用古人典故就是“不俗”了,文中以两处题名指出了这一观念的问题。在“曲径通幽”,宝玉言之“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这自然是常说的“古雅”了;而在“沁芳桥”宝玉又不喜欢别人那些“述古”的名字了,这引起了贾政对他的不满:“方才众人编新,你说‘不如述古';如今我们述古,你又说粗陋不妥。”而宝玉将其“沁芳”的命名,自评为“新雅”。述古未必就“雅”,再看整章行文各人对诸命名的评论,正是在说一个“雅俗之辨”的问题。
通观全篇,其所涉用典之俗的问题大抵有四。
2.1 陈旧
所谓陈旧,就是用典太过俗滥,了无新意。如众人到了潇湘馆时,论此处匾该题四字。有人说:“淇水遗风。”贾政道:“俗。”又一个道:“睢园遗迹。”贾政道:“也俗。”显然,在政老口中直接说出的“俗”,也是作者眼里的定论。二者一处用《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典,另一处用睢园,即汉梁孝王“绿竹荫渚”(《水经注》)的菟园之典,都同潇湘馆最点景的物“竹”有关,也算应题,为何被政老称“俗”呢?其因主要在于,这两个典故是文人看到“竹”最容易想到的典故,因经常用在有竹的景致中,几乎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就如园林之于小辋川、小蓬莱、小终南之类,太过俗泛,而由自我妙思所感知的此处景致之独特也自然不可见了。
2.2 落实
所谓“落实”,字义上就是过于直白,不够含蓄,换言之,其只会根据表面的形象寻求命名,而不能将自我的经验推至意义的深处,而丧失了园林空间中的生命灵动之气。因此,落实和俗套常常是同义的。如“蓼汀花溆”一景,书中描写乃是忽闻“水声潺潺,出于石洞;上则萝薜倒垂,下则落花浮荡”,这景色令清客们想到了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旧典“武陵源”。贾政对此名的看法则是“又落实了,而且陈旧”。经过几千年的典故流传,“桃花源”早已被滥用,或有落英夹于两岸,溪水出于石洞,或单是田园乡舍之景,便名之“桃花源”之类,抑或根据“桃花源”之典而“实造”如此之景色,都是“落实”。贾政在此说“又落实”,实在因为这是前面屡次出现的情况。如开门的“曲径通幽”之景,有人名“锦嶂”,只是开门叠山的一般形容,并无对“我”之经验的领会,这就是缺少含蓄之意的“落实”。又如“沁芳”桥,一个清客题名“翼然”,这只是根据亭子的形状又因欧阳修《醉翁亭记》之典而来,而没有自我的经验在其中,亦是“落实”。
2.3 犯忌
犯忌者,多是同政事人情相悖之意。这看似同雅俗无关,但所“雅”者,乃是寓于此间而得其遗世独立之精神;若不能意会禁忌之“度”,便是同时俗产生了冲突,难得独我之幽趣了。文中提到的3处犯忌:1)犯在违制。如“沁芳桥”一景宝玉指出的“泻玉”有“倾泻”意,故“粗陋不堪”,不宜用在“应制”上面。还有“蓼汀花溆”一景,有人拟出“秦人旧舍”,宝玉立即指出“越发背谬了”,桃花源之典故,本是讲“为避秦乱”而隐居的一村人,他们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无疑暗藏着对政治的不满。故尤不宜。2)犯在重名。“稻香村”最初有人题名“杏花村”获得众人赞赏,贾政却向众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村名,直待请名方可。”“杏花村”这样广为人知的名字,不宜重复取之。3)犯在“颓丧”。在蘅芜苑一处拟联,有人道是:“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众人指出“斜阳”二字不妥,那人便引古诗“蘼芜满院泣斜阳”句,众人皆云:“颓丧,颓丧!”此评看似和大观园作为省亲之所有关,其实从园林拟名传统整体看去,那些诗意之中优美宛转之趣有之,旷远物外之象有之,但是同样也常出现在文人诗句中的颓丧、牢骚之气,却是静观的园林中需要避免的。
2.4 不中
所谓“不中”就是本来显然需要提及的点题景物,没有说出或者说漏了,或者明明没有的景致,却在匾额和对联中生造出来。前者如怡红院之处,有人提出“蕉鹤”,有人提“崇光泛彩”,宝玉就说“此处蕉棠两植,其意暗蓄‘红'‘绿'二字在内。若只说蕉,则棠无着落,若只说棠,蕉亦无着落。固有蕉无棠不可,有棠无蕉更不可”。而后者如在蘅芜苑中清客们的“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三径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二联,贾政问宝玉的意见,宝玉便回道:“此处并没有什么‘兰麝'‘明月'‘洲渚'之类,若要这样着迹说起来,就题二百联也不能完。”说“不中”是“俗”,似乎也有些不妥,但是“俗”并不只针对文辞不美,还针对那些华美却不切景的辞藻。真正的“命名”乃是根据“此景”各种幽致深蕴而从生命经验中流露出来,而非为了炫耀自己的文学才华而生搬硬造出来的。
从根本上讲,“不入俗”之难在于不能回到自我观照的世界中来,而只在“外部”的典故、概念和比拟中打转。在这一回中,尤其彰显宝玉才华的,或者说特别表露出“雅”的含义的,是连贾政也比较欣赏的“沁芳”桥之命名以及“蘅芷清芬”的对联。“沁芳”之名拟出后,贾政的态度是“拈须点头不语”,脂评“六字是严父大露悦容也”[3]353。宝玉在评价前人时已提出,“雅”虽要切景,但却不能太“实”,而是要“蕴藉含蓄”;而其“含蓄”处,却是一种真正的“实在”。之所以“含蓄”,乃在于命名不能是对眼前景致的一般描述或比拟,而要将自我的生命经验沉浸于作为整体的园中世界,并前追古人之生命,将之也化入此刻自我的生命中来。这也便成了自我“本真的存在”—其表达了超出有限生命而回旋于历史之中的“我”的存在,同时这一历史之中的“我”之中又显现出当下的世界。张岱写范长白之园时评价其“小兰亭”云:“地必古迹,名必古人,此是主人学问。但桃则溪之,梅则屿之,竹则林之,尽可自名其家,不必寄人篱下也。”[7]74学者萧驰在对寓山园题名的研究中也指出,“美景在此只是此一存有者在与整体存有界同现共流之中对意义的领会和开显而已”,也就是计成之“借”字所点出的“此处之景赖于一时之兴”[8]229。“沁芳”之名,看似同此“亭”的物质存在无关,但却正在这种对物质性的遗忘中,宝玉将自己作为时空之“主”,同大观园这一空间整体的往复相与,反过来,“沁芳”的一时之兴,也依赖园林整体布局,这在文中早有所伏。前面石洞中的“佳木茏葱,奇花烂漫,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泻于石隙之下”,又经过了“渐向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最后才见到桥而亭,这一脉蜿蜒杳霭的水流,有显有隐,携着上游落花,溶溶荡荡,至此桥下渐发散开来,最后在这小桥之中“沁”入宝玉的心脾。不过,这种精妙的构思,或许造园者有之,但恐怕只有宝玉这样细腻清透的性灵,可以捕捉到其幽微之处,而点出“沁芳”之语。此名之“蕴藉含蓄”之意,恰又将前面“雕甍绣槛”之北方园林的富丽之象洗尽,转为文人园天真清新的质性,这无疑也是曹雪芹个人趣味的流露。
后面写蘅芜苑之处,从前文主要讨论匾题过渡到主要讨论对联,这是作者错落的写法。宝玉在理论了前面的人所题不合其景之外,给出匾题“蘅芷清芬”,而更展现其才华的在其对联“吟成豆蔻诗犹艳,睡足酴醾梦亦香”。贾政指出这是套用前人旧联,而众人则举例说李白“凤凰台”诗也是套崔颢“黄鹤楼”,并说“只要套得妙,如今细评起来,方才这一联竟比‘书成蕉叶'尤觉幽雅活动”。贾政笑道:“岂有此理。”在文句后面,我们甚至也可以感受到曹公自己对此联的得意之态。这两句也是另一个“以古为新”的例子了。套用古人之句,并不见得好,还有可能落入窠臼,而此联之所以妙,首在切题,此地的确乃奇葩异卉香草环绕之所;次在“幽雅活动”,其“吟成豆蔻”“睡足酴醾”的感觉,自然不单纯是描绘景物,而是将自己作为一位栖居者的体会沉浸到这一环境之中,这也不是一般的居住者体验,而是作为诗人的真实的自我生命在这一空间中感受到一个艺术化的世界从世俗中超逸而出,进而将这一生命活泼泼的真实经验注入了文采风流之中。
以上二例,便可知所谓“无一字不俗”,所谓“雅”,其实就是将自我作为存在者的“主人”去面对真实的世界,面对真实的此刻的显现。然而古今鲜有人可做到极致,又知这一“真实”是极难寻找的。这一回的叙事展现出,对真实的意义的寻找乃是基于对许多“不真”的表达的涤除与反省,在这种反省之后重新回归到本真的存在中来,回归到在此的自我中来,世界的“真”便从被遮蔽的俗套和成见中显露现身了。
3 曲径通幽
大观园的第一处名字“曲径通幽”出自一句中国人皆知的诗句,甚至18世纪的西方人也发现了中国园林的“曲”的妙处。威廉·肯特(William Kent)提出的“自然厌恶直线”,故发明出了“蜿蜒式园林”(serpentine garden)。在中国园林里,自然也有“羊肠小径”,也有“清流一带,势若游龙”,然而“曲径通幽”之妙处,并不在于形式上“蜿蜒”,而是在主体的经验中。作者对此景的描写,开门后“迎门一带翠嶂挡在前面”,贾政评说:“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而后一段“羊肠”,则由宝玉点明,乃是“探景一进步耳”。“探景”自然需要道路不能太过平直,那样便一望无余,无可“探”矣,但也不一定必须要固定的“蜿蜒”的样貌。倘若只有蜿蜒但却无探景,远景一览无余,甚至如英国园林虽有前景的树木,但后面的景色亦可以清楚地望见远方,令前路明确,也绝不是曲径通幽。在大观园这一景中,首要的并非小径,而是开门后的迎面假山将背面的景致掩映起来,才能有后面曲径通幽的妙处。故而众人亦道:“极是!非胸中大有丘壑,焉想及此!”“胸中丘壑”,不在翠障,而在通幽,不在显,而在隐,不在外表,而在委曲。从此山的布景看,“白石碐嶒,或如鬼怪,或如猛兽,纵横拱立,上面苔藓成斑,藤萝掩映,其中微露羊肠小径”,前面的叠石令人如脂评“想入其中,一时难辨方向”,苔藓和藤萝则令人恍然入古,而后一条羊肠小路,令人不知去往何方,如此一个引人入幽的布置便完成了[3]350。
这一处“曲径通幽”描写,不禁让人想起《二十四诗品》中的“委曲”一品:
“登彼太行,翠绕羊肠。杳霭流玉,悠悠花香。力之于时,声之于羌。
似往已回,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鹏风翱翔。道不自器,与之圆方。”[9]143
这一品的意趣,可以说贯穿于大观园诸景的描写之中,甚至令人怀疑这第十七回就是按照“委曲”这一品的线索写出来的。“登彼太行,翠绕羊肠”,入门后见翠嶂,后有羊肠曲径之意,这正是大观园迎门一景的手法。委曲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曲折蜿蜒”之意,这需要有“登彼太行”来营造探景的意趣。而“杳霭流玉,悠悠花香”二句,无疑说的就是文中接下来写的“沁芳”。此处的“曲”,就不再是一个单独的景致的营造了,而涉及更远的不可见的空间。同“探景”那种即时的经验不同,人在此处的感受,一定要经过前面的游历,体察到造园者的匠心,又足够的细腻敏锐,能将前面的所观花木的经验在一段流转之后,仍能留存为记忆,而这记忆由于流水而不必成为一种回忆,花的芬芳在这一流水之中再度“在场”,令人在整个园林中的经验“时间之中”。这也便是“委曲”中说的“力之于时”的道理。
过了沁芳桥,正式开始了对园林中诸轩舍的描述。作者以游历经验之笔,透过众人的情感表达出这种“探”的意趣。几乎各处景致的引起,都能看到“忽见”“忽闻”这样的表达,如:“忽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众人都道:‘好个所在!'”(有凤来仪);“一面说,一面走,忽见青山斜阻。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墙,墙上皆用稻茎掩护”(稻香村);“池边两行垂柳,杂以桃杏遮天,无一些尘土。忽见柳阴中又露出一个折带朱栏板桥来,度过桥去,诸路可通,便见一所清凉瓦舍”(蘅芷清芬);“因半日未尝歇息,腿酸脚软,忽又见前面露出一所院落来,贾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红香绿玉);“忽闻水声潺潺,出于石洞;上则萝薜倒垂,下则落花浮荡”(蓼汀花溆)。每一处驻足栖居之所,都不是一览无余的,在沉浸于游赏的经验中时,正当心有别意,忽然又邂逅另一处令人惊奇的布置,而重新让人回到对“此处”的认识中来,又不知道哪里是这奇妙之所的尽头。在稻香村“忽见青山斜阻”之后的庚辰本双行夹批点明了这一手法布局在整个园林的用处:
“诸钗所居之处,若稻香村、潇湘馆、怡红院、秋爽斋、蘅芜苑等,都相隔不远,究竟只在一隅。然处置得巧妙,使人见其千邱万壑,恍然不知所穷,所谓会心处不在乎远。大抵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全在人之穿插布置耳。”[3]357
“使人见其千邱万壑,恍然不知所穷”,这一处评语可谓道出大观园布局之妙,不在于大,而在于其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布置的巧妙,可以令人在有限的空间中,体味庄子所说的“游于无穷”的不拘之感,这“一游”的感受不在这方,而在这里,在我处。故更可有心灵中“不可穷尽”的恍然之趣。脂砚斋又引用梁武帝在华林园“会心处不在乎远”之句,这正是庄子在濠梁之上体会鱼之乐的“在我”境界。“委曲”品所谓“似往已回,如幽匪藏”,曲径不是为了“藏”,而是为了显露那个真实地存在“于世界中”的自我。
不只是整个的布局,大观园中每一个院落内部的布局也都在某方面显出“曲径通幽”的妙处。譬如“潇湘馆”的布局,便是宛转回环,令人无限流连。文中描写了3个“曲”处:连接着门口同宅院的游廊之曲;一明两暗的房间以及房间同后院的内外之曲;后院墙下绕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的泉水之曲。在后面的“稻香村”一节,宝玉便说出他们对这一布置“天然之趣”的欣赏。而宝玉后来所居的怡红院中的“曲”,同潇湘馆恰成映照。其中的布景先是以门、窗、书架、窗纱隔断,这已经将“曲”布置到了迷宫的地步,而人在其中迷离不可知之时,却见一面镜子,将这迷幻之境再加倍。这当然是对宝玉在此度过那“太虚幻境”中所指引的生活的暗示。
这一处布置,或许也是受到祁彪佳寓园中“宛转环”一景,“层层旷朗,面目忽换,意是蓬瀛幻出是”的影响。这种布置的手法,也易令人想到17世纪法式园林中的迷宫景象,但二者有根本的不同。童寯先生曾注意到这个问题说:“为了获取形形色色的对景和各式各样的游赏中心,不仅小径幽曲,而且地面标高也常做不规则变化,因而一时的视线只能限于一个局部。欧洲园林则与之不同,其开敞布局使景物一览无余,令人感到厌怠。为此,不得不以迷宫和曲径来满足好奇心理和不可捉摸感,为弥补直线式的单调,凡尔赛的绿丛中也点缀着小小的隐秘花园。”[10]67迷宫的出现是一个局部的游戏,而曲径通幽则是园林整体的布局。迷宫以寻找到“出口”的路线作为目的,人在其中所体会的是向着终点的“迷”,而“曲径通幽”的布置,则是令人在一个“环”中体会到那不可知的永恒的梦幻以及在梦幻之后的觉悟,故有“移步换景,非静观玄对,那得见此”的说法。
到了本章结尾处,作者又着意布置了一“环”。贾琏在怡红院引着贾政及众人转了两层纱橱,果得一门出去,院中满架蔷薇。转过花障,只见青溪前阻。众人诧异:“这水又从何而来?”贾珍遥指道:“原从那(沁芳)闸起流至那洞口,从东北山凹里引到那村庄里,又开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总流到这里,仍旧合在一处,从那墙下出去。”一整回中,处处是“曲处”,而处处因“曲”而幽、而幻、而梦、而会心于此。朱良志先生说,“委者,顺也。委运任化之谓也。即就中国园林多曲线少直线的形式表现而言,直线与力感、秩序、知识、对称等相连,而曲线又与优美相连。但在传统美学观念中,曲线最重要的含义是‘随顺',与物优游,与物潆洄,或者与物沉浮。”[9]145委曲说的并非是形式上的曲,而是与世界相往来的自在。
4 天然图画
在这一章的“稻香村”一节,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以较大的篇幅谈论了中国园林中一个最常提到的话题:“天然图画”。此处乃是在一山坳之中仿建的乡村图景,在其中种稻田、蔬菜,以表“农耕”之意。这一处景致中,贾政和宝玉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喜好上的矛盾。贾政之理想,乃是传统士大夫的“归田”之趣,而此处则正是一个田家之象。再入其中茆堂中的布置,“纸窗木榻,富贵气象一洗皆尽”,令喜爱简朴的儒士贾政更是欢喜。正当众人纷纷暗示宝玉也说喜欢此处时,刚刚得到父亲夸奖的宝玉,却不由得意忘形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来。在他眼里,这一处最为还原“乡野”的自然景致,“不及‘有凤来仪'远矣”。贾政当然十分不满宝玉的态度,认为这是他不爱读书的缘故。但宝玉给出自己的道理说:
“此处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成的: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无脉,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那及前数处有自然之理、自然之趣呢?虽种竹引泉,亦不伤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恐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即百般精巧,终不相宜……”
表面上看,这天然乡村的图景,正是一幅优美的“天然图画”了。西方在18世纪所开始实践的“如画”(picturesque),最初正是“模仿”克劳德·洛林(Claude Lorrin)的乡间绘画而来的。但这模拟绘画的想法宝玉并不认可。真正的天然图画,在他看来,就是符合“自然之理”“自然之趣”的景致,而不是外表上“模仿”某幅图画或是景色。宝玉言“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无脉,临水无源”,也是从地势上去谈这个问题,也即景致应因地制宜,与整个环境浑然天成,方才是“大观”。
这是晚明以来文人造园的核心问题。《园冶》的题词中,郑元勋曾解释造园之法无法单靠模仿学习得来:“是惟主人胸有丘壑,则工丽可,简率亦可。否则强为造作,仅一委之工师、陶氏,水不得潆带之情,山不领回接之势,草与木不适掩映之容,安能日涉成趣哉?所苦者,主人有丘壑矣,而意不能喻之工。”[11]143这一段说法,应许正是宝玉“天然图画”之说的来源。《园冶》卷三之“掇山”有所谓“深意画图,余情丘壑。未山先麓,自然地势之嶙嶒;构土成冈,不在石形之巧拙”[11]288。叠山中的画意和丘壑,实际上不在石头的外形,而要先寻得自然地势。从郑元勋的口气中,可知在当时的园林中,大抵也有不少的景致委托工匠营造而有“造作”或是宝玉所说的“穿凿”的问题。
晚明的另一位有名的造园家张南垣,对这一问题体会颇深。清代吴伟业所撰《张南垣传》中则说:“华亭董宗伯玄宰、陈征君仲醇亟称之曰:‘江南诸山,土中戴石,黄一峰、吴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画脉者也。'”[12]2059所谓“知夫画脉”,指的是张南垣深晓黄公望、吴镇等画家笔墨的布局和气势之自然。曹汛先生在对张南垣的研究中,指出他对于那种过分做作的“以小见大”的批评,认为这种末流的“流波覆篑”“俯藉人机”的所谓“聚盆盎之智,以笼岳渎”[13]49。如李渔在芥子园中所置北山,有茅亭、栈道、石桥,还有人给他捏的渔翁塑像,其趣味实在有如大观园中这个假作的“农庄”。还有那些仿造雕塑或是真山形式的假山,也是此理,看似“自然”,却只是对自然景致的表面模仿,并没有真正理解“自然”的奥义。顾凯在研究中也指出,张南垣重视峰石的“动势叠山”,乃是“对身体浸润其中”的一种境界的体会,而非简单的“以小见大”[14]13-19。事实上,早有学者根据张氏父子的言论,认为他们就是《红楼梦》中营建大观园的造园设计师“山子野”的原型,从大观园的营建思想看,这一说法也颇可成立[15]285。
在祁彪佳的寓园中,也布置一处农家的景致,名为“丰庄”。深受老师刘宗周影响的祁彪佳,和贾政一样心中有着儒家传统的“农圃之兴”[5]。只是在这一农家景致的上面,祁彪佳非常重视园林整体布局对“自然之理”的“相适”。《寓山注》中“让鸥池”一景之注中就提道:“(让鸥)池南折于水明廊,北尽丰庄,中引踏香堤,而以听止桥为素湍回合之所……”[5]故此园中之水一系相成,农圃的营造并非刻意穿凿,乃因迂回曲折的水脉自然而兴。祁彪佳在《寓山注》的序言中,还特别说道自己的造园经历时对“天开”之意的领悟:
“客有指点之者,某可亭某可榭。予听之漠然,以为意不及此。及于徘徊数日,不觉向客之言,耿耿胸次,某亭某榭果有不可无者,前役未能罢,辄于胸怀所及,不觉领异拔新,迫之而出。每至路穷径险,则极虑穷思,形诸梦寐,便有别辟之境,若为天开。”[5]
对天然的寻求,不是复制一幅“像自然一样”的景观便可以了。所谓“宛若天开”,那是需要深入到人的胸怀深处,“极虑穷思,形诸梦寐”方能领会到“得宜”,只有在“果有不可无者”处,才能透露出“天开”的境界。
5 结语
《红楼梦》一书深领中国艺术哲学的幽微之妙,并将其细化在它的文本叙事之中。从第十七回的文本叙事一例便可领会,园林的深旷隽永之意旨,并非仅存于一个物质的载体之中,是在个体的深度经验以及各种观念的讨论与反省之中显露出来的。所谓“以意造园,复以园造意”,文人的书写,绝不仅仅是作为园林的附庸,此乃为真正“表达”造园之意,又将园林更进一步推向有情的生命宇宙中的机杼所在。而命名对联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乎园主能否深寓于这一有情世界,能否得其涤洗世俗心胸而超迈于全体之境的“真赏”。
从园林的角度看,这一生命宇宙的显露,正是所谓“天开”的意义。曲径通幽和天然图画,看似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其要旨都立于“天开”之意上。它们都反对一种直白的陈列和模仿,因为如此便将人同这个世界的距离疏远了;前者要求将自我始终寓于园林的整体情境之中,而后者则要求将园林寓于宇宙自然理势的脉络之中—这也是文人画之气脉所在。然而臻于如此之境实为不易,无论从《红楼梦》的文本还是计成、张南垣、祁彪佳等造园鉴赏家的著述中都可以看到,对这一“寓”的理解,是一个经由体验、探索、沉思、梦寐,最终化为“栖居”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