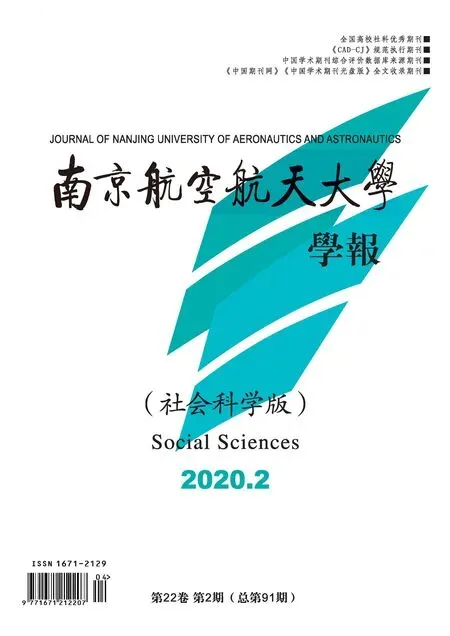浅析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事故”的判定
宋 刚,耿绍杰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5)
航空运输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人们出行的重要工具。跨国航空运输在航空运输中占据很大比例,199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以下简称“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是规制跨国航空运输的重要文件,将近二百个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中有一百多个成员国都加入了该公约。本文所称国际航空运输所指的就是该公约意义下的国际航空运输①“国际航空运输”系指根据当事人的约定,不论在运输中有无间断或者转运,其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是在两个当事国的领土内,或者在一个当事国的领土内,而在另一国的领土内有一个约定的经停地点的任何运输,即使该国为非当事国。就本公约而言,在一个当事国的领土内两个地点之间的运输,而在另一国的领土内没有约定的经停地点的,不是国际航空运输。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与其前身1929年《华沙公约》一样将国际航空运输分为两类,一类为不存在经停地点的国际航空运输,另一类为存在经停地点的国际航空运输。第一类国际航空运输要求航班的出发地与目的地在两个不同的缔约国境内,例如出发地为上海虹桥机场目的地为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该航班适用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出发地为成都双流机场目的地为芭提雅国际机场的航班则不是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意义上的国际航空运输,因为泰国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第二类国际航空运输的经停点并不要求位于公约缔约国境内,例如成都双流机场起飞经停芭提雅机场然后返回成都双流机场的航班属于该公约意义下的国际航空运输。对国际航空运输的认定关键依据就是当事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对出发地、目的地以及经停地的约定。而非1944年《芝加哥公约》所指的国际航空运输②1944年《芝加哥公约》所指的国际航空运输指的是经过一个以上国家领土之上的空气空间的航班。。然而是否属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意义下的国际航空运输意义重大。[1]这关系到该公约能否得到适用,如果是该公约意义下的国际航空运输,则该公约适用。如果不是该公约意义下的国际航空运输,则该公约不适用,也就无所谓“事故”的判定。因该公约未对“事故”作出定义与解释,所以旅客与航空公司之间经常发生争执、产生矛盾,各国法院对“事故”的判定也是有所差异的。目前“事故”的判定主要有“事故构成三要件说”和“事故构成两要件说”两种方法,本文将解析这两种判定方法,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公约起草者未对主要术语作出定义的原因及影响
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于1997年设立了一个“将华沙体制合并为一体之现代化的专门小组”。[2]该研究小组是国际民航组织为了推动华沙体系的改革,制定现代化的《华沙公约》而专门成立的。①现代化的《华沙公约》即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研究小组提出应继续沿用华沙体系下各公约的术语且不给这些术语作出定义。[3]时任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的Assad Kotaite先生在1999年蒙特利尔大会上的发言也表示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是华沙体系下各公约的一体化,而不是彻底性的创新与颠覆。②参见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ir Law, Montreal, May 10-28,1999, ICAO Doc.9775-DC/2,Vol.I,Minutes,36-37(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44Montreal Conference Minutes).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条文来看,该公约相较于华沙体系下各公约仅新增了对“第五管辖权”这一术语的定义,而对诸如“事故”“延误”“上、下航空器的过程中”等术语均未进行修改且未作出定义,这也证明了研究小组和理事会主席所言非虚以及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主导思想。但是,并未有公开的官方正式资料解释为何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不对主要术语作出定义。笔者认为原因在于: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各个国家的法院在对华沙体系下各公约主要术语进行判定的时候会有所差异,但是整体上已经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赋予了主要术语较为妥当的定义。这些判例并未偏离1929年《华沙公约》制定者使用这些术语的最初目的,若在新公约中强行予以定义可能造成语义涵盖范围不全、各国法院对主要术语的新定义进行解释可能出现推翻华沙体系形成的判决先例(即颠覆华沙体系,这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主旨不符)、文本翻译不一致导致的理解差异(例如1929年《华沙公约》法文文本的dol和英文文本的wilful misconduct的理解差异③关于dol和wilful misconduct的理解差异不是本文的讨论对象故不多加阐述,详情可见:赵维田.《国际航空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86.)等问题。故公约起草者采用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仍然不对主要术语进行定义,继续将术语的判定工作交给各国国内法院。
新公约未修改“事故”“上、下航空器”等主要术语的表述也没有赋予其定义,但是过去华沙体系有关这些主要术语的判例在新公约中也应该得到适用和参考。例如,某法院依1929年《华沙公约》对某一案件是否构成“事故”进行了判定,那么在新公约生效以后,判定某一案件是否构成“事故”仍可沿用1929年《华沙公约》判定“事故”的方法。可以认为,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中主要术语是对华沙体系下各公约中主要术语的继承,除了新增“第五管辖权”的定义外并未出现新的变动。
二、司法实践中对“事故”的判定
1.“事故”与“事件”的比较
公约中未对“事故”作任何解释或定义。因此在实践中,判定是不是“事故”,就由法官来决定。[4]判定是否构成“事故”对于乘客和承运人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使乘客遭受损害的原因构成“事故”,则承运人可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5]318反之,则不承担。1929年《华沙公约》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中“事故”这一主要术语均出现在公约文本第17条第1款,所用英文单词均为“accident”。④《华沙公约》第17条第1款:对于旅客因死亡、受伤或身体上的任何其他损害而产生的损失,如果造成这种损失的事故是发生在航空器上或上下航空器过程中,承运人应负责任。《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第1款:对于因旅客死亡或者身体伤害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死亡或者伤害的事故是在航空器上或者在上、下航空器的任何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责任。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在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承运人对乘客行李的赔偿责任和第18条对托运人所托运的货物的赔偿责任所用术语为“事件”,所用英文单词为“event”,这与第17条第1款“事故”(accident)是不同的。⑤《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第2款:对于因托运行李毁灭、遗失或者损坏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毁灭、遗失或者损坏的事件是在航空器上或者在托运行李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任何期间内发生的,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责任。第18条:对于因货物毁灭、遗失或者损坏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损失的事件是在航空运输期间发生的,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责任。在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起草过程中,部分国家要求公约第17条第1款、第2款以及第18条均使用“事件”一词,但是遭到了大多数国家的反对,故公约第17条1款仍采用“事故”一词。[6]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对“事故”的阐释:“事故是一个非有意的、不能预见的、未按事物常规发生且不能被合理预见的损害事件。”[7]由此可见,“事故”是属于“事件”的,“事故”是“事件”项下的一个子类别,从范围上讲“事件”比“事故”的涵盖范围要大很多,即“事故”一定是“事件”,但有些“事件”并不一定是“事故”。
2.事故构成三要件说
对“事故”判定的早期司法实践是DeMarines V.K.L.M航空公司案和Warshaw V.TWA航空公司案,两案均是由于飞机在爬升或降落过程中机组成员改变机舱内气压导致乘客耳部受伤。法院判定两个案件均不构成“事故”,承运人无须对旅客承担赔偿责任。通过归纳两个案件对“事故”的判定过程可以总结出“事故”的构成要件为:①事故必须是意外的、异常的。②事故不是因旅客健康原因导致的。③事故必须是航空运输的固有风险引起的。①参见DeMarines v.KLM Royal Dutch Airlines,433 F.Supp.1047(E.D.Pa.1977).Warshaw v.Trans World Airlines,Inc.442 F.Supp.297(E.D.Pa.1977).笔者将其称之为“事故构成三要件说”。美国最高法院后来通过Air France V.Sakes案,在支持上述两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事故”的判定必须根据周围情况灵活认定,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同时明确指出“事故”指的是导致乘客所受损害的原因,而非乘客所受伤害这一事实本身。②参见Sakes v.Air France,470 U.S.392(1985).笔者对美国最高法院的观点表示支持,因为乘客所受伤害这一事实本身基本都是意外的、非常规的(除非他自己故意所致)。如果将“事故”认定为乘客所受伤害这一事实本身,那么基本上只要旅客受伤了,承运人都得进行赔偿,这显然是将“事故”与“事件”等同,是不合理的。只有将“事故”限定为导致旅客所受损害的原因才能合理地、正确地对“事故”进行判定,否则“事故”的范围会过于宽泛。正如英国的林德利勋爵在一个案例中所指出:“就公约所指事故而言,不论从立法历史还是从条文措辞,都应理解为造成损害的原因。”[5]319以最典型的空难致旅客伤亡为例说明判定过程:首先明确造成旅客伤亡的原因是空难,然后将空难套入该模板中:①空难对于旅客而言是意外的、是异常的。②空难不是旅客健康原因导致的。③空难是航空运输的固有风险。故得出结论空难属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意义下的“事故”。
3.事故构成要件之航空运输固有风险
美国法院通过上述三个案件确立的“事故构成三要件说”的判定标准风靡全球,成为了全球大多数法院对“事故”判定的标杆和模板。但是,“事故构成三要件说”的第三个构成要件,即“事故”必须是航空运输固有风险引起的,遭到了一些质疑。各国航空法和各公约没有对何为航空运输固有风险进行定义。在司法实践中,法国最高法院于1966年的Mache V.Air France案将航空运输固有风险解释为:“只有实际驾驶航空器产生的危险,才属于航空运输固有风险,并且它必须存在于商业性的航空运输中。”③参见(1963) 26R.G.A.275(C.A.Pan’s,18 June 1963),Cassion,(1966)29R.G.A.E.32(Cassciv.1re,18 January 1966),on Remand,(1967)30 R.G.A.E.289(C.A.Rouen,12 April 1967),aff’d.(1970)32R.G.A.E.300(Cass.Civ.re,3 June 1970).法国法院的这一解释为以后的争论埋下了伏笔。劫机事件的出现使得“事故构成三要件说”走向了风口浪尖,航空公司的观点认为遭受劫机所受损害这一原因不构成公约所规定的“事故”,因为劫机属于恐怖活动,而遭受恐怖活动并不属于航空运输固有风险,这就不满足“事故构成三要件说”模板中的第三个构成要件。在Hussrel V.Swiss Air Transport案中,主审法官Taylor认为如果承运人不对劫机引起的损害承担责任,则有悖于华沙公约的规则与宗旨。④参见Husserl v.Swiss Air Transport Co.,Ltd.,388 F.Supp.1238(S.D.N.Y.1975)该法院的逻辑是直接造成旅客受到伤害的近因是劫持飞机并胁迫飞行员实际操纵飞机,所以该法院将因劫机引起的损害视为航空活动的固有风险。[8]然而,并不是所有法院都采取这种近因理论,持反对观点的法院从宏观上认为恐怖活动在哪个领域都可以发生,不属于航空运输固有风险,进而这些法院判定恐怖活动造成的旅客损害不构成事故,航空公司不必承担赔偿责任。例如Martinez Hernandez V.Air France案法院的判决就指出:“恐怖活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风险,不单纯是航空运输带来的风险。”⑤参见Martinez Hernandez v.Air France,545 F.2d 279(1st Cir.1976),cert denied,430U.S.950(1977).不仅有国外法院反对将劫机等恐怖活动排除在“事故”范围之外,我国也有学者持此观点:“劫机和破坏民用航空器的活动都被认为是与航空运输操作无关的事件。”[9]
4.事故构成两要件说
事实上,在航空运输固有风险的范围尚未明确之时,美国各法院对“事故”到底是否由航空运输固有风险导致的作出了不同判决。例如,Pittman V.Grayson案中航空公司被指控走私原告的女儿到国外,法院判定不存在“事故”,因为不存在航空运输固有风险。⑥参见Pittman v.Grayson,869 F.Supp.1065(S.D.N.Y.1994).Price V.British Airways案中两名旅客打架,法院同样以不存在航空运输固有风险为由判定不构成“事故”。①参见Price v.British Airways,1992 WL 170679(S.D.N.Y.1992).相反,在Laor V.Air France案中,承运人把一名长时间使用卫生间的旅客强行带回到座位上则被法院认定为事故。②参见Laor v.Air France,31 F.Supp.2d 347(S.D.N.Y.1998).在Halmos V.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航空餐食中毒案中,法院认为即使不存在航空运输风险,旅客食用了航空公司提供的餐食中毒也构成公约所规定的“事故”。③参见Halmos v.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Inc.,727 F.Supp.122(S.D.N.Y.1989).更有甚者,在Rhodes V.American Airlines案中,法院判定吃航空餐食的过程中被鱼刺卡到喉咙也属于“事故”。④参见Rhodes v.American Airlines,Inc.,1996 WL 1088897(E.D.N.Y.1996).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五个案件的审理除了Rhodes案外,其他都是纽约南区法院审理,该法院在其审理的Halmos案中认为“事故”不需要考虑航空运输固有风险,但是在后来的Pittman和Price案中又认为“事故”需要考虑航空运输固有风险。而在最后的Laor案中,该法院又将态度转变回来。可见,即使是同一个法院,其判定“事故”构成要件的标准也是不同的。通过Laor、Halmos和Rhodes三案,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法院认为引起旅客人身损害的原因是否构成事故只需要考虑两个要件,即引起旅客受损的原因对于旅客而言是否是意外的、不寻常的,以及该原因是否是旅客自身健康因素之外的。也就是说,只需要考虑“事故构成三要件说”的前两个构成要件,而无须判定该原因是否属于航空运输固有风险。若该原因对于旅客而言是意外的、不寻常的而且不是旅客自身健康因素所致,那么就可以被判定为构成“事故”。在此种判定方法下,航空运输固有风险这一构成要件就变得可有可无的了,引起旅客人身损害的原因是否属于航空运输固有风险都不影响“事故”的判定。笔者将Laor、Halmos和Rhodes三案的事故判定方法称之为“事故构成两要件说”。
笔者认为“事故”的判定标准完全可以去除航空运输固有风险这一构成要件,只要造成旅客伤害的原因是旅客意料之外的、非正常的、不是旅客自身健康因素所引起的,就可以被判定为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意义下的“事故”,承运人需要为此承担赔偿责任。显而易见,“事故构成两要件说”比“事故构成三要件说”使乘客得到赔偿的可能性更大,且更有利于对旅客的保护,因为这将原本不存在航空运输固有风险造成旅客伤害的原因纳入到“事故”赔偿范围之中。这是符合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前言中所写的确保消费者利益,也是公平合理的。同时,采取“事故构成两要件说”可以省略对航空运输固有风险的判断,以减少判决争议。“事故构成三要件说”的真实意图是尽力保护正在快速发展的民航业,将“事故”的范围限定于与其自身联系最为密切的航空运输固有风险,而不管其他相关联的风险。这与1929年《华沙公约》限制责任制度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这种思想在前几十年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当时航空运输业正在发展,需要政策、司法的保护以使其快速成长。但是时至今日,航空运输业经过百年的时间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不再需要特殊的保护,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依旧采取“事故构成三要件说”,会引起众多旅客的不满,旅客很可能转而选择其他交通工具以代替乘坐飞机出行,这无疑会导致航空业的衰退。再者,《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第19条、第29条、第30条、第33条、第37条、第45条、第46条综合显示了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赔偿责任引导意图。[10]265该赔偿责任引导意图是指:在航空运输责任期间内,有关旅客人身伤亡或者因延误遭受损失的纠纷处理规则都应当是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中所规定的,并且旅客的索赔对象都应当先行直接指向承运人而非他人,承运人先行承担责任之后再由承运人根据具体案情的不同向他方当事人追偿。[10]266公约第37条明确写道:本公约不影响依照本公约规定对损失承担责任的人是否有权向他人追偿。以航空餐中毒案为例,中毒旅客可要求承运人承担“事故”赔偿的责任,承运人之后可以向提供航食的公司进行追偿。此种机制的好处在于中毒旅客可以较为容易的得到赔偿,航空公司证明航空餐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能力又远在旅客之上,最终承担责任的将会是航食公司而非承运人,承运人并不会因为“事故”构成要件删去航空运输固有风险而蒙受损失。所以将“事故”判定标准变为“两要件说”既能体现公约公平公正的主旨,又保护了旅客权益还不会过分加重承运人负担。
5.三要件说事故构成之扩张解释
“事故构成两要件说”将“事故”的范围扩大很多,可以将旅客乘坐飞机时所遭受的绝大多数的伤害事件判定为“事故”。采取该标准很容易将很多与航空公司本无过多联系的造成旅客伤害的原因纳入到“事故”中。例如,两乘客在飞机上打架斗殴引发旅客伤亡或者一个旅客摔倒在另一个旅客身上造成旅客受伤等情况若采取“事故构成两要件说”均可构成“事故”,这样会使承运人承担较以往更多的赔偿责任。正如上文所述,这将更好地保护旅客的利益,使旅客受偿更为容易。
但是,如果在现阶段突然将航空运输固有风险这一要件删除,转而采取“事故构成两要件说”,那么势必会遭到“守旧派”法院和航空公司的抵制,进而导致对“事故”判定的分裂,这与华沙体系所期望的统一实体法理念是相冲突的。“守旧派”法院和航空公司认为华沙体系下各公约所规定的“事故”以航空运输固有风险为基础,承运人只对特定航空活动的风险所引起的旅客伤亡的损害承担有限责任。故笔者认为,为了平衡航空公司与旅客的利益,应将三要件说的构成要件进行扩张解释的方法,其中前两个构成要件完全与“事故构成两要件说”一样,扩张解释之处在于将航空运输固有风险的含义进行扩张,把机组成员①此处指广义的机组成员:包括飞行组、乘务组和安保组。对待旅客的行为纳入到航空运输固有风险的含义之中,即扩张解释的航空运输固有风险不仅包括为实际驾驶航空器所产生的风险,还包括机组成员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侵害旅客的行为。具体来说,要观察机组成员对待旅客的行为是否与旅客所受损害存在因果关系并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旅客所受伤害介入了机组成员的行为,其行为构成了旅客人身伤害的因果关系中的一环,那么将会构成“事故”。反之,则不构成事故。采取对航空运输固有风险进行扩张解释的方法将机组成员对待旅客的行为加入其中,一方面考虑到了“守旧派”法院和航空公司认为的“事故”需要有航空运输相关要素,另一方面考虑到了采用该方法旅客获得赔偿的可能性大于原来的“事故三构成要件说”使得旅客权益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不失为一种过渡性的、折中的“事故”判定标准。以Diaz Lugo V.American Airlines案为例,机组成员将咖啡洒在旅客身上造成烫伤构成“事故”。②参见Diaz Lugo v.American Airlines,Inc.,686 F.Supp.373(D.P.R.1988).按照扩张解释的方法进行推理:首先,造成旅客烫伤的原因是机组成员将热咖啡洒在乘客身上这一行为,这一行为是旅客意料之外的,旅客有理由相信机组成员经受过严格训练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其次,这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之外的因素导致的。最后,机组成员的行为构成了旅客人身伤害因果关系中的一环。综上,推理得出机组成员将热咖啡洒到旅客身上的行为构成“事故”。另外,笔者认为采用该方法还可以促使航空公司尽力提高机组人员的服务水平以减少事故的发生。
三、结论
华沙体系下各公约均未对“事故”等主要术语进行定义与解释,这就意味着以往的判决先例对现在的术语判定依旧有参考借鉴的意义。对于“事故”的判定方法对乘客保护最为有利的是“事故构成两要件说”,且采取该种判定方法因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确立的赔偿责任引导意图的存在不会过大地加重承运人负担。但是考虑到“守旧派”法院以及航空公司对“事故”判定的观点以及为了平衡航空公司与旅客利益,可以选择笔者将“事故构成三要件说”中的航空运输固有风险这一要件进行扩张解释的方法作为过渡,待过渡期平稳度过后,便可采用“事故构成两要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