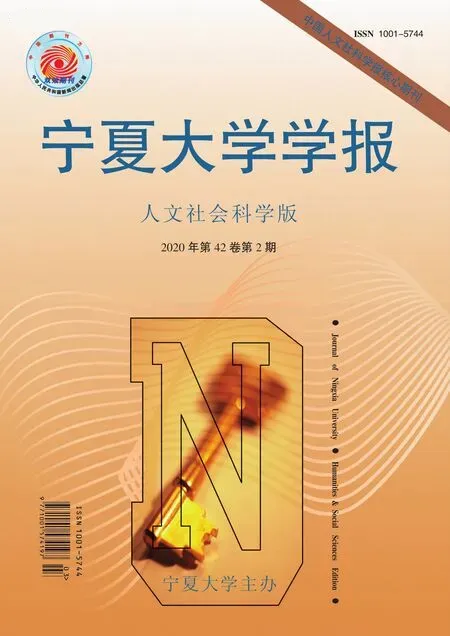清官侠客合流模式的“血酬”观察
丁峰山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银川 750021)
清官侠客合流模式是近代侠义公案小说的标志性特征。 “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1]。 早期研究者对这种模式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持肯定意见者认为清官与侠客联手除暴安良,客观上符合人民的利益,主观上也是倾向人民的,具有进步性;持批判意见者则视清官为皇帝之臂膀,侠客为清官之爪牙,二者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侠客投靠清官,宣扬了奴性,削弱了反抗性;中立派认为该模式是除暴安良的人民性和维护封建统治的落后性互见,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学现象,应该审慎对待,不能简单否定或简单肯定[2]。陈颖《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1998),曹亦冰《侠义公案小说史》(1998),吕小蓬《古代小说公案文化研究》(2003), 苗怀明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2005),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2008)等后出研究专著及学术(位)论文,如:武润婷《试论侠义公案小说的形成和演变》(2000),刘希欣《清官与侠客的结盟与分离——以〈三侠五义〉为例》(2003),占骁勇、李艳杰《试论侠义公案小说的形成》(2007),魏思妮《侠义公案小说中官、侠的结合及其原因——以〈三侠五义〉为例》(2012)等,对上述争议亦作出回应,分歧依旧。
的确, 随着时代观念和社会思潮的不断变化,人们对清官侠客合流模式的看法也必然随之多元化。 不论从哪个角度考察和立论——思想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文学的,都有言说的理据,不必相互否定。 从众说纷纭的研究现状来看,这个模式能持续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成为常说常议的话题,足以说明其本身的丰富内涵和多重指向。 本文借助历史学者吴思提出的“血酬”观点,在揭示历史上和小说文本中侠客的暴力属性、生存困境和道德困扰的基础上,讨论侠客选择与清官合作的现实和历史必然性,以期为清官侠客合流模式研究补充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一
侠之义训本明。《说文》:“侠,俜也。从人夹声。”“俜,侠也。丂部曰:甹,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甹。然则俜甹音义皆同。 从人甹声。 ”[3]“甹,侠也。 此谓甹与俜音意同。 人部曰:俜,侠也;侠,俜也。 《汉·季布传》:为人任侠。 《音意》:或曰任,气力也;侠,甹也。三辅谓轻财者为甹。 所谓侠也,今人谓轻生曰甹命,即此甹字”[4]。 可见,侠的底色是“轻财”和“轻生”,即不贪财,不怕死之人。 然自韩非以来,对于侠之身份属性、行事方式、精神气质、价值判断多有增添变异,议论蜂起,致使什么是“侠”,成了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是,不论侠的面貌如何,有一点大家是认可的,即“侠以武犯禁”[5]。 使用暴力是侠的第一要义,不论战国的游侠、两汉至唐的豪侠、剑侠,还是宋以后的武林、绿林、秘密社会之侠,都建立在暴力这个基础之上,离开暴力,侠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暴力不止于武功或武力,泛指强势而令人屈服的力量。 “在最基本意义上,暴力意味着:(1)以杀戮、摧残或伤害而对人们造成损害。 (2)可以扩展到包括这种损害造成的威胁,延伸到心理与生理两个方面的危害。 (3)可以包括对财产的侵害。 (4)暴力体现了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意志关系,即强力意志或屈从意志”[6]。 暴力作为权力现象和意识结构,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中:“只要考察帝国如何兴起和失败,个人威望如何确立,宗教如何分裂,财产和权利如何继承和转移,思想家的权威如何增强,精英的文化享受如何建立在被剥夺者的辛劳和痛苦之上,就足以发现暴力无时不在,无所不在”[7]。
暴力无处不在,所争夺的利益无所不包。 吴思称这种获益方式为“血酬”,“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 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 ”[8]侠是暴力最强者中的一员,也是血酬利益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 侠之所争,与大多数人并无二致:一曰“名”。 “行剑攻杀,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廉勇之士。 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9]。 “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10]。 “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11]。 侠靠立名来招揽好勇斗狠之辈,形成强势集团,也靠名望来统领徒属,应对挑战。 “名”是侠固人自固最核心的要素,称侠者无不以争名为先。 二曰“财”。 虽然侠以“轻财”为底色,但在仗义疏财之前也得有财,不然自身如何生存,如何供养徒属,如何振人不赡? 司马迁早就指出此中关捩:“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12]侠与非侠的区别不在于争不争财,而是怎样用财。 朱家“家无余财”、剧孟死后“家无余十金之财”是因为救助贫贱,郭解“家贫,不中訾”是因为养了大批门客。 郭解迁徙茂陵,“诸公送出者千余万”,郭解全都接纳了,道出了侠不拒财的实情(《史记·游侠列传》)。 三曰“权”。 侠一出现,就以挑战既有规则为务,韩非屡次以“犯禁”抨击这些“弃官宠交”(《韩非子·八说》)的“不使之民”(《韩非子·显学》)。 司马迁虽对游侠报以同情,但也开明宗义地指出其“扞当世之文罔”,“不轨于正义”的行径(《史记·游侠列传》)。 当侠的势力发展到豪强阶段,“权行州域,力折公侯”[13],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14],直有替代官府之势。 这已到了暴力争夺的顶峰——制定规则和维护规则的权力。
争夺暴力收益,必然要承担暴力对抗带来的风险。 侠的“血酬”风险显而易见:首先,是身体风险。侠“行剑攻杀”,各种打斗不可避免,自身伤亡时有发生,风险时刻伴随。 其次,是法律风险。 “背公死党”,“令行私庭”,对抗统治者的法律体系和执法机构,挑战既定规则,必然“陷于刑辟”(《汉书·游侠传》),受到法律制裁。 最大的风险来自政治风险,即规则制定权的抢夺。 侠很少一个人在战斗,大多会组合成或紧密或分散的团体, 与其他势力相抗衡,形成集团对集团的拼杀。 这种拼杀已进入划分势力范围,制定稳定收益规则的阶段,如果交通权贵,卷入政权之争,则“其罪已不容于诛矣”,“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汉书·游侠传》)
“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15]。 暴力收益与风险成本是正向关系,争夺的资源越稀缺,风险越大,暴力烈度也随之加大。 对于个体来说,死亡是最彻底的损失,所以保住自身性命是暴力的底线,也是风险的最高值。 对于以暴力为根基的集团或朝廷来说,失去规则制定权和执行权,意味着彻底失败和出局,定会动用一切暴力手段和方法。 当二者都在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时,以性命为成本的侠客们会有怎样的结局,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二
当然,侠如果仅依靠暴力为所欲为,便与一般恶霸强梁无异,并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尊敬。 “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决,游侠亦丑之”[16]。 孔子最早用“义”来限定规范暴力,隔离盗乱。“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7]。
何为义? “利者义之和”(《易》);“义,利之本也”(《左传》);“夫义,所以生利也”,“言义必及利”(《国语·周语》);“义以生利”,“夫义者, 利之足也”(《国语·晋语》);“义, 利之本也”(《大戴礼记·四代》);“爱利出乎仁义”(《庄子·徐无鬼》);“义者, 利也”(《墨子·经上》);“义者, 万利之本也”(《吕氏春秋·无义》),“义之大者, 莫大于利人”(《吕氏春秋·尊师》[18]。 综合来看,此“利”为利人、利他之义,是儒道墨诸家共同认可的含义。
如何行义?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杨伯峻依据朱熹《集注》释为:“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规定要怎样干,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干,只要怎样干合理恰当,便怎样干。 ”[19]《中庸》云:“义者宜也”,朱熹释:“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 ”[20]《说文解字》段玉裁注云:“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也。 ”[21]即从行动层面来说,只要行为人觉得这样做是合理的、正当的、应该的,就是好的,就放手去做,没有外在的规定。 孟子甚至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22]。 只要本着真心做事,说话可以不算数,行为不一定有始有终,给行义留下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可见,实行层面的“义”是一个开放性的道德范畴,其内涵和外延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周延性。 什么行为符合“义”? 谁来判定是否正当、合理? 不同时空、不同情势下变化很大,没有统一固定的标准,人人心以为然即可。 不仅行义者可以自行判断“宜”与“不宜”,墨子曰:“义,志以天下为芬(分),而能利之,不必用。 ”[23]不必在上位,随分而能利人,就是“义”了。 接受者亦有判定权,且无须考虑施予者的身份地位及行为方式如何。 司马迁云:“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 ’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 ”[24]跖、蹻乃危害社会的残暴大盗,但受其恩惠者依然以“义”视之、谢之,道出了“义”人人可议、交相非议的性质。
因此,就普遍意义而言,“义”可以这样来理解:义是一种利他的精神和情感,是一个正向的道德标准,只要施利者或受益者主观觉得正当合理,就可以实行或者认同, 不必考虑事件的客观性质和后果,不受具体的外部规则束缚和限制,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教育”需要完善的教育管理运营体系,方能保障其最终的教学成效,而并非线上线下教学的简单叠加。因此,除课程设置、教育资源、教育模式、技术平台、学习机制、教学评价变革外,尚需建立线上线下同步管理的相应运行机制,对教育资源协作和教与学的各过程环节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管理。
严格说来,侠之“义”不等同于儒墨之“义”,但它们在历史上一直互有交叉和影响, 尤其是明末“忠义说” 兴起后, 儒家之义基本上收编了侠客之义。 侠因暴力属性与“义”结合,且借助“义”将自己从盗匪乱民中剥离出来, 使自己的暴力行为得到“义”的加持和护佑,获得了普遍认可和广泛活动空间。 但是,侠客们也因此被套上了枷锁:一是暴力行为受到道德制约,“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李德裕《豪侠论》),既成了侠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也成了社会评判和认同的标准,行侠必得仗义,否则人人以盗匪视之,限制了暴力的使用范围和强度。 二是“义”的自由解释权也让侠客快意江湖的同时面临着极大的现实风险。 扶危济困、打抱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济贫、锄强扶弱……这些行侠仗义的标准行为背后,无不埋藏着泯是非、蔑国法的隐忧,以抵触道德禁忌和政教律法为代价,随时面临险境。 侠客或者道德层面认为适宜的、可以做的事,不见得符合法律规定和统治者的意愿,面对“义”与“不义”最终谁说了算的冲突,侠客们该如何选择?
三
现如今,受当代武侠小说熏染的读者心目中的侠客武功高强、纵横江湖、重情重义、一诺千金、惩恶扬善、对抗邪恶黑暗势力,甚至肩负国家民族大义,完全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豪杰形象。 其实,这与历史上真实的侠相去甚远,大多是文学作品浪漫想象的产物。 可以说,侠的精神气质与生命情调是由历代文人参照侠的历史形迹反复构造出来的,是文人们释放现实压抑的象征载体,一定程度上寄托了人们对公道、正义、自由、美德的理想追求。 但是,来自民间说唱艺术的、更接地气的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客活得却不那么潇洒自在, 放意自恣。 他们与初始形态的侠一样承受争名夺利的压力,同样要为暴力行为负责,境遇比一般人更加残酷凶险。
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客首先为财打拼,他们获取经济利益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偷。 展昭、白玉堂、丁兆蕙、韩璋都施展过妙手空空之技,偷走成百上千两银子;韩璋、徐庆、蒋平、柳青胃口更大,盗走凤阳太守孙珍献给庞太师的寿礼万两黄金 (《三侠五义》)。二是抢。偷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大多数侠客干的是啸聚山林、拦路抢劫的活。 正如《彭公案》中神眼季全所总结的:“我想众位寨主,也无非是在大道边上,或在漫山洼,或在树林之中,遇见客旅经商,拦住去路。 保镖之人软弱无能的,你等得财到手;倘若遇见活手之人,就是以多为能。 ”[26]三是组建暴力集团,制定规则,获取稳定收益。 《三侠五义》中丁家兄弟与陷空岛五鼠以芦花荡为界,各自收取松江渔业资源,起了冲突,必须按规矩处理(第31回)。 陈起望的陆彬、鲁英组建庄园,收取渔民、猎人的交易费,维护日常交易秩序(第104 回)。
名扬天下是大多数侠客的最高追求,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荣誉心,也可以号令同道,但所冒风险也更大。 白玉堂为了与“御猫”争名气,“纵然罪犯天条,斧钺加身,也不枉我白玉堂虚生一世,哪怕从此倾生,也可以名传天下。 ”[27]《彭公案》中,濮大勇激将黄三太不敢做大事。 黄三太闷坐书房:“我今年已六十岁,常言说得好:宁叫名在人不在。 我必再往京都做一件轰轰烈烈之事,留下英名,传于后世。 ”[28]二人闹京城、闯皇宫、拿库银、劫圣驾,名满天下了,可要维持这个名,就要付出更高代价。 白玉堂命丧铜网阵,黄三太惹起了康熙的杀心,不得不整天谨小慎微。
综观《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基本上都是侠、盗、匪三位一体的绿林草莽,行为上是忙于生计的盗匪——水旱剽掠、坐地分赃、聚义劫财、甚至杀人越货,观念上“义者宜也”的侠义。 他们对行为本身的作案犯科性质和私斗死伤风险是清楚的:
吃酒之间,濮大勇说:“众位恩兄贤弟,我想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想你我当年结拜,都是二十余岁的英雄,如今数十年来,都成了老头儿了。要论豪杰,在北方还数李煜大哥,你历练得真好,只要红旗一展,无论哪路的镖,就要送你几两银子。 凤凰张七哥,他所为与黄三哥是一个样,永不须伴,孤身出马,有一千银,尚留三百两,所取贪官污吏,还是济困扶危,周济孝子贤孙,除贪官分文不取。如今黄三哥是洗了手啦!咱们大家一回想,侠义的朋友,死走逃亡,真个不少,也有遭了官司,身受重刑的,死于云阳市上;也有死于英雄之手的”[29]。
如何自保,如何避免行侠风险? 侠客们有着非常理性的判断和选择,那就是与朝廷——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合作。 《三侠五义》中小诸葛沈仲元表现得最为典型。 他先在恶霸马强处混迹,马强被剿灭,沈仲元暗下报效朝廷的决心, 随众投奔襄阳王,偷偷当起了奸细。 遇到智化, 表明了心迹:“有的,没的,几个好去处,都被众位哥哥兄弟们占了,就剩了个襄阳王,说不得小弟任劳任怨罢了。 再者,他那里一举一动,若无小弟在那里,外面如何知道呢? ”[30]这番话透露出三重信息:投奔官府是大多数侠客的选择;进入官府竞争比较激烈;侠的对立面不是朝廷,而是贪官污吏、乱臣贼子,帮好官灭恶官即是剪恶除奸的侠义行为。
可见,相对于与贪官、乱臣为伍,投靠清官乃侠客的最优选择:一则避祸。 每位侠客在投身清官之前,不论是追求个人名利,还是打抱不平,都背负着“原罪”——偷盗、抢劫、行刺、杀人、称霸一方等等,无不触犯法网。 一旦归属于清官,罪责全免,且可以官爵加身或者倚仗清官之名,拥有高人一等的身份地位,畅行江湖。 而对抗清官绝对没有好下场,即便投靠了权贵——《三侠五义》 里钟雄因交通襄阳王使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水寨毁于一旦,就是显例。
二则回头是岸,找到正常的人生出路。 许多看透绿林是条不归路的好汉们归顺清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己身的生存,若能得到一官半职更好,得不到亦自认命,充斥着功利算计。 《施公案》里计全劝何通路归顺时的对话就很有代表性:
“想你我幼年之间,不务正业,打劫为生,空混了半生,年纪都不小了,须当想个养老的主意,才能保得住收绿林结果。你瞧哪一个挣下房产地土咧?一辈子不落人手,这就算头等的光棍……我如今跟着他吃碗闲饭,冻不着,饿不着,我就算知足。 像贤弟,依我的拙见,何不跟着大人南巡? 路上但能立一两件功劳,大人回京时见驾面圣,只要当今圣主一喜,你的功名有份,强似一生落个贼名……怎么说呢? 你我也老了,王法也紧了,这时候想不出个收场结果来, 也就难为了一世男子……”那人闻听计全之话,回道:“老哥不忘旧日交情,才领小弟正道上行。 多承老哥指教,小弟情愿跟随大人南巡,烦老哥回复大人去罢。 你说我不为保举升官,但愿饱食暖衣,到老善终就足了意咧”[31]。
三则可以“合法”使用暴力,满足行侠欲望。 不是所有的侠都只为温饱投靠清官。 有的崇敬清官清正廉明、为国为民的人格魅力,如展昭、五鼠;有的为了报恩,如黄天霸;有的为了更好地实现行侠仗义理想,如《彭公案》中李七侯所言:“咱豪杰中讲究的是杀赃官,斩恶霸,剪恶安良,是大丈夫之所为,不能显姓扬名,暂为借道栖身。 ”[32]当他们成为“官侠”之后,行侠方式并没有多大改变,但因为拥有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可以放开手脚、无所忌惮地杀人取财,剿灭仇家,甚至公然栽赃陷害,制造冤假错案,如《三侠五义》中的马强案。 率性施暴与破案惩凶合而为一,更加痛快淋漓。
人类使用暴力时,必定权衡成本和收益。 “成本至少有四类:(1)良心。同情心和正义感。(2)机会成本。 在权衡中,与卖命并列的还有卖力、卖身和卖东西等选项,人们会比较血、汗、身、财的付出与收益。(3)人工和物资的消耗。 (4)暴力对抗带来的风险。无论是暴力镇压,暴力反抗,还是暴力掠夺者之间的竞争,暴力掠夺都要面临一定的伤亡风险”[33]。 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客们大多精于成本与效益核算:(1)把暴力风险降至最低,起码保住自身性命,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白玉堂绝不是众侠客效仿的对象。“暴力可以制造死亡,因此,暴力最强者拥有规则选择权或决定权。 这就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34]。 (2)同样是刀尖舔血的活,行走江湖还是为清官破案更有机会获取稳定甚至超预期收益,一目了然。 (3)侠与盗匪的最大区别是“义”,即有点良心,讲点道理。 同样是偷,展昭、白玉堂等人针对的是恶俗乡宦、忘恩负义者、吝啬鬼等有道德缺陷之人的不义之财;同样是抢,侠客时时标榜给被抢者留一部分且将到手的匀一些出来济困扶危;同样是杀人,侠客就地处决者多为淫贼、恶霸、贪官、小人,心安理得。 可是,这些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的行径,经得起法律上的推敲乎? 经得起官府的追究否?
四
对照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一书中所举的真实案例,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与之遥相呼应,说明清官侠客合流模式是民间说书艺人和整理者基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加工创造,一定程度上接近“历史的真实”。 就侠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侠与朝廷一直是既对抗又合作的关系,尤其是宋以后,侠走向世俗化,已没有令行私庭、力折公侯的势力。 他们要么对官府敬而远之,要么适当合作,主动反抗王法的意识已相当淡漠。 陈山《中国武侠史》,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郑春元《侠客史》,汪涌豪《中国游侠史》,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传承》,龚鹏程《侠的精神文化史论》等著作对侠的演变过程有详细梳理和研究,此不赘述。
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大多是 “盗跖居民间者耳”(《史记·游侠列传》),以流血拼命为本钱,用暴力手段讨生活的众生之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投靠清官,既能降低暴力风险,又名利双收,趋利避害,人性使然,不必以奴才贬之。 他们没有公共权利意识,没有为了追求普遍正义、自由,而同不公平的命运或规则进行抗争的实际行动,更没有流露过进步的政治见解。 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危济困的义举,往往激于意气,随意、随机的成分很大。 “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 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35],故不必以人民性捧之。 他们信奉“士为知己者死”的义气,清官能肯定他们的能力和作用,便以知己视之。他们认为贪官恶霸扰乱了王法和社会秩序,清官能不畏权势、主持公道,为受侮受害者申冤昭雪,便甘为前驱。 这正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清官崇拜观念,清官与侠客互相合作、相辅相成、主持公道、惩恶扬善,体现了大众的良好愿望,虽有庙堂、江湖之区分,但心理上从来不是对立关系。
在胡适看来,此类小说“著书的人多半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也没有什么浓挚的经验”,是一种没什么思想见地“确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的平民消闲文学[36]。 我们若以现代人的思想观念、政治意识和人生追求过分拔高或贬低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客,便会以今绳古,自说自话,脱离真实的历史情境。 如王德威 《虚张的正义——侠义公案小说》一文,用现代正义、司法、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革命、权力话语等观念,从诗学正义和叙事秩序视角去寻找侠义公案小说“虚张”“消解”正义的“故意”和“吊诡”。 虽富于启发性,但不得不令人生疑,这类小说是否隐含了如此超前、如此高深的见识?
另外,清官侠客合流模式的形成也受到文学传统的规制,不能一味以现实反映论来解读。 且不论立功边庭、封侯受赏的游侠诗传统,就古代白话侠义小说的演变来看,“是侠义小说之在清, 正接宋人话本正脉, 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37]。 该模式也是其来有自、流传有序,并非凭空而生。 陈平原明确指出:“‘侠客投靠清官’这一情节模式,在《水浒传》里已埋下种子,经过众多英雄传奇的着力培植,到清代侠义小说那里只不过是自然而然的“‘开花结果’”[38]。 我们若从非文学的角度过度阐释清官侠客合流模式所散发的信息,坐实社会背景、侠客史实等一般原因,忽视小说传统的制约作用及小说虚构性、想象性的本质属性,不仅脱离了作品的具体描述,也复杂化、扩大化了该模式的意义。 只有回到小说、立足文本,庶几可以真正看清该模式的本来面目,也才能将侠义公案小说安放在小说史上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