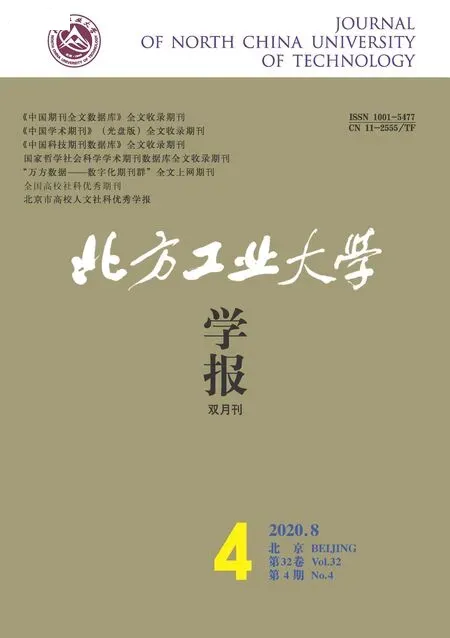历史书写的断裂与民族诗学的坚守*
——论格日勒图《断裂》的艺术品格
于东新
(内蒙古草原文学理论研究基地,028000,通辽)
长篇小说《断裂》(作家出版社2018 年版)是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图建构科尔沁蒙古史、试图重塑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艺术尝试。 小说以浪漫而理性、敏感而冷峻的笔触,波澜起伏的艺术结构为读者再现了17 世纪初期即明末清初时代科尔沁草原一段波谲云诡的历史记忆。 在作者从容不迫的叙事中,迭宕起伏的历史细节里,使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小说文本对历史现场的还原与民族诗学的建构。 文学创作成功的标志是文学的独创性,即独特的思想寄托和艺术个性。 这正如罗丹所指出的:“在艺术中,有‘性格’的作品,才算是美的。”[1]而《断裂》就属于这种有“性格”的作品。
1
作为坚持以母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图对于蒙古民族的历史是熟悉并有深刻了解的,而关注历史是因为他对现实有更多的思考,这正是其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断裂》的思维原点,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我们的时代总是思考的时代”,是“反省的时代”[2],小说家选取历史题材作为写作对象,是因为作为人类的历史,“现时是过去的结果,未来必然应该在现时这个基础上得到实现”。[3]从历史的过去、现时和未来的相互关联来看,现时的一切问题都应当从历史中寻求答案。[4]惟其如此,格日勒图才将17 世纪前叶蒙古族的历史目之为“断裂”,认为是对波澜壮阔、大气恢弘的蒙古民族史的一种“断裂”。 “我们的祖先南征北战,将大半个世界收于麾下建国立业,在跌宕起伏的历史长河中,一路走到了今天,谁都灭不掉我们。”[5]但到了明末清初时期,由于林丹汗的心胸狭窄与昏庸无能,各部台吉诺彦的猜忌、内斗,并随着建州女真的迅速崛起,北元政权已不可逆地走向式微的局面,蒙古民族史的辉煌因而随之发生了“断裂”。 小说即以1621—1632 十余年间科尔沁蒙古政权图存与壮大为中心,还原了努尔哈赤、林丹汗与奥巴洪台吉为首的科尔沁各部的“三国演义”。 小说这样叙写科尔沁:“北元时期,科尔沁部的实力在蒙古各部中最强,有左右两翼十三个鄂托克。 ……因此,又称其为‘阿巴嘎科尔沁’,人口近二十万,有着‘四十万蒙古,二十万科尔沁’之说。 他们的游牧地,北起大兴安岭向南延伸至浑河流域,西至黑龙江嫩江盆地,与内喀尔喀五部接壤,土地肥沃,牧场丰美。”[6]但小说也道出了17 世纪前叶科尔沁部尴尬的历史处境:“嫩科尔沁像一只钻进岩缝中的大山羊,钻不出去又退不出来。 努尔哈赤把女真各部统一之后,将触角伸向科尔沁,欲从边角将其掏空。 林丹汗为加强汗廷统治,结束蒙古的分散割据,想尽一切办法恢复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央集权制,秣马厉兵只待时机。 ……嫩科尔沁被两强夹击,进退维谷,处境可忧。”[7]就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出场了,这个人物就是奥巴洪台吉。
1.1 真实的“人”:奥巴洪台吉
历史就像一条千年流淌的大河,有时平平静静,有时风急浪高,而那些突转的弯道,陡峭的断崖,就像历史的转折关头一样,成为历史进程的新开端。 《断裂》展现的就是这种历史转折关头,科尔沁蒙古人对民族、国家和未来的把握与奋斗。 而奥巴洪台吉就是其中的代表,一方面他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有振兴民族的历史责任感,他从父亲翁果岱洪台吉那里继承了“为科尔沁的未来着想,不能辜负祖宗的寄托,重振科尔沁雄风”的嘱托,所以他和努尔哈赤周旋,反复考量和后金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更希望林丹汗心胸开阔,不再猜忌,能够团结蒙古各部,大家拧成一股绳,完成蒙古帝国再度辉煌的伟业。 但另一方面他又是无助的,甚至是无力的,他孤立无援,甚至连儿子巴图拉都不是他的支持者,并且他也似乎缺少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没有纵横捭阖驾驭复杂局面魄力,至多是一个守成之主。 所以,奥巴洪台吉既雄心勃勃,又犹豫矛盾、贪图享乐,缺少一种过人的英雄气魄。 抑或说,小说无意将奥巴洪台吉塑造成一个传统的英雄形象,它似乎更愿意将他塑造成一个真实立体的“人”。 小说写他热爱科尔沁草原,礼敬旱獭达日巴老人,珍爱宝马燕白,与后金使者赫巴、林丹汗使者恩和乌力吉等人周旋应对,战场上也骁勇善战,这些都使得奥巴具有一种政治家的“真实”;但小说还写他最后接受了努尔哈赤的拉拢利诱,成了“土谢图汗”,并且娶了满洲的公主,做了“土谢图额驸”。尽管其中有形势所迫的因素,但却看不出奥巴洪台吉忍辱负重的心志:“奥巴洪台吉喜悦无比,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情不自禁地瞧了一眼貌美妙龄的新哈屯,更是喜上眉梢。”但后来皇太极在征讨察哈尔的时候,要求奥巴出兵相助,他却推诿不前,待接到皇太极的“问罪书”,他又被迫到盛京“负荆请罪”,小说这样写他的一系列举动:
奥巴洪台吉拾阶而上,心里虽然打鼓,却下定决心绝不给皇太极下跪磕头。 他心想:“你即便是长生天,我也不会给你下跪。 我绝不辱没蒙古黄金家族的英名,不给哈布图·哈萨尔的英灵丢脸。 我身为科尔沁的一部之长,为顾全大局可忍受一时耻辱,但绝不吃眼前亏。”奥巴洪台吉进殿后故装胆怯,右手放胸前微屈单膝说道:“科尔沁的奥巴以蒙古人的礼节拜见英明的天聪皇帝。”却在心里想:“我就不给你下跪,看你能把我怎样! 你可杀我,却无法赢我。”[8]
由此可见奥巴犹疑矛盾的性格,以及有些“精神胜利”的可笑。 不仅如此,小说还写了他的自私与残忍,比如抢夺马倌哈丹铁穆尔的心爱骏马——燕白,最后竟残忍地准许察嘎力博以哈丹铁穆尔为“人牲”活祭敖包的行为,使得一个只有20 岁的青年失去了生命,进而也成了呼和铁穆尔一家被迫出走、流浪他乡的原因。 所有这些都表明,《断裂》的主人公奥巴洪台吉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传奇英雄,作者有意在“解构英雄”,因而一改传统历史小说描写英雄、崇尚传奇的通常写法,而是还原了历史中的真实人物,这在中国小说艺术史上也算是一种“断裂”,当然这也是一种“新变”,其将英雄传奇式的历史小说转变成了历史的写实主义。 当然,也必须看到,尽管奥巴洪台吉犹疑彷徨,从拒斥到被迫接受,但他的选择最终还是确立了科尔沁蒙古在未来历史中的政治角色,成为满清政权重要的政治同盟,为科尔沁蒙古族后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2 并非“勇士”的巴图拉与“虎头蛇尾”的哈丹铁穆尔
不仅主人公奥巴是这样的“真实”,其他的人物也没有多少“英雄主义”的豪气,如奥巴洪台吉的儿子巴图拉。 巴图拉是一个优秀的摔跤手,但却不像洪台吉的儿子,他胸无大志,比如对父亲艰苦卓绝的熬鹰行为,他的认识是“父亲呀,您这是何苦来的。 非给自己找罪受! 我可不愿像您这样折磨自己,除非有人用刀架着我的脖子来逼”。[9]他没有重塑蒙古族辉煌的责任感和使命担当,可以说父子两代人在精神上是断裂的。 自从迷恋上弟媳阿莉娜,他对这种不伦之恋,尽管也犹豫挣扎,但还是情欲战胜了理智,并以为这是找到了真爱。 如果是换作一般平民子弟,这样的人生或许勿需过多指责,但作为嫩科尔沁部洪台吉的长子,在当时非常复杂危险的政治局面下,他这种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作为,就让人不敢恭维了。 最后他抛弃一切,和心上人远走他乡,在被父亲追赶上后,他自杀谢罪。 这种“生死不渝”的爱情,对于奥巴洪台吉“光复大元一统天下”的事业无疑是重大打击。 巴图拉,在蒙古语中是“勇士”的意思,但小说何尝不是一种反讽,这个贾宝玉般的人物怎么能是“勇士”?
再如哈丹铁穆尔,这似乎是作者“用心”塑造的人物。 小说设计了他英雄般的出场:“年轻的马倌哈丹铁穆尔穿了件只剩半条油子的白茬皮祆,骑着一匹海骝马从哥哥呼和铁穆尔身边呼啸而过。 他来到山丘上,勒住缰绳踩着马镫踮起身子、手搭凉棚向根切尔城望去。 那威武的身姿好比格斯尔故事中,镇压了十二头黑莽古斯凯旋归来的阿斯尔查干海清。”[10]接着他驯服了他相中的四岁儿马——燕白:“哈丹铁穆尔冲进马群,……将套马杆向前一伸,绳索便牢牢锁住了白马的脖颈。 ……白马为了甩掉背上的哈丹铁穆尔,一会儿竖起前蹄在空中打旋,一会儿又在原地跳跃。 围观的人们生怕哈丹铁穆尔被甩下来,为他捏着一把汗。 哈丹铁穆尔却粘住了似的,稳稳地骑在马背上,任凭白马怎么撒欢尥蹶子,也没有被甩下来……”[11]而后哈丹铁穆尔杀狼、力败黑狐,一个身手矫健、气概凌云的蒙古英雄呈现在读者面前。 直到后来,当奥巴洪台吉夺走了他心爱的白马,他一气之下赶着两匹儿马远走乌珠穆沁,做了土匪——他似乎成了反抗强权的英雄。但最终还是被押解回来,并被察嘎力博压在哈拉敖包底下,当了活祭敖包的祭品! 本来读者试图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个反抗强权的英雄形象,满足关于传奇故事的阅读心理,但作者似乎无意于此,他只是还原了那个时期一个普通马倌、奴隶悲喜交加的短暂人生。 这种“虎头蛇尾”的艺术处理,表明了作者历史书写所秉持的一种别样的艺术原则。
1.3 宏大历史叙事的日常书写
有学者指出:历史侧重于叙述历史事件和事实,文学则侧重于表现人和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历史小说不是简单的叙述历史,而应当是历史事件和个人事件的结合。[12]正如别林斯基所主张的,在历史小说的世界里,没有史诗、神话那种规模的英勇生活,没有高大的英雄形象,有的是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是普通的人,“对于长篇小说来说,生活是在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举凡人的心灵与灵魂的秘密、人的命运,以及这命运和民族生活的一切关系,对于长篇小说来说都是丰富的题材”。[13]这也就告诉我们,历史小说要突出人,突出人的命运,以表现人的心灵世界,即既具有历史感,又有文学味,这就是《断裂》历史书写所秉持的艺术原则。 它并不是机械地复述历史事件,而是写了一群鲜活的、有长处也有缺点的“人”:有点志大才疏的奥巴洪台吉、身陷爱情旋涡而不能自拔的巴图拉与阿莉娜、传奇的老猎人旱獭达日巴、命运悲惨的哈丹铁穆尔、狡诈狠毒的察嘎力博、胆小懦弱的呼和铁穆尔、用情专一的卓岚格日勒、善良无邪的少年巴德拉,还有谋略深沉的努尔哈赤、能言善辩的使臣赫巴,以及技艺高超的根敦胡尔奇等等,通过这样一群性格迥异、命运殊途的人物,小说生动地还原了在那个历史转折时期蒙古族的一段鲜活的历史。 “历史小说仿佛是一个点,作为科学看的历史,在这个点上和艺术融为一体,它是历史的补充,是历史的另外一个方面。”[14]它揭示了历史事实内在的方向,引导读者走进历史的日常生活,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 通过生动直观的形式获得了一种更为形象和深刻的理解。
但《断裂》又不是一个让人感到沮丧的历史书写,它仍然给人以奋进的力量。 小说结尾写奥巴洪台吉西征之前的心理活动:“科尔沁蒙古人只要不放弃理想,胯下的坐骑就会驮着我们抵达欲到之处。 任凭坐骑来认路吧。 蒙古历史的新征程即将开始。 在辽阔无际的草原上,随着东升西沉的太阳延续……”[15]上述这种书写使得小说充满了亮色,给人以奋进的希望,历史即便是出现了断裂,但它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生呢!
2
在艺术上,《断裂》具有浓郁的民族性,是一部集现代性和民族性为一体的诗性文本。 格日勒图对本民族的历史、民族心理、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的理解,要远远超过其他民族的作家,因此,《断裂》表现出浓郁的蒙古民族风格,显示出特有的民族诗学特征。
2.1 民族性的艺术传达
首先,小说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草原民族所特有的生活内容,如狩猎、驯马、熬鹰、婚俗、天葬、那达慕、祭敖包、萨满法术、蒙古长调、乌力格尔等等,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充满草原色彩的历史生活画卷。 比如书中有很多处描写草原景象的文字:“1620 年清明时节,根切尔谷地上蹄声震耳。 马群从山丘上涌入谷地,如汹涌的江水般气势恢宏。 四蹄生风的骏马踏起阵阵尘埃,弥漫在山谷间像袅袅薄雾般缭绕。 ‘嗬 依——嗬依——’牧马人收群的声音粗狂而豪放,领头的儿马停下来仰头嘶鸣。 马匹在谷地上汇集起来,风中飘动的马鬃和马尾,在阳光的照耀下仿佛束束金光,使平静的大地瞬间充满了活力。”[16]“天空明朗笼罩四野,山丘起伏连绵无止尽。 朵朵白云似洁白的绒毛,在湛蓝的天上缓缓飘移。 山脚到河谷满眼翠绿,各种各样的野花争奇斗艳,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 河水在绿毯的怀抱中,像一条长长的银带蜿蜒。 牛羊散在河边吃草,水鸟飞起飞落不住地啾鸣。”[17]——一幅幅优美的草原风情画跃然纸上。 这种“草原性”的场景简直不胜枚举。 就在作者娓娓道来的描写中,神奇而特别的草原生活景象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得小说显示出浓郁的民族风味,又具有了“地方性知识”①的标识。
其次,《断裂》的民族性书写还表现在对蒙古族的宗教信仰、风俗礼仪的反映上。 小说详细而又生动地描绘了巫师察嘎力博、莽古思根敦、胡尔丹萨满等一系列祭天、祭敖包、祭苏力德之类的求神问卜、代神预言等一系列宗教活动,对原始宗教的描绘为小说创造了一种神秘的艺术氛围。 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根敦胡尔奇吟唱“劝奶歌”,使得母驼接纳幼崽的场景:
根敦胡尔奇以沙哑的嗓音低沉地唱起古老的民歌《孤独的白驼羔》:“孤独的白驼羔/在揪心的哀嚎/没奶吃的驼羔/就要饿断肠了/有妈带的驼羔在沙地上玩耍/没妈带的驼羔/在伤心的哀嚎。”
焦躁的母驼忽然安静了,似乎也在听忧伤的的歌儿。 ……
“断崖上盘旋而飞的/是乌鸦麻雀两种鸟/在心怀中常思念的/是爸爸妈妈两个人/雄鹰和麻雀/在悬崖上鸣叫呀/常喂我母乳的/妈妈你在哪儿……”
……山石融化了,草木哭泣了,大地也在轻轻震颤。 ……母驼仰起头嚎叫了一声,心已融化,情已归来。 琴声在草原上飘荡,感动了天地,感化了人畜。 幼驼的哀嚎更加悲悯,母驼呼应着它的哀嚎,仰头长嚎起来。
“没有乳汁的燕子/还会叼食喂幼雏/分泌乳汁的母驼你/为何不给驼羔喂奶? /咕兮,咕兮,咕兮∥没有乳房的麻雀/还会啄食喂幼雏/生下羔崽的母驼你/为何嫌弃亲骨肉? / 咕兮,咕兮,咕兮!”
母驼温情满满地看着幼羔,洁白的乳汁从奶头上滴落而下。 驼羔钻进妈妈的腹下,噘着小嘴“咻咻”吸允起乳汁。 母驼低头嗅着幼羔的胯尾,大颗大颗的泪滴从眼角滚落下来。[18]
这样神奇的景象只有草原才有。 蒙古人似乎精通自然万物的语言,根敦胡尔奇的弹奏与吟唱,与母驼、驼羔的叫声应和在一起,妈妈和母驼的泪水交汇在草地上。 一曲感天动地的母亲之歌,唤醒了母驼的纯朴母爱!
老猎人旱獭达日巴是小说里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作者对他着墨不多,但写他捕获海东青,尤其是他的死亡过程却写得充满了神秘色彩:
旱獭达日巴觉得憋气,呼吸急促着脑袋向后微微一仰,头顶上放了块宝石般,闪着一道耀眼的蓝光,就停止了呼吸,睡去一样安详地走了。……于是,依老人生前嘱托,亲自带领老少众人,将其尸体拉到后山大卸八块后,在嘴里反复念叨着:“老人家,您是我们中间的智者,请安详地长眠,安心地赴往另一个世界吧。 希望您在来世再托生到科尔沁草原。”当送葬的队伍离开时,食肉猛禽纷纷汇聚而来,低空盘旋在尸体上方。 有只黑狐狸也来到附近,“嗷嗷”地仰天长嚎着。[19]
至于像祭敖包、根敦成为胡尔奇的过程,都充满了神秘色彩,反映出北方民族隐秘的文化心理:
阿拉坦希日格图敖包是科尔沁地区最古老的敖包。 ……奥巴洪台吉偕众台吉诺彦,以顺时针方向围着敖包转三圈后,从察嘎力博的手里接过盛有酸马奶的木桶,边吟诵“愿敖包神祇永驻!”边将酸马奶扬洒三次祭祀敖包,然后随手捡了几块石头添了上去。 在牧民心中,敖包象征神祇在其位。 出于信仰之心,有放马嚼子的,有放马绊子的,也有人把剪下来的头发放在上面。 神祇没有肉身没有嘴巴,却有吃喝之欲。 为博得神祇开心,祭祀红白食物燎出香味儿,祈祷牲畜发展,人丁兴旺。[20]
这是对祭敖包场景和民众心理的描述。 此外,小说还有许多蒙古族的民俗禁忌以及生活经验的诗性书写,给读者以获取知识的新奇与愉悦。 比如蒙古人不掏鸟窝,忌讳把影子落在鸟蛋上;蒙古人忌讳用烟杆敲击人和动物的头部,那是头颅落地的噩兆;爱犬死了,蒙古人“割断爱犬的尾巴,往它嘴里放了把米,埋在后山脚下。”还有:“母驼怀胎一年才能够生下幼崽,通常情况下不嫌弃孩子,偶尔才发生这种情况。 早年间密葬蒙古帝王,杀了一峰驼羔,将其血液洒在埋葬陵寝地作标记。 多年之后,埋葬地林木密布灌木丛生,已难以找到墓地。 人们牵着母驼来到洒过驼羔血的周围地带,它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墓地,洒着大颗大颗泪滴悲悯地嚎叫。”[21]诸如此类的文字,都真切地反映了蒙古民族特有的文化特征。
再次,《断裂》的语言也与一般小说的语言迥然不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标识。 其所运用的比喻、成语、俗语等,既是蒙古民族独特表达方式的结晶,更反映了蒙古民族的智慧和心性。 比如:“歌唱能让苍天高兴,驰骋能使大地欢喜”;“气大伤身,山高累马”;“树有年轮,人有根,代代相传,薪火旺”;“积雪压山,年岁压人”;“不生孩子的婆娘,不懂生孩儿婆娘的痛”;“林中起火,最先遭殃的是小鸟;河流干涸,最先死去的是小鱼”;“诺彦命丧于宴席,恶狗死于肉骨头”;“骨头烂在锅里,丑事不能外扬”;“忘记历史的人,跟野兽没区别”等等,这类语言都表现出草原民族的文化特征,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2.2 魔幻描写与现代性
还要特别指出的,《断裂》的艺术品格除了具有鲜明的民族诗学特征以外,还有现代性特色。作者采用了“史传+抒情诗”的模式,即继承并发展了历史叙事加抒情诗的叙事技法。 在叙述过程中,每每用抒情诗的形式来表述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情感,如奥巴洪台吉、阿莉娜、努尔哈赤、卓岚格日勒等人,或在苦闷彷徨之时,或在酒酣耳热之际,用大段的心理描写,或用长调短歌表露心声,显示了蒙古民族丰富而幽微的精神世界。其中,最明显的,作者似乎深谙西方魔幻现实主义艺术之道,有许多精彩的超现实的“魔幻”描写。 如奥巴洪驯服海东青,人与鸟的辩诘对话,以此来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透视出奥巴坚强的意志。 在科尔沁蒙古部落准备追随皇太极,征讨察哈尔林丹汗的前夜,奥巴洪台吉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小说设置了奥巴与死去的先祖、父亲翁果岱等亡灵的对话,如梦似幻,充满神秘感。 最有特色的描写是根敦成为胡尔奇时的神秘遭遇:除夕夜他到明安泰胡尔奇的坟茔旁守夜:“他忍不住困倦打了个小盹。 不远处燃着一堆篝火,火堆旁摆着小桌,两个年轻女子和白须垂胸的老人夹桌而坐举杯酌饮。 ……老人捡起他的朝尔拉奏开来。 琴音响起的那一瞬,周围的坟墓全部消失,被亮着烛光的一座座房屋所取代。 ……一曲终了,老人把潮尔还给他,既像命令又像教导似的说:‘潮尔是天上的乐器。 握好琴弓,闭上眼睛拉一首最熟悉的曲子。 你要记住了,用手拉琴,用心感受,才能成为真正的胡尔奇。 把心中的情感抒发出来吧。’……小根敦手里的琴弓变得沉重无比。 于是,闭上眼睛运了一口气。 奇迹出现了,双手有如神助,《天上的风》被他拉奏得悠缓而舒美。 他睁开了眼睛,不见白须老人,也不见年轻女子,又回到了半梦半醒中。”[22]从此,根敦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说书人。 还有,关于卓岚格日勒自杀殉夫前种种幻觉的描写、老猎人达日巴奇异的离世场景、海东青最后被胡尔丹萨满咬断脖颈,以它的血来祭旗的骇人情节等等,这样的文字都堪为“魔幻叙事”,是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吸收与借鉴。 即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要发现存在于人与人、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神秘关系。 具有神秘色彩的现实的客观存在,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源泉”。[23]小说家之所以这样做,安徒生·因陪特认为:“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试图借助魔幻来表现现实,而不是把魔幻当成现实来表现。 小说中的人物、事物和事件本来就是可以认识的,是合理的,但是作者为了使读者产生一种怪诞的感觉,便故意把它们写的不可认识,不合情理,拒绝给以合理的解释,像魔术师那样变幻或改变了它们的本来面目。 于是,现实在作者的虚幻想象中消失了。”[24]
正是这种“魔幻”与现实结合的笔法,既生动地表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也很好地诠释了草原文化特有的神秘性特征。 这是因为,蒙古族传承久远的原始宗教和具有神秘色彩萨满文化,使得草原具有得天独厚的“魔幻”特质。 这样,“魔幻”就不仅是一种“神秘叙事”的手法、一种现代性,其实它也是草原文化的一种诗性表达,是一种民族诗学的形式,这里的魔幻现实主义是对草原“现实生活中种种神秘世相的描写和对深植于民族传统之中信仰世界的神奇再现”。[25]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与民族性在格日勒图的小说中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统一。 这就使得《断裂》的艺术品格既具有民族特色,也有了现代性的气韵。
综上所论,格日勒图是一个坚守民族诗学立场、擅长以母语创作的小说家,其《草原之魂》《安代》《阴阳树》《云青马》等作品都曾在草原文坛上产生过重要影响,而《断裂》蒙文版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荣获了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索龙嘎”奖第一名。 可以说,《断裂》是一部近年来草原文坛难得的文质俱佳的长篇小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学创作要“立足中国现实”,“守住时代之魂”,“阐释好中国精神”,“深刻生动解读沧桑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 我想这既是格日勒图的艺术追求,也是《断裂》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所谓“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不是一般描述词,而是来自人类学的一个概念。 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与法律的关系》中把法律视为“地方性知识”,是指它对应并服务于历史形成的特定生活秩序,是具有实践功能的知识,而非抽象的理论观念。 而地方性知识,必须通过追溯其历史背境,才能得到比较确切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