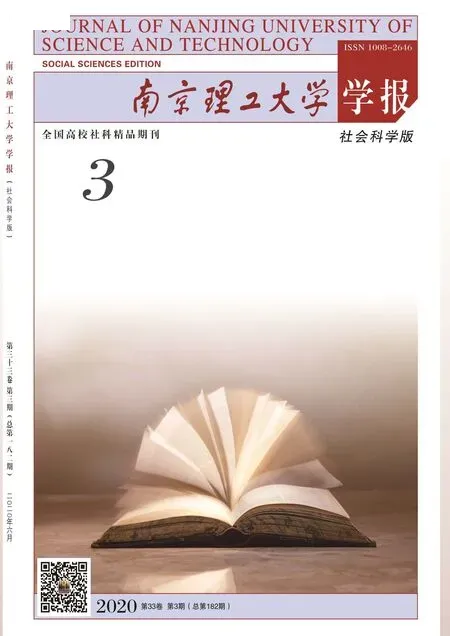真情—仁性—良心:“不忘初心”的儒学释读
李 翚
(南京理工大学 出版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4)
“初心”出自佛教语词“初发心”,意指做某件事的最初的愿望、最初的原因,即初衷、本意、本愿之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忘初心”之后,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革开放、人民群众、和平发展道路与党的建设等八个方面赋予了“初心”新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与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两个重要讲话报告中,对“不忘初心”都作出了具体全面的阐释。笔者还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自信”等也是这两份报告共同的关键词,报告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因此,本文尝试从儒学的视角来释读“不忘初心”,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刻内涵。
一、儒学“真情—仁性—良心”的理论路径
无论是历史考察,还是逻辑分析,儒家思想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脉络,这就是“情—性—心”的思想进路,即由本真的情感发现仁善的人性,而真情与仁性统一,构建成为“良心”,“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2]331可以说,“良心”不仅是儒家所奉行的做事的“最初发心”,也是人之本具的“本然之初心”。
说到真性情,今人往往将之归为道家的理论特点与人格形象。本文认为,儒家,尤其是孔子,恰恰是从人最本真的情感发现与阐发“仁”的。《论语》载:“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2虽是孔子的学生有子的一句话,但我们从以直报怨、父子相隐、乡愿为德之贼到尊亲重孝等相关表述中可以看出,这应当是孔子的思想,他正是由“亲亲”这种天然的人类最本真的情感作为“仁”的原点,然后以同情同理之心推己及人,建构起“爱人”“泛爱众,而亲仁”的仁学体系。后来孟子予以了具体而贴切的表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4]322。由己及人,由真向善,由情制礼,正是孔子仁学的思维路径。所以冯友兰先生在给仁定义时说,“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推己及人者也。仁以同情心为本,故爱人为仁也”[5]。
孟子丰富与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拓展了仁的范围,提出具体的仁政主张。更重要的是他为仁产生的根源或存在的根据给予了回答与论证。孟子首先论证人性为善,皆有“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而且这种品质与能力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恻隐之心就是仁的发端。与孔子罕言性与天命不同,孟子阐发了心、性与天命的关系,将三者贯通起来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4]301这就将仁的存在根据归结为每个人天生具有的一种道德良知。
但无论是情,还是性,即使孔孟将其认定为天然本善,都必须面对“善花何以结出恶果”这个现实问题。所以汉唐以来,董仲舒、韩愈、李翱等一代又一代的儒者提出“性三品”“性情相分”“性善情恶”诸说来应对这个挑战。到宋时,朱熹继承张载、二程等人的观点,对心、性与情等范畴的内涵与关系都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与阐发,提出“心统性情”之说,认为“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还说,心具有觉知与主宰功能,虽然天性本善,但若不主敬涵养,也会受到干扰而丧失本性,这时心的主宰性就体现为存心养心,保持善性。性已发时,便是“情”,“情”的表露或发泄,如果循“性”而动或率“性”而为,就不能说是人欲,这是因为“心主”;如果与性相违而动或动而“过与不及”,那就成人欲了,此时更需要“心主”。这样,朱熹的“心统性情”就是主张存养与省察结合起来在未发已发两端同时用力以保持或复归至善。陆九渊与王阳明更是上承孟子,不惟以心论理,也以心论仁,更以“发明本心”“致良知”为成仁之路径。无论是朱熹的“觉心”,还是陆九渊的“本心”,抑或王阳明的“良知”,都内在地蕴含了本真之情与仁善之性。本真之情与仁善之性,既是觉知之心的内容,又由其主宰,本文以“良心”归统。
综上所述,孔子由直论真,以亲亲之情为人最本真的情感或者说是人之常情,并以此为仁爱之本源;孟子继之,一方面循“亲亲—仁民—爱物”之等差而推扩“仁”之内涵与外延,另一方面则以发自本然之情感的“心之端”论性,以人性本善论证由情而仁的合理性;自董仲舒以后,韩愈、李翱,乃至北宋五子等等,致力于性情之说,都在于对“仁”之生发与依据,对“善花何以结出恶果”的挑战予以解释和回应;朱熹、陆九渊与王阳明都强调心之主宰的涵义以突出“为仁由己”之自觉自主。儒家就是这样以“真情—仁性—良心”这个历史与逻辑的进路,完成了“初心”的建构,而修养此心,就是“不忘初心”。无论情、性、心,儒家终其根本是要达成“知行合一”且以日用之“行”为落脚点。这个“行”不仅表现在“诚意正心”的个人修养上,也表现为他们“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政治主张上。
二、“民本”观与“根基在民”
儒家学说能够成为中国一千多年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历代儒者都提出了丰富而系统的政治主张,而且都是以公义正直、和乐大同为终的,故而能够成为历代治政的思想来源与理论基础。而历代儒者一以贯之的核心观念是民本思想。
孔子论政,以修身为本,以正为核心,“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152即是说,为政者只有以身作则、做好表率,才能使民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所以为政者与君子一样,首先要修身以正己,然后才能安人、安百姓。以此为基础,他反对以暴力为基础的治理,提倡德治,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对民众要以德服人,以礼规治,以利予之,进而达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3]58的理想社会。孟子把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328提醒君王得民心者得天下,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因此,为政者应行仁政,如果能施仁政于民,就可无敌于天下,“仁者无敌”。如果像商纣那样推行暴政,民众就有权起来推翻之,因为失去民心,就成为独夫民贼,而不再是君王,所以即使杀了他,也不是所谓的“弑君”,“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4]42孟子还就推行仁政提出了“制民之产”“庠序之教”“省刑罚”“薄赋敛”等保民、养民和教民的具体措施。到汉武帝采董仲舒之策独尊儒术,虽是奉君权神授,但也以天谴灾异之说相制衡。唐代《贞观政要》以“重民举贤”为旨,发挥了儒家德治与民本思想,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喻君民关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经典表述。宋代理学家中,政治思想较丰富的是王安石与朱熹。王安石实施变法虽然失败,但他的“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的民生思想却是儒者的共识。朱熹奉持“天理君权”观,但也有“民本”思想,提出“为政以宽为本”,认为国家最根本的任务,没有比体恤民众更大的了。他自己在为官一地之时,就能够自觉地从民众的立场来施行治政,力图取消“无名之赋”,他讥讽道,如果不认为百姓是自家百姓,就不这么做。如果真正以民为本,就应当“省赋恤民”,甚至“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6]316。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民主君客”论彻底否定“君权神授”之说,坚持并发展民本学说,直承《礼记》“天下为公”的思想,提出“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并设想了民众参与治理的制度方案。
综而述之,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就是以民众为立国之基、治国之本。这固然与以民为主的现代政治理念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其合理内涵与价值观念仍具有现代价值,并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思想与文化资源。在习近平总书记纪念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阐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第六条是“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7]我们从党的“根基在民”“力量在民”的表述中,可以读出儒家的民本观。
三、“众乐”观与“为人民谋幸福”
有不少学者称中国文化为“乐感文化”,以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东邻日本的“耻感文化”。且不论人们如何争议,但以乐为最高境界的情感体验,的确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特征。
《论语》开篇即说学习与交友之乐,此后又有颜回之乐、曾点之乐等等,孔子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3]81体现出他乐观的人生态度与追求快乐的人生与社会目标。所以二程求学于周敦颐时被要求“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孔子说“仁者不忧”,意思是只要达到了仁者的境界,就可以“乐在其中”。孟子也表述了“君子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所提出的“众乐乐”也成为儒者的追求。到宋代,“乐”成为儒者普遍论及的一个哲学范畴,成为既是情感又超越情感的一种精神境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从“和民”“成民之欲”的社会角度谈到乐。范仲淹从孟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4]33化用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如果这只是表达了儒者的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那么周敦颐要求二程寻“孔颜乐处”已经是在思考乐的哲学依据了。在他们看来,孔颜之乐,当然不是贫贱富贵之乐,而是诚、仁之性所自有的快乐,这种乐的实质就是同宇宙本体合一,与天地变化合一,不仅超越了自我,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社会伦理。朱熹在注释四书时就特别注意与推崇这一点。在注孔子“饭疏食饮水”段时说,圣人的精神境界是与天理浑然一体的境界,达此境界,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保持精神的自得与快乐。疏食饮水与箪瓢陋巷一样,贫困的生活本身并不值得乐,而是贫困不能妨碍与改变精神上的满足,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所以有这样的自得与满足,是因为体验到了天理。这种体验是内在的,不由外在的力量与环境所左右,所以人生之乐,不是向贫贱处求,也不是向富贵处求,而是反身向内,“只去自家身上讨”,就是去除私欲,回复天理所赋之本性。他解释“曾点之乐”说,孔子和曾点与圣人志同道合,当一个人完全没有私欲之时,就会心胸完全敞开,与天合一,与理合一,“日用之间,莫非天理,在在处处,莫非可乐”。[6]1027。
由此归纳儒家之乐:一方面是个人的情感体验与精神境界。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生与社会,儒者并非不知其苦,但他们更愿意以人生为乐,以积极乐观的入世态度,在自然与人世的万事万物与风云变化之中,体会人生的乐趣,感受生命的快乐,并在此中体会出“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是对众乐与天下之乐的期许与追求。儒者从“独乐”到“与人乐”再到“众乐”,乃至“天下之乐”,不仅体现出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更表达出其以天下之乐为乐的终极追求。就此意义而言,儒家的“众乐”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民幸福”。以此来释读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可以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反映了中国人民与儒者千余年的呼声与愿望。
四、结 语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儒学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都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不同的儒者所倡言的核心思想与关键词也各有不同,孔子说仁,孟子存养良心,宋儒论天理,陆九渊发明本心,王阳明致良知,李贽赤子之心等等,都内在地涵有“真情—仁性—良心”这个思想路径与逻辑结构,虽然不是现在所说的“初心”,但可以说都是其思想与文化资源。儒家一以贯之的民本思想以及对于“众乐”的关切与追求,也与“根基在民”“为民造福”等论说一脉相连。当然,“不忘初心”的内涵更多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发展的先进文化理念,远非儒学所能涵盖与释读。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所说的,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的思想体系,“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8]。因此,本文以儒学来释读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之说,既是以儒学来释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以体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明的民族特色,更是以此来“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更重要的是,以儒学来释读“不忘初心”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也是为了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