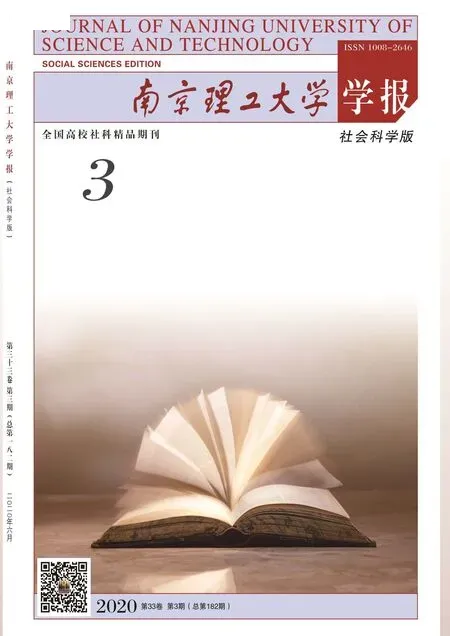基于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传统聚落保护研究
——以长泰珪塘非遗保护为例
林银焕
(福州大学 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4)
“聚落”一词,《史记》载云“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1],《汉书》载云“(黄河)时至而去,则填淤于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2]。本文的聚落概念是文化地理学的范畴,以区别于今天的行政村概念,是指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因人口的聚合而自然形成的居住形态,即自然村落,它是由一定的族群、文化和业态所维系和发展的聚居体,也包括因族群的繁衍、居住形态的延展而产生的村落集合体。
一、走向现代化:传统聚落及其文化遗产的困境与机遇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一方面城中村和城市周边的乡村大量被拆迁和改造,城市记忆中的乡村景观快速消失;另一方面,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乡村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空心化情形。传统乡村的人力资源、社会结构、产业方式、民俗生活都出现了比较大的改变,乡村发展的内动力不足,不仅聚落形态出现了比较大的改变,聚落文化也因为人口的流失和文化空间的丧失而失去其持续发展的内在活力。现代文化的侵蚀以及部分地区旅游业的过度开发,也使原来独具特色、形态丰富的传统聚落文化日益变得平庸、同质化和失去原真性。几千年来所积累沉淀的传统聚落文化正在快速走向式微、消亡。
然而物极必反,这种困境一方面在不断地延续,一方面也在酝酿着变革,文化的生命力在不断地自我调整中与自然环境形成一种新的再生力量以适应外部的挑战,这也是传统聚落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城乡之间发展的巨大差距和失衡使得二者之间也产生了一种制衡和调整的力量。快速发展的城市产生了大量的“城市病”:拥挤、污染、紧张、冷漠等等,这使得乡村作为其对立面成为一种理想化的文化景观,成为对现代性进行批判进而疗伤的情感对象。改革开放40年中涌入城市的两三代人集体产生了乡愁,那种与故乡母体天然的关系和情感不断地在发酵,回归和反哺成为乡村重建的潜在的心理能量。现代交通、物流和“互联网+”则进一步打破了乡村发展的障碍。消灭贫困、减少城乡差距、保护环境、激发农村活力的工作从社会公共管理层面被提上日程。2018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乡村振兴成为一种国家战略。作为乡村振兴计划中的精神层面,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显得尤其重要。
近几年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走向了更广阔的空间,也进入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文物保护工程和非遗保护工程陆续深入开展,一大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街、名村相继挂牌认定,非遗项目的认定和传承人的认定也在神州大地上波澜壮阔地展开。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资源调查和重点项目的申报认定上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辉煌成绩。政府层面和学术层面的重视使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了更多的顶层设计,以及政策、执行的保障。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兴起,文化旅游成为一种更为时尚、更有内涵的旅游方式,文化体验、游学等方式方兴未艾。静态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对于濒临灭绝的非遗特别有效果,博物馆保护方式是其重要的和基本的形式之一,但同时也只是一种阶段式的保护方式。如何使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互依存、共生共荣,文化环境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谐相处、持续发展,文化生态——一种新的动态的、活态的、多样的、共生的、整体的、系统的文化可持续发展保护模式,成为当前文化遗产保护迫切要探索的途径。
二、闽南文化生态视域中的长泰珪塘聚落文化
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1955年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H Steward)倡导建立,是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主张从人、社会、文化、自然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3]。2000年以后,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和立法,文化生态学也被引进我国并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理论依据。2004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7年文化部在福建厦漳泉地区率先成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08年至2010年徽州等其它7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也相继成立,2011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颁布,这些实践和立法都使文化遗产保护进入文化生态保护的新的历史阶段。
所谓文化生态保护区, 是“指在一个划定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区域, 为达到保护目标而指定或实行管制和管理的地区。有自然遗产‘整体生态环境’: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乡镇、传统民居、历史古遗迹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依相存, 并与人们的生活自然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和谐相处”[4]。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要“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相结合、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努力保持、维护自然和文化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5]。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正是遵循这个定位和原则开展了相关的保护工作。
闽南族群来自中原地区,衣冠南渡,筚路蓝缕,在与当地闽越族融合过程中,以宗族为核心形成了新的族群,并持续地迁徙,广泛分布在台湾、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中原文化与与闽越文化、南洋文化,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各种交汇形成了今天闽南别具一格的聚落生态和文化生态,并在闽南大地生生不息、融合创新。2014年福建省政府出台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截至2016年,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厦漳泉三个历史文化名城,漳州古街、泉州中山路和厦门中山路3条历史文化名街(区),12处历史文化名镇(村)、古村落;有南音、妈祖信俗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5项,国家级非遗58项、省级155项,认定了一批非遗传承人,并建成了非遗中心数据库;建设有完整的非遗保护区域、非遗项目生产基地、非遗示范点、非遗示范园、非遗传习中心体系,以及闽南文化研究院和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长泰珪塘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珪塘是长泰县岩溪平原上的一个传统聚落,因为河塘沟通、阡陌纵横,原称沟塘,又因聚落形同玉圭,故雅化为珪塘,明清时期称为长泰旌孝里珪塘社。珪塘传统聚落以现在的珪后村为核心,包括了珪前、谢谭等村落,主体为聚族而居的叶姓宗人。珪后村是闽南众多传统聚落中的一颗明珠,其申报的主要文化资源,就是以叶姓珪塘文化遗产为蓝本。
作为传统聚落的珪塘,山明水秀、物产丰饶,历史上就是全国优质水果“长泰芦柑”的主产区。自南宋末年叶棻开基以来,历600多年,开枝散叶、瓜瓞绵延,现有人口上万人。丰饶的土地、繁盛的家族,也孕育了十分发达的农业文明。叶姓宗族名人辈出,明清以来科举名人有30多人,不乏文武进士、名宦巨贾、军政要人,而今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各领域也是人才济济。有下水操、元宵点灯等省级著名的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传承空间关联的主要建筑遗产有霞美堂、祥云堂、积庆堂、大学庴等古民居,普济岩、追远堂等庵庙祠堂,以及牌匾壁画、碑刻铭文、古树老井、方塘古陂等丰富的文化古迹,农耕遗产、信俗遗产、宗族遗产、建筑遗产等共同构建了珪塘十分典型的闽南聚落文化生态。今天走进珪塘,依旧是一幅传统与现代交汇共荣的生活画卷,文化遗产不仅仅是静态地展示与保护,而且表现出了传承与创新的勃勃生机。
三、珪塘文化生态与非遗可持续发展
珪塘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雄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现在很多乡村衰败的直接原因就是其区位的局限和经济基础的薄弱。比如长泰县隔壁的安溪县上智村,其白头格古村落也被评为福建省古村落、泉州十佳古民居,但因为地处深山辟地,村民大都外出谋生或迁居,现今胡姓人口急剧下降,只剩老弱病残,而周边的旅游资源也不够典型和丰富。尽管白头格胡姓家族中的胡钢及其上市公司“新大陆”有意进行保护和开发,但实际操作难度很大:传统聚落中仅有古民居建筑而无人、无生活形态,其文化遗产保护基本只能走民居博物馆式的纯旅游开发模式。而珪塘地处平原中心,交通发达,土地肥沃,经济能力强,与外界的关联密切,村民有很强的归宿感和家园意识。其富庶和发达足以从经济层面和生活层面支持其保持较好的文化生活状态和文化遗产的传承。有人生产、生活的聚落,其文化生态就有了依托,就能与现代生活产生现实关联,而不会被自然消解和破坏,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就有了保障。
建立在富庶发达的物质文明基础上的传统聚落,其文化遗产具有非常强的内生性和普适性。农耕文明和儒家文明高度融合的传统社会文化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色,其文化内在凝聚力、整合力和辐射力在今天依然非常强大。珪塘叶氏宗族中,耕读传家,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这强烈地表现在其两项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上。下水操是珪塘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号称珪塘的狂欢节。叶氏先祖、长泰县尉叶棻曾力助陆秀夫抗元而殉职,儿子亦在威海卫抗元战斗中牺牲,为纪念陆秀夫背负南宋小皇帝赵昺跳海的崖山之难,叶氏后人遂于每年正月十七以众汉抬神下水巡游的形式表达他们对陆秀夫忠心殉国的崇敬并弘扬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三公“忠义勇”精神,历500多年,成为珪塘当地最重要的民俗节庆活动之一。而另一项元宵点灯,则是为了祭拜祖宗,表达人丁(灯)兴旺的祈愿,生丁或科举成名都要在叶氏宗祠追远堂举行点灯仪式。这两项仪式都是儒家忠孝文化在民俗活动中的一个外化。没有形式就没有内容,民俗仪式恰恰就是传统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最好的一种载体。
这种民俗仪式的生命力,来自于聚落族群上下一心的文化遗产保护自觉意识和参与热情。聚落中的权力机构的引导和推行也是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重要力量。族长和村长共同构筑了聚落的权力结构。族长(或宗族理事会),聚落中族群文化的代表,意味着文化权威和精神权威,实际上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代表性人物,其作为核心的向心力和辐射力可以有效促进文化生态的整合和推行,比如族规民约、婚丧嫁娶、仪式崇拜、族谱修订、宗亲联谊、公益活动,是村行政权之外潜藏的族权。有些族群工作,比如移风易俗,把元宵点灯习俗的资格扩展到生育女娃、现代升学,这就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是传统文化自我调适、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一个良性案例。而村长(或村委会)作为基层行政权力代表,其与各级行政机构文化政策的上下接合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统筹和推进,比如乡村振兴规划、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申报、乡情馆建设、文化旅游推广以及土地、民居、公共场所等的调整,也关系着文化生态的存活。这种地方行政机构的引导、推动,既有利益考量,也有文化内生力量的制衡因素。村民的素质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文化的归宿感和自信力,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都会影响到其文化遗产保护的态度和参与的自觉意识。而文化遗产的拥有者,比如建筑所有者和非遗传承人,其生活状态和文化素质对于文化生态的构建也是意义重大。村民对于乡村改造和古建筑修缮的理解和支持,甚至主动让出或献出古建筑作为文化旅游和乡情馆展示空间,这也是传统文化感召力量和文化自觉意识的体现。
与此相关联的是文化空间的存在。这种聚落的文化空间,主要体现在祠堂和庙会空间。追远堂作为叶氏祭祖和点灯习俗的活动空间,对于承载家族文化活动和庆典活动有重要的时空意义。而叶氏支系分宗的祖庴之一——升庴,经过动员后原住居民都搬出了老宅,为珪塘的乡情博物馆建设留下了充足的建筑空间。另外普济岩庙前广场和池塘则为下水操大型民俗游神活动保留了宝贵的仪式空间。珪塘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聚落的基本形态没有过多地被人为破坏,古村落和现代建筑相对独立,彼此保持了一种友好共存的关系。珪塘聚落中旧有宅基地的现代翻建较少,整体建筑风格和聚落形态没有被模式化的新农村规划和建设所破坏,这也为传统聚落保留了较为淳朴和感性的视觉肌理,传统文化空间的基本功能得以保留,这也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前提。
传统文化空间在保存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效承载了文化生态,进而使文化遗产得以辐射其瑰丽的色彩,创造了文化旅游和文化体验的经济价值。美丽乡村建设和文化旅游的有机结合,作为一种外在的驱动力也促进了传统聚落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发展。长泰的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发展很快,不仅拥有天成山、天柱山、十里蓝山这样的自然风光,而且还有马洋溪漂流、三重古村落、上蔡慢客村、龙人古琴古村落这样的休闲旅游圣地,长泰还拥有漳州唯一的状元文化,作为生态旅游和鱼米之乡,长泰的全域旅游前景广阔。与此相对应的是珪塘文化旅游的应运而生,珪塘成熟的传统文化生态有其特有的吸引力,珪后村适时结合新农村建设开展乡村文化景观的改造,因地制宜地建设开放的传统文化体验旅游,并通过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传播和民俗活动吸引潜在的游客。2019年春节,首届珪塘民俗文化节拉开序幕,向世人展示了其原生态的民俗节庆和乡村休闲生活方式。珪塘文化中的中医文化,比如药签和道医董奉;建筑遗产中的霞美堂,即叶文龙故居,都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挖掘和开发。这类潜在的特色文化资源还很多,比如南音、闽南大厝建造技艺、美食等等,共同组成了珪塘文化生态系统。当然,旅游开发应该是适度的,特别是其聚落族群文化生活的原生态和原真性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否则杀鸡取卵,得不偿失,那样不仅无助于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是从精神维度上消灭了聚落文化的灵魂。
四、结 语
今天,在城市化进程喧哗与骚动的背后,是传统聚落文化和乡村生活最美丽的风景,是乡愁定点投射的情感对象和价值逻辑。2019年李子柒成为全世界的网红,某种程度上也是传统聚落文化和乡村生活魅力、潜力爆棚的一个最好的导游词。如何保护好传统聚落文化生态,挖掘其中富有特色的非遗文化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使文化遗产保护和新农村建设成为一种良性互动,从而打造一个生态友好、文明发达、诗意栖居的人居聚落,依然是我们不断实践和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