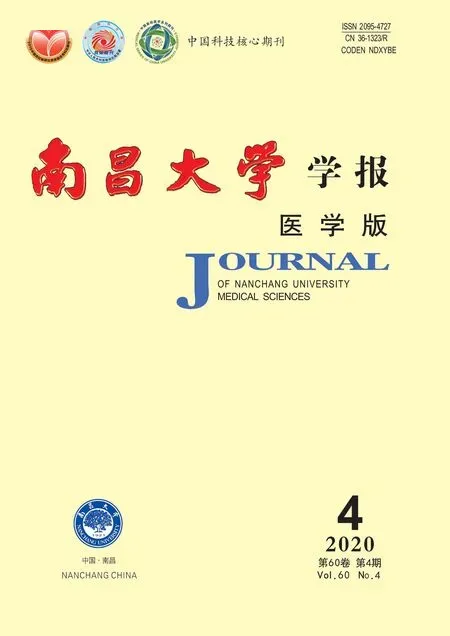地塞米松对脂多糖激活的核因子-κB信号通路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杨忻宸,周全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麻醉科,上海 200233)
炎症反应是人体免疫系统与受损组织间的相互作用,诸如感染、创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有毒代谢物等多种刺激因素均可造成组织损伤从而引发炎症反应。革兰氏阴性菌是造成感染的常见病原体,其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之一脂多糖(LPS)是重要的炎症诱导因子[1-2]。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是先天免疫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并且在适应性免疫系统的建立中也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人们最早发现的Toll样受体4(TLR4)可与LPS结合并被激活,由此启动核因子(NF)-κB通路触发促炎因子的转录与表达[3]并最终造成局部炎症的产生,参与疾病的发病。因此,TLR4/NF-κB通路在炎症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地塞米松作为糖皮质激素(GC)的代表之一,被广泛应用于治疗炎症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过敏性疾病以及防止移植排异反应[4-5]。多项研究[6-7]表明,地塞米松可通过下调多条炎症通路包括NF-κB通路的表达而发挥其抗炎等作用,且早期应用地塞米松似乎对LPS引起的脓毒症预后有积极作用。然而,也有研究[8-9]表明,在治疗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时大剂量或者长期应用地塞米松将导致其抗炎作用减弱,甚至使急性炎症转为迁延不愈的慢性炎症。因此,探索地塞米松对LPS-TLR4/NF-κB信号通路的作用及调控机制对指导脓毒症等炎性疾病的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1 地塞米松药理学特性
数十年前,地塞米松这一强效且廉价的人工合成糖皮质激素被认定为炎症性疾病治疗的金标准。然而,医学发展至今,地塞米松的临床应用却因其严重的副作用而受到了限制,如:胰岛素抵抗、肥胖、青光眼、骨质疏松、伤口愈合困难甚至库欣综合征等[10-12]。
为了尽可能发挥地塞米松等糖皮质激素的临床治疗效用并且规避其副作用,学者们尝试了从分子层面解读其作用机制。最终发现,地塞米松通过与糖皮质激素受体(GR)结合而发挥其抗炎、抗免疫等作用。静息状态下GR所位于细胞质中,与地塞米松等结合后可发生核转位并与DNA序列相互作用从而启动靶基因的转录,最终导致多条炎症通路,包括NF-κB通路,改变炎症甚至疾病的发展过程[6,13]。近年来,通过全基因组定位GR靶基因以及分析小鼠突变模型等,学者们正逐步揭露地塞米松及GR的分子机制并有望以此为理论基础探索出更加安全、副作用更小的治疗方法[14-15]。
2 LPS诱导的TLR4/NF-κB信号通路激活
Toll样受体是一种跨膜模式识别受体,可识别来源于包括病原体、不同的细胞因子等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16],使胞质中相对应的适配蛋白向其聚集以诱发进一步的级联反应,最终激活TLR4/NF-κB通路,启动促炎因子等的转录。
迄今为止发现的众多可被TLRs识别的PAMPs中,最著名的就是来自革兰阴性菌细胞壁[17]的LPS。LPS可被TLR4识别并作为配体与之结合,再通过胞吞作用进入细胞[18]。随后,通过TLR4适配蛋白髓样分化因子88(MyD88)依赖或非依赖通路最终激活NF-κB。其中,最主要为MyD88依赖通路。LPS与TLR4复合体入胞与MyD88相结合[19],通过一系列激酶和因子的参与可激活2条亚通路。1)经典的NF-κB抑制蛋白激酶(IKK)通路:IKK被MyD88激活后,使静息状态下的NF-κB抑制蛋白(IκB)/NF-κB复合体解离,同时IκB磷酸化并降解。此后,游离的NF-κB二聚体(由p50和p65两个蛋白亚基组成)向细胞核移位,结合至DNA中的同源位点并启动编码白介素(IL)-6及白介素(IL)-12的基因转录,最终促进主要的促炎因子释放[20]。2)有丝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s)通路:MyD88也可激活MAPKs从而对胞质一些转录因子包括活化蛋白1(AP-1)的活性进行调节,使其发生核转位并启动下游信号传导过程,最终同样推动促炎因子的表达[21]。
3 地塞米松对LPS-TLR4/NF-κB信号通路的影响
LPS对机体的侵犯可使细胞内TLR4/NF-κB信号通路激活,促进IL-6、IL-12及肿瘤坏死因子(TNF)-α等促炎因子的释放,导致局部炎症反应的产生甚至SIRS的爆发。地塞米松可通过与胞内的GR结合,转位至细胞核后干扰NF-κB通路的下游转录过程从而调节下游的转录过程[22],最终可影响炎症因子、TLR4以及抑制蛋白IκB等NF-κB通路各组分的表达水平,改变炎症的转归。
3.1 GR的基因组作用
早在上世纪末就有学者[7]发现,地塞米松可激活细胞质中的某些核受体使其发生核转位,核受体与DNA的特定位点结合后,可启动目标基因转录过程从而对下游炎症通路进行调节;糖皮质激素可增加NF-κB抑制蛋白IκB的含量,进而推断地塞米松是通过这一方式将NF-κB“固定”在胞质中使其信号通路得到抑制。但是,HECK等[22]利用突变的GR进行实验发现地塞米松作用后虽然IκB水平未得到提高但NF-κB的活性仍受到了抑制。这一发现大大推动了人们对核受体GR的进一步研究。
CAELLES等[23]发现,当对促炎信号发挥拮抗作用时,GR可直接对MAPK通路进行干扰最终导致基因调控水平的抑制。此后,针对GR的作用机制人们继续提出了数种猜想,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GR入核后是通过蛋白质间的相互作用与AP-1或NF-κB结合以抑制下游转录过程,而不是直接作用于DNA[24]。也就是说,当LPS激活TLR4/NF-κB通路后,NF-κB或AP-1入核并与DNA结合,此时GR进入细胞核并与它们相互作用,抑制靶基因的转录与表达。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25]提出GR可与其他转录因子共同与基因组中的复合元件结合并影响炎症靶基因的转录,这一复合元件是由GR的结合位点和其他转录因子的同源序列部分重叠而形成的。例如,GR的DNA结合域(DBD)可与NF-κB同源序列中的一个新识别出的序列相结合从而抑制NF-κB所启动的转录,这一与NF-κB反应元件相重叠的GR结合位点被称为NF-κB反应元件(κBRE)。
3.2 地塞米松对TLR4的影响
TLR4作为跨膜模式识别受体可直接与LPS结合,是整个LPS-TLR4/NF-κB信号通路的起始点。有研究[26]表明,地塞米松可下调TLR4的表达以达到抑制整条炎性通路的作用效果,用0.19 μmol·L-1的地塞米松和LPS共同培养小鼠巨噬细胞24 h后,检测细胞株的TLR4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发现与未加地塞米松的对照组相比,试验组TLR4的表达大幅下调。此外,GE等[27]以地塞米松作用于被LPS刺激的角质形成细胞也观察到了TLR4蛋白和mRNA水平的显著下降。
3.3 地塞米松对NF-κB核转位过程的影响
NF-κB核转位的成功是后续众多炎性因子基因表达的必要条件,因此从IKK被激活后使IΚB/NF-ΚB复合体解离,到游离的NF-κB入核这一过程是LPS-TLR4/NF-κB信号通路的核心。有研究[7]发现,地塞米松可抑制ⅠκB的磷酸化从而使炎症模型大鼠组织中ⅠκB水平回升至基线水平,同时降低NF-κB p65核蛋白的表达。BAYIR等[28]利用大鼠胸膜炎模型研究发现,小剂量地塞米松(0.5 mg·kg-1)即可明显下调NF-κB的表达,抑制炎症反应中NF-κB通路的激活。
3.4 地塞米松对炎症因子的影响
地塞米松可通过对先天免疫系统中诸多细胞(如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树突状细胞等)的影响来发挥其抗炎及免疫抑制作用[29]。其中,巨噬细胞作为重要的炎性及免疫细胞,在受到刺激时可分泌多种炎症因子,参与炎症反应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调节组织内稳态[30]。根据其刺激源的不同,巨噬细胞可表现出M1和M2两种表型[11]。M1型巨噬细胞介导促炎反应;而相对的,M2型巨噬细胞主要分泌抗炎因子并介导抗炎反应。前文所述TLR4/NF-κB信号通路经LPS激活后即可使巨噬细胞向M1表型极化,最终分泌促炎因子诱发炎症。地塞米松可刺激巨噬细胞向M2表型转换,同时通过其基因组作用影响NF-κB的基因转录过程从而抑制IL-1和IL-6等多种促炎因子的基因表达,最终促进抗炎因子IL-10的分泌[31]。IL-10作为巨噬细胞M2型刺激物又可以进一步推动转换过程,使M2型巨噬细胞数量增多,分泌的抗炎因子数量也就上涨。总的来说,地塞米松可通过使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达成抗炎因子增多而促炎因子减少的作用效果。
WANG等[32]亦证实了上述观点,他们测定了经LPS及地塞米松处理的小鼠骨髓来源巨噬细胞中M1型巨噬细胞标记物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和IL-12,以及M2型标记物精氨酸酶1(Arg-1)和CD206的mRNA水平,最终发现前二者的表达有所下调而后二者恰好与之相反,这也就证明了地塞米松可使巨噬细胞发生再级化,即由M1型转为M2型;同时,他们还发现经地塞米松处理后,与未做处理的对照组相比,TNF-α及IL-1β两大促炎因子的含量显著减少,表明地塞米松可使促炎因子含量减少而发挥其抗炎作用。最近,GABBIA等[7]通过结扎胆管制成的胆汁淤积大鼠模型进行了类似的体内试验,他们发现经低剂量(0.125 mg·kg-1)地塞米松治疗的大鼠与未治疗组相比,血清中TNF-α、IL-6及IL-1等促炎因子的含量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再次证实地塞米松对炎症因子含量的影响。
4 地塞米松对LPS-TLR4/NF-κB信号通路作用的影响因素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应用地塞米松可抑制被LPS激活的TLR4/NF-κB信号通路,导致抗炎因子的分泌增多及促炎因子减少,但其不良反应的产生机制仍有争议。目前,学者们大多认为地塞米松的用药剂量和给药次数是影响其对NF-κB信号通路作用结果的重要因素。
4.1 地塞米松的剂量
有学者[33]指出,地塞米松的药效学及药代动力学是剂量依赖性的。TANG等[34]发现,分别以1.0、2.5、5.0 μmol·L-1的地塞米松处理LPS诱导的小鼠巨噬细胞后,得到NF-κB的活性依次降低,并且当浓度为1.0 μmol·L-1时NF-κB活性与未经处理的对照组相比并无差异。除此之外,他们通过测定TNF-α、IL-6及IL-1β的mRNA表达发现地塞米松对这些促炎因子的抑制也是呈浓度依赖性的。另一项针对LPS诱导成熟的树突状细胞(DC)的研究[4]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应用10-5、10-7、10-9、10-11mol·L-1的地塞米松处理DC后得出,LPS诱导的IκB磷酸化受到了部分抑制,且这一作用程度似乎和地塞米松的剂量呈正相关。结合上述研究可知,在某一范围内地塞米松的抗炎作用将随用药剂量的增加而增强。然而也有学者[7]发现,当对脓毒症小鼠模型应用大剂量地塞米松(12 mg·kg-1)时,其对促炎因子TNF-α等的抑制作用反而弱于小剂量组(1.2 mg·kg-1)。
4.2 地塞米松的给药次数
尽管地塞米松在抗炎及免疫抑制等方面有显著的优势,但目前普遍认为其副作用的产生是与治疗时间成比例的。有学者[9]发现对山羊长期应用小剂量地塞米松(0.2 mg·kg-1,21 d)后,地塞米松将作为慢性应激源导致TLR4/NF-κB信号通路的全面激活,最终造成组织损伤,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地塞米松诱导了DNA甲基化的改变。然而有临床研究[35]表明,多剂量(20、10、10 mg,每24 h给药1次)与单剂量(20 mg)的地塞米松应用相比,可使手术后患者血清IL-6水平显著降低,减轻术后疼痛。这也就说明,短期多次全身应用地塞米松对人体似乎是安全且可耐受的[36]。
5 总结与展望
地塞米松是临床常用的抗炎药物,该药物在治疗过程中表现出的强大抗炎作用以及其可累及全身的副作用一直受到广泛关注。目前人们已发现了GR的存在,并阐明地塞米松可通过与GR结合干预LPS诱导的NF-κB核转录过程、下调TLR4的表达、抑制IκB的降解从而阻止NF-κB核转位,以及促使巨噬细胞向M2型再极化以达成抗炎因子增多而促炎因子减少的作用效果。然而,对于地塞米松的安全剂量范围及药物副作用的产生机制仍不完全清楚。因此,进一步探究地塞米松对LPS-TLR4/NF-κB信号通路的作用机制,确定地塞米松的理想剂量及给药次数,对全身炎症反应如脓毒症以及一系列慢性炎症性疾病的治疗具有极为重要的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