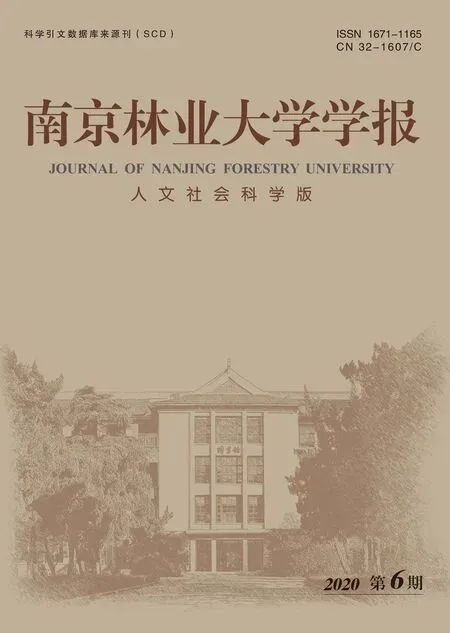大卫·哈维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探析*
田小聪,杨慧民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随着资本与空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空间即资本,资本即空间”[1]的发展背景下,如何从空间出发思考和解决生态问题,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尤为重要。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深入挖掘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空间理论和生态思想,基于资本空间生产逻辑审视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开辟了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新向度。他的生态批判思想呈现出空间性、差异性和辩证性的理论特征。
一、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多维表现的揭示
“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2]通过消灭空间实现资本积累是资本空间化的基本运行机制。因此,空间不但成为资本生产和再生产得以布展的方式,而且深刻改变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哈维基于资本空间生产逻辑,揭示了不同维度下的资本主义生态问题。
(一)全球生态维度:生态帝国主义
从全球生态维度出发,哈维揭示了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导致的生态帝国主义问题。哈维认为:“从资本主义逻辑的观点来看,帝国主义的特征在于通过开拓非均衡性地理环境,并利用空间交换所必然产生的,我称之为‘非对称性’的关系来进行资本积累。”[3]具体而言,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展开剥夺性积累,“主张自然资源全盘私有化和自然资源配置彻底市场化”[4],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签订一系列短期合同,将落后地区和国家的自然资源私有化后占为己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改善国内生态环境,将自己国家产生的污染转移到其他欠发达地区和国家。“萨默斯备忘录”就证实了这一点。当资本空间扩张到了过度危险的境地,甚至不能允许资本平和地做到这些时,资本主义国家就会通过“再领土化”“去疆土化”等比较隐晦的方式继续在全球进行资源掠夺和污染转移。作为剥夺性积累的一种延伸手段,“资本已经将环境问题转化为大生意”[5]276。资本主义国家将生态危机商品化,通过碳税和碳排放权等碳交易新市场进入各个发展中国家并从中获利。这样的手段不仅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漂绿”行为,也带来了“碳殖民主义”。
(二)城市生态维度: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
从城市生态维度出发,哈维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问题。“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必然以打破空间障碍和加速周转时间为目标,那对其无情的资本积累的议程来说是基本的。”[6]472资本通过空间扩张、区隔和修复等方式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生态问题。第一,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扩张阻隔了城市与腹地之间的生态循环。哈维认为,“城市经济安全极为重要地取决于其地方化的代谢支持系统的质量”[6]471,但由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每一个乡村都在不断退缩,导致城市与腹地之间不断分化。于是,一方面城市的供给受到腹地有限生产能力的制约;另一方面城市生产生活产生的排泄物无法顺利回转到腹地,城市与腹地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被中断了。第二,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区隔、分类和等级化发展,引起了环境正义的失衡。不同阶级、种族、性别和民族身份的人居住在不同的城市环境里。大量被边缘化的人和贫困人群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不仅如此,生活在这里的穷人为了获得环境补偿款以维持生存,不得不牺牲人居环境质量,竞相接纳垃圾填埋场项目的投标。不正义的城市环境既影响了城市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空间,也给“人本身的自然”造成了戕害。第三,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修复过程。“当某一发展阶段(资本主义阶段或前资本主义阶段)所塑造的地理景观成为进一步积累的障碍时,受地方限制的固定性和资本的空间流动性之间的张力便爆发一般性危机。”[6]340此时,资本会对地方的空间结构进行优化和改造,新的城市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旧的地方不断地被遗弃,整个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就是在这样不断“创造性破坏”的修复过程中不时地被打断重塑。
(三)生态美学维度:空间均质化
从生态美学维度出发,哈维揭示了资本空间生产中的空间均质化问题。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提出“空间生产”概念时指出“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的空间,乃是量化与愈形均质的空间”[7]。在资本空间生产逻辑中,空间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同其他商品一样进行着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多样、独特的生态景观在资本的空间生产中被剥离了,只留下一个共同的商品化形式。另外,哈维发现不少地方为了吸引资本,故意突出所谓的“地方性”和“差异性”,模糊了空间个性化和差异性的判定标准,呈现出空间均质化的新样态。一方面,各地纷纷制造“地方特色”来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各地特意创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中心、地方风景来吸引消费者。殊不知,“试图标榜自己受欢迎的那些地方最终创造了一种连续的同质性的复制品”[6]342,富有个性、差异的地方生态之美被十足的资本美学代替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均质化,不仅暴露了资本主义由于一味追求功能美学价值以致自身变得单调乏味、极其贫瘠的特质,也破坏了公众集体记忆的历史根基和情感归属地,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和冷漠。
二、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破解路径的探索
哈维认为资本空间生产逻辑下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生态问题。他不但揭示了这些生态问题,而且提出在“生命之网”的隐喻下,运用“社会-环境变迁辩证法”进行生态规划,主张把生态问题的破解路径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融合在一起,最终走向生态社会主义。
(一)构建“生命之网”
当前,人类深嵌于生活之流,人们的行为影响着生活中的其他事物,当然这些事物也深深地影响着人类,整个世界都困于一张“生命之网”中。但哈维认为:“我们是被困于‘生命之网’中的积极的行动者。”[8]213-214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使自身成为“生命之网”的积极行为主体,在“生命之网”的隐喻中寻找兼顾生态和社会的发展路径来构筑未来,把自身能力的运用和发挥置于“生命之网”的境域,既要对人类负责,也要对自然负责。另外,“地球生命之网变得如此受人类影响所渗透以至于进化的道路严重地(虽然绝不是惟一地)依赖于集体行动和活动”[8]216。所以哈维认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环境保护运动,而要通过识别和评估不同时空规模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将环境保护运动这种“战斗的特殊主义”与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相结合,把对“人类和自然的共同责任需要在多种时空规模间以一种更加动态的、共同进化的方式连接起来”[8]227,实现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
(二)运用“社会-环境变迁辩证法”
哈维认为,关于社会-生态变迁的历史地理记录清晰地表明了所有的生态问题都与各种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互相纠缠、相互作用。“社会竭力地为自身创造出生态条件和环境生境,这些条件和环境不只是有利于它们自己的生存,而且亦是它们特殊社会关系的‘本质’表现和例证。”[6]208无论是关于“自然”的话语辩论还是对生态系统的人为改造,背后都映射着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每一次生产方式的转变也会引起自然本质的变革。所以,我们要设法弥合“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各种人为裂隙,把“社会-环境变迁辩证法”置于生态变革和社会变革的中心。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不仅仅是生态危机,更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危机。我们不仅仅要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来解放自然、化解危机,更要通过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解放。
(三)走向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
我们从哈维的“社会-环境变迁辩证法”可知,要彻底地解决生态问题,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把生态问题的解决同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走向生态社会主义。哈维认为,我们还应该在以下五个方面继续努力:第一,通过复归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的解放和发展。当然这种复归不是传统浪漫主义美学式的,而是更高形式的,即“通过更加敏感的科学、更加敏感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实践以及有意义的劳动过程向感性世界的‘返魅’”[6]225。第二,一切生态规划必须充分考虑其相应的社会关系,全部社会关系的改造必须嵌入生态规划的全过程,建立生态规划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张力结构。第三,技术在生态规划嵌入社会关系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资本主义强加给的各种技术合成物,我们必须拒绝或者逐步改造,使其符合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第四,运用共性和差异的辩证法思维。根据社会-生态计划的差异和变化阐述社会主义的斗争原则,而不是对社会主义采取同质的结构。第五,由于“人类作为生态中介时的活动时空范围会不断变化”[9],所以要在不同规模的时间和空间中规划生态社会主义。
三、对哈维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的评析
哈维构建了富有特色的生态思想,这不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而且拓宽了生态政治学的研究边界。他将环境保护运动嵌入反资本主义运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时代性。但由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存在理解偏差,并且未能从资本的反生态本性展开生态批判,所以他的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最终无法将这种理论引向实践。
(一)哈维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的贡献
首先,在哲学上,哈维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辩护和修正的新道路来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坐标展开研究,并形成不同的派别:以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本·阿格尔(Agger Ben)、泰德·本顿(Ted Benton)等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修正;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戴维·珮珀(David Pepper)、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等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则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进行了深入阐发。哈维则以辩证法为研究坐标,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唯物辩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构建“生命之网”的生态哲学观和运用“社会-环境变迁辩证法”,“严肃地考虑社会和生态变迁的双重性”[6]209。他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关系,把自然和社会结构纳入一种共生的关系中,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危机,认为生态危机的解决实质为人类自身的解放。
其次,哈维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展开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这弥合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间向度。资本空间化的过程必然会将自然空间资本化。资本通过对自然空间和地理景观的独特改造,将自然空间赋予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使得自然-社会关系的变迁深嵌在资本主义的时空逻辑中。哈维指出,在这种时空逻辑中生态正义问题不断凸显,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空间修复”和剥夺性积累在全球时空范围内进行资源掠夺和污染转移造成全球生态环境的不正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秩序等级化导致了国内生态环境的不正义。另外,哈维还指出,为了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和盈余等问题,资本占据空间后对其不断地进行“创造性破坏”,将自然空间演化为一种积极的积累策略,发挥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作用。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自然地理空间根据资本的运动形式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这些看起来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样态无一不反映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造成空间的均质化和同一化。
最后,在反资本主义运动上坚持“战斗的特殊主义”和全球抱负相结合,推动环境正义运动向社会正义复苏的转变。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变化,加之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思潮的泛滥,反资本主义运动因而也变得相对碎片化、多元化了,“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人中间都会发现反资本主义的力量(以及,因此出现的积极斗争的潜力)”[6]492。但是,这些运动受制于自身特殊主义的战线内部,无法将“战斗的特殊主义”与全球反资本主义抱负相结合。环境正义运动正是如此,哈维就曾指出,“环保运动一旦超越表面功夫或政治改良的层次,必须是反资本的”[5]280。但是,目前的环境运动要么是抵制污染,要么是禁止商业采伐,无法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构成威胁。因此,他强调反资本主义斗争不仅需要同资本主义不平衡的时空发展相一致,根据资本主义不平衡的历史-地理发展条件和易变的不平衡发展空间展开灵活斗争,还要将不同领域的运动统一起来,从多种差异中寻求政治共同性,实现阶级联盟。也就是说,我们要跨越环境运动和社会关系间那条能够形成普遍政治问题的界限,将环境正义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通过环境正义运动复苏整个社会的正义运动,为“战斗的特殊主义”找到一条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政治解放道路,从而形成具有全球抱负的反资本主义运动。
(二)哈维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的缺陷
首先,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自然观存在认识上的误解。马克思是从“实践”出发来建构有机自然观的,强调人、自然、社会是在“实践”基础上耦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而哈维在“社会-环境变迁辩证法”中虽然强调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性和有机性,但他是基于“过程辩证法”,从“过程”思维出发认为人、自然、社会这些“部分”和“要素”产生于一个机体系统中,具有浓厚的怀特海主义色彩。正是因为哈维没能从“实践”出发理解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导致其在破解生态危机的路径中回归到了人性和美学上,对科学技术持有悲观主义的偏见。另外,哈维的这种“过程”思维虽然能够在一定意义上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划清界限,推动生态哲学观的进步,但正因为这种强调“过程”的思维方式使其在“生命之网”的生态哲学观中,赋予自然与人类同等的价值福祉,这样容易导致价值泛化,从而难以与“万物有灵”论划清界限,甚至陷入有神论的错误思潮。而且哈维未从“实践”出发理解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必然导致人们在践行“生命之网”的生态哲学观时,沉溺于只靠发挥意识潜能的幻想,忽略和脱离现存的现实条件,陷入唯心论。总之,脱离“实践”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无法立足于现实,无法与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相区分,最终也就无法领会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魅力。
其次,哈维未能从资本的本性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将世间的一切都纳入自身的价值体系,将自然界的一切都祛魅,自然仅仅是资本“效用原则”的具体体现物。另外,资本不但把自然界视为自身的有用工具,而且将这种工具应用到资本增殖的本性中,无休止地利用自然界的有用性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然而,资本在无限增殖的过程中会受到自然资源有限性的限制,所以“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0]。因此,资本不得不创新其发展形态,从而转向空间生产,一方面不断扩张物质生产资料的来源地,另一方面将空间中的各物质元素不断地进行“创造性破坏”,满足其增殖的欲望。
可见,“空间生产的发展状况受到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特定表现”[11]。然而,哈维受到自身地理学学科的视域限制,无法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从资本本性出发考察生态危机。他虽然意识到资本空间生产带来了生态问题,但其只能从空间生产的经验层面分析问题,不能像马克思那样把空间生产置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分析和思考,所以无法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根本批判路径出发分析生态问题,无法从不断变化的空间生产过程中找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内在本质矛盾。这样不但不能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把脉会诊”,而且容易使人们对空间生产本身产生误解,盲目地放弃空间生产这种生产方式。
最后,哈维的生态社会主义规划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缺乏具体的实践指向,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哈维在走向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中特别强调“社会关系和生态计划”“共性和差异的辩证法”“时间和空间规模问题”[6]226-230等,但这些仅仅是一种学术理论,没有具体的实践指向,也不能产生现实的实践结果,并且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空间。比如,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生态规划,以达到预定的生态效果;如何协调共性与差异之间的关系,既能辨别差异也能发挥共性;如何在差异的时间和空间规模中开展环境正义运动,并且要在这种持续变化的时空规模中容纳以上的社会关系、共性和差异等。哈维对这类棘手且十分麻烦的难题并没有作具体的论证。另外,哈维虽然强调了阶级联盟在开展环境正义运动中的重要性,但是对阶级的主体力量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阶级规划也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即使哈维敏锐地发现了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阶级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中产生了内部分化的离散力,发达国家的工人与资产阶级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合谋了。但是很遗憾,他并没有指出克服这些离散力的具体路径,最终无法在“战斗的特殊主义”与全球抱负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之间找到一条双向互补、切实可行的道路。
总之,哈维的生态社会主义规划与约珥·克沃尔(Joel Kovel)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规划一样,没有揭示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路径,也没有指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在生态方面的具体运行机制。他的生态社会主义规划不清晰,仅仅停留在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考察上,需要克服诸多的理论和实践难题,还有一段艰难且漫长的道路要走。
四、结语
综上所述,哈维基于空间视角,坚持“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社会-环境变迁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富有特色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尽管他的这种思想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弥合了生态批判和生态建构的“空间失语”。这为人们认识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也对我国推动生态治理国际化、促进城市化绿色转型、构建绿色空间格局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