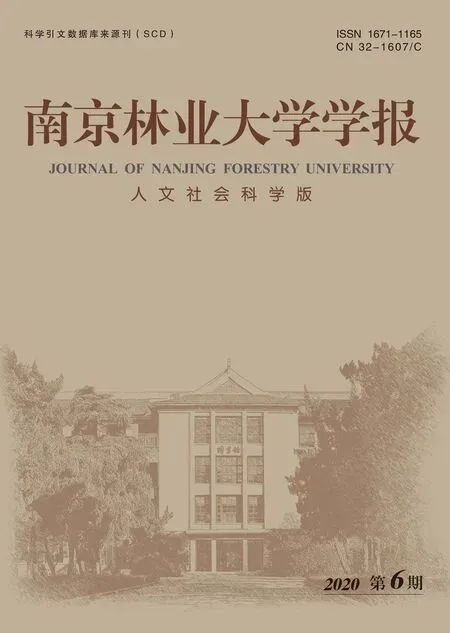适应主义与生物适应性*
刘华军
(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适应与适应主义不同。适应(adaptation)概念历史悠久,艰涩难懂。在达尔文之前,适应为自然神学所利用,作为造物主上帝存在的证据。适应不但要处理结果和过程的关系,而且要处理结果与功能的关系。解释适应是进化生物学的核心问题,但是适应确实需要用在真正必要的地方。[1]4-5适应主义(adaptationism)主要指以自然选择解释适应性的一类观点,这类观点认为自然选择具有普遍性、方法论优势。针对适应性命题争论不断,持续40 多年的论争对生物学相关领域产生重要影响。[2]适应主义及其反对者都不是否定适应,但是需要从适应主义论争中展现适应的正确内涵。
生物体与生俱来的复杂性决定生物学无法以简单性描述来实现。原子论在解读生物体现象时有点力不从心,但是人们又不知原子论到底错在哪里。甚至有的生物学家说,没有还原论生物学研究将束手无策。《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建立自然选择理论,认为保持各种有利变异,拒绝各种不利,是为自然选择。达尔文在遗传和变异之间寻找某种关系,但是并未确定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唯一方式。由适应问题必然延伸到目的论,目的论并不是对神创论简单复归。适应性命题不是自然选择的同义反复,而应成为还原主义的否定。
一、适应主义的还原论特质
以选择定义适应是适应主义的主要做法。第一,把适应界定为自然选择成功的表现。第二,如果性状A 选择成功,那是因为A 有使其成功的特性,也就是适应。对于第一点,可以从结果上理解适应。因为现象可以表现性状,所以对于结果的描述不难。但是,对于第二点,阐述起来比较困难。如果说性状成功意味着起初存在涉及生物体与环境匹配的特性,这种特性使性状趋向成功,那么第二点又回归于第一点。
如果说适应性是为了解决生物学中非经验性问题,那么关于有用与优势的讨论实际上是赋予适应以经验特性。若把生物体某些性状优势交给“选择”来决定,则适应与“选择”相关联。“如果适应的话语被保留,并且可以回避是因为它的使用将非经验观念引入生物学的可能性,那么对适应的分析表明适应意义并不必然依赖于目的。”[3]当然,沿着有用与优势这种表述,适应问题又被推向生物体与环境关系的讨论。
说动物适应了,也就是说这动物为了生存而适应;说这是物种一个适应的性状,也就是说这种性状是为了物种生存而适应。因而理解适应的路径出现可讨论的地方,即将适应指向目的论,适应成为对目的论的回应。若倾向于目的论,则适应是生物体有目的的特性;若不倾向于目的论,甚至反目的论,则性状的适应变成自然界中所有重要变化。将适应与功能问题相连是目的论倾向的延伸。适应主义把许多问题其实交织在一起。[4]
适应主义被分成三种形式:经验的、方法的和解释的,但是因与还原论混杂变得异常难解。经验的适应主义实际是将适应转译为自然选择,然后从经验上折服于自然选择。但是,这恰好证明自然那种强大且无所不在的力量不能为选择所表达。将适应界定为一种方法论,就是承认适应是一种有用的策略。可是从其对自然选择的态度来看,自然选择需要在层级世界的结构中进行。这种策略与传统方法论没有什么不同,同时,将自然选择引入一个误区。以自然选择为解释基础将会颠倒适应与自然选择的关系,因为适应的复杂性并非自然选择所包容。自然选择只是表达适应,而不是解释适应。不能将适应降格为自然选择的一部分。解释的适应主义将杂合经验的因果关系回归于形而上学,结果是事与愿违,必然隐藏自然选择对目的论的否定。
在传统思维中,生物体性状进化必须面对结构。如果承认结构存在层级,那么就必须考虑层次间效应。层次间效应又与初始变化一致,也似乎是必然结果。[5]一个层次上变化在相邻层次上产生结构变化,层级结构的结构者是建构这种结构所设计的实体。比如,基因复制是生物体层次上的适应。根据适应主义,局部优势引起种群变化,超越其他种群,但是每一个生物体只有局部优势,没有生物体共享的和谐。适应是进化论给出的一种原则性承诺,即最适合的生存。[6]14-15那么这种承诺有什么问题呢?生物体生活在既定的环境之中,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因而性状有局部优势,但却没有办法确定哪一点对生物体有用。
迈尔指出,还原论所表现出来的野心使其呈现三个样态。第一,构成的还原。迈尔并不否认这种还原论,他甚至指出,这种还原论能够为大多数生物学家所接受。当然,前提是不信活力论。第二,解释的还原。这种还原并不拒斥将生物体分成部分,但是相信部分组成的结构有层级,还原可以在层级之间进行。这种还原在内格尔那里变成理论间的解释,如此做法还有一个作用,即试图以此解决科学进步性问题。第三,理论的还原。人们重点关注生物学向物理化学的还原,但关键问题不在这个地方。生物学概念能不能以物理化学概念来解释,对此争论常常变成生物学是否是独立自主学科的解读。生物学内部学科间自由转换也成为寻找还原论证据一个突破口,不过事实上并没有解决进化综合论所带来的基本问题。迈尔的分析与适应主义的基调是一致的。[7]49
生物体复杂性要求否定还原论。主流生物学也正因此而容忍非选择因素倾向。Maynard Smith于1982年建立最优化(optimality)分析,选择总是产生适应问题最佳可能的解决方案。分子“中心论”则主张在分子层面遗传变异不能根据选择解释,它是突变、遗传漂移的结果。[8]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无论是在形态学方面还是在基因方面,都有人声称,自然选择有能力选择最好的,即那些保证最适合的。这种极端说法很容易被驳倒。比如,在进化过程中存在这样的现象,遗传变化是由于随机过程而不是选择,“低等”基因经常被纳入基因型。如果适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对适应的适应就是对自然选择的约束。从选择的结果来看,适应可以演绎成“为生存而斗争”的结果,适应将与竞争相关。竞争的胜利者则成为适应的代言人。然而这种论证存在矛盾。选择个体如何确定?这不仅是适应而且是选择必须回答的问题。种群中个体或是物种之间竞争导致对手灭绝,适应主义对此中行为无法解释。[9]
二、反潘格罗斯范式的悖论
毋庸置疑,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Gould)与理查德·路顿(Richard Lewontin)1979年这篇《圣马可的拱肩和潘格罗斯范式:适应主义纲领批评》是批判适应主义的重要檄文。文中主张,适应论有两个传统,一是Wallace 和Weismann 传统,一是达尔文传统。古尔德与路顿在这篇文章中借用“拱肩(Spandrels)”对第一种传统观念进行批判,反对“自然选择是生物适应的主导力量”,反对自然选择万能论。他把第一种适应论称为“潘格罗斯”范式。
潘格罗斯博士(Dr.Pangloss)是伏尔泰(Voltaire)笔下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坚信莱布尼兹的信条。他相信“我们生活在尽可能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为了最好目的而做”。但是,在如此强烈幸福感之后逻辑却是混乱的。“鼻子用来装眼镜,所以有了眼镜;腿是为了马裤而设计的,所以穿马裤。”“如果哥伦布在美洲那个岛上没有得那种疾病,那种毒害生殖之泉,甚至经常阻碍生殖的疾病,显然与自然的意图相反,我们就没有巧克力和胭脂虫红颜料。”[10]
面对“潘格罗斯”范式,古尔德等人认为原子论将进化论带入歧途。他们认为适应论是进化生物学家持有还原论的托词。在“没有适应的选择”这个标题之下,古尔德和路顿写道:“一个使个体繁殖力加倍的突变将迅速席卷整个种群。如果资源利用效率没有变化,个体将不会留下比以前更多的后代,只留下两倍多的卵,过剩的卵会因资源有限而死亡。在什么意义上,个体或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比以前更好地适应?事实上,当一个处于不成熟阶段的捕食者在不成熟物种更为丰富情况下被引导转向物种,种群规模可能会因此而减少。但是,自然选择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利于具有更高繁殖力的个体。”[11]
另一方面,古尔德等人又认为,适应主义并没有做到还原论的要求。适应主义纲领意味着缺少约束,以至于适应的直接产物成为所有有机形式、功能和目的的原因。而适应主义纲领不成功的地方是结构与功能简单匹配。比如虽然知道霸王龙前脚趾可用来挑逗雌性伴侣,可是不能说明为什么它这么小。也就是适应主义纲领不能说明生物体同一性(或者说perfect)。在他们看来,适应主义对待等位基因(allele)非常随意;结构解释是适应不能包含的,比如异速生长、多效性、物质补偿、机械强迫相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同样强调适应和选择不可分割。
生物体是一个整体,不是某个东西的离散组合。亚里士多德认为本质就是每一个事物指向实体的东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体;一是存在具有的原因。若要以优化定义的自然选择成立,前提条件是生物体的原子化。由性状建立起来的结构相互作用,并归因于部分与部分间权衡(trade‑off)。面对生物体整体性,优化结构无法容纳性状的多样性和层级性。即便是“次优”(sub‑optality),也根本不能成立。比如,遗传漂移这样微小的变化都会引起物种的灭绝。潘格罗斯范式的进化论带有非常浓厚的形而上学影子。
“为什么要如此奇怪的方式颠倒整个体系,把整个文化看作一种增加肉类供应不寻常的副现象。拱肩不只为容纳布道者而存在。”[11]显然,如此质疑来源于对还原论的不合理解读。Aztec人祭祀品被提升到解决食品短缺的高度,其中试图以一种理论还原为另一种理论的心路历程非常明显。然而,从古尔德的文本中完全可以看出,“适应”本身如何理解是关键。如果把工具的设计表征为适应,那么适应将势必走向对于起源的探究。在所谓“原初”“起源”思维模式下,“拱肩”表现出解释力不足,这与还原论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这种模式本是还原论重要构成。事实上,这种模式还是在形而上学的框架下。但是,有什么理由否定这种期待,否定从“原初”“起始”那里寻找答案的思维方式呢?适应并没有为此提供空间。
科学内部知识的积累或科学进步被恩斯特·内格尔称之为理论间的解释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彻底改变原有思维方式,并没有排除原有形而上学框架。以理论还原的方式讨论理论间关系建立在康德哲学基础之上,术语及其关系的抽象实质是在强调形式的连续性,内容似乎可以替换。而连续性探源必然建立在某种历史哲学基础上,这种历史哲学如果排除“有机论”的因素,它实际上就是西方传统理性试图坚守的形而上学。[12]
生物学发现冲击着传统思维模式,人们构想世界方式、建构有序时空的理念必须因生命复杂性而有所改变。物种与自然选择关系的辨析,基因作为生命本质阐述的基础等问题改变着传统科学哲学。物理学基本粒子探索给个体性问题蒙上阴影。个体特性“涌现”作为还原论解释的替代,用来说明生命现象的特殊性。涌现概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验相关性。解释的前提是建构事物间某种关联,寻找构成世界的基本单元,以及单元之间的结构关系。从物理化学现象中产生的“涌现”,与其说是认识论,不如说是本体论或是形而上学。
三、个体选择不否定适应性
驳倒基于群体选择的适应主义思维模式是乔治·威廉对进化论批判的根本出发点。他把选择定位于基因层面,也把适应定位于基因,因而主张与群体相关的适应并不存在。虽然他认为将突变和进化作类比是一种误导,但是他说“随机突变是对适应的毁坏”,这实际上是将适应与进化相混淆。[1]101当然,生命现象一定程度可以通过部分来解释,部分所具有的特性一定程度可以说明整体特性。可是选择一定只有在基因层面进行吗?事实上,当人们追问基因序列和功能之间关系、基因组与表型之间关系时,除了功能从部分中涌现,其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个体选择并不对立于群体选择。个体的自然选择能不能产生群体相关的适应,这取决于对适应的正确解读。
针对个体性状多用途特性,古尔德等人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延展适应(exapta‑tions)。适应对应于功能,延展适应对应于结果。他们认为生物体器官特征有的只是为其他用途进化而来,或者根本没什么功用。适应只是为了当前用途而建构,但对于前适应(pre‑adaptation)和其他后续用法来说,“适应”这个术语完全没有意义。适应不表示静止状态的结果。在他们看来,适应是为变化的历史过程或者确定功能而创建。但是又不能排除适应的另一面,这一点是为变化的原因和结果所表述,其中还有它们所遵循的机制。古尔德等人注意到适应概念中变与不变的关系,但他们没有说清楚,而且在进一步论证中走向这种论述的反面。
以他们给出关于鸟类羽毛功能的认识过程为例,对于延展适应的解读实际上是在阐述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一系列适应只不过是不同结论的延展适应,而在这种理论间的相互交替过程中进化发生,理论解释得以深化。鸟的羽毛设定为保持体温,这是一种适应。但是后来鸟的羽毛可以用来捕捉昆虫,这是一种延展适应。为了适应捕捉昆虫的需要,大规模羽毛发育及其在翅膀上的排列对于飞行来说又是一种延展适应。羽毛的覆盖是为了飞行的适应,对于羽毛覆盖做神经方面的修饰又是为了捕鱼的适应。[13]
适应若指向当前的角色,延展适应则是某些特征的初始状态。然而,如何确立初始性状,甚至什么是初始性状根本不能确定。也就是说,古尔德等人对于适应主义的反对源自还原论,可是又回到还原论。而众多问题根源就在于还原论,即便是对于反适应主义的反对。还原论在对于独立个体的静态解析中有效,但是一旦把个体置身于环境,在一个动态时空条件下,还原论将失去功效。如果强调性状起源,那么“一旦性状演化成现在的样子,其存在就不需要遗传机制之外的解释了”,“用什么来证明首先选择的特殊身份”。[14]
迈尔说,所有生物都属于屈指可数的基本设计,这种设计在形态学上称之为“身体构型”(bauplan)。古尔德等人认为身体构型受到上述三种约束,适应主义只是肤浅地修正身体构型。身体构型的过渡涉及未知的内在机制,而在历史宏大叙事中身体构型很大程度上被放弃。所以他们提出以身体构型来处理与选择力相对应的变化路径。但是,事情并未如反适应主义者所愿,适应主义思维方式不降而升,并没有因古尔德等人鼓吹身体构型而衰减。人们甚至质疑,“身体构型引发的热议显示出适应主义可以包含更加丰富的东西”[15]。身体构型如果不能成为新的工具,理论检验将会受到阻碍。人们相信调节发育基因在身体构型进化中起到主要作用,也是打开过渡路径的关键,但是文献显示,这个假说仍然不能得到实验支持。[16]身体构型与自然选择论在关键问题上是一致的。同样存在“整体主义”与“原子主义”相对立的问题。不同之处在于强调世系与发育约束,世系与生育约束在限制生物体宏观结构变化方面影响非常大。
机械的还原论遭到质疑,主要针对“部分”的本体论阐述。个体性(individuality)阐释无法归因于特性(property),还原论在解释层面失去意义。例如,孟德尔决定因子统计学上相互独立,豌豆植株长茎的机会对豌豆长出皱纹和光滑的机会没有影响。这种独立只是极端情况,决定因子(所谓基因)大多数情况下与其他基因连锁。这个例子说明还原论逻辑不成立,相似类型的概念演化和重新界定是还原的结果。科学理论的变化不是由还原引起的。自然选择在产生适应中起到主要作用,否定自然选择或否定适应都不是好办法。“试图将组织非目的论特征与机械—还原论纲领相一致。但是在形成独立状态变量间关系时,结论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释。”[17]
反适应主义否定在还原论基础上建构的三种约束形态,即所谓建筑、发育以及发育路径的约束。这只是对适应主义不同形式的回应,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生物体“适应”本身。古尔德他们认为种群规模与选择没有关系,但不能否定个体领域概念化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说,在幼体发育形态中寻求适应性意义是愚蠢的;它主要是选择的副产品,用于快速的世代循环。”[11]而他们反对者则认为可以通过个体进行选择,排斥群体选择反而更有利于探究社会行为的进化。对此,古尔德等人否定自然选择,可是在寻找替代方案时遇到困难。这实际上是双重否定,既否定还原论,又否定自然选择。但是他们的论述中充满着矛盾,既反对还原论,又主张还原论,既主张不被证明的叙事(story‑telling),又主张可预期实验的科学(experimental‑predictive science)。[18]对于生物学来说,结果必然是双重标准。双重标准就是没有标准,既不能否定自然选择,也不能否定适应。适应与自然选择没有被拉开距离。
四、进化论不是消解适应性
达尔文式进化论成就在于提出以自然选择来解释生命体的改善与起源,将生物学适应从自然神论剥离。[7]358不可否认,自然选择是最重要的力量;也不必怀疑,解释适应是进化生物学的核心问题。但是,自然选择是对适应的唯一解释吗?[19]如果将适应界定为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适应必然指向变化。可是,适应不只是指向变化,还有不变的后果。因此,目的论语言没有以适应来表达恰当。那么能不能够说适应就是一种选择机制呢?事实上,达尔文没有对适应作一个清晰的描述。
达尔文曾说过,自然选择是最重要的进化机制,但不是唯一一个。1880 年他给Nature编辑写一封信,回应英国皇家海军挑战者号上首席科学家Wyville Thomson 的挑战。Thomson认为,深海动物群根本不能支持这样理论,也就是不能把物种进化界定为自然选择的结果。达尔文回应说,“Wyville Thomson爵士能说出谁说过物种进化只依赖自然选择吗?”“有许多误解,声称我把物种的修正绝对归因于自然选择,可能我在本书第一版做过这样的评价,接下来,我把下面的话放在显眼的位置——与导论部分一起,‘我确信,自然选择是主要的,但不是绝对的修正工具。’也许这样说作用不大,因为误解的力量是巨大的。”[11]
在自然选择过程中,生物体性状存在一种功能向另一种功能转换的现象。类似于秃鹫(vulture)头上裸皮,在不同生物体之间所表现的功能不一致。结构与功能互相对应是还原论前提下因果机制的主要依据,但是这种依据在自然生物体面前发生动摇。“人们认为,哺乳动物头骨上的缝合线是有助于分娩的美妙适应。无疑,它有助于分娩,或许对分娩来说必不可少,但是对于鸟和爬行动物头骨上的缝隙来说,因为它们是从破裂的卵里爬出来的,所以可以想像这种结构源自生长法则,只是在高等动物的分娩中被利用罢了。”[20]140
古尔德认为达尔文进化论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确立所谓“机构”(agency),确定自然选择发生在哪一个层级之上。表现在生殖成功上的自然选择,依据的是生物体作为选择的位点,生物体优势在斗争中从“更高阶”涌现。从这一点上看,自然选择论中并没有摆脱那个时代还原论影响。第二是所谓“功效”(efficacy),目的是解释所有主要进化新事物的起源。事实上,那些反对达尔文的生物学家,针对的根本不是自然选择,而是适合(the fit)。根据达尔文的说法,自然选择不过是弱小和否定的力量,处于自然变异的假定之下。创造适合并消除不适合。第三是充分的外推,微观进化能够充分产生复杂和多样的生命史,根本不需要其他因果原则。[6]1288
但是,自然选择的复杂性还不只是体现在这种生物学之间的类比上。达尔文自己在后期《物种起源》再版(第六版)时强调历史在自然选择中的作用。“许多结构对它们拥有者没有直接用途,或许它们的祖先从未使用过,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的形成就是为了美观或多样……每个生物组织的主要部分都是由于遗传,尽管每一存在确定适合其自然中位置,但是许多结构与现在生活习惯没有密切和直接联系……几乎不可能决定多少事情能够解释这些变化的原因,如同外部条件确定作用,所谓自发变异,复杂生长规律。”[21]
事实上,历史作用在进化论中另一种表述应该称之为遗传。然而,遗传与变异之间关系,却很少有人涉及。遗传与变异关系异常复杂,若将论述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之上,不仅结论的可靠性没有把握,就连结论表述同样难以进行。在《物种起源》绪论中达尔文指出,即使得出“物种不是被独立创造出来的,而和变种一样,是从其他物种传下来的”这样的结论,但是无法使这个结论令人满意。[22]因为面对世界上无数物种,根本无法阐明它们怎样发生变异。历史维度本身将为自然选择行为增加复杂性,同时将造成对于自然选择理解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有其自身原因,也与人类认识能力相关。
达尔文知道,生物体结构的完善和复杂是其建立理论的关键,也是困难所在。“假定眼睛由自然选择形成,这种说法极有可能是荒谬的。”[20]148根源需要阐明完美结构如何能够表达相互适应性(co‑adaptation)。达尔文主张物种是从另一个物种进化而来,但没有说清楚这种进化机制。[23]达尔文的解决办法是,物种个体微小可遗传变异是物种巨大差异的基础,依赖环境以不同比率不同形式生存和繁殖,这种分化繁殖导致种群周期变化并最终为另一种形式所替代。如果它们占据不同的生境,那么同一物种不同种群将分离为另一种群,最终成为另一个不同物种。
依据迈尔,达尔文不知道变异的来源,直到遗传学兴起才为人所理解。达尔文所谓进化变化是选择的结果,选择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产生变异;每一代都有产生大量的变异。他们所有经验知识就是物种间大小差异。第二步为了生存而斗争;那些存活下来的个体将最有能力应对环境。它们的性状在下一选择周期产生作用。[24]自然选择是基因型非随机差异复制,只在生物体的表型产生作用。个体要继续存活下去,必须处理这个机制,即自然选择。对于自然选择来说,选择力是个体表型对于单一环境因素的需求。也就是说,选择成为个体为了生存而斗争。但是选择不总是个体间的斗争。为生存而斗争不必然得出进化变化,关键要有两种不同基因型。然而,种群如果在环境承载力之下,基因型非随机复制将是个例外。[25]当然,这里不仅有环境因素,还有生物体自身。
五、生物体与环境共同变化
适应体现在生物体各个部分,而认识适应就需要对这些部分及部分的属性特征化(characterized)。沃尔特·博克(Walter J.Bock)认为这属于形态学内容,可以通过描述特征(feature)的形式与功能来实现。形式是指物质构成的特性与物质排列,功能是这些特性与排列行为的表现。因为形式与功能之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所以从功能与形式对比的角度得不到适应概念。但是博克认为,特征具有适应本性(nature)。因而需要知晓谁来决定适应本性,也就是需要证明特征是适应的,只是适应本性与进化机制不同。[26]
这个证明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生物学角色,一是自然环境。从中可以看出,博克的论述不想强调后者。他虽然把生物体的表型特征定义为适应(adaptation),但是他把生物体个体和群体排除在外,个体和种群表现的不是适应而是适合能力(fitness)。他实际上是将适应界定在生物体内部,强调内在环境与内在选择,自然选择力发生在生物体内部。所以他认为适应性进化变化的因果机制与适应性历史描述相混淆使人们误读了适应。解释特征的进化实际上是从历史角度展开,而适应的特征则不是。
至于生物学角色,仅就形式与功能关系讨论根本不能充分表达。比如说,有这样一种做法,即把特征分为构成单位,进而考量每一部分的适应意义。虽然说特征表现为对于特定选择力的适应,但并不意味着特征的所有部分对其他任何选择力的适应。尽管特殊的物理和化学特性确实对形式和功能之间关系提出挑战,但是功能和形式是不是特征的两种属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特征有功能,但是特征有“形式的范围”,部分为个体所利用。用优化表达适应并不是好办法,因为缺乏优化标准,选择力也在不断变化。那么适应是不是博克所谓处于内环境中的选择力呢?
选择力如果建立在个体特征功能性相互作用的一般原则之上,再让个体特征成为由部分所组成生物体的结果,那么无法解释“适应是依赖于形式与功能的复合体”。因为很难把握部分化之后部分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不能说选择力量仅来自环境,因为还有生物体自身行为,但又不能不强调环境的重要作用。“适应是生物体的特征,具体而言,就是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以至于个体能够生存和繁衍。”[13]留下后代是成功的条件之一,也是继续进化的条件。这种特性在一个群体中传播,被认为是一种适应。适应是生物体在特定环境中完成特定功能的一种遗传特性,生物体的祖先通过这一特性产生的后代比没有相同特性的生物体更多。许多生物体占据了世界,环境微小变化意味着生物体生活条件发生微小变化。因此,必须进化的新生境在某种意义上与多维生境空间的旧生境空间紧密相关,进化物质也将局限于与他们祖先极其相似的物种上。
环境问题在于没有解释清楚什么是进化,并忽视物种多样性。所有进化都是由于微小的遗传积累而成的,受到自然选择的引导,种间进化只不过是在种群和物种内部发生事情的外推和放大。[27]进化意味着连续性变化,通常具有方向性。进化生物学把生物拆解为部分,然后描述每一部分解决了什么问题,再将适应性功能用于每一部分。Richard Lewontin 把这种判断性状适应过程称之为生物体的工程分析。可是,类似工程分析并不能证明生物体部分能够成为选择的单元。例如,人们试图把人类下巴解释为适应选择的结果,并不成功。齿状区和牙槽区都表现为幼态延续。下巴只是生长率相对回归的结果,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牙槽区比齿状区收缩得要快。下巴只是人们的一个心理建构,而不是进化单位。[23]
适应既描述存在的状态,也描述存在的过程。在环境与生物体关系中总会出现不对称,也就使理解“适应”变得困难。当谈到适应时,人们总会认为生物体很好地解决环境产生的问题。环境是问题的提出者,生物体只不过是对问题的回应。与之相反,生物体不是对环境的适应,“生物体建构环境自身每一个方面”[28]。过分强调生物体与环境关系,或者割裂二者关系都不是最好的选择,不必坚持某一方面具有形而上学优先性。适应问题在于环境如何理解:环境是建构的,包括生命体在内。生物体改变环境,不仅涉及自然环境,而且需要考虑行为自身的演变。生物体对环境影响形成一种遗传体系,下一代继承父母塑造的环境。生物体与环境的初始状态,作为选择的背景在选择压力下发生改变。生物体对新的刺激作出回应,改变种群中与此相关的选择压力,导致遗传变化。遗传物质在这里只是跟随者,而不是领导者。[29]在与自然的讨价之后生物体作出选择,最后的结果既是选择的结果,又是适应的结果。选择虽是生物体自身的选择,但主要是因为外部环境。适应主要是自身的,适应中有自身的变化;适应是对外部环境的反应,适应中也有外部环境变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