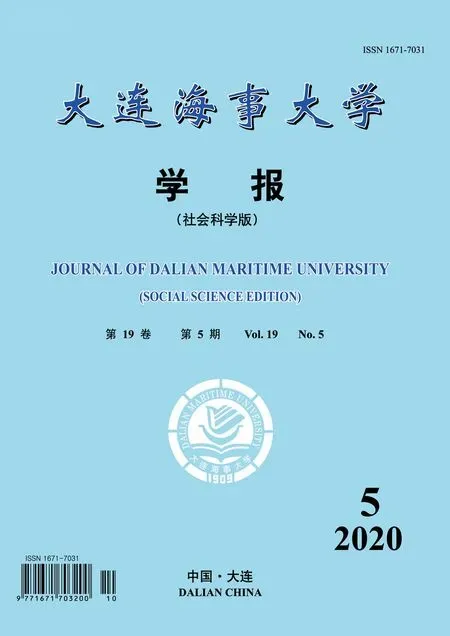从《莫罗博士的岛》到《密友》:试论科幻文学中的海洋情怀与现实书写
李 珂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一、引 言
科幻小说这一文学样式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祥地,勃兴于美国。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本身面临的伦理问题日益明显,科幻文学通常借助将对未来社会的预言转换成现实的方式来警醒和反思现代科技的发展。作为现代科幻小说的先驱,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十分注重写作技巧,对自己的作品在艺术和风格上有着较高的要求,其小说的“文学性”特征甚至成为科幻杂志编辑“忌讳”的对象(1)1927年,有一位读者写信给雨果·根斯巴克的《惊奇故事》,称H·G·威尔斯“在描写一个情景时用词太多”,而后,《惊奇故事》的编辑总是要求作者少注重语言,多注重叙事。。美国科幻作家詹姆斯·冈恩(James Gunn,1923—)说:“儒勒·凡尔纳以其潜水艇和炮弹探索深远的地方,威尔斯则探索主题。冒险提供了故事的框架,其间也偶尔有些思辨,但正是主题创造了科幻小说这一文学样式。”[1]2探索主题的科幻文学,成为威尔斯甚至是整个英国科幻小说进行现实书写的实践文本。《莫罗博士的岛》(TheIslandofDr.Moreau)发表于1896年,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爱德华·普伦狄克在海上遇难后漂流到一个荒岛上的离奇见闻。小说基本上并没有突破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范式,但是却在某些重要方面改变了读者对于现实社会的既有看法。透过其笔下的人物,读者可以看到威尔斯对英国社会的沉思与理想。
如果说在科幻小说发展中,英国科幻对现实的沉思,造成了其与美国科幻小说的不同(2)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和美国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影响,预测性的小说在美国欣欣向荣,而英国公众却无动于衷,他们无法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参见文献[1]第5页。,那么二战后日本科幻的兴起则是另一幅面孔。矢野彻(1923—)是公认的日本科幻元老,他通过大量翻译西方的科幻小说,开拓了日本科幻的天空。除此之外,矢野彻还主动进行小说创作,其中短篇小说《密友》讲述了日本一名流浪青年与一个被遗弃的机器人相遇后一起在海边生活的故事。相比于英国科幻小说“忧郁的讽刺色彩”,《密友》中天真温馨的童话特征,可以视为矢野彻在借鉴西方科幻作品的基础上形成的自身特色。另外,像是其代表作《纸飞船的传说》,也几乎没有描写硬科幻的部分,而是着重刻画外星人奥森与村子里的人们相处的细节。就思想倾向而言,矢野彻的这种创作偏好使其跟威尔斯的沉思一样,都远离了美国科幻小说创作强调的“进取的企业家精神”。英国科幻小说与文学文化的联系比其与科学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说来也奇怪,英国科幻小说从未完全从主流文学中分离出来”[1]10。随着美国科幻杂志,如《惊奇故事》对小说的商业化操作,才使科幻小说被列入到如今的通俗文学之列。
20世纪中期,随着科幻文学“新浪潮”的出现,美国科幻杂志对科幻小说创作的影响让位于书籍出版物,作家有了更大的自由去出版自己的书,于是力求职业化。更多作家也有了选择在科幻创作中强调“文学化”倾向的自由,因此,科幻小说的内容也被引向了历史、神话、文学的解读域,[2]读者对科幻作品中诸类叙事要素的解读,可以更接近作者的审美选择与创作意图。本文将《莫罗博士的岛》与《密友》作为对比分析文本,从作为“背景”的“海洋”说起,分析“海洋”如何从以往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场所上升为叙事的重要部分,以及作家的海洋情结如何隐藏在主题之外的线索中。当作为背景的海洋因素得到强调时,读者就会发现作者的写作中心其实也发生了从人到人类“创造物”的转变。这种对创造物的主体性的刻画,将读者引向了伦理道德的解读域。《莫罗博士的岛》与《密友》代表了科幻作家对科技伦理的两种书写方式。
二、从作为“背景”的“海洋”说起
《莫罗博士的岛》与《密友》分别代表了科幻创作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种倾向。在《莫罗博士的岛》中,主人公普伦狄克在海难中被救起后,随着运输动物的大船来到了一座荒岛。岛上有一位叫莫罗的科学家,他在荒岛上对动物进行了大量残忍的解剖实验,并且利用器官移植和变形手术创造了新物种——具备人类习性的两足动物。莫罗甚至给动物们做了声带手术,教它们讲话,并利用野兽们的恐惧心理使之服从,从而成为它们的“神”,但违背自然规律和伦理法则的后果是莫罗最终葬身于其创造物的撕扯之下。《密友》的篇幅较短,小说的人物只有两个,机器人和机器人的青年主人,两者关系看上去十分和谐。落魄的流浪青年在一所破屋前发现了被遗弃的机器人,于是两个人开始了在海边的生活。机器人会说话,并且掌握许多知识,他教授青年学习英语,并且在青年饥饿贫穷的时候帮助他——下海打捞沉在海底的金器去卖钱。最后,在青年因车祸去世的许多年以后,机器人仍然守候在他们的海边小屋前,端坐在那里,就像他们第一次见面那样,不时发出嘶哑的声音:“我不会哭,但是我能发出哭的声音。朋友,你就当我在为你哭吧。”(3)矢野彻小说在国内的译本不多,目前暂找不到《密友》纸质版。文本内容可以参考文献[3],下同。
抛开“海洋”意象本身的审美意蕴及其背后的隐喻联想,最直观的是,两位作者对“海洋”的描写始终都处于故事的“背景”之中。德国犹太裔学者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在其著作《摹仿论》中比较奥德修斯的返乡与亚伯拉罕献祭的故事的叙事手法时,提出了关于“前景”(foreground)与“背景”(background)的论述。《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在返乡后,女仆为他洗脚时,洗脚的场景、伤疤的来源,一切都被荷马事无巨细地展现出来,放置于读者一眼就能望得见的“前景”中。与此相反,亚伯拉罕献祭的故事是欲语还休、充满着裂缝的,上帝发出献祭的指令时身处何方、亚伯拉罕面对可怕的命令时的内心活动等,都需要读者自己参与和解释,而线索都被隐藏在看不见的“背景”中。[4]在奥尔巴赫看来,后者的叙事手法更具有阐释价值。同样地,将《莫罗博士的岛》与《密友》两篇小说中的“海洋”意象放大,就会发现这不再仅是关于科学家与机器人的冒险故事,与《海底两万里》《巨齿鲨》等直接将海洋放在前景中描写的科幻作品相比,《莫罗博士的岛》与《密友》中“背景化”的海洋将读者引向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
首先,海洋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审美意象,而是作为文本中有着独立叙事功能的“故事空间”。在《莫罗博士的岛》的开头,普伦狄克与海尔玛、水手在救生艇上漂泊了八日,“第二天之后,大海慢慢地平静下来,海面像镜子一样平静”[5]9,然后作者叙述三人的沉默和纠结。在这里,威尔斯试图用一种空间上的固定——“平静的海面”,来将故事空间与世俗空间暂时摘离,使其固定下来,进而表现一种人物内在的“现实”。正如但丁在《神曲·地狱·第十篇》中将法利那太、加尔发甘底等全然不同的人物放在同一级别的地狱中一样,普伦狄克三人也被放在了同一个级别的困境中。然而,这种看似已经深陷沼泽的现实困境却演绎着自己的生动性。这三个人的个性、职业各不相同,面对他们共同的现实时,态度也是不同的。海尔玛和水手试图利用抓阄来决定吃掉同伴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强壮的水手被选中后却反悔,两人争执不下,跌落大海。因此,普伦狄克可以以微弱胜于其余二人的人性和悲悯被上帝选中,登上了蒙哥马利的船。在这里,海洋与现实社会的联系是微妙的。一方面,它提示着读者,这些人物不是在真空中被塑造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处于社会历史的网络之中,读者在现有的故事情节以外还面临着更多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海洋自身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空间,不再像是在《海底两万里》《幽灵水母》一类的幻想小说中只是作为一个幻想与游戏的发生场所,也不像在《海的女儿》中那样被人为地赋予了某种情感色彩。
《密友》中的“海洋空间”与其所占的文本空间成反比,初看海洋似乎只是一个被顺手拈来的符号,构成了故事情节中一个不起眼的布景。但如果进一步思考——机器人要从海中打捞金器古董,海中的金器和古董从何而来?就会意识到这是人类在海上活动的历史证据,青年不只是当下的失业青年,从他失意的社会关系中,可以推演出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问题在个人身上的反映。在《密友》的开头,矢野彻写道:“这是一个21世纪的大城市。朦胧的远方隐隐约约露出高耸入云的大厦和高速公路。在远离城市的郊外,残留着一些早已被人们忘却了的简陋棚屋。”[3]《密友》写作于日本战后的萧条时期,矢野彻的创作也具有同西方科幻作家一样的忧患意识,看到了科技发展的同时人类伴随的精神隐忧。机器人和青年所居住的郊外海边,某种意义上象征着远离城市的“原始”空间。像是艾·略特《荒原》中的圣杯传说、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中的原始神话、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回家主题等,都可以找到相同的“原型”——当现代人的精神陷入颓废迷惘时,习惯于从原始空间中寻求安慰。海洋带给青年和机器人的和谐生活与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精神的崩坏之间形成一种镜像对照关系,于是海洋意象也从外部环境而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
作者的海洋情怀并不体现在主题上,而是渗透进看似不经意的线索与情节之中。《莫罗博士的岛》的故事主体部分虽然一直在突出岛上的兽人社会对人类的模仿,但真正描写人性却是在普伦狄克登上荒岛之前——普伦狄克不忍参与两位同伴残忍的抓阄游戏以及蒙哥马利前后两次对深陷大海的普伦狄克展开救援等情节,这种内在的从善从美倾向才是作者要追溯的、人类道德建立的源头。而威尔斯借助莫罗之手在人魔岛上建立的兽人秩序,从残酷的解剖实验,到教会它们生存的法则和禁忌,再到放逐它们到山林中自己生存,看似是在试图模仿人类社会,在岛上建立类似的伦理秩序,但兽人社会的崩盘、兽人重返兽性,则证实了一切都是徒劳,试图为兽人施加人性的莫罗,最终在人魔岛上建立的是一个非人性的残忍世界。这两条对人性书写的线索,一明一暗,在讲述同一个主题,却未获得统一。普伦狄克面对岛上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切时是矛盾的,他起初以为那些会说话、会盖房子的动物原本是人,是莫罗的实验让他们变成了兽,因此他是害怕的,他尝试离开人魔岛,“转过身去,朝大海的方向走去”,“我走到海水的边缘,感觉安全了”。而同一章节,他又被莫罗和蒙哥马利说服,那些兽人原本是就是动物,只是一些正在进行的前沿科学实验让他们变成了这样,于是他又选择尝试站在莫罗这边,用主宰者的姿态审视一切,这时他又“走上海滩,向他们走去”。[5]104此处的海洋,不仅在地理上构成了文明的分野,还承担了某种救赎的角色,是理性的审视者和镜子。普伦狄克从本性出发,他畏惧人魔岛,畏惧残忍的动物实验,岛上动物的惨叫会不自觉地启动他内在固有的慈悲与怜悯,所以他渴望海洋、接近海洋,甚至幻想自由的海洋可以给人以重新开始的机会。而兽人的反应相反,它们是远离海洋、害怕海洋的,当普伦狄克指挥它们将蒙哥马利的尸体丢入大海时,它们表现得不仅害怕尸体,也在害怕未知的神秘海洋,“它们急急忙忙地回到岸边,一副害怕的模样,在银光闪闪的海面上留下一条条长长的黑色的痕迹”[5]171。当读者跟着莫罗的动物实验,发现人与兽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时,研究者多从兽人社会秩序的崩坏这一点去阐释两者的区别,但如果认为威尔斯想要强调人性多于伦理秩序,那么对海洋的关注或许可以解决这个困境,因为两者面对未知的海洋的反应,完全是出于内在固有的本性。
三、创造物的主体性与科幻文学的现实书写
机器人走到海边,沉思着:“我已经很旧了,如果海水从手脚的关节部分渗进,身体内部可能要生锈。可是,即使我牺牲自己,也必须帮助朋友。”机器人脑袋里的电子计算机在1秒钟时间里就把这个问题考虑完了。接着,它一步一步走进了海里。它不需要呼吸,很快就潜到了水底。[3]
按照以上逻辑,《密友》中的机器人看似比兽人多了人性,以及作为个体的主体性特征。因为要使青年不饿肚子,他就要从大海中打捞金器去换钱,哪怕海水会使他生锈,加速机器磨损的进程,他也义无反顾,而这一切都是出于他的自主意愿。海洋带给他结束生命的可能性,也使他具备了人类才会有的奉献与牺牲精神。不过,如果从生态主义立场上来看,海洋承担的资源角色也暴露了人性的贪婪与堕落。海洋提供了青年的生活来源,在不触碰法律、不偷不抢又不想劳动的情况下,他只能靠机器人一次次下海打捞来赚钱,因此,海洋和机器人都是被掠夺的对象。而机器人之所以被矢野彻赋予人类的外形,而不是像一台机器那样,在于其有了人性、人的感情,这也是整个故事最动人的一部分。可是,他的对话内容永远在强调自己只是个“佣人”,“机器人私自藏钱是不应该的”,这种关系是从属的、不对等的,这与海洋给予人类慰藉,而人类只懂得索取甚至破坏,本质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机器人所做出的令人感动的牺牲,其实也是由人类预先设定的,一旦人工智能系统也出现崩盘,后果更加不堪设想,电影《I, Robot》就是对这种后果的演绎。从这个角度看,《莫罗博士的岛》中兽人社会的建立与《密友》中机器人的牺牲都充满了对现实的警示意味。
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将作家笔下的现实主义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个体日常生活经验的现实;二是影响历史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外在现实,奥尔巴赫认为这一现实是现代现实主义(modern realism)所表现的主要内容;三是一种内化了的,或者意识化了的外在现实,即伍尔夫、普鲁斯特所表现的“内在现实”。[6]《莫罗博士的岛》与《密友》现实书写的对象和内涵显然更接近第二种,可见威尔斯还在秉承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寄希望于既有的现实社会。这种沉思与理想渗透在其科幻文本中,也使他与注重科学内核的“硬科幻”小说拉开了距离。同时,以科技生活作为主题的科幻小说其实应该能够反馈社会现实,尤其是未来社会现实的走向,包括人类面对变化的世界所做出的回应,而这种现实书写,不动声色地将写作中心从纯粹的人类社会转移到人类的幻想物、创造物身上。
在两篇小说中,无论是被迫模仿人性的兽人还是具有自主意愿的机器人,都表现了在科幻创作中,人的主体话语权发生转移,将表达人类社会现实与内在心理状况的话语让位给这些作为客体的“创造物”。这是科幻作家观察社会的角度和思路,两篇小说中“海洋”作为空间意象所承担的某种叙事功能与社会功能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最明显的还是这些创造物身上表现出的主体性特征。当人们将《弗兰肯斯坦》作为世界科幻小说诞生的标志时,其实也不自觉地强调了这一点。正如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布莱恩·奥尔迪斯(Brian Wilson Aldiss,1925—2017)所指出的,《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家是“疯狂科学家”的原型——并不在于他敢亵渎上帝、创造生命,而是他不敢正视自己所创造的生命。[1]2倘若后现代作家的意图是解构历史、解构上帝,读者还能见到人的主体性在控制故事的走向方面发挥着作用,那么这两篇小说的主旨则是解构人类自身,表现之一便是对客体精神的强调。
在这些创造物身上,读者首先看到的一个悖论是人类的理性膨胀同人类主体地位预设的失败。《密友》中青年本身对机器人的存在并不惊奇,可见这是一个机器人大规模服务于人类的时代,科幻与童话的区别在于前者代表了对未来的预测,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现实。小说里机器人的功能在现在也已经得到实现:水下打捞机器人的出现,电子词典以及手机拓展的siri功能等。《莫罗博士的岛》中的莫罗试图成为造物主,以个人取代上帝的权威,他给他的创造物赋予人性,并且强调这是最高级的进化阶层。在这两篇小说中,人类看似都被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会发现,科技越发达,人却越来越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主体的人甚至异化为金钱、科学技术的客体。机器人取代了人的劳动,社会价值是由机器人创造的,人的劳动意义便会缩减,失业者增加,整个社会的待业人群上升,于是才有了故事里的流浪青年。莫罗所热衷和致力于建设的兽人社会也并没有实现。
这种悖论的形成与人的信仰缺失密不可分。现代科技改变和重构了人类生活的世界,人类的创造物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甚至参与与取代了人类的生活。机器人能帮助人们做好所有的事,那么人类自己应该做什么呢?人们可以利用自己以外的劳力获取自己的私利,于是也获得了盲目的自信,自认为提高了身份,获得了主体性自由,认为掌握了科技就是掌握了世界。莫罗进行动物实验的背景是维多利亚时期,这个时期的大英帝国走向了世界之巅,科技的快速发展与理性精神的强势崛起打破了科学、宗教、艺术长久以来的微妙平衡,“一度生机勃勃的信仰已偃旗息鼓”[7],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取代了基督教信仰,人们抛弃了神性启示,验证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诠释的,实践主体的意志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崇高与尊严。但显而易见,《密友》和《莫罗博士的岛》证明,这种理性膨胀的后果并不似人们想象中那般自由快乐,正如俄国思想家别尔加耶夫批判康德时认为的那样,客体化导致了人自由的丧失,使人完全陷入了异己的世界,并认为是基督教首次将自由精神引入人类社会,而康德等人将认识真理的机会统统交给了理性,等于杀死了精神。也正因如此,《密友》和《莫罗博士的岛》的背后竟然都是对人的道德期望的最终落空。矢野彻与威尔斯共同强调的是,道德最终得以实现,不在科技与知识,而在约束与神圣。
四、乌托邦与童话:科技伦理的两种书写方式
科幻小说始终关注的是人类的整体命运,因此,其中的灾难题材、对外太空星球的幻想才显得宏大而具有现实意义。像威尔斯的《神食》(1904)、《月球上最早的人类》(1901)等背景较为微观的小说,其所关注的也并不是发明家的失败或者成功,而是不断引领读者思考关于这些发明潜在的社会影响,以及不断强调着科学家应该承担的责任。根据这种立足全人类的视角,英国评论家、作家埃德蒙·克里斯平甚至将科幻小说称为“种族小说的起源”[8]。但是科幻小说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同其他小说类型一样,有些科幻小说也有塑造人物的诉求,时代发展与集体精神的矛盾症候也多在个人身上出现,一个科学家因对社会的不满而做出的疯狂举动并不比外星人入侵地球引发的世界大战缺少惊奇感。再者,虽说如今的科幻创作是建立在早期威尔斯等人对科幻小说的尝试和探索的基础上,但威尔斯的小说写作是多样的,像《新人来自火星》《时间机器》等小说就有明显的对个人情感和心灵的关注。《莫罗博士的岛》主要就是通过有关个人精神的部分表现了威尔斯书写科技伦理的方式。
《莫罗博士的岛》中,大海是普伦狄克登上人魔岛或者重返人类社会的一条必经之路,海洋构成了文明的分野,一面是人类正在进行的现实社会,一面是科学家乌托邦。莫罗站在上帝的角度,对动物们扮演了造物主的角色,用尼采的话便是“上帝已死”,人上升为主体,可以扮演主宰的角色,甚至兽人群体中的兽人也想要扮演这种角色。威尔斯在其科幻小说中多次提及尼采,例如他在《新人来自火星》中提出一种假设,即人类中总会出现极少数天才,这些天才很有可能是火星人在地球上投放的试验品,天才的才能和天赋就是“火星”成分,这从侧面也隐喻了一些科学天才与地球伦理限制的不相容。莫罗身上的超理性部分与其说是兽性,倒不如认为是“火星”成分。他因为热衷于残忍的生物实验而被社会排斥,他不满于人类社会所建立的伦理秩序,他想在人魔岛上建立一套新的秩序而非简单地复制人类社会模型。从这一点看,这种秩序的建立并不是对人性的歌颂,也非兽性的放纵,而是源于莫罗“火星人”的品质。按照尼采的观点,道德是下等人用来约束天才的工具,那么莫罗作为一个疯狂的天才科学家,他不需要道德,他在岛上所做的兽人实验、指定的道德体系和行为规则,是想凌驾于道德之上。他不断实验是为了自由地探讨未知的所有可能性,而不是为了一个预设的目标。莫罗的死是早就可以预见的,他本人也不会有太多遗憾。这既是天才对庸众的反抗,也验证了王尔德的那句名言“每个人都戕害了他所热爱的事物”。他越是想要冲破伦理界限去做自己的动物实验,他引发的后果只能越使社会所禁忌。
其实这才是威尔斯对英国社会现实状况的隐喻,那就是过度放纵个人自由,可能会引发人们意想不到的后果。20世纪初,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1900—1954)的《消失的地平线》(LostHorizon)所描写的便是这种后果引发的精神危机。主人公在对西方社会秩序充满失望后,转而向东方寻求“中庸”的学习之法,体会“适度的美德”。这可能是融合了《莫罗博士的岛》的无限疯狂和道德伦理秩序的保守之后的做法,转向在温和中寻求自由的裂缝。正如在《莫罗博士的岛》的结尾,普伦狄克的身上虽然也有着类似莫罗的“火星”成分,但他依然享受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孤独,也在这孤独中寻找着自己本分的希望。与《莫罗博士的岛》中海洋所构成的文明分界不同,《密友》中的海洋将故事与现实隔离,形成一个自足的童话世界。青年是站在时代发展末流的人,每当青年遇到了经济上的窘境,机器人都会沉入海底去打捞古董,然后去卖钱。最开始机器人并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做的事情”与“能做的事情”的区别,当青年说想吃东西时,机器人想要去偷、去抢,直到青年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会被警察抓去。机器人并不懂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法则,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与人类一样有着感情。他喜欢青年给他讲桃太郎的童话故事,在青年提及母亲去世时,他用坚硬的大手给予安慰,甚至调侃青年去将心爱的姑娘带回来给他看。矢野彻想要塑造出一个具有真正的“人性”光辉和奉献精神的机器人,试图用审美感性去对抗技术理性。
威尔斯试图通过海洋的分界建构一个科学家乌托邦,科学家妄想模仿人类的起源,挑战人的信仰和道德底线,而威尔斯又亲手摧毁了这个乌托邦,其中隐藏的伦理道德解读,也全在这幻想和摧毁之间,威尔斯在试图将读者引向一个问题域。矢野彻似乎没有这些沉重的考量,他在用一个机器人身上的奉献精神,用一个在海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童话,来唤醒人们的觉知和善良。虽然这使《密友》的主题不免流于简单,不及威尔斯的深刻,但仍可以看作是一个简单的进步,给人以美好的安慰。因为无论是对于科学家还是读者,道德上的觉醒,不能仅靠暴力美学的揭露,还要唤醒他们内心隐藏的慈悲。两位作家探索的都不是“进取的企业家精神”,而是在现实发展中的科技应许之地。
事物的根本规律和永存的法则存在于宇宙之中,而不存在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心中超越兽性的部分在它之中找到了安慰和希望。只有希望才能使人活下去。因此,在希望和孤独中,我的故事就此结束。[5]197
——H·G·威尔斯《莫罗博士的岛》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机器人还是坐在原来的地方,发出哭泣的声音。渐渐地,机器人身上长出了锈,发声的部位也开始生锈了。有一天,哭声终于停止了。现在,机器人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坐在小屋边。[3]
——矢野彻《密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