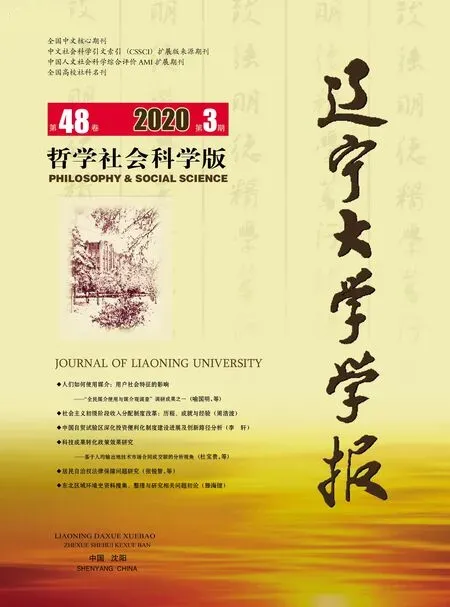知识书写与社会变迁:清代东北方志物产志研究
安大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历史学具有人文性与科学性双重属性。科学性不只是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如考据、实地调查、计量、测绘等),还体现在研究对象上,应该更多关注不同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爬梳历史上自然——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探究其内在演变的机制和规律。”〔1〕在方志各门类中,物产志记载了各地自然资源的基本情况,反映人们的物质生活,集中体现着人与自然的联系与互动。古人在长期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自然知识。而知识具有历史性,随着清末的社会大变革,知识分子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本文并不着意于对物产本身的研究,而是将方志学与知识史的研究方法相结合,透过现存110余种清代东北方志物产志对物产的记载与书写,管窥清代知识分子对自然环境认知的变化,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变迁。
一、从史料到文本:对方志物产志的知识史考察
以往学界对方志物产志的研究比较薄弱,主要将之作为农史、经济史的研究资料看待。实际上,方志物产志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近代知识分子的自然知识水平,可以之为切入点来考察古代知识分子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及其近代转型。
(一)方志物产志研究概述
民国以前记录我国自然资源的典籍以农书和方志为主,现存古农书有2千余种,而旧志有1万余种。方志这一史书体裁在宋代趋于成熟,体例始备,《物产》一门集中载录了一地有关自然资源的资料,地方志物产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对于农史、经济史、环境史、生物学史、医学史研究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但目前专门研究方志物产志的成果并不多,较有代表性的有:衡中青《地方志知识组织及内容挖掘研究——以〈方志物产·广东〉为例》对《方志物产·广东》物产载述概况、分类、异名别称以及引书概况和模式进行了研究。李昕升等《农史研究中“方志·物产”的利用——以南瓜在中国的传播为例》梳理了“方志·物产”的沿革、利用和价值。芦笛《近代地方志中的物产概念和文本信息组织——以上海官修方志为中心》,认为近代上海官修方志的物产信息既沿用了传统方志中的物产概念和分类体系,又在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下发生新的变化。王新环《方志中的物产史料价值探究——以河南地方志为例》,说明了河南方志中的物产内容,及其对研究当地农业种植、民生日用、开发利用方面的史料价值。徐清华《明清海南方志中〈物产志〉的研究》论述了明清海南方志《物产志》的体例、内容、价值和不足〔2〕。
资料汇编方面的主要成果有: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从8000多部地方志中摘抄整理物产门目资料,汇编成431册《方志物产》。60年代出版了《上海地方志物产资料汇辑》《江西地方志农产资料汇编》。90年代出版了《广西方志物产资料选编》《山西方志物产资料综录》。2019年出版了北师大历史学院主编的《中国地方志分类史料丛刊·物产卷》。
(二)知识史视野下的《物产志》与《物产志》中的知识转型
如果把方志物产志作为史料来运用的话,通过物产记载的变化固然可以管窥某一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文献并不只是史料,更是记录知识的载体,文献本身就是为了利用才产生的,知识性是文献的基本属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文献的编纂、流通和阅读的过程,就是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的过程。
王利华教授提出“生态认知系统”这一学术概念,“是指人类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对周遭世界各种自然事物和生态现象的感知和认识,既包括感知和认识的方式,也包括所获得的经验、知识、观念、信仰、意象乃至情感等。”〔3〕而知识不是人先天就具有的,是通过长期实践累积而成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这促使人们对自然环境知识的不断探索。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为民生之本,因此地方志多数都有《物产》一门,成为我们今天了解中国古代、近代知识分子对自然环境认知的重要来源。
许卫平教授认为近代方志学的上限在光绪后期〔4〕,笔者赞同这一观点。鸦片战争之后虽然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但真正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只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无论是修志指导思想,还是体例内容都未发生明显变化。甲午战败之后,社会各阶层普遍意识到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进而掀起了救亡图存运动、学习西方科技与思想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经历剧变的时期,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均对修志产生较大影响。方志编修思想、体例内容都呈现出转折性变化,东北方志物产志的知识认知由博物观趋向经世致用,知识内涵由生产经验总结趋向吸收西方科学思想,知识建构由强化满洲统治趋向培养爱国情怀。需要说明的是,在文化的近代化过程中,传统的一面仍然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存在,因此光绪后期以前《物产志》的知识特征在清末仍然存在,但社会变革与西学东渐造成的知识转型,业已鲜明可见。
二、《物产志》的知识认知——从博物趋向实用
中国古代士人追求博闻多识、通晓众物,方志物产志以内容丰富、引书广泛相尚。清末知识分子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物产志》中物产概念与文本书写也相应发生变化,知识的博物性转向实用性。
(一)传统的博物观念
东北森林覆盖率较高,历来是物产丰饶之地。早在魏文帝时,古族挹娄便向中原王朝进贡毛皮。《晋书·四夷传》载“周武王时,献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辅成王,复遣使入贺。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来贡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属。”〔5〕现存最早的有物产志的东北方志是明嘉靖本《辽东志》,在《地理志》中下设《物产》一门。通观《辽东志》《全辽志》与清康熙年间盛京地区府州县志,对物产的记录基本都是简单罗列,几无介绍,体现出对物产不够重视。从康熙二十三年本《盛京通志》开始,物产书写模式逐渐形成,考证与注释也日益丰富。《(康熙)盛京通志·物产志》分谷之属、蔬之属、草之属、木之属、花之属、果之属、药之属、禽之属、兽之属、水族之属、虫豸之属、货之属十二子目,光绪后期以前东北方志物产志大体遵循了这个分类体系。这种复合型分类体系本身体现出古代士人的博物观念,谷、菜、草、木、花、果以植物属性为分类依据;药是以动植物经济用途为依据;禽、兽是以是否被驯化为依据;水族是以动物生活环境为依据。乾隆元年本《盛京通志》有言:“志中所载物产,充贡赋者,微物必详。经见闻者,所知皆记。考古证今,删繁摘要,物增于前,文减于旧。”〔6〕康熙以后,多数东北方志对物产的记述都比较详细,虽然志书续修内容基于前面的版本,官修与私修、府州县志与乡土志互相都有借鉴的部分,但仍然根据生态环境的变化,增补了大量资料,《物产志》丰富的内容反映出编纂者广博的知识。
《昌图府志》载,“盖以物土所宜,详考其名称、性质,亦吾中国古学之所尚也。”〔7〕记物产名称、品种、形貌、分布、用途是《物产志》最主要的内容。记别名俗称,如《(康熙)盛京通志》记莺,“或曰黄鸟,或曰黄鹂,或曰仓庚,或曰黄栗留,俗呼黄雀。”〔8〕考证物种名称,如《吉林通志》记英莪,“案:清语谓稠梨子为英额。作鹦哥者,以声同致误。高氏反以英额为误,非也。”〔9〕考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之误。记物产品种,如《长白汇征录》记稻,有“紫芒稻,赤芒稻,青芋稻,盖下白稻。”〔10〕记品种来源,如《岫岩州乡土志》记稻,“岫属所种粳为水粳,种自朝鲜来。”〔11〕记品种优劣,如《通化县乡土志》记绿豆,“粒粗而深绿者为上,粒润而淡绿者次之。”〔12〕记资源分布,如《墨尔根志》记蚌珠,“出嫩江源及那杜尔、多博库、漠鲁尔、和落儿等河。”〔13〕描述形貌,如《三姓乡土志》记鰉(鳇)鱼嘴,“此鱼咀(嘴)长尖,无鳞,脊背两肋三道骨甲,皮厚无刺,骨有脆骨。”〔14〕说明用途,如《(宣统)海城县志》记紫蟹,“辽沈各处多购,以为馈献珍品。”〔15〕
除上述基本内容之外,部分志书还记述了自然资源的数量、生长过程、生活习性、动物迁徙、开发方式、种植情况、贸易往来及相关历史典故等。记物产的数量,如《辽阳乡土志》载“约计境内骡马十五万头,驴牛十三万,羊豕各五十万,鸡鸭五倍于羊豕。”〔16〕记植物生长过程,如《盛京通志》记龙芽,“树龙芽叶似椿而大,初长刺条,来年于顶上吐芽,采为茹,其条便枯。”〔17〕记生活习性,如《铁岭乡土志》记雁,“雨水北来,霜降南去。”〔18〕记动物迁徙,如《镇安县乡土志》记虎,“昔年地广人稀,山深林密,时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矣。”〔19〕记开发方式,如《黑龙江外记》记载当地人捕鲟鳇鱼之法:“长绳系叉,叉鱼背,纵去,徐挽绳以从数里外,鱼倦少休,敲其鼻,鼻骨至脆,破则一身力竭,然后戮其腮使痛,自然一跃登岸,索伦尤擅能。”〔20〕记种植情况,如《岫岩志略》记木棉,“比年以来种植渐夥,收成亦佳。”〔21〕记贸易,如《吉林通志》记人参价格,“足色者,斤售银十五两;八九色,斤售银十二、三两;六、七色,斤售九、十两;对中者,六、七两;泡,三两。”〔22〕记典故,如《黑龙江外记》记桦木,述宋代洪皓使金“流冷陉,写《四书》于桦叶教弟子。”〔23〕
清代东北方志物产志引书也十分广泛。总体观之,经书引用《尔雅》《礼记》《诗经》《周易》的频率最高,医书引《本草经》很普遍,方志中《大明一统志》《盛京通志》、字书中《说文解字》引用比较多。此外,还有乾隆四十九年本《钦定盛京通志》引《后汉书》《晋书》《北史》《新唐书》《宋会要》《金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吉林通志》引《后汉书》《三国志》《魏书》《旧唐书》《册府元龟》《通艺录》《柳边纪略》《绝域纪略》《宁古塔纪略》《东华辑要》《扈从东巡日录》等。《黑龙江外记》引《月令章句》《吕览》《异域录》《元史》《本草集解》《梦溪笔谈》《清文汇书》等。《长白汇征录》引《广雅》《通雅》《埤雅》《释名》《正字通》《字说》《易卦通检》《禽经》《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群芳谱》《说文解字》《拾遗记》《陷虏记》《荆州志》《风俗通》《乾宁记》等。《吉林外纪》引《述异记》《本草经疏》《本草纲目》《临海志》《管子》《博物志》等。《岫岩州乡土志》引《酉阳杂俎》《运斗枢》《春秋说题辞》《后燕录》等。《义州乡土志》引《山海经》《农书》《说文义证》等。涉及经书、农书、字书、正史、方志、文集、类书、笔记等各类历史文献,既有先秦古书,也有本朝著述,既有官修方志,也有私人笔记,既有诗词歌赋,也有民谚俗语,引书浩繁。如《(康熙)盛京通志》所言“著其方言,区其种类,以俟博物者详考云。”〔24〕《物产志》编纂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典籍,将有价值的资料汇集于此,以考证辨析物产的名称、种类,并对其习性、特征及相关典故作以补充说明。《物产志》可以作为衡量古人自然知识水平和博物观念的一面镜子。
(二)清末实用思想的勃兴
清末方志编修者充分认识到物产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南金乡土志》载“有物产而人始生活”〔25〕。《长白汇征录》载“竭天地自然之利,储国家于不涸之源。”〔26〕《承德县志书》载“物产之盛衰可以觇国计民生之贫富,知物产之于地方尤关重且要也。”〔27〕
《绥中县乡土志·物产》小序载:
物产,社会上之要素也。凡地理学、实业学家,罔不以物产为研究之一大宗。乃中国儒者,以门户相高,以书痴相尚。以研究物理、调查生产为鄙俚行,竟不语田野物,不知草木、鸟兽之名。若是者,只知有朝廷历史,而不知有社会历史。赋税者,物产之子息也;物产者,赋税之元素也。赋税为朝廷历史,而物产即为社会历史。故无论飞、潜、动、植,皆宜研究其性情,考察其体用。〔28〕
物产不只是地方对朝廷的贡赋,更是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物产志》也不只是博物之书,应详考其“体”与“用”,为实业家和学者参考和研究资料。
“物产”在此前志书中主要指天然出产,清末《物产志》中将人工制造品同样视为物产,并加以区分。反映出人们从单纯向自然索取生产生活资料,到重视加工自然资源制作产品,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表现。如《(光绪)开原县志》载“旧志纪物产而不详慎天然、人工之别,于人为进化之理殊背。兹特区以别焉,使人之用物不知患穷,而患不能造。”〔29〕《呼兰府志·物产略》有“工业品”“商业品”二类,言:“食肉寝皮,不解制作,我以为生货而贱鬻于人,人制为精器而贵售于我,利权外溢,滋可惜也。”〔30〕均强调本国制造品之重要。《昌图府志》未设《物产志》,直接在《实业志》下记当地谷类、植物、畜牧、禽兽鳞豸,作为发展实业的利用之资。
“物产”在此前志书中主要指动植物,对矿物的记述比较少,矿物原本放在“货之属”下,或如《吉林通志》和乾隆四十九年本《钦定盛京通志》置于“宝藏”下,总之将之视作财物。清末志书突出矿物的地位,看到了矿产资源对工业发展的重要性,为进一步开发矿产资源提供指南。如《(光绪)宁远州志》《抚顺县志略》《呼兰府志》《安图县志》《辉南厅志》均有矿物一类,体现出指导地方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目的。
清末乡土志与府州县志在体例与内容的变化趋势上是一致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学部颁布《乡土志例目》,载“物产:分天然产、制造产二端,动物、植物、矿物是也。……均应分大宗、常产、特产而注记之。又有本境之天然而在他境制造者,或他境之天然而在本境制造者,尤应分别详载。”〔31〕清末东北乡土志基本都遵循此体例,突出了人工制造品、矿物和特产的地位。如《新民府乡土志》载“寻常之品物又不胜毛举,兹就动、植、矿三物之重要及可为制造品之原料者,列表于左。”〔32〕《辽阳乡土志》天然产中有蚕桑、林业、矿产,制造产列表展示出其工厂、岁额、销场、原料。《(光绪)海城县乡土志》“动物制造”后附蚕业和渔业,“植物制造”后附柞树栽培法、木炭制造法。着重记述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价值的物产、植物栽培技术和矿物利用方式以及近代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清末方志物产志更加注重记录用途,“用”与“实业”是出现的高频词汇,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晚清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经世学风再度兴起,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成为国人的奋斗目标,因此各类文献中有关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内容大为增加。二是晚清随关内百姓大量涌入,东北土地开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开启经济近代化进程,形成了近代产业。从而使《物产志》由传统博物学式的资料汇编,转向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用性指南。
三、《物产志》的知识内涵——从经验趋向科学
传统方志物产志中对物产的介绍,不论其形貌、习性还是用途,大都源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观察和经验的总结。随着晚清西方科学技术的到来,人们开始用科学的眼光看待自然环境,自觉地将生物学研究成果呈现在《物产志》之中,以资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
(一)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
光绪末以前编修的方志物产志,虽也记录了不少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的知识,但大多属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康熙)辽阳州志》小序载“谷以养民,菜实佐之,木作器用,药以疗疾。山珍水错,货财所殖,皆以资民用也。至花草亦地气之秀丽,足供文人吟咏,可或阙欤?”〔33〕记录物产的顺序大都按先植物后动物、与人的生活关系密切程度排列。
与记人文知识不同,记自然知识更强调实地考察。《吉林通志》标明哪些知识由采访获得,如记大豆,“又小白豆,丛生,子赤色,和蜀黍炊饭极佳(《采访册》)。”〔34〕部分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借鉴农书的体例,如《吉林通志》载“今略仿《南方草木状》之例,称名辨物,别性类情,无取泛滥,亦不敢失之荒陋。”〔35〕因古代方志除名志外,其他一般只在本地流传,以资地方官员治理地方。《塔子沟纪略》载,“汇而载之,亦以广耳目、充识见云尔。”〔36〕士人阅读《物产志》又多是为了增长见闻,故而缺乏进行科学研究的动因。
记物产用途,有作饲料或肥料之用,如《辽中县志》记苏油,“油箍可喂牲畜,亦制作肥料上地。”〔37〕有人们衣食住行之用,如《长寿县乡土志》载“小豆,古谓之苔著,有绿,赤、白三种,可煮可炊,可粥饭,可作(做)面食馅。色赤粒小者入药,县境居民以小豆合米煮饭,磨粉为蔬。”〔38〕《吉林外纪》载“有以桦皮作船”“又以桦皮盖窝棚”〔39〕。皆日常使用经验的总结。
记动植物生长之习性,如《锦县乡土志》记蟹,“出海中,逢立夏至小满多而且美,逾时则不见矣。”〔40〕《承德县志书》记草,“此细微之物,亦足见气候之寒暖、地脉之肥瘠焉。”〔41〕清末以前方志物产志对动植物的记载,只是通过生产生活中的观察和利用而形成经验性的知识,甚少深入研究。有些认识还具有盲目性,如《锦西厅乡土志》记喷云虎,“尝于晴时吐气如云,顷刻上升甘霖下降,农人以为占雨之验。”〔42〕对昆虫的记述带有传奇色彩。
(二)清末科学知识的萌生
清末东三省大规模丈放官荒,设立了一批实业机构、试验研究机构,从事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试验、推广工作。而方志编纂人员又有不少为新式学堂学生,催生了方志物产志中的科学知识。
从分类中清晰可见西方生物学知识对清末方志编修的影响。如《海城县乡土志》动物分脊椎动物和节足动物,脊椎动物下分哺乳类、鸟类、鱼类,节足动物下分甲壳类、昆虫类、多足类。《靖安县志》“土性”与“物产”合为一门,“土性”一词本身就是晚清西方传入中国的科学名词,看到了土性对物产生长的重要意义。《(光绪)开原县志》载:“是书之纪疆域则地理也,纪人事则历史也,纪物产则格致也。”〔43〕物产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
清末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使传统志书中关于物产的不经记载得到更正,科学知识日益增多,反映出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水平显著提高。如《昌图府志》载,“近世物理学东来,精于格致之家类,能察众卉原质以显其功用。”〔44〕开始运用科学知识对植物进行研究。《长白汇征录》载:“白山一带产虎为多,据日本调查谓与孟加拉(国)地方之虎同种。”〔45〕此借鉴外国研究成果。
光绪三十年(1904)“癸卯学制”实行后,“格致”是初等小学堂所教授的八个科目中的一个。“格致要义在使知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大略形象质性,并各物与人之关系,以备有益日用生计之用。”〔46〕乡土志作为小学教科书,更注意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授,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如《彰武县乡土志》载:“边外地气较寒,不宜养蚕,且系平原沙漠,亦无虎豹等物。”〔47〕认识到气候、土壤对动物生长的影响。《海城县乡土志》记蚊,“产卵水中,其幼虫为孑孓(倒跂虫),夏令人饮凉水入腹,若有此虫,能传染病之媒介。”通过对虫类、鼠类的记录,预防疾病传播。〔48〕记鸠,“达尔文养鸠研究,其种变以主淘汰说。”〔49〕这说明鸠由于人的饲养,而出现鸽的变种。达尔文物种进化论给清末中国知识界以极大震动,促使人们以“进化观”来认识生物,进而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
四、《物产志》的知识建构——从首崇满洲趋向爱国爱乡
教化是方志的基本功能之一,清末以前教化是围绕维护本朝统治展开的,官修方志是传达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工具。清末方志着意培养百姓的乡土之情,进而由爱乡而爱国。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方志物产的知识建构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指向。
(一)巩固满洲统治
在清代,东北地区具有崇高的地位。因东北是清朝统治阶层——满洲贵族的发祥地,被清朝统治者视为“根本之地”。除了地方行政制度与内地不同,还以限制资源开发的方式垄断东北经济利益,阻碍关内百姓出关。对于珍贵自然资源,除非官府发给凭证,否则不允许民人私采,而由盛京内务府、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组织旗丁统一采集,或由边疆各部落进贡,供王公贵族、八旗驻兵和官府衙门享用。这在《物产志》中均有明确标注。如《(康熙)盛京通志》记银,“今为我国家发祥重地,不复采取,以护元气也。”〔50〕《岫岩志略》记硝磺,“岫岩城守尉衙门,遣员前往巡查以防偷采。”〔51〕《吉林外纪》记东珠,“每年乌拉总管分别派官兵,乘船裹粮,溯流寻采。”〔52〕《吉林通志》“土贡”独立于“物产”之外,形成一个三级类目。凡须进贡的特产,在志书中往往都有标注,如《墨尔根志》记野猪“每年捕之入贡。”〔53〕
进贡的土特产一为饮食之用,一为穿戴日用。满人对东北的珍珠、毛皮、野味情有独钟,“国朝品官坐褥冬用皮,有定制:一品用狼,二品用獾,三品用貉,四品用山羊,五品以下用白羊皮。公、侯极品用虎豹皮。”〔54〕物产象征王朝的等级制度,也象征着满人的生活方式与习俗。如果将满洲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那么《物产志》中所记录的满洲贵族对东北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索取和利用,则体现出鲜明的满洲物质文化特征。
在清代东北方志物产志的书写模式中,东北物产的丰饶归功于清朝统治的昌明和龙兴之地“风土之厚”。如《(康熙)开原县志》载:“今开原为圣天子发祥之地,其珍异所出,草木禽鱼皆应运而兴以资用。”〔55〕《奉化县志》载:“钦维列圣缔造经营,仁风远被,茂对时育,迈隆古焉。故奉化荒寒边徼,本貊地也。古者唯黍生之,今则五谷殖、庶类蕃矣。”〔56〕不仅是官修志书,私修志书也流露出对本朝统治的颂扬,如励宗万《盛京景物辑要·物产》按语:“谨别芸生,并详品性,庶见圣朝位育之隆,王基风土之厚,且以备博物之一端云”〔57〕。将自然物产与政治统治相关联,作为证明满洲统治合法性、合理性的一种政治文化策略。
此外,清帝东巡途中作了不少歌咏东北风物的诗篇,在志书中附注于相应物产之后,在《盛京通志》和《吉林通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钦定盛京通志》记人参:“乾隆十九年有《御制人参诗》,四十三年有《御制盛京土产诗》三曰《人参》。俱恭载《天章门》。”〔58〕本来该诗已经收录于《天章》一门,又标记于此,同样也是方志编纂中强化满洲认同的体现。
(二)清末的爱国爱乡情感
鸦片战争后,中国不再是想象中“天下”的中心,国人的国家观念开始由王朝国家转变为近代主权国家。近代的地方意识是国家意识的产物,“对地方志的书写,就是对‘国家’如何在‘地方’存在的历史的叙述。”〔59〕随着晚清知识分子“国家”观念的觉醒,地方乡土意识也得到强化。如《辽阳乡土志》载,“乡且不爱,何有于国。欲知爱乡,必先使人知此乡之历史沿革,及往事现势之经营缔造,人事天产皆足宾爱。”〔60〕爱国始于爱乡,而爱乡的前提是知乡,不但知晓人事,还要了解物产。通过介绍地方丰富的物产来传播爱乡观念。《(光绪)开原县志》载,“务求合于鼓吹人民爱国进化之利器为目的。”〔61〕志书编修的目的即为激起爱国之心。
晚清列强侵华,东北饱受俄、日等国的侵害,大量资源被掠夺。如《东平县乡土志》载,“牛自乙巳年日俄构兵,俄人入境,搜食殆尽,现间有之。”〔62〕《抚顺县志略》载,“千金寨、杨柏堡、老古台煤矿,日人采运,获利独厚……财源外溢不能遏止,恨国势之太弱,誓来轸之方长,当思所以挽回之策而为自强之基也。”〔63〕《物产志》中记录自然资源被侵略者掠夺的情况,意在激发地方百姓爱国爱乡意识,以图自立自强。
结 语
在思想意识层面揭示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是十分有意义的学术课题。方志物产志对于区域环境史、经济史、农史、生物史、医疗史、饮食史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样也可以将之视作知识载体,从知识史角度出发,考察不同时代知识分子对自然环境认识的变化,以及所反映出的社会变迁。本文从方志物产志的编纂角度考察清末知识分子在知识认知、知识内涵、知识建构方面的变化和转型。此外,还可以从目录书、丛书、类书、政书、农书、荒政书、近代教科书等其他类型历史文献入手,将文献学、知识史和其他相关学科相结合,考察编纂者对自然的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另外,近年来书籍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从书籍的流通与阅读角度考察自然环境知识的传播与接受,也有较大的探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