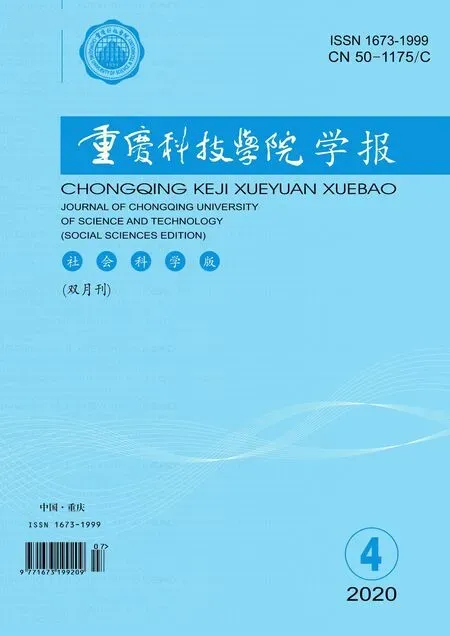愁思与悲情
——论李清照词中的听觉叙述艺术
张静若
人们解读古代诗词的时候,很容易将视觉意象与情感体验联系在一起,却往往忽视了体验世界的另一种感官媒介——听觉。听觉也是把握和感知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马克思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其实,听觉在诗词创作的时候,更会触发深层次的情感体验,李清照的诗词就有许多关于听觉感知的描写。本文通过研究李清照在不同创作阶段围绕“愁思”与“悲情”所用的不同声音意象与听觉叙述手法,窥探“声音-听觉”在古代诗词创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展现她的听觉叙事艺术。
一、词中听愁声:声律与词的融合
李清照在《词论》里认为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清浊轻重[2]。她对于词的语言极具敏锐的辨析力,一方面是对于当时宋代流行词体音乐的深刻理解与个性化的阐释,另一个方面是对于词的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节奏和音律高度敏感。李清照注重词的文学性与声韵之间的融合,在她看来,词是音乐文学,需要做到声与词、曲与词等和谐结合,才能保证词的艺术魅力。听觉这类特殊的情感经验在词中需要转换成感官性的语言,声音词语在李清照的词中承载的情感大多是浓浓的愁思与悲情。
李清照的词体现了声律与词的融合,解决了当时新内容与旧形式的传统表现手法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经历了由北到南的历史变革后,词与音乐更是难以结合在一起。人们评价她“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以寻常语度人音律”。首先,她词中的词语是脱出观念性束缚的感性显现,并且节奏符合音乐。如《声声慢·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用7组叠字奠定了全词的基调。既描写了作者在经历了许多波折后,因若有所失而到处寻觅的一种精神恍惚状态,又真实地表达了她寄身异地、无人为伴、孤独寂寞的处境。其中叠字的平仄抑扬之变化,使得字与词具有强烈的节奏感,而节奏是音乐动态结构的体现,也是词体善感的又一个重要的艺术结构要素[3]228。
其次,李清照的词中声音描写与情感表达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是“显性的声音”无不使人闻声起意,如《行香子·天与秋光》:“闻砧声捣,蛩声细,漏声长”;《菩萨蛮·归鸿声断残云碧》:“归鸿声断残云碧”等。声音词语沟通了客观事物与主题之间的联系,从而更能凸显出声音的“在场性”。另一方面是“隐性的声音”,是指声音的隐含,如《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在词中缓缓地道出主人公划船时力量之大,声音之响,惊起了滩上的鸥鹭,从而体现出活泼灵动的听觉之态。
再次,李清照词作中的“愁声”也间接地影响了意境的呈现方式。因为声音所营造出的意境延伸了词的动态多维空间性,打破了词的静态之感,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不断发出动态的声音景观。如《好事近·风定落花深》:“魂梦不堪幽怨,更一声啼鴂。”写风定花落之后,落红堆似雪一般,醒目的红白相映之境,虽落英满院,可甚为凄美。在叹息花事将了之时,又忆酒阑人散,青灯孤影,魂梦幽怨,一片凄凉溢出景外,静态的景物被一声鴂啼唤醒。似水年华安静地逝去,却无法带走一位老人无穷无尽的愁思与悲情,将自然的静态画面化为连续不断的动态愁思,动静之中这一声鴂啼拓展了词的纵深度,并延伸了词的空间。词中的愁思化为时空中读者与作者的共同愁思,使得愁思在共鸣之中开始,又留下不断令人回味的动态声音。
最后,李清照词境的声音描写具有一定的基调性。这种声音被傅修延称为“主调音”,它确定起整幅音景的调性,形象地说,它支撑起或勾勒出整个音响背景的基本轮廓[4]。李清照词中的声音有寄托愁思的雨声,蕴含凄凉的啼鸣之声,羌笛与箫声更是点明并渲染了浓厚的悲凉情感,如“忍一声羌笛”“伤心枕上三更雨”“草际鸣蛩,惊落梧桐”等,看似简单的声音背后却交织着多重意蕴与独特的韵味。同时,通过景物的声音衬托出作者的主体存在,特别是能够凸显出作者在“听”的过程中所融入的情感,例如,“坐上客来,尊前酒满。歌声共、水流云断。”“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他人的嘹亮歌声和欢声笑语与作者内心的冷清孤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显作者之孤独。而“无我之境”则是景与情的彼此交融,不论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还是“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景与情无不展现出浓浓的愁思与悲情。
二、拟声知愁意:声音与时空意识
李清照的词作被称为“皆以寻常语言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妙者难”。她的词中不仅多见叠字与对偶的运用,丰富了词的音韵,还将口头语化为神奇,用平淡口语书写内心真挚的情感。她的叠字不乏对声音的模拟,拟声多是不断的愁绪,稀见轻松活泼的词作。颠沛流离的人生际遇让她拥有了年少时的闲愁、婚后的离愁和南渡后的哀愁。
李清照词作的拟声多见拟雨之声,雨的意象从《诗经》开始就奠定了离别愁绪的原型。李清照在写雨的词作中塑造了人物孤独的形象,模拟雨声之态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滴嗒”的雨声。说明了此时的雨声比较小,例如,“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凄清。”“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反复的“滴嗒”到“嗒滴”的雨声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时空间距,产生了时间的延宕性,使得声音置于时间之中。在诗歌中,时间以一种流动的、暗示的方式展露出来,它弥漫于诗歌的字里行间[5]。作者的愁思置于时间流逝的无奈之中,“滴嗒”的雨声展示了绵延无尽的愁绪。这种审美想像,伴随着对过去年华的追忆,使自己清醒地意识到当下的处境,更加产生失落感和悲戚的情绪。不仅强化了声音的时间艺术,更延伸到对空间之“远”的艺术感知,给人一种令人可以反复咀嚼的审美韵味。
其次是“潇潇”的雨声。当雨声渐大时,风和雨融为一体,例如,“小风疏雨潇潇地,又催下千行泪。”“恨潇潇、无情风雨。”“潇潇微雨闻孤馆。”此时的雨声是“潇潇”之声并伴随着不同的风,可见风雨交加的天气更多生寒意之感。这里的雨声不再是“滴嗒”之声,给人以静态的思考,而是伴随雨声的逐渐增大,覆盖了词中之人的听觉感知。声音在此时占据了感官的主导地位,无形中影响了听者的心境,在一定的空间场景内产生了共鸣。正如“泪水”是词中之人听雨声之时内心情感的外化,“恨意”则是听雨声后“愁意”的升华。罗兰巴特认为,对于空间的听觉占有从古至今都有[4],从声音中可以辨别“熟悉”或者“不熟悉”的空间。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词作里对雨声的描绘和体验,其实是一个空间感知的过程,词人通过自身全方位和立体化的空间性体验,将雨声描绘出来。海德格尔说:“此在通过‘去远’的方式将世内存在者带到近旁,从而使自己获得空间性。”[6]因为文本不同于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声音传达,它是间接地呈现出声音,需要结合相应固定的声音意象才可以塑造出一定的听觉空间。同时,读者处于由文本所塑造的声音空间,读者一边“聆听着”已经形成的听觉空间,一边结合自身的经验对文本所塑造的听觉空间进行再创造,并创造出赋有个人经验的听觉空间。所以“潇潇”雨声形成的听觉空间,既是人们所“熟悉”的普通的听觉空间,又是“不熟悉”的特殊的听觉空间,从“潇潇”的雨声之中,创造出属于独特听觉的审美空间。
最后是雨声与其他意象的组合。如雨声和梧桐的组合:“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雨声和芭蕉的组合:“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还有雨声和梨花的组合:“雨打梨花深闭门。”在这些意象的叠加组合之中,是声音与意象的融合,更添其中的愁意。一方面,词人赋予自然景物以人性化的特征,并和自然景物形成一种“对话”关系,意象之间组合后产生的声音在使用了一定的艺术手法后,不仅使人产生了动态之感,更形成了属于自然界独特的音乐。声音是属于大自然更为高级意义的语言,自然本身就构成合目的性的审美对象,声音就成为欣赏和了解大自然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雨声和芭蕉、梧桐的意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音乐之感。这种音乐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音乐,是利用文字的一些要素,比如韵律、重复、语调、节奏等,美化其声响效果。这种间接的音乐之感让文字的表意性和音乐的表音性结合起来,间接地产生音乐上节奏韵律的乐感,在人们的脑海中产生诸如旋律、节奏、和声的效果。苏珊·朗格认为:“我们叫作‘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情感形式——增强与减弱,流动与休止……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7]人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声音的世界,音乐则是从古至今都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从人体的脉搏和心跳、肌肉的紧张和松弛,到自然界的鸟语花香、电闪雷鸣……一种声音往往会激起人的某种心理的波澜,从而附上某种认知、情感、想像、意志等方面的内涵[8]。
三、视听浑融之中的悲情
柏拉图认为:“美只起于视觉和听觉所产生的快感。”[9]黑格尔说:“艺术的感性事物只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觉,至于嗅觉、味觉和触觉则完全与艺术欣赏无关。”[10]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听觉是可以和视觉之间相互联系的。朱光潜在评论英国诗人史文朋和法国的象征派诗人时认为,这类诗人想要把声音抬到主要的地位,甚至有一部分象征派诗人有“着色的听觉”,并把这种现象称为“感通说”,以为自然界现象如声色嗅觉等之间其实是可以相互感通的,是可以互相象征的。当视觉和听觉感官互通,可以使得词本身超越了文本本身,所构造出的意境具有浑融之感。同时,以通感手法写词,也可以调动听者的感官以及感官之间互通的能力。因为通感互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对象的完整性,具有心凝形释、浑然无彼此的效果[3]258。朱光潜的论述正好符合李清照提出的诗歌形象的完整性,体现一种浑然一体的美学旨趣[3]210。李清照使词作里的愁意上升为悲情,这是由于词人本身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在南渡社会变乱的世事影响之下,逐渐从自身转向社会离乱为主的感受。其中个人的忧患意识强化为忧时、忧世与自我情感相结合,如《题八咏楼》:“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李清照在词作中塑造了孤独的人物形象,这也成为她承载自身悲情愁绪的形象载体之一。如《武陵春·春晚》:“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词人将无法言说的愁情化为可以承载的厚重,给人以形象化的深沉与悲凉。
李清照词作中的视觉词语和听觉感知之间的描写可以分为“视听相融”“以听感视”这两类,都可以使得词作中的意境韵味余长,词作之中蕴含的悲情更显其深,而且能够在文本中找寻属于“听觉的诗意性”,让读者置身于听觉诗意之下,感受到视觉和听觉融合所带来的审美直观与审美想像的魅力。在她的词作之中,视觉画面的直接描写和听觉相互融合,用各类声音词汇或是听觉与丰富形象的视觉直观词汇相结合,以强化视听相融的感官效果。视觉上的直观词汇如“帘”“归鸿”“碧云”“落雪”等,与词作中的具有听觉特质的“语”和“声”结合在一起,这些词汇将视听融为一幅具体场景的画面。而人与物都偏向于“实”的展现,视听艺术形象彼此直接和具体地表现为作者内心的悲情作铺垫,例如,“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归鸿声断残云碧,背窗雪落炉烟直。”“魂梦不堪幽怨,更一声啼鴂。”在这些词作里,词人既追忆他日年华与今日之凄楚,又道出对故国亲人的思念。他人的欢声笑语之景与自我的孤独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词人还运用了视觉上色彩词“碧”“金”“红”等,这些词属于偏向鲜明的暖色给人以欢快之感,而听觉“归鸿声”“鴂啼声”“雨声”等赋予了它们凄凉与愁思的内涵,给人以悲凉之感,视觉和听觉词语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视听相融”不仅仅是把视觉和听觉融合在一起,更是通过视听不同感官之间的对比将词人内心细腻感性的情感体验传递出来。“以听感视”是通过声音的描写间接地来想像视觉的画面,具有“虚”的表现特征,这种审美想像活动通过一定的艺术形象间接地展现了视觉上比较具体形象的画面。如《忆秦娥·咏桐》:“烟光薄,栖鸦归后,暮天闻角。”随着乌鸦返巢,鸦声逐渐地消逝,又隐隐传来了军营的号角声,词作者注入了社会和政治的意象。这样的延伸意象,有助于解释词里的不断持续悲伤愁苦之情[11],使得读者想像秋季的萧瑟与戍守边疆军旅生活的艰辛,这是读者对具体声音的场景再想像。又如《南歌子·天上星河转》:“凉生枕簟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通过渲染环境氛围继而写词人起身解下罗衣且问当下时辰,塑造了主人公夜不能寐,孤身一人的形象。这里的“聊问”可以解读为主人公的心理估量,这是词人心中的声音。另外,如:“玉钩金锁,管是客来唦。”“起来敛衣坐,掩耳厌喧哗。”这两句都是写他人之声与自我境遇,以他人声音的嘈杂与喧哗衬托自我内心的孤寂,看似听声,其实是听人。这是对词作背后隐藏的作者形象与时代背景之间的想像。
李清照在词作里极为重视身体感官的运用,除了听觉和视觉的描写,还出现了触觉、嗅觉等,例如,“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朱光潜认为,诗的境界是用“直觉”呈现出来的,它是“直觉的知”的内容而不是“名理的知”的内容[12]。注重身体感官的运用,标志着李清照词作的艺术感觉走向细腻,也展现了词人的独特感性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