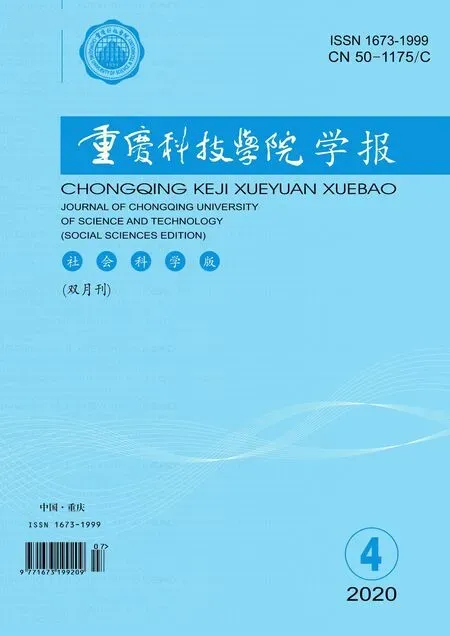土家族诗坛上的“歌者”
——论冉庄的诗歌创作
乔军豫
土家族诗坛是一座芳香迷人的百花园,五彩缤纷,争奇斗艳,如花满春山,形成了一派蓬勃发展的势头。土家族诗人们在运用民族、民间文学形式创作时,抓住民族生活、民族风情、民族家园等方面的表现题材,抒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给重庆乃至全国诗歌界增添了奇光异彩。他们领会少数民族的地域审美观念和文化精髓,依托于美丽的河山和人文景观,播撒诗歌种子,在民族的诗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土家族诗人的星空中,冉庄是较亮的一颗,与所处的同时代诗人一样,顺应时代浪潮,关心社会现实和人民大众的生活,继承本民族的诗歌传统又有所拓新。语体新颖,且采纳民族化、群众化的大众语言入诗,坚持民族化和群众化。深受20世纪50年代诗歌理论的影响,其诗反映了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步伐,倾听人民心声,投入生活潜心创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诗人遵循这样的原则:“诗歌要忠于时代和人民,诗歌要反映人民的心声,要讴歌时代的主旋律”[1],自觉倾向诗歌的大众化、民族化,努力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为自己的诗歌创作定位。
一、土家“歌者”
出身土家族的冉庄创作题材多样,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其中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斐然。著有诗集《唱高调的黑母鸡》《泼水梦》《沿着三峡走》《山河恋》《山海心曲》《与云为伴》《冉庄诗选》等。这些诗歌展示了诗人的创作整体概貌和诗路历程,对民族地域风光的歌唱,对生活情怀的真诚流露,是他创作内容的主要方面。诗集出版后反响较大,获得晓雪、钱光培、张同吾、吉狄马加、朱先树、潘颂德、查干、尹在琴、刘扬烈、万龙生等人的好评。《文艺报》《民族文学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文学》等20余家报刊都载有对冉庄的诗评。杨四平的研究专论《交点上的艺术》对冉庄的诗歌进行了详细的述评。随着创作风格的成熟,冉庄的诗歌也得到了诗歌史的认可,吕进在《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中对他的诗歌作出了较高的评价。
冉庄出生于贫困之家,因一场民族部落纷争不得不远离酉阳亡命他乡,用箩筐挑着坎坷的命运躲避到重庆,开始了风雨飘摇的生活。在那种家庭的境遇下,冉庄从小吃尽了苦头。他没有抱怨和嗟叹命运的不公,相反,他在极端贫乏的物质生活和生存困境中寻找着诗意,发掘着蕴藏诗的富矿。看来,早年的不幸铸造了他的诗魂,成为诗人后来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精神资源。冉庄自1956年发表第一首诗以来,便长期扎根于生养他的土地,深入社会生活,努力探索诗歌民族传统与现代转换问题,他的诗鲜明地体现了巴蜀文化的精髓和独特的地域观念。
每一个民族都有只属于它自己的本质特点,这种特点在诗歌创作中的反映,就是诗歌的民族特色。它集中反映了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特有的历史文化氛围以及特定的民族情感、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诗人,冉庄通过异彩纷呈的民族生活,特有的民族韵味,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质的作品。冉庄的诗具有显著的民族特点,反映了本民族的精神风貌、性格特征以及心理状态。
诗人冉庄是民族文化的代言人,拥有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立足本土,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突破以往少数民族诗歌在中国文学大格局中处于弱势、边缘的状态。从冉庄的诗歌里可以看出,他在创作时不仅了解和掌握民族的自然环境与地域风光,而且熟知民族的风土人情、乡间习俗、民族信仰等精神文化内涵,善于从民族的细微生活中看出其精神面貌。例如,民族的节庆、婚嫁、丧葬、祭祀等常常纳入诗人艺术观照的视野,成为诗歌取得民族性与地域性的重要依托。
二、山水情缘
冉庄给全国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冉庄诗选》曾获得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描绘、歌咏大西南的山水与民族风情,是冉庄诗歌的主要内容。他的足迹踏遍西南的山山水水,以迥异于我们常人的目光打量村落山寨的风物,体验土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聚集地的生活,感悟大自然的美妙与壮观。他一路行吟歌咏,奏响柔婉和谐的琴弦,弹出赏心悦耳的乐音。
沿着三峡走,/两岸景色秀:/秋风染红叶,/金橘满枝头,/站在船头望,/颂歌飞出口。/啊,美丽的峡江,/日夜在我心上流。//沿着三峡走,/如在画中游:/白帝笑颜开,/神女挥彩袖,/长虹从天降,/江天铺星斗。/啊,雄伟的峡江,/日夜在我心上流。
三峡是诗之峡,是一片诗的沃土。三峡地处西南边陲,森林茂密,河流纵横,多民族杂居,各民族历史文化汇融与交流,形成了它绚丽多姿的文化景观。冉庄表面上在写三峡的景色风光,实际上在礼赞这个地区的民族风情。三峡是少数民族的家园,这里居住着多个民族,它们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彼此了解对方的心理和性格,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他们共同劳动创造着美好幸福的生活。诗人从三峡的雄奇、秀丽的静态美到“观之以心”“日夜在我心上流”的动态美,主客交融,视角与时空交错,避免了单一感,诗情画意令人心折。三峡大地是诗人冉庄文化生命的母亲,在这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之根,确立了他诗歌创作的姿态和内容。
纵观冉庄的诗歌创作,山水诗占了绝大部分。“寄情山水自然是冉庄诗歌的特点。”[2]《黄山吟》:“踏遍长江山和水,/惟觉黄山美;/深潭流泉淌,/峭壁苍松翠,/云海浩瀚,/雁绕山飞。”诗人以景观物,把自我隐藏到景后,“无我之境”变得更加清丽和纯粹。《澜沧江》:“画廊悠长悠长,/凤尾竹与油棕树,/簇拥着傣家楼房。//落日余晖,/从云隙撒下,/道道光亮。//卜哨赶摆归,/拖一片彩霞,/洒一路芳香。//姑娘挽筒裙,/孔雀飞入江,/澜沧江翻起喧腾声浪。//醉了山,醉了树,/晚霞悄悄,/偷望迷人的澜沧江。”诗人用通感的手法来描写迷人的澜沧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绝壁苍松》:“侧着身子,/向着太阳,/攀着悬崖,/扎根石缝,/满脸微笑,/迎着春风。//雨淋日曝,/冰雪融融,/从不低头俯身,/从不随风西东,/不管风吹雨打,/依然坚定不动。”诗人以景抒情,“一切景语皆情语。”苍松面对恶劣的环境“依然坚定不动”,喻示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和从容淡定的性格,也象征了诗人自己。
山宁静而水跃动,山高耸而水长流,山崇高而水秀美,山神秘而水亲近,山永恒而水易逝。所以,山与水构成了静与动、高与长、庄严与灵秀、神秘与亲近、永恒与易逝的交响乐,在这个交响中,山是为主的,水是为附的。诗人从这交响乐里获得无尽的诗意。冉庄挥情山水,心扉洞开,诗意汩汩而来。时时同山水对话,把心付与自然,有返璞归真之意。诗人写山水之美,重视人在山水之间的活动,审美指向人的活动之美。如《三峡黎明》中诗人精心描绘了一幅多彩多姿的三峡黎明图,赞美了“航运姑娘”“岸边小伙”的辛勤劳动和心灵之美。
西南的山水与诗人冉庄结下了不解之缘,山水是他逃离滚滚红尘的绝好去处。他在《山水情缘》里写道:“数十年过去了,我对山水之情依然如初。然而我对山水的体会却随着年岁上增而渐变:年轻时,只肤浅地知道在山水之间有情感变化;中年时,只陶醉于山水灵性的审美抒发;年岁渐老,心境才渐渐融入山水自然,与之同化,与之合一。”诗人钟情于山水,山水的灵气慰藉着他的心灵,山水的灵性是他写不尽、述不完的主题。
冉庄迷恋于山水,他在《山水情缘》中说:“我只想写出山的灵性,事物的表里,人的本性与真情,从而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喷薄的日出,奇峭的山崖,奔腾的江流,烂漫的春花,恬静的原野,使之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去追溯消失的自我。”诗人专注于山水不是简单地欣赏把玩,而是给疲惫的身心寻找一个“栖息地”,给自己的诗歌寻找一个创作的突破口,在山水里追求一种体验颇深不好言说而又必须言说的存在。他的山水诗高扬着生命意识、个体意识与时代意识,流淌着山水的乐趣和艺术的潮汐,达到物我交融、物我偕忘的意境。
冉庄的山水诗诗情盎然,画意甚浓。“诗中有画”是我国古代诗人一直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也是我国诗歌的宝贵传统之一。他继承和发扬诗歌这一优秀的传统,写诗如布景一样,每一首诗堪称一幅画。诗的色彩,大多清淡,但淡而有致,有山水的神韵,有山水的光泽。他的山水诗所具有的艺术元素还表现在其对音乐的借鉴上,不仅讲究有情绪的消长起伏引起的内在韵律,而且讲究语言的节奏、押韵和句式的排列。
吉狄马加说:“冉庄在创作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美,追求明朗清新的风格,诗作大多简洁而富有韵律,注重语言锤炼,而在随手可见的化用古典诗词和考究的对仗、排比中,能够深切地感到传统文化在诗人身上的薪火相传。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积淀,使他的作品充满了凝重之思、质朴之情、古典之美,从而显示出独树一帜的诗歌品质。”[3]冉庄的山水诗是对中国古代山水诗的继承和超越。我们应充分认识他的山水诗的价值,本真、超脱、无功利性的品格在我们世俗的环境中因稀有而珍贵。
三、民族情怀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习俗,在诗人冉庄的笔下,勾勒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民族风俗画和风景画。如《泼水梦》:
是天上雨/飞洒长空;/是人间情,/把我心拨动。/半城欢笑,/半城雨,/来到允景洪,/半醒半是梦。/孔雀湖畔,/青草坪中,/水蒙蒙,/雾蒙蒙,/半似月牙半似弓,/半如彩带半如虹……
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是傣族重大的节日。民族的狂欢,水当然成了最主要的符号和共情元素。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水,水是圣水、福水、吉祥水,泼得越多越有福,泼得越猛越有福。这种民族的狂欢意识能使人们在激情兴奋中感受到水给予的生命力量,体验到水对于民族生存、民族壮大、民族生活建构的重要性。这首诗汲取古典诗词的养分和民歌精华,注重意象的营造,语言精工,使用对仗、排比、比喻等修辞方式,把泼水节欢快、热闹的场面展现得生动活泼、淋漓尽致。
阅读和检索冉庄的诗歌,民族气息迎面扑来,那些写土家族、傣族、苗族、白族、布依族、彝族、藏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的诗歌,一一展现在眼前,顿感浓浓的诗意中蓄积着深厚的民族情愫。
冉庄以高远的眼光和宏大的民族视野进行诗歌创作,他的诗里有民族的情结,有民族的气质,有民族的魂魄。如《鸭江山寨》表现了布依族人民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金银岗》《金梭飞》赞美了苗族人民勤劳、勇敢、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些民族诗尽显少数民族地区所特有的风光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精气神。诗歌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让人过目不忘。泼水节上的少男少女,风华正茂;凤尾竹前的傣族姑娘,光彩夺人;蝴蝶泉边的白族小伙,能歌善舞;花溪湖边的苗族黛帕,笑语朗朗……民族风情尽收眼底。
冉庄歌颂民族团结和民族之间深情厚谊的诗,总能打动和鼓舞人心。“一首溜溜的情歌,/唱红了一座山,/唱红了一座城。/唱得大哥大姐,/情真意切,/相依为命。//唱得汉藏同胞,/和睦团结,/谊长情深。”(《听〈康定情歌〉》)诗维系着人间爱,连接着民族情,是民族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少数民族之间亲密交往,四海为一家,其乐融融,读来让我们感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睦和温暖。
冉庄虽长期居家重庆,但对自己的故乡酉阳充满无限的深情和眷恋。土家族人民乐观开朗、热情好客、重情仗义等性格特征也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在他的思乡诗中,那魂牵梦绕的山寨,那敦朴厚道的乡风,那血肉相通的乡亲,那熟悉亲切的乡音,那割舍不断的乡情,那形影如随的乡恋,格调颇似“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送友人》),处处动人心弦。“寻根人乌江,/一路热泪横”“到了故乡恋亲人”“大妈拉我手,/认我同宗人;/溪边浣衣女,/原是我侄孙。/东家迎,西家请,/山乡家家都沾亲。”“亲人倾谈故乡事”“老者噙泪小儿笑,/中天明月是乡心。”(《乡恋》)“谁人不夸故乡美?/故乡山水浓似酒。/离乡数十载,/情在我心头。”(《乡情》)读这样的诗,我们仿佛看到诗人跃动的赤子之心和热诚之爱。他置身于自己的民族家园,把对民族家园与生俱来而又得到升华的爱,由此形成广博的民族感情。
四、民族语言
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塑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物和思维过程。语言是诗歌的第一要素,只有掌握丰富的语言,从思维中提取准确精炼富有穿透力的语言才能创作出好诗来。民族语言文字蕴含有特定的思维规则、表现形式及丰富的文化现象,是传承民族所特有的文明和思想内涵的活化石,是靠长期积淀而来的精神财富,阐释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语言的多元一体的内涵。在冉庄的诗歌中,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反映在民族特定的词汇上,如傣族语“卜哨”即少女的意思,使用这样的词汇感觉倍加亲切,符合民族的审美和情趣,是别的语言所无法替代的。这些词汇都是从民族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具有民族生活的鲜明烙印,恰当地运用,有助于表达特定的民族思想,有助于刻画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有助于抒发民族情怀,有助于民族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我们在强调诗人的少数民族身份和诗歌的民族性,并不是要求诗人局限于狭隘的视野之中。一味固守本民族传统艺术模式的外衣不放,就难以克服其弊端和适应时代的要求,就不会获得更大的艺术空间。诗人冉庄的诗笔长期行走在巴蜀大地上,千山万水皆著情,一草一木皆怀意,他自然而然也就受到巴蜀文化的浸润和熏陶。巴蜀文化以“下里巴人”为主要特色。三峡地区是巴蜀文化的主要代表地。三峡地区巴人的竹枝词,通俗易懂,易于诵唱,深受土家族人民的喜爱和欢迎。冉庄不断借鉴和学习前人和民间的诗歌创作经验,在坚守传统诗歌艺术表现的基础上适当地汲取有益的元素,形成自己的语言特色和民族风格。如明白晓畅、洗练平易、短小精致、注重格律、“三美”凸显。
诗人冉庄熟知诗歌创作的种种语言技巧,但“不刻意追求任何技巧”。他认为诗要看重的不是技巧而是真情实感、自然本色。在《山水情缘》里他说道:“我的任何一首诗,都是写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任何一首诗都有我真实的感觉和燃烧的情感。我总是在作品里袒露自己的真情和内心世界,让读者在品味中如闻其声,如见其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民族的作家有权利和责任在自己的文学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冉庄自觉继承民族的文化传统,努力把诗歌写成既是民族的诗,又是个人的诗,在共性中着力追求自己的个性。处于文化身份重构中的诗人冉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选择走简单的回归传统的道路也是行不通的,排斥其他文艺思潮和美学风格,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将步入死胡同。只有热情地融入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重新建构中,把所有的生存体验化为自己的创作来源,诗歌创作的活力才不会枯竭。冉庄十分认可涂鸿对自己的评价:“冉庄是一位十分传统但不守旧的诗人。从艺术修养上看,一方面,他深受传统诗歌美学的影响,整个审美倾向和艺术范畴是传统的;但另一方面,迅速变化的诗坛,现代诗歌的崛起,又不能不使他试图扬弃传统,更新自我,探索出一条新路来。”[4]
五、民族气质
少数民族诗人在精神上要跨越不同时代,面临不同的文化参照,因而他们的诗歌创作本身就构成了一对矛盾:诗人既要坚守自己的民族立场,努力保持自己作品的民族特色,又要用文学理论来审视民族的文化,学习和借鉴整个人类的先进文化,旨在不断调整和规范着自己的诗歌创作。冉庄洞悉诗歌艺术的发展规律,正确处理诗歌创作本身具有的矛盾,在民族文化和他者文化的平衡中进行诗歌创作。冉庄的诗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应该是综合性的混合体”[5]。冉庄的艺术探索精神和审美价值取向对其他少数民族诗人也有着启示的意义。
“任何一首成功的诗,都是诗人对于大千世界的综合感受而形成的一种艺术把握,是诗人渗透情感的外部世界的艺术折光。”[6]诗贵在情,“繁采寡情,味之必厌。”[7]感情是诗的生命,诗歌的本质重在抒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动于中,莫贵于真。诗是真实强烈的情感之歌,真诚的生命之歌。没有情感的诗歌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是苍白的、羸弱的。诗歌之美重在情感,以情感人是诗歌实现其价值的重要手段。诗传递的是真情,是感动人的力量;唤起的是真情,是把人感动的力量。否则,再漂亮的文字也是“纸老虎”,无法走进人的心灵,因而也就不具备感染读者的精神天地和灵魂活力,这样的诗,其生命是不会长久的。只有真实忠诚地反映民族的生活和心声,诗才具有民族的精神气质和价值。那种脱离民族的生活和历史发展进程的诗作,既缺乏宏大的视野而显得小家子气,也容易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冉庄关注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现实,以深沉的眼光打量和检视民族文化的历程,将民族的道德价值、地域风情、族源亲情、习俗信仰等呈现于诗作,情感摇曳,有对生命的体悟,有对风光的赞美,有对亲情的寻觅,有对爱情的歌颂,有对家国的守望,有对故人的感怀,有对岁月的回望。情感的民族性不断发酵、壮大,延展成为一种博大深广的人类共同的情感,唤起众多人的认同和共鸣。只有真正熟悉并掌握民族生活的真谛,真情地创作,真诚地歌唱,才有可能了解并正确运用民族的艺术表现形式,才有可能接触到民族特点的实质和精髓。
在冉庄的诗中,色彩浓郁的抒情和强烈有力的议论是一亮点,二者有机结合,显示出诗的情感与理性的力量,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了诗人的独立思想、价值取向和民族立场,具有本土化特色。冉庄的诗具有土家族的气质,少数民族的生活气息也弥漫在诗行里,有真感情。对于一个清醒、有自觉追求的诗人而言,始终关注现实,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关注生活,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听从时代的召唤,传达人民群众的声音,以诗的方式介入现实和生活,以诗的方式呈现现实和生活,这是比较宝贵的品格。但他的诗过于追求平实,过于追求原生态,缺少凝练。对诗歌这一文学体裁而言,是不太符合诗歌讲究“蕴藉”“含蓄”的美学特征的。海明威创作小说很讲究“冰山原则”,他认为小说创作要像海上漂浮的冰山,有八分之七应该隐藏在水下,这样才能获得一种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旨。诗歌创作又何尝不是这样?这是冉庄先生应该注意到的一点,也是我们每个诗人应该注意到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