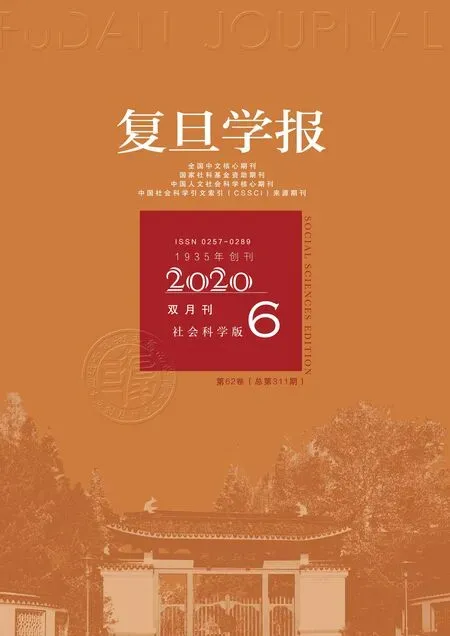19世纪英国草药知识的全球化和普遍化
——以丹尼尔·汉璧礼的中国草药研究为中心
[韩] 安洙英
(上海师范大学 世界史系,上海 200234)
放眼19世纪英国的药材学史,丹尼尔·汉璧礼(Daniel Hanbury,1825~1875)尤引人注目。他专注于药学,在植物学方面也颇有建树。然而,他的研究很难划分到当代的某个学科中去。他很少关注药物的化学成分或生理效应,因此其研究或不能算作当代“药理学”,(1)就像贝勒曾经对他作出的评价“博学的药理学家和能干的植物学家”,许多作者(包括他本人)都把汉璧礼的学术领域定义为“药理学”。在出版汉璧礼论文汇编,约瑟夫·因斯称之为“主要以药理学和植物学为主题”。见Emil Bretschneider,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vol. 2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and Company, 1898) 815. 另见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2.而应当被称为“药材学”。具体来说,便是广泛地考察各种用于医药或其他经济用途的植物和天然材料,并关注它们的历史、贸易和使用。汉璧礼的学术活动是跨学科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定义——如“本草学(Materia Medica)”“生药学(Pharmacognosy)”“医学植物学”或“经济植物学”。
汉璧礼的学术生涯很短暂,仅有二十年,但仍然是辉煌的。他在《药学杂志》和《林奈学会学报》等著名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在他的弟弟托马斯·汉璧礼的主持下,由约瑟夫·因斯(Joseph Ince)收集和编辑。这部论文集取名《科学论文——以药理学和植物学为主》,于1876年出版。(2)Daniel Hanbury, Science papers, Chiefly Pharmacological and Botanical, ed. Joseph Ince (London: Macmillan, 1876).汉璧礼对各种外来草药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且在同时代科学家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力,但却极少为当前的科学史研究所关注。(3)见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p. 102; Edward Joseph Shellard, “A History of British Pharmacognosy. Part 6. The Life and Work of Daniel Hanbury (1825-1875),” Pharmaceutical Journal 227 (1981): 774-7. 关于汉璧礼职业生涯、生活和藏书等等各个方面的详细介绍,尤其对于他与英国皇家药学会的关系,参见该学会网站上的一系列近期文章,例如Karen Horn, “Drugs According to Daniel Hanbury.” RPS blog, http://blog.rpharMScom/royal-pharmaceutical-society/2018/04/27/drugs-according-to-daniel-hanbury/, 2018年4月27日、2018年11月1日读取。实际上,汉璧礼进行了广泛的通信交流及标本交换,他的研究素材取自世界的各个角落。(4)例如,在1852年末到1855年末的大约三年间,他曾同时与二十多人进行交流,以交换各种豆蔻的标本。见Wellcome, MS 8355。最重要的是,他的这种研究兴趣很好地体现了大英帝国的商业影响力是如何在19世纪缓慢扩展到美洲、非洲和亚洲等地的。
汉璧礼对中国植物抱有极大的研究热情。(5)Bretschneider,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vol. 2, p. 815.他在《林奈学会会报》及《皇家药学会会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了产自中国或在中国被广泛运用的药材和植物,这些文章日后被集结成册,题名为《论中国草药》。(6)Daniel Hanbury, Notes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London: John E Taylor, 1862).此外,在1851年后的二十五年间,他还陆续收藏了一批中药标本,很可能已经建立了那个时代英国最为丰富的中国草药标本库。红枣、四川胡椒树、肉桂、白虫蜡、高良姜、两种绿色植物染料,以及几种豆蔻,这些都是汉璧礼的植物标本。(7)见Edward Morell Holmes, Catalogue of the Hanbury Herbarium, in the Museum of the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1892) 25-7, 17, 99, 109.
本文以汉璧礼和他的学术实践作为主轴,结合同时代的其他研究,考察19世纪英国药材学家如何通过命名草药并建构科学知识体系,制造出便于知识全球化的概念系统工具。(8)笔者在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Wellcome Library)找到了汉璧礼的笔记本(共16册),其中就有他亲笔信的手写副本,它们名为Notebook containing notes on materia medica等,下文简称Wellcome。通讯员们的回信则散见于许多档案中,我所引用的主要来自伦敦皇家药学会图书馆(Royal Pharmaceutical Society Library),它所收藏的文献名为Hanbury, Daniel. Hanbury Collection of Printed Reprints and MS Material, 1826-1875, etc., Hanbury Collection Manuscripts, Acc. 201.045.——下文简称RPS。从汉璧礼寄往世界各地的信件、他的手稿和著作来看,帝国主义的商业扩张是19世纪西方科学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它不仅决定了科学家们积累知识的方法和收集素材的范围,还决定了他们在重构草药学知识时的基本动机、目标和框架。
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贸易网络的发展,草药的具体流通渠道也在发展和更新,从而跨越和连接了广袤的地区。草药流通的这种极速扩大化,使特定草药的称谓越来越多,渐趋复杂。为了鉴别与日俱增的域外草药、使草药贸易正常运行,并且随着越来越多前所未知的草药跨越文化和语言的边界而进入药材学家的视野,药材学家们开始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命名系统。这个系统应当能够放置大量跨越文化边界的自然事物,特别是来自异域的草药。
因此,英国药材学家的学术实践大部分是围绕草药名称的收集和翻译进行的,其工作的具体流程与意义便是本文所要关注的。这些科学家不仅进行了现代科学所要求的实验或观察,还涉及大量的“文本实践”,也就是从诸种文献中考证草药的当地名称和拉丁语名等。(9)对于“文本实践”概念,见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pp. 93, 111-2.换言之,草药和植物的名称不仅从国外收集,也从各种文献中搜索出来。在这一过程中,近现代“药材学(Materia Medica)”逐渐转变并融入到现代植物学。前者主要通过各种方法来叙述“药”的信息,是无定形的;而后者则以独一的植物学命名法和普遍、统一的结构为特征。
在汉璧礼的时代,现代西方科学中草药知识的基础、惯例和结构还处在变动、形成的过程中,而与现代的科学概念不相吻合。笔者将仔细考察汉璧礼的研究,尝试一窥19世纪英国科学家研究世界草药的独特模式,并揭示其历史意义。
一、 药材学知识的现代转型与命名法的更新
1735年林奈《自然系统》的问世标志着全新植物命名法的产生。它提供了一个固定的植物分类系统,使得追踪某种草药的源植物、进而确定草药种类成为可能,因而被认为是革命性的。(10)参见Lisbet Koerner, Linnaeus: Nature and N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林奈命名法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接纳并命名所有新的事物,兼具开放性和普遍性。(11)见Ernst Mayr,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72.此后建立的早期近代欧洲博物学致力于将外来植物一一纳入到现代植物分类法之中去。在林奈所处的欧洲,自然知识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博物学打下的基础,包括后者所积累的植物标本、材料以及观察日志。(12)Pratik Chakrabarti, Materials and Medicine: Trade, Conquest and Therapeutic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6; Richard Drayton, Nature’s Government: Science, Imperial Brit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8.而到了19世纪,困扰植物学家们的问题则转变为“如何按照已经建立的系统来命名大量涌现的域外植物”。他们希望简化标本的流入手续、更有效地处理海量实物和信息,因此发展出了各种新的科学研究手段。这种趋势的意义只有在一个统一的认识框架逐渐形成的背景下,才能被清晰地理解。
在19世纪的伦敦,许多植物或草药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类体系中,其繁复的名称被彻底简化为基于林奈命名法的标准化名称。在这一过程中,将世界草药材料置于普遍框架下的构想逐渐被确立为现代植物学的愿景。以下将以豆蔻的命名过程为例,说明这项独特的标准化事业。
早在17世纪末,欧洲市场上就出现了名为“豆蔻(Cardamom)”的植物种子。在短暂的一个世纪中,豆蔻的药用价值迅速获得了欧洲市场的认可——它既能“暖和、滋补、健胃和驱风,用于增加血管的张力和体液的活力(motion),以及促进水状液的分泌”,又能用于制作酊剂,还能榨油,(13)见William Lewis, The Edinburgh New Dispensatory, 3rd American edition, ed. Joseph Black (New Hampshire, 1796) 469, 480, 482, 492, 493; Donald Monro, A Treatise on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Chymistry, and the Materia Medica, 3 vols., vol. 3 (London: Printed for T. Cadell, 1788) 45-6; George Motherby, “CARDAMOMUM,” A New Medical Dictionary; or, General Repository of Physic. Containing an Explanation of the Terms,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Various Particulars (London: J. Johnson, 1775).因此欧洲各国对豆蔻的需求量大幅上升。但是,欧洲各国却没能成功地在本土种植豆蔻,不得不依赖海上贸易来获取这种重要的药食两用植物。(14)英国人关于在印度生长的豆蔻的最早的详细记录可能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写的物品清单,那里它被列为从东印度群岛“迫切需要得到之物”(Desiderata)之一。Joseph James and Daniel Moore, A System of Exchange with Almost all Parts of the World. To which Is Added, the India Directory, for Purchasing the Drugs and Spices of the East-Indies, &c. Published for the Editors (New York: Printed by John Furman, 1800) 119, 138.
汉璧礼十分关注豆蔻的各种品种、产地及其商业价值,这反映在他的标本室里成串的姜黄科标本目录中。就对豆蔻的了解而言,同时代的其他植物学家很难与他匹敌。(15)约瑟夫·因斯表达汉璧礼对豆蔻的浓厚兴趣说:“他对姜科植物进行了研究,仿佛他深爱着它们。”Hanbury, Science Papers, Chiefly Pharmacological and Botanical, p. 9.为了收集豆蔻果实、种子甚至蒴果,汉璧礼与遍及亚洲的联系人进行了通信往来,最多时他曾同时与二十多人通信并交换各种豆蔻的标本。(16)基于他的一本笔记本,Wellcome 8355,以下仅列举1852年末至1855年末的三年间参与他的豆蔻标本和种子交换网络的一群人中的一部分:宁波(玛高温);上海(雒魏林);广州(约翰·里夫斯);锡兰(思韦茨);广州(罗存德); 路易港(弗勒罗);乔治敦(斯图伯里);新加坡-婆罗洲-巴塔维亚(莫特利);新加坡(奥克斯利);香港(Bowring);新加坡(帕迪);曼谷(罗伯特·亨特); 乌普萨拉,瑞典(汉贝格);爪哇(无法识别);加尔各答植物园(托马斯·托姆森);仰光,伯马(麦克里兰),分别见于该手稿第306、335~336、338、344~345、348、356、362~363页。全球贸易下的物质流通导致伦敦市场出现了大量似是而非的品种,它们都被笼统地称为“豆蔻”,给市场带来了不少混乱。汉璧礼通过鉴定市场上的未知品种、确定它们的源植物,为辨识这些似是而非的“豆蔻”品种作出了重大贡献。
最终,那些数不清的市场名称都被草药研究者抛弃了,他们提出了基于林奈双名法的名称——属名“豆蔻属”(Elettaria)和种名“Elettariacardamomum”。这两个名称很快取代了“马拉巴尔豆蔻”“小豆蔻”“真正的豆蔻”等称呼,被研究草药及其他经济植物的科学家广泛采用。比如,马顿(Maton)指出马拉巴豆蔻与豆蔻属的区别、倡议另立一属时,“豆蔻”这一总称指代的不同种类、名称和起源之间的混乱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他在1811年的一篇文章中仔细考察了这个问题,却不清楚古代作者究竟将哪一种植物命名为“豆蔻(Amomum)”。(17)David White, “A Botanical Description and Natural History of the Malabar Cardamom,” Transactions of 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 10 (1811): 251-4.随着种属名和豆蔻分类的确立,各种新的豆蔻品种如雨后春笋般不断被辨识出来,使得广义上的“豆蔻”目录得到了不断的补充和修订。例如,比较佩雷拉同一著作的1842年版和1850年版,就能看出“姜科(Zingiberaceae)”的扩展和完善。在1842年版中,佩雷拉列出的姜科植物包括七个豆蔻属物种、两个小豆蔻属物种,以及八个“尚未被鉴定”的物种。随着对每个物种的进一步观察,在1850年版中,豆蔻属被重新分类并最终增加到九种;又在姜科中添加了两种高良姜属植物。因此,在1842年版本的姜科植物篇仅有15页,1850年版则扩展到33页,篇幅是前者的两倍多。(18)Jonathan Pereira, The Elements of Materia Medica and Therapeutics 2 (1842): 1022-37; Jonathan Pereira, The Elements of Materia Medica and Therapeutics, 2, part 1 (1850): 1115-47. 目前,姜科植物共有50个属,包括非洲豆蔻属(55)、山姜属(248)、豆蔻属 (178)、姜黄属(92)、小豆蔻属(11)和姜属(146),该科物种总共有1594个接受名称(包括种下分类群)。
19世纪初英国科学家辨识豆蔻不同类型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了欧洲草药知识发生的转变。作为一个普遍的命名系统,林奈双名法的建立对药材学知识传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关于林奈双名法对自然的经济效用的高度关注及其政治含义,参见Kapil Raj, Relocating Modern Science: Circul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South Asia and Europe, 1650-190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7), chap. 1; Staffan Müller-Wille, “Nature as a Marketpla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innaean Botan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5.5 (2003): 154-72; Lisbet Koerner, “Purposes of Linnaean Travel: a Preliminary Research Report,” Visions of Empire: Voyages, Botany, and Representations of Nature, ed. David P. Miller and Peter H. Re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7-52.随着这一体系的普遍化,新的植物分类学不断发展,各种欧洲药典也随之改写。相应地,关于药的所谓“科学知识”也就被看作是符合林奈双名法或现代科学标准化语言的知识。(20)David L. Cowen, Pharmacopoeias and Related Literature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618-1847, vol. 700, Aldershot: Variorum, 2001, pp. 40-1; Antonio Lafuente and Nuria Valverde, “Linnaean Botany and Spanish Imperial Biopolitics,” Colonial Botany, ed. Londa L. Schiebinger and Claudia Swa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134-47.
因此,这一时期欧洲对每种草药的命名和理解,完成了从随机命名到现代植物学命名法的转变。前者赖以命名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天然特征或市场偏好,后者则严格依据林奈命名法。然而,这种变化要求药材学家从草药的两个维度着手——既要确定某种草药的源植物,又要对该植物进行分类。于是,对天然本草的真伪、效用的甄别开始依赖于林奈分类法。由此可以发现,草药知识从“药材学”到现代植物学的转变,源于校正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药品掺假问题。换言之,在新的框架里,为了在充斥市场的许多“假”药中正确地挑选出“真”药,需要为它的源植物“验明正身”。
可见,草药知识发展的原动力是解决因全球化的商业活动中出现的新问题,而表现为将市场上出现的繁复名称转化为单一、清晰且科学的名称。(21)约瑟夫·胡克即其中之一。见Joseph D. Hooker, “On Some Species Amomum, collected in Western Tropical Africa by Dr. Daniell, Staff Surgeon, etc. etc,” Hooker’s Journal of Botany and Kew Garden Miscellany, vol. 6 (London: Reeve, Benham, and Reeve, 1854): 289-97; Joseph D. Hooker,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of Amomum, from Tropical West Africa,” Hooker’s Journal of Botany and Kew Garden Miscellany 4 (1852): 129-30.在药材学家们适应并最终接受林奈分类法的过程中,他们跨越了各不相同的种种知识背景,目光遍及广泛的地理范围,而一种特殊的翻译成为了他们的首要任务——在不同的书籍、不断变化的学科和不同的语言之间建立联系,欧洲现代科学的语言便随之成为这一过程中的核心纽带。这一过程并不仅仅是以一种语言的译名对应另一种语言的原名,因此仅仅以“翻译”来概括之,恐怕不如“译校”来得恰当,也就是既要在不同语言的概念之间建立对应关系,也要甄别具有多种名称的同一实物的属性,将之纳入西方的植物命名体系之中。
二、 考异与重构:19世纪英国植物学家对早期文献草药名称的研究
在19世纪,英国已建立起一个横跨伦敦与中国的巨大科学网络,这使草药标本、信息和人员不断向伦敦流动并在那里得到积累,逐渐被加工成所谓“科学知识”。汉璧礼作为主要活动于伦敦的植物学家,同样主要依赖欧洲以外的通讯员来获取植物标本及信息。也就是说,这一网络不仅运输物质材料,还输送了名称、文本等抽象材料。它们不仅存在于异域这一空间上的远处,而且存在于文献这一时间上的远处。文本的交换和名称的翻译同时发生。名称的“翻译”通常是通过重新发现前人留下的海量文本来进行的。正如下面的考察所显示,重新发现以前的文本,与重新书写植物的许多外文名称进而把它们换成易读的名称同步进行。相较于收集植物的本土名称,这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而且,它往往优先于化学分析等科学手段。因此,在多个文本之间对名称进行一系列的对照和对应,在把药材学转变为具有普遍化术语的全球性科学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这一特殊的翻译表明,前林奈时代的博物学作家以及他们对于异域自然界研究的成果,如何被后林奈时代的学者们对待和接受。新发现的从前写就的文本,在重新梳理植物神秘莫测又繁复的名目时往往更有用。
至于中药和有关植物,汉璧礼参考了许多较早的文献,包括中国古典和早期欧洲博物学著作。他的兴趣集中在书中的各种药名和植物名称,并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识别和翻译,以将中国植物群纳入西方科学知识体系。接下来,笔者将阐释这一过程中他们面临的双重挑战。
(一) “名”与“实”的断裂
第一重挑战是植物名与实物之间始终薄弱的对应关系。19世纪以前关于中国植物的博物学著作大多基于两方面的理由而被植物学家们束之高阁,其一是西方语言译名的缺失,其二是图像材料的匮乏。笔者将从这两方面入手,解释这种植物名称与实物之间的断裂现象。
首先,在大多数著作中,植物名称大多采取以罗马字母标记汉语拼音的方式表记,(22)见Wellcome, MS 8354, p. 207. 在这里,汉璧礼提到了一种类似于姜黄的根,叫做“郁金”(音译成Yue-kin或Yo-kin),但没能为它想出一个学名。没有英文名或拉丁名。这样的做法,使欧洲读者难以判定作者观察和描述的到底是哪种植物。正如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等提及的,引入仅有中文名称的未知植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缺乏关于中国植物的统一术语的情况下,许多叙述都因无法提取有效信息而黯然失色。(23)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Mélanges Asiatiques, ou Choix de morceaux critiques et de mémoires relatifs aux religions, aux sciences, aux coutumes, a l’histoire et a la géographie des nations orientales (Paris: Dondey-Dupré, 1825), chap. 250.因此,早期博物学留下的成果对于19世纪欧洲药材学知识的影响非常有限,而后者正按照林奈双名法重新建构知识体系。(24)关于19世纪的欧洲药材学家如何依据林奈双名法重新命名,从而“为自然本身及早期植物学赋予秩序”,可参考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24-5; Patricia Fara, Sex, Botany and Empire: The Story of Carl Linnaeus and Joseph Banks (Cambridge: Icon Books, 2004) 21; Staffan Müller-Wille,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nnaean Botan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C: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38.3 (2007): 541-62.有类于此,当时英国科学家对中国、日本草药的博物学著作也缺乏兴趣。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科学家依然认为这些著作里的植物既无法辨认,又没有实际的经济价值。这两种情况使得早期博物学著作仅仅被当作一种异域知识,而对欧洲各国的国内经济发展没有什么实际效用。
于是,在19世纪,除人参、茶叶、大黄等大名在外的植物,大量的中国植物和中草药仍然未被认识。它们没有欧洲语言的译名,自然也没有科学名称,只能以汉语拼音的方式被提及,并被视为奇异的事物。(25)Linda Barnes, Needles, Herbs, Gods, and Ghosts: China, Healing, and the West to 184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71-72.例如,尽管英国人对作为染料的各种植物非常感兴趣,却只能以音译指称之——如“Waifa”“Wai-hua”或“Wai-hwa”等。(26)Wellcome MS 8354, p. 261; Wellcome, MS 8356, pp. 36-37. 另见Wellcome, MS 8354, p. 239.
直到19世纪中英政治关系及经济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后,这一形势才发生了改变。 由于拥有潜在经济利益的草药不断增多,植物学家们开始着手解决这种混乱局面。针对陌生的草药,一方面许多当时研究者提出了新名字,另一方面它们失落的名字也从早期著作中被重新发现。因此,早期著作受到了新的关注,拼音名称也被转换成科学术语的名称。这项工作,使得早期的博物学著作与欧洲当时状况相连,创造出有效的知识,从而使中国物产成为可识别的商品,最终用于出售。
从18世纪中叶起,用拉丁语为每种仅有汉语拼音名的植物或药材命名,逐渐成为植物学研究的重要部分。随着林奈双名法的广泛运用,新一代科学家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27)参见Anna Pavord, The Naming of Names: The Search for Order in the World of Plant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08).以詹姆斯·坎宁安为例,在19世纪科学家的眼里,他留下的手稿和图画似乎不适合作为参考,因为它们大多数只标记了带有汉字和英文音译的名称。(28)Wellcome, MS 8355, pp. 79-80. 在这里,汉璧礼贴一张小纸条写道:“一本关于中国植物的书,各个植物有中国名字以及拉丁语解释——由M.Cuningham寄给W.Petiver(Additional mss. 1782-1835: No. 5292-5294)。”关于引起汉璧礼注意的这份手稿,笔者在2018年访问大英图书馆时发现,由于手稿的参考代码有所变动,现在无法确定,但如果我从汉璧礼所提到的描述推测,该手稿也许是:“James Cuninghame [Cunningham]: Notes on Botany and Zoology in East Asia and the Canary Islands, plus Correspondence with Juan Baptista Poggio and Isidorus Arteaga de La Guerra,” 1706, British Library, Sloane MS 2376. 其中包含的一部分——“植物目录,其图像在‘中国描绘’中”(“Catalogues Plantarum, quarum Icones in China delineate Sunt”)——该部分主要罗列了植物的中文名称(罗马字母拼写),并提供了每种植物的简要描述(fols. 82-110)。这些描述应该附在另一份共43张的图谱上。参见Raymond P. Stearns, “James Petiver, Promoter of Natural Science, c.1663-1718,” Proceedings of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62 (1952): 268-69.伦纳德·普卢肯特(Leonard Plukenet,1641~1706) 在《植物大全》(AmaltheumBotanicum)一书中对坎宁安在中国收集的植物进行了详尽的描绘,但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异国自然的好奇心,而不是为了在现实中发挥作用。(29)Leonard Plukenet, Amaltheum Botanicum, Londini: [s.n.], 1705. 这本小册子是《植物图集》(Phytographia)的第四卷。尽管这本书有104幅图和对400份中国标本的描述,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读者无法用可读的欧洲名字辨认每一种植物而一筹莫展。(30)Wellcome, MS 8355, pp. 79-80. 见 Richard Pulteney,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Progress of Botany in England, vol. 2 (London: Printed for T. Cadell, 1790) 18-29.因此,在该书出版一个世纪之后,林奈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吉塞克(Giseke)对两者的工作进行了彻底的编辑和校阅,并根据林奈双名法对书中的植物进行了重新编排。(31)Paul Giseke, Index Linnaeanus in Leonhardi Plukenetii opera botanica (etc.), (Hamburgi: prostat apud auctorem et Carolo E. Bohn Commissum, 1779). 参见Emil Vasilievitch Bretschneider, 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1) 44.
与此类似,德国植物学家恩格柏特·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的研究也得到了重新关注。他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医生,驻扎日本出岛期间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及各种植物进行了观察,结集出版为《异域采风记》(Amoenitatumexoticarum)。其第五卷有145页,题名《日本植物》(Plantraumjaponicarum),尤其值得关注。其中许多植物是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抑或是与中国品种相同。(32)Engelbert Kaempfer, Amoenitatum exoticarum politico-physico-medicarum fasciculi V (Lemgoviae: Typis & impensis Henrici Wilhelmi Meyeri, aulae Lippiacae typographi, 1712). 由坎普法撰写的《日本历史》也是汉璧礼查阅的另一个信息来源:Engelbert Kaempfer, The history of Japan …, trans. John Gaspar Scheuchzer (London: Printed for the translator, 1727). 见Wellcome, MS 8354, p. 203; RPS, P273MS, fol. 28.坎普法著作的最大优点在于,他描述各种植物时忠实地遵循植物学家的态度和规范。(33)Wolfgang Muntschick, “The Plants that Carry His Name: Engelbert Kaempfer’s Study of the Japanese Flora,” Bodart-Bailey, Beatrice M. und Derek Massarella (Hg.): The Furthest Goal, Engelbert Kaempfer’s Encounter with Tokugawa Japan (Folkstone: Japan Library,1995) 81.这本书既包含一系列的植物插图,还流露出对植物形态的特殊兴趣,这与现代植物学的关注点相同。例如他对人参的描述是用“专门性的描述语言”写成的,这正是日后科学性权威的渊薮。(34)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p. 29.然而,坎普法的作品与坎宁安相似,直到出版几十年后才最终在林奈以后的植物学系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瑞典医生和博物学家图恩伯格(Peter Thunberg)是坎普法成果的伯乐。(35)Federico Marcon,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Jap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136-39.作为林奈的门徒,他在日本呆了十六个月,首次尝试根据林奈双名法对日本植物进行命名,这项工作对日后影响深远。他的著作《日本植物志》(FloraJaponica)记录了530种以上的植物。(36)Carl Peter Thunberg, Flora japonica (Lipsiae: In Bibliopolio I. G. Mülleriano, 1784).书中的植物标本主要是由他本人调查收集的,但也有许多是通过观察约瑟夫·班克斯所藏的坎普法标本得来的。(37)Marcon,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Japan, pp. 135-37.图恩伯格作品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它同时使用了林奈双名法和日文名两种命名方式来描述和鉴定这些日本植物。
此处以菊花为例。菊花作为观赏植物,在中国和日本很受欢迎,但迟至19世纪初,它还是欧洲人眼中的异域奇葩。(38)坎普法、图恩伯格和卢雷罗是亲自观察到该植物的人,他们的叙述“被认为在调查这一问题上提供实质性的帮助”。Joseph Sabine, “XXIV. Observations on the Chrysanthemum Indicum of Linnæus,” Transactions of 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 13.2 (1822): 561-78.在坎普法留下的只言片语中,他提到“当地人称之为Kik,Kikf或Kikku”,汉字写作“菊”。(39)Kaempfer, Amoenitatum Exoticarum Politico-Physico-Medicarum Fasciculi V, pp. 875-77.林奈和威德诺没能从这样的记载中辨认出这种植物,他们的书《植物种志》(SpeciesPlantarum, 1753)没有反映坎普法著作中的信息。但图恩伯格将坎普法的观察与菊花的林奈名称(ChrysanthemumIndicum)联系起来,还补充了更多的日语名称——“Kikokf, Kiko no Fanna, Kik, Kikf或 Kikku”。(40)Thunberg, Flora japonica, p. 320.
另外,由于缺乏可供查阅的样本或插图,19世纪以前著作中有关植物的描述往往模棱两可、指代不明。这种缺陷集中体现在卢雷罗(Juan de Loureiro,1717~1791)的《交趾植物志》(FloraCochinchinensis)中。卢雷罗是一名葡萄牙籍耶稣会传教士,曾被派遣到印度果阿和中国澳门。尽管他在《交趾植物志》(FloraCochinchinensis)中提供了大量关于东亚植物的新信息和详细的叙述,但却没有被同时代的欧洲科学家接受为参考书籍,因为里面的描述大多是文字性的,没有包含任何标本或植物图。(41)Juan de Loureiro, Flora Cochinchinensis:Sistens Plantas in Regno Cochinchina Nascentes…, 3 vols (Ulyssipone: Typis, et expensis Academicis, 1790). 他于1742年来到交趾支那,在那里作为数学家、博物学家工作了35年。从1777年起,卢雷罗在广州待了三年。参见Georges Métailié,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4, Traditional Botany: An Ethnobotan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538-39; Elmer Drew Merrill, “Loureiro and His Botanical Work,”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72.4 (1933): 229-39.此外,尽管花是林奈双名法中最为强调的部分,卢雷罗却往往不依据对“活植物的花朵”的观察来进行分类,这使得他的工作对汉璧礼和其他人来说缺乏说服力。(42)Daniel Hanbury, “Some Rare Kinds of Cardamom,” Pharmaceutical Journal 14 (1855): 352-355, 410-422; represented in Daniel Hanbury, Science Papers: Chiefly Pharmacological and Botanical (London: Macmillan, 1876) 105-6.
然而,对汉璧礼等19世纪中后期英国植物学家来说,卢雷罗的著作是非常有价值的材料之一。在18世纪,还未有任何其他科学家在中国植物研究这一领域取得如此非凡的成果。用贝勒的话说,卢雷罗“毫无疑问占有最突出的地位”,“至少与他那个时代的一般水平相比”,他既是个认真的观察者,又拥有良好的植物学知识。(43)Bretschneider, 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of China, pp. 132-84.《交趾植物志》中描述的很多亚洲植物,是卢雷罗首次发现、记录,并亲自用林奈法给它们命名的。(44)在他所描述的1257种植物中,这位葡萄牙耶稣会作家观察并命名的中国植物共有539种,其中245种仅在中国发现,大部分在南部。在现在的植物分类学中971种植物被认为是由于卢雷罗首次命名的。见“国际植物名称索引”:International Plant Names Index, 2018年,http://www.ipni.org,2018年10月8日读取。另见Bretschneider, 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of China, pp. 134-35.因此,这本书的意义在于作者为许多中国本土植物提供了广东话或普通话名称的拼音以及科学名称,根据林奈双名法——“无论首发与否,无论正确与否”。(45)Bretschneider, 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of China, pp.132-3; Elmer Drew Merrill, “A Commentary on Loureiro’s “Flora Cochinchinensi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24.2 (1935): 44.
尽管如此,《交趾植物志》的命名还是很难取信于下一代研究者。这是因为卢雷罗没有留下任何植物图或标本,下一代研究者无法完全确定他亲眼观察到的到底是什么植物。在19世纪的植物学家看来,如果不能检查真实的标本,仅仅依靠“卢雷罗提出的论断”似乎是不可信的。(46)Hanbury, “Some Rare Kinds of Cardamom,” pp. 98, 105-6.
例如当卢雷罗将观察到的草果命名为Amomummedium时,他是唯一一个对其进行描述的人,却没有留下样本或插图等任何实质性证据。对此,一个世纪后的法国草药科学家吉布尔只能猜测,他观察到的“球卵形中国豆蔻”标本可能与卢雷罗所观察过的Amomummedium相同。关于这一点,汉璧礼也不敢断言。(47)Hanbury, “Some Rare Kinds of Cardamom,” pp. 105-6; Wellcome, MS 8354, p. 207; Wellcome, MS 8355, pp. 320-22. RPS, P273MS fols. 1, 9.在他看来,显然卢雷罗也没有亲眼目睹这种植物的花朵,这使得他所留下的描述更加“不完整”,只能对Amomummedium的身份持保留态度。(48)Hanbury, “Some Rare Kinds of Cardamom,” pp. 106-7; Hanbury, Notes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 26; Merrill, “A Commentary on Loureiro’s “Flora Cochinchinensis,” p. 118.
因此,尽管卢雷罗是首先为许多中国植物进行科学命名的植物学家,而且他的叙述本身是一项罕见而有价值的成就,但却难免落入植物名“名”与“实”断裂的窠臼。这是由于他仅仅留下了文字性描述,没有其他实质性的根据。这种断裂或分离导致了他提出的林奈式名称与后代研究者所提出的那些往往不相吻合、舛错迭出。正是因此,美国植物学家埃尔默·梅里尔(Elmer Drew Merrill,1876~1956)说,“目前,我们依然不能轻易地把卢雷罗编写的草药志引为参考”。(49)Elmer Drew Merrill, Merrilleana: a Selection from the General Writings of Elmer Drew Merrill (Waltham, Mass.: The Chronica Botanica Co., 1946) 254-5; Métailié,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6, Part 4, pp. 634-5.
(二) 草药名称的纷繁演化
19世纪英国植物学家面临的第二重挑战,则是草药名称在广大空间与漫长时间中的纷繁演化。在广土众民、历史悠久的中国,同一草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有不同的名字,在同一时期的各地也可能有不同的名字,甚至即便是同一名字,也可能因各地的方言差异而听来一头雾水。以下将顺次举例说明。
无论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存在前人书中提及的名称与生活中普遍使用的名称之间如隔天堑的现象,以致查阅古典文献并不像汉璧礼等所期望的那样富有成效。一种草药的分类、鉴别和评价方法随着时间而改变,这使得用林奈命名法来识别任何一种草药都变得相当困难。(50)见 Anna E. Winterbottom, “Of the China Root: A Case Study of the Early Modern Circulation of Materia Medic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28.1 (2014): 22-44.因此,很难将一个相对确定的名称与特定的实物联系起来。(51)关于药材名称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研究比较少。较近的包括:Marta Hanson and Gianna Pomata, “Medicinal Formulas and Experiential Knowledge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Epistem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sis 108.1 (2017): 1-25; Carla Suzan Nappi, “Bolatu’s Pharmacy Theriac in Early Modern China,” 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 14.6 (2009): 737-64.
例如,《本草纲目》所列举的每种药材都有“释名”,在该条目下列出了它的种种异名,汉璧礼等科学家自然乐于利用此书。但由于《本草纲目》成书于16世纪后期,很多名字在19世纪的中国药店和市场已经踪迹全无。比如,汉璧礼通过他的通讯员打听到了各种豆蔻的名字,却发现只有“益智子”一种出现在《本草纲目》中。(52)李时珍:《本草纲目:金陵版排印本》中册,第711~713页。因此,汉璧礼对“东坡豆蔻”这个名字感到困惑,事实上这是当时市场上常用的一个别称,而《本草纲目》的用语则是“白豆蔻”。(53)Hanbury, Notes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 28; 李时珍:《本草纲目:金陵版排印本》中册,第709~710页。同样,《本草纲目》将“草豆蔻”列为“豆蔻”的异名之一,但汉璧礼观察到的却是 “草蔻(Caokou)”。(54)Hanbury, Notes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p. 25-6.;李时珍:《本草纲目:金陵版排印本》中册,第707~709页。
在中国被称为“阳春砂”和“缩砂密”的豆蔻,也显示出实践和文本之间的差距。汉璧礼的通讯员在上海、香港以及新加坡市场上收集到了一些以“Yang-chun-sha”命名的标本,经过观察,认为它与卢雷罗的Amomumvillosum相同。(55)Hanbury, “Some Rare Kinds of Cardamom,” p. 109; Jonathan Pereira, The Elements of Materia Medica and Therapeutics 2 (1854): 1140; de Loureiro, Flora Cochinchinensis: Sistens Plantas in Regno Cochinchina Nascentes 1, p. 4.然而,卢雷罗将该物种的中文名称记录为“So Xa Mi”,而汉璧礼从未从中国收集到过被冠以这种名称的果实。后来,汉璧礼在《本草纲目》发现了一个与“So Xa Mi”相同的名字——“缩砂密”,他确认两者应是一物,又向汉学家求证,得知这个词现在通常音译为“Suh Sha Meih”。《本草纲目》还解释说,这类植物以前是从波斯等西域国家传来的,自10世纪开始在中国南方种植。(56)见李时珍:《本草纲目:金陵版排印本》中册,第710~711页。在《本草纲目》,李时珍将缩砂密以各种不同的叫法记录下来了,例如“缩砂”“缩砂仁”及“砂仁”。在中国本草著作中,直到现在普遍认为“砂仁”一词可以与“缩砂密”互换使用。事实上,汉璧礼从中国收到的只是缩沙密的蒴果部分,而这种蒴果又被称为“Sha-jin-ko”,即“砂仁壳”。“阳春砂”则是另一种中国植物,它的名字来源于产地阳春县。实际上,阳春砂和缩沙密是同一个物种的不同变种——缩沙密是Amomumvillosumvar.xanthioides(Wall. ex Baker)T.L.Wu & S.J.Chen,而阳春砂是Amomumvillosum, Lour.——因此汉璧礼和大多数中国人很难将它们区别开来。但是,在19世纪的中国市场上常见的只有进口的缩沙密蒴果“砂仁壳”和国产的“阳春沙”,换言之,“缩沙密”这个名字在当时中国已很罕见了。(57)Hanbury, Notes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p. 26-7.
虽然英国博物学家经常参考《尔雅》《本草纲目》以及其他古籍,但考证文本中的植物或药材名依然面临着许多困难。(58)E.C. Bridgman and S.W. Williams, “Notices of Natural History 1. the Peen Fuh or Flying Rat and 2. the Luy Shoo or Flying Squirrel Taken from Chinese Author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7 (1838): 90-2.首先,在不同的文献中, 一个物种有许多不同的名字。例如,当汉璧礼与其他研究者交流并提到“白豆蔻”时,通常用翻译名称“圆形或簇状豆蔻”来指代它,(59)见Wellcome, MS 8355, 335-336; Wellcome MS 8356, pp. 123, 245.它“生长在苏门答腊岛和印尼群岛的其他邻近地区”,在中国处处有售,是常用草药。(60)John Lindley, Flora medica: A Botanical Account of all the More Important Plants Used in Medicin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8) 566-67.然而,像这样一种果实具有不同名称的现象使汉璧礼困惑不已。暂且不论“Hang-kow”和“Seaon-kow”,光是“Po-tow-kow”与“Tung-po-tou-kou”这两种音译,就足以使人困惑。实际上,前者应当是“白豆蔻”,后者是其别称“东坡豆蔻”。(61)汉璧礼发表这篇文章后不久,师惟善在1911年出版的书中证实这一点,还指出了 “白豆蔻”和“东坡豆蔻”,这两个俗名被确认是同一种物质。Frederick Porter Smith,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Materia Medica and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1) 36-7.在这一案例中,中国人使用了至少四种名称来称呼一种果实,而在市场上,常用的别称可能同时对应同一对象,并且这些别称还会不断地变化。
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考虑中国的种种不同方言。不同的方言对同一个汉字名称的发音差异极大,常常使外国人感到困惑。(62)Samuel Wells Wil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Canton: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4) p. vii.而且,一种草药在不同的地方经常有着完全不同的名称。比如,帕里什发现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花椒样制成品在天津等地的市场上频频现身,而且亲眼所见“这种制成品的源植物在南京和芝罘等地非常茂盛”。他曾听说这种制成品源于Zanthoxylum piperitum(山椒)和Zanthoxylum alatum(竹叶花椒),但他在满洲的市场上听到的名称却是“Tche-whau”。(63)参见RPS, P273MS, fol. 1.不过,那些对中国比较熟悉的欧洲博物学家大部分都清楚这种情况。除了那些因地而异的俗名,显然还存在着一个“意义更为固定的、经典而学术性的名称”。(64)Léon De Rosny, “Lettre à la SBF,”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Botanique de France 3.4 (1856): 238.
三、 从描述到展示:普遍而扁平的世界自然
在19世纪英国的药材学和植物学中,对异域草药的本地化描述工作占据着核心地位,这在对大量植物和草药名称的一系列“翻译”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种工作主要包括与当地通讯员通信,交换药名表格并反复修改。首先,汉璧礼等将一张白纸划为数列,将草药的汉文名、俗名、音译、标本编号和外文正式名分别列出,一一匹配(图1)。他们一边密切地观察、比较这些标本,一边仔细比对标本名称的写法、读法。同样地,他的中国通讯员也要完成这两方面的工作,也就是将标本“全部放在瓶子或盒子里,再仔细地贴上标签”,标签上要清晰且详尽地注明植物的当地俗名。除此以外,他们还负责检查汉璧礼的药名表格,确认其中汉文的字形、发音无误后,再将之寄返。(65)Wellcome, MS 8354, p. 115; Wellcome, MS 8355, p. 283.
这些药名表格在伦敦和中国各地之间一再往复,其中的词条不断得到丰富——汉字、汉文拼音、英文名、林奈名逐渐拼合,成为某种植物完整信息的各个侧面。(66)RPS, P273MS, fols. 4, 5, 7.尽管汉璧礼一般依据植物的根、果实、种子等某一个部分来进行分类,但归根结底是要“用植物学命名法来分类并为草药验明正身”。也就是说,把每种草药纳入林奈的现代分类系统,进行重新定义。(67)RPS, P273MS, fol. 10; Wellcome, MS 8354, p. 141.如此一来,便逐步形成了一套以欧洲植物学语言可识别的、完整的中国草药目录。可是汉璧礼没能做到十全十美,他鉴定出的草药仅占收集到的一半,剩下的只能加上属名,或是标记问号,表示他已无能为力。
汉璧礼和他的通讯员交换各种信息和材料,积累了大量药名和标本,进而更新了文本知识和样本库。汉璧礼的科学实践主要是将每一个样本与它们的汉字名对应起来,再将其与前人的记录、林奈名相联系。只有经过如此广泛的翻译工作,才有可能掌握异国的自然知识,从而将全世界的自然纳入到一个普遍而统一的结构中,加以理解并利用。(68)见Arif Dirlik, “History without a Center? Reflections on Eurocentrism,” Across Cultural Borders: Historiography in Global Perspective, ed. Eckhardt Fuchs and Benedikt Stuchte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247-84,
汉璧礼为了追踪包括果实、种子、根,甚至外壳在内的、每种草药的来源植物,在中国各地的市场上收集了许多草药和植物的名称。从豆蔻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植物的当地名称一方面在当地通讯员与中国人的交流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作为线索,有助于汉璧礼将早期文献中的种种记载串联起来,并与卢雷罗等人曾提出过的林奈式名称挂上钩。因此,每当汉璧礼收到一种从未见过的草药,他便会比较其标本、果实、种子和其他各部分,并参考文字描述和图画材料。一旦他通过比较得出这个标本与任何已知物种不同,便会给它起一个林奈名。
一位19世纪的植物学研究者是否成功,要看他是否很好地完成了不同植物名称之间的多重“翻译”工作。在这种特殊的翻译过程中,最重要、最可靠的参考依据总是实物,亦即标本。尽管汉学家已经十分熟悉植物学主题的文本,却还是不得不经常查阅“中国和日本著作里的植物图”,因为他们必须在缺乏干燥植物标本的情况下将植物名与实物对应起来。 而且所谓“对中国和日本著作中植物学部分的翻译”,实际上是按照林奈命名法鉴定每种植物。(69)Rosny, “Lettre à la SBF,” pp. 236-38.从这个角度来看,19世纪植物学家的翻译工作非常独特。翻译的前期工作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从不同文献中收集文本证据,并将其与收集到的各种名称对应起来;第二步则是将实际标本与之前所有的描述进行比较。最后才是核心的翻译过程——用一个林奈式植物学名替换所有收集到的名字,从而把每一种草药安置在一个普遍的系统中,并用科学家的语言来理解它们。
四、 结 语
19世纪中叶,英国的标本网络逐渐扩展并覆盖了中国全境,最终成为英国中药研究的支柱,使中药脱离了神秘色彩。植物学家将中国植物从本土和文化脉络中抽离出来,将其与来自世界其他角落的标本相比较。于是,中国的枫香与爪哇的枫香被放在一起,在全球联系下它们的身份被重新构建。(70)参见RPS P310和Wellcome, MS 8360, p. 89; Holmes, Catalogue of the Hanbury Herbarium, pp. 25-7.博物学家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将这些分散部分组合在一起的统一框架,为此他们创造了“展柜”——这种新的空间具有新的远近、相邻关系。它使得处在伦敦的观察者对全世界的植物和自然一览无遗,而这种秩序是那些处在世界各处的人从未见过的。(71)[法]布鲁诺·拉图尔著,刘文旋、郑开译:《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383页。参见Drayton, Nature’s Government, p. 25.因此,作为这种新空间的制造者,英国植物学家们的工作实质上是用清晰易懂的分类标准来体系化世界各地的大量标本、名称和信息。
于是,19世纪中叶英国科学家的植物标本室逐渐成为“全球植物大商场”的缩影。植物标本室和林奈命名系统即是统治世界、经营植物产品交易的工具。这种清晰易懂的框架使人们纵览全球海洋、陆地的草药生产、交易网络,而作为商品的植物则以一目了然的科学名称排列。
19世纪英国人的研究实践都围绕着生产“全球知识”这一目标展开。那时的西方自然知识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笔者认为,由欧洲构建出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其精髓即在于“全球性”。尽管罗克斯堡、卢雷罗以及汉璧礼等19世纪欧洲博物学家也搜集并处理植物名,却已不再循规蹈矩地沿着18世纪学者的文献路径前进,而是放下书本,转向世界各地的药材市场展开调查。在这一点上,林奈体系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了横向联结世界的可能性,它扁平而开放的框架与全球化的愿景相吻合。
汉璧礼等英国科学家将异国文化下的材料、植物名、书籍以及观察得来的各种信息纳入到科学的框架之中,再现于他在伦敦的庞大植物标本室内。汉璧礼的草药翻译在“全球贸易”与“普遍的科学结构”等要素节点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将来自广袤自然和漫长过去的所有名字转换并纳入到一个普遍的架构中。这种全面的“翻译”工作,正是在植物标本室和林奈命名系统中积累和排序自然,使人们得以“系统地看待事物”。(72)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2nd edition (Routledge, 2005) 145-46.因此可以说,19世纪英国科学家的具体科研实践是与他们对世界、现代性和科学的思考同步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