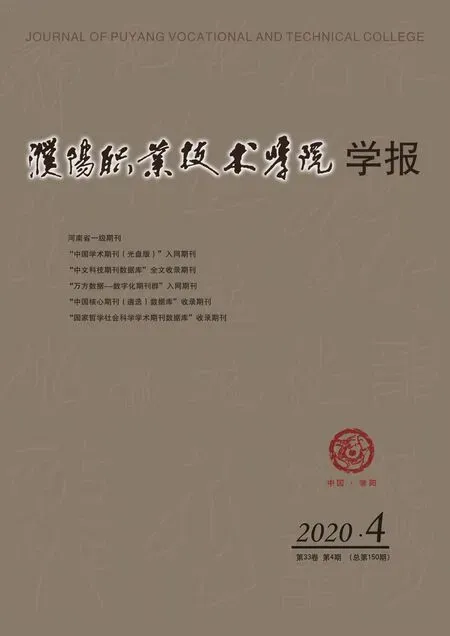土家族摆手舞的历史文脉与生命关怀
罗中玺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贵州 贵阳 551400)
世居在贵州乌江中下游地区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土家的先民巴人离开湖北武落钟离山发祥地,在经历了历史的大起大落之后,一路风尘,其中的一支最终栖息于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的乌江中下游地区。自此,土家族人民在这里生息繁衍,欢歌载舞,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创造了本民族典型的山地文化。如摆手舞、肉莲花、哭嫁歌、薅草锣鼓、打镏子等,其中摆手舞是土家族最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之一,它与土家语言、土家织锦(西兰卡普)三者共同构成了土家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志,是研究土家民族的“活化石”。
一、土家族摆手舞的历史文脉
摆手舞,为土家族祭祀祈求先祖神灵的一种舞蹈样式。整个舞蹈过程一般由土老司“梯玛”主持掌坛。在土家族人的观念中,梯玛是能够沟通人、鬼、神之间的神巫。摆手活动是一个请神—敬神—送神的祭祀过程,而此过程都必须贯穿摆手舞。那么,摆手舞是如何产生的呢?它的产生有什么样的历史文脉?
每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关。据零星的文字记载与民间传说,土家族摆手舞或为表现古代战争的“马前舞”,或为狩猎生活的“打猎舞”,或为农业生产的“农事舞”,其文化意象均带有楚巫巴舞的特点,是巴楚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的结果。
巴楚文化,即巴和楚的文化,其特征首先表现为“地域内的重合交叉”及“文化内核中的深层融合”[1](23)。乌江中下游地区位于贵州东北角,地处黔、渝、湘、鄂四省(市)边区结合部,历来为巴楚文化的交融之地。作为民族民间歌舞文化,土家族摆手舞历史悠久,在其时空框架中,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变化,必然留下巴楚文化交融的深深烙印,同时也表现为“民族间的联姻通婚”致使“习俗上的涵化混同”。从相关资料得知,最迟从楚共王 (前601年—前560年)始,巴族与楚族就已然通婚。由此可以断言,无论在巴文化和楚文化中,由于两族之间的相互联姻,其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必然具有杂交型文化(cross culture)或混融型文化的成分。为了加深对土家族摆手舞历史文脉的进一步理解,有必要对巴文化和楚文化作一番历史介绍。
(一)巴人尚歌舞,敬白虎
据史料记载,约4000多年前,一支骁勇浪漫、能歌善舞的远古族系生活在今长江流域渝、鄂、川广大地区,被称作巴人。《华阳国志》云:“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讨伐,前歌后舞’。 ”[2](21)可以想象,当年巴人“龙贲”军气势雄壮,声威凌人,在参与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牧野之战中,在独特的战舞中,迫使纣王军队阵前倒戈,推翻了商朝。秦朝末期,四川阆中巴人领袖范目率七姓帮助汉高祖“还定三秦”,在激烈的战争中,巴人歌舞亦起了重要作用。史籍载:“阆中有渝水,賨人(为巴族的一支)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阵)。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2](37)巴人将这种战争舞蹈命之为“巴渝舞”而引进宫廷,后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虽曾数易其名,仍盛演不衰。唐以后,“巴渝舞”虽在宫庭中逐渐消失,但在民间仍在世代传承,历经演变,原始的武舞演变成祭祀性或庆典性舞蹈。土家族是巴人的后裔,其祖先巴人被中原华夏民族先后称为“廪君蛮”“板楯蛮”“武陵蛮”“五溪蛮”等。传说巴民先祖廪君(即巴氏务相)死后魂魄化为白虎,故巴人崇拜白虎,以白虎为图腾。为此,巴人又被称为“白虎夷”“巴氏虎子”等。据史料载,因巴人助武王克殷有功,在西周 (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初期分封的71个诸侯国中,“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2](21)。 巴氏由此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巴子,因而叫巴子国,简称巴国。公元前316年,巴国为秦国所灭,巴王被虏。其有兄弟五人,为避秦害,流入五溪。其中一支以巴子酋为首,部族百余人由今之涪陵溯乌江而上,向酉溪开进。就这样,巴人开始在武陵山区这片混沌未开的蛮荒之地筚路蓝缕,开启山林,重建家园,经过民族繁衍,其子嗣如今遍布在乌江中下游重庆酉阳、秀山及贵州思南、沿河、印江一带。
可见,土家族从族源来看,与古代巴人存在着天然的血脉关系,而巴人尚歌舞的民族基因也被土家族承续了下来。公元940年,土家族统治者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在溪州(今湖南永顺)结盟铸铜柱为记。今永顺城郊存石刻古诗云:“千秋铜柱壮边陲,旧姓流传十八司。相约新年同摆手,春风先到土王祠。”可见,摆手舞历史悠久,并成为了年节喜庆、祭祀祖先所必须举行的民俗活动。
(二)楚人巫风盛行,以凤为图腾
最初的人类为什么要跳舞,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比如巫术说、游戏说、劳动说、宗教祭祀说等。其中,影响最大的为巫术说,这也是西方学者关于艺术起源的一种很有影响的理论。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中提出:“野蛮人的世界观就是给一切现象凭空加上无所不在的人格化的神灵的任性的作用……古代的野蛮人让这些幻想塞满自己的住宅,周围的环境,广大的地面和天空。”[3](131)由此看来,巫术是产生于原始社会的一种“万物有灵”的文化形态。为了求得神灵的护佑,谋求较好的生存环境,人们幻想与神灵沟通、对话,而沟通人神的使命,又似乎非舞蹈莫能,因为舞蹈的物质外壳就是人类自身,人是生物界中的智者和灵者,是“万物有灵”中最合宜不过的灵魂符号与生命载体。舞蹈就是试图通过这种符号和载体以无声的肢体语言来实现同那些无形的神灵进行接触、交流、对话的目的。人们相信,在这种既娱神又娱人的境界中,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就能够彼此联通,相互理解,所以,先民总是用舞蹈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按照这种观点,土家族摆手舞作为舞蹈大花园中的表现形态之一,自然与原始社会时期的巫术有关了。确切地说,它与楚巫文化有着极大的关系。
楚国先民原生活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黄帝时期。《史记·楚世家》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楚人先祖重黎,在帝喾任部落联盟首领的时候,担任“火正”官,被尊为“祝融”。由此,楚国先民所建立的部落后称之为“祝融部落”。夏商时期,为逃避中原战乱,“祝融部落”历经了数百年,迁徙至淮水以南的汉水流域和荆山地区,与当地的百越、百濮、东夷等土著部落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即商周文献中谓之的“荆”“楚”或是“荆蛮”。 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和繁衍,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地盘的极度扩展,在西周时期,楚最终发展成为位居我国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带的一个经济雄厚、文化独特的诸侯强国。楚人南下时,将所携带的中原殷商文化因子与南方楚蛮的屈家岭土著文化因子相结合,由此便具有了十分复杂的文化因素,成为一种相互杂糅而又独具特色的“泛楚文化”。不过相对于楚文化而言,屈家岭蛮夷文化色彩则更为浓厚,如“礼教意识淡薄,鬼神观念浓厚等”[4](171)。春秋战国时期,当中原地区的神话文化或者宗教文化已经被消解,开始向着理性化、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时,生活在楚地的人们还在对着他们笃信的自然神祇虔诚地祈祷并存在了几千年,土家族的摆手舞便就是其中的文化痕迹。
楚地这种巫风盛行的现象不仅在《楚辞》《汉赋》等诸多文学著作中有所表现,同时,也大量存在于古人的典籍之中,如班固《汉书·地理志》:“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朱熹《楚辞集注》:“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王夫之《楚辞通释》:“巫咸,神巫之通称。楚俗尚鬼,巫咸降神,神附于巫而传语焉。”
楚人好巫由来已久。传说中的楚人先祖祝融就是中国原始社会巫的代表。“巫,祝也”,故祝融即为巫融,有光融天下大巫之意。历代楚王大都兼有巫长职能,如楚昭王芈熊轸,楚灵王芈熊虔、楚怀王芈熊槐等均为有名的巫长。所以在楚国,从事巫师的人无论大小都有着显要的地位,如楚昭王(约前523年~前489年)时的楚大夫观射父,就因通晓宗教礼仪,并“能作顺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而受到昭王的重用。昭王有不明了的天地之事,都要向观射父咨询,观射父因此被誉为“楚之所宝者”,即视为楚国的国宝。生活在楚怀王(?―前296年)时期的诗人屈原在《楚辞·离骚》中亦自称为楚巫,并自述生辰“惟庚寅吾以降”,“庚寅”日为楚族始祖祝融重黎被帝喾诛杀的日子。屈原自称生于庚寅日,是否有“祝融转世”的思想已无可知晓,但庚寅日在楚人的观念中是为神圣的日子,谓之太阳庆、光明日,在这天诞生的人具有高贵不凡的内质秉性,适合为巫。《淮南子》注曰:“巫成知天道,明吉凶。”即巫为人神之媒介,通过取悦神之舞蹈,将神的旨意告诉人,将人的祈求禀告神。后来人们发现巫的跳神舞蹈动作还可使人快乐,巫风最浓的楚国便产生了对舞蹈形式美的自觉追求[1](52)。由此可见,在历史上,巫文化是楚文化甚至是长江流域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
从一定意义而言,巫文化是一种泛神文化,浓烈的巫风培养了楚人对于神灵顶礼膜拜的虔诚情感和“飞登九天、周游八极”的非理性的浪漫主义幻想,这也是楚人心中所向往的自由而又美好的境界。因此,在这种思想意识的影响下,楚文化中,又包含了富有浓郁巫术色彩的“凤鸟”崇拜。时至今日,在荆楚之地湖北仍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说法。
(三)土家族摆手舞是楚巫与巴舞及多元文化的混合体
关于土家族摆手舞的起源和历史演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源于巴人原始舞蹈、源于民间传说、源于原始祭祀的巫舞、源于巴楚文化的交融等观点。这些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彼此孤立或硬性地将它们撕裂、割开。事实上,任何一种民族民间文化事象的产生,其构成的因素是多方面而又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因此,我们在考察土家族摆手舞的历史渊源中,应该有一个完整、全面、综合的态度。
尽管土家摆手舞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变化,已成为集歌、舞、巫(祭祀)、社交、体育、物流为一体的群众性集体舞蹈,但从其内容和表现形态来看,仍明显地具有巴、楚文化交融的痕迹。除此之外,土家族摆手舞还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从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以来,随着“湖广填四川”的几次大移民,加之土家族与世居在乌江流域的苗族、侗族、仡佬族等长期相处、相交,使得土家族文化又渗入了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的许多因子,表现在摆手舞中,其祭祀主体由过去的单纯的土王崇拜演化而为多神崇拜以及宗族宗教敬仰;其舞蹈形式由过去的大摆手(战前舞)派生出小摆手,即在宗祠前举行。这些现象说明,土家摆手舞是一种以巴楚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相互交织而衍生出的具有民族及地方特色的民间舞蹈艺术形式。
二、土家族摆手舞的敬祖生殖崇拜
民间舞蹈(folk dance)是人类与生俱来,用肢体语言抒发人们深刻、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诸如古代先民的狩猎生活、战争经历、图腾信仰及生殖崇拜等社会生活及民族精神面貌的艺术形式。它起源于人类劳动,具有强烈的社会、宗教、文化功能。
(一)祖先崇拜——思时之敬
敬祖,源于原始让会“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的母系氏族时代,是基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鬼魂崇拜与血缘关系结合的产物。按照表现形式、内容及产生的时序,土家族的敬祖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在土司制度时期得到了发展,至“改土归流”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因而其内涵深邃丰富,形式繁杂多样,表现出浓郁的原始情调和民族气息。土家族敬祖包括对女神、对远祖、对家先的祭祀活动等。
敬女神。与世界许多民族一样,土家族古代先民在追寻宇宙的来历和思考人类起源的种种问题时,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形象就折射出土家族对人类思考与探索的轨迹。在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一直流传着关于诸多女神的故事,如始祖女神卵玉娘娘、佘婆、春巴妈帕等;生产女神梅山女猎人、火畲神婆、五谷娘娘、西朗卡普等;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卵玉娘娘、春巴妈帕是生殖女神外,土家族的生殖女神还有咿罗娘娘、阿米麻妈、雍妮等[5](10-11)。 女神是土家族崇拜的最原始的神灵,反映着人类在母系氏族时期寻找生命之源的文化困惑以及对生命的敬畏和惧怕心理,从而形成母祖崇拜。
敬远祖。从土家族敬祖的发展轨迹来看,虽然最早产生的是对诸多始祖女神的崇拜和祭祀,但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对“八部大神”、向王天子、大二三神、土王神、“社巴神”等远祖神灵的崇拜,他们多为氏族、部落的男性首领。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父系氏族逐渐代替了母系氏族,诸位始祖女神逐渐沦为远祖男神的附庸,是在男神统治之下的专司某职的神灵。
敬家先。即对本家庭、本宗族祖先神灵的祭祀。“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的敬祖习俗中,只祭祀始祖神灵和氏族、部落祖先神灵,无祭祀家先神灵的习俗,“改土归流”以后,由于汉文化及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冲击和交融,土家族的敬祖已由过去单一的始祖神灵和氏族、部落祖先神灵祭祀逐渐转变为家庭、宗族先祖神灵祭祀。如在黔东北土家族乡村,每户人家的堂屋正面板壁上写有香火,正中书写“天地君亲师”或“天地国亲师”,两侧为本堂“历代祖先”及“九天司命太乙君”“观音大士”“神农黄帝”“四官大神”等诸神之灵位,这种多神杂然相列的情况,显然糅杂了儒、释、道等思想。由于土家族人长期生活在高山深谷中,其自然屏障,使土家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时,也保留了自己民族大量的原始宗教信仰习俗。比如,在土家族“祭祖还愿”的傩堂戏中,所祭主神是作为民族始祖的“傩神”“坛神”等,而儒、释、道三教的尊神们仅作为陪祭对象,而在影响最大的祖先祭祀仪式“摆手祭祖”活动中,则完全是土家族自己的祖先神灵。同时,也由于高山峡谷的地理面貌,给各地土家人之间的交往带来不便,从而使居于不同区域的土家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以土家族历史文脉为基础,结合各自的政治领袖或领主因素,而呈现出各自相对独立的宗教文化形态,其地域特征十分明显。体现在敬祖习俗上,武陵山脉酉水流域的土家人多信奉“八部大神”“彭公爵主”,驱赶白虎,流行“摆手”;大巴山脉清江流域的土家人则信奉“向王天子”,崇敬白虎、土王,流行“跳丧”;湘西是供奉彭公爵主,向老倌人,田大汉;鄂西是敬覃、田、向三位“土王”;渝东南主要是祭祀冉、杨、田三位“土王”;而黔东北土家族的敬祖又似乎对上面的习俗兼而有之。
摆手舞是土家族作为族祭的形式而出现的,在表演的过程中,始终围绕敬祖这个中心来展开。如《旧唐书·刘禹锡传》:“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永顺宣慰司志》:“古设庙以祀八部大神。每年正月初一,巫祀试白水牛,以祈一年休祥。”据《永顺府志》,土人“四月十八、七月十五夜祀祖,又祭婆婆庙。六月中,炊新米,宰牲,亦曰祭鬼。九月九日,合寨宰牲祀重阳,以报土功。十二月二十八日夜祭祖,亦曰祭鬼,禁闻猫犬声”。《古丈坪厅志·民族下》:“土俗,各寨有摆手堂,每岁正月初三至初五、六夜,鸣锣击鼓,男女聚集,摇摆发喊,名曰摆手,以祓不祥……惟人死不用僧道,只用土老师作法,神为旧宣慰社把,如彭王、田大汉、向老倌入云。”
摆手舞分为大摆、小摆两种。“大摆”场面气势恢宏,以祭“八部大神”为主,表现开天辟地、人类繁衍、民族迁徙、神话传说、古代战争等,整个舞蹈,气象万千,动人心魄。“小摆”规模较小,以祭彭公爵主、向王天子、大二三神、土王神为主,表现狩猎捕鱼、桑蚕纺织、刀耕火种等农事生产活动以及饮食起居日常生活等。总之,土家族摆手舞粗犷古朴,生动形象,节奏强烈,以双手摆动为特色,以史诗般的结构和炽热的色彩,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幅气势磅礴的土家敬祖画卷和风情浓郁的土家生活画卷。
(二)祭祖求福——繁衍生息
从本质上而言,土家人各种类型的敬祖仪式其终极目的在于祈降福祉与禳除灾祸,这也是贯穿于任何一个民族宗教信仰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功利性特征。清道光《思南府志》载:“祈禳,各以其事祷神,逮如愿则报之,有以牲醴酬者,有以彩戏酬者……傩亦间举,皆古方相逐疫遗意……期以邀福。”而其中“人丁的兴旺”是所有祈福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因为,它涉及到维系家世、繁衍亲族、聚合民族等最直接的利益和根本保障。在这种直接利益的支配下,土家族的敬祖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性与功利性,即通过祈福禳灾以求子嗣,就成为土家人祭祀祖先的重要目的和终极目的,从而也产生了生殖崇拜。作为祭祖仪式之一的土家族摆手舞,就表现了这样的“生殖”主题。
如果我们避开种种历史的因素,仅从艺术探源的角度出发,土家摆手舞无疑是在土家最古朴的民族舞蹈“毛古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事实上,在今天土家族摆手舞的演出中,已穿插了“毛古斯”的舞蹈表演,二者已融为一体。
在过去,土家人在演出“毛古斯”舞之前,一般都要到附近的一个很深的山洞里去烧香祭奠一番,然后用瓜瓢舀一碗井水出洞,供上神桌。我们知道,洞穴是早期人群的生存繁衍之所,与女阴相似,而洞中的水又似女人的经水,具有相似律思维头脑的原始初民,必然将它与女阴和经水相提并论,并赋予其与女阴同等的生殖力量。毛古斯从洞中出来,就是象征着土家族先民从母腹中诞生。当然,土家族人之所以祭祀山洞,是在其特定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土家人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乌江中下游地区,处于喀斯特地质带,这里悬岩嵯峨、岗谷相间、溶洞连连。在这种地理环境中,土家人所崇拜的祖先神灵自然与山和洞纠结在一起,如“八部大神”威镇八峒,“向王天子”发祥于山中洞穴[6](7),各种祖先神灵植根于山洞之中,依山洞而生存,据山洞而生威。
如果说祭祀山洞,从形象而言,反映了土家族对女阴崇拜的话,那么,在“毛古斯”的正式演出中,则又体现了对男根的崇拜。在“毛古斯”的舞蹈阵容中,有老“毛古斯”和若干小“毛古斯”,他们穿着用树叶或稻草做成的衣服,头戴草帽,下垂五根辫子,腰上捆一根草扎的粗鲁棒,象征男性生殖器,头下用红布包着,据说这是象征交媾、繁衍。跳舞时双手捧着男根,或左右摇摆,或前后跳跃……“毛古斯”舞蹈虽然是表现土家人狩猎的生活图景。但其中的祭祀以及表现出来的舞蹈语言印记着土家族先民从母系社会的女阴崇拜到父系社会的男根崇拜这一演化的历史遗痕。事实上,以类似山洞和粗鲁棒这种自然物来象征女阴或男根,并加以崇拜,是我国各地民族民间中最为原始最为普遍的现象。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说:“在讨论象征型艺术时我们早已提到,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的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更具体地说,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7](49)黑格尔可谓是一个看清楚了东方性文化的西方学者。
在土家族生息的乌江中下游地带,冷藏和积淀着土家族古老而又丰厚的文化信息,在土家族古老文化的遗存中,摆手舞无疑是土家族古老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异的民族风格色彩。千百年来,生活在乌江中下游的土家族也正是通过摆手舞和其他巫歌傩舞艺术形式潜化和孕育并培养着这个民族的气质与性格。随着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土家族摆手舞的内容不断丰富,从原始的渔猎活动到刀耕火种的“砍火畲”“撒小米”,从“挖土”“种苞谷”的旱地生产再到“插秧”“打谷”的水田耕作,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到体育、社交、经贸以及男女爱恋等各种社会活动等,展现了土家族从启蒙渐步走向现代文明的生产发展史。同时,在功能上,土家摆手舞也逐渐从重祠祀、敬祖神以及通过各种巫术祭祀行为以达祈降福祉与禳除灾祸的目的,逐渐成为以审美方式追求精神性、娱乐性为主的大型民族民间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