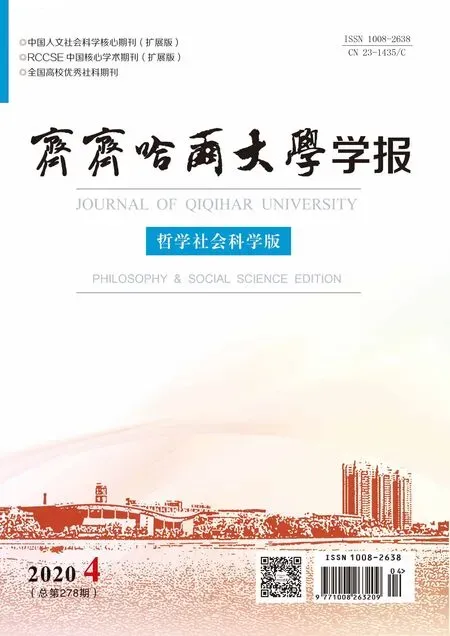张养浩怀古散曲的书写模式、情感内涵和文学价值
雷晶晶,宫臻祥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张养浩不仅是元代庙堂之名臣,也是元代文坛之作手。元代特殊的政治生态和张养浩的人格思想不仅直接影响其仕隐选择,亦深刻影响其散曲的创作内容和情感基调。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饥民相食。”[1]张养浩时年六十,“特拜陕西行台中丞”,[1]在西行进陕途中,他从洛阳至咸阳写下九首怀古散曲,这九首怀古散曲不仅描写了特定地域的文化景观,深刻体现了文学景观与文学创作互动的双向关系——文学创作是促进文学景观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文学景观一旦形成后又为新的文学创作开辟书写空间,进一步丰富文学景观的内涵,进一步革新文学书写的内容;而且反映了张养浩在特定时期的人生体验和散曲风格——张养浩在仕、隐之后,再度出仕,加之该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其心境自然较以往士大夫文人有所不同,张养浩复杂的思想和情绪在这组散曲中可见一斑,因而这九首散曲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本文拟审视特定地理时空对散曲创作内容和形式的影响,分析九首怀古组曲的艺术特征和文学价值,并观照这九首怀古散曲背后所反映出的张养浩特定时期内的特殊心境及心路历程。
一、张养浩怀古组曲的书写模式及时空结构
天历二年(1329),张养浩西行进陕济灾,道途所至,各作散曲,共计九首,分别是《洛阳怀古》、《北邙山怀古》、《渑池怀古》二首、《潼关怀古》、《骊山怀古》二首、《未央怀古》和《咸阳怀古》。这组怀古散曲的共通之处是在同一曲调下——“山坡羊”,作者对不同地域的历史时空古今之变的书写,贯穿着相类的情感内涵。在这组怀古曲中,作者移步换景,在经行途中,地域空间作为契机,作为起兴感怀的触媒,作为辅助情感抒发的载体,具有了重要作用。
在《洛阳怀古》中,作者站在九朝古都洛阳的“天津桥”(人文环境)上,看着滚滚洛水向东一去不返,逝者如斯,洛水的客观流向引发张养浩对时间飞逝不还而叹惋的主观感慨,洛水波涛的卷伏涌起暗合着发生在历史长河中的人事起伏。在诸多历史场景中,作者选取“春陵王气”这一文学景观作为咏怀对象。“春陵王气”原是说洛水两岸葱郁的嘉木曾经作为天子出现的预兆,于此地迎来了汉光武帝刘秀的天子之兆。在张养浩的《洛阳怀古》中,曾经“树苍苍、水茫茫”的“春陵”依旧,而汉光武帝及辅佐其建国的文臣武将,亦即“王气”都“不见”,皆已“凋丧”。洛阳这一权力中心的古今之变通过“春陵王气”的盛衰生动地反映了出来。《洛阳怀古》中,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互相观照,洛水不变的东逝与洛阳变化的人事激发了作者对历史兴亡的感喟,即人物对权力的追逐最终导致权力尽将人物吞没。自然地理的客观性质和形态(“春陵王气”的物质基础)契合了作者主观情思表达的需要,打开了作者的写作思路,同时作者于此地获得的主观体验又增加了自然空间的情感及文化内涵。地域空间与散曲创作相互影响,构成了怀古组曲的基本书写模式,即:
地域空间性状的变化比照地域空间内部人文历史的变迁激发怀古内容的创设。
在《北邙山怀古》中,自然空间的“风”、“烟”、“尘”连同人文空间的“残碑断铭”一道构成激发作者怀古情思的要素;两首《渑池怀古》散曲中的“秦赵渑池相会”(地理事象)一事,《潼关怀古》中的“山峦”、“波涛”(自然环境)和“西都”、“宫阙”(人文环境),《骊山怀古》中的“骊山”、“汤泉”、“草”、“树”(自然环境)及历史空间内的“阿房一炬”(地理事象),《未央怀古》中的“遗基”、“山河”及谏言的“三杰”,以及《咸阳怀古》中的“城池”与隋唐易代,多以此笔法写出,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角逐在这组“山坡羊”中显示出了它们的合力及魅力,也构成了“山坡羊”的基本时空结构和鲜明的时空结构特点。
文学作品中的世界是经过心灵改塑的主观世界,其时间与空间的组合、转化不仅构建了文学作品本身独特的风格,形成作品独特的个性生命,同时也是作者情思内蕴与心灵空间的渐次展开,显现出作者诗性思维的链接过程,“这种客观空间存在通过抒情主体心灵的折射,成为词作中的生命时空形式”,[2]80形象表达着作家的艺术人格结构。
张养浩九首怀古散曲有着相类的时空结构,即相同空间内,时间的非线性变化,具体表现为“今——昔——今”的结构模式,时间转换的跨越性与空间转换的联想性,是这组怀古散曲中时空结构的基本特点。
在《洛阳怀古》中,“凭栏遥望”四字点出了古今时空的错织,于历史遗迹上(现今、此地)追想当年历史风光(往昔、此地),“春陵王气”是作者联想往昔的主要内容。紧接着,作者的思绪又跳回现实,尽管“天苍苍、水茫茫”的自然空间依旧,然而人文空间内的王气已然凋丧,今昔空间状态的对比,牵引出作者对人事在历史迅速的变迁中所产生的虚无与失落感。《北邙山怀古》亦是相似的时空笔法。由现今的风烟与碑铭联想过往帝王将相的雄姿伟业,转而又跳跃到当下残缺碑铭对曾经风云际会的消解,发出死去皆空的人生感叹。《潼关怀古》中,由此际河山、西都联想至既往秦汉宫阙,又迅速回转至繁华消亡的当下,感喟兴衰背后恒久的悲哀。《骊山怀古》、《咸阳怀古》同样从当下破败空寂的自然空间,引申至其奢侈华贵的过往,展眼又嗟叹现下之颓败萧索。同一空间内,时间的流转改变了空间的面貌,现今与往昔的对比为情感的抒发和思想的表达不断蓄势,并自然强化了作家此际的情感倾向,产生动摇人心的力量。
值得指出的是,在《渑池怀古》和《未央怀古》中,作者采取了另一种时空结构,即按照自然时间的先后顺序,采取线性结构方式,写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认识评价和情感态度。《渑池怀古》中,直接指出秦赵之对比,蔺相如之事迹,继而发出作者的意见,《未央怀古》中,也是首先指出“汉初三杰”的风姿及事迹,进而观照现实,发出感叹。直切与地域紧密相关的人物,直击怀古内容的关键,由昔至今,今昔相较,空间内部的核心要素,即人物的流逝,使得整个空间变得空洞,这便是引发作者喟叹的直接因由。
时间意识的产生意味着人类对天地万象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认识和把握;意味着人类脱离了混沌迷茫的状态,并由此开始了向内的自身体验。“时间意识一头连着宇宙意识, 一头连着生命意识。”[3]214在张养浩怀古组曲中,时间意识呈现出鲜明的主观性、内倾性。客观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内容在作者的主观筛取下,表现出对时间的感伤和超越,这种感伤和超越是“山坡羊”的情感基调。
二、张养浩怀古组曲的情感侧重
自然的恒常与历史的无常牵引出物是人非的沧桑与空幻,然而,这九首散曲在各自的书写中,由于地理空间性状和人文历史积淀的差异,作者怀古的具体情感内涵亦各有侧重。总体上可以将九首散曲中的具体情感分为以下几类:
(一)感朝代兴亡的无差别
以感朝代兴亡无常为主要情感内容的散曲分别是《洛阳怀古》、《北邙山怀古》、《骊山怀古》和《咸阳怀古》。散曲中的这些地域都是曾经皇权、政治中心的象征地。其中,洛阳是九朝古都自不必说。三百米高的北邙山上有六个朝代、二十四位帝王长眠于此,骊山自周、秦、汉、唐以来,一直作为皇家园林地,秦始皇的陵寝就建在骊山脚下。咸阳是秦朝古都,因其毗邻长安,而被当做京畿之地和茔藏之野,分布着八百余座帝王及王侯将相的陵墓。生死兴亡在这片土地上一遍遍上演:开国的君王、建功的将相、奢靡的宫殿都在历史长河中被冲刷,留下的是残缺的碑铭、朽坏的城池、枯败的野草与纷乱的荆棘。逝者长已已,带给张氏的却是功名不久长、威权如云烟、繁华难驻、世态变改的无常感。以《北邙山怀古》表达得更为真切,其原文如下:
悲风成阵,荒烟埋恨,碑铭残缺应难认。知他是汉朝君,晋朝臣? 把风云庆会消磨尽,都做北邙山下尘。便是君,也唤不应;便是臣,也唤不应!
尘埃的无差别泯灭了君臣之间的森严的等级,暗喻着死亡的降临终结现世的所有生存秩序。死亡终会降临,历史上曾经为功名富贵而绞尽脑汁,乃至拼送性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不由得引起作者的思考。在《北邙山怀古》中,作者激愤地表现了历史的机械式的循坏这种无差别,为元朝现有的黑暗政治倾轧敲响了警钟。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以上四首怀古散曲再次较为鲜明地体现了有着历史积淀的地理空间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这些象征着皇权的空间,激起了作者对历史运行轨迹的回顾与反思,触发其对朝代兴亡、世事无常的感叹。由于特定空间内蕴含着具体的历史内容,所抒之情便有了附丽,在描写叙述的推进中产生了真切动人的力量。
(二)叹英雄人物的失落感
《渑池怀古》二首、《未央怀古》这三首散曲,以感怀渑池和未央两地上人物的事迹为主要内容。渑池曾是秦国为牵制赵国,又欲加羞辱赵惠文王、强取赵国城池之地,蔺相如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使秦国毫无所得,并舍命护国威,保护了赵王安全,保全了赵国尊严。作者行至此地,自然引起了对该地上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迹和历史人物的追思,在秦强赵弱鲜明的国力对照下,在秦凶赵怯分明的性情比较下,蔺相如能够于险象环生的渑池之会中以一己之力对抗强秦,必然充满了九死一生的惊险。作者站在历史的另一端,重新审度蔺相如的行为,并发出自己的评价。面对强敌和弱国,渑池之会中蔺相如的选择过于“粗疏”和“血气”,倘有闪失,便是万劫不复。对于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负面评价反映出张养浩对英雄的怜惜及其特殊的颓势心境。《未央怀古》中,对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立功立言的追慕,表达山河依旧,而英雄难觅的沧桑与失落,从中见出作者悲英雄失途,叹豪侠难求的思想感情,流露出作者对时政的不满与自我身世的伤悲。
作为空间内部的核心要素——人物,予其叙写能够最大程度上反映作者对史实的基本认知和情感态度。不论是《渑池怀古》中对蔺相如否定性的特写,还是《未央怀古》中对英雄们肯定性的泛写,以比照突出现世英雄的没落,都表达着英雄人物难于找到恰当的位置、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和历史使命,都与作者当下所处的政治生态和特殊心理有着紧密的关系。
(三)念生民疾苦的深重性
《潼关怀古》集中表现了作家对阶级对立和人民处境的清醒认识。潼关“壮观险峻特质、地理形势范围、作为关隘之功能”[4]12历来都使其与政治军事紧密关合在一起,这方关口也见证了波澜起伏的历史演变,潼关在此更多地被当做人文空间进行叙写。此时的潼关,在见证又一个生灵涂炭的时刻,一场天灾人祸的饥荒,使得作者眼中现下的潼关带上了“怒”的情感特质。“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5]105秦汉的兴荣和衰败都过去了,然而兴亡之后的代价,是百姓恒常的苦难。兴盛之际,统治者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粉饰太平;败落之时,兵荒马乱,狼烟四起,百姓或无奈疆场厮杀,或被迫流离失所,繁华安定与衰微动荡对于百姓来讲实无二致,他们永远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对象。秦汉易代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统治者出现在与人民对立的政治舞台,继续进行着压榨与剥削的政治角色。张养浩对历史与现实的清醒认识和生动表达,使得整个散曲中激荡着历史的教训与对生民的深切同情。
“伤心秦汉经行处”,当作者看到因旱灾而“饥民相食”的场景,张养浩从因自然灾害导致生民悲惨至此,联想到人为的杀伐对百姓生活、生命的巨大破坏,进而揭示出统治者与百姓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渗透着作者对历史与社会的深刻认知与深沉感慨。
在这组怀古散曲中,即景、言事或说理都是辅助作者抒发感情和表达思想的手段和载体,作者采取对比否定或例证肯定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对历史兴亡的无差别的认识、英雄人物难施才干的叹惋和对生民被压迫灾难深重的悲鸣不仅反映出作家的认识、情感和态度,同时也关合着特定历史时期文人士大夫群体的特殊心境和思想情怀。
三、张养浩怀古组曲的文学价值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237对历史的感怀往往包含着现实的动因。“人们观照历史、吟咏古人,不可避免地会以时代价值取向来评判古人的功过是非,以时代需求导向来弘扬、放大某些特质,同时隐藏、缩小另一些特质,重新对古人进行解读、重构甚至曲解,最终完成的形象虽脱胎于历史,却有着深刻的现实精神的烙印,染上了浓重的时代色彩,并为实现寄托集体理想、干预现实生活的功用服务。”[7]14这即是说,怀古在披上历史的外衣后,重心和实质仍在当下。张养浩怀古组曲不仅是个人特殊心境和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文人群体心态和信念的表征。
(一)用尽为民为国心的表征
延祐七年(1320)张养浩因上疏英宗硕德八剌勿以元夕张灯若鳌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1]而“犯颜撄鳞”,致使“帝大怒”。至治元年(1321)“以父老,弃官归养”而退隐。元代统治者的荒淫暴虐致使仕人心中儒家思想的圣殿骤然崩塌,连同仕人自身的生存亦受到极大威胁。对朝廷的彻底失望是张养浩在朝廷先后七次征聘而始终不起根本原因。然“及闻西土凶荒,一命即驾,出币发粟,全活生灵,不知纪极,斯其胸中所蕴。”[1]天历二年(1329),时隔八载六十岁的张养浩以进陕赈灾再度出仕,即此说明儒者为民之风范。张养浩摒弃贪权谋利之私心,仕隐之间以生民疾苦为权衡。西行道上的九首怀古散曲,再次表明了儒者张养浩的为民为国心。
在两首《骊山怀古》中,对秦国奢靡享乐的讽刺,“当时奢侈今何处”,正是对元代统治者的讽谏。历史已经表明,贪图享乐、苛政暴虐的王朝是短命的,即使生前铸造了“汉铭唐碑”这样的重器,仍不及“尧舜土阶”,“生,人赞美;亡,人赞美”,作者旗帜鲜明地反对穷奢极欲,并把人民的反应作为评价历史功过的标准。“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8]189尧舜施仁政,故民赞美之,而历史上施行暴政的王朝,早已堙没在衰草枯杨、断碑残铭中。张养浩思想的锐利使得《骊山怀古》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鲜明的人民性。“尧舜土阶君莫鄙。生,人赞美;亡,人赞美”与现代著名诗人臧克家名篇《有的人》中的“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9]241“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10]242神脉相通,如出一辙。然未经革命洗礼,早在三百年前,张养浩即能有此识见,足证《骊山怀古》的思想价值。
在《潼关怀古》中,张养浩更是彻底揭露封建社会统治中的一组基本矛盾关系,统治者和“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深刻冷峻地揭示了长期被粉饰美化的统治背后,统治者残酷虚伪的真实面目和百姓永远苦难的生存状态。“他是站在广大被压迫者的立场与角度进行换位思考,并且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规律作了本质的把握后得出的深刻结论,具有惊世骇俗的重大文化意义和可贵的精神关怀的价值。”[9]55故此,《潼关怀古》能够突破地域限制、突破历代怀古慨发一己哀乐之窠臼,而成为情感激越、鞭辟入里的千古警语、隽语。
诚如曾大兴所言,“地域性只能体现作品的地域特色,普遍性才能体现作品的广度、深度和高度。”[11]348这九首散曲虽是张养浩在特定的地理事象、地理物象的激发下写出,而作家本人的生命意识却能够超越一时一地之限制,其以仁者情怀、儒者视角观照历史和现实,在元代黑暗暴政之下与百姓同历苦难,深刻真实地道出历史发展之本质,深情真诚地倾诉百姓悲惨之处境,以上品质使得张养浩的怀古散曲站立元代曲界巅峰,具有永恒的文学价值。
(二)特定历史时期士大夫文人心态的曲折反映
尽管张养浩有爱民治乱之志,然而时代的重负之下,儒者宏伟的心愿和高洁的操守,面对朝局的崩坏和灾情的肆虐,充满了济世的无力感和历史的幻灭感,这是特殊历史时期文人的真实心态。张养浩是真实的,其散曲是真实心境的自然流露,他写出了一个时代文人的特殊感触和心绪,即历史的幻灭感和人生的无力感。
历史的幻灭感在张养浩九首怀古散曲中俯拾即是。《洛阳怀古》中的“千古转头归灭亡”,是非成败转头空,所有现存的一切注定了都是要灭亡的,回首历史,兴亡乱治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咸阳怀古》中的“世态有如云变改”再次强调既往历史的瞬息万变与不可把捉。《北邙山怀古》中的“都做北邙山下尘”写出历史最终的走向,化为随风游走、不具辨识的尘埃。轰轰烈烈亦或畏畏缩缩,光明磊落亦或阴暗卑鄙,所有曾经相关或不相关、对立或不对立的,都无差别地一同消逝在历史的尘埃里。波澜起伏的历史过程并非是作者所咏怀的主要内容,反倒是无数个起落沉浮的历史发展特征成为了作者所关注的主要对象,这是张养浩的这九首怀古散曲不同于其他时代文人作品之处。因而张养浩在两首《渑池怀古》中,对蔺相如以命相搏、力护国威的行为作出了“动粗豪”、“太粗疏”等否定性评价,其根源在于元代暴政致使传统儒家忠君爱国、建功立业思想根基崩塌。
继历史的虚无感之后的是人生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是从观照历史的兴亡无常中得来的,人事的微茫,人力的渺小在怀古散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曾经的宏图远志、王霸基业、煊赫声名都在时间的洪流里倏然而逝。生前无尽的尊贵,而今连刻印着王师将相丰姿伟态的石刻都被岁月销蚀,矮小的北邙山下,断碑颓铭随着无尽的风沙也渐渐归于尘土。人的意志、人的力量在时光面前微不足道,不堪一击。这种无力感联系张养浩散曲创作的背景主要表现在生活的残酷和时间的无情上。其一,生活的残酷一方面指元代社会政治的黑暗霸凌,天下百姓连同作家本人的生存随时面临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即天灾横行,老百姓深重的灾难无法获得解救。张养浩西行进陕,亲历灾荒之下饿殍遍野,“十里路埋千百家冢,一家人哭两三般。犬衔枯骨筋犹在,雅(鸦)啄新尸血未干。”[12]220面对如此惨不忍睹的情境,人的脆弱与无力无处遁形。其二,时间的无情,时年六十岁的张养浩历经宦海沉浮,纵有济世救民之志、治乱安民之心,终年事不允,回天乏术。这种反差与矛盾带给张养浩无尽的挣扎和痛苦,而人的生存意志又抚慰人,促使把这种腐朽败坏的政治与黑暗畸形的现实化作对历史虚无的理解和人生无力的感触,其代表了元代文人在政治高压和悲惨现实面前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是对元代暴政、元人处境的曲折反映。
综上所述,张养浩的九首怀古散曲在咏怀对象和情感内容上虽各有侧重,但其相类的时空结构和叙抒笔法都产生了真实警策、撼动人心的艺术效果。这九首怀古散曲复杂隐微的情感倾向,不仅与元代特殊的时事背景密切相关,更与作家的人生阅历和自我选择紧密结合,其反映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元代文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张养浩晚年的思想内核,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和深厚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