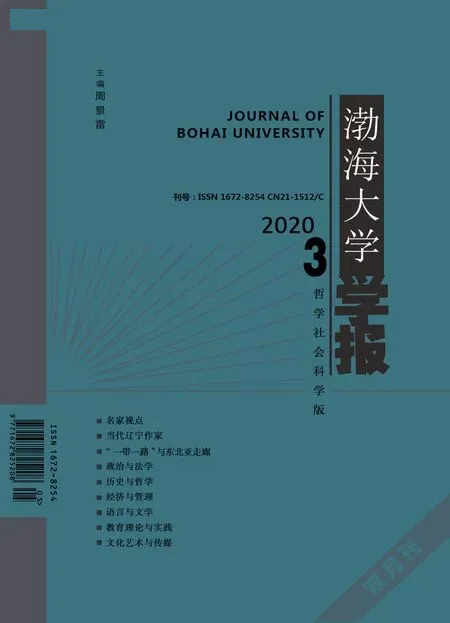重写“东北”:当代沈阳青年作家的集体创作
王娅姝(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100875)
双雪涛,1983年出生于沈阳,代表作有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猎人》等;班宇,1986年出生于沈阳,代表作有中篇小说《逍遥游》,小说集《冬泳》;郑执,1987年出生于沈阳,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我只在乎你》《生吞》,中短篇小说《仙症》《他心通》等。
近几年,上述三个名字频现于文学界和大众视野,被讨论到的除了作品,还有其“80 后”“沈阳人”“小说家”的共同身份。2018年12月,郑执在“匿名作家计划”中凭小说《仙症》摘得首奖,双雪涛及班宇也均入围决选名单;这一事件,可算作“当代沈阳青年作家”群体集中登场的时刻。伴随三人的书写,东北也再度成为文本内外引起关注、共情与讨论的话题。
对于写作者,以笼统、类化的思路去加以描述似乎是粗暴的,但三人在年龄、地缘、成长体验等方面的共通,又确实在其写作姿态和价值逻辑中有不同程度的折射,构成值得讨论的创作现象。文学史上,上一次东北作家的集中出现,似乎还是在萧红、萧军、舒群、骆宾基等人的年代。双雪涛、郑执、班宇立足于当代的写作,有别于历史上“东北作家群”建立在国难和离散视野下的宏大壮阔,相对更具私人性和平民意识。在那些使他们备受关注的作品中,作者以短促、精悍同时兼有情感张力的语言,勾勒出20世纪90年代末东北一代人命运的上升与坠落。父辈形象、工业空间及其内外的身体,以及发端于故土故人的情感价值,是三人作品中突出的特点,建构起某种写作上的共性。透过三人的创作实践,我们看到一种书写东北的新的可能。
一、“父”的形象:个体与时代记忆
在由“一席”举办的讲演活动伊始,郑执将父亲青年时代的照片投放在身后的屏幕上,称“私心想让这张脸在荧幕上多停留几分钟”,因为这是亡父“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正式亮相”,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1]。郑执的表述带出了当代沈阳青年作家一个突出的写作特征,即对“父亲”意象的偏爱。在最受瞩目的作品中,三人不约而同地集中刻画了父子关系,从子辈视角展现父的形象与故事,如双雪涛的《大师》《平原上的摩西》《北方化为乌有》,郑执的《我只在乎你》《他心通》,班宇的《逍遥游》《肃杀》等;若未出现父亲,小说的核心人物一般也会具备父的叙事功能,如郑执《仙症》中的大姑父王战团,班宇《盘锦豹子》中的小姑父孙旭庭等。
这些形象,与文学传统中的父亲形象存在鲜明反差。小说中的父亲迥异于父权式的骄傲威严,降落在小人物、失意者的层面,在家庭中往往也远离中心,居于被轻视或被驱逐的边缘位置。班宇《逍遥游》中的父亲许福明,骑人力车占机动车道、将患病女儿的蜂蜜偷走送给相好、在离婚当天大肆庆祝,是女儿眼中“办事没一件得体”[2]的人;郑执《仙症》中的大姑父王战团,因不时发作的癔症成为家族异类,在一次带着“我”烤食刺猬后,被明令禁止不可再与家中孩子接触;双雪涛《走出格勒》中的父亲出狱后不久再度被判刑入狱,自此拒绝“我”和母亲探视,要求家人忘记自己,断绝来往。
直观上看,这些父亲绝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有些甚至一生背负着罪恶、疾病或不可告人的秘密,颇不足取。但随着叙述的深入,人物的复杂性逐渐成立,其主题功能也在反向塑造的笔法中清晰化。得知女儿患病后,本已开始新生活的许福明“灰土暴尘地赶过来,衣服穿得里出外进”,留下一句“我肯定管,管到底”[2](39)后转手将攒钱买来的小货车卖掉了;面对“我”和“我”的口吃,父母及家族其他长辈均以严厉规训为手段,只有疯子王战团懂得将“我”视为正常人对待;《走出格勒》中的“我”出生于艳粉街,一个“像沼泽地一样藏污纳垢”的贫民区,父亲送“我”一支“像一颗细长子弹”[3]的钢笔,这支笔蕴藉的意义与希冀,帮助“我”完成了对命运的改写和救赎。
对于此类人物,著名学者王德威将其同时命名为“报废者”与“报信者”:生活的败北者是废物,是渣滓,却总有深藏不露的一面,当代沈阳青年作者笔下的父亲们,也总有流露出“无用”之用的可能[4]。
另一端,故事中与父亲形象相对的,则往往是一个被躁动、迷茫、自卑等情绪裹挟的少年形象。借助带有伦理关系的旁观者身份,作者建立起一种既近且远,既深入又抽离的人物距离。“我”既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旁观者,也充当着“父”的镜像,在历史和代际的更迭中,将其精神的遗产纳入自我。
双雪涛的《大师》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父亲是拖拉机厂负责看仓库的工人,沉默寡言,像仓库门前一把人形的锁,他唯一的爱好就是下棋,也因过于痴迷下棋而婚姻破裂、失业下岗、一辈子无所成就。但是,在棋盘上,父亲是高手,32 个子,横竖18 条线,父亲顾虑周全,思路清晰,远近闻名。小说结尾,一辈子没输过棋的父亲,在曾经的对手、如今过得比自己更加落魄的和尚面前主动让了一子,认输。双雪涛着意借儿子的视角,为父亲输棋的时刻加冕——“父亲站起来,晃了一下,对我说:我输了。我看着父亲,他的眼睛从来没有这么亮过”[3](72)。
《大师》中的父亲是世俗层面的失意者甚至失败者,但是,在儿子眼中,在一个抽象的绝对层面,父亲是体面、尊严、悲悯的,如同武侠小说里拂衣而去的一个影子。用故事中和尚的话说,棋里棋外,父亲的东西都比他多。对此,双雪涛的解释是,“一个人把一种东西做到极致,就接近了某种宗教性,而这种东西,是人性里很有尊严的东西,普通人也有自己的神祗”[5]。这是一种发自生命本体的、内在的质感,作者将父亲人生的能指和所指相剥离,穿过其简陋的、微不足道的一生,小说主题指向带有温度及厚度的灵魂。
对父亲的描刻,一部分源自对父辈、故乡及成长经历的伦理性追忆,它们以一种迟滞的状态在作者成熟的写作时刻集中迸发。另一方面,则与地域性的、历史性的背景直接勾连。在父亲的身份之外,小说的主人公们还有另一重身份,即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东北工人。90年代市场化浪潮滚滚袭来时,他们正值中年,产业工人的“身份先进性”突然消失了,在“下岗再就业”的相关语境中,他们的身份修辞由“改造主体”变成了“被改造对象”[6]。面对工厂遣散、动迁移居、失业离婚等看似突然的变化,他们既无理解能力,亦无招架之力,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沉沦并消失在时代转弯处,成为了下沉、隐匿的一代人。双雪涛等人以父之名的书写,既是个体意义上儿子对父亲的几番追忆,也是集体意义上当代人对前人的回访及重遇。借助写作,当代沈阳青年作者们复现了已逝岁月中一代人的爱与痛。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东北三省的下岗职工数约占全国总下岗人数的四分之一,辽宁和黑龙江两省的历年下岗职工人数更是多次跃升至50 万人以上。双雪涛、班宇成长于夫妻均在工厂工作的“双职工家庭”,经历了父母双双下岗、生活困窘的处境;郑执相对幸运,父母于“下岗潮”正式来临前自主离开工厂,但时代的变动同样以一种曲折、隐晦的方式影响着他与父亲的命运。对三人而言,那段时期既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阵痛期,更是个人记忆中有血有肉、可供触摸的现场。他们的创作及虚构,来自父辈的真实,也来自童年、少年时代半是懵懂半是深刻的体验与旁观。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混合、同构,织就了关于父亲的故事,也同时带出了历史的边框与轮廓。
二、工业空间与身体:历史的创伤印痕
时代既由时代中的人所体验、记忆和表达,也被时代性的空间见证、捕捉和指称。在父亲形象之外,当代沈阳青年作家创作中的另一类重要元素是工业空间与空间中的身体。围绕工厂、工人社区及其他衍生场所,文本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描刻,双雪涛的《走出格勒》和班宇的《工人村》,更将空间升格为书写主体,使其甚至具有超越于人物和情节的重要地位。在带有隐喻性和时代感的特定空间内,人的身体则充当空间的延伸,以其创伤、疾病和死亡,印刻着“个体—时代”充满危机的、不确定的多元关系。
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7]。东北,既是写作者的故土,也曾是新中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因靠近苏联,幅员辽阔,物产丰饶,具备重工业基础,东三省大型工厂林立,成为新中国的工业重地,被称为“共和国长子”,风头一时无两。伴随工业的高速发展,城市文化开始兴起,某些巨型工厂内的工人社区,其功能的全面、完备已堪比小型城镇,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各个环节,均有相应的厂区配套设施予以接纳。空间的先进性、便捷性与包容性,一再昭示并巩固着产业工人作为新中国主人翁的主体性地位,使其看去似乎永不变动,恒久如常。然而,90年代开始的巨大变动,使一切看似牢固的契约关系在不到10年之内纷纷瓦解,计划经济的消逝取消了作为共同体的国营工厂,工厂的解体和随之而来的生活的困顿导致大量家庭离散,生产结构和生活结构的同时改变,使情感结构内遍布焦灼与迷惘,人逐渐失去对主体身份清晰、稳定的把握。
班宇的小说《工人村》便以空间上的变化暗喻了这种命运上的变化。工人聚居地,在20世纪50年代,只几年时间,“马车道变成人行横道,菜窖变成苏式三层小楼,倒骑驴变成了有轨电车,一派欣欣向荣之景”;而进入80年代后,“新式住宅鳞次栉比,工人村逐渐成为落后的典型”。作者在文中发出慨叹,“万物皆轮回,凡是繁荣过的,也必将落入破败”[8]。
对于东北和东北人命运的沉浮,工厂是最典型的折射体,双雪涛、郑执和班宇的书写抓住了这一点。文本内的工厂,是衰败、空无、静止并作为遗迹存在的空间,空间的生产性让位于空间的符号性,成为列斐伏尔意义上由生产的空间向空间的生产的过渡。萧条的、停摆的、锈蚀的工厂,既直接呈示现在时态中的苍凉和怅惘,也时刻映照出光辉岁月的“曾经在场”,进而深化当下的悲剧色彩。
双雪涛的《跷跷板》中,曾经效益最好的大工厂现已破败,并成为不可告人的藏尸地,作者写道,“我站在大门口,发现厂子比我想象得还要大,如同巨兽一般盘踞于此,大门有五六米高,只是没有牌子,也没有灯”[9]。空间是荒芜的、无名的,同时又是真实的、不可撤销的,这种对比,侧写出时代性的暴力及其荒谬。在《走出格勒》中,双雪涛对“煤电四营”的刻画则更具某种残酷的诗意:“所有东西都生锈了,车胎也早就干瘪,铲车的翻斗里,盛满了雨水。这里不是列宁格勒,这是一个遗失的世界”。[3](197)“煤电四营”中,空间与时间一道风干也一道腐朽,成为集体记忆的木乃伊。
铁西区、艳粉街、舞厅、小饭馆、理发店,以破败、衰颓和难以填补的空洞,形构出底层世界的空间景观。东北重工业时代的遗迹,在贫穷、衰落和静止中演化为牢笼,封锁了身处其间的人们的现时生活。想要过上好日子,就必须要“走出格勒”,离开这里,忘记它们,头也不回地甩掉这些曾经引以为傲的集体与个人记忆。
在当代沈阳青年作家的文本中,空间与人的根本性的生活经验紧密连接在一起,而这种连接多数时候是借助身体实现的。身体赋予意义、储藏感觉,使人与世界发生关系成为可能[10]。郑执的《仙症》中,在一飞厂即将跻身小组长的王战团,焊接战斗机翼时忘记戴上面罩,火星呲进眼睛,从梯子上翻落,醒来后便发了癔症。工厂与工人,因意外、疾病的发生而产生了不安定的、充满危机的关系,迥异于此前似乎永不分割的共生关系。类似的设计在班宇的小说中也可找到,《盘锦豹子》中,下岗潮来临前,孙旭庭被自己亲手组装的“鲍德海”牌印刷机卷进去半只胳膊;《逍遥游》里,身患尿毒症的许玲玲,在疾病与贫穷的双重限制下,没能走出山海关,想象中的逍遥旅行最终在北方的寒夜中归于寂寥。
身体的创伤和疾病,标记出一种深层的被动性和无力感,强化了个体命运中被驱逐的、落魄的部分。此外,小说还借助身体的畸零和死亡,将叙述更为直接地带入主题性的部分。双雪涛《跷跷板》结尾,“我”在废弃工厂中挖出一具身着工人制服的无名尸骨,“我”盯着骨架看了一会,在心中想着适合将之安葬的墓地,关于细节,“我”如此想:“墓碑上该刻什么,一时想不出,名字也许没有,话总该写上几句。”[9](20)——被深埋于废弃工厂的无名尸骨,成为一句寒冷的比喻,面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无声且无名的消逝,小说温情且悲悯地强调,要为之写上几句话,留下旁观者的悲悯和哀悼。
三、故土故人:重拾小人物的尊严
面对时代进程中难以回避的隐痛,不依不饶的讨伐或面目狰厉的清算都是少有价值的,从美学而言,也是不善、不真的。在这个意义上,双雪涛、郑执和班宇创作的可贵之处在于,尽管从未回避时代创痛,但三人却不约而同地拒斥了宏大叙事,从民族、历史、时代等总体性的修辞中,回落到私人的、日常的、情感的向度。他们拒绝迎合外界对东北及其衰败的猎奇,而是以“人”的精神重写东北,呈递出一个在不可回避的萧条之余,兼有浪漫主义与救赎意味的北国。
言及创作,双雪涛表示,他的小说中没有任何大时代的借口,而只是个人的命运、悲喜、上升和坠落。小说家无意折射时代,只想写好一个人和他的故事,这是一种充满温情的创作姿态,在郑执和班宇的作品中也俯拾即是。郑执的《生吞》以沈阳“三八大案”为背景,围绕罪案和少年秘事,展开长达十几年的奔逃与追索。但说回到创作缘起,郑执则多次谈到小学班上一个被大家孤立、欺凌的女同学,她面对不公时的沉默和平静,给儿时的郑执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她成为了《生吞》中黄姝的原型,被作者升华为一座神像,一种纯粹的理想。小说对平凡人的打捞和拯救,尽管是在虚构意义上的,但却具有突破性。在崇高和宏大的书写维度内,时间以历史单位被划分,只具有宏观特征,而缺少微观的呼吸声。沈阳青年作家的写作,则极力将大的、铁板一块的东西向远景处抛,而将画面的中心位置全心全意地奉献给那些平平无奇,甚至多数时候有些潦草的甲乙丙丁。
班宇《盘锦豹子》中的孙旭庭一生落魄,因为老实而吃了太多的亏,于是在小说结尾处,班宇让他在逆光里以一头豹的形象冲出屋子,“从裂开的风里再次出世,挺着脖子奋力嘶喊,向着尘土与虚无,以及浮在半空中的万事万物”[8](44)。双雪涛《我的朋友安德烈》中本应是天才的少年安德舜,在走向成人世界的过程里,在福柯意义上的“规训与惩罚”中泯然众人,终至陷入癫狂;但当“我”的至暗时刻到来,他却以几乎不符合常识及逻辑的方式从精神病院“越狱”,风雪中奔来,义无反顾地支持朋友。郑执《他心通》中,父亲临终前突然信佛,儿子不解,以为父亲被人骗了,父亲却说,“装老衣太磕碜了,我不喜欢。我想穿海青服,朴素,高雅。我喜欢”[11]。
尊严,小人物的尊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尊严,是三位作者创作的圆心,不论故事如何向外扩散,形成怎样多重的话题与样态,其价值和逻辑总向着尊严回归。如果说90年代的遭际,是东北地域、曾经的“共和国长子”一道被剧变撕开的伤口,那么双雪涛、郑执和班宇立足当代的创作,则借助底层人物的尊严感,将这道伤口一针一针郑重地缝合起来,使其从某个角度看上去,也能威风凛凛。
当下,三人笔下的人物和时代已经老去、远走,逐渐向着过去时态让渡。对此,双雪涛用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创作冲动——霍尔顿漫游在十字街头,口中不断低语着“不要让我消失,不要让我消失啊”;面对东北以及曾在这片故土上认真生活的人,作为写作者的双雪涛,也希望用一支笔把他们留下。郑执则取用“灵魂的遗址”这一更诗意的表述,他认为,对于那些曾经在此的人,他们的灵魂遗址就如同历史的遗迹,等待被人用某种方式,从命运的、轮回的暗河当中打捞出来,然后被重新地解构、塑造、发挥想象,最终“化身为一种不分高低贵贱的永恒”,在他看来,“文学正是那种方式”[1]。
创作中的同质化,或许同时也是当代沈阳青年作家今后需要去解决的切实问题。在关于东北的书写中,三人由于相似的成长背景和审美价值结构,不可避免地在多个方面呈现出相似的特质,有时也正是这种相似性的集中迸发,才使东北地域及其历史在一段时间内被不断提及和讨论。但是,对于写作生涯依旧要向前展开的作者而言,书写故乡也许只是另一个起点。诚如郑执所说,“作家写作的道路大概是一个菱形,一开始是一道窄门,大家都从这道门挤进去,这是写作最基本的门槛:语言、结构、叙事、对小说的意识。跨过这道门槛,是一个越变越宽的过程。很多道路给你走,你完全可以跟别人不撞路。”[12]其实,在三人近期的创作中,这种分野已经逐渐有所体现,双雪涛从《飞行家》开始,有意识地部分脱离于东北叙事,在最新的小说集《猎人》中,他以一种更加意识流、抽象和私人的方式,垦拓出迥异于《平原上的摩西》的风格。郑执继《仙症》后,开始逐渐明朗化某种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蒙地卡罗食人记》一篇,在时空处理、情节变化与人物塑造方面,都有强烈的超现实性;疾病、死亡、痛苦、宗教等扑朔迷离的元素,在他的笔下萦绕。作为三人中唯一一个继续生活在沈阳的作家,班宇坚持着他的冷冽、肃杀与偶尔涌现的愤怒,在书写沈阳之外,做了多年乐评人的他,有更广阔的领域给以滋养。
双雪涛《猎人》的序言里写着这样一句话:文学不可能站在爱的反面,即使站过去,也是因为爱的缘故。离开沈阳,他们的创作会去往何处尚无从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由沈阳、东北而起的对人类命运及灵魂的拥抱不会停息。诚如郑执未说完的下半句话,写作的道路是一个菱形,但最后,仍然会殊途同归。归结到一点:“人性中,几千年未有新的发明”[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