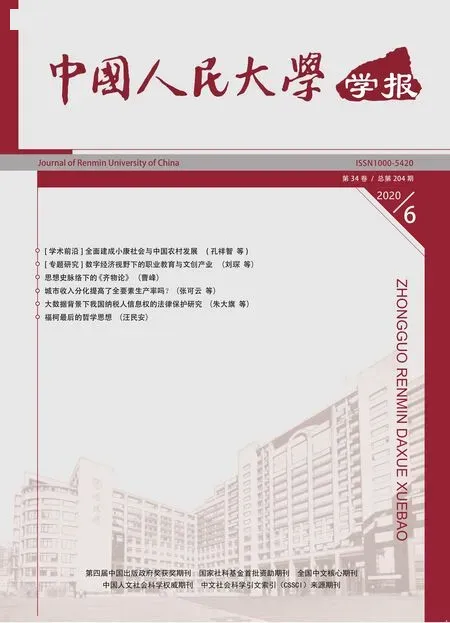从孟、告“生之谓性”之辩看物性与人性
李记芬 向世陵
自告子以“生之谓性”引出物性与人性之辩后,这一问题在人性论发展史中就始终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至今议论不已,其中有不少的论点值得人们思考。典型的一点就是,从孟子的“羽雪玉”之白如何导向“犬牛人”之性?而“生之谓性”本身则为后来宋明理学的性论探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引发了长久的思辨。
一、“生之谓性”与孟子的归谬
《孟子·告子上》云: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生之谓性”是告子的代表性观点,孟子不同意,故而有接下来的反驳。由于文本中没有记载告子最后的回应,而以孟子的反问结尾,故后来儒者大都认为孟子的归谬取得了胜利。(1)其实不少儒者对此仍是有怀疑的。比如朱熹就曾说过:“孟子辟告子‘生之谓性’处,亦伤急。要他倒,只就他言语上拶将去,己意却不曾详说。非特当时告子未必服,后世亦未能便理会得孟子意也。”参见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五十九,13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但就孟、告论辩本身言,仍有不少值得后人思考之处。
孟子归谬的机巧,是利用不同物类(羽雪玉)之色同一(白)的共有感觉经验,去诱导引出不同物类(犬牛人)之性同一的不当结论。从简单的逻辑推理说,如果遵循“异类不吡(比)”(2)“吡”即“比”,比较。参见谭戒甫:《墨辩发微》,216-2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的一般原则,羽雪玉之色与犬牛人之性在逻辑上属于并列的相异关系,不可能由前者之同推出后者之同,故孟子的类比属于无效推理。(3)徐复观认为,从逻辑上说,告子生之谓性的命题,是全称(Universal)判断;其形式为“凡S皆是P”。而孟子只认为生而即有中的“几希”(四端)是性,这是用的特称(Particular)判断,其形式为“S中的若干是P”。告子的全称判断是推论的大前提,若承认他的大前提,则他的推论都是对的,告子的性论自己成了一个完整系统。孟、告前提不同,其结论自然有异。“所以在不同的前提下所做的争论,是实质上或效果上的争论,而不是逻辑形式上的争论”。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170-171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在传统经学的层面,赵岐、孙奭注解《孟子》,明显已察觉这一问题,故而采取规定羽雪玉三物之性内涵的方式,弥补孟子的罅缝:
赵岐注:
孟子以为羽性轻,雪性消,玉性坚,虽俱白,其性不同。问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
孙奭疏:
孟子以谓羽毛之白,则其性轻;白雪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坚,是其性有不同其白也。曰“然”,告子不知为有异,故亦以为诚然也,言则同也。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4)赵岐、孙奭:《孟子注疏》,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7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赵、孙注疏的根本点,是认为孟子已经将色与性区分开来,即羽雪玉虽然“俱白”,但其性均不同,三物之性均不同其共有的白色,从而将孟子设问本来的三物之“白”之同,变成了“三白之性”之同,从而引向结论的荒谬。但赵岐此说——“问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明显是超越了文本的自我发挥。假定孟子真的直接问告子:羽雪玉这三种白色(物)的性相同吗?以《孟子》所载告子前后问答的智慧,决然不可能是“然”的回答。
赵岐将孟子语句中的“白(色)”转变为“(白的)性”,以证明孟子的胜利。然而,孙奭其实已发现孟子问难是别有用心,可“告子不知为有异,故亦以为诚然也,言则同也”。这个告子不知的“有异”,一则可理解为告子不知孟子“生之谓性”犹如“白之谓白”的诱导有诈,贸然认可,结果落入将非本质属性的白色与本质属性的物(人)性相混的陷阱;二则告子只看到羽雪玉三物同白,而忽视了它暗含着色同则性同这一孟子归谬的手法,结果导致了不利的窘境。
再往下,孟子利用色与性直接关联这一误导性的前提,推出了犬牛人之性同这一在孟子眼中最为荒谬的结论。可以说,在没有告子应答的情况下,可以推定为孟子反驳的胜利。不过,这一胜利根本上是建立在孟子性善论的基础上的。孟子主张人先天性善,并引《诗经》“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来支持他的仁义礼智“我固有之”,而这在犬牛并不享有,从而明确标示了人禽之别。简言之,人与牛羊犬马不同类——“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孟子·告子上》),故物性与人性决然不同。
不过,如果站在告子“生之谓性”的立场上(略过被孟子的误导),说犬牛人之性同,也并非不可以理解。因为孟子自己也说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那么,就占“人”之主体的庶民言,他们只追随食色(之性)而丢失德性,也不妨说他们之性与犬牛同。(5)劳思光以为,犬与牛、与人秉性自殊,孟子所说人性,乃指人与其他存在不同之性即Essence而言;而此性之内容即求理之价值自觉,此种自觉能否发挥其力量,又纯依人之自觉努力而定。参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166、170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既如此,并不具有“自觉努力”的庶民(“庶民去之”),按孟子的语境,其人性就与犬牛之性不殊了。
这样说并非曲解了孟子。因为未被教化的庶民,在孟子正是“近于禽兽”。这可以说是孟子理论的另一方面,或者说现实的方面。孟子在批评农家许行的学说时曾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饱食、暖衣、逸居”的食、衣、住方面的物质生活满足,本来也属于人之道,在今天又被归属于生存权与发展权;但仅仅满足于物质需要而缺乏人伦理则,则与禽兽相混。于是,“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那么,孟子意下的“人道”,也就包括了对人在衣食与人伦(五伦)双方面的要求。但逆推这一教化过程,人类在“圣人有忧之”前的“无教”,实际的表现便是父子不爱、君臣无义、夫妇无别、长幼无序、朋友不信的无道德状态。在此意义上,孟子“道性善”,就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一则它不能支持人的当然向善;二则善在此时还无从发生,它实际是圣人教化的产物。一句话,此时的人类尚只有质朴的天性而无善性。正因为如此,就可以发展和联系的眼光重新审视孟、告之辩,将告子的“生之谓性”与孟子的教化成性(善性)视作为一个从原始人类到文明人类、从庶民(禽兽)到君子的道德演进的序列。人性善成为“生之谓性”的质朴天性被教化后的产物。
人因教化而善,在后来成书的儒家经典《孝经》中得到了呼应。《孝经》提出了“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6)唐玄宗注《孝经·圣治章》曰:“亲,犹爱也。膝下,谓孩幼之时也。言亲爱之心,生于孩幼。比及年长,渐识义方,则日加尊严,能致敬于父母也。圣人因其亲严之心,敦以爱敬之教。故出以就傅,趋而过庭,以教敬也。抑搔痒痛,悬衾箧枕,以教爱也。”邢昺:《孝经注疏》,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5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的观点,以为幼儿的爱心或善并非先天本有,而是生于后天的教化——源于父母的爱敬之教。事实上,在利益至上、贪欲横行的战国中后期,人性本善的价值设定不可能被社会普遍接受,而与告子“生之谓性”相关联的荀子的“性者,本始材朴也”(《荀子·礼论》),则能更大程度地适合社会的需要。不过,就思想的发展来说,从战国到汉唐时期,人们对人性与物性的区分及孟、告之辩胜负的判定,并不具有太多的理论兴趣。孟、告人物之性同异的论辩,直至宋以后才重新成为一个争议的话题。
二、司马光“疑孟”与胡宏、张栻的再“释”
自宋开始,孟子的地位上升,但这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同时,宋初的人性论走势也是多面向的。“生之谓性”虽然受到孟子批驳,但由于在揭示人性与物性一致性方面的独特价值,仍然在相当层面发挥着影响。二程“体贴”天理,维护性善,注意人与物、人性与物性由于禀气不同而导致的差别,但同时也看到了告子学说的长处。因为儒家学者都是肯定生生的原则的。在此前提下,“生之谓性”与孟子性善主张的对立,关键就不在“生”的原则本身,而在如何处理犬牛与人,或者物性与人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这是认同“生之谓性”的二程需要说明的。
二程对“生之谓性”做出了多方面的解说,并因此提出了认知人物之性的新的主张,当然这是在与孟子“人性善”相折中的情况下。“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7)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载王孝鱼点校:《二程集》,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即把论性的重点转向了“生之谓”即“人生而静以下”的现实人性上。“未生”或“人生而静以上”,则“不能谓”或“不容说”也。人们一旦“谓”或“说”性,就已经不是先天本性,而是顺承天道生生不已而来的后天人性(善性),从而有了孟子所称的“人性善”。“生之谓性”与“人性善”也就可以协调起来。(8)二程关于“生之谓性”的具体论述,可以参见向世陵:《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第一章第四节,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兹不详述。“人性善”既然已不是先天性善,教化的因素自然也就掺入其中,道德评价也因之具有了现实的可能。
比二程兄弟年长、但与二程又十分“相知”的司马光,则根本不满孟子的性善论而为告子辩。对于“羽雪玉”之白与“犬牛人”之性之问,他认为回答应当是:
孟子云:“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告子当应之云:“色则同矣,性则殊矣。羽性轻,雪性弱,玉性坚。”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来“犬牛人”之难也。孟子亦可谓以辩胜人矣。(9)司马光:《疑孟》,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8册,537页,成都,巴蜀书社,1992。
司马光基本上是承袭赵岐、孙奭之说,故告子陷入窘境是自己缺乏思虑的缘故。从赵、孙注疏到司马光之“疑”,突出了不同器物之“性”的差别性。以差别性为依据,“犬牛人”既明显差别就不可能推出其性同一。
孟子诱导告子在色同则性同,司马光的辩驳则基于色同而性殊,即“犬牛人”色同而性却殊,告子“亦皆然之”,结果落入孟子构筑的窠臼。个别事物之间,其形色表征可以相似,如“犬牛人”之白色,但形色与内在本性的关系是间接的,不可能由前者的相似推出后者的同一,所以孟子的反驳立论不稳。但司马光的辩难存在自身的问题,即所说羽雪玉的“轻弱坚”之“性”,并非是羽雪玉的本质属性,而是与“白”同属于可感知的经验知识,即不具有区分开犬牛人的根本意义。
在孟、告论辩的场域之中,“犬牛人”之性应当是指物或人的本质属性,在孟子意下即为人先天所具的仁义礼智,故人不可能同于犬牛,人性是善的。然而,这正是司马光“疑孟”的基点,即反对孟子的人性善。在他这里:
孟子以为仁义礼智皆出乎性者也,是岂可谓之不然乎!然不知暴慢贪惑亦出乎性也。是知稻粱之生于田,而不知藜莠之亦生于田也。(10)司马光:《善恶混辨》,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8册,513页,成都,巴蜀书社,1992。
善与恶在司马光是共存于天性,这一设定虽难以正面确证,但却可以反面逆推。即从汉唐以来性三品说的圣、愚两极来说,“必曰圣人无恶,则安用学矣?必曰愚人无善,则安用教矣”(11)司马光:《善恶混辨》,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8册,513页,成都,巴蜀书社,1992。?所以,耘其藜莠而养其稻粱方才成为必要。在他眼中,性善论解决不了像“丹朱、商均自幼及长,所日见者尧、舜也,不能移其恶”的问题,“岂人之性无不善乎”(12)司马光:《疑孟》,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8册,537页,成都,巴蜀书社,1992。?人性在他是差别的存在,善恶不等,故先天性善是不成立的。历史上只有扬雄的性善恶混才是对人性问题的恰当解决。
司马光对孟子的驳难在逻辑上并不严密。因为他是以后天人性的现实善恶、或者说是以丹朱、商均的后天恶行反驳孟子的先天性善,这不能说是充足的理由。退一步,即便按司马光的理路,丹朱、商均的不善也可在孟子性善论的框架中(放其良心而不知操存扩充)得到解释。所以,到南宋,胡宏虽然推崇“司马文正之贤”,但对其学说并不苟同,针对司马光的《疑孟》作《释疑孟》,以为孟子辩。他说:
告子不知天性之微妙,而以感物为主,此孟子所以决为言之,使无疑也,此圣学之原也。而司马子乃引朱、均之不才以定天性,是告子之妄乱孟子之正,其不精,孰甚焉!(13)胡宏:《释疑孟》,载吴仁华点校:《胡宏集》,3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告子分不清“人生而静”的寂静天性与“感于物而动”的现实人性,不知“圣学之原”的微妙性体;而司马光以圣人之后的丹朱、商均不能移其恶反驳人先天性善,则是将“性恶”融入“生之谓性”的结果,以此来批评孟子,实际上是以邪乱正,所以是不精之甚。
当然,孟子的性善论并不完善。因为先天之善既然不能保证后天人为确定向善,实际的善恶都是人在后天与环境作用的产物,那么,人先天性善的命题,其存在价值便会受到质疑。不过,孟子论人性善虽有“未能从容中道”处,但较之于持性恶和性善恶混等其他各家人性论,其对仁义和善的天性的坚守仍值得推崇。“今司马子徒以孟子为辨,其不穷理之过,甚矣!”(14)胡宏:《释疑孟》,载吴仁华点校:《胡宏集》,3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但胡宏的主张是以性为本,而非孟子的人性善。他为孟子的辩护,重心不在论证善的现实性,而在发明性的本体地位,力求将主要立足伦理层面的孟子的人性善转移到他自己的性本论立场上来。他的基点是“形而在上者谓之性,形而在下者谓之物”。形而上的性之“大体”虽然唯一,但散在于万物却是善恶吉凶百行俱载,所谓“物有定性而性无定体矣”(15)胡宏:《释疑孟》,载吴仁华点校:《胡宏集》,3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犬、牛、人的不同之性,其实都是同一性体的特定表现和存在方式。“告子知羽、雪、玉之白,而不知犬、牛、人之性,昧乎万化之源,此孟子所以不得不辨其妄也”。(16)胡宏:《释疑孟》,载吴仁华点校:《胡宏集》,3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告子的根本问题是不懂性与物的形而上下之分,也不明白一源和万流的关系:羽、雪、玉之白色虽同,犬、牛、人之性却各异,这是因为不同人物在生成初始,源于同一性体的各自之性就已经确定了。司马光“不穷理”的过错,就在于他没有能明白本性与现实性(善恶)到底是何关系,将形而上的先天同一本性与形而下的后天善恶百行混为一谈了。
胡宏的学生张栻接续其师说,又有更详尽的推论。其曰:
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以言乎各正性命之际则可也;而告子气与性不辨,人物之分混而无别,莫适其所以然。孟子知其蔽于此也,故以“白之谓白”为譬,而又以玉之与羽、羽之与雪为比。告子以为然,是告子以人物之性为无以异也。以人物之性为无以异,是不察乎流形所变之殊,而亦莫知其本之所以为一者矣。则其所谓“生之之谓性”者,话虽是而意亦差也。(17)张栻:《孟子说·告子上》,载邓洪波校点:《张栻集》,344、345页,长沙,岳麓书社,2010。

张栻是将本体论、生成论融入人性论来讨论问题的。“故太极一而已矣,散为人物而有万殊。就其万殊之中,而复有所不齐焉,而皆谓之性,性无乎不在也。”(18)张栻:《孟子说·告子上》,载邓洪波校点:《张栻集》,344、345页,长沙,岳麓书社,2010。“万殊”既是气殊也是性殊(气禀之性),所以非本质关系的羽、雪、玉之白色虽同,而决定人物本质的犬、牛、人之性却不同。告子的“生之谓性”,本来可以引出正确的结论,但他自己却不明白究竟,所以其意也就差了。
三、从余允文到朱熹的评说
南宋初中期,余允文(字隐之)著《尊孟辨》及《续辨》和《别录》,与胡宏一样批评司马光《疑孟》而为孟子辩护。余允文没有明确的理学师承,但他推崇程颐对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的称赞,并讥讽北宋以来那些对孟子“非而诋、诋而骂”的论说“何损于岩岩”(19)余允文:《尊孟辨原序》,《尊孟辨》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519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可见,他是认同理学家的尊孟观的。后朱熹作《读余隐之尊孟辨》,完整引述了余允文之说。(20)不过,朱熹又以为司马光之“疑”与余允文之“辨”的文意不是太清楚,存在“未明”之处。参见朱熹:《读余隐之尊孟辨》,《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35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故有必要先看余氏对司马光《疑孟》的批评:
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告子当应之云:“色则同矣,性则殊矣。羽性轻,雪性弱,玉性坚。”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来“犬牛人”之难也。孟子亦可谓以辨胜人矣。
余氏辨曰:孟子白羽之白与白雪、白玉之同异者,盖以难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也。告子徒知生之谓性,言人之为人,有生而善、生而恶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迁,所习不慎,流浪生死,而其所禀受亦从以异。故有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其本性未始不善也。犹之水也,其本未尝不清,所以浊者,土汨之耳。澄其土,则水复清矣。谓水之性自有清浊可乎?孟子非以辨胜人也。惧人不知性,而贼仁害义,灭其天理,不得已而为之辨。《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以言万物之性,均惟人为贵耳。性之学不眀,人岂知自贵哉?此孟子所以不惮谆谆也。(21)余允文:《温公疑孟》,《尊孟辨》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524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余允文为孟子辩,认为孟子不是逞口舌之强,而是有理有据。其理由有三:一是孟子“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的反问,并不是故意设套,而正是针对本身无意义的“生之谓性”命题打的比方。二是告子从“生之谓”论人性天生有善有恶,是不懂得性善的意义。现实人类有恶,乃是因为后天所“习”不慎,在“流浪生死”之中被环境影响的缘故。故尽管人物之性不一,但并不妨碍人的本性为善。三是人性本善如同水本清净一样,尽管被泥土污浊,但只要通过“澄”的工夫,便可以由浊返清,即浊非水性本身所有。
余允文虽不是理学家,但他对天理的维护和以浊水澄清喻人性本善,明显有二程学术的影子。在他这里,孟子因为担心人们不能认识内在的善性而戕害仁义、灭绝天理,所以不得不与告子辩。余允文也引了《孝经》,但却是“天地之性人为贵”这一条,以期说明人性贵于物性,人之性也就异于犬牛之性。“性学”之不明,就在于人们不知道区别于物的人类自身本性的尊贵,所以孟子要谆谆告诫。不过,朱熹虽转录了司马光与余允文二说,但认为其意较含混,余氏的辩驳本身亦有不甚明了之处。从思想自身来说,余允文的性学强调以性为本,可能也受到了其时“最盛”的湖湘学的影响。他在反驳苏轼性无善恶论的观点时申明:
本性也,无形之可见,无声之可闻。天地得之为天地,鬼神得之为鬼神,人得之为人,物得之为物,莫非性也,是不可指名者也。万殊之性,人物之性也。其在人,则有圣狂愚智之别,刚柔缓急之异;其在鸟兽,则有猛鸷者,有搏击者;其在草木,则有曲直者,有寒温者;是皆气习使然,非性之本然也。论性之本,无不善也。(22)余允文:《苏子辩孟》,《尊孟续辩》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563、563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本性”无形声,不可闻见,即不可“指名”。但天地人物无不得此性而生成,可以说是性外无物。但本性落入具体人物,又形成万殊不同之性。就后者言,不仅人与物不同,人与人也不同,这都是“气习”造就,而无关于性之本然。结合善恶判断,万殊之性有善有恶,性之本然则至善无恶,因为“吾儒自本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之善,扩而充之,于日用常行之际,而全乎广大精微之致”(23)余允文:《苏子辩孟》,《尊孟续辩》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563、563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这与尊孟的理学家的性善论,可以说并无二致。从此出发,本性虽一,气性则万殊,人物之性就不可能同一,人之性自然异于犬牛之性。
朱熹虽然“读”了余允文的《尊孟辨》全文(不含《续辨》和《别录》),但只是照录而并未发表他的读后感言。朱熹自己的立场,可以从《孟子集注》中看出,就是坚持从形而上下审视孟、告之辩。这与他认为由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概念的提出,争议了上千年的人性善恶问题终于获得解决,在理论进程上是一致的。朱熹解释说:
(告子曰:生之谓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觉运动者而言……与近世佛氏所谓“作用是性”者略相似……“白羽”以下,孟子再问,而告子曰“然”,则是谓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则犬牛与人皆有知觉,皆能运动,其性皆无以异矣。于是告子自知其说之非而不能对也。(2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3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按朱熹的解释,告子“生之谓性”的“生”,是指人物知觉运动的生成而言。人物有生便有知觉运动,故可从知觉运动的现状去解释其性。这与唐以来禅宗主张的彻见眼前之作用即见佛性的观点是相似的。“作用”涵盖人的四肢运动和五官官能的一切行为,故处处可以见性。关联到告子——当然是朱熹理解的告子之言,就是凡有生者、凡有知觉运动者,均为同一之性使然,结果导致了结论的荒谬。
其实,禅宗的“作用是性”,重点还不在“作用”本身能否见性,因为理学家强调从日用伦常中去体贴天理,也可说是一种从“作用”见性的工夫。症结在于,如果只是从个体(主体)的作用去规定性,则忽视了儒家天理或天命之性的客观本体地位。性作为本体,它是形而上的至善,不论你是否“见”它都是如此。这可以说是理学最根本的立场。用弟子陈淳的话,即“佛氏把作用认是性,便唤蠢动含灵皆有佛性,运水搬柴无非妙用。不过又认得个气,而不说着那理耳”(25)陈淳:《北溪字义·性》,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朱熹正面阐发自己的意见说: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
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2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3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人物之生,都是天命性理与气禀的结合,这表现在共有知觉运动的生物本能或所谓“作用”上。但就仁义礼智的善的“本根”说,物虽分有却不完全,人则因禀赋完全而为万物之灵。告子只知道禀气之性和人物共有知觉运动,而不知性本天理和仁义礼智之粹然,所以错误就不可避免了。
朱熹之说要点有二:一是认定告子“生之谓性”之“生”就是指知觉运动而言,由于犬牛人皆有知觉,皆能运动,所以走向其性为一的荒谬。二是人物均禀理气而生,但人禀其全而精,物则有缺而不纯。所以,人物之性就是有同有异,而不能一概视之。当然,这不是孟子之义“精”,而是理学家的新孟说。在这里,如果再细分人物禀赋的“全”与“粹”,朱熹要更重视“全”的方面。人健顺五常之德无一有缺,而物则不能如此,如虎狼无义、蝼蚁缺仁、马性无顺、牛性缺健等。(27)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六十二,1376、14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这两点合起来,实际上就是气同而理(性)异,客观天理与至善本性是合二而一的。
在弟子陈淳眼中,不少儒者虽然高谈性命,但大都走到了佛教“作用是性”一路,而根子仍不过是告子“生之谓性”之说。然而,毕竟“作用是性”与儒家同样注重作用(工夫)在形式上相似,孟子本人亦主张“践形”,强调“形色,天性也”(《孟子·尽心上》)。这就需要在理论上分辨清晰。陈淳认为问题的关键,其实就在性善原则的坚守上。譬如,“谓人之所以能饮能食,能语能嘿,能知觉运动,一个活底灵底便是性”,但这在“道理”上根本不可通:
且如运动,合本然之则,固是性。如盗贼作窃,岂不运动,如何得是性?耳之欲声,目之欲色,固是灵活底。然目视恶色,耳听恶声,如何得是本然之性?只认得个精神魂魄,而不知有个当然之理,只看得个模糊影子,而未尝有的确定见,枉误了后生晚进,使相从于天理人欲混杂之区,为可痛。(28)陈淳:《北溪字义·性》,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性固然是人发生知觉运动的根据,但运动有运动之则,作用有作用之本,这即是善。善是本然之性的“的确定见”,即最后的定盘针。陈淳之说,重要点在将日常以为支配人活动的精神作用、生理本能等等,彻底与儒家的本然之性(道德本性)剥离开来。后者即是以仁义礼智为代表的至善天理。以知觉运动或作用说性,区分不开对恶的欲望的追求,将天理人欲混为一谈。在陈淳,这些在当年本来已被孟子“扫却”的“邪说”,现在又重新被拈作“至珍至宝”,实在令人“可痛”。
不过,如果一定要讲“道理”的话,至善本性至多只能是一种价值的设定,人的理性并无可能给予证明。前面已提及,程颢申明“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后胡宏又强调“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29)胡宏:《知言》卷四,载王立新校点:《胡宏著作两种》,30页,长沙,岳麓书社,2008。,都说明人的道德评价(善恶)无法指向形上本体,本性其实是无(所谓)善恶的。一句话,“人性善”只能适用于后天的领域。同时,陈淳推崇孟子的先天性善,仍是为老师和自己的理学立场站台,并不完全吻合于孟子理论本身。
回到孟、告双方的论辩,告子的“生之谓性”,固然只是就形而下说性,但就是孟子的论说,在朱熹眼中也显得粗疏。朱熹说:
(告子)说来说去,只说得个形而下者。故孟子辟之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又辟之曰:“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三节谓犹戏谑。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竟亦不曾说得性之本体是如何。(30)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六十二,14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戏谑之言自然谈不上严谨。告子的根本问题仍在以知觉运动说性。人的知觉运动和行为举止表征着特定的人性,但此性乃是气质或气禀之性,非性之本体自身,这才是孟告之辩所应吸取的最重要的经验教益。“说来说去,只说得个形而下者”。这是朱熹以为告子和佛教性论共有的问题。
孟子的“三节”反问,虽然言语上似乎胜过了告子,但孟子自己也未能真正揭示“性之本体是如何”的道理,而这才是朱熹真正关心的问题。(31)具体可参阅向世陵:《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载《孔子研究》,2011(3)。朱熹一生都在建构、完善他的性理学说,能否在形而上的层面挺立至善天理,是他判断一切理论优劣的根本标准,绝不能让气质交杂的现实人性与形而上的性本体混为一体。因此,他虽然推崇孟子,但对孟子理论的不明晰、不完善处,也时常可见他提出的批评。
四、戴震的总结
从朱熹到陈淳,他们议论孟、告之辩,批评告子以知觉运动为性而混淆人物之分,在朱学作为官学的元明清时代,有极大的影响。不过,当人们从气学的层面来进行总结时,对其学说又有了不同的评判。清代中叶,戴震批判理学,认为朱熹意下的孟子批评告子的基本论点——理气不分、知觉运动人物同、仁义礼智人物异等,都说不通。因为倘若此,孟子只需要区分开人与物就够了,又何必去区分牛之性与犬之性呢?而仁义礼智粹然与否,在犬与牛之间并无意义;如果告子真是以知觉运动为性而人物相同,那他为何不直接应之以“然”而不吭声了呢?所以知觉运动不能作为人物性同的依据。(32)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载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182、183、156、184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
戴震理论的特色,是不讲本体作用,而讲气化生成,天地间万物,一切都源于阴阳五行气化之分,人物分有气化不齐,所以成性各殊,而表现为知觉运动也不相同。“知觉运动者,人物之生;知觉运动之所以异者,人物之殊其性。”(33)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载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182、183、156、184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故重点不在于知觉运动这一人物之生共有的现象,而在于不同的人物之性决定了各自知觉运动的差异。至于作为性善内核的仁义礼智,只能是人的智慧(神明)达到最高境界的产物:“人之异于禽兽者,虽同有精爽,而人能进于神明也。”“神明之盛也,其于事靡不得理,斯仁义礼智全矣。”(34)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载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182、183、156、184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精爽”指禽兽与人共有的基于血气的知觉本能,神明则是人所特有的理性智慧,所以人之仁义礼智全于犬牛,不在于天然的禀赋,而在于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对于人伦物事的分析辨别能力。换句话说,善是人的智慧选择的结果,而且“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而后儒以为别如有物凑泊附著以为性,由杂乎老、庄、释氏之言,终昧于六经、孔、孟之言故也”(35)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载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182、183、156、184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戴震强调理存于欲,反对将理欲对立起来,理在于欲中,仁义礼智依存于血气心知之气。朱熹认定人的善性是所得于天之理,即“别如有物凑泊附著”于心,这与孟子所谓仁义礼智“我固有之”实则是一致的,戴震只是以经过他“疏证”的孟子回击宋儒罢了。
戴震对性气、理气关系的总结,已经体现了一定的近代气息,但他将人物之性的异同一概之于阴阳气化的分有不齐,实际上把问题简单化了,在思辨的层面还有所退步。物性与人性的异同、性善的先天后天等问题也并未获得根本的解决。今天的科学和哲学仍然在对此做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