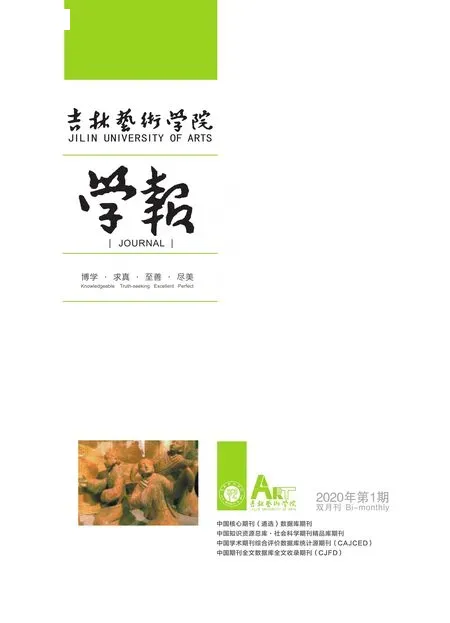《怒吼吧,中国!》在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的传播
何爽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 长春,130033)
1924年6月22日,受邀到北京大学授课的苏俄诗人特列季亚科夫在中国游历时目睹了一桩发生于中国船工与英美侵略者之间的冲突事件,他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史诗,后改编成剧本《金虫号》,1926年首演于梅耶荷德剧院,并在革命戏剧倡导者梅耶荷德的建议下更名为《怒吼吧,中国!》。此剧因国际革命运动的题材,以及“全体一贯,渐次达到高潮的,没有间息的紧张”[1]等艺术表现力,引起国际戏剧界的广泛关注。《怒吼吧,中国!》及时、正面地表现重大政治事件,描写中英之间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以及英苏之间的尖锐矛盾,与30年代内忧外患的中国现状相吻合,成为中国戏剧界的热门演出剧目之一,它“形成也限制了中国左翼关于‘伟大作品’的想象”,成为30年代左翼戏剧的“原点与起点”。[2]《怒吼吧,中国!》得到了欧阳予倩、陶晶孙、田汉、徐懋庸、胡愈之、董每戡、茅盾等人的高度评价,在30年代的中国被看作为一场大型的反帝斗争话剧,是“风靡30年代的戏剧力作”。[3]17这一戏剧风潮也吹向了抗战时期的东北地区,但是由于殖民战争的笼罩和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存在,这部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和政治宣传意图的戏剧在东北地区经历了迥异于关内地区的传播与演出境遇,显示出战时东北戏剧场域的复杂性。
一、“有生命的戏剧”:《国际协报》对《怒吼吧,中国!》的宣介
1931年11月7日,在以“表演真实人生”为宗旨的哈尔滨《国际协报》“戏剧”专栏上,登载了“剧的呼声”“剧的将来”和“本刊的职责”三篇短文,声明与传达了栏目创办者在国难危机时刻以戏剧展现、鼓励、指导人生的文艺态度。与之一同登载的还有戏剧《怒吼吧,中国!》的相关文章,包括《怒吼吧,中国!》的本事(署名春冰),理论文章《从“怒吼吧中国”说到塞北戏剧》(署名鲁孙),以及《怒吼吧,中国!》最后一幕的演出剧照。
在“剧的将来”一文中,栏目主办者号召东北戏剧家们“要像园丁开辟荒芜的园地一样的勤劳操作”,在东北戏剧“荒僻的原地”“赶快干起有生命的戏剧”,[4]而同期登载的《怒吼吧,中国!》即是这种有生命的戏剧的代表。1930年,欧阳予倩在广州组织演出《怒吼吧,中国!》,带给全国戏剧界广泛的影响和冲击,这种影响也波及战时的东北戏剧界,以致东北的戏剧工作者们希望“在哈市能有《怒吼吧,中国!》的公演机会”。战时东北剧界对此剧的看重和渴望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考虑。一方面是因为这部戏剧的剧情直指殖民侵略者,对处于日占区的东北地区有指导和借鉴意义。1924年,特列季亚科夫在中国游历时目睹的惨案以及由此创作的戏剧表现了中国与英美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冲突。美籍商人与中国船工在一艘英商船上发生争执,美国商人不慎失足落水溺亡,中国船夫逃逸。事发后,游弋于长江水面的英国军舰舰长要求中方在两天内捕杀船帮会首,或绞死任两个码头苦力抵命,否则将炮轰县城。英国政府同时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派英国驻重庆领事督办此案。英国的暴虐行径和中国军阀政府的软弱处置引起了中国百姓的愤怒,致使百姓愤而反抗。《怒吼吧,中国!》“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侵略和种种耻辱行为,以及帝国主义者以军事和宗教的方式来进攻中国”,“并十足表现民众的痛苦,及弱国外交的委曲求全”,这对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仅2个月的东北沦陷区具有强烈的醒示意义,“像这本戏,应在各地都有公演的机会,而使民众有深切的瞭望和觉悟”。另一方面,战时东北对《怒吼吧,中国!》一剧的看重来源于关内多地演出的良好反响和效果。此剧在20世纪30年代的广州、上海、武汉、桂林等地相继成功出演或计划演出。1930年,欧阳予倩为纪念“六二三”沙基惨案,组织广东戏剧研究所搬演《怒吼吧,中国!》,成为此剧在中国的首演。1933年,应云卫带领上海戏剧协社在法租界的“黄金大戏院”上演《怒吼吧,中国!》,目的是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两周年,以“每日三场,连演六天”的盛况推广此剧。“戏剧从来就不是纯粹的艺术类别,它是直面所处时代的冲突和危机的艺术”。[3]21《怒吼吧,中国!》在关内地区的演出盛况,尤其是应云卫一剧的热烈反响,给东北戏剧界带来极大的刺激:“连演了六次,给了民众很深刻的印象,当台上高呼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很齐整的反响而喊起来,是多么激动!”此剧在民众中取得的热烈效果正是东北戏剧家所倡导和渴望的,“艺术是民众的,应该仍归还到民众的手里。戏剧是艺术界的一大部门,而且是一个最应接近民众的部门”。“戏剧民众化”的探索在20世纪30年代的关内地区已经逐步展开,“北平的熊佛西,南国的田汉,广州的欧阳予倩等,他们虽仍没有深入到民众的下层去,但已做到走进了小资产阶级和学生的群众里去!所选的剧本,也逐渐的离民众近了”。反观东北戏剧,“虽也不断的看见各种团体的表演,然而离开时代,离开民众都很远”,“各团体及学校所演过的剧本,还是在个人主义的享乐中走路”。[5]对于“戏剧是娱乐的玩意”“艺术是供人玩赏的消遣品”“国难危机还干戏剧运动有何用”[6]等戏剧观点,正是东北剧运者们所要极力破除的。因此,如《怒吼吧,中国!》一般能深入民众,引发观剧热潮的戏剧是东北剧界急需的。
从《国际协报》连载的“《怒吼吧,中国!》的本事”来看,与1929年《乐群》杂志十月号刊出的陈勺水翻译的《发吼吧,中国!》相似,此版本是根据1929年9月日本东京筑地小剧场演出脚本翻译而来,也是国内最早的译本。剧本本事中,美国人伙莱在与中国船夫老计的争执中溺水身亡,英国舰长的“四条要求”将英美军方的蛮横无理与中国官员的卑躬屈膝展现无遗,“舰长要求:送尸体到坟墓去的时候,要市上的高等官员伴随前去,这是一。要用市上的钱,在墓上建一个十字架,这是二。要抚恤死者的家族,这是三。等到市长都勉强同意了以后,舰长又提出第四条来了。明天早晨,九点钟,把罪人处死刑。”[7]这一系列的要求将殖民者的残暴、无耻暴露无遗,也是引起中国民众愤恨的关键情节。在九·一八事变仅仅过去两个月后,《国际协报》登载、宣传《怒吼吧,中国!》一剧,其目的是揭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灾难,给处于殖民压迫、深陷痛苦中的东北民众以鼓舞,唤醒民众的反抗意识,刺激国人如醒狮般发出怒吼之声,投入抗战,获得胜利。《国际协报》的这次宣传以文本刊发和理论探讨为主,并没有做实际的演出,《怒吼吧,中国!》真正在战时东北地区的实演有两次,一是1942年奉天(沈阳)“满洲国”的公演,二是1944年大连“关东州厅”的公演。
二、殖民文学手段的失败:《怒吼吧,中国!》的奉天实演
在1931年《国际协报》对《怒吼吧,中国!》的宣传11年之后,奉天协和剧团于1942年将此剧搬上舞台,在战时东北进行实际的演出。此时,东北地区的文化环境较1931年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1年的东北处于抗战初期,伪满政权还未正式建立,日伪的殖民文化统制还在最初的尝试与准备阶段。伪满文艺政策以“建国精神”为核心而建立“国策文学”,在思想上宣扬伪满洲国的“独立”特质,在文化上灌输伪满是“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文化对东北民众进行同化教育。抗战初期的东北文坛,尤其是在北满地区,包括戏剧在内的文学创作依旧能够传达明确的民族抵抗精神,如《怒吼吧,中国!》一样具有鲜明抵抗精神的文学作品还能够找到发表的空间,作家们利用文学撕掉日伪的伪善面具、表现异族统治之下东北民众真实处境和感受的创作目的还能够实现。随着战争的持久和伪政权的建立,伪满文化统制政策逐步完备,从1933年设立情报处,管理东北新闻、出版、广播等文艺部门;到1937年成立日伪思想文化统治的中枢——伪总务厅弘报处,对文化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管和审查;再到1941年伪弘报处将多个部门的管辖任务进行统一规划,发布伪满文化的“大宪章”——《艺文指导要纲》,日伪在东北的殖民文艺规范日臻完备,也越发严苛。戏剧成为日伪文化怀柔的重要手段之一,扶持剧团演出和剧本创作,发挥与扩大戏剧的宣教价值,借此达到“歌功颂德”“点缀盛世”的目的。尤其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社会进入紧张的战时状态,戏剧成为伪政府“决战文艺”的组成部分。随着日伪政策的夹紧,内涵民族抵抗色彩的文学创作渐失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奉天协和剧团于1942年上演表达反抗殖民的话剧《怒吼吧,中国!》,显现出战时东北戏剧生态的复杂境况。1942年的这次演出在编演目的上与1931年戏剧者的宣传初衷南辕北辙,却收获了意外而又殊途同归的传播效果。
协和剧团是战时东北地区三大职业剧团之一,是奉天话剧表演的先锋。剧团成立于1939年,前身是1938年成立的业余性质的协和剧团,由李乔、安犀、徐百灵、成雪竹、田菲等组成。从编演目的上看,1942年奉天协和剧团的这次演出依旧是想要激发起民众的反抗之情,反对侮辱与压迫,但其最终的目标是企图借助《怒吼吧,中国!》中英美侵略中国的剧情,引起中国人对英美的仇恨,以达到配合日本“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日伪寄希望于剧中英美对中国百姓的压迫暴行能够重新燃起战时东北民众对老牌殖民宗主国的仇恨,以彼时故事映射和暗示此时环境,达到文化殖民之目的。日伪的这一操作是殖民文艺创作中惯用的思路和手法,将日本与中国的民族矛盾和仇恨进行外化,转嫁给英美,从根源上挖掘中英的历史恩怨,将此时的战争矛盾指向英美,模糊日本在战争中的“肇事者”身份。同时利用与中国邻近的关系,假塑日本的“友邦”身份和战争“同盟”关系,一方面强调日本在“帮助”东北铲除军阀、建立伪满“新国家”的功绩。另一方面突出日本“圣战”的神圣使命,将之拔高至整个东亚乃至世界范围。这是日本殖民侵略者在文化统制上经常使用的伎俩和手段,存在于战时东北诸多内涵附逆的文学作品中,用以辅助日伪在东北的文化管制政策。但从演出的最终结果来看,协和剧团的这次演出未能按照日伪所设定的路线行进,演出效果与编演目的之间出现了严重偏差,演出的最终效果令日伪当局十分尴尬。《怒吼吧,中国!》上映后,东北民众确实争相观看,造成了观剧热潮。但是戏剧最终激起的并非是东北民众对英美的仇恨,而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以及伪满当局的愤恨与不满。剧中发生在同胞身上的惨剧让东北民众悲痛而愤怒,直指异国的战争侵略和强权统治给东北带来的伤痛。在民怨面前,日伪不得不终止该剧的上映。同时为消除这一失策的举动,日伪当局改演日本人端山进炮所作的多幕话剧《渤海》,编造日本人帮助中国民众抗击英美海盗的故事,却依旧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演出时十座九空,最后不得不停演”。[8]《怒吼吧,中国!》在奉天的这次演出成为此剧演出史中的特殊案例,其演出意图与结果之间的落差,证实了日伪殖民主义文学话语炮制手段的失败,是伪满文化统制的失策之举。
三、日伪政策下的艺术抵抗:《怒吼吧,中国》的大连实演
1944年,在奉天演出2年后,大连地区的官办剧团“金州会兴亚奉公青年队演艺部”在大连协和会馆再次搬演《怒吼吧,中国!》。此时,由于战争的逼紧和日本在军事战场上的接连失利,日伪在鼓动文学为“大东亚圣战”服务后,进一步提出了“决战文艺”的口号。1943年,伪满召开的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表达了强烈的“决战”意欲,探讨如何以“满洲”文学文化配合日本的“大东亚战争”。[9]随后召开的“全国文艺家决战大会”发出了以文学辅助“大东亚战争”的“宣言”[10],表明伪满文学进入了“决战文学”的阶段,文学以服务“圣战”为宗旨。在如此文化环境下,东北戏剧亦被卷入服务“决战”的洪流中,要求演剧的基础是“置于日本精神和日本艺能传统之上”,目的是“为了今日的战争而作”,重点在“大众国民的自觉意识上”。[11]1944年编演《怒吼吧,中国!》一剧的剧团是大连“金州会兴亚奉公青年队演艺部”,此剧团成立于1943年,与奉天协和剧团同是官办剧团,但是它的成员多是金州一带的劳工和社会上的适龄青年,加上金州城的文艺爱好者、教师、职员,组成“兴亚奉公青年队”,参加日伪“勤劳奉公”活动的同时,搞点文艺节目。从演出时间和此时东北地区的文化环境上看,大连地方剧团在1942年奉天演出失利2年后再次编演《怒吼吧,中国!》,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可能是配合日本殖民统制和“大东亚”战争,是殖民主义文学话语炮制手段的延续。但是戏剧演出时编演者担心“‘怒吼吧,中国!’这一词语会引起日本人的不满”,因此将剧名改为《指南针》,意思是“影射中国人要像反对英美一样去反对侵略中国的一切侵略者”[12],带有民族抵抗的意义。《怒吼吧,中国!》一剧的“指南”意味与1926年发生的“万县”惨案相关。距离《怒吼吧,中国!》在莫斯科首演仅仅7个月后,中国四川万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1926年6—8月,英国殖民侵略者在长江流域万县段制造了多次血案。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轮船“万流”号再次撞沉中国木船3艘,导致多人淹死,同时袭击了中国派去查讯事件经过的轮船。9月5日,英方派两艘军舰抵达万县,妄图以武力强行劫走“万通”号,中方士兵还击。英方再次派出三艘军舰,炮轰万县两个多小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县“九五惨案”。“万县惨案”使得《怒吼吧,中国!》成为一部“带有预言性质的”戏剧,国际左翼阵线纷纷排演此剧,日本筑地小剧场于1929年9月在东京上演,英国未名社于1931年11月在曼彻斯特上演,美国戏剧协社于1930年10月在纽约上演,德国、北欧的一些剧团也演出该剧。大连演出时对剧名的改动反映了创作者对戏剧编演初衷的反拨,显示出战时东北文艺创作者在无法逃脱的文化管控夹缝中的挣扎和努力,在日伪时局与政局文化高压下,作家以主动性和能动性支配作品的情感倾向,以戏剧独立的文学和艺术价值抵抗殖民文化的困囿。同时,迎合日伪政策的演出目的和带有抵抗意味的剧名更改也是抗战时期东北戏剧复杂面向的集中表现。此外,战时东北地区的大型演剧活动,尤其是知名剧作或是伪官方推行的戏剧演出,各大报刊多登载剧本本事或者梗概以及评论文章[13],甚至是伪官方组织的集中探讨,以扩大戏剧影响。但是对于《怒吼吧,中国!》在奉天和大连地区的两次演出,各大报刊鲜有对其所用剧本和相关评论文章的登载,致使我们无法得知编演者采用何种版本的剧本,对剧本做了怎样的改编,演出的实际效果如何,以及观众产生怎样的反馈状况。但也正因为相关批评的缺失,透露出日伪官方对戏剧演出情况的有意遮蔽,从而侧面证明了《怒吼吧,中国!》在战时东北的意外遭遇和失败经历。
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左翼戏剧《怒吼吧,中国!》在进入抗战时期东北地域文化土壤后,生发出迥异于关内地区的戏剧传播效果。由于殖民战争的笼罩和傀儡政权的存在,这部带有强烈政治宣传意图的戏剧在战时东北戏剧场域中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既是唤醒东北民众醒狮怒吼的民族戏剧,又是迎合日伪殖民文化政策的政治举动;既是日伪殖民主义文学话语炮制手段失败的证明,同时表现出东北戏剧工作者在夹缝挣扎的艺术抵抗,且提供了抗战时期戏剧史上的独特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