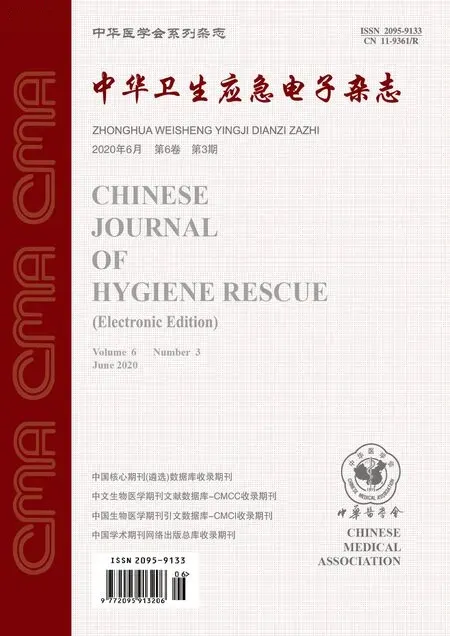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并发MODS的可能机制及紧急救治对策探讨
岳茂兴 付守芝 朱晓瓞 孙同文 刘青云
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了多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患者。随着疫情的蔓延,我国其他地区也相继发现了此类患者。该病作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已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按甲类传染病进行管理[1]。引起此次疫情的病原体——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属于β属的冠状病毒,有包膜,颗粒呈圆形或椭圆形,常为多形性,直径60~140 nm。其基因特征与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相关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related coronavirus,SARSr-CoV)和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related coronavirus,MERSr-CoV)有明显区别。目前研究结果显示,2019-nCoV与蝙蝠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样冠状病毒(bat-SL-CoVZC45)同源性达85%以上。体外分离培养时,96 h左右即可在人呼吸道上皮细胞内发现,而在Vero E6和Huh-7细胞系中分离培养约需6 d。对其毒理化特性的认识多来自对SARS-CoV和MERSr-CoV的研究。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56℃ 30 min、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氯已定不能有效灭活病毒[2]。
2020年2月25日24:00,全国已经报告确诊的COVID-19患者78 064例,累计死亡2 715例,现有重症患者8 754例[3]。作为一种传染性极强的严重新型呼吸道传染病,COVID-19重症患者的救治难度比SARS更高。一部分重症COVID-19患者死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sdrome,MODS)及多器官功能衰竭(multiple organ failure,MOF),但其导致MODS及MOF的机制尚不十分清楚。所以,研究COVID-19并发MODS的可能机制及紧急救治对策已是当务之急。随着对该疾病认识的深入和诊疗经验的积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已经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进行修订,形成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2]。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长期救治MODS及急危重症患者的临床经验,对COVID-19患者并发MODS的可能机制及紧急救治对策进行探讨,以期为临床一线救治人员提供参考。
一、COVID-19并发MODS的机制探讨
(一)COVID-19并发MODS死亡患者的病理学特点
对1例确诊死亡患者的肺、肝、心进行穿刺活检的研究结果显示,COVID-19的病理特征与SARS和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冠状病毒感染非常相似[4]:双肺可见弥漫性肺泡损伤伴细胞纤维粘液样渗出物,有明显的肺水肿、肺细胞脱落和透明膜形成;显微镜下可见以淋巴细胞为主的间质单核炎性浸润,肺泡腔内可见多核合胞体细胞,胞核大、胞浆呈双亲颗粒状、核仁突出,呈病毒性细胞病变样改变;但未发现明显的核内或胞浆内病毒包涵体。肝组织呈中度微血管脂肪变性和轻度小叶和汇管区炎症。外周血流式细胞分析显示,淋巴细胞减少症是COVID-19患者的常见特征;T细胞过度活化,表现为Th17的增加和CD8细胞的高细胞毒性,部分原因是严重的免疫损伤[4]。2月16日凌晨3:50,全国首例COVID-19患者遗体解剖工作已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顺利结束,14 h后该团队又完成了第二例遗体的解剖工作,其后的一周内,又有9例患者遗体病理解剖被陆续完成[5-6]。现有的有限尸检和穿刺组织病理结果显示[2]:(1)肺脏呈不同程度的实变,支气管黏膜膜部分上皮脱落,黏膜上皮和Ⅱ型肺泡上皮细胞胞质内可见冠状病毒颗粒。肺泡腔内见浆液、纤维蛋白性渗出物及透明膜形成;渗出细胞主要为单核和巨噬细胞,易见多核巨细胞。Ⅱ型肺泡上皮细胞显著增生,部分细胞脱落。Ⅱ型肺泡上皮细胞和巨噬细胞内可见包涵体。肺泡隔血管充血、水肿,可见单核和淋巴细胞浸润及血管内透明血栓形成。肺组织灶性出血、坏死,可出现出血性梗死。部分肺泡腔渗出物机化和肺间质纤维化。肺内支气管黏膜膜部分上皮脱落,腔内可见黏液及黏液栓形成;少数肺泡过度充气、肺泡隔断裂或囊腔形成。电镜下支气管黏膜上皮和Ⅱ型肺泡上皮细胞胞质内可见冠状病毒颗粒;免疫组化染色显示部分肺泡上皮和巨噬细胞呈新型冠状病毒抗原阳性;RT-PCR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2)脾脏明显缩小,灶性出血和坏死,脾脏内巨噬细胞增生并可见吞噬现象。脾脏和肺门淋巴结淋巴细胞数量减少,可见坏死;免疫组化染色显示脾脏和淋巴结内CD4+T和CD8+T细胞均减少。骨髓三系细胞数量减少。(3)心肌细胞可见变性、坏死,间质内可见少数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和(或)中性粒细胞浸润。部分血管内皮脱落、内膜炎症及血栓形成。(4)肝脏和胆囊体积增大,暗红色。肝细胞变性、灶性坏死伴中性粒细胞浸润;肝血窦充血,汇管区见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细胞浸润,微血栓形成。胆囊高度充盈。(5)肾小球球囊腔内见蛋白性渗出物,肾小管上皮变性、脱落,可见透明管型。肾脏间质充血,可见微血栓和灶性纤维化。(6)脑组织充血、水肿,部分神经元变性。(7)肾上腺见灶性坏死。(8)食管、胃和肠管黏膜上皮不同程度变性、坏死、脱落。
(二)COVID-19并发MODS的病程
大范围COVID-19患者的临床发病过程表明,其临床病程发展基本符合MODS及MOF的病程规律:2019-nCoV侵入人体引起机体损伤→应激反应→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MODS→MOF。因为MODS及MOF实际上是在动态变化过程中的两个术语,其差别仅在于损害的程度不同而已,所以临床上可把COVID-19并发MODS的病程一般分4期:(1)第一期为“病毒血症期”,即病毒增殖期。病毒在体内大量繁殖,引起发烧、干咳、呼吸频率加快等。(2)第二期为“过度免疫应答期”,即肺、肾等器官功能损害期。肺部受损,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窘迫,氧合指数(PaO2/FiO2):≤300 mmHg(1 mmHg=0.133 kPa),无论呼气末正压(positive end expiratory pressure,PEEP)的水平高低;正位X线胸片显示肺浸润性阴影。(3)第三期为“免疫麻痹期”。继发感染等各种并发症。(4)第四期为“恢复期”[7-8]。一部分患者经治疗进入“恢复期”,此类患者器官功能的损伤是可逆的,一旦病理生理机制被阻断,器官功能可望恢复;一部分患者病情进一步加重而死亡。这也与Bone[9]提出的MODS病程分期基本相一致。
笔者在对MODS长达40多年的研究中证实:除不同原发疾病的致病因素外,机体自身失控的过度炎症反应及异常的免疫反应,在MODS及MOF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三)导致COVID-19患者死亡的原因
临床患者研究表明,2019-nCoV感染后出现的大部分病理损伤,并非完全由病毒直接破坏肺部细胞造成的,而是人体自身免疫应答造成了组织的损伤。1991年8月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ACCP)和美国危重医学会(Society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SCCM)在芝加哥举行会议,对SIRS的名词进行了明确的定义:(1)体温>38℃或<36℃。(2)心率<90次/min。(3)呼吸频率>20次/min或过度通气,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4.27 kPa(32 mmHg)。(4)白细胞记数>12.0×109/L或<4.0×109/L或幼粒细胞>10%。而COVID-19患者的发病特征就具有上述SIRS临床表现中的前3项。此次疫情发生后,科研人员也发现,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 6,IL-6)是诱发炎症风暴的重要通路[10]。SIRS可理解为一种超常应激反应,COVID-19则是由2019-nCoV感染引起的一个统一的动态连续性病理过程。因此,笔者认为,此类MODS及MOF是在2019-nCoV引起非典型肺炎的刺激下,因控制局部炎症刺激的免疫反应过弱,而远隔器官过度免疫反应,过度产生自由基,激活并释放大量有害的炎性介质,从而导致炎症反应失控,并通过细胞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发生了器官功能衰竭。综上所述,失控的炎症反应是产生此类MODS及MOF的主要启动因素。当COVID-19患者达到免疫失衡状态时,也就达到了MODS的最终阶段。这种状态是由难以控制的炎性反应造成的,并将导致处于激发状态的免疫细胞产生更为剧烈的反应,从而超量释放体液介质。它们作用于靶细胞后,还可以导致更多级别的新的介质产生,从而形成瀑布样反应,更加重了细胞缺氧、缺血。随之发生的就是多种器官功能衰竭的多米诺骨牌现象——全身功能系统一个一个衰竭。
许多研究提示,SIRS和MODS患者病死率与持续性高水平的炎性介质直接相关。器官衰竭是由持续发展的炎性反应造成的,除非炎性反应能够被下调,否则死亡就会发生。但持续的免疫抑制又可导致免疫失衡并增加死亡风险。实际上,促炎症介质与抗炎症介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是动态平衡的过程:当不同介质之间彼此取得平衡,则内环境的稳定得以保持;否则,将发生过度炎症反应或SIRS,或是免疫功能低下,或无免疫发应性。如果机体可以通过自身调节或医疗手段恢复平衡状态,那么免疫失衡的患者就有可能重新得到器官功能的恢复;反之则导致器官功能的衰竭。COVID-19患者病情发生急转直下的原因,一个是免疫过度应答(过激反应)造成组织损伤,另一个就是免疫低下或“麻痹”引起继发感染。持续性抗炎症介质高血浓度,以及持续性促炎症介质高血浓度一样,都能抑制细胞的免疫功能,从而增加了全身性感染的危险性,导致MODS及MOF的发生,使病死率明显增加。因此,在SIRS和MODS阶段,只有快速谨慎处理,协调抗炎与促炎之力量,使之达到(恢复)衡态,才可以避免死亡。
二、紧急救治策略
(一)救治的总趋势
COVID-19并发MODS时的救治工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需要一整套合理、高效、科学的管理方法,精干熟练的技术骨干,和不断加强并完善的医疗预防及救护系统[11]。该系统工程的完善是保证抢救成功的关键措施。目前,对COVID-19还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所以救治比较困难,重症患者的死亡率较高。防止COVID-19并发MODS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早期识别,一旦发现,其后续的多学科联合综合治疗至关重要,一定要从整体与局部关键因素上协调有效处置。
救治的总趋势是:一方面指向外来入侵的2019-nCoV引起的组织损伤,采取有效的抗病毒病因治疗,并快速为患者提供新陈代谢必需的辅酶、底物和强劲的动能;另一方面,应该指向机体自身炎性反应的合理阻断,以避免其过度激活而引起瀑布样连锁反应和诱发组织细胞的失控损伤;再一方面,还应指向处于临界状态的器官功能保护,监测全身重要脏器功能的评估,及时干预、支持。
(二)治疗的关键措施
关键措施包括4点。一是要针对病原体进行比较有效的治疗。二是要努力调控过度的炎性反应及异常的免疫反应,全力防止并发ARDS。三是要积极治疗内毒素血症。四是要对慢性基础疾病进行有效的调控。
1.强调对COVID-19并发MODS的早期预警、早期识别、早期检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在治疗上统筹兼顾,防治结合,中西医并重。强调器官的相关概念,要对疾病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和治疗,即需从病毒、炎性介质、内外毒素、微循环障碍、免疫功能失调、营养代谢紊乱、基础疾病、脏器功能等8个主要方面进行兼顾和并治[12-13]。笔者认为,COVID-19并发MODS的发病及病理生理改变主要涉及上述8个方面,特别要强调的是:对确诊的COVID-19患者,一开始就要提高警惕,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采用抗病毒、合理供氧、减少肺组织渗出、上皮细胞损伤、肺水肿的程度、改善通气、快速提供人体新陈代谢必需的辅酶、底物和强劲的动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与免疫功能、利尿、解毒、保护大脑及神经系统功能等中西医结合重要措施,尽一切可能阻止COVID-19患者并发ARDS的发生。千万不要等到ARDS患者已经出现双肺弥漫性肺泡损伤伴细胞纤维粘液样渗出物,大量粘液胶冻样物质堵塞支气管时才采取措施,此时肺细胞脱落和透明膜已经形成,已为时已晚。预防确诊COVID-19患者并发ARDS发生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发挥专家组集体会商或远程会诊制度是很好的模式。若能对此采取针对性措施,也许能降低MODS的发生和病死率。
2.指向外来入侵的2019-nCoV引起的组织的损伤与抗病毒治疗。可试用γ-干扰素(成人每次500万U或相当剂量,加入灭菌注射用水2 mL,2次/d雾化吸入)、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成人200 mg/50 mg/粒, 2粒/次,2次/d,疗程不超过10 d)、利巴韦林(建议与干扰素或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联合应用,成人500 mg/次, 2~3次/d静脉输注,疗程不超过10 d)、磷酸氯喹(用于18~65岁成人:体重>50 kg者,500 mg/次,2次/d,疗程7 d;体重<50 kg者,第1、2天500 mg/次,2次/d,第3~7天500 mg/次,1次/d)以及阿比多尔(成人200 mg,3次/d,疗程不超过10 d)。要注意上述药物的不良反应、禁忌症(如心脏疾病患者禁用氯喹)以及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等问题,同时在临床应用中仍需进一步评价目前所试用药物的疗效。不建议同时应用3种及以上抗病毒药物,出现不可耐受的毒副作用时应停止使用相关药物。对孕产妇患者的治疗应考虑妊娠周数,尽可能选择对胎儿影响较小的药物,以及是否终止妊娠后再进行治疗等问题,并知情告知。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可能出现新的有确定疗效的抗病毒药物,可根据临床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3.抗菌药物治疗应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物,尤其是联合使用广谱抗菌药物。由于免疫失调或低下导致继发性细菌感染时,可用大环内酯类、氟喹诺酮类等抗生素进行治疗广谱和经验性抗菌治疗,再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病原菌敏感的抗菌药物对症处理。
(三)重型、危重型患者的治疗
1.治疗原则: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积极防治并发症,治疗基础疾病,预防继发感染,及时进行器官功能支持。
2.卧床休息,加强支持治疗,保证充分热量:注意水、电解质平衡,维持内环境稳定;密切监测生命体征、指氧饱和度等。隔离治疗,并尽早收入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
3.密切监测病情根据病情监测血常规、尿常规、C-反应蛋白、生化指标(肝酶、心肌酶、肾功能等)、凝血功能、动脉血气分析、胸部影像学等。有条件者可行细胞因子检测。
4.呼吸支持:(1)氧疗:重型患者应当接受鼻导管或面罩吸氧,并及时评估呼吸窘迫和(或)低氧血症是否缓解。(2)高流量鼻导管氧疗或无创机械通气:当患者接受标准氧疗后呼吸窘迫和(或)低氧血症无法缓解时,可考虑使用高流量鼻导管氧疗或无创通气。若短时间(1~2 h)内病情无改善甚至恶化,应当及时进行气管插管和有创机械通气。(3)有创机械通气:采用肺保护性通气策略,即小潮气量(6~8 mL/kg体重)和低吸气压力[平台压≤30 cmH2O(1 cmH2O=0.098 kPa)]进行机械通气,以减少呼吸机相关肺损伤。在保证气道平台压≤35 cmH2O时,可适当采用高PEEP,保持气道温化湿化,避免长时间镇静,早期唤醒患者并进行肺康复治疗。较多患者存在人机不同步时,应当及时使用镇静以及肌松剂。根据气道分泌物情况,选择密闭式吸痰,必要时行支气管镜检查采取相应治疗。(4)挽救性治疗:对于严重ARDS患者,建议进行肺复张。在人力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每天应进行12 h以上的俯卧位通气。俯卧位通气效果不佳者,如条件允许,应当尽快考虑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
5.循环支持:在充分液体复苏的基础上,改善微循环,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并进行密切监测血压、心率和尿量的变化,以及动脉血气分祈中乳酸和碱剩余。必要时进行无创或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如超声多普勒法、超声心动图、有创血压或持续心排血量监测(pulse indicator continous cadiac output,PiCCO)。在救治过程中,注意液体平衡策略,避免过量或不足。根据监测变化情况密切观察患者是否存在脓毒症休克、消化道出血或心功能衰竭等情况。
6.肾功能衰竭和肾替代治疗:对出现肾功能损伤的危重症患者积极病因,如低灌注和药物等因素。对于肾功能衰竭患者的治疗应注重体液平衡、酸碱平衡和电解质平衡,在营养支持治疗方面应注意氮平衡、热量和微量元素等补充。重症患者可选择连续性肾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
7.康复者血浆治疗:适用于病情进展较快、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用法用量参考《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临床治疗方案(试行第1版)》。
8.血液净化治疗:血液净化系统包括血浆治疗、吸附、灌流、血液/血浆滤过等,能清除炎症因子,阻断“细胞因子风暴”,从而减轻炎症反应对机体的损伤,可用于重型、危重型患者细胞因子风暴早中期的救治。
9.免疫治疗:对于双肺广泛病变者及重型患者,且实验室检测IL-6水平升高者,可试用托珠单抗治疗。首次剂量4~8mg/kg,推荐剂量为400 mg、0.9%氯化钠注射液稀释至100 mL,输注时间>1 h;首次用药疗效不佳者,可在12 h后追加应用一次(剂量同前),累计给药次数最多为2次,单次最大剂量不超过800 mg。注意过敏反应,有结核等活动性感染者禁用。
10.其他治疗措施:COVID-19并发MODS患者的治疗关键在于维持免疫系统的平衡,针对不同的患者、不同病程的具体需要,当高热不退,感染中毒症状突出,氧合指标进行性恶化、影像学进展迅速、机体炎症反应过度激活状态的患者,早期适量用激素等免疫抑制药物,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可酌情在短期内(3~5 d)使用糖皮质激素,建议剂量不超过相当于甲泼尼龙1~2 mg/kg/d,应当注意,较大剂量糖皮质激素由于免疫抑制作用,会延缓对冠状病毒的清除,在使用激素时,还应积极防治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并加以预防。
此外,还可静脉给予血必净100 mL/次,2次/d治疗;可使用肠道微生态调节剂,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预防继发细菌感染。儿童重型、危重型病例可酌情考虑给予静脉滴注丙种球蛋白。患有重型或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孕妇应积极终止妊娠,且剖腹产为首选。除此之外,患者常存在焦虑恐惧情绪,应当加强心理疏导。
(四)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
传统祖国医学的阴阳平衡及脏俯理论认为,机体整体水平上的“阴平阳谧”是维护各脏腑系统功能平衡的生理学基础。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是多成分、多环节、多靶点,通过综合效应发挥药效,早期使用中医药,可以阻断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也可明显减轻发烧、呕吐、腹泻、食欲减退等症状,还可缩短发烧时间和病程,减少后遗症。本病属于中医“疫”病范畴,病因为感受“疫戾”之气,各地可根据病情、当地气候特点以及不同体质等情况,参照下列方案进行辨证论治。涉及到超药典剂量,应当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1.医学观察期:(1)乏力伴胃肠不适,推荐中成药:蕾香正气胶囊(丸、水、口服液)。(2)乏力伴发热,推荐中成药: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颗粒)、疏风解毒胶囊(颗粒)。
2.临床治疗期(确诊患者):清肺排毒汤适用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危重型患者救治中可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合理使用。基础方剂及服法详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2]。(1)轻型:根据寒湿郁肺症、湿热蕴肺证,辩证选择推荐处方[2]。(2)普通型:根据湿毒郁肺证、寒湿阻肺证,辩证选择推荐处方[2]。(3)重型:①疫毒闭肺证:推荐生麻黄6 g、杏仁9 g、生石膏15 g、甘草3 g、藿香10 g(后下)、厚朴l0 g,苍术15 g、草果10 g、法半夏9 g,茯苓15 g、生黄芪10 g(后下)、生大黄5 g,葶苈子10 g、赤芍10 g。服法:1~2剂/d,水煎服,每次100~200 mL,2~4次/d,口服或鼻饲。②气营两燔证:推荐生石膏30~60 g(先煎)、知母30 g、生地30~60 g、水牛角30 g(先煎)、赤芍30 g、玄参30 g、连翘15 g,丹皮15 g、黄连6 g、竹叶12 g,葶苈子15 g、生甘草6 g。服法:1剂/d,水煎服,先煎石膏、水牛角后下诸药,每次100~200 mL,2~4次/d,口服或鼻饲。(4)危重型(内闭外脱证):推荐人参15 g、黑顺片10 g(先煎)、山茱萸15 g,送服苏合香丸或安宫牛黄丸。出现机械通气伴腹胀便秘或大便不畅者,可用生大黄5~10 g。出现人机不同步情况,在镇静和肌松剂使用的情况下,可用生大黄5~10 g和芒硝5~10 g。
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的中药注射剂推荐用法:中药注射剂的使用遵照药品说明书从小剂量开始、逐步辨证调整的原则,推荐用法如下:(1)病毒感染或合并轻度细菌感染:0.9 %氯化钠注射液250 mL+喜炎平注射液100 mg或0.9%氯化钠注射液250 mL+热毒宁注射液20 mL或0.9%氯化钠注射液250 mL+痰热清注射液40 mL静脉滴注。(2)高热伴意识障碍:0.9%氯化钠注射液250 mL+醒脑静注射液20 mL静脉滴注。(3)SIRS和(或)MOF:0.9%氯化钠注射液250 mL+血必净注射液100 mL静脉滴注。(4)免疫抑制:葡萄糖注射液250 mL+参麦注射液100 mL或生脉注射液20~60 mL静脉滴注。功效相近的药物根据个体情况可选择一种,也可根据临床症状联合使用两种。中药注射剂可与中药汤剂联合使用。柴黄参祛毒固本中药[14]:本方为临床经验方,是汉·张仲景《伤寒论》柴胡汤与血府逐瘀汤、三黄泻心汤合方化裁而成,乃表里双解、气血同治之剂,具有清解少阳阳明、清热解毒、通腑泄热、扶正固本、调理气血的作用。选用柴胡、黄芩、黄连、黄柏、玄参、党参、人参、金银花、栀子、连翘、防风等药物为主,每袋含生药12 g。临床应用和动物实验表明:该组方对细胞因子有良好的调控作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紊乱状态,缓解高热等炎性反应,提高患者对高敏状态的耐受性;可缓解重要器官的病理改变,对重要脏器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可通过机械排出作用,改善微循环,增加血流量,减少内毒素诱导的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等细胞因子的产生,起到免疫调理作用;无副作用。也可用于COVID-19患者的治疗。
3.恢复期:根据肺脾气虚证、气阴两虚证,辩证选择推荐处方[2]。
(五)代谢营养支持及免疫营养支持治疗
代谢营养支持的方法可分肠外营养(parenteral nutrition,PN)和肠内营养(enteral nutrition,EN)两大类。施行PN的患者每天应从中心静脉或周围静脉注入肠外、白蛋白强化治疗等;EN可选择易于消化和吸收的要素饮食,如能全素、安素、爱伦多等。
某些营养物质不仅能防治营养缺乏,还能以特定方式刺激免疫细胞增强应答功能,维持正常、适度的免疫反应,调控细胞因子的产生和释放,减轻有害的或过度的炎症的反应,维护肠屏障功能等。具有免疫药理作用的营养素已开始应用于临床,包括:谷氨酰胺、精氨酸、n-3脂肪酸、核苷和核苷酸、膳食纤维,益菲佳、能全素、安素、爱伦多、益力佳等等。也可以使用免疫调节剂,如胸腺肽、丙种球蛋白和干扰素治疗。
(六)改善微循环,防止微血栓形成,扩张支气管,减少肺组织渗出
0.9%氯化钠注射液50 mL+山莨菪碱20 mg+地塞米松20 mg,采用微泵24 h静脉持续泵入,共3 d。若患者不适合应用地塞米松,可以单独应用山莨菪碱。由于给药方式为24 h静脉持续泵入,所以一般不良反应不大。能遏止危重状态进展、促进症状缓解、改善微循环,有良好的降温、抗毒、抗炎、抗休克作用,还可扩张支气管,减少肺组织渗出,对重要脏器无损伤作用[15],能在阻止COVID-19患者并发ARDS的发生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七)抑制自由基的过量产生
对2019-nCoV感染者早期给予大剂量维生素E、维生素C或者其他抗氧化剂红霉素、黄连素等治疗,以抑制自由基的过量产生。
对严重COVID-19患者,在给予激素等治疗时,加强抗氧化剂如维生素E、硒、超氧化物岐化酶、谷胱苷肽等的综合治疗等。
(八)并发症防治
为防治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应同时应用甲氰米胍等药物静脉注入,以预防应激性溃疡的发生。特别应该注意监测肠道菌群的变化,积极防治二重感染的发生[16-18]。应从患者的病理生理角度,慎重实施输液和营养支持,严格计出入量,量出为入;动态监测电解质和血气分析,随时调整输液,以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等内环境的稳定。适当应用血小板衍生因子、转化生长因子、表皮细胞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等积极促进机体的修复和愈合。
三、解除隔离、出院标准以及出院后注意事项
(一)解除隔离、出院标准
满足以下条件者,可解除隔离出院:(1)体温恢复正常3 d以上。(2)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3)肺部影像学显示急性渗出性病变明显改善。(4)连续2次痰、鼻咽拭子等呼吸道标本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至少间隔24 h)。
(二)出院后注意事项
1.定点医院要做好与患者居住地基层医疗机构间的联系,共享病历资料,及时将出院患者信息推送至患者辖区或居住地居委会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患者出院后,建议应继续进行14 d的隔离管理健康状况监测,佩戴口罩,有条件的居住在通风良好的单人房间,减少与家人的近距离密切接触,分餐饮食,做好手卫生,避免外出活动。
3.建议在出院后第2周和第4周到医院随访、复诊。
四、转运原则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转运工作方案(试行)》[19]执行。
五、医疗机构内感染预防与控制
严格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一版)》[20]、《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护中常见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试行)》[21]的要求执行。
六、小结
本综合治疗措施在实际抢救过程中要根据具体情况,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适当调整用药剂量和顺序,以便获得最佳救治效果。综合治疗措施并不等于各种治疗方法的简单叠加,是考虑和注意到了各种治疗方法疗效的互补性,从而避免了疗效的拮抗和毒副作用叠加,以期取得较好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