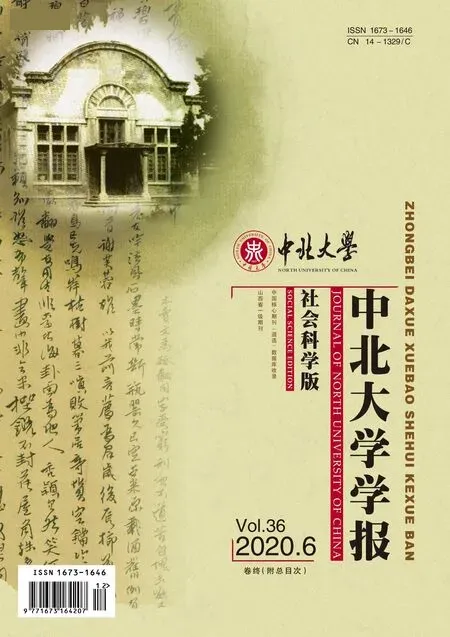教育的民族品格: 论乌申斯基教育民族性思想*
曹文明, 吕 卉
(1.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2. 海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乌申斯基(1824~1870/1871?)是俄罗斯教育科学的奠基人, 教育民族性思想是其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 教育民族性思想是对俄国教育精神的探求, 发端于俄国知识分子精英对“民族性”问题的求索, 并伴随着俄国近代教育发展而产生。 教育民族性思想厘清了俄国教育“自我”与世界教育的关系, 对俄国近代教育发展理念进行定位。 本文将系统考察教育民族性思想生成的理论逻辑, 全面审视教育民族性思想的多元构建。
1 追溯思想渊源
教育民族性思想源于19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思潮中的热议话题“民族性(народность)”。 “民族性”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 深化的体现, 是俄国精英分子对历史发展中民族地位问题的思考, 其旨归是如何正视俄国发展道路与民族历史经验、 民族传统的关系问题。 十二月党人显现出了“民族性”意识的觉醒。 政论思想家П.Я.恰达耶夫的公开批判推动了“民族性”意识自觉的进一步增强。 19世纪30年代以来, 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战中, 斯拉夫派诠释了“民族性”问题。
“民族性”一词最早是由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П.А.维扬泽姆斯基于1819年提出的, 是民族学研究常用的学术词汇。[1]введение作为社会思潮的“民族性”是在对俄国制度责难基础上构建的, 十二月党人展现了“民族性”意识的觉醒, 拉开了俄国民族自觉史的序幕, 其表现为由忠君、 守制到叛君、 改制, 捍卫民族自尊和人民权利。 十二月党人呈现的“民族性”意识觉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兼顾思想的大转变和革命行为实践。 十二月党人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抗击拿破仑侵略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远征军, 或是从阶级属性、 亦是从政治信仰思考, 他们都是沙皇专制的拥趸和农奴制的受益者。 从忠君守制到叛君改制的初衷改变得益于他们思想上的彻底转换, 信守西欧民主、 自由和平等思想。 1812年, 他们开始国外远征, 期间, 置身西欧民主思想熏陶, 亲历考察西欧政治制度, 最终接纳了西欧民主、 平等、 自由思想, 并成为认识俄国社会的思想工具。 回国后, 经过10余年思考比较, 亲视俄国沙皇专制腐朽和农奴制野蛮, 最终, 他们摒弃忠君守制固有信念, 投入革命实践, 成为推翻旧制度的革命战士。 1825年, 他们发动推翻沙皇专制和农奴制的革命起义, 起义失败, 惨遭屠杀和流放。 由此思考, 十二月党人呈现的“民族性”意识觉醒有着形式和内涵的双重思考。 直观形式是向俄国旧制度宣战, 发动革命, 破除原有政治信仰, 建立民主制度(君主立宪或共和制), 深层内涵是赋予俄国民众“人民”概念的具体意义, 即人民的政治自由、 自尊和权利。 自古以来, 在沙皇专制和农奴制这两重枷锁下俄国人民的自尊和权利是虚无的, “民族性”意识根本无从萌发和彰显。 只有以革命形式推翻旧制度, 才能把“民族性”解放出来, 民族性情、 人民性、 社会法律、 民族历史经验才能自然、 自由地体现, “民族性”所蕴含的力量才能真正作用于俄国历史发展。[2]2然而, 十二月党人呈现的“民族性”意识觉醒存在着历史局限性, 觉醒仅限在十二月党人有限个体身上, 同时, 主张用西方的形式和手段改造俄国。 从历史发展看, 十二党人“民族性”意识觉醒功在千秋, 促动了俄国民族意识的生成, 启蒙了俄国民族意识, 唤起了俄国新精神, 唤醒了俄国一代人。
恰达耶夫则以批判、 否定式爱国主义情怀深化了俄国“民族性”意识的觉醒, 其特征是赋予“民族性”意识群体效应。 19世纪30年代, 俄国社会看似平静, 实际上思想的交锋极其激烈, 但真正公开走在前锋的很少。 恰氏站在时代沿头, 以俄国著名杂志《望远镜》为媒体平台, 用批判声腔向国民致信, 对俄国制度进行全面地批判。 恰氏痛斥俄国弊政, 揭露农奴制的罪恶, 认为农奴制奴役了“民族性(精神和肉体)”, 东正教对沙皇反动统治的献媚进一步加重了对人民的奴役程度, 使其陷入历史的黑暗深渊。[3]120-121恰氏对俄国制度的批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直指沙皇专制和农奴制抑制了民族所赋有的创造历史的力量, 误导了自我识别。 恰氏认为, 历史上, 俄国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 从没有过以精力充沛的历史活动和人民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 从没有合法、 有效地去探察、 界定民族传统中不朽的经典。[4]162-163恰氏公开言论审判, 对于当时俄国群体无疑是具有号召性的, 消弭了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隔阂界线, 挖掘出社众内心暗沉弥久的民族知觉, 无论是西方派, 还是斯拉夫派都为之感召, 民族的命运成为了时代关注的焦点。[5]488-489在俄国民族自觉史上, 恰氏对俄国政治制度和农奴制的犀利揭露, 无疑是爱国主义的表达, 最终目的是试图通过严厉、 深刻的民族自我批判来深化、 强化民族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 恰氏所指涉的“民族性”意识已不再是有限个体的觉醒, 而是普通群体共有的意识, “民族性”已成为一个历史问题, 为斯拉夫派“民族性”群体论证做了铺垫基础。
19世纪30年代以来, 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战中, 斯拉夫派系统地论证了“民族性”问题, “民族性”已内化为俄国历史进程表征。 斯拉夫派“民族性”观念的逻辑主要有两个层面, 其一是“民族性”的批判前提, 即彼得一世的欧化改革。 在斯拉夫派看来, 为了实现欧化进程, 彼得一世侧重西化, 忽视民族传统。 出于民族和人民人道主义精神的抗争, 斯拉夫派公然向当权者及其政治集团发出批判, 并阐明“民族性”思想的第二个层面内容, 即“民族性”的内涵要义。 在内涵要义上, 斯拉夫派首先为俄罗斯民族辩护, 斯拉夫派是土生土长的贵族保守派, 是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自恃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 主张从民族、 国家历史中挖掘优秀遗产。 其次, 斯拉夫派表明了俄国道路立场, “民族性”就是俄国的发展道路。 斯拉夫派认为, “民族性”是俄罗斯民族纯粹的部分, 是民族的历史、 社会、 自然条件, 是智慧的苍穹处和能量的富集地, 斯拉夫派把“民族性”视为俄国发展依赖基质依托, 统一于民族的历史。[6]44-47依斯拉夫派, 俄国应尊崇民族自身的历史发展经验, 而不是追随西方道路。 由此, 在“民族性”整体考量上, 斯拉夫派的“民族性”观念是对前两代“民族性”观念的现实路径化, 认定民族是俄国发展道路的拓行者和护航者, 民族诉求已成为俄国历史进程表征。
综上可知, 俄国“民族性”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渐进深入的过程, 一致的命题是在国家发展上要倚重民族自身, 遵循于民族特征。 斯拉夫派领袖А.С.霍米亚科夫指出, 在俄国始终存在“民族性”坚守和“西化”追求两个对立面, 这两个面此消彼长, 相互制约。[7]19019世纪上半叶俄国对“民族性”问题的大讨论促使“民族性”观念参与俄国的历史进程, 蕴化于民族话语体系, 影响着19世纪下半叶俄国各个领域的改革。 在教育改革领域, 俄国先进教育家诠释了教育民族性思想。
2 教育民族性思想内容布局
俄国对“民族性”的求索, 为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改革做足了思想和精神准备。 在教育领域, 爱国知识分子精英以“民族性”为逻辑向度, 不从陈说, 另辟蹊径, 试图勾勒俄国近代教育发展图景, 诠释了俄国教育民族性思想新理念。 教育民族性思想塑造了俄国教育的民族品格, 展示了教育的民族力量和民族自信,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反思沙皇政府教育逻辑脱离民族实际的倾向; 民族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和向标; 推行教育民主, 实施人道教育。
2.1 反思沙皇政府教育逻辑偏离民族实际的倾向
在俄国近代教育史语义组块上, 教育为沙皇专制政治服务和教育模式西化借用成为俄国恪守的两个重要价值指示项。 自彼得大帝以来, 俄国教育对孤立主义进行自我破冰, 西化逻辑占据了的主流, 俄国教育迎来了一个新路径时代。 然而, 在路径幅面上, 沙皇政府在教育为沙皇专制政治服务方面施用过度, 同时, 抄袭西方教育模式, 教育发展逻辑脱离民族实际的倾向凸显。 这一教育发展路径上的偏颇成为了乌氏檄文笔伐的一个靶向。
在对沙皇政府教育发展逻辑脱离民族实际的反思站位上, 乌氏走在了前列, 并以此作为其教育民族性思想演绎的首要破点。 在俄国, 把以学校作为组织形式推行公共教育作为一项国策始于彼得大帝。 18世纪以前, 俄国针对青少年的学校公共教育是不存在的, 教育仍旧限于教会与政府、 贵族合作兴办的少数教会识字学校, 教育受众极其窄仄。 俄国教育文化积淀瘠薄, 在发展上很难提供智性支持, 以彼得大帝为首的俄国政府想打开一个公共性的教育局面是极其艰巨的。 凭借沙皇专制政治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和借助于西方教育模式以求俄国近代教育的飞跃成为沙皇政府的决策取向。 在这一方略的指导下, 俄国教育逐渐走向了教育为沙皇专制政治服务的道路, 并机械借用西方的教育模式。
沙皇政府教育发展逻辑脱离民族实际倾向内化弊损过程加剧始于19世纪30年代确立的官方教育理念。 1933年, 沙皇尼古拉一世重用国民教育部大臣С.С.乌瓦罗夫和俄科学院院士А.Н.佩平, 并授意二人杜撰官方“民族性”理念。 他们二人撰制了三位一体(专制制度、 东正教和民族性)的官方“民族性”, 认为, 专制制度、 东正教和农奴制是国家存在, 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根本, “民族性”是对沙皇专制顺从和对东正教信诚的品格。[8]22-26同时, 沙皇政府把官方“民族性”理念灌输到教育领域, 建立苛刻的教育监察和文化书籍出版检查制度, 对学校教育内容实施严密监控, 取消教育连续制度, 中断各教育阶段间的连续性, 教育被专制意识形态驱使。 此外, 沙皇政府全面效仿德国, 采用德国教育管理制度。 事实上, 进入19世纪以来, 俄国政府极力提高近代教育水平, 但贫于发展依赖的教育文化基础支撑, 乏于近代教育管理, 在教育发展逻辑上, 主体地位不坚定自信, 急于教育成果巡礼, 导致俄国近代教育在发展关键阶段侧重外援取力, 俄国近代教育脱离民族实际的倾向显现。 针教育现状, 乌氏批判地指出, 官方教育理念以沙皇政府曲解的“民族性”作为外衣, 其实质是为其反动教育构建合法化, 赋予教育过度的政治意识形态承载, 是反动的, 为民族和人民的自由发展筑以壁垒阻碍, 实质上, 就是依靠教育最大程度上培养对沙皇专制的拜服品性和对东正教的敬崇品格。[9]24-26由此, 沙皇政府的教育倡导是脱离现实的, 教育应由人民、 民族的发展历史决定, 是人民生活要素之一, 必按照自己的特殊道路前行, 不应抄袭西欧其他民族教育模式, 沙皇政府教育理念进入误区, 也成为了以乌氏为代表的先进教育理论家批判的焦点。
2.2 民族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和向标
19世纪上半叶, 俄国教育仅仅是沙皇专制的编纂, 俄国近代教育难以逃避教育失格的诟病。 在乌氏看来, 俄国教育发展应立足于人民, 植根于民族。 民族是教育历史生活的唯一源泉, 是国家教育发展的基础和向标。 同时, 也要树立教育的世界意识, 寻找教育发展的外部力量。
至于俄国近代教育, 关键要点在于发展逻辑参照的本旨立定, 回归到民族本位。 19世纪60年代, 沙皇政府和社会先进教育力量极力扳正这一发展方向。 农奴制废除后, 俄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公民社会意识逐渐增强, 教育供给亟待解决。 这也是俄国近代教育实现与社会、 人民、 民族一体共命运发展的历史机遇, 突出教育的民族特征和主体地位。 而实现这一历史转变, 就要破除俄国教育政治意识形态一元支配局面, 立足民族, 塑造教育的民族品格, 显现民族力量。 回溯俄国近代教育轨迹, 其发展软肋就是没有实现教育发展与民族的高度契合, 包括先进的教育思想家和理论家很少论证教育与民族的关系, 要么固步自封, 或是全盘西化, 乌氏却实现了教育发展与民族内在的逻辑勾连。 19世纪上半叶社会各界对“民族性”的大讨论, 给予教育的启发就是民族孕育教育发展的生机, 同时也是教育发展的向标。 在乌氏看来, 民族既具有形式的丰富, 也有内在的渊源, 形式呈现是具有不竭力量源泉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 内在是沉淀在民族机体上的物理特质和历史蕴育下来的民族精神, 民族本体就蕴含着教育发展的动力和能量源泉。 因此, 教育要依靠民族承载聚化而产生的力量, 树立教育的民族身份, 以社会整体为平台、 实施基于整体国民的教育, 进而推动整个民族的科学、 文化的发展和道德水平的提高。 具象地来讲, 就是用自己有的、 潜在的民族资源去办教育, 秉持民族内在的基质, 重视历史进程的经验价值。 不难看出, 乌氏倡导的民族之于教育而言有两个逻辑思路: 首先, 民族具有固有的特征, 教育要遵循于这一特征, 不能照搬他国模式; 其次, 民族肩负国家、 社会发展使命, 教育与民族同行, 助推民族、 国家发展伟业, 教育实现了民族、 社会、 国家的高度密切结合, 一致前行。 最后, 基于教育的民族立意, 乌氏提出了俄国教育发展的三项向标性要素:“科学” “文化”和“民族”[10]166-170。
乌氏主张教育立足民族, 树立民族标旗, 但并不是闭门发展, 傲视一切, 应与世界教育文化交流, 借鉴世界教育发展经验。 民族是教育实施的根本, 应该从民族肌理结构出发来发展教育, 对待世界教育经验, 不能完全照搬。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教育系统, 而这个系统所依附、 依赖的存在基础无不体现民族的独特性、 独立性和完整性。 对于俄国, 其他民族教育系统并不适用, 以此教育系统标准, 来构建自己的教育体系是不可能的。 乌氏指出, 俄国所追求的非彼原则, 如果不加辨识, 机械地挪用, 自身的内核精神也会受损, 照搬他国教育模式和经验, 即使成为可能, 对于民族、 国家发展来说也起不到明显的作用, 更不会进入到高水平层次。[8]由此, 民族作为教育发展的基础和向标, 解决了俄国教育的路径问题, 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教育应该是民族、 人民的教育, 体现民族特征。 同时, 教育不能局限于民族, 需要世界教育经验。
2.3 推行教育民主与实施人道教育
推行教育民主, 实施人道教育是乌氏教育民族性思想构建的现实抱负。 乌氏立足国情, 锁扣近代教育的“民主”和“人本体”两大至尚理念论证, 在理论和实践上论证其合法性, 推行教育民主, 实施人道教育是确保教育与民族发展同行的规则金律和保障举措。
推行教育民主是确保教育与民族发展同行的规则金律。 1861年改革, 从历史深处看, 俄国力图创建公民社会, 在全域包括僻远的农村倡导、 实践呈现全新面貌的生活方式。 而新的生活方式的启动要以推行教育民主为先锋, 让教育成为国民的教育。 推行教育民主, 拓深教育程度, 从本质、 内在上对国民施加教育影响, 追求人民精神生活上的进步, 推动社会、 人民真正地发展向前。 恪守教育民主, 教育面向全体国民与俄国所处的时代及民族的发展运动状态是应然的。 1861年改革带给俄国的历史活力是前所未有的, 尤其在农村基层, 已经唤起了民众的强烈学习愿望, 社会和国家势必要拿出满足这种强烈学习愿望的教育模式, 那就是推行教育民主, 实施国民教育, 助推民族发展进步, 启发民族智慧, 强化、 充实民族意识。 否则, 教育与民族发展的力量不相映衬, 与时代的发展也不协调, 民族的进程要落后于历史的进程, 这样的落差会招致灾难, 延缓历史。 这也是1861年“2月19日改革法令”所关注的重大历史内容, 推行教育民主, 让教育现实地参与民众生活, 使受教育权利完全成为俄国民众心灵、 智慧享用的权利, 并捍卫、 保护这一权利。 由此, 1861年俄国大改革后, 推行教育民主, 教育面向国民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只有践行教育民主, 教育才能以民族发展作为参照标准, 才能发挥最大的功用和实现社会价值, 教育才能成为国家、 民族的日常事务, 真正融入到的人民的日常生活, 与民族的发展状态和民族的本性进行交互融和, 植根于民族的观念和特征。 这一切的实现都必须以教育民主和公平为历史前提, 科学、 知识、 技术这三项现代社会的典型要素才能内化于民族历史进程。 可见, 在发展国民教育事业中, 坚守教育民主是金律规则, 只有如此, 教育才能与民族同行, 强化、 巩固教育的民族品格, 产生巨大的教育力量。
实施人道教育是确保教育与民族同行的保障举措。 1861年, 俄国废除农奴制成为了教育抚慰民族精神创伤, 塑造教育民族品格的新历史起点。 怎样培养孩子?教育孩子?怎样办好国民教育?这些问题亟待做出科学回答。 乌氏给出了根本性地解答, 即在国民教育中实施人道教育, 人道教育先行, 使教育与民族发展轨道同迹。 在初等、 中等、 高等教育学校先行贯彻实施人道教育, 人道教育要先行于专门实科教育。 因为, 无论从教育的过程结构, 还是从人成长的历程层次, 人道教育的作用和意义是首要的。 人道教育一般地思考为从内在发展人的精神和心灵, 灌输信念, 培养、 加固爱国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 养成有信念、 有理想、 遵法守信、 诚实、 谦逊和意志坚强的品质。 专门实科教育则指的是传授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 在乌氏看来, 人道教育和专门实科教育不可或缺, 缺一不可, 但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或各级学校中侧重面不同。 在初等和中等基础教育阶段, 应侧重人道教育, 但科学知识也是实现初等和中等基础教育目标必需的。 在高等教育阶段, 人道教育要伴随着科学知识教育而进行, 通过科学知识的学习来进行、 巩固人道教育。 可见, 人道教育在初等、 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仍旧是主要任务。 乌氏指出, 在各个教育阶段, 如果人的人道方面不首先发展, 那么科学知识和实科技术对人是有害的, 它会使人的精神变得干枯直至死亡, 人道教育对于专门实科教育来说也是是基础性的。 人道教育是乌氏教育民族性思想的精华部分, 因为关系到教育的每一位受众, 同时, 也关乎教育实践中人的健康成长。 人道品质对于不同的民族来说存在差别, 但却是民族品格特性中的核心质素。 通过教育培养出的理想的人对于不同的民族同样存在差异, 但任何民族都竭力追求通过符合民族的教育在人的身上培养出体现民族特征的人道品格。 对于任何民族, 人道品质与这一民族的性格和品格是相符合的, 由民族的社会生活决定, 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 正是通过实施人道教育牢固确保人的成长符合民族对人的理想诉求, 以最美好的人道品质对理想的人进行雕塑。 在国民学校、 各个教育阶段和各级学校实施人道教育, 并作为一项主要任务, 无疑是一项保障性举措。
综上, 俄国教育民族性思想是在对官方教育理念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 同时, 受容了俄国社会思潮中“民族性”观念。 教育民族性思想以“民族性”为硬核逻辑, 从内在视野把俄国近代教育纳入国家议程, 重视民族历史进程中的经验价值, 塑造教育的民族品格。
3 结 语
乌申斯基对教育民族性思想的阐释, 既不同于西欧派主张照抄西方教育制度, 也区别于斯拉夫派固执排外, 拒绝西方经验遗产。 教育民族性以俄国公共教育作为背景图像, 以民族话语作为方法论, 明确了俄国教育的发展观。 教育民族性思想呈现出了教育发展与民族、 国家发展内在密切的逻辑关联。随着时代的发展, 教育与民族、 国家的关系不仅仅是决定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 同时也是教育发展的规律性表征, 人是教育的核心概念, 国家是教育的逻辑舵盘, 民族是教育的灵魂。 教育民族性思想具有永恒的意义, 立之于当今, 置之于世界, 仍可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