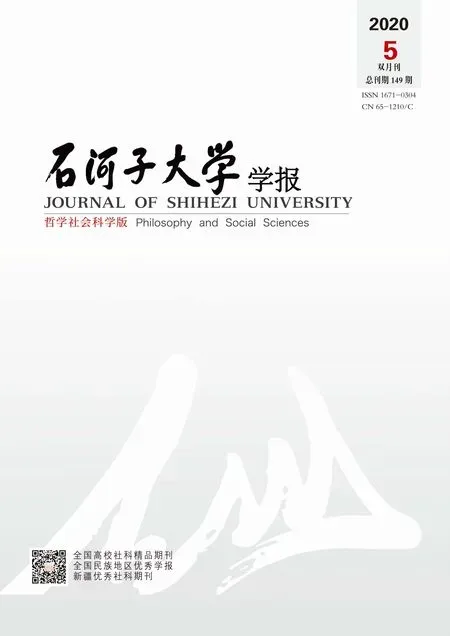敦煌佛教邈真赞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李小荣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邈真,又作邈影、写影、写真、绘真、图真、彩真、真仪、真影、真像、真容等,与此相关的文学作品,最常见者叫邈(写)真赞,它们属于中国传统文学题材之“像赞”类。而敦煌所出者,无不和当地丰富多彩的佛教社会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故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本文在总结前贤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关注敦煌佛教邈真赞研究的新动向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几点个人研究设想,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已有研究之回顾
纵观已有研究成果①敦煌佛教邈真赞,常常归于“敦煌碑铭赞”的研究范畴,相关研究综述主要有陈焱《近四十年来敦煌碑铭赞语言文学研究综述》,载于《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5-9页。另,范英杰、陈焱《百年敦煌碑铭赞研究论著目录》,郝春文主编《2018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29-370页,则从“敦煌碑铭赞校录与整理”“敦煌碑铭赞本体研究”“书评”等13个方面对已有论著进行分类,也有参考价值。,主要包括四大层面:
(一)文献整理
敦煌文献主要是写本抄本和稿本,俗字盈篇,修改和笔误都较常见,因此,正确的释读与录文,是保证高质量、高水平研究的基础和根本前提。总体而言,这方面的成果多能后出转精。就拿几部有代表性集成式论著来说,陈祚龙197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五代敦煌名人邈真赞集》(首次较全面地校释相关作品),因主客观多种原因,录文失真之处较多①陈祚龙先生其他敦煌文献校录也一样,虽有刊布传播之功,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参张涌泉《陈祚龙校录敦煌卷子失误例释》,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6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320页。。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在饶宗颐指导下完成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所收篇目增至92篇,录文质量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②王惠民《〈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评价》,载《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第153页。。张志勇《敦煌邈真赞释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则在敦煌佛教邈真赞文学的普及方面作出了新尝试,虽然“做到普及性与专业性的统一”,但离“深入浅出”还有距离③刘跃进《深入不易 浅出亦难——张志勇〈敦煌邈真赞译注〉平议》,载《兰州学刊》,2016年第3期,第5-8页。;而且,因作者未全面核对原卷,所以在校勘、训释方面存在不少问题④龚泽军、张嘉楠《敦煌文献注译与阐释中的语言学问题——以〈敦煌邈真赞释译〉为例》,载《社科纵横》,2018年第3期,第113-119页。。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皇皇三大册,127万余字,是目前辑录最全、解题最详的校录本,整理者并且把相关历史人物的文献汇集到一块,极具参考价值,学术性、实用性也最强⑤该书1992年由甘肃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2019年增订,经过20多年打磨,质量更臻一流。郑先生《自序》又说,将推出《敦煌写本碑铭赞研究》,我们对此甚为期待。。然由于写本文献的复杂性,故仍然存有少许值得斟酌之处:如《凉州御山感通寺圣容记》之“依峰树刹,丹采(彩)于重宵;因林构宇,晚朱青于谅画”(第1497页),细察原卷图版,“重宵”之“宵”是“霄”之笔误,所缺之字,其右半部尚存“东”,结合上下文语境,似可录为“陈”;“谅画”之“谅”,当作“凉”,书手因形音相近而致误;从骈偶结构看,“晚”与“陈”词性不合(后者为动词),原本似作“掩”⑥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载贞观二十二年(648)释道恭之诗曰“不持金作缕,还用彩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绮相氛氤”(《大正藏》第50册,第258页下栏)。又,朱青,即丹青,后世类似用例颇多,如宋人孔武仲《子瞻画枯木》“更无丹青相掩翳”、华岳《雪中有戏》“尽将纯素掩丹青”等。,书手因音近而误为“晚”。
(二)史学问题之检讨
这是国际敦煌学界利用相关邈真赞而取得成果最多的领域,如前述范英杰、陈焱整理的《百年敦煌碑铭赞研究论著目录》中,就列有“敦煌碑铭赞”与“史事考辩”“职官制度”“政区地理”“民族关系”“世家名族”“石窟营建”“宗教文化”“社会生活”等八方面的成果,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制度、家族、建筑、艺术、宗教、区域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等专门史,并在相应领域多有补白之功。其中,饶宗颐对敦煌文物价值的判断及其研究方法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敦煌石窟所出的经卷文物不过是历史上的补充资料”,并“喜欢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们作为辅助的史料,指出它在某一历史问题上关键性的意义”⑦饶宗颐《我的学术自述——以敦煌学为例》,载《民族艺术》,2013年第3期,第5页。。
(三)佛教美术研究
敦煌佛教邈真赞各具体作品的生成皆和相应的邈真(画)有关,因此,从敦煌佛教的历史语境出发,借鉴美术史、美术考古学、图像学和视觉文化之研究范式所取得的成果日渐丰富。如饶宗颐《文选序“画像则赞兴”说》《敦煌白画》⑧前者原载南洋大学《文物丛刊》1972年创刊号;后者为法国远东学院考古学刊1978年中法双语版。、姜伯勤《敦煌的写真邈真与肖像艺术》⑨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7-92页。诸文,对佛教邈真赞的历史渊源、分类及相关画工组织有较全面的梳理;沙武田《敦煌写真邈真画稿研究——兼论敦煌画之写真肖像艺术》⑩《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第43-62页。,则详实考订了P.4522V等三份人物写真白描画的性质及其艺术特征;张善庆《高僧写真传统钩沉及相关问题研究》⑪《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第97-106页。,重在检讨敦煌高僧禅定写真图(特定个案)形制规范的历史渊源及“双履”意象的特殊功用;郑炳林《敦煌写本邈真赞所见真堂及相关问题研究——关于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研究之一》⑫《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6期,第64-73页。,则结合大量传世的唐五代文献,对邈真赞(文学文本)与所涉及神圣空间(真堂)的关联性有深入讨论;马德《敦煌绢画上的“邈真”与“邈真赞”》①参见颜廷亮主编《转型期的敦煌语言文学:纪念周绍良先生仙逝三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又特别研讨了前人有所忽视的绢画类邈真(即关注特殊的物质载体);郑弌《中古邈真赞论稿》(科学出版社2019版),称得上是本专题研究的最新成果,它以邈真从祭祀到纪功的功能变化为切入点,纵横交错,点面结合,大小传统并重,对敦煌有代表性的阴家窟、三家窟、曹家窟以及洪、隋文帝邈真、僧伽邈真等个案作品,皆有精彩论断,新见迭出,显示了“80后”佛教美术史新锐研究者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视野②郑弌已有多篇总结、反思佛教美术史研究方法的论文,如《宗教美术史研究方法论的三组主题词》,载《美术观察》,2016年第9期,第105-111页;《论宿白“区域模式论”的生成》,载《美术》,2016年第9期,第116-119页;《2017—2018年中国宗教美术研究新趋势》,载《艺术探索》,2019年第2期,第39-46页;《敦煌学与敦煌佛教美术研究新动向》,载《美术研究》,2019年第10期,第41-45页。。
(四)文学与文体学之探讨
这主要是从相关写本文献所展示的文学手法、语言运用(包括音韵、典故等)和文体学特征进行的研究:它们或从断代入手,通论某一时期邈真赞的内容特色;或着眼于具体写卷和单篇作品的文本阐释;或从文体比较出发,旨在揭示敦煌邈真赞的特异表现与成因。林林总总,成果虽不少③参前引陈焱所作之综述,此不赘论。,却尚未有深度理论性的总结之作问世。
在上述四大方面的研究中,文献整理是基础,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家的校录与释读可成为完整无误的定本,因此,这项基础性的工作仍然需要持续加力,特别关注。而且,文献校录也非易事,与其他三方面的研究一样,学人们同样要有多学科的知识背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否则寸步难行(这点也是敦煌学研究的共性所在)。此外,从已有成果的研究路径看,研究者多把邈真赞当作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主要聚焦于它们对专门史问题域的补白之用,成果虽然最多,但个人认为,其结论只是我们考察邈真赞创作背景、生成场域的一种参考,或者说,它们只为具体文学文本的真实性、应用性提供有力支持。
至于佛教美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与敦煌邈真赞的联系,相对说来,比历史文献学更为密切。一是图、赞往往置于同一神圣空间或应用场所,在仪式中互相配合而发挥功用,此在净土法门、密教坛场的表现尤为突出;二是因为大多数赞文生成于图像绘制之后,赞的创作常受制于图或粉本画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赞是图的文学表达④皎然《画救苦观世音菩萨赞》(载董诰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236页下栏)之“序”明确指出绘工画像的方式是“按经图变”,则知皎然像赞创作后于像,而且是“经”变为“像”后的文学书写,或者说是对“经”二重变奏后的情感表达。,而图像的构成要素及其排列组合、色彩运用、观看方法等,莫不对赞的写作产生影响。换言之,作家要写好邈真赞,首先须学会理解画师(工)创作的邈真,然后才会有自己独特的情感抒写。因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为深入阐释邈真赞文本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以免盲人摸象,缺少整体感和方向感。但当下邈真赞的文学研究,往往在这方面存在问题,即缺少佛教美术学思维和图像学视野。
当然,一个省份篮球事业的发展,不单靠一个俱乐部就能完成。广东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三支CBA球队、一支WCBA球队的省份。宏远队拿过8个CBA总冠军,而在去年举行的天津全运会上,广东篮球在男女成年组、青年组以及三人篮球项目中一共斩获三金、一银和一铜。
总体说来,目前敦煌佛教邈真赞的研究,主要以“邈真赞”之“邈真”为中心,而对“赞”本身的研究,并不充分。或者说,目前对邈真赞的研究,是重“史”轻“文”、重“真”轻“赞”。
二、未来研究之展望
对敦煌佛教邈真赞的文学研究⑤郑炳林《敦煌碑铭赞及其有关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日第5版,其着重从专门史的角度,对包括佛教邈真赞在内的敦煌碑铭赞与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归义军史的联系,提出了应重点关注的四大方面的问题。但涉及文学时,只讲了功德记的体例演变问题。,我们认为基本原则有二:一是固本强基,即继续加强原始文献的校读与整理,对此敦煌学界应通力合作,争取早日有相对可信的校录本问世;二是文学本位和跨学科的文化阐释相结合,具体例证详见后文。而未来的研究重点,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概念辨析及其细微差别
邈真、邈影、写影、写真、绘真等在佛教语境中常被视作同义词,虽然已有研究者指出了它们的某些细微差别:如姜伯勤主张“‘邈真’用指绘制佛像时”,“所‘邈’写的是佛的‘圣容真身’,这是一种想象的、理想化的图像”,用指现世人物“写真”时,“是依据真人肖像的真实比例来绘制”⑥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84页。。郑弌则进一步注意到邈真栖息之所的“真堂/影堂”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异同,他认为两者大体可视为一律,然从供奉对象看,真堂可以供奉多人,影堂祭拜主体更为单纯,多为本宗或本寺先师①郑弌《中古邈真赞论稿》,第4-6页。。诸如此类的观察都很细致,颇能给予人启迪进而发现更多值得思考的细节问题。如元明以降的佛教文献中,敦煌普遍使用的“邈真”就无影无踪了,而唐人未曾使用的“道影”出现频率较高,像憨山德清《八十八祖道影传赞》、鼓山永觉元贤《诸祖道影传赞》、紫柏真可《龙树尊者道影赞》、郑溥元《雪峰即非禅师道影赞》等,尤其是周永年编撰《吴都法乘》卷12还专门辑有《道影篇》,从其小序“起写人形,过有绘事。画佛菩萨,爰及其次。师僧所居,禅请律寺。龙象趋随,中瓶执侍。人有存亡,像惟一视。水边林下,图厥高致”②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第34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年版,第423页上栏。及所收明本、法藏、真可、范成大、倪瓒、宋濂等人作品看,作者不分僧俗,无论自赞、他赞,只要赞颂佛教影像者(包括居士,如徐学谟《任隐君像赞》等),悉可归入“道影篇”。换言之,在周永年心目中,“道影”可以涵盖全部的佛教人物画像乃至佛教人物的遗物和遗迹(如舍利、遗发等)。当然,若穷源竟委,模写僧人道影之举,一则与古印度“佛影”东传华夏有关,二则受贾岛《哭柏岩禅师》之名联(颔联)“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③齐文榜《贾岛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的广泛流布之影响④按,此联宋代以来的诗话类著作,如《六一诗话》《竹庄诗话》《西清诗话》等讨论甚多。,是“行道影”之略称⑤“ 行道影”,本身也是名词,如明河撰《补续高僧传》卷10载宋瞎堂远“室挂行道影”,《卍续藏》第77册,第434页上栏。此外,后世也有借用贾岛诗句者,如徐祚写广教寺云“写得旧时行道影,不教尘土涴袈裟”,吴之鲸《武林梵刹志》卷4,《大藏经补编》第29册,第541页上栏。。“行道”和“坐禅”,则是互文,即柏岩禅师所留下的“道影”是邈其坐禅之真像⑥如敦煌第17窟即是洪的影堂(影窟),其中所塑即为洪之禅定像。,结合李益《哭柏岩禅师》颔联“影堂谁为扫,坐塔自看修”⑦〔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16页中栏。,此“道影”当置于柏岩圆寂后的影堂中。
再如,前述郑弌讨论过的“真堂”,《佛光大辞典》释义为:“禅家安置祖师肖像之堂。通常与土地堂分建于大殿之左右侧,其内置有达摩祖师、百丈、临济及各宗派开宗祖师之像。”⑧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年版,第4220页上栏。但此界定仅限于禅宗。其实,不论僧俗皆可建真堂,如P.4660(9)《沙州都押衙张兴信邈真赞》是“乾符六年九月一日题于真堂”⑨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422页。,P.4660(14)《河西都防御右厢押衙王景翼邈真赞并序》云“痛临坟之哽噎,写真迹于真堂”⑩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451页。,P.3718《程政信和尚邈真赞并序》谓“图刑(形)绵帐,邈影真堂”⑪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1039页。,此等皆为明证。齐己《题东林十八贤贞(真)堂》“白藕花前旧影堂,刘雷风骨画龙章……何人到此思高躅,岚点苔痕满粉墙”⑫王秀林《齐己诗集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5页。又,本诗“影堂”“真堂”交替使用,则知其时二词无意义之别。,由此则知净土宗也有“真堂”之设。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十月,有敕曰“每年内中出香一合,送西明寺故道宣律师堂,为国焚之祷祝”⑬〔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0页。,则知律宗同样存有真堂(影堂)。
又如“真容”,《佛光大辞典》释义为“原指本来之姿容,于禅林中,指开山历代祖师之尊像”⑭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第4218页中栏。。编撰书时似有禅宗中心主义之倾向,解释义项时常常往禅宗那里靠。实际上,它可指圣像(如“三宝”之“佛”与“僧”),也可指俗人之容貌。前者如S.4511《结坛转经发愿文》曰“是以挂真容于内阁,结神坛于宝台”⑮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603页。,此“真容”当指坛场中所观想的各种尊像(包括佛、菩萨等);后者如P.3718《归义军节度押衙曹盈达写真赞并序》说“生前仪貌,逝已奔驰;死后真容,丹青仿佛”①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1009页。,并且“真容”和“仪貌”互文。更可注意的是,有的敦煌文献表明,“真容”除了指单尊的佛、菩萨像,有时也可以指称经变类的故事画,P.3302V《某氏宕泉创建三龛功德记》曰“主事已毕,愿写真容。遂于绵帐上接绘弥勒三会并侍从,下接绘貌真影”②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1481页。,反复揣摩上下文,此真容应涵盖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弥勒菩萨在龙华树下成佛时三会说法而度人的故事(弥勒经变),二是供养人的写真像,即供养人把自己作为三会说法时的听众之一。波斯顿美术馆藏No.201570开宝八年(975)所绘《观音经变》,其榜题“或在须弥峰”“坠落金刚山”“或漂流巨海”“推落大火坑”显示,该经变至少讲述了观音救难中的四个小故事,题记概述绘制目的时又明确说“邈写真容,结当来之胜福”③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1614页。,则知此画所邈写的真容(邈真)包括《观音经变》中的人物(六臂观音、善童子、恶童子、四个落难者)及相关供养人(记中交代是灵修寺法律尼义净、明戒)。甘肃省博物馆藏淳化二年(991)《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上有《绘佛邈真记》曰:“上图佛会而融千,下邈真仪而一样。”④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1647页。“佛会”云云,主要指中心画面的经变内容,“融千”似指最上端七佛的教化之用;下邈的“真仪”则指下部的供养人法律戒行之像。它和前述《观音经变》的最大不同是,抄录了《佛说报父母恩重经》的经文,故有人怀疑该绢画是悬挂讲经之用⑤郭晓瑛《甘博藏敦煌绢画〈报父母恩重经〉内容新探》,《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2期,第74-81页。。
其他如真影、真像、祖堂、灵祠等词语,都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并且,前述名词,无论表图像还是表空间处所者,在儒、释、道三教文献中并用,因此,它们在不同宗教语境中的异同,更值得深入细究。
(二)跨学科的文本阐释
敦煌佛教邈真赞作为特定图像的说明性文字,后世读者在进行阐释时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一是原图多数已被历史的尘沙所吞噬,图文合一并保留至今者寥寥无几,因此无法全面系统地做到一对一的图、文对照研究,要是以文学文本来还原特定图像的全貌,可能是劳而无功之事,何况邈真赞的作者对进入文学文本的图像要素也有一定的选择性。二是不同读者因其自身的关注点不一,或侧重于图像内容的考释,或关注图文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及其史学价值,等等,故所得结论不尽相同。三是后世读者与邈真赞作者,虽然都是读图之人,却因时代变迁,读后感、观感却未必相同。当然,相对说来,赞文作者比后世读者更具优势,因为他们多能亲临邈真的创作、使用或留存所在⑥如前文所引《河西都防御右厢押衙王景翼邈真赞并序》“痛临坟之哽噎,写真迹于真堂”,可知此赞作者王氏邈真的创作、使用情况都有亲身的感受。再如,贞元四年(788)沙门义全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作邈真,符载亲临现场作《写真赞》十三章,参氏著《剑南西川幕府诸公写真赞并序》,载《文苑英华》卷783。。四是有时邈真的图、赞、书者各一,这对图、赞传播有较大的影响。拿敦煌来说,就有画工制图、名僧悟真写赞、恒安而书的多篇文献⑦参P.4660(4)《都僧政曹法镜和尚邈真赞》等。;传世文献中这类记载也不少,如华严宗清凉澄观示寂后,是“相国裴休奉敕撰碑,文宗皇帝敕写国师真奉安大兴唐寺供养,御制赞”⑧〔清〕道霈编《华严经论疏纂要》,载《大藏经补编》第3册,第5页。,疏山证禅师灭后由“门人写影,法眼赞”⑨《景德传灯录》卷20,《大正藏》第51册,第367页下栏。。总而言之,出自名家手笔之真、赞,常“为世所贵”⑩语出《宋高僧传》卷29《唐越州大禹寺神迥传》,第724页,作者特别称赞了神迥“辞笔宏赡,华藻纷纭”。、教化之用也更大⑪如《宋高僧传》卷12载余杭径山释洪諲“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辞众而卒。霅溪戚长史写貌,武肃王为真赞”,第284页。武肃王,即钱镠,其亲制赞文并执丧礼之举,自然对洪諲及其弟子大行教法于两浙甚有助益。。
鉴于上述几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尽可能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才能对敦煌佛教邈真赞的文本作出更有效的阐释。兹以P.4660(24)《敦煌唱导法将兼毗尼藏主广平宋律伯彩真赞》(原题如是,署“鄯州龙支县圣明福德寺前令公门徒释惠菀述”)为例,略作分析如下。原赞曰:
维大唐咸通八年岁次丁亥六月庚午朔五日甲戌题记。
弟子比丘恒安书。
宋法和尚灵塔,讳志贞,灵图寺①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第502页。。
本赞作者惠菀、书手恒安皆为像主宋志贞的弟子,“彩真”之“彩”字,说明邈真不是白画或画稿,而是彩绘之作。此赞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详细描述像主的容貌,只是以志贞的家世、宗教实践经历为线索,重在歌颂其化导之功。赞词虽然使用了不少佛教名相(人我、七众、苦、空等),但看不出志贞的宗派归属。而且,赞词本身也比较平淡,已有程式化的倾向②惠菀还有《敦煌都毗尼藏主始平阴律伯真仪赞》,录文参前引郑炳林书,第570页,两者写法完全相同。。表面看来,它的文学价值并不突出。
不过,如果从制度文化史的角度③笔者曾有尝试之作,参李小荣《制度文化视域下的唐宋寺松意象群——以松僧、松塔为例》,载《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1期,第68-75页。来看待这篇佛教邈真赞,它自有特殊的文学价值:一者它牵涉到敦煌佛教文学讲唱制度的历史演变问题④参姜伯勤《变文的南方源头与敦煌的唱导法匠》,载《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395-422页。。题目中的“唱导法将”点明了志贞的唱导师身份。中土的唱导制度,东晋庐山慧远法师有过第一次改革,即设立了首席唱导师制度,简称“导首”,隋代译经僧释彦琮进行了第二次改革,其所撰《唱导法》在后世深远影响。二者涉及到讲唱文学内容的变化,唱导原以佛教“经”部故事为主,此时则“经”“律”兼备。题目中的“律伯”一词,最早似见于“惟杨(淮扬)龙兴寺桑门藏诸”大历三年春所作《法华玄赞决择记序》“律伯清公,修饰之”⑤《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34册,第126页上栏。又,《法华疏决择记》是由杭州沙门崇俊撰、杨州禅智寺释法清集疏。,清公指释法清。“毗尼藏主”,点明了志贞的律师身份⑥姜伯勤《敦煌毗尼藏主考》,《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323-339页。又,姜先生特别指出,敦煌“律伯”类高僧,多禅、净双修。。换言之,志贞在“开畅玄宗,七众归化”的弘法活动中,是把“唱导”与“律讲”⑦律讲是佛教讲唱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法华经玄赞要集》卷1开篇即说“栖复自大和末,罢律讲后,屡涉京师,辄厕经论末行”,《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34册,第171页上—中栏。而唐诗叙述律僧讲律者也较常见,像张籍《律僧》“持斋唯一食,讲律岂曾眠”、《送律师归婺州》“京中开讲已多时,曾作坛头证戒师。归到双溪桥北寺,乡僧争就学威仪”、张祜《题惠昌上人院》“律持僧讲疏,经诵梵书文”等,从中可见,律师重威仪,讲律时可依据特定的律疏。进行整合。值得注意的是,S.6651把说三归五戒和讲唱《佛说阿弥陀经》的内容合为一卷(尾残),其文本性质,和志贞“开畅玄宗”之举颇相契合。三者“灵塔”一词,表明该彩真用于志贞舍利塔丧之时,“涤垢莲池”是门徒的荐福之词,意在祝愿老师往生西方净土。而类似“塔”“影堂”“邈真”之佛教文化意象组合,也见于中唐王建五绝《题柏岩禅师影堂》“山中砖塔闭,松下影堂新。恨不生前识,今朝礼画身”⑧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756页下栏。,因为“画身”就是邈真,同样为影供瞻仰礼拜之用。
(三)应用文体的多功能阐释
邈真赞从本质讲是实用文类,按照郑阿财敦煌佛教文学“赞颂”“自证”“弘传”三大功能的分类⑨郑阿财《敦煌佛教文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顾名思义,邈真赞自然是属于“赞颂”类。但是,实际情况则复杂得多,如有的“自赞”,既有“自证”内容,又有“弘传”之用⑩此在传世佛教文献更常见,如敬遵、宗杲、了元、怀深、祩宏等都有自赞画像之作。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王十朋等佛门居士有自题写真之作。特别是禅师应别人之请而作的“自赞”(如宗杲),多有“弘传”之用。。考赞的起源,和音乐关系甚为密切⑪刘勰追溯“赞”之起源时说“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页。,部分赞词还可以引导信众的礼拜和观想,如净土宗有“赞叹门”,其歌赞的引导之用尤为突出。因此,对敦煌佛教邈真赞的阐释,仅从单一功能论出发,很难分析全面而得出满意的结论。
敦煌佛教邈真赞的文本结构,从抄存形态看,主要有两种:一是赞前有序①需要指出的是,不少写卷标题有“并序”二字,却未抄写“序”,如P.4660(11)释悟真撰《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持节瓜州诸军事富守瓜州刺史兼左威卫将军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康使君邈真赞并序》等。,二是有赞无序②当然,也存在本来有序而书手省略的例子。。赞词本身句式多样,常见的有四、五、七言(偶见骚体),个别用接转体③如P.4660(20)悟真撰《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是恒安所抄,赞文主体是四言一韵到底,但最后四句是骚体六言。参《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484页。。而序、赞完整者,序为散文,赞(或称词)为韵文,韵文基本是对散文内容的重复和高度浓缩(只是语言表达更为简洁精练),此种模式与汉译佛典的“祇夜”(应颂、重颂)颇为一致,较早像卢照邻《相乐夫人檀龛赞》、严郢《大唐大广智三藏和上影赞》(并序)之像赞,分别用“重宣此义,敢为赞云”④董诰等编《全唐文》,第747页上栏。,“重宣此义而作赞曰”⑤《大正藏》第52册,第847页中栏。,显然还带有鲜明的佛经语言之特色。敦煌佛教邈真赞,虽未用“重宣”一类的提示语,但好用“聊申短颂”“聊为赞曰”一类的套语,叙述创作背景时又好用“毕功记”,凡此,都是姜伯勤所归纳的敦煌邈真“程式化”⑥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84页。写作的表征之一。郑炳林、郑怡楠谓P.4660(33)李颛撰《沙州释门都法律氾和尚写真赞》与P.3726释智照撰《释门都法律京兆杜和尚写真赞》相比较,“除少数句子稍有增删外,其余完全一样”,故推测“李颛抄袭智照之文,稍加改动而成”⑦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551页。,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它恰恰是敦煌邈真赞程式化的表现之一。
敦煌僧人之邈真,无论生前预写或营丧时所绘,通常都安置在真堂、影堂或影窟。但是,在具体营葬进程中则会使用多种运载工具,其中和邈真像有关的是邈舆和生仪舆⑧如P.2856V《乾宁二年(895)三月十一日营葬榜》载僧统和尚悟真迁化后,安排在当月十四日葬,而“准例排合葬仪,分配如后”:“邈舆,仰子弟、庆林律师、智刚律师”“生仪舆,仰当寺”。P.2930《都僧政和尚营葬差发帖》则说邈舆“孟老宿、保印、智光、保护”,“生仪舁:智胜”(舁、舆,义同)。又,敦煌还有专门的行业组织,S.4252V《付物物历》就提到了邈舆社、邈生社等。。二舆之别,大概邈舆所载是丧葬写真,其像更具理想化、程式化之色彩,生仪舆则为生前写真,与后世所说肖像画更加接近⑨按,此点受王中旭《敦煌吐蕃时期〈阴嘉政父母供养像〉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3期 ,第114-115页)启发而有所推论,特此说明。。考 P.4660(31)《禅和尚赞》云“于此路首,貌形容仪。丹青既毕,要叚(假)文晖”⑩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536页。,从“路首”推断,知此“禅和尚”的邈真先安置于交通要道,一则方便来来往往的善男信女观瞻,二则该邈真应该是用邈舆或生仪舆载回其最终栖息地真堂或影堂的。而敦煌车载邈真像之举,当和印度传入的行像仪轨⑪对印度佛教行像的详细描述,可参《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卷1等。有较大的关联性,因为二者都有纪念意义,只是纪念对象有别而已,即一为现世高僧,一为佛陀。因此,从印度行像仪式的中国化、在地化(特指敦煌)视角来检讨相关邈真赞,也可能是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敦煌佛教邈真赞叙述观像感受时,最常用“瞻”字组合如“瞻谒”“瞻攀”“瞻礼”等,而其他观像者如亲临真堂、影窟的信(观)众,或像主的后代子孙,甚至千年之后的当代读者,理解邈真及赞,都离不开佛教特殊的“观看之道”⑫李小荣《观看之道:佛教图像学传播的哲学思考》,《学术研究》,2014年第6期,第128-134页。。如P.3556《河西管内都僧统康贤照和尚邈真赞》“上图灵像,永奉福田;下题形影,恒祈香坛”、P.2481V《沙州修缮大云寺及州东大寺功德记》“仍裁绵帐,上绘观音,下邈真形”⑬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893、1083页。等所描述的上绘尊像、下绘供养人邈真像的构图模式,其供养人和尊像与之间的“观看”关系,即属于“四种观看”中的第三种或第四种观看①李小荣《观看之道:佛教图像学传播的哲学思考》,载《学术研究》,2014年第6期,第1314页。。英藏敦煌幡画Ch.liv.006彩绘观世音菩萨一躯,菩萨下方则绘男女供养人两躯,题记把亡故的供养者(比丘尼严会、试殿中监张友诚)之像都称作“邈真”②参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1600页。,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天成四年(929)清信弟子樊宜信所造药师琉璃光如来绢画,记中又明确交代“兼邈二亲,对释尊之足下。日常焚香,拜降福之瑞获”③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1604页。,故综合判断,无论供养人在世与否,邈真像与尊像的共置,是隐喻供养人佛教实践中的永远在场④图像叙事研究,又需要关注“不在场的在场”(指代际传承的族群知识)。参孟令法《“不在场的在场”:图像叙事及其对空间神圣性的确定》,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47-156页。。因此,从图像的“观看之道”来阐释邈真赞,也很有必要。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当代读者、邈真作者与画师画匠“观看之眼”的异同及其对像、赞表达与理解的影响⑤参李小荣《“经”“像”“诗”的双向互动——观看之道与唐五代释家绘塑类诗歌的文本解读》,载《学术研究》,2017年第2期,第146-148页。当然,“四种观看”的前两种观看及佛教传统的“总观”“别观”,在敦煌邈真及赞中都有体现,限于篇幅,此不赘举实例。,同时,这也是该研究路径的难点所在。
前引P.2856V、P.2930等叙述敦煌僧人营葬的社邑文书,除提及邈舆、生仪舆之外,还有灵车、香舆、钟车、鼓车、九品往生舆、纸幡、大幡等多种物品,由此推测,当地高僧的丧仪较为复杂,既受儒家传统影响,更受佛教文化之熏染。如“九品往生舆”和净土宗在敦煌的流行息息相关,而“纸幡”所绘引路菩萨,具有接引往生的宗教功能⑥王铭《菩萨引路:唐宋时期丧葬仪式中的引魂幡》,载《敦煌研究》,2014年第1期,第37-45页,特别是第43页。。像法国吉美博物馆藏MG.17662太平兴国八年(983)清河郡娘子张氏绘佛邈真中,引路菩萨是披帽地藏王,“邈真赞并序”明确指出创作背景是张氏“掩弃人寰,难明前路之黑白。遂减资财,兹绘真容,用益亡灵”⑦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1627页。,因此,释读本赞及其图像的含义,必须结合相关的丧葬礼仪之制度。
(四)佛教美术思想观念的深度挖掘
敦煌佛教邈真,无论祭祀纪功,都是实用性很强的宗教美术作品,但它们除了实用性之外,其他方面的美术(或美学)思想观念也值得再挖掘。前贤时彦在这方面已有所总结,如段文杰以敦煌壁画为例重点分析了传神艺术(以人物为主)的类型和表现手法⑧段文杰《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载《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107页。;姜伯勤详细阐述了“邈影如生”观念对敦煌美术“以形写神”的贡献⑨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86-90页。;杨娜发现敦煌陷蕃以后的画赞,其传统来自中原,但其高僧写真像赞有其特殊之处,即它不是以寺院祖师像为主体,而是从属于僧官的谱系⑩杨娜《吐蕃占领敦煌时期邈真赞问题的探讨——兼论唐代高僧写真赞》,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艺术设计版),2011年第2期,第33-35页。。诸如此类,都给人良多启示。未来对此方面的检讨,我们认为,只有在更全面的比较视野之下,才能更深入地挖掘敦煌邈真所蕴含的独特的佛教美术思想观念的深刻性。兹举3例如下:
一者 P.3405(4)《营窟稿》指出敦煌石窟相关塑像之原则是“龛中素象,模仪以(与)毫相同真”⑪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以”,按照河西方音的读法,可校为“与”,参邓文宽《敦煌邈真赞中的唐五代河西方音通假字例释》,载《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第310页。,此“同真”思想,是敦煌各种邈真像(尊像、高僧、信士等)共同遵守的指导思想⑫如P.4660(11)《瓜州刺史兼左威卫将军康秀华邈真赞》即说“图形新障,粉绘真同”。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 430 页,“真同”,即“同真”。。然考其历史来源,又和更早的南方造像、长安邈真中的美学思想之影响有关:如道宣《续高僧传》卷30《隋蒋州大归善寺释慧偘传》说慧偘“翘敬尊像,事同真佛”⑬《大正藏》第50册,第652页中栏。,意即观瞻造像与佛陀本人的教化效果并无不同;严郢《大唐大广智三藏和上影赞》又称赞不空真影“画图惟肖,瞻仰如在”①《大正藏》第52册,第847页中栏。,“惟肖”“如在”,意在强调“邈影如生”的重要性,何况不空在武威所译密教经典和仪轨在敦煌多有流传呢,想必长安所绘遗影,与其译经一样成了敦煌密教必不可少的读物之一。而后世僧人所绘邈真,亦追求“真”与“神”,像北宋文彦博《贤大师以诸巨公画像见示,传神写照,曲尽其妙,兼丐拙诗,辄成一首奉呈》开篇即说“用志专精妙入神,援毫肖像夺天真。能将绘素传奇表,似与公侯结胜因”②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4页。又,从“与公侯结胜因”分析,邈真及赞还是僧俗交往中重要的文学艺术媒介之一。,“天真”与前述“同真”,其义一也。
二者法国吉美博物馆藏MG17659太平兴国六年(981)绘千手千眼观音菩萨邈真像上,其功德记写道“会命丹青,笔涤绢帛。间邈菩萨,尊绘侍圣之相辉辉而洞明;境界似活,形仪光显显而夺人眼根”③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1623-1624页。,此“似活”和S.3929《节度押衙知画行都料董保德等建造兰若功德记》“画蝇如活,佛铺妙似于祇园”④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1437页。的“如活”,含义完全相同。但前者着一“境界”,较“同真”偏重于个体形象的真实性而言,“似(如)活”似更强调人物群像及其生活场景的可信性,或者说,“同真”更侧重于个体形象的静态美,“似活”更重视群体形象的动态美(或静中求动)。
三者敦煌邈真对所描述的僧人、居士形象,无论从价值判断、审美判断看,全都持肯定态度,偶像崇拜的倾向比较明显。但在同时或后世的禅宗文献中则恰恰相反,禅师往往从般若性空或中道思想出发,反对执著于色像之假有。如曹洞宗良价禅师《真赞》说“徒观纸与墨,不是山中人”⑤《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大正藏》第47册,第516页上栏。,《宏智禅师广录》卷9载天童正觉禅师《禅人并化主写真求赞》又云“秋生眉目,霜侵发须。诸法之相了空寂,妙存之性非有无”⑥《大正藏》第48册,第114页中栏。。原因何在,拟另作专文再检讨。
总之,敦煌佛教邈真赞作为特殊的文学品类,因特殊的创作背景、使用场合以及它们具有历史学、图像学和宗教仪轨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未来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