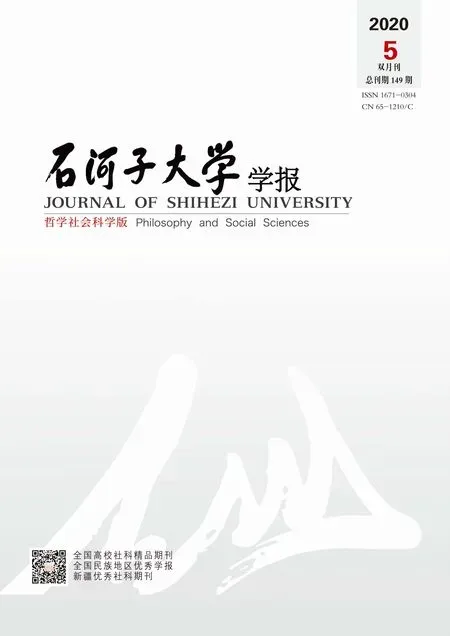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信息披露义务
包红光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3;2.湖南科技学院 法律系,湖南 永州425199)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 3月,欧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CJEU)收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undesgerichtshof,BGH)提出的请求,让其澄清版权所有人可以从网络平台获取哪些有关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的信息①参见《CJEU将确定版权侵权数据请求的范围》,http://www.ipr.gov.cn/article/gjxw/ajzz/bqajzz/201903/1933649.html,2019-03-15。。事情的起因是,在德国康斯坦丁电影公司(Constantin Film)诉YouTube著作权纠纷案件中,版权所有人请求BGH判令YouTube披露涉嫌侵权人的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及IP地址。根据《德国著作权与邻接权法》第101条第3款,负有提供信息义务的人必须告知侵权者的“姓名(名称)和通信地址”[1]140。BGH有意裁定涉嫌侵权者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应被披露,但不确定权利人是否有权获取网络用户的IP地址,因为IP地址与设备而非人有关,可能不被视为用户的个人地址。BGH于是请求CJEU确认IP地址是否包含在欧盟《知识产权执法指令》第8条第2款①欧盟《知识产权执法指令》第8条第2款规定:第1款中所需提供的(和知识产权侵权有关)信息包括生产商、制造商、销售商、供应商、其他预先持有人及后续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姓名和地址,以及商品生产、制造、销售、接收和预定的数量和价格。规定的信息范围之内,以及如果包含在内,是否能扩展至用户上一次登录平台账户的IP地址,无论用户在该时间点是否实施了版权侵权行为。
早在2008年,欧盟法院在Spanish right holder group Promusicae诉 Telefonica(网络服务平台)一案中就裁定,不能从欧洲立法中得出成员国网络服务商有义务在民事诉讼中提供个人数据,以确保有效保护版权[2]。可见网络服务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ISP)②网络服务提供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包括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内容服务提供者、存储服务提供者和信息定位服务(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狭义上特指单纯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主体,不包括内容服务提供者(ICP)。本文采狭义,因为ICP由网络服务商直接提供内容,因此不存在披露网络用户著作权侵权信息的问题。信息披露并非一个新鲜的话题,而是存在长期的争论。ISP的著作权侵权信息披露涉及版权人与ISP之间的利益角逐,也关乎版权保护与公民隐私权、表达自由之间的价值取舍,各国对此立法态度不一。我国已于2013年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规定了ISP对著作权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但是较为粗疏。现行有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06)只规定了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基于查处侵权的需要可以要求ISP披露涉嫌侵权人的身份信息,其他立法对此问题则并不明确。司法实践中为数不多的判例仍然沿袭已经废止的《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精神,且有所变通,司法与立法不尽一致,反映出该问题在我国还存在较大争议。因此,有必要剖析著作权领域ISP信息披露涉及的利益和价值冲突,考察域外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并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建立完善进行展望。
二、争议的根源——利益纠葛与权利冲突
(一)版权集团与ISP的利益之争
版权制度自诞生至今,一直都是资本各方利益争夺的战场,保护作者利益和激励文化创新不过是点缀其上的饰品。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法——《安妮法案》的出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出版商为了继续垄断图书出版市场所做的努力和游说[3]12。20世纪50年代,在以信息技术、材料技术和空间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之下,留声机、唱片、电影摄影机、收音机和广播电台先后问世,原先的版权法捉襟见肘,各个利益群体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游说和艰苦卓绝的谈判[4]。最终的结果是版权进一步扩张,资本的利益得到了平衡和维护,公共领域日渐缩小。20世纪后期,当数字技术与网络通信技术相结合,一种全新的作品传播方式——信息网络传输产生了。信息的收集、储存、加工和传播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网络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传播速度,降低了作品的复制传播成本,侵权开始泛滥,尤其是网络信息分享平台的搭建和P2P技术的推广,更是为盗版提供了滋长的温床。传统版权集团的利益遭到侵蚀,新兴的网络运营商的能量也不容小觑。为了平衡双方的利益,立法机关一方面重申“版权至上”,另一方面又为ISP提供了免责的避风港,即ISP没有审查网络的义务,但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之后,应当及时删除侵权信息。美国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率先确立这一规则,并迅速在世界各国推广开来。
按照“避风港规则”,ISP只要遵守“通知+删除”要求,一般来说就可以免除侵权之责。版权人为维护自身利益需要追及直接传播作品的侵权者,网络的隐蔽性却让版权人无从下手,惟有借助于ISP对涉嫌侵权者身份信息的披露。很多国家在确立“避风港规则”的同时,也规定了ISP的信息披露义务,以期再次平衡各方利益。对于ISP而言,信息披露会影响到其视之为“衣食父母”的网络用户的去留,过多的信息披露也会产生巨大的运营成本,错误的信息披露还可能带来违约和侵权的风险,他们自然会表现出强烈的抵触。版权集团和网络运营商再次发生利益之争,不同的取舍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同国家相关立法的不同安排。
(二)版权保护与隐私权、表达自由的价值冲突
不管背后的利益之争如何云谲波诡,从公共话语来看,版权人要求ISP披露侵权者的身份信息,其最大的阻力来自公民隐私权和表达自由的保护,这也是ISP运用更多的抗辩理由。
1.信息披露与隐私权的冲突
隐私不存,人之完整性亦将不在[5]16。在西方社会,隐私被奉为人类最重要的一种需求,是个人尊严的基本依托。除了维护尊严和约束侵犯,隐私的作用还在于可以限制政府的为所欲为。正如学者劳伦斯·莱斯格所言,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的世界中,那将是对“被孤立”概念的一大挑战[6]228。一般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7]12。印刷版权时代,个人使用对权利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并未进入版权人的视野;电子版权时代,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发展让个人使用变得轻易而频繁,个人使用开始受到质疑,但是基于“市场失灵”和使用者隐私权等人权保护的考虑,个人仍未成为版权法规制的对象;信息网络时代,个人使用的成本趋近于零,个人使用的方式发生结构性变化,个人使用行为的潜在影响逐步增加,个人逐渐成为版权实施的监控对象,版权保护与使用者隐私权的冲突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8]27-29。ISP的信息披露与使用者隐私权的冲突更为直观。网络用户在网络上注册的信息包含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尽管姓名、性别、联系方式等信息并不属于传统隐私权的范畴,而是一种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的可识别的社交信息。但是在网络环境下,这些信息一旦被披露、被恶意利用,就极有可能对个人的生活安宁造成严重影响,实践中“人肉搜索”酿成的悲剧反复证明了这一点。更何况,IP地址中可能包含了用户不愿为他人知悉、属于绝对隐私范畴的访问信息。在发生网络迟延的情形下,该IP地址很有可能已被分配给了该侵权用户之外的第三人。对于企业而言,这些信息中还可能包含了他们的商业秘密。无论是隐私还是商业秘密,一旦被披露,都具有不可逆转性。版权当然需要给予尊重和保护,但公民的隐私权作为基本人权应当放在更为优越的位置,尤其是在侵权是否成立尚不能确定的情况下,信息披露要更加慎重。
2.信息披露与表达自由的冲突
表达自由作为一种“前宪法事实”存在,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9]34-40。现代意义上的表达自由是指言论主体利用一定的传播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自由地表达意见、传递并获取信息的权利[10]3-15。作为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宪法性权利,表达自由强调通过交流说服对方、取得妥协、达成共识,体现了平等、自由、理性的公共价值,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要求,在权利位阶中具有极高的位置[11]196。表面上看,信息披露和表达自由似乎并无关联,其实不然。表达自由包括了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自由,二者相辅相成,无论是信息获取还是信息传播受到阻碍,都不能成立完整意义上的表达自由。与中世纪的出版特权不同,现代版权制度将作品的权利赋予给作者,使作者可以突破诱致性限制行为的影响而自由选择其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促进表达自由的实现[12]41-48。通过活跃、繁荣表达性文化,版权保护也为表达自由的充分实现创造了有利环境[13]201。版权与表达自由又存在“冲突与妨碍”的负相关性,对版权的过度保护又会限制信息的传播,影响公众的信息获取和思想表达,加重ISP的信息披露义务意味着对版权保护的强化。如果对信息披露的限制太少,网络用户因担心自己的身份信息被泄露,必然会谨言慎行,一方面确实能够更好地遏制网络盗版行为,另一方面对监控的恐惧可能会产生一种“寒蝉效应”,导致用户因为担心自己的兴趣被监控和记录而不去寻找特定的知识资源或阅读特定的材料,不敢发表言论,版权边界的不确定性也很有可能会无意中为自己招来侵权的风险,表达自由遭到钳制[14]。
德国作为欧洲发达国家,对于个人隐私和表达自由尤为重视,联邦最高法院在立法不尽明确的情况下请求欧盟法院确定IP地址是否包含在信息披露的范围之内就再正常不过了。
三、他山之石——域外相关立法、司法实践考察
(一)《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协定》)
TRIPS协定规定了知识产权侵权信息披露的问题,其第47条规定:缔约方可以规定,除非与侵权的严重程度在比例上失调,司法机关有权责令侵权者将从事侵权行为的第三方的身份及销售渠道等信息提供给权利人。该条文针对的是所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限于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侵权。该条文使用“可以(may)”而非“应当(shall)”,因此成员国可自行决定在国内立法中是否采用该条款。同时,该条规定提供信息的“义务”主体是侵权人而非一般的“被告”。此外,该条款强调披露“义务”适用的前提是存在严重侵权行为,可获得的“信息”也仅限于侵权者的“身份”和“销售渠道”[15]84-89。这些与很多国家的规定均有明显区别。当然,TRIPS协定只是划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下限,各成员国可以提高自己的保护标准。
(二)美国
美国 DMCA第 512(c)、(d)条规定了 ISP的“避风港规则”,第512(h)通过“传票制度”确立了ISP的信息披露义务。按照上述条文,版权人可以请求地区法院的书记官向ISP签发传票以获取侵权者的信息,版权人应向书记官提交第 512(c)款第(1)项(A)目所称通知的复本(用于证明权属和网络用户的侵权事实)、拟议的传票和一份保证所获信息只用于保护版权的声明。ISP应以其掌握的信息为限向版权人披露涉嫌侵权人的信息,否则依照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处理。美国的传票制度相较于普通的诉讼程序更为便捷,有利于权利人尽快获得侵权者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第512(a)之规定,作为纯粹中立的技术接入服务提供者对于网络侵权行为不承担侵权责任,自然也不存在所谓的信息披露义务。然而随着P2P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用户之间的信息传输不再依赖于集中服务器,很多情况下掌握用户信息的只有网络接入服务者。制度应当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变革,在立法尚未调整的情况下,美国的司法实践采取了相对保守的立场,在RIAA诉Verizon一案中,一审法院认为网络接入服务商应当向版权人披露涉嫌侵权者的身份信息,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决定,判决不必披露。美国最高法院承认现行立法难以适应新的技术环境,但法院无权修改法律,因此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16]。此外,尽管DMCA没有规定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在信息披露程序中的参与权,但为了避免错误披露,在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Inc诉Does1-40一案中,法官就在传票中给予ISP一定的期限以通知网络用户,听取其意见,体现了美国司法实践对立法的变通和弥补[17]46-52。
(三)加拿大
2015年生效的《加拿大联邦版权现代化法案》第41.25条至第41.27条规定了ISP的信息披露问题。按照以上条文,版权人发现网络版权侵权的,可以向ISP发出侵权警告通知,但不得含有要求和解的内容,以防止“版权流氓”滥用知识产权。ISP应当将该通知发送给涉嫌侵权的行为人,并告知警告人通知的发送情况或者无法发送的原因,保留侵权记录6个月,ISP未履行通知送达和记录保留义务的,警告人有权通过法院要求其给予5 000~10 000加元的法定赔偿。ISP无需删除相关侵权内容,只要履行了上述通知及数据保留义务,即不负任何责任,这为ISP提供了避风港。加拿大的上述“通知—转通知”制度,体现了对侵权人程序参与权的重视。司法实践中,ISP显然不会主动披露网络用户的身份信息,版权人只能向法院提起无名氏之诉[18]15-22。从已有的判例来看,加拿大法院在此类案件中非常注重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信息的披露以维权之必要为限,与侵权无关的隐私信息必须过滤,信息披露只能针对争议当事人而不能延及他人,披露信息之请求与提出诉讼之间不得延迟,以避免泄露无辜者信息的危险[19]122-128。近期发生的加拿大影片发行公司ME2 Productions与网络服务商Teksavvy的著作权纠纷案中①See Teksavvy Wins Appeal in Defense of Accused'Pirating'Subscribers[EB/OL].https://www.husham.com/teksavvy-wins-appeal-in-defense-of-accused-pirating-subscribers/,2019-03-17.,针对ME2 Productions要求Teksavvy披露几个网络用户的个人详细信息,加拿大联邦法院威廉·彭特尼(William Pentney)法官称:网络用户获得通知是信息披露的前提,侵权证据充分才能批准第三方披露令。因为原告提交给法院的信息存在出错的可能,隐私权有遭到侵害的危险,当并未参与诉讼的用户的隐私处于险境时,法院不能支持原告的单方诉请。表明了加拿大法院高度重视保护个人隐私权的立场和倾向。
(四)日本
日本的著作权法并未规定ISP的信息披露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著作权侵权日益严重,但网络的隐蔽性让权利人的维权异常困难,掌握了侵权者身份信息的ISP应否披露该信息没有法律上的依据。鉴于此,日本于2001年11月颁布了《特定电信服务提供者损害赔偿责任的限制及请求披露发布者信息的法律》,并于随后陆续发布了相关准则,以规制网络著作权侵权中ISP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及侵权者信息的披露问题,平衡各方利益。按照日本立法和总务省令,权利人在掌握明显侵权事实的情况下,基于保护著作权之必需,有权请求ISP披露的涉嫌侵权者的个人信息包括用户的姓名或名称、传输者的地址、传输者的电子邮箱、侵权信息有关的IP地址、传输侵权信息的日期和时间[20]24-30。除非无法联系或有其他特殊情况,ISP接到信息披露请求后应听取涉嫌侵权者的意见。ISP未披露信息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除非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无需承担责任。权利人获得涉嫌侵权人的信息后,不得随意使用,不得不正当地扰乱其生活。当ISP拒绝披露信息时,权利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请求披露之诉。关于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是否为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日本立法并不明确,司法实践中,起初日本部分地方法院持否定态度,之后一些法院转变了立场,判定接入服务商也有信息披露义务,并最终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21]。
从上述考察可以看出,面临急剧增加的网络著作权侵权,为平衡版权人、ISP和网络用户之间的利益,在TRIPS协定的指引下,各发达国家先后规定了ISP的信息披露义务,但对于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条件、内容、限制、程序和法律责任的规定都不尽一致,各具特色,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诸多争议,值得我国相关立法的考量。
四、我国ISP著作权侵权信息披露立法、司法实践评析及展望
(一)我国相关立法、司法实践考察与评析
1.我国的立法沿革
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并无关于ISP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最早规定ISP著作权侵权信息披露义务的是2006年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按照该条例,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为查处著作权侵权行为有权要求ISP提供涉嫌侵权者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资料。ISP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①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3条、第25条。。该条例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所作的规定,有权要求披露信息的主体是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ISP无正当理由拒不披露信息的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随后实施的《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则规定,著作权人在出示身份证明、著作权权属证明及侵权证明的情况下有权要求ISP披露涉嫌侵权者的注册信息,ISP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应承担侵权责任,著作权人指控不实的,应对被控侵权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7条第1款、第8条。。该解释中请求披露的权利主体是著作权人,义务主体是ISP,无正当理由拒绝披露承担的是民事责任,至于披露的内容范围则不够明确。至此,我国民事法律意义上的ISP信息披露制度有了明确的立法规定,但是网络用户在此过程中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关注。201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尽管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在我国确立了“避风港规则”,但并没有提及ISP的信息披露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网络传播权若干规定》)于2013年1月1日施行后,前述《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同时废止。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传播权若干规定》一反常态,并未规定ISP的信息披露义务,而且还规定,著作权人有初步证据证明ISP提供了相关作品,但ISP能证明其仅提供网络服务且无过错的,不应认定构成侵权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进一步从举证责任这一程序的角度免去了ISP的信息披露义务。至此,我国关于ISP著作权侵权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只剩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即ISP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负有信息披露义务,而著作权人能否请求ISP披露涉嫌侵权者的信息再次变得无法可依,2014年公布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重申“避风港规则”的同时对ISP的信息披露义务也未作规定。
2.我国的司法实践
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ISP著作权侵权信息披露的案例并不多见。在浙江东阳天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电信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①参见〔2012〕海民初字第16396号民事判决书,〔2013〕一中民终字第2232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东阳公司以被告北京电信公司在起诉前未及时按照其请求披露侵权人的IP地址构成侵权为由,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北京电信公司对其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北京电信公司为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法律对其有无信息披露义务未明确规定,但在P2P技术背景下,为平衡著作权和用户的隐私权,当某个IP地址存在较大规模侵权嫌疑时,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也负有披露该IP地址用户信息的义务。为了保护用户隐私,避免权利滥用和过分加重网络服务商的负担,信息披露应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或者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披露,而不是直接依权利人的请求披露。由于原告未提供权属证明,一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请,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关于本案的判决,信息披露义务的确认和权利人提供权属证明的要求,都在《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的规定范围之内,其特别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认定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有披露义务,但是以发生大规模侵权为前提,这与前述TRIPS协定的相关规定类似;二是主张信息披露应采取公力救济(诉讼)的方式解决,体现了法官面临该类案件时的利益权衡和审慎态度,尤其是对网络用户隐私权的重视。在北京海蝶音乐有限公司诉上海青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②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8〕沪73民终168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用户的作品传播行为负有注意义务和发生侵权时的用户信息披露义务。最终,法院认为被告既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也因为没有建立完善的实名制而未尽到信息披露义务,故侵权成立。该案发生在2018年,《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已经废止,判决认定ISP应负信息披露义务,否则承担侵权责任,似乎缺乏法律依据。
在快乐米(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杭州快定网络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③参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4〕杭滨知初字第28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在庭审中披露了被控侵权者的用户昵称和邮箱,但法院认为这不足以证明被告仅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被告提供的上传者信息亦不足以证明涉案游戏系网络用户上传,故认定侵权成立。该案中被告主动披露信息意图证明自己仅为ISP,判决对于ISP在实体上是否负有信息披露义务没有提及,但认为披露的信息过于简单不足以认定被告的ISP性质,似乎从程序的角度变相为ISP附加了信息披露义务——不披露即不能定性为ISP而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实务中很多人也持此种看法。其实不然,这只是个案中表现出来的倾向,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按照《网络传播权若干规定》,ISP能证明其仅提供网络服务且无过错的,不应认定为构成侵权,证明的途径有多种,披露网络用户的信息只是其中之一且不是必要的途径。假设本案的被告换作百度文库或其他众所周知的信息共享平台,ISP无需披露用户信息也能很轻易地证明自己仅提供了网络服务。
在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诉纽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侵害著作权案、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纽海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④分别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29334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7051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在起诉之前均已向原告披露了涉嫌侵权者的注册信息,故法院也没有就被告是否负有信息披露义务进行阐述,另外,这些侵权案件均发生在电子商务领域,被告作为电商平台的信息披露义务与著作权法一般意义上的ISP的信息披露义务也不能等同视之,因此这两个案例对本文的研究没有太大的标本意义。
由此可见,关于ISP对著作权人是否负有侵权信息披露义务,我国立法先是肯定,后来又废止了相关规定,目前态度并不明朗。司法实践中的相关判例较少,在《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废止前后,法院均认为ISP负有信息披露义务,否则构成侵权;基于保护网络用户隐私权的考虑,个别法官还在立法之外创设了一些规则,比如请求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披露信息应以“大规模侵权”为前提,应当通过公力救济而非私自请求进行等,对今后的立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我国相关制度建设的展望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的避风港规则,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版权人和ISP之间的利益关系,兼顾了版权保护和技术发展进步的需要。然而,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日益泛滥导致双方的利益再次失衡。在版权利益集团要求立法确认ISP的信息过滤义务面临重大争议一时难以落地的情况下,以立法再次明确ISP的信息披露义务十分必要,但基于利益平衡的需要,如下几个方面应当重点考虑。
1.要充分认识到ISP的信息披露不仅涉及到版权人与ISP之间的利益平衡,更为重要的是还关乎版权保护与公众隐私权和表达自由的价值取舍,关系到信息的自由流动,也影响民主社会的政治构建,必须给予充分的考量。因此,应将ISP的信息披露定性为一种必要的、迫不得已的选择,从而进行严格的实体和程序限定。具体而言,在向受害人提供救济时,要全面考虑救济措施本身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对相关产业可能造成的损害和预期的社会效益,信息披露义务应控制在义务主体力所能及和权利维护的必要范围之内,将可能对相关主体造成的伤害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
2.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网络存储服务和信息定位服务(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作为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并无争议,它们也是承担信息披露义务的主要义务主体。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有无信息披露义务则不无疑问。在传统的以ISP(网络存储服务和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为运转中心的技术背景下,网络存储服务和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掌握和控制着用户的相关信息,处于完全中立地位的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没有信息披露的必要。随着P2P技术的发展,网络用户之间的信息共享已经可以完全脱离网络服务商的集中处理器,网络服务商无法对用户的行为进行掌握和控制,一旦发生著作权侵权行为,权利人只有从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处获悉侵权者的信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基于此,有学者主张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应承担信息披露义务[22]42-48。上文提到的东阳天世文化传播公司诉北京百度公司、北京电信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法院也认为在发生大规模侵权的情况下,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应负信息披露义务。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仅向用户提供接入国际互联网服务,而不直接控制用户提供的信息内容,处于完全中立的地位,本身不具有任何自主倾向,根据技术中立原则,不能因为P2P技术的发展和版权人维护私权的需要而对其施加信息披露义务。
3.关于信息披露的程序或模式。就世界范围而言,存在公力救济,如美国的传票制度和私力救济,加拿大的“通知——转通知”制度两种模式。公力救济更具权威性,但是也存在程序较为繁琐的困扰,尤其是在没有无名氏诉讼制度的国家,以谁为被告提起信息披露之诉也是一个问题。私力救济赋予受害人直接向ISP索要信息的权利,有利于受害人迅速采取措施,更加适应网络信息传播迅速、侵权范围短时间急速扩大的特点[23]9-14。但是将网络用户是否构成侵权交由ISP来判断,ISP事实上充当了准司法的角色,这将大大超出其能力范围。更何况,从相关国家的实践来看,私力救济对ISP的约束力十分有限,不仅没有实现权利人的快速维权,反而延缓了维权的进程。就我国而言,考虑到很多情况下权利人可以针对ISP直接提起侵权之诉,信息披露并非完全必要,为了防止著作权人滥用权利打击竞争对手,也考虑到ISP尤其是新兴互联网企业的侵权判断能力和成长问题,确定公力救济模式更为合适,具体由著作权人以ISP为被告提起信息披露之诉。此外,可以借鉴域外经验,规定由ISP通知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听取其意见,一定程度上保证其程序参与权,便于更加全面地确认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
4.关于信息披露的条件、限制及内容。如前所述,信息披露关系到网络用户的隐私权和表达自由等重要的宪法性权利,信息披露的滥用可能导致类似于版权特许时期的舆论审查问题,不足为取。因此,立法规定ISP的信息披露义务时应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将“权利人维权之必要”确定为信息披露的前提,具体而言,应该是侵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不披露相关信息权利人将无法获得救济,换言之,应该是ISP严格履行了注意义务和“通知—删除”义务不构成侵权,或者权利人起诉ISP侵权未获胜诉的情况下。至于我国司法实践中有法院在个别案件中将“发生了大规模侵权”确定为信息披露的前提①参见〔2012〕海民初字第16396号民事判决书。,笔者认为不妥,著作权侵权信息披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权利人获得法律救济,无论是大规模侵权还是个别侵权,权利人获得救济的权利都是法定的,也是平等的,不应区别对待。关于信息披露的内容,也应以确定涉嫌侵权人的身份信息,以便权利人维权为限度,除此之外的信息不应在披露的范围之内,即便获取了也应加以过滤。具体而言,应披露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住址、IP地址等,个案中以确定网络用户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为限度进行最终确定。而且无论如何,获取到的个人身份信息的使用不能超出依法维权的目的范围,否则侵害网络用户隐私权的,应承担法律责任。
5.关于具体的立法安排,笔者建议,可以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之后增加一条,具体内容为:如果网络用户的著作权侵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网络存储服务提供者、网络搜索或链接服务提供者履行了本条例规定之义务不构成侵权,或者权利人起诉上述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未获胜诉的,著作权人可以针对上述网络服务提供者提起著作权侵权信息披露之诉,要求其披露该网络用户的相关身份信息,以维权所需为限。收到诉状之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通知该网络用户,听取其意见。
总而言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信息披露义务是网络环境下保护版权的必然要求,在相关的制度安排中,要合理平衡版权人和ISP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版权的同时防止对一方造成过重的负担,尤其是要将网络用户的隐私权和表达自由放在更为优越的位置进行考虑,严格限定信息披露适用的实体条件,注重网络用户对相关诉讼程序的参与,听取其意见,以最大程度实现版权人、ISP和网络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版权产业、互联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