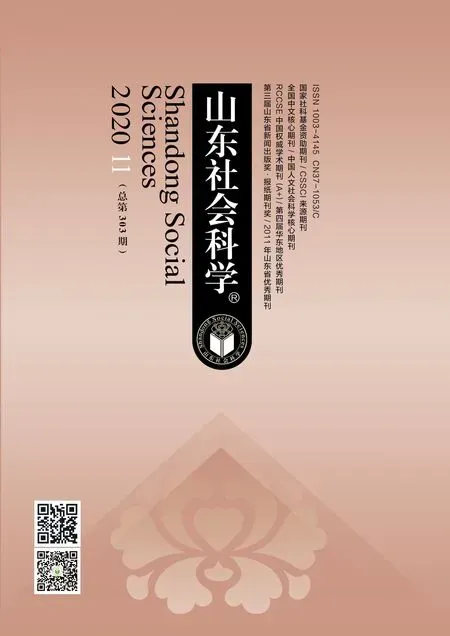政府采购合同授予阶段纠纷解决的第三人心理分析
刘赫喆
(山东师范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随着行政合同等互动型管理方式逐渐普及,政府采购这一典型公私合作行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当事人的利益矛盾一并凸显,而心理状态是促使不同身份主体开展政府采购活动的根本要素。因此,只有把握各方心理,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及控制,才能保证政府采购相关争议得到有效解决。根据我国政府采购现有的法律规范,对供应商采用广义理解。具体而言,有意向投标的潜在供应商以及满足条件实际参与竞争的投标供应商,在纠纷解决上不同于中标供应商,其与招标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差异,争议产生的原因亦有较大不同。在此,笔者将其统称为第三人,作为一类特殊而重要的主体单独予以分析。
一、政府采购合同授予阶段纠纷解决的现状及特征
纵观政府采购合同争议发展,合同授予阶段纠纷所占比重日益增大,投诉率明显上升,且通常由第三人提出。根据《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所提供的数据可知,2016年全国政府采购案件达到5011起,分别是2015年及2014年案件数量的1.5倍和3倍,而2017年仅中央一级处理各类案件即达到549起。总体而言,政府采购合同授予阶段纠纷解决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以保障合同成立及履行为目的
第三人提出的对政府采购过程的异议,主要分为两类情况,均指向较为缓和的纠纷解决方式,以保障政府采购整体进程顺利。虽然第三人作出此种判断的具体原因不同,但都是基于维护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双重考量。
一是尚处于缔约磋商阶段时,其与采购人发生纠纷并提出解决主张,若及时化解合同依然可正常订立。这是由于缔约阶段的救济具有特殊性,最佳状态是在政府采购合同授予前解决纠纷,并纠正缔约违法行为,使第三人回归竞争秩序。在公正环境下结束整个程序,可以获得各方都能接受的采购结果。欧盟调查委员会发现,多数被指控的合同违法都发生在合同最终签订之前,主要是有意或无意忽略强制性程序,或不遵守其中的某一步骤。假定能够及时发现,就足以在采购程序结束前予以纠正。(1)余凌云:《行政契约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我国《政府采购法》第51条、第52条明确规定,可以向采购人提出询问和书面质疑;第55条允许供应商对答复不满时,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作出认定招标无效,并要求重新组织招标的处理意见,促使采购程序重新开始,可以避免进入合同履行阶段引发更大争议。
二是纠纷虽发生于缔约阶段,但政府采购合同进入履行阶段后才提出争议。此时重新选择供应商未必具有现实可能,为了不妨碍合同的正常履行,应尽量避免因争议处理而造成履行中断,因此诉讼方式并非最佳选择。此时由第三人提出的采购程序争议,可能涉及合同能否成立的问题。如果行政主体的违法或不当行为,不足以导致合同缔结无效的结果,出于维护公共管理稳定的考虑,司法外救济通常倾向于维持合同履行。对第三人而言,即使对采购人作出额外惩罚,加重其责任负担,自身并不能因行政性惩戒行为而获得实际利益补偿。因此,当第三人因采购程序存在实际支出且预期利益不能实现时,损害赔偿就是不二选择。且合同进入履行阶段甚至履行完毕时,缔约中的过错行为不再具有修正的可能性,采购人也只能通过经济性补偿方式承担责任。相较于行政诉讼而言,这种处理方式更加温和,也更有利于合同状态的保持。
(二)第三人产生异议的事由相对集中
在不同的政府采购活动中,第三人认为诸多因素均可能构成对公平竞争秩序的破坏,指向采购人或中标供应商,其异议事项也无外乎实体与程序两大方面。
一是实体性规范设置缺乏公正性,主要表现为采购人在供应商选择标准的制定或选择结果的作出上有失公正。具体而言,一方面是对采购人的标准判断提出异议,认为存在恶意排除潜在供应商参与竞争的倾向;另一方面是对中标供应商的资质保留看法,认为其不具备承担项目的资格。此类异议在政府采购中屡见不鲜,往往因缺乏事实依据而未获支持,却始终难以避免其对行政成本的不合理消耗。
二是在采购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程序瑕疵,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上升而违反公平竞争要求。具体而言,一方面是采购人违反回避要求,其中包括与采购事项存在利害关系,与潜在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以及存在其他影响公正性的情况。除了禁止其参加直接的准备工作和决定之外,还包括咨询或施压等间接措施。(2)[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07页。另一方面是不单方接触的要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必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9页。。在采购筹备至进行阶段,采购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与任何潜在供应商,就采购事宜进行私下单独接触,从而避免对相关标准的泄露,或者供应商对标准设置进行干预。《招标投标法》第44条明确规定,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私下接触投标人,更不得收受财物等好处,或透露与评标工作相关的情况。
(三)纠纷在行政系统内部即可化解
司法不宜成为争议解决的开端,诉讼机制不是解决合同授予前争议的首选。国外救济制度运作及我国实践经验表明,以司法外途径解决纠纷,容易得到较为圆满的结果,这是由于政府采购自身特性与司法外救济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保证采购顺利进行并将争议对合同的不良影响降到最小,是选择救济途径的首要出发点。为使采购行为连续性不受妨碍,法院审查行政系统内部救济的最终结果,可能比每一阶段都直接寻求司法干预更加有效。
在合同授予阶段纠纷解决中,行政立法往往设置询问、质疑等手段,为协商这一自行救济方式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设定。在美国,政府合同纠纷经由当事人申诉,通常由特别合同执行官员裁决,若不服可继续向内部的合同申诉委员会申诉。(4)Peter L.Strauss,An Introduction to Administrative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Durham:Carolina Academic Press,1989,p.285.相较于单纯的双方协商,此种裁决虽归属于行政权行使范围,但无疑为其解决争议施加了更多负担。我国《政府采购法》要求,“采购人应在收到书面质疑后七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通过对答复期限进行明确规定,形成对行政主体的客观约束。此类救济方式的优点在于灵活性,本质上没有逃离自行协商的藩篱,其对于采购人的限制非常有限,依旧面临监督不足、规制空泛等问题。
当未作出答复或对答复不满时,第三人还可向同级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受理投诉的部门有权对争议事宜作出处理,同时可以对采购人的违法行为作出判断。《政府采购法》对投诉处理期限以及作出决定的书面形式加以规定,赋予其必要时暂停采购活动的权力,并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55-57条,对取证、审理等具体事项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在部门规章的制定上,早在2004年,财政部就颁布了《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作为投诉处理的操作指南。随着2018年3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正式生效,这一救济方式在政府采购中的应用已经趋于成熟。一系列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完善,为采购阶段以投诉方式解决争议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还需注意的是,虽然《政府采购法》第六章“质疑与投诉”中,统一使用“可以”而非“应当”的表述,没有明确行政系统内部救济是必要前置环节,但实际操作中,诉讼仅为投诉处理结果不满时启动的最终保障手段,几乎不存在直接诉讼的情况。这就引发一个现实问题,质疑与投诉的对象原本为招标人,诉讼事由却只能是对投诉处理决定不满,此时被告变成了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机关。即使第三人的诉讼主张得到支持,法院也只得作出决定不当、要求相关部门重新作出的判决,并非直接对第三人关于政府采购事宜的异议作出答复,而是使程序倒退回行政系统内部救济阶段。这显然不符合争议解决的正常逻辑,亦无端降低了行政效率。可见,直接寻求司法救济的可行性,往往因行政系统内部救济的有效性而被忽视。
二、第三人心理对政府采购合同授予阶段纠纷解决的影响要素
法律规制以趋利避害为出发点,正如休谟所言,任何学科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法学对行为的关注远胜于人性本身,但终究无法摆脱主体心理因素的干扰。因此,应对第三人在采购过程争议处理中的心理进行剖析,发掘其与纠纷解决发展趋势存在的关联性,进而为法律规制方案的设计提供思路。
(一)对质疑采购人权威产生潜在顾虑
第三人作为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存在天然的地位不对等,因此在提出争议、解决争议的全过程中,难免存在顾虑心理,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国传统法律心理,可以归结为权力—法律—道德的三元结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与道德的附庸。当冲突发生时,第一反应是通过说情、论理以摆平,而非以法律手段解决争端,即勒内所概括的,中国人处理关系以合乎情理为准则。(5)[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页。这种无讼、息讼理念,源出儒家以和为贵的中庸思想。但随着社会发展与法律制度的完善,人们逐渐摆脱“泛道德主义”的羁绊,法律权重越来越大。(6)戴健林:《法律社会心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69页。在政府采购争议中,近年来由第三人提出异议的比例显著提升,这是法律意识觉醒的直观体现。厌讼心理使得第三人往往将缓和的协商手段作为首选,对于冲突性较强的诉讼手段有意识地进行规避。
二是对权威存在信赖与敬畏心理。一方面,采购人在招标等采购过程中公开了相应信息,并在回应质疑时提供一定依据,具备充分理由,第三人对其抱有基本信任。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它是公众心理深层人格化、道德化的法律化身,出于对权威审查结果的认可,第三人不会将行政诉讼作为必要选择。另一方面,作为处于弱势一方的行政相对人,第三人往往以焦虑防御方式处理纠纷。焦虑是寻求逃避的内心状态,弗洛伊德将其视为危险即将发生时自我发出的警报信号。(7)王杨:《弗洛伊德“焦虑”范畴解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三人内心将与行政机关的争执视为现实存在的威胁,从而以调整、躲避的处理方式杜绝使其产生焦虑的情境,即不敢轻易提出质疑或者尽可能避免司法救济。第三人在质疑或投诉答复不满时,常常选择息事宁人,这并不代表认同招标人的做法,而是强行压抑自己的不满,自我说服以配合接受。此时第三人的防御方式表现为反向形成,实则是一种十分微妙的蔑视,通过反向行动以避免面对自己的本质。(8)[美]查尔斯·S.卡弗、迈克尔·F.沙伊尔:《人格心理学》(第5版),梁宁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页。
三是第三人不愿意与采购人产生尖锐矛盾,而强调争议解决的合意性,这是出于长期合作的考虑。一方面,对于处于不利地位的第三人而言,其解决争议的愿望往往比采购人更为强烈,若争议持续存在且解决遥遥无期,其危机感较之行政机关更甚。(9)胡宝岭:《行政合同争议司法审查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因此,双方会尽力达成合意以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尊重并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诉求。双方直接沟通或者借助第三方的力量进行调解,能够更加直接、充分地表达意愿。只要采购人和第三人从各自所拥有的手段中,确认某个妥协点是能够得到的最佳结果,这样的解决即可获得。(10)Thomas C.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Boston:Harhard University Press,1961.即使依靠司法途径解决争议,双方最终均获得完全满意的结果也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实践操作中,第三人主观上往往不希望因个别政府采购争议提起诉讼,而使与采购人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在英国,即使《王权诉讼法》简化了诉讼程序,并将行政合同争议全部纳入受案范围,纠纷解决依旧不会主要诉诸法院,而将非正式谈判或仲裁方式作为首选。彼得·坎恩认为,这种现象是由政府与相对人之间的长期互利合作关系所决定的,双方合作并非一次性商业交易,诉诸法院易产生负效应。(11)Peter Cane,An Introduction to Administrative Law,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p.263-264.解决手段相对温和的司法外救济,无疑是第三人的理想选择,在化解争议的同时,又为此后与采购人继续进行合作保留了余地。
(二)对维护自身利益具有原始需求
第三人针对采购事项提出异议,根本上是为了维护自身参与公平竞争的权利,并争取从中脱颖而出的机会,因此其纠纷解决的一切行为,都是追逐个人利益的心理反应。
一是第三人刻意无视自身不足,而本能寻找客观理由以自我保护。在防御机制上,首先表现为否认,即拒绝相信中标结果并排斥采购人对其投标行为作出的评价,认为肯定存在某种误会,以隐藏其真实的软弱。这是因为在政府采购进入买方市场以后,采购人占有交易上的优势,第三人相对被动。政府作为采购人,多数情况下以组织者面貌出现,会不自觉地以强者地位自居,第三人容易产生采购人利用优势地位而恣意行为的臆断。(12)马海涛等:《政府采购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其次,按照勒温的社会格式塔理论,第三人的心理冲突表现为接近—回避型,一方面是自己想得到的,另一方面则是极力回避的。第三人在选择质疑或投诉之前,内心是冲突的,如果主张没有得到支持,可能徒增时间、经济成本并恶化与采购人关系,这是其想回避的一方面;接近方面则是,其主张获得支持,将会重新回归采购程序甚至成为中标供应商。此时第三人将进行理性衡量,只要其满足质疑、投诉的受理条件并掌握一定依据,通常倾向于提出异议以争取个人利益。
二是第三人将快速解决问题作为纠纷处理准则。沃伦法官认为,以诉讼手段解决争议存在局限性,应建立一种机制,以最短时间、最低费用及在参与人承受最小压力的情况下,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13)[美]Herbert M.Bohlman、Mary Jean Bundas:《商法企业的法律、道德和国际环境》,张丹、林莺、李勇、陈婉婷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在没有穷尽行政系统内部救济时,由于尚未对争议相关事实及依据进行收集、分析,司法审查时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基础性准备工作,因此程序相对复杂,救济成本较高,即使最终采购过程的争议得到解决,合同成立的最佳时机也可能已经错失。第三人以保障个人利益为目的,并非为使采购人承担被诉的不良后果。只有使其认识到法律所提供的救济途径是迅捷、有效且公正的,才能激发其主动寻求法律救济的热情。在国外实践操作中,司法外救济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也已经得到证实。然而,司法外争议解决也可能招致新的问题。鉴于第三人沟通及判断能力较为有限,在交涉过程中容易陷入采购人设置的陷阱,甚至会产生损害公共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后果。
(三)对获得竞争胜利存在不良心理
有时第三人提出异议,并不在意其主张是否获得支持,而是基于报复、发泄的不良目的。这种所谓的维护权益行为,通常带有明显的攻击性与敌意,是一种病态性的非理性心理表现。
一是第三人提出异议有时不存在充分依据,更多表现为冲动行为,通过任意表达不满以避开未能中标的焦虑。此时在防御机制上,一方面表现为投射,即通过将个人无法接受的冲动或渴望归咎于他人以减轻焦虑,从而隐藏对自身不喜欢方面的认知,同时表现出无法接受的品质,这是一种高度歪曲的形式。(14)赵秀凤、刘辰诞:《心理空间理论视角下的“投射”结构及功能》,《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在投射中,第三人延伸出采购人对自己不满或恶意将其排除在竞争外的解释。尽管歪曲使得压抑的内驱力得到表达,但此种表达微弱且低效,冲动的压力仍持续存在。另一方面,这种不满可以上升为合理化防御,第三人通过为无法接受的未中标结果寻找一种合理解释或借口以减少焦虑,目的在于维护自尊及优越感。依据斯金纳操作性行为模式的分析,当参与政府采购的结果未能使第三人感到满足或程度不够,投标行为得到负强化,第三人将自动调节使这种行为在以后发生的可能性降低。(15)乐国安、李安、杨群:《法律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33页。也就是说,当此类负面失望情绪过重或者涉及的第三人范围过大时,极易导致招标困难,不利于政府采购项目乃至行政管理的开展。
二是出于嫉妒和偏见,有时第三人选择以恶意诬告的方式,故意拖延采购进程并给中标供应商造成不利影响和成本损失。西蒙的决策理论认为,有限理性的人在决策时只考虑可想到的选择,一旦有个别选择可达到所希望的标准,个体就会接受并不再考虑其他可能。(16)岳成浩、程婧:《危机能管理吗?——基于西蒙决策理论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1期。因此第三人提出不良异议的决策,是一种“踌躇—选择”的主动操作性动机行为。其常常对中标人的资质吹毛求疵,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提出质疑,即使经过严格审查供应商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规定,只要怀疑推定具有一定合理性,第三人并不承担任何惩罚性后果,财政部门仅能作出驳回投诉的处理结果。正是利用这种侥幸心理,其不存在后顾之忧,通过任意投诉却可以达到采购程序暂停,增加中标人支出的效果,以达到泄愤目的。按照斯金纳的主张,强化刺激会增加反应发生的概率。如果第三人恶意提出异议的行为未得到惩罚,并为中标人带来不利后果,这种政府采购争议只会不断增多。
三、基于第三人心理设计的纠纷解决对策
通过了解第三人在纠纷解决中的心理状态不难发现,现行政府采购救济规制的漏洞导致第三人权益主张受到压制,这也是诱发其不良心理的要素。必须依据第三人心理特征,完善对政府采购合同授予的法律规制,并设计相应的纠纷解决路径作为保障,方可引导第三人妥善行使救济权利,并达到监督采购行为的目的。
(一)组织采购活动的透明化处理
依据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内在心理与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涉及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同化是个体把外界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原有认知结构之内,顺应则是个体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而发生改变。(17)[瑞士]J.皮亚杰:《生物学与认识——论器官调节与认知过程的关系》,尚新建、杜丽燕、李浙生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6-176页。由此可知,如果第三人在作出纠纷解决的决策前,将政府采购过程中不公正、不透明等信息吸收到已有认知结构中,而导致心理平衡被打破,从而认知结构转向恶意提出异议、诬告或拒绝参与竞争,就是其顺应的过程。第三人碰到采购过程存在瑕疵等问题时,采购人及相关监督审查机构大多能够妥善处理,所产生的认知是应通过政府采购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矛盾,那么新的平衡建立,其将借助合理有效的救济方式维护个人竞争权益。为了使第三人尽可能吸收全面准确的采购过程信息,并形成正面认知,采购人开展采购活动的全过程应当公开透明,以下几点需要特别注意:
一是采用更易被第三人信任的方式开展采购活动。除了选择招标等透明度较高的供应商选拔方式这一基本要求,还应注意招标活动的分散性处理。在一些地方,依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关于集中采购目录的规定,采购以统一招标的方式进行,由固定职能部门或代理机构负责。这种方式存在潜在风险,即部分供应商与招标人长期接触,容易建立稳定而隐秘的利益输送关系,从而引起其他新加入供应商对于招投标过程暗藏不正当竞争的猜疑。为了更好控制供应商的不信任心理,采购人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自行组织或单独委托代理机构进行,若无明文规定无须集中某一地域或部门的采购执行权力。不同项目的组织方不同,供应商与采购人提前串通的可能性下降,招标方案及供应商标准的设置也将更具专业性及针对性。
二是完善采购程序,核心是对采购信息的公开,以此实现标准设置透明化,将纠纷扼杀于萌芽之中,以避免无谓的争议。按照公共选择学派将博弈理论运用到行政过程的思路来分析,第三人作为机会主义者,在参与竞争过程中存在利益需求,但整体而言个体知识有限,同时负担不起正确决策所需的信息费用,即存在“信息悖论”。若仍想形成“囚徒困境”,则须打破双方信息不对等的局面,即由占据优势的采购人一方完成信息提供,而第三人通过招标书及公告获取有限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不安全感无法避免,为了尽可能降低危机心理引发的无端争议,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采购人不能共享作出决策的信息依据或者公开不充分,第三人为摆脱信息压制中的不利地位,将采取非常方式以达到目的。(18)翟月玲:《行政责任法律规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为了杜绝以上不良心理,首先,在招标、竞争性谈判等采购方式中,供应商选择标准的公开是寻找参与竞争者的首要步骤。而在标准制定上,采购人享有裁量权以及最终决定权,若不能做到透明化,很容易出于对某一特定竞争者的照顾,设置特殊门槛以限制其他竞争者参与竞争。同时,以采购人公开的选择标准作为依据,第三人才能对中标供应商进行考量,看其资质是否与公开标准相符合,从而在对供应商资格提出异议时具备充分依据,使其接受公众审视以确保合理性。
其次,采购人应对决策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政策、公益等裁量考虑因素予以说明。具体而言,在确定中标供应商后,采购人应向其他参与竞争者说明选择理由,包括采用的选择标准,以及其不适宜缔结合同的限制条件。在英国,法律将这种责任,视作行政机关对未被选中而有权获得解释的当事人承担的义务。(19)郑秀丽:《行政合同过程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按照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第三人在对结果产生异议时,有权利要求采购人进行解释说明,对解释不满可向其主管机关投诉。需要强调的是,第三人提出异议时,有些采购活动仍在进行,此时要求采购人说明理由,实际是及时纠正错误的途径。
(二)争议解决路径的体系化设计
若想达到第三人妥善行使救济权利的目的,合理且完善的争议解决体系是必要的制度保障。具体而言,一是确保第三人提出采购异议的权利,从而加强其解决纠纷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首先,第三人与采购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且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即具备提出异议的资格。英国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定,曾经或正在试图成为获得公共工程合同的人,只要能够证明与采购活动存在某种联系,均可对政府采购人违反规则损害自身权利申请救济。(20)余凌云:《行政契约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164页。当然,第三人超过合理范围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依照日本“契约成熟度”理论,缔约磋商过程如同慢煮料理,应按成熟程度决定其不同阶段的责任。(21)朱广新:《信赖责任研究——以契约之缔结为分析对象》,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23页。以招标方式为例,参与投标的供应商,仅是接受招标方的要约邀请参与竞争,处于与招标方发生接触的起始阶段,甚至未进入磋商过程,此时因参与投标支出一定财产,属于自愿承担的风险,若未能中标不能因此要求赔偿。
其次,这种权利应当通过行政救济路径实现,否则会使第三人轻视政府采购行为的权威性。目前我国政府采购争议处理的法律规范存在矛盾之处,《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而合同授予阶段争议通常涉及优益权行使,如采购人选择标准制定不合理,此时理应适用行政法律规范。而且《政府采购法》第六章“质疑与投诉”中,明确将采购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纳入公法救济范围,实际上承认了采购争议的行政属性。立法时将采购过程与政府采购合同分离,至少承认了其缔约阶段即采购过程的行政属性。例如,在Hotel Andalucia Palace案中,按照“可分割行为理论”,将行政主体在采购过程中实施的包括采购决定在内的所有行为,与最终签订的合同分离并由行政法调整。(22)Order of the TS of 17 Octorber 1961 and STS of 4 February 1965.Cited from José M.Fernández Martín,The EC Public Procurement Rules:A Critical Analysi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pp.244-245.然而这种矛盾可能造成不同地区的行政监管部门,对《政府采购法》法律条文的理解和适用选择存在分歧,从而导致同一类型争议的处理依据不同,加重第三人抵触情绪。而在行政救济模式下,将根据争议性质首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当行政规范不能提供依据时,再以《合同法》等民事相关规定作为补充,在适用标准上统一且合理。这是由于政府采购行为受到特殊公法规则的约束,其来源于公共利益的要求,甚至足以代替合同条款发生作用,这与私法救济模式下的合同原则存在一定出入。(23)L.Neville Brown,John S.Bell,French Administrative Law(5th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203.如果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分析,第三人寻求采购活动争议的解决,也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具象表现。正如德国学者耶林所言,权利人以自身权利维护法律,并借助法律维护社会秩序,(24)[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梅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因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区分是相对的。
二是政府采购争议解决机制体系化建设。首先,应当充分发挥调解、质疑、投诉等司法外救济的优势。合理的救济模式,有助于争议得到彻底且高效的处理,否则容易因争议处理结果不当产生新的争议,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司法外救济依赖合意的作用,现实合意过程中,规范性契机始终存在。(25)[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总而言之,这种制度设计有助于从源头入手及早发现并解决问题,其为采购人提供反省机会,尽可能在司法部门未介入之前,通过直接交涉解决纠纷,这种参与使第三人对处理结果的内心认可度相应上升。行政系统内部自行解决难免存在“既是参与者又当裁判者”的弊端,在处理公正性上易受猜疑。在不被过度限制的前提下,应当提升采购人以答复质疑等协商方式解决纠纷的能力,可以设立协商过程监督和结果备案制度作为辅助,使争议处理结果更为公正合理。
其次,救济制度不应当剥夺第三人的诉权。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发生于各阶段的行政合同纠纷均具有可诉性。虽然司法外救济更为便利,但以硬性规定的方式,将其作为诉讼的前置步骤是不合适的,反而可能造成行政效率的下降。先行适用司法外救济途径,还是直接进入司法救济阶段,应视争议具体情况及第三人意愿而定。我国《政府采购法》第58条的规定,实际把投诉作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前置。此种设置无疑是对第三人救济选择权的不合理限制,易引发其逆反心理。面对司法外救济优先,但进入司法救济存在限制的法律规制缺陷,域外实践为保证救济效率提供了可参考的处理办法:一方面,规定合理的处理期限,简化和缩短司法外救济过程,使第三人得不到有效救济时可以尽快进入司法阶段。另一方面,附加第三人告知义务,将其诉讼意愿提前告知采购人。西班牙为了克服司法外救济前置导致程序冗杂的弊端,施加通知义务作为代替手段,要求提起诉讼之前,当事人应通知对被诉行为负有责任的行政主体。(26)José M.Fernández Martín,The EC Public Procurement Rules:A Critical Analysis,Oxford:Clarendon Press,pp.208,260.由于程序性义务不构成独立救济阶段,故不会导致时间拖延。
(三)第三人主张权利的合理化限制
既然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那么向相对人施加必要限制并加强教育,是行政主体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是设置相应的惩罚措施,作为杜绝第三人恶意投诉或诬告的手段,这在当下政府采购法律规范中明显欠缺。想要达到减少第三人恶意提出异议的目的,就必须使其对伪造证据或诬告等行为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由于恶意行为会诱发道德性焦虑,其产生于良心这一超我组成部分,若第三人即将违背道德准则,无端攻击采购人或中标供应商时,会产生害怕情绪,主观上接近罪疚感或羞耻感。可以借助反射研究,以强化与惩罚为条件,在刺激与反应的相互作用下引导第三人产生妥当的纠纷解决行为。(27)John B.Watson,BEHAVIOR: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sycholog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4.具体而言,第三人把抒发个体不满情绪与刻意引起采购争议这个行为进行联结,但一旦有行政处罚的苦果代替泄愤后的愉悦,若干次后其将在对惩罚的畏惧与恶意提起异议之间形成新的条件反射。当原有条件反射被打破而新反射形成时,恶意行为将逐渐消失。
二是加强对第三人的引导教育。依据班杜拉提出的观察学习论,人的行为通过观察、模仿而获得,攻击行为得以保持,是外部强化、替代强化、自我强化交互的结果。第三人自己或看到他人因恶意提出异议,使得采购人或中标供应商因采购流程拖延、项目实施成本增加而陷入痛苦状态,将会增强攻击快感,从而提高相似情境下实施类似行为的频率。若第三人把攻击行为理解为实现个人利益或满足心理需求,那么攻击行为将持续加强;如果理解为攻击行为对社会利益与他人利益带来不利后果,是违背社会道德准则及法律规范的,那么攻击行为将大幅下降。通过把握第三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在媒体报道、社会舆论方面给予积极强化引导,提高相关法律规范的普及程度,将会有效控制恶意攻击的产生。在此基础上,认知因素在学习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正如罗德提出的,人的行为特点在于目的性和功利性,因此第三人将依据个人期望与纠纷处理结果的吻合度,对个人的行为方式加以调整,这一结果也为其提供心理预期。(28)乐国安、李安、杨群:《法律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如果能够使供应商在参与政府采购时,对常见争议及救济途径有较为全面了解,其对于未来纠纷处理结果的可接受度将显著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