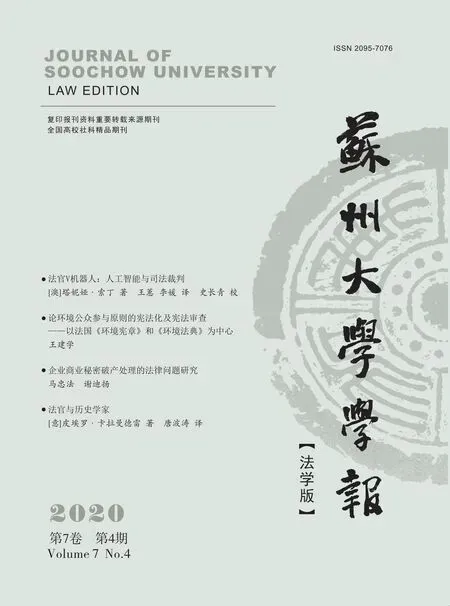论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宪法化及宪法审查
——以法国《环境宪章》和《环境法典》为中心
王建学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公众参与发挥着必不可少的功能。它“不仅必然有助于实现民主目标,而且能够催生更加良好和更灵通周全的政策决定”。①(1)①Cary Coglianese, Heather Kilmartin and Evan Mendelson, Transparenc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Federal Rulemaking Proces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New Administration, 77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924, 927(2009).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众多社会生活领域中,环境构成最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人类只有在健康的环境中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因此环境公众参与成为公众参与机制的最主要表现,也是法律实践和法学理论中的热点问题。如学者所言,“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不仅关系到参与式民主和环境正义的理念,而且经常被置于环境权学术研究的前端。”②(2)②A. du Plessis, Public Participation, Goo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Fulfilment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11 Potchefstroom Electronic Law Journal 1, 3(2008).
环境公众参与原则不仅在各国环境立法中得到反复重申并成为现代国际环境法的普遍原则,甚至被明确写入越来越多的宪法文本并上升为宪法原则。环境公众参与原则是否必然或应当宪法化?其宪法化是仅仅流于形式还是意味着实质变革?其作为法律原则与作为宪法原则是否存在差别?我国环境法治近年来正处于急剧变迁期,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订,③(3)③新《环境保护法》第5条明确将公众参与规定为基本原则,第五章专门规定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2018年生态文明入宪,晚近有迹象表明环境法典的编纂和制定随时可能启动。①(4)①吕忠梅教授建议将环境法典编纂列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参见吕忠梅:《将环境法典编撰纳入十三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载《前进论坛》2017年第4期,第50页。另外,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时,有委员建议制定环境保护法典,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制定环境保护法典》,载新京报网,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9/12/29/667754.html,2020年1月5日访问。在此过程中,如何从宪法高度统筹考虑环境公众参与原则,以及是否有必要将其宪法化?本文旨在分析法国环境公众参与原则宪法化的过程,并结合其宪法化过程中的经验为我国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考和借鉴。
一、公众参与在法国环境法中的发展史
国家治理的民主化为环境公众参与提供了前提,现代环境问题的爆发特别是其对个人生存所产生的全面影响直接催生了环境公众参与。在规范表述上,环境公众参与在获得法律承认之初表现为一项具体机制,然后上升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一)宪法和环境法的民主化与环境公众参与的诞生
法国环境法起源于旧君主制时期,最早可追溯至规定森林保护和管理的1669年科尔贝法令(Ordonnance de Jean-Baptiste Colbert)。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单行法律和法规一直是环境保护法的唯一形式,这不同于民法、刑法等传统部门法既存在体系完整的法典又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环境法的独特渊源表明其在源头上是国家有针对性地应对环境问题的法律产物。在君主制背景下,环境法主要规定了国家所采取的单方面治理措施,并不考虑个人的治理感受,也不存在公众参与的问题。
现行1958年宪法确立了法国的现行民主政体,但环境法仍然延续了之前的君主制传统,并没有立即向公众参与敞开怀抱。随着现代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特别是城镇化中的各种环境问题频发,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也离不开个人的参与,况且国家的单方面治理措施已经日益乏力。因此,环境单行法开始在特定治理领域承认公众参与的作用。法国议会通过1976年第76-629号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首次建立了协商(concertation)以及公共调查(enquête publique)等制度,②(5)②Art. 1er de la loi n° 76-629 du 10 juillet 1976 relative à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借此征求和收集相对人和特定公众的意见。这是公众参与机制的雏形。此后,随着1983年第83-630号关于公共调查民主化和环境保护的法律等的颁布,公众参与的内涵、形式和具体机制不断丰富和扩大。③(6)③Art. 1er & 2ième de la loi n°83-630 du 12 juillet 1983 relative à la démocratisation des enquêtes publiques et à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二)1995年巴尼耶法: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确立
1995年2月2日,法国议会制定了1995年第95-101号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的法律,由于其是在环境部长巴尼耶(Michel Barnier)的推动下制定,因此又简称为“巴尼耶法”。该法律总结、提炼和强化了既有各类环境单行法,既将环境公众参与等明确规定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又创造或提出了一些新的制度或要求,因此是公众参与由具体机制正式上升为法律原则的标志。该法在第1条第1款明确宣告并定义了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具体包括风险预防原则、损害预防行动与纠正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等。其中,公众参与原则是指“每个公民都必须有权获得与环境相关的信息,其中包括获得关于危险物质和危险活动的信息”④(7)④Art. 1er de la loi no 95-101 du 2 février 1995 relative au renforcement de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不同于此前将公众参与仅仅作为一项国家制度,这开创了以公民权利来定义公众参与原则的传统,并且这种定义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为了落实公众参与原则,该法在第一部分专门对公众参与和环保社团设置了一系列具体规则,而对其他三大原则却没有专门配置相应的具体机制。“可见法国环境法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放在了异常重要的位置。”⑤(8)⑤彭峰:《法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原则的实施及其对我国的借鉴》,载《环境科学与技术》2009年第11期,第202页。从内容上看,该法律对环境公众参与的基本制度作出了较为完整的规定,包括关于领土整治的决定在作出过程中征求公众和社团意见的机制,环保社团的协商同意机制与民事诉讼机制,公法人的民事诉讼机制等。从参与的主体上看,既包括了个人的参与,也包括了环保社团的参与,甚至还建立了省和大区的环境委员会、全国公共辩论委员会(Commission nationale du débat public),后者作为独立行政机构专门负责在全国范围内监督和确保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落实。不过,该法律也存在一定不足,比如公众参与原则的定义过于偏重知情权,其具体参与机制则主要附属于乡村法典而对其他环境领域的作用较为有限。
(三)2000年《环境法典》: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完善和体系化
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者,法国一向将法典编纂视为特定法律部门走向成熟的标志,环境法亦不例外。早在1990年10月,法国环境部就正式公布了环境法典化的计划,随后环境法典化工作逐次展开。经过了一系列困难和艰苦的努力,2000年9月法国政府根据议会授权通过并颁布《环境法典》(Code de l’environnement)的法律部分。①(9)①《环境法典》由法律部分(Partie législative)和行政法规部分(Partie réglementaire)组成,后者迟至2007年才编纂完成。关于《环境法典》的具体编纂过程,可参见彭峰:《法典化的迷思——法国环境法之考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120页。《环境法典》的编纂完成标志着法国环境法的内容体系趋于成熟。其在第一卷共同规定的第一编总则部分首先宣告和定义环境法的诸多基本原则,其中第L110-1条(首条)第2款第4项明确规定了环境公众参与原则,据此,“每个人都必须有权获得与环境相关的信息,其中包括获得关于危险物质和危险活动的信息。”②(10)②Art. L110-1 du Code de l’environnement.
在第一编的原则性宣告之后,该法典第二编专门规定了“信息和公民参与”。其中,首先宣告具体原则和一般规定,再分章设置公众参与的具体机制。就具体原则和一般规定而言,第L120-1条第1款规定,环境公众参与的实施将考虑到:1.提高公共决策的质量和促进其民主正当性;2.为当代人和后代人确保健康的环境;3.促进和引导公众参与环境保护;4.改善和传播环境信息。该条第2款规定,公众参与赋予公众的权利包括:获得保证其有效参与的相关信息;要求参与程序的落实和执行;享有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合理期限;获知其意见和建议在有权机关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得到考虑的方式。③(11)③Art. L120-1 du Code de l’environnement.
为使这些具体原则和一般规定得到落实,《环境法典》分章设置了公众参与的具体机制,这些具体机制依次包括下列七个方面:1.公众参与制定对环境有影响的规划、计划与项目;2.环境评价;3.对影响环境的决定的公众参与;4.环境相关信息的知情权;5.其他信息模式;6.项目申报书;7.与地理信息基础设施相关的规定。④(12)④这七个方面分别对应于《环境法典》第二编第一至七章的标题,每章之下还存在节、目和具体条文作详细设置,中文内容可参阅《法国环境法典(第一至三卷)》,莫菲等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需要说明的是,《环境法典》的修订极度频繁,因此中译本不可避免地存在越来越严重的滞后性。这些具体机制不仅完整地涵盖了环境公共决策制定过程的各个方面,还涉及诸如国家公众听证委员会、核安保透明与信息高级委员会等专门机构;不仅涉及常规的环境公共决策,还涉及网络服务、元数据等新的环境技术手段。
从总体上看,《环境法典》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宣告并定义了环境公众参与原则,而且将这一原则具体化为一系列权利和子原则,配备了公众参与环境公共决策的具体机制和规则,设置了各类独立委员会来予以执行、监督和落实。尽管这些内容并非无可挑剔,但它基本上保障了公众以各种方式对环境公共决定的有效参与。
二、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宪法化及其影响
环境公众参与由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继续上升为宪法原则,并且与程序性环境权建立关联,与环境人权、参与式民主相衔接。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宪法化意味着环境法的革命,使环境法经由与宪法的结合而成为“公民法”。
(一)2004年《环境宪章》: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宪法化
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宪法在最高规范层次作出回应,如希拉克总统在2001年所说,有必要“将生态人道主义铭刻在我们共和契约的心脏”。①(13)①Discours de Jacques Chirac, le 3 mai 2001 à Orléans, Revue Juridique de l’Environnement, n° spécial, 2003, p.78.作为这种回应的结果,法国议会于2004年按照立法程序通过了《环境宪章》(Charte de l’environnement)。后经总统提议修宪,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以修宪程序通过2005年3月1日第2005-205号宪法性法律,将《环境宪章》写入现行1958年宪法序言,即法兰西人民庄严宣告恪遵“2004年《环境宪章》中所明定的权利和义务”。作为宪法规范的组成部分,《环境宪章》在第7条专门宣告:“在法律规定的条件和限制下,每一个人都有权获得由公权机关掌握的与环境相关的信息,并参加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公共决定的制定。”由此,环境公众参与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也是程序性环境权的构成要素,兼具宪法原则和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
从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制宪过程来看,尽管负责起草《环境宪章》的科庞委员会(Commission Coppens)在环境公众参与的具体表述上与政府方面存在一定分歧,但就基本内容和定位而言,环境公众参与属于“宪章诸多条款中所取得的快速共识(rapide consensus)”。②(14)②Yves Jégouzo, Le Rle Constituant de la Commission Coppens, Revue Juridique de l’Environnement, n° spécial, 2005, p.83.这种共识的取得具有多种原因。首先,环境公众参与自1995年由巴尼耶法确立为环境法基本原则以来,已经在环境法律实践中得到系统展开并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治理效果,这为其宪法化奠定了实践基础。其次,从国际层面来讲,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③(15)③里约宣言于1992年6月14日由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其在原则十规定:“环境问题最好在所有有关公民在有关一级的参加下加以处理。在国家一级,每个人应有适当的途径获得有关公共机构掌握的环境问题的信息,其中包括关于他们的社区内有害物质和活动的信息,而且每个人应有机会参加决策过程。各国应广泛地提供信息,从而促进和鼓励公众的了解和参与。应提供采用司法和行政程序的有效途径,其中包括赔偿和补救措施。”和1998年奥胡斯公约④(16)④该公约的全称是《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是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发展的里程碑,1998年6月25日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于2002年开始对法国生效。等已经普遍承认环境公众参与原则,这些宣言或条约已经得到法国的承认或批准,因此将相关内容写入宪法不仅顺理成章,也是法国履行其国际法义务的表现。最后,《环境宪章》的起草过程本身也充分体现了公众参与,科庞委员会在草拟宪章内容的过程中特别采取听证会、互联网等途径随时征求社会公众意见,这也为环境公众参与提供了连贯的支持。
(二)环境公众参与原则宪法化的意蕴
将环境公众参与原则宪法化并不仅仅是规范形式的升级,更是环境法实质内容的深刻变革。法国著名环境法学家普里厄教授将宪法化视为一个走向“新环境法”(un droit de l’environnement renouvelé)的过程。“环境是所有人的事务。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每个人都同时是环境的参与者和受害者,都同时是污染者和污染对象。正因为如此,《环境法典》宣告了环境是国民的共同遗产,每个人都应当致力于监督和维护环境”,借助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宪法化,环境法经由与宪法的结合而成为“一个公民法(un droit citoyen)”。⑤(17)⑤Michel Prieur, Vers un Droit de l’Environnement Renouvelé, Les Cahier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n° 15, Janvier 2004, p.134.
从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的角度来讲,环境法与宪法以及环境法学与宪法学原本是相对独立的不同部门,但是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已经将这种狭隘和孤立的观念彻底淘汰。无论是宪法还是环境法抑或其他部门法都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来应对环境问题,由此,围绕环境问题所形成的不同种类和层级的规范,包括宪法环境规范、环境法律规范特别是法典、环境法规等在内的所有规范,构成一个应对环境问题的新的综合系统。如法国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部部长所说,“《环境宪章》提出了若干宪法原则,据此人们在反对环境损害的斗争中和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利用一个真正的环境法(un véritable droit de l'environnement)更有效地实现目标。”⑥(18)⑥Réponse à la Question écrite de M. Serge Mathieu, Sénat, in Journal Officiel, 24 juill. 2003, p.2390.就公众参与原则而言,它不仅是公民的参与权本身,而且与环境人权、参与式民主等宪法价值相互衔接。
(三)以宪法实施为目标的《环境法典》修改
既然《环境宪章》《环境法典》和其他相关规范构成一个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新系统,那么这一系统在法体系和教义学的意义上就必须是内在融贯的。宪法规范、法律规范、法规规范等不同规范尽管效力不同,但却构成内容协调一致的整体,因此就必须保证下级规范符合并更好实现上级规范所确定的原则、价值或目标。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宪法化对《环境法典》等其他规范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通过法典条文的进一步完善来保证环境公众参与作为宪法原则的充分落实。就完善《环境法典》的条文而言,法律修改的作用成为首选。
自从《环境宪章》生效以来,为了消除违宪和努力合宪,《环境法典》的修改几乎成为家常便饭。比如法国议会专门制定了2012年12月27日第2012-1460号关于实施《环境宪章》第7条规定的公众参与原则的法律,对《环境法典》中原有的公众参与原则和制度进行修改、补充和优化。从形式上看,该法对《环境法典》的重要修改主要包括原则和机制两方面。
在原则方面,它扩大了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定义,将其定义表述修改为“每个人均得获知与环境相关的公共决策草案,并提出其意见,由有权机关予以考虑”①(19)①Article 1er de la loi n° 2012-1460 du 27 décembre 2012 relative à la mise enœuvre du principe de participation du public défini à l’article 7 de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与前述旧定义表述相比,新定义不再局限于知情,而是涵盖了知情和参与等各个方面,由此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定义和适用变得更为一般化。
在机制方面,该法围绕新的公众参与定义修改、补充和完善了重要的环境公众参与机制,从而使整个具体制度体系臻于成熟。在制度层面最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其建立了哪些新机制,而是其通过引入地方试验制度②(20)②关于法国地方试验法律制度的总体评介,可参见王建学、朱福惠:《法国地方试验的法律控制及其启示》,载《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7期,第89-92页。使公众参与机制具备了通过地方试验、科学评估和推广普及来实现自我升级和优化的能力。该法第3条规定,为实施《环境法典》第L.120-1条的规定,得以试验的名义暂停或变通内阁法令或部长指令,在18个月期限内试行特定参与机制,在试验到期前6个月由政府向议会提交评估报告,以决定将参与机制推广普及还是修改或废止试验。
三、作为宪法审查依据的环境公众参与原则
修改《环境法典》是立法者实施《环境宪章》第7条的表现。但事实上,环境公众参与作为宪法原则的所涉范围远超出立法者和立法过程。在宪法审查过程中,宪法委员会作为审查者、议会作为立法者和被审查者以及公民和环保社团等作为参与者形成了广泛互动。
(一)环境公众参与原则审查的形式特点
《环境宪章》是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规范,因此是宪法审查的当然依据。据笔者统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宪法委员会共援引《环境宪章》作出40项判决,③(21)③关于《环境宪章》实施的总体情况,可参见王建学:《法国的环境保护宪法化及其启示——以环境公益与环境人权的关系为主线》,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67-68页。其中20项援引第7条的公众参与原则暨程序性环境权,相比之下,第1条实体性环境权仅为11项,其余各条则为个位数。通常认为环境权作为《环境宪章》的基础包括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两方面,第1条实体环境权的适用频率低的原因在于其内容主观性强,因此宪法委员会的审查立场较为谦抑,而对于程序性参与问题,宪法委员会则可以有更多的置喙余地。④(22)④法国宪法委员会的立场代表了审查者的通常选择,但在实践中也不乏例外。比如欧洲人权法院在Guerra案中的审查似乎走得更远,其判定意大利政府未公开相关信息导致申诉人不能充分评估其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因此侵害申诉人受《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所保障的私生活和家庭生活受尊重的权利,参见《欧洲人权法院对未公开环境信息是否构成侵犯人权的认定——盖拉等诉意大利案》,李雪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9年第1期,第158页。显然,第7条受到宪法委员会的高度重视,而且在20项援引第7条的判决中有15项仅单独援引第7条。环境公众参与原则毫无疑问地构成法国环境宪法体系的拱顶石。
前述20项援引第7条的宪法判决在总体上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第一,从时间上看,全部判决均分布于2008年至2019年,具体而言:2008年2项,2011年2项,2012年5项,2013年3项,2014年3项,2015年3项,2016年1项,2019年1项。第二,从审查程序上看,15项适用事后审查程序(QPC)即由普通诉讼的当事人提请,3项适用事前审查程序(DC)即由特定国家机关提请,2项适用法律与行政法规权限争议程序(L)即涉及立法权归属。第三,从判决结果来看,违宪判决占绝对多数,具体而言,仅2项合宪,2项附保留合宪,其他均含有违宪认定,包括全部违宪、部分违宪和特定期限内违宪三种形式。
前述第一和二项特点表明,作为环境公共决策参与者的公民和环保社团在相关审查程序中具有重要作用,他们是最活跃的审查提请者。值得指出的是,法国的事后审查程序设立于2008年,以保障基本权利包括环境权为唯一宗旨,①(23)①关于事后审查机制及其效果,可参见王建学:《法国事后宪法审查机制的十年:总结与启示》,载《财经法学》2019年第6期,第121-133页。这也是全部判决均分布于2008年以来的原因所在。如出庭律师于格洛所指出,“事实上,事后审查程序维持了必要的机制,使得立法机关被激励去适用公共参与原则并保证相关立法符合宪法规范。”②(24)②Christian Huglo, La QPC: Quelle Utilisation en Droit de l’Environnement?, Les Cahier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n° 43, avril 2014, p.57.第三项特点则证明了这种激励作用,大量违宪判决倒逼着议会修改法律,从而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具体机制。
(二)环境公众参与原则审查的实体内容
从实体内容看,第7条的公众参与原则包含两类程序性环境权:一是知情权即获得环境相关信息的权利;二是狭义环境参与权即参与制定环境公共决定。当然,这两项权利的实现受到法律保留的限制,即“在法律规定的条件和限制下”。宪法委员会在多项判例中阐释和发展了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实体内容,保证法律在其中发挥恰如其分的作用。在2011年10月14日的判决中,宪法委员会确认了第7条属于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之列,该条要求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确定该原则和权利得以实现的方式。③(25)③Décision n° 2011-183/184 QPC du 14 octobre 2011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此后,宪法委员会基于第7条进行了多次审查,不仅拓展了第7条的适用范围,建立了相应的审查标准,还发展了违宪认定的生效方式。
首先,就适用范围而言,宪法委员会在2012年7月27日的判决中认为环境公众参与原则不仅适用于条例性决定,也适用于具体或个别性决定。④(26)④Décision n° 2012-269 QPC du 27 juillet 2012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在2012年7月27日的判决中,宪法委员会认为,第7条不仅适用于对环境具有消极影响的决定,也适用于对环境具有积极影响的决定,⑤(27)⑤Décision n° 2012-270 QPC du 27 juillet 2012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这一原则在2016年的判决中得到重申。⑥(28)⑥Décision n° 2016-595 QPC du 18 novembre 2016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宪法委员会在2012年11月23日的判决中提出第7条适用于其生效(2005年3月3日)前已经存在的法律。⑦(29)⑦Décision n° 2012-283 QPC du 23 novembre 2012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其次,就审查标准而言,宪法委员会在2012年11月23日的判决中将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对环境具有直接(directe)和重要(significative)影响的非条例性决定”,⑧(30)⑧Décision n° 2012-282 QPC du 23 novembre 2012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建立了直接性和重要性的审查标准,此判决直接促使议会出台前述2012年第2012-1460号法律,全面更新《环境法典》中的相关内容。最后,就违宪认定的生效方式而言,宪法委员会在2014年5月23日的判决中认为受指摘的法律自2006年12月30日第2006-1772号法律以来构成违宪,但自2013年1月1日开始不再违宪,因为2013年1月1日起《环境法典》第L.120-1条经重新编撰后终止了违宪状态。⑨(31)⑨Décision n° 2014-396 QPC du 23 mai 2014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三)环境公众参与的宪法互动
总结《环境宪章》颁布以来所出现的环境法的宪法化过程,特别是围绕环境公众参与原则所形成的宪法和环境法变迁,可以发现包括宪法法官、立法机关、普通法官、公民等在内的所有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宪法互动。如阿吉拉法官所说,“宪法法官通过强有力地建立一种新的司法动力机制,赋予了《环境宪章》条文以完全的效力。按照宪法原则来改造环境法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已经为环境法创造了一种改革动力机制。其中,立法机关在宪法委员会的推动下,发挥着首要作用。最终,在一种‘环境民主’的框架内,公民不仅是《环境宪章》所承认的权利的主体,而且也是《环境宪章》所施加的义务的主体。”①(32)①Yann Aguila, Les Acteurs Face à la Constitutionnalisation du Droit de l’Environnement, Les Cahier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n° 43, avril 2014, p.43.因此,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宪法化绝非可有可无的形式,而是实现环境法变革的重要途径。当然,仅在形式上将环境公众参与写入宪法文本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宪法文本进入宪法审查的层面。
《环境宪章》将环境提高到受宪法保障的人权的高度,具有引领时代的地位。这种引领性地位特别体现在第7条的环境公众参与原则上。通过第7条的反复适用,宪法和环境法形成了环境治理合力,不同的宪法互动参与者共同编织着环境民主和环境正义的蓝图。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环境宪章》仍然受到很多内在与外在限制,同样也面临很多挑战。在《环境宪章》颁布实行十周年之际,普里厄教授曾专门撰文回顾其实施情况,他认为,“尽管《环境宪章》时至今日仍然受到种种质疑和争论,但《环境宪章》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改变,其背后的宪法动力已经慢慢走上正轨,包括宪法法官和普通司法法官与行政法官在内的司法者已经在逐步适用它。随着它越来越具有实际的效力,《环境宪章》今后能够将公共政策导向新的环境伦理,从而足以应对生态紧急情况、下一代人的权利和地球生态挑战。”②(33)②Michel Prieur, Promesses et Réalisations de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Les Cahier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n° 43, avril 2014, p.5.
四、我国环境公众参与规范发展的前瞻
在我国,环境公众参与刚刚迈入环境单行法原则阶段,其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未来的环境法典编纂应注重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规范形式和制度建构,同时也有必要从宪法和宪法审查层面前瞻性地考虑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地位。
(一)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发展阶段定位
中法两国现代环境法均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但我国环境法特别是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发展速度明显更慢。学界常将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6条解释为环境公众参与,但这只是学者们“在教材著作中予以‘拔高’而已,其效果无非类似于‘往国人脸上贴金’罢了。现实情况是,我国至今尚无一条环境法律条款明确宣示确认公众参与为环境法之原则,更不能企及立法已明文确定其为基本法律原则”。③(34)③竺效:《论公众参与基本原则入环境基本法》,载《法学》2012年第12期,第128页。2002年《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1条最早设立了公众参与制度。④(35)④“《环评法》最为突出的成就是确立了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但是公众具体享有哪些权利,又有何种程序保障这些权利,以及如何救济这些权利?《环评法》都没有明确规定。”高敏、谷德近:《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制度的完善》,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12期,第74页。此后该制度虽有所发展,但在总体上看,“环境法中有关公众参与的规定覆盖领域不全,彼此间呼应不足”⑤(36)⑤史玉成:《论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价值目标与制度构建》,载《法学家》2005年第1期,第131页。。
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订首次明确将公众参与确立为环境法基本原则,国家环保部随即出台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目前,环境公众参与的规范变迁正处于环境单行法基本原则的阶段,大体上与法国1995年巴尼耶法类似。客观而言,这种发展阶段在世界范围内较为落后。而且与巴尼耶法不同,我国的环境公众参与并非在积累环境公众参与机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由具体机制总结、提炼和上升为法律原则,⑥(37)⑥公众参与在我国的展开显然是先原则后实践、以理念倒逼实践。事实上,公众参与原则写入新《环境保护法》近乎为意外事件,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和二次审议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中均未有规定。更没有受到《环境宪章》那样的宪法价值、目标或原则的指引。因此,在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实践中,环境公众参与原则几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环境保护法》的文本中孤零零地飘荡。因此,未来应当借鉴法国经验,一方面建构更为健全的参与机制和实践作为基础,另一方面在宪法和宪法审查层面统筹宪法与环境法的关联。
(二)环境法典编纂远景下的环境公众参与
为落实环境公众参与原则,首先需要发展和完善《环境保护法》第五章所设置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近几年来,我国的环境公众参与机制实践正处于不断完善的缓慢过程中。从法国经验来看,完善参与机制体系的过程需要注意以下三方面问题。
首先,环境公众参与机制宜以公民权利为价值指针,从而在扭转环境保护国家主义的同时激发环境保护的社会活力。环境问题早已超出国家本身的治理能力,因此必须借力公众参与来实现环境治理目标。正因为如此,国家主义传统浓厚的法国在1995年巴尼耶法中以公民权利来定义环境公众参与原则。我国的环境公众参与也一直由国家主导,“公众参与的进程一直处于自上而下的状态,政府处于主导地位,由其任享予取予夺之权力”,①(38)①黄云:《我国环境领域公众参与之法律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0期,第103页。因此,权利本位的环境公众参与原则及其制度建构是必要且适当的。
其次,环境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应避免体制改革决策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降低体制变革的错误成本,由此必须采取科学方法。就此,法国2012年所建立的环境公众参与机制的改革试验制度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将试验引入公众参与机制的好处是,在维持既有参与机制整体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在特定地方或领域采取法律或法规变通的形式,能够有机会在特定期限内试行新的参与机制,最终在对新机制的效果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提炼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并进行推广普及,从而实现参与机制的渐进式改良。2015年《立法法》第13条已在法律层面建立试点机制,显然该机制在环境公众参与领域具有广阔的适用空间。
最后,眼下的环境法典编纂有必要注重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规范形式和制度建构。学界普遍承认编纂环境法典的必要性,目前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已形成基本框架,环境保护的主要领域也已基本实现有法可依,但分散式环境立法模式导致环境法律法规之间存在重复、矛盾等现象,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典化来消除这些弊端,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系统化的法律规范体系保障。②(39)②参见王灿发、陈世寅:《中国环境法法典化的证成与构想》,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2页;窦海阳:《推进环境规范的法典化》,载《中国国情国力》2018年第11期,第35页;张梓太:《中国环境立法应适度法典化》,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第239页。但公众参与原则在未来环境法典中的地位则尚未受到关注。笔者认为,公众参与原则应当毫无疑问地构成环境法典的总则原则,并且其具体机制应当在环境法典分则中占有最重要的一席之地。以公民参与权为价值指针努力在实践中科学地发展和完善具体的环境公众参与机制,有助于为环境法典相关章节的起草积累实践经验。
(三)宪法审查远景下的环境公众参与
除法律层面特别是环境法典编纂远景下的考量外,也有必要在宪法特别是宪法审查层面考虑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地位。学界一般认为,现行宪法第2条第3款为公民环境参与权提供了基础,其中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环境保护当然可以涵盖在经济和社会的范畴内。也有学者将公众参与的依据转移到宪法自由权规范,“需要承认自由权的程序参与功能,即肯定公民在其自由权可能受到行政决策侵犯的时候,有权参与决策程序。”③(40)③谢立斌:《公众参与的宪法基础》,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4期,第106页。其实宪法第2条第3款和自由权规范均构成环境公众参与权的规范依据,二者对应着公众参与权的二元区分,即公众参与的“公众”包括“有利害关系的公众”和“无利害关系的公众”两种不同主体。④(41)④参见徐以祥:《公众参与权利的二元性区分——以环境行政公众参与法律规范为分析对象》,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63页。
难点不在于公众参与的宪法解释,而是如何将其有效运用于审查实践。晚近几年,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宪法审查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在环保领域,仅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撤销地方立法文件580件。⑤(42)⑤乔晓阳主任在参加“2019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发布暨研讨会”(2020年1月4日)时透露了该数据。借助审查机制不断强化的契机,显然有必要提高公众参与机制的合法性与合宪性,塑造从宪法到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在内的融贯的环境公众参与规范体系。环境公众参与意味着个人的主动地位,这种地位也应当反映到相关的审查程序中。从法国经验看,作为环境公共决策参与者的个人,在宪法审查机制中同样应当发挥重要作用,构筑环境公众参与宪法互动的起点。从环境公众参与的侧面看,我国的审查机制也需要倚重个人的审查提请,无论是诉讼中对法规规章的附带审查请求,①(43)①目前行政诉讼中较少见直接针对公众参与具体问题的诉请,参见朱芒:《公众参与的法律定位——以城市环境制度事例为考察的对象》,载《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11页。还是依《立法法》第99条提出的审查建议。
五、结语
我国法学界近年来对环境公众参与原则和公民环境参与权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虽然越发细致,但缺乏总体法律观和历史纵深感。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着通过中法横向比较和历史纵向发展来探讨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宪法化。五十年前在“文革”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我国不仅派员参加了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而且奇迹般地在国内拉开了环境保护事业的序幕。②(44)②关于该时期我国环境保护法制的奇迹般萌芽,可参见曲格平:《梦想与期待——中国环境保护的过去与未来》,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我国环境保护的开端不可谓不早,起点不可谓不高,但就环境公众参与的法律规范体系而言,则仍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本文旨在强调一种必要性,即在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历史发展中准确定位我国相关法律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以此为基础,在宪法和环境法的综合统筹下构建环境公众参与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