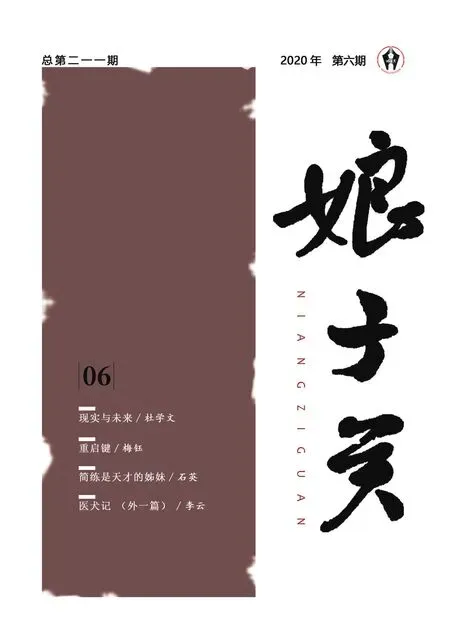心梗
文 师郑娟(临汾)
余老汉看着枝叶下面,那水汪汪的大桃子,眼睛不由得又伸向了沟那边。不知为什么,今天,他特别想见到那个小媳妇儿……
小媳妇儿名叫白小手,原本姓钱,那还是她嫁过来的时候,一双婴孩般的小胖手,白白嫩嫩的占据了人们对她的记忆,真名儿叫什么,怕是只有她自己知道了。白小手和余老汉相差二十几岁,就住在和他一沟之隔的果园对面。三年前,她男人因与人酗酒斗殴,一个酒瓶砸下去,那人就捂着胸口告别了世界。虽然查出死于心梗,但也是白小手男人刺激所致,一下判了他七年。这事儿害的白小手守了活寡,也落下个心病,总是觉得心口疼,人固然一死,可突然死去有点恐怖,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脏器。男人被拉到外地服刑时,她追着警车嘶声喊:我绝不会心梗死掉!我就当你出了趟远门!娃儿们我能招呼好,你说了让我享福哩!可是,这个倒霉的男人,还没有让深爱他的白小手,过上一天好日子。
现在,白小手只有靠在果园打工,自个儿供养着一儿一女上学了。成日,啥活儿重她干啥,啥饭省钱她吃啥,但各种药品不能断,药是她的安全感,是她五脏六腑的保护神。特别是那软化血管的,预防脑梗心梗的,只要听说到的药名儿,她都要第一时间吃一吃,用她的话说,不吃命就悬着哩!几年下来,一个原本娇俏的人儿,变得疯疯呆呆,特别是那双白白嫩嫩的小手掌,被一双粗糙的五指耙所代替。每天除了吃药干活别无二事,常爱不知羞耻地,有意无意地挑战着余老汉衰老的躯体。这是余老汉被聘到这百十亩的果园后,意外艳遇的乐趣。一面管理着园中的果树,一面还享有包工头的权利,园中除草、施肥、打药这些活儿,要怎么干、怎么用人,都是余老汉说了算。这个叫作白小手的女人,就是服他这一点。

桃熟的季节,已带有几分霸气的炙热。余老汉看着空荡荡的路尽头,无望地垂下了软塌塌的眼皮子,靠着一棵桃树歪坐到荫下,昏睡了。他的汗水洇湿了身上黄色的T恤,胸前那位戴墨镜的漂亮女郎,已被他磨得面目全非。这是儿子退下来的衣服,穿在余老汉身上有点滑稽,但他已经过了讲究穿戴的年龄,儿子给什么他就穿什么。饭时到了,余老汉肚里早饿得叫唤,可他乏累的身子不想动弹,只有操起筋骨满布的老手,哗啦哗啦拧开随身的水壶,仰头咕咚一口,又大大喝了一口,末了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余老汉的水壶比别人的都大,杯口系着一个不长不短的蓝布带子,正好斜挎在他又瘦又薄的肩背上,虽然是个塑料制品,但它却是余老汉的贴身宝贝,一天到黑泡着一些低级的茉莉花茶,渴了是水,饥了是饭。
今儿端午节,余老汉唯一的工人,就是那个叫白小手的女人,早早回家过节去了。余老汉很不习惯地在宽阔的地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很想摘几个挂红的桃子,给那小媳妇儿送去,她们孤儿寡母的,日子可是咋过的呀?天天吃啥花啥,家里有个扛的背的,她一个女人家……可余老汉转念又想起了儿子。儿子是他和老伴儿晚来的独苗苗。前几年,国家掀起了搬迁浪潮,他们抛家舍田地搬到了城里,虽然公家安置了新房,可来来回回的,包括装修那些,花去了他们两辈人的积蓄,还有那物业费,生活费更是得他和儿子到处打零工顾全。孙子入学后,各种培训班的费用开支,也让余老汉瞠目。他很怀念在乡下的日子,米面粮油菜都是地里长的,顶多花个电费盐钱,现在倒好,一下不干就得到大马路上喝风去!余老汉时常站在繁闹的街头发呆,他觉得自己就是城市里多余的人,那个属于他的生命,早已跟着拆迁的老屋消失了,魂儿不过游荡着。
还有一个最要紧的,令余老汉伤心。在乡下的时候,儿子儿媳每天都能安安分分地跟着他的计划种田做事,自从搬到了城里,原本两张温和的脸,就像突然戴上了一副讨债的面具,见他便拉下两尺。不是唉声叹气地与人攀比,就是揍骂他五岁的孙孙,捎带老子没本事,抱怨命运不公平。余老汉疼惜儿子,不能让他受这个熬煎,便鼓励他和城里朋友一样,买上一辆小轿车,进进出出不就风光了?年轻人嘛,不能在人前面上太窝囊。人活啥呢,不就是为了下一代?儿子高兴比啥都强!
“老伴啊,你别愁,只要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动弹,肯定能把他这三年的按揭款管了,每月三千块钱,我出。家里的生活费,孩子的学费尽量他自己出。往后,我也用不着啥钱了,不吸烟不喝酒的,儿子剩下的衣服,我死了怕都穿不完。你……老太婆,你要是走了哇,我一个人就到外头给人扛活儿去,吃的住的人家不是都管了?月尾把钱给他拿回来就对啦!”这是余老汉给弥留之际的老伴儿许下的承诺。说话时呜呜咽咽一个劲儿哭,像个孩子,老伴儿心疼地想拉拉他的手,可没抬起胳膊,人就歪过头,去了。
老伴活着的时候,知道余老汉好一口甜食,虽然生活不宽裕,可每到一个节气,她都会花点心思叫余老汉过下嘴瘾。像今天这样的端午节,粽子啦,油糕啦,红烧肉啦早都摆到桌上了,说不定还会叫他小酌一口。记得有一年端午,天也是这样的热,太阳也是这样的高,余老汉在地里给要开镰的麦田里修路,最后几平车的土,本打算拉完了再回去吃饭,可就迟了那么一会儿,那老婆子竟叽叽喳喳地寻到地里,嚷他不看饭时,不看日子,非叫他扔下工具立马回去!余老汉不肯,坚持拉完,老婆子坚决不让,为此两个人还差点打起来!那个老婆子啊,脾气可真倔!那么大力气,硬是我没弄过她!余老汉想着想着,就咧嘴笑了。
他缓缓站起身来,悠悠地看着太阳底下,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果园,绿油油的那个美啊,小风儿一吹,满树的果子都露出嫩脸来,它们簇拥着,热闹着,将这个年近七旬的老汉,毫不顾及地淹没在远离故土的凄凉之中。这样的场景,余老汉做梦都没有想过。不是因为美,而是因为他多么孤独啊。人在肚子饿的时候,也最容易想家。可是,那个家啊,怕是死都回不去啰!听说门都叫人钉上啦。我那贤惠的老伴儿呢,到底去了哪里啦?那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咋能过着过着,就成了我一个人的光景呢?余老汉怔怔地站在太阳底下,灰塌塌的眼睛,显得无比空洞,仿佛掉进了记忆的深潭里,醉得那样透彻……
“嗨!包工叔!”突然炸响的声音,惊得余老汉一个趔趄。
“哈哈!包工叔,你想啥哩!咋都哭了呢?”白小手探过身子,瞧着余老汉挂着泪痕的眼睛,手就摸到了他的脸上。
“憨女子,来也不出个响声!”余老汉歪过身子,吸溜着鼻子。他讨厌别人看见他落泪。
“我来给你送饭吃!”白小手说着,就从宽宽的阔腿裤里,掏出来一疙瘩扁扁的东西。
“人家媳妇巧,都拿叶子包着吃,咱从小娘惯得也没学下个手艺,我家只能吃这个!嘿嘿!”她一边说,一边打开塑料袋。一碗雪白的粳米饭露了出来,隐约散着些白糖。
“你,你这是干啥嘛?给我送这干啥!”余老汉瞅了一眼旁处,赶紧说:
“不吃,快拿回去!”
人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到了余老汉这个岁数,吃饭防噎,走路防跌的觉悟还是有的。余老汉咕咚了一口他的茶,眼睛又看向了果园子。
年轻那会儿,余老汉在村里可是好强的人物。当过村干部,还会嫁接管理各种果木。乌黑茂密的头发见天就洗,丝一样光亮,衬着一双浓眉大眼,给他不爱说笑的性格多了几分招摇,没少惹得别家小媳妇大姑娘惦念。但余老汉只爱他的老婆孩子和日子。现如今,就算是老了,但凭他当年风风光光落下的气质,也不是她一个傻女人能接近的呀!
余老汉又陷入了从前的种种骄傲中。
白小手急切地迈前一步,举着饭说:“包工叔,你就吃了吧,好歹是个节呀!又没人瞧见我送饭的,我是捂着跑来的。喏?”说着,褪下裤腰,朝余老汉露出了烫得红红的白肚皮。
余老汉讲究为人作风,他不愿意和这个年轻的女人,在这荒山野地纠纠缠缠。毕竟,他心怯女人那栖栖惶惶的眼睛哩,仿佛随时都会将他拉下水。如果……如果,这事儿在梦里,余老汉还是有一些想法的。
白小手见余老汉并不买账,哽咽了说:“我娃嫌弃我不吃,你个老汉也嫌弃我……”说着眼里噙着的泪水,就混着汗水一股一股往下流。
余老汉心内一软,没话再说,接过饭来,折了一根蒿杆子,就地呼呼噜噜扒起来。啊嗬,香甜得很嘛!余老汉边吃边看了一眼傻站在旁边的女人,便擦了嘴,几步到田头摘来了几个又大又鲜的桃子,递过去说:“别看了,快拿着回吧!”说话间,他又看了下旁处,小了声儿说:“给人送饭,好歹该有个讲究,再不能别在裤裆里头唵!”白小手笑了,黑红黑红的脸凹里,皱起一道道细纹,赶忙掀起褂子擦把眼泪,叫余老汉把桃子给她放到褂里裹上。余老汉抬眼妈呀一声,磕巴说:“你,你手拿着回!”白小手立刻放下褂子,接过桃子,挤着笑成一溜缝的眼睛,往余老汉身边蹭着,慢声说:“包工叔呀,那今天,你能不能多记我一个工呀?!”
自从老伴儿死后,儿子就将余老汉和他的铺盖卷儿,送到了这十几亩的果园里,凭着老爹年轻时学下的那点儿手艺,帮哥们看管这个受了荒的桃树林,每月三千块钱的工资,桃园老板会在月头按时送来。余老汉再随后交给儿子,偿还车贷。他时常心中祷告,希望在这风天野地里,平平安安地熬上个三年,不敢生病,更不能死,对他来说,三年就是翻过了一座大山,只要给儿子车贷还完了,日子也就轻松点,那时候,他想回去养个老。
余老汉每天认认真真地侍弄着这些桃树,熬着太阳冒出山尖儿,又看着太阳沉下山去。其间月亮到底圆了几回,老汉记不清了。但他总记得在月亮很圆很圆的时候,把头脸洗净,换件干净的衣裳,正儿八经地走到桃林里,给树们讲他和老伴儿从前的故事。他觉得,万物都有灵性,特别是在月满的时候,树们看似不说话,可它们比人明眼,人再聪明,不是还有睡过去的时候?树有吗?树没有!它一年四季都在和太阳月亮对话哩。世间谁人谁事,树们都明白着哪!还有,他相信,人死了是有灵魂的,就像老伴儿从来不会离开他,那个魂儿,一定是借物存在的。老伴儿活着的时候,那么善良,兴许现在修了个神哩!兴许还是个树神。所以,余老汉格外爱护这些树,没事就给它们捉虫拔草施点肥,树们也越来越旺盛了,虽然不能说话,但它们会用喜人的果实感谢他,就像他从来没对老伴说过谢谢,但他心里只装她哩。余老汉笑笑,有点混沌的声音又散向桃林,树叶儿一动不动,月光白花花落了一地,余老汉又讲:
进门时,她才十七,瘦得一阵风都能刮跑,但就是这样的身板,却会心疼男人,有口吃的紧着男人,有个喜脸也给男人。白天跟我下地干活,晚上哄我吃饭睡觉。只要我的小呼噜啊,呼噜呼噜拉起来,拉匀了,拉稳了,她才悄悄溜出被窝,又到灯下缝缝补补。我一个庄稼人,硬是叫她打扮得越来越像个干部。那些年,有她做后方保证,我全力竞选上了村主任,一颗心扑在村里杂七杂八的事情上。有一年,刘老大家的牛被偷了,他老婆气得头不停撞树,最后还是我拿着干粮走访三个县,五十个庄,才从牛贩子那里把牛给追了回来。那次连续了走二十几天,回来时,我家儿子已经从她肚里掉到炕上了,头发还湿腻腻的,可她没有埋怨我半句,见我回来,一下扑进我怀里,又是掐我的肉,又是亲我的腮,烧火做饭的一阵儿忙活。那时候,有人数落她,你傻呀,没见过男人吧,稀罕成这样!她却说,我把他当成我的一件作品哩,作品好看,证明我就能干!我的树们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时,笑得合不上嘴,但笑着笑着我就哭了,我是哭我那早死的娘哩,她活着的时候也没给我亲成这样子哇!那时候,我就发誓,我要一辈子守住她的好,别家的女人,光光溜溜抹身蜜,我也绝不正眼瞧!这叫忠诚!
在一个知了嘶鸣的晌午,白小手顶着大日头,第二次给余老汉送来了饭。当她及时地出现在余老汉门前的时候,像个报喜鸟一样,俩眼笑眯眯地瞧着正要烧火做饭的老汉。
“喏,现成的!”她举起来,朝余老汉炫耀说。
“啥东西?”老汉抬头问。白小手便拉着余老汉,走到屋里的一个凳子跟前,将袋子放上面打开给他看。余老汉瞅了一眼,馋水滋儿的一下就冒了上来,那扑鼻的香气,那细细碎碎的葱花,和鼓得圆圆的肉团子,像极了富人们白白胖胖的耳朵,好看极了!
“好饭嘛!”余老汉高兴地问:“哪来的?”
“外卖。”白小手嘿嘿笑着说,“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吃。”
“咦!这女子,花这钱干啥?”
“该花。你照呼我哩!”白小手说着,就从墙上的塑料袋里,取出了这屋里唯一的筷子。余老汉接过筷子,朝白小手感激地笑笑,顺势就圪蹴在凳子旁边,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这样精致的食物,余老汉已经忘了多久没有吃过了。他嚼着嚼着,就嚼出了一阵阵心酸,嘴巴一张,眼泪就下来了。白小手赶紧找他的水壶,忙问:
“辣的吗?这里头辣的吗?”余老汉摇摇头,夹起一个,对白小手说:
“你也吃个。”
“我不吃,我来前吃了俩辛伐他汀和阿司匹林,但我还想再吃上一点三七粉。”
“吃那顶饭?”
“顶哩,起码我不会心梗。突然死了多可怕呀,和那狼食一样,害人害己!我可舍不下我那俩娃儿!”
白小手边说边拿来水壶:
“我打听了,要凑人家活动买。每月也就二三百块钱……”她说着看着余老汉,可余老汉并不看她,便不言语了。等老汉袋子吃空了,一个饱嗝打上来,才又把茶送到了他的手里。余老汉满足地咂了咂嘴巴,白小手紧忙扶他坐到凳上。余老汉看看跟前热乎乎的小女人,幽幽的眼神又看了远处,叹气说:
“唉,现在死活也没人管了。”
“我知道你一个可怜的,见天就靠着那一壶茶水。”
“老了,没啥正经了。”
“你还会挣钱啊,还是我的头儿,不老!”
……
“包工叔,你咋不找个伴儿呢?”白小手往耳后别了别她的短发,俩黑眼珠眼瞧着余老汉问。
“年纪大了,不算人了。”
“每月有那三千块,找个女人过好日月哩!”
“好女子,难为你给我送吃的,你快回吧,时间不短了。”余老汉说。
“我不,我不走!”白小手突然胳膊一甩,将肥圆圆的屁股一扭,就坐在了余老汉床头。
“你……咋了?这是,”
“我就是不走。”白小手干脆挺着胸脯,逼近余老汉撒起娇来。
“这娃儿,快走吧,别让人看见!”
“看见就看见!天下人和物,都不是有个公和母?谁不知道干啥哩!”
“咦!说些憨话,我这么大年纪了能干啥?”
“我不信!王翻他爹比你还老,见黑就往大长腿家钻!”
“那是人家有钱。”
“你月月也拿三十张哩!”白小手抓抓衣襟,低了头轻说,“不干男人的事情,你活的啥兴趣?”余老汉不吭气,白小手又说:
“包工叔,我知道你心肠好,我家男人没出来,我想和你搭伙过日子哩,你想吃啥,我就学着做啥,给你洗洗衣服说说话,你也不用在这荒山野地流泪了。”
“唵,这能行?可是你说咋过哩?”余老汉转过身,嘻嘻地看着白小手,灰灰的眼睛泛出了亮光,像个年轻人一样面含羞涩。
“我,我倒也没啥心思,咱俩幸福就好。就是,每月娃儿们的学费,和我那点药钱……”
“啥,你说叫我出这钱?”余老汉一下绷起脸来,忙说:
“我可没钱!”
“我又不白要你的,有个年轻女人黑夜白天在身边,你想想。”白小手说着就去拉余老汉的手,可余老汉却一步抢到门跟前,指着门外嚷:“原来是搞经济哇,我一分钱都没有,你走!你快走!”
“你个死老汉,我咋看着你是好人哩?我家娃儿可怜的,他爸进去了,我就不能让他和别家娃娃一样了?娃们这期的补习费,拿不出我还活啥人!”白小手哭了,呜呜哇哇的哭声,像雷声一样震慑着老汉。
“为了这钱,村里我都跑遍了,没人把我当人呀!”
……
“这,唉!那咱俩说清,管和管可不一样。我又不是你什么人。”余老汉正色说:“你跟我干活,急用钱,可以给你拿一些,但你得给我打个条,咱要说好,下个月这钱从你工资里扣。”白小手擦擦眼泪,点了头,余老汉便拿来了纸笔,白小手接过去,不等余老汉说话,就写下了两千块钱的字据。
“啥!你当我是开银行的?”余老汉瞪大眼睛说:
“不行,我儿子要还车贷哩!”
“俩娃儿学费就得拿走一千二,月底还要给姐姐随礼,剩下的,我总得买点救命的药啊!”
“那也不行,太多了!重写,你重写,最多五百!”余老汉发着脾气坚持的时候,白小手的眼泪又扑扑簌簌流下来,哭着哭着,身子就像泥团一样跪在余老汉脚下,余老汉拉她不起来,只有从床头褥下,拿出了老板才送来的工资。
“你把日子也写上。下个月这时候要还我。”余老汉平静地说着。给白小手一张一张数钱的时候,他也流泪了。
几天后,余老汉的老板来吩咐余老汉尽快组织人手,桃园两天后正式开园,会有事先联系好的批发商来运走果子。不但要他注意卸果装箱时的品级分类,还要保证桃园套种的西瓜秧苗不被踩伤。这个通知让余老汉又急又喜,急的是这么大的工程,老板只做甩手掌柜,他真怕自己有个疏忽,比如货车的进出路线啦,工人的采摘搬运啦,还有时间进度安排等。可喜的是,看着自己精心守护培育的桃子,从发芽,开花到坐果,终于要风风光光走向市场了,像一个个待嫁的姑娘,多眼馋哪!眼睁睁一个丰收年!老板高兴,余老汉心里也高兴。
……
开园那天,人车交错,鞭炮齐鸣,异常热闹。往日只有风和阳光的桃林,今日像花果山的猢狲们下了山,好不热闹,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尽管树下套种的瓜秧之前做了防备,但余老汉依然不放心谁的脚丫不长眼睛,一脚送了瓜胎的性命,他紧张也兴奋地干脆找来一面铜锣,巡山一般流动在桃园各个装车的卡口,对着众人敲起来:
嗨!嗨!
各位老乡听我言,摘桃注意脚下边。
桃树林里套西瓜,瓜秧还小正扬花。
一不留神踩下去,秧断花残剩泥巴。
你踩一脚不打紧,老汉辛苦白干啦。
都是苦巴庄稼汉,我说你听不见怪。
今日脚下积点善,来日瓜熟好招待。
……
老板是个留着平头的年轻小伙子,激动地拉过余老汉的手说:“余伯伯啊,您老是我的福星啊!这个荒了的园子硬是让您弄成啦!瞧瞧,多气派!”余老汉放下铜锣,笑着将他拉到一边,好生说:
“娃儿,伯给你说,差不多的时候,工资能加你就加点吧?都怪不容易哩。”
“余叔,我和您儿子是好哥们,给您的工资不低呀!”
“不低,不说我,是她,活儿不轻……”余老汉说着,看向了正在干活的白小手。
“哈哈,我说嘛!敢情您老怜香惜玉啦?她一个罪犯老婆,又不正常,用她满是可以啦,您这么大年纪,最好还是少沾惹!”余老汉一下噎得没话说。手里的铜锣瞬间似有千斤重。
这次开园采摘,余老汉一共寻来邻村二十个男女。当然也包括白小手。他把他们十人各分一组,一组负责一辆货车。车又兵分两路,南北各开一道,为了保证活量和瓜秧不被踩伤,特意分派白小手和他各担任一组组长,下桃的同时,得把一些余心操到,果子的大小摆放啦,品种归类呀,负责点数呀,不过,他们点数也是点自己的数,具体还是到地头余老汉做最后统算。从树上摘下一筐是五块钱,从地里搬到车上是七块钱,白小手热心这个七块的,干得吃力而特别认真,搬起一筐桃子,像肚里挺个足月的娃,俩脚踩风一样往前窜,一晌午下来,搬运的数量竟比男工还多出六筐,前胸后背的褂子汗津津贴在肉上,像个白花花的萝卜裹了层纱,惹得那些开车的司机小伙低头窃笑总瞅她。
“哎,我说白小手,你干脆脱球了算啦!”一个中年男人吆喝着,白小手还没听明白,那边就爆出了一阵哄笑。
白小手愣怔了一下,看着那些人,忙低头含胸揪着粘在身上的衣服。这件褪了色的红褂子,还是男人在家的时候给她买的,就是成天脏了洗干了穿,薄得成了蝇翅膀,不怪男人们稀罕她,毕竟人家没有么。白小手几次也想买件新衣换上,可她每月不停地干,也就那么一千五百块钱,孩子们没事不回来,回来就是要钱的,给的慢了,连妈都不给她叫。不过。白小手相信,孩子们大了一定都会孝顺她,到时候他爸也刑满出狱了,一家人的好日子才会真正开始。现在穿烂点,邋遢点都没有关系。只要在男人回来之前,心梗脑梗猝死等,别来找她,那就阿弥陀佛了。再说白小手的男人,是个很帅气的英俊男人,只要他往白小手身边一站,其他男人都得靠边。白小手当年不顾家里反对,就是图他这一点。白小手想着想着就笑了,红彤彤的脸上充满了希望和喜悦:
“看呀,看呀,你们看看能多个啥呀!”
男人们安静了,一丝风声也没有,他们睁大眼睛,溢着口水,像个突然被定住的雕塑。白小手喊道:
“每人给我搬十筐桃子,可别欺负姑奶奶我男人不在!”
……
就在他们说逗的时候,余老汉已经默默地往白小手的桃堆上,摞起了很高的垛子。
忙到第五天的时候,果园里原先红艳艳的一片就变了颜色。尽管树木没有损坏,可远看近看还是一目狼藉。桃子卸完了,人也泄了气,余老汉拿着他的水壶,坐在果园旁边的山坡坡上发呆,灰灰的眼睛又静静地看着远处,垂下的眼袋,像被人抽空了的茧壳儿,耷拉着。
“包工叔,这下咱们干啥呀?”白小手一边撩起衣服扇着风,一边朝余老汉走来。
“没啥干了就歇歇。”
“不行呀,我可不能和你比,家中有俩讨债哩!”白小手说着就挨着余老汉坐下来。一股浓烈的汗气味儿,瞬间扑进了余老汉的身体,说不清的味道,撩得他浑身颤抖。
“包工叔,一会儿,你还得给我拿上俩儿,管心梗的药又快完了,明儿让人给我捎回来,备着。”余老汉转过眼睛看向她。他对白小手三天两头的借钱,已经成了无力抗拒的事情,甚至觉得被她需要,成了一种自己的需要。但不管怎样,他都清醒得知道,在白小手每次借钱之前,都要认认真真地叫她打条。
“嗯。钱是钱,你以后,少在男人跟前聊骚。”余老汉看着远处,嗫嚅说。仿佛说出这个话,要他承担什么后果似的。
“你是说我俩这个?”白小手拍着自己的胸脯,问他。余老汉不回答,白小手却莫名其妙发了脾气,大声吼起来:
“叫你看你不看,还能挡住别人看?!再说,他们给我挣了八十块钱哩!”
“我没本事么,唉……”余老汉沉默了,眼睛呆呆地看着远处,一声叹息之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那你,是不要女人了吗?”
“要不要能咋?谁能白跟我!”余老汉嘣的一声,从地上揪起一根草叶说。
“……你等着!”白小手突然起了身,低头绕过旁边的小树向地头走去。
“干啥去?”
“你等我一下。”
……
回来的时候,白小手手里缠着一块大红色的床单,对着绿油油的草地,哗啦一扔,就平平展展地铺开了。
“老余,坐过来。”她轻声说。“来呀,坐过来嘛!”
“干啥?”余老汉吃惊地瞧着白小手,不动。
“你,你啥意思吗?”
“让你做我的男人哩。”白小手红了脸说。
“唵?你……是不是,你要和我卯账哩?”
“这老汉,不卯,白纸黑字可在你手上呀。”
余老汉还是不动。
“你往我身边坐一坐嘛,老余。”
女人拽着余老汉衣服,猫一样叫唤。
“老余,你把手给我。来,放我这里。”
“老余,你闭上眼睛。你感觉好吗?”
“……好。”
余老汉的喉咙里,渐渐发出了呼呼的声音。手也活动起来。
“……来,那你上来。老余。”
“我……等一会儿。”余老汉突然睁大眼睛,瞪着天空,气喘说:
“你,你要等,等一会儿!”
天空那高远,那样湛蓝,火红的太阳拖着缤纷的光辉,慢慢向西滑去,不过一会,天就要黑了,黑的会将大地万物吞没。一天的结束,就像一个生命在结束之前,不过虚空一片。余老汉想到了自己的年纪,何不就是这落日余晖呢?忙死忙活的,到底能还有几日的活头?那白胖胖的女人,酥麻麻的女人,朝他散发着阵阵香气,多么令他迷醉!他清楚地听到,自己还未老死的心脏,咕咚咕咚狂跳不止,血管里的血液,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周身,他的咽喉,只要他稍微闭上眼睛,他饥渴的嘴巴,就会将这个颤动的女人,撕成八瓣吃掉喝掉!噢噢!那是怎样的酣畅淋漓啊?!可余老汉,却啊呀一声,惊坐起来:
“不能不能!坚决不能!”
“你咋了?”白小手欠起身子拉着他问。
“这事不行,今天不行!”
“能行,能行了。”白小手握着他说。
余老汉一把推过她:
“过下个月了吧!”白小手松了他,骂道:
“你把欠条吃了呀!”
儿子、媳妇和孙子来到果园的时候,余老汉正在地头的小房子门口做早饭。太阳刚刚冒出山头,一缕缕斜斜的金线,将果园和周边山洼都铺连起来,树林里雾茫茫的水汽还在,罩着林中早起鸟儿,欢声啁啾。
余老汉今天要吃什么呢?许久也没买菜了。他在巴掌大的屋里看了看,除了一张单身床,一个铺盖卷,就只有一个蔫黄的灰白菜了。不过墙角还有面。
“吃蒜水揪疙瘩吧?省事。”余老汉自己和自己说着,就挽起袖子,和了面,生了火。他从房子门口挂着的塑料袋里,翻出了一个大蒜头,蹲在路边剥起来。年纪大了,手也懒了,他不愿意将时间花在做饭上,每顿从地里回到小屋中,他就坐下不动了,张嘴打上几个哈欠,就撑不住要躺倒床上睡一觉。临了,啃上一块馒头,再给他那容量巨大的水壶里灌满了水,泡上一撮新茶叶,这顿饭就算将就交代过了。
“爷爷,爷爷……”
隐约的,一声声叫唤,将余老汉从思绪里唤了回来。他又想起他那贤惠的老伴,从前锅台上的事儿,可从不让他沾手哇。
“爷爷,我来啦爷爷!”
余老汉终于看见,他那唯一的小孙子,在他熟悉的黄土小道儿跑来了。余老汉缓缓起了腰,俩眼瓷瓷地盯着那个小小的身影……
“爷爷,你咋不去我家啦?我都想你啦!”小孙子扑通一下跳过来,搂住了余老汉的两条腿,仰着头问他。余老汉突然想起,差不多半年都没离开这个桃林了。
我的宝贝孙子啊,你又长高了哇!快让爷爷抱一抱……余老汉将沾着面痂和蒜皮的手,来回搓了好几搓,又在身上抹了抹,一下就把那可爱的小孙孙举到了他的心头上。
“哎呀!你啥味道,臭死啦!”孙子突然挣扎着喊叫,一把推开了余老汉。
“爸,今天我们工地休息,我带云和孩子来看看你。”儿子和媳妇走过来,手里提着红的白的塑料袋里,疙疙瘩瘩的吃食。
“爸爸爸爸,爷爷身上啥味道,臭死啦!”孙子捏着鼻子给儿子告状。余老汉一阵儿脸红,结结巴巴解释说:
“洗了也没多少时候的……”
“别理他!”儿媳妇走过来说:“爸,这是我俩专门给您割的肉,菜,还有蛋糕,对了,还有刚子给您的茶叶,瞧!这可是好茶,他都舍不得喝呢!”儿媳妇打开袋子,一件件给余老汉展示着:
“我们邻居都夸您儿子孝顺哪!王强他爹一年到头也见不了王强一个肉渣渣,就那,又是给他买房子,又是给他接送娃儿,真让人羡慕呀!”
“哦,爸,上次你让老板捎信说,你的工资借人了,这都一个月了,该还回来了吧?”儿子插过话问。
“爸啊,不是我说您,您干您的活儿就行了,扯那人情干啥?”媳妇又抢着说。
余老汉低着头,听着他们,一语不发。像一条犯了错误的老狗。
“爸,咱再熬上个一年多,车贷还完了,我和云就接你回家住,好好给你养个老。你可要把钱赶紧要回来啊,我着急用呢!”
“嗯,要哩要哩。肯定要哩!”
“爸啊,你要记住,把咱家日子过好才是正事哩。”
“哦,爸知道。”余老汉点着头说:“儿子,你的车呢?我咋没见你的车呢?”
“云说这里风景不错,她要下来走走,我就把车放到路那边了,爸,你等着,我这就去给你开过来!”儿子说着,就大步流星沿路走去。几个月没见,儿子阔气了。
……
“爸啊,那钱您可要抓紧,现在骗子多,目标就是你们这些单身老汉!挣个钱多不容易,您给啥人借走了啊?”余老汉又一阵儿脸红,忙解释说,人家要给的,要给的。
“那就行。爸,我来还想给您说点事儿。”
“啥?”
“咱们原来的那房子平米太小,环境也不好,邻居们一天到晚说话跟吵架似的,咱们皮皮越来越大了,我们想给他换个好点的环境,学学人家孟母三迁嘛!”
“这……”
“爸啊,给您说,我想把咱们那房子卖了,分期再倒换一套大点的,市中心的,明后年车贷就还完了,趁您现在身体还硬朗……不然,以后可咋办呀?就您儿子那本事。”
余老汉听完,松松的眼袋又垂了下来。灰色的眼睛掠过一片无边无际的愁云。可他,转脸却又笑着应承:
“能行,你们换吧,只要人家老板还要我,我就一直干下去。”
“爸!爸,快上车,我拉你走转转去!”儿子开车过来了,对余老汉招手呼唤着。眼前豪华黑亮的小轿车,和坐在车里潇洒的儿子,突然让余老汉有一种陌生。
“爸,快坐上,可舒服哩!”儿媳妇高兴地扶着余老汉的胳膊说。
余老汉慢慢地,有点羞怯的,走到小车跟前,明亮油光的车体上,立马照出了一个瘦长老汉的身影。走近看了,不禁一惊,自己咋就成了这副模样?!稠稠的头发不见了,眼窝深了,满嘴豁牙,胡子拉碴,脸上像裹着一层烤焦了的黄牛皮,皱皱巴巴,唉,不能看了,不能看了哇。余老汉不禁一阵心颤,退后几步,摆摆手说:
“你们回吧,爸改日坐,爸今天脏。”
……
车开走了,儿子带着他的老婆和孩子,卷起一溜儿尘土,回去了属于他们的世界,那样欢乐,那样自然。余老汉一个人站在荒无人烟的大路边,他又想起了他的老伴儿,同时也不自觉地想起了白小手,他多么渴望能再和儿子一样,享受回家的感觉啊,哪怕一次也行。可是,对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一切想法都是荒谬的。眼下,除了维护好继承他血统的儿子,其他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后悔,上月没有扣下白小手的工资,更后悔压根就不该把钱借出去,这下倒好,看着一天栖栖惶惶的女人,怎么开口?怎么开口!可,不管怎样,钱都是必须得要回来的,儿子才是他的责任,白小手和他什么关系!这次,他决不能再心软了!想到这里,余老汉掉头就往桃园南面走去,白小手正在那里给西瓜打药,他必须要告诉她,两天之内,务必把钱还回来!
“手儿,日头大的,你歇歇。”余老汉看着满脸流汗的白小手,一改往日口吻说。
“不累,再有一壶就完了。”
“你歇歇,我要给你说个事……”余老汉见白小手不停,就笑盈盈说:“刚才是我儿子,你见了吗?他来拿钱,没办法,你得……”
白小手停了,扭过脸问:“老余,你是叫我还钱吗?”
“嗯。”
“我一天挣多少你不知道?”
“小手,你听我说,你是真该还我了,上个月儿子都没打车贷,再不还,人来就把他车开走了!”余老汉靠近一步哀求似的说。
“我没钱,这几个月家里这事那事多,叫我拿啥给你哩?”
“你先少给点,慢慢给,我知道你供俩娃上学不容易。没见,上个月都没有扣下你的。”
“他年纪轻轻,小车开着,老婆搂着,不害臊你六七十了给他养着?”
“小手啊,我得往人家手里死哩,你别让我为难哇!”
白小手从背上卸下了喷雾器,咣当扔到地上,说:“说这话,有钱我能借你的?”
“你先少给点,慢慢给。我儿子指望这钱哩。”余老汉又说。
“老余,你是非要我说出个什么吗?没有就是没有!我一个女人家,你可别把我逼下个心梗!”白小手突然哎哟哎哟叫起来,捂着胸口离开了。
后来几天,白小手都没到果园上工,也没有任何消息。余老汉越想越窝囊,凭什么?凭什么借钱的时候,你是个人,要钱时就成了鬼?!还拿心梗吓唬人!我老汉帮你就是人情了,你难道还要讹我不成?将近五千块钱哩,可不是个小数。余老汉懊恼万分,他后悔极了,不该沾惹这个女人,可他到底也没怎么她呀,幸亏没怎么,不然可真是……幸好,幸好有欠条,幸好白小手上次说过,她的娘家哥哥,要给她一笔搬迁的补贴费,余老汉觉得逼紧点,这钱应该能要下。只是,怎么个要法呢?余老汉思忖起来,看她那个样,这女人怕是软的不行,看来只有硬的了!可,总不能打她一顿吧?再说,打了再被她告下,可真会讹上哇。要不行,真不行,就痛痛快快睡了她,放个响屁?呸呸呸,余老汉为他突然冒出的想法感到耻辱。五千块,睡她?呸呸呸!余老汉怎么也想不出个办法,突然,他想到白小手扔在地上的农药,对了,对了,就这么办!
第二天一早,余老汉就气冲冲地寻到白小手家里,进门,一条黄狗爬在墙角,余老汉一惊,那狗却一动不动,甚至对他摇尾巴,余老汉便跺响了脚步跨进门槛。屋里悄悄地,几样破旧的老家具,死气沉沉地依着泥土斑驳的墙壁,这三间老式的泥瓦房,让余老汉瞬间高大起来。他左右环顾,药味儿弥漫的空气中,除了几只豆黑的苍蝇飘浮,没有任何响动。
“谁呀……”一个微弱带着沙哑的声音,从另一侧屋里传来,余老汉耳根一转,几步就跨到那人跟前,抬手“咚”的一声,将一个瓶子,狠狠地墩在躺着的白小手面前。白小手好像病了,蔫蔫地躺着,通红如血的眼睛,看了看余老汉,又看了看写着“敌敌畏”的瓶子,苦笑着问:
“你这是来逼账的啊?”
“白纸黑字你看清楚,一分都不能少!”
余老汉大声叫嚷着,哗啦一下,又掏出了白小手之前写下的欠条,决绝地扬在她的面前。白小手吃力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想要伸手去接住,可余老汉却又闪了回去,戳着门外恨喝着:
“不给咱就上法院!弄急了我死你门上哩!”白小手愣了,看着往日还算仁义的包工叔,傻了。她俩眼一动不动地盯着余老汉,嘴角抽搐了几下,咬着牙说:“钱是没有!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死了,心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