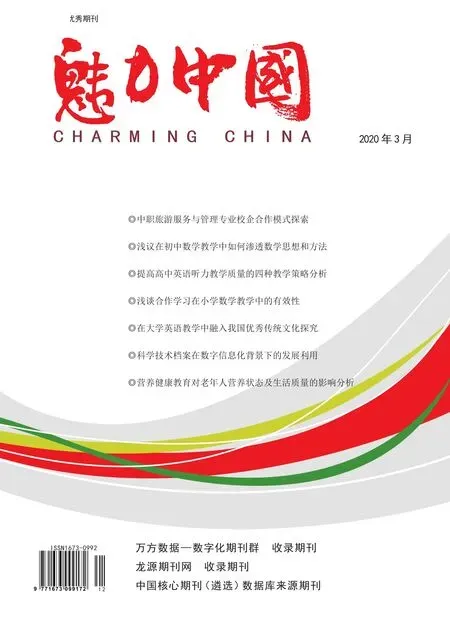论晚明叹世散曲的修辞运用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四川 德阳 618000)
明代晚期,由于政治上内阁擅权和朋党纷争导致朝纲松弛,加之商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贪腐之风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同时,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受到极大冲击,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使得人们主体意识逐渐觉醒,这虽然有利于人性解放,但是却也直接导致世风败坏,社会失去了道德规范和纲常法度。明代晚期一批抱有传统入世理想的文人有感于当时的世道与人心,创作出了大量叹世题材的散曲,这类散曲不仅蕴含丰富,有着较高的思想价值,而且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对比、比喻、用典、反语等修辞手法的大量运用,使得散曲语言具有高度概括性,同时也不乏灵动诙谐、发人深省的艺术特点。
一、对比
对比这一修辞手法在晚明叹世散曲作品中极为常见,曲家们通常以对仗的方式,将具有矛盾关系的事物或要素放置在一个完整而统一的表达体系中,从而使之形成鲜明对照以增强其艺术效果。
对比在叹世散曲中运用广泛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类散曲所要描摹的世情百态纷繁杂芜,如果一一赘述,必将有损其审美价值,这一修辞手法将极端对立的两个方面呈现出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寥寥数语就可使读者领会作者言语之外的深意。比如朱载堉在【南商调·黄莺儿】《求人难》中摹写当时世态“锦上花争先添补,雪里炭谁肯送去”[1]2981。“锦”和“雪”分别代表一达一穷两种极致且截然相反的人生状态,世人对达着竞相追捧,对穷者冷眼相待,那么在介于“达”和“穷”这两者中间地带的处世原则,也可想而知了。曲家薛论道在【双调·沉醉东风】《题钱》中刻画出在拜金主义盛行于世的晚明,金钱对人心的异化程度,这组散曲全篇都通过对比手法构建,全面而形象地表现出富者的得意之姿和贫者的落魄之态,比如有钱时可以享受肥羊美酒、缓带轻裘,没钱时就只能赤身露体、忍饿耽饥;有钱时说话眉扬气吐,胆大心粗,没钱时只能箝舌闭口、爽背缩头……将有钱时的显贵通达之态和没钱时的困顿窘迫之况这两种极端的状态进行对比,不必穷形尽相,便能使晚明社会中被金钱欲望操控的人性丑态毕现。
生活的贫与富、命运的穷与通、人心的善与恶、世态的炎与凉,以及传统士人的节操意识与极具诱惑力的现实利益这些矛盾事物都统一在晚明纷繁杂芜的社会现实中,而在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摹写和抒发时,运用对比手法,通过形成鲜明的反差,从而为作品内容营造出一种巨大的落差感。如薛岡【双调·玉江引】《警世》中的“谈笑情高,机关百样巧。礼貌虚嚣,心肠百样狡” [1]2953,表面和内心形成强烈反差,将社交场上人们的口蜜腹剑一笔道尽。再如薛论道在【南仙吕入双调·朝元歌】《世味》中写道:“忠肝义肝,颠倒生忧患。神奸巨奸,到处多称赞。”[1]2841忠义之士和奸佞小人是官场之上最具反差的两类人,忠义之士本该受到世人崇敬和景仰,奸佞小人本该藏头缩尾不得见光,但是由于当时皇帝的不作为,导致宦官专权,奸佞当道,忠肝义胆之士被倾轧排挤,甚至有杀身之祸,所以总是活在极度的忧患中,而奸猾之辈却可以在这污浊的社会环境中混得如鱼得水,薛论道用对比的手法将这黑白颠倒、贤愚不辨的官场现形记刻画得入木三分,令人读之着实意难平。
二、比喻
晚明的曲家们也常常通过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对所叹对象的特征进行描绘渲染,使其具体可感,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比喻主要分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种。明喻的例子如王锡爵在【双调·对玉环带清江引】《和唐六如叹世词》中觉悟命运穷通人生沉浮皆是上天安排时发出的无奈感慨:“智似灵龟,何尝脱死期;巧似蜘蛛,何尝不忍饥。”[1]2908作者将睿智聪慧的人比作灵龟,但就算寿比灵龟,最终还是有形神俱灭的一天;将擅于钻营的伶俐之徒比作蜘蛛,但即使如蜘蛛般灵巧机敏,也难免有机关失算忍饥挨饿的时刻。暗喻的例子如薛岡在【双调·玉江引】《警世》中写道的:“仕路蹊跷,连云栈一遭。人世浮薄,乌金纸一条。” [1]2953作者将仕途之路比作连云栈,可见官场之险恶,将人情世态比作乌金纸,可见人心之凉薄。
晚明叹世散曲中常见的比喻类型是借喻,借喻以喻体代替本体,本体和喻词都不出现,这样就使语言简洁明快的同时,也具有深厚含蓄的表达效果。如胡文焕的【南仙吕·桂枝香】《叹世》中讽刺世人虚伪的句子:“樽俎中暗伏干戈,唇舌间滥加褒贬”[1]2921,通过借喻的手法,将社交场形容得如战场一般,觥筹交错间的言语措辞可以伤人于无形,所以作者将其比作“暗伏”的“干戈”。再如薛论道在【中吕·朝天子】《不平》中抒发“得意鸱鸮,失时鸾凤,大家捱胡撕弄” [1]2723的感慨,也运用了借喻的修辞手法,“鸱鸮”最早见于《诗经》,从“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 [2]227一句中就可以看出此鸟之恶,后薛论道也以“鸱鸮”为题写过一支小令:“青天不举夜纵横,鬼魅行来到处凶,声音笑貌惊鸾凤。又何曾识大鹏?恶名儿无类相从,万物中君独怪,百鸟丛尔最凶,无怪乎世不相容。” [1]2756欺凌弱小,刁悍蛮横,青天白日之下藏头缩尾,夜半更深时分凶煞纵横,这不仅是鸱鸮的行为特点,更是当时社会上那些势利小人们所共有的处世特征。“得意鸱鸮,失时鸾凤”两句借喻,吐尽作者对于鄙陋猥琐之辈窃居高位、得志猖狂,而清廉高洁之士却屡屡碰壁、命途多蹇的愤懑不平之气。
三、用典
用典即援引前人的事迹或语言,来表达观点或者抒发感情。当晚明曲家们对眼下的生存现状感到茫然无措又找不到精神出路时,探寻的视角就会不自觉地在历史的轮轴上往前回溯,这样也不可避免地会在前人的过往经验中遇见与自己感受相契合的人生体验,所以当他们在创作叹世题材的散曲时,大量用典,借前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例如薛论道【南仙吕入双调·朝元歌】《叹世》中“气死周郎,忙杀梁父,都自把春秋虚度”[1]2820,借用《三国志》中周瑜之事和汉唐乐府《梁父吟》的典故说明仕途误人,名缰利锁对人的羁绊之深,不如随心所欲,受用些当下的良辰美景。再如薛论道在【双调·水仙子】《成败》中感慨功名地位等世俗价值的虚无性时,写道“楚霸王千钧力,苏季子三寸舌,到头来谁是豪杰?”“楚亚父千条计,汉淮阴十大功,到头来谁是英雄?”“叹李斯谋猷壮,咲晁错智量高,到头来谁是英豪?” [1]2750楚霸王曾叱咤风云,后来却兵败自刎;苏季子曾六国封相,后来却被车裂于市。范增、韩信、李斯和晁错等人曾经都位高权重,但最终都没有逃过落魄而亡或身死族灭的下场。通过用典,让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否泰循环不可把握,宦海仕途沉浮不定,不必为了注定会灰飞烟灭的俗世功名而营营役役。
散曲作家们借古抒怀,让自己表达的观点更富有说服力,而由于典故本身所暗藏的历史经验和情感能量,可使曲家创作时既保持内容的充实和蕴藉的深厚,又减少言辞之累赘,达到辞约旨丰的效果。如王克笃在【中吕·红绣鞋】《阅世》中写道:“几曾见十全到底?那里有不散筵席?鹤长凫短不能齐。” [1]2446鹤长凫短语出《庄子·骈拇》:“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3]88王克笃借典故之义说明事物各有特点,人生在世亦不可强求十全十美。再如朱载堉在【南商调·山坡羊】《交情可叹》中唏嘘朋友之间尽是虚情假套的可悲事实时写道:“如今人那有刘备关张,也没有雷陈管鲍。”[1]2979春秋时期的管仲和鲍叔牙,汉朝的雷义与陈重,以及东汉末年刘备、关羽、张飞三个异性兄弟,皆因其情深义重而成为千古美谈,朱载堉意在表达对当时社会人情冷漠、人心不古的悲哀,运用典故,不仅使语言凝练干脆,同时也使作品中蕴含今昔对比之意,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传统的精神美德正逐渐消解在商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晚明社会中。
除此之外,晚明叹世散曲中还涉及夸张、互文等诸多修辞手法,如王克笃【中吕·红绣鞋】《阅世》“急煎煎油锅插手,恶狠狠钱眼翻身” [1]2446运用夸张的手法传神地摹绘出当时世人见钱眼开的种种丑态。王锡爵【双调·对玉环带清江引】《和唐六如叹世词》的“拜将封侯,是英雄钓钩;按簿持筹,是愚夫枷杻” [1]2908运用互文的方式发出感叹:不管对于豪杰英雄还是凡夫俗子,功名地位的诱惑背后都是暗藏机关的陷阱。通过对于这些修辞表达的研究和解读,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去领会晚明叹世散曲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以及作者隐藏于字里行间的情感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