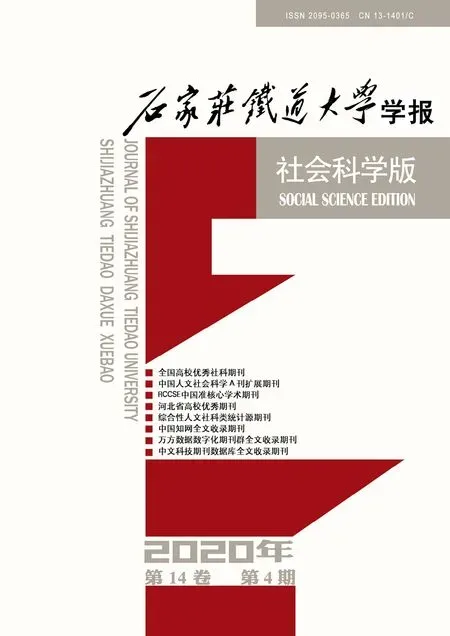天人之际:董仲舒德道思想的生成境域
白立强, 张 铭
(衡水学院 董子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
汉代初期,虽然黄老之学一度被奉为圭臬,但最终儒家文化因符合统治阶级的治理需求而被“定于一尊”,从而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而被普遍认同[1]。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针对汉武帝提出的“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对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汉书·董仲舒传》)在此,董子将汉武帝关注的“大道之要”“至论之极”锁定在“天人相与之际”层面,即人君治理国家的方式、水准绝非单极性向度,就本质而言,其情状终将与天发生内在关联,此旨在使人君“强勉行道”,以达至“进德修业”之目的。
思想预期与社会现实总存在距离。具体到历史进程中的“社会思想”[2]141而言,“‘汉承秦制’的制度设计与‘独尊儒术’的经典认同”始终以“儒表”与“法里”的矛盾存在着反差[2]144,但鉴于汉武帝之于现实社会的终极关切,董子依然将之引入到上达天道的形上场域之中,从而型构了人与天(基于现实又不止于现实的整体复合域)之际互通的一体谱式,二者相互关涉、涵容。一则天涵摄人,“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以下只注篇名))二则人映射天,“人受命乎天也”,“唯人独能偶天地”(《人副天数》)。天人在双向涵容与互动过程中渐进于德道。“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深察名号》)由是,天人在“际与”之中搭建起了“通理”“相益”的动感模式,也自然启动了天人大化的“德道”生成境域。
一、天、天人之际基本内涵
董仲舒哲学是“天的哲学”[3]304。其天人关系“把有形与无形”在客观上连结起来,此中不再具有“知识的意义”[3]365,这似乎回到“古代宗教的人格神”[3]370。故有学人将董子思想归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哲学体系”[4]“神学经学哲学”[5]94“神学的唯心论”[5]128“中世纪神学的正宗思想”[6]84等。然而,从中国文化史来看,“天人关系是先秦以来人们所普遍关注的根本问题”,“孔子也试图沟通天与人之间的关系”[7],“然只是引而不发”[8]。因此,虽然今人对天人关系以神学、唯心而视之,但在初民时代,天人关系完全是“真问题”“元问题”[9]。甚至可以断言,“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
故天人关系成为大到国家关注重视、小到个人安身立命的文化情结,甚至构成了标识文化源流的基本尺度。如有学者认为,天在中国文化中就是“绝对者”,“对‘绝对者’的觉悟”是一种文化“成为本原性文化的标志性事件”[10]。由此看来,华夏自古以来对天的聚焦本身就折射着“源发性”之文化意蕴。“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汉书·董仲舒传》),天乃人生存发展的首要场域。就理论层面而言,天即无所不包的一切存在,涵摄了时空、性情、品格等多重向度。出于研究需要,多有学者对董子之天进行了明确性类别划分。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同时也极易因其过于具体而导致简单化、狭隘化其内涵。就其实质而言,天乃多重复合型范畴,虽然包含诸多方面,但各个方面之间并非具有明确的边界,而是相互涵摄、补充、内在交融于一体——包含此向度但非仅仅限于此向度,既表现为某种程度上的具象性,更意味着抽象性、广延性以及无限性;既是人之外世界(如果可以如此断言),更体现为与人相关联、乃至内化于心、升华为“信念”及其所赋予的价值与意义世界。总之,天是物质、精神、信息以及能量等诸多向度的复杂复合叠加与统一。尽管自近代以来,学者通常罗列出“天”或“道”的多重面向,并据此论证随着“人文觉醒”,“去神化乃至无神化”成为趋势。但在先秦人文意界中,“天的多重含义恰恰是被用来申述天的绝对性的不同环节:不管是义理之天,还是命运之天、自然之天,甚至所谓物质之天(如果有的话),都可被归到作为神圣绝对者的‘上天’之下,绝对之天据此获得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因此,在这里的天并不因被分解、分层而失去了绝对性与统一性,倒是因获得了更丰富的统一性而获得了更生动与具体的绝对性。”[10]故任何将天以确定性分层、分解都不能无视天的整体性、人文性与至上性。这同时表征着不应将天“过于对象化”[11]109,而应予以“非物质实体性”[11]70的理解。换言之,天是形下与形上的统一、时间与空间的统一。就一般意义而言,天乃“以一切存在之共同构成而表现此世界之意义与价值者”[12]45,“凡属存在皆是天”[12]44。“天者,百神之大君也”(《郊语》),此即天之“好生之德”(《尚书·大禹谟》),以其生生不息之机而为“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顺命》)天作为万事物相之源出,构成了传统哲学的本体,一切均可以在天的框架下得到说明,从而成为传统文化基本范式。
“中国古人所谓万物一体”,“此一体,中国古人亦谓之天。”[12]45但尤为不可忽视的是,“天也,人也,物也,性也,诚也,神也,其实皆一也。其机括则只在于一己之自尽而成。”[12]34天、地、人、物乃至“神”等因人之诚而融为一体,即“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朱子注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13]31在天人关系方面,董子于人以十足的良善体认,“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玉杯》)。人与生俱来承载着上天之“善善恶恶”之性,故以“诚之者”趋向天道,由此搭建了天人之际与的可能性。
唯有首肯天人之诚,“始可进而言中国思想之所谓天人合一。”[12]44在“诚”之性能下,人道即天道,人天之间自然消弭了界域与分际而成为“天因人而彰,人因天而成”的统一体。再者,“仁者,人也”(《中庸》),“仁”作为人之正“名”,“取之天地”,“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深察名号》)。为此,人之“诚”绝非出于人性好恶而产生的道德期许,而是与天俱来的人之质性。性者,“无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天质之朴也”(《实性》)。这是人天之合的先天基础。在此意义上,天人于交互态势中生成着“天因人而灵动,人以天而荣光”的自然暗合。由是形成了天人之际与的现实性。
在中国文化之中,一则“人资诸天”(《王道通三》),天是人世生活的“真正凭依”[14]导言2;二则天地之宇宙论又“建本于人生论”[12]40。由此观之,“天人相与之际”是隐寓人心中潜在的思维定势。“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天人因同类而“相应相求”,结为一体。这意味着,天人之际与实为在彼此互通共在过程中建构起人天互鉴涵容之境域,亦天亦人、即天即人。《王道通三》:“天,仁也。”“仁者,与物贯通而无间者也。”(《慎言·作圣篇》)又“‘仁’为生意,故有相通、相贯”(《东西均·译诸名》)之义。天人无间,即“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为人者天》)天是人生存之根据,故天人同构成为传统文化基本特征,而天人合一乃至相应则是天人际与的典型表达。这正是传统文化作为“最高凝聚”与“主体设计者”[15]的思维方式,有学者认为,如果冠之于当下广为认同的科学称谓,此则为“物性儒学(复杂科学)”[16]前言1“构造整合法”[16]7的鲜明体现。
2500多年前,孔子以“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汉书·董仲舒传》)洞察、隐寓了天人之际与关系,董子承继孔子之文进而以阴阳五行具体建构了天人一体图式。人身小天地,天地大人身。“天人相通”在董子哲学中成为“完整的宇宙论系统”[17],并被“开放性超巨复杂系统理论”[18]所证明。从现代科学来看,人作为“生物个体,无疑具有和整个宇宙相同程度的广延性”[19]12,这意味着,人之个体承载着整个宇宙的信息。就理论而言,人之生存空间(天)既是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也成为人之本身。其中存在密切相关性,《立元神》有言:“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为此,“所谓某一生物的环境就不仅是包含着整个宇宙,而且对这个生物本身来说,也成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总之,虽然生命体及其所在环境在表象上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事物,但实际上是“融合为不可分的一体”[19]12。
二、天人际与境域下的德道生成进路
何谓道?就其本源而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就其内涵而言,“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汉书·董仲舒传》)。道之根本在于天,天以其自在性蕴含着道体法则。如此判断并非意味着天道之外另有人道,相反,天道以其先在性必然隐寓着人道。故“圣人视天而行”(《天容》)“人理之副天道”(《王道通三》)“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天地之行》),“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阴阳义》)等。“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汉书·董仲舒传》),此人道即天道,“人道者,人之所由,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天道施》)之所以“乐不乱、复不厌”者,乃“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王道通三》)。由是,道因人而彰,人藉天而成。在人天境域之中,道彰而德成,“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深察名号》)“德道犹道德。”[20]
由道则有德。“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13]53天道流行,自蕴其德,故曰“德在天地”(《正贯》)“其德昭明”(《观德》)。“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人副天数》)天地昭明,其德性之光大更因人而显卓。“天地与人,三而成德”,“天之大经也”(《官制像天》)。人以其之德义在与天地同律中成天之德、助地之化。就表层而言,天地人似以其各自分途而示现其德,实际上,人之德义可贵之处就在于以通天贯地中正之为而成天地之文。此中,天人因通而律动,因律动而德道成,“万物动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道也。”(《天道施》)天地人同脉共振、浃洽涵泳,“化天理而义”而成“人之德行”(《为人者天》),此之谓德道。
就理论而言,天地就是无形之气及其有形界域的诸相体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易经·系辞传》)。气、阴阳之气既是天人际与的交互作用媒介,也是能量信息,毋宁说天地人本是阴阳之气聚合、运化的动态过程集合体。无论有形抑或无形,显性还是隐性,一切皆在阴阳之中。“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其澹澹也。然则人之居天地之间,其犹鱼之离水,一也,其无间。”“是天地之间,若虚而实,人常渐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殽也。故人气调和,而天地之化美,殽于恶而味败,此易之物也。”(《天地阴阳》)尊道或背道则天地应之以“化美”或“味败”。王者与天地相参,其行迹信息与天地通过阴阳之气感而遂通,治乱必以正邪而应。“人主之大,天地之参也”,“荡四海之内,殽阴阳之气,与天地相杂”,“治则以正气殽天地之化,乱则以邪气殽天地之化,同者相益,异者相损之数也,无可疑者矣。”(《天地阴阳》)为此,王者之治同道,则与天而相益,背道而相损,“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汉书·董仲舒传》)天人因阴阳之气而搭建起“际与”之路径,展演着德道之成失。
德道生成于天人相与之际,似与天俱来带有鲜明的形而上色彩。实际上,天人始终根植于现实社会之中。相对而言,天人之际构成了天人关系的抽象逻辑,现实社会中的人间秩序则为天人关系的具象呈现:无论“屈民而伸君”(《玉杯》),还是“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在民、君与王之后均潜隐着天的情结。王者之治“奉天而法古”(《楚庄王》),承天德为正理,自是入道臻德之化境。“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为政之理”(《威德所生》),“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正者,王之所为也。”王者“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汉书·董仲舒传》)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喜怒之发,威德之处,无不皆中其应,可以参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时已。故曰圣人配天。”(《威德所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四时之副》)王者以上奉天道,下应民意之行思察微知著、谨始慎终,“奉本”以省“二端”,“观德”以立“度制”,从而在与天本的观照中于现实社会应现着上苍元道、演化着人间至德。
天地德道最终体现为仁义礼乐、人伦秩序。天以人显,道以器彰。所谓“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汉书·董仲舒传》)道乃王者治理之进路,践履王道具体方式则须凭依制度规范与德性教化。历史昭示:圣王虽去,而治世为继数百岁者,皆礼乐教化之效。是故为人君者欲求善治之道,择《诗》《书》《礼》《乐》等六艺培养人的德性,以“遂人道之极”(《玉杯》)而涵养天道德风。正所谓“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汉书·董仲舒传》)本立而道生,故上达天之为人性命之正,行仁义而羞可耻,即“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汉书·董仲舒传》)如是,道通天地、德寓人君,大化流行、道深德盛,天人在际与、映照之中以天道化人道、以人道立天道,在现实人伦秩序中再现天地德道之意蕴。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五行相生》)。天地人通过阴阳气化往来交互,儒家视之为“不息不已,至诚实有”“至神”。天地运化、至诚无息,生生不息、变化莫测,“诚与神,皆天地大化之所以为化,亦即此大化所具有之德性。”[12]30由此言之,董子天人之际与因阴阳之气即“至诚至神之德性”而成就人生与宇宙融成一体——天人合德。天人囿于共在同一宇宙信息系统之中,故内含着同样的能量密码,此即由道而入德。天地大化“本具同一之德性。此种德性,直上直下,即体即用,弥纶天地,融通物我,贯彻死生。”鉴于此,董子之整体宇宙观即“德性一元或性能一元之宇宙观”[12]31。董子之所以特别强调“元年春,王正月”,盖本于此。
三、德道意蕴中的自由隐寓
“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汉书·董仲舒传》)天成为芸芸众生潜在心理支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无绝人之路”“皇天不负有心人”“天道酬勤”等,一切都可以藉天以通理、从事以达道。“惟德动天”(《尚书·皋陶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尚书·秦誓中》)、“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等均体现了远古先民的尚天观念。
有学人认为,董子之天人际与观就是从天的角度对专制君主的限制。董仲舒通过“君权神授而要求人主知天法天,把人主的行为纳入他所主张的与天道相配合的君道之中”[21],借“虚构中的天的力量”,“用灾异恐吓皇帝,要求他反省自己的错误。”[22]无疑这“有助于人君改善政治,起到见微知著的作用,用以检讨朝政,避免酿成祸患。”[23]可以说,“在君权至上的条件下,处于权力边缘的思想家常常只有借助于超验的神化力量才能实现对现实政治的干预。”[24]而有学者甚至认为,董仲舒的神学把政治“涂上了上帝的油彩”,成为皇权的“最高护符”,“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存在在绝对皇权那里都是合法的”[6]102。“以神权作为政权的助手”[25]“略以助政”(《论衡·卜筮》),“效仿天道甚或寻求与天道的统一”是董仲舒“宗教理论的基础”[26]。周桂钿曾分析古今学者对董仲舒天人际与说所持态度[27]。概而言之,多是从术的层面予以肯定。当然也有观点在肯定其策略性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其深层意义,即“假天道进谏”,陈“祥异之占”[28],以此匡正君主。然随技术兴起,日食、星变皆可预测,故灾异论遂成牵强附会。但“《春秋》所书日食、星变,岂无意乎?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不得以今人之所见轻议古人也。”[29]
在技术决定论者眼里,物质世界唯有技术主导一切,而技术一旦冠之以科学,即假使“以科学为唯一标准的泛科学主义”盛行[30]15,则其他自然归入非科学甚至荒诞谬误之域。方东美认为,仅仅从物质机械系统看待宇宙并将其视为人生整体环境,属于“科学齐物论”,这极易导致科学技术对宇宙系统的裁剪与割裂,进而产生“科学的自然理性与宗教的神圣理性”的分离、“自然界与超自然界”隔绝以及“知识与价值”的分裂[31]。
学界对于董子天人际与思想之所以仁智并见,焦点主要集中在其思想是否属于或折射着宗教意蕴。鉴于此,董子成为“思想史上很难处理的一位大思想家”[3]271。
实际上,就文化人类学而言,人作为独特的精神生命现象,始终趋向于通过无限性追求以不断超越自身有限性存在。为此,无论传统还是现代,人类文明的存在皆为宗教性存在,无论基督教还是儒家,均为宗教性的人文教化系统。[32]董子天人之际与亦然。但不可无视的是,宗教、形而上学均基于道德[30]68董子思想在“天人之际”境域下开显,天人之间在交互际与的感应程式中恒久共在与互现,言天必及人,道人亦涉天。“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篇》)董子“天学的指归在于人”[14]导言5,“天的人伦性或与人事政治相关性”,是“董仲舒‘天学’的核心”[33]。故董子之天论始终不离对现实社会的关照,而在对现实社会的审视中又“本天元命”(《玉英》),追溯着天元本体,故“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汉书·董仲舒传》)。“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春秋繁露·玉英》)徐彦疏:“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34]10
“唯天为大”(《论语·泰伯》)是中国文化基本色调。天因其超越了具象世界而成为至上性的“德道”存在,由此自然具有了中、正、和之天道品格。
董子《天人三策》以“天人际与”起,以“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之“大一统”终(《汉书·董仲舒传》)。这意味着,虽然董子“对策”是以解答刘氏“家天下”之问,但其治道取向依然锁定在“‘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3]270之上。“一统乎天子”“随天之终始”(《符瑞》)与“一统于天下”“作科以奉天地”成为董子思想一以贯之的为政主张——“大一统”,“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疏曰:“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34]10“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者,王之所为也。”“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王道自是而“极理以尽情性之宜,则天容遂矣。”(《符瑞》)董子将王道之端归于天,其目的在于以天道匡正人道、以人道效法天道,从而达至以天和导引人和之社会格局。
牟宗三认为研究历史起码两个标准:一个是历史判断,一个是道德判断。[30]12董子“天人之际”既是汉代治理制度理念设计的端点,又以“上揆天道”的方式折射着对现实治理模式的超越,天、道、天道等所承载的德道意蕴型塑了董子思想的基本底色。实际上,“天人之际”正是在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中探索着通向“秩序自由”的人文之路,大一统主导下的王道思想即是明证。所谓“秩序自由”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与规范的设计为人提供具体可行的行为标准和价值尺度,以在秩序框架下实现生命活动自由。秩序自由是建立在规制之上的,社会规则是保证自由实现的前提。之所以如此断言,正如辜鸿铭所言:“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循规蹈矩”[35]5。就此而言,中国自2500年前即通过礼乐制度的设计以追求“自由主义”的精神表达了“现代精神的觉醒”[35]31。
孔子以“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演说映射着对现实世界之上的“宇宙的神圣秩序”的领悟[35]44,董子继往开来,将阴阳五行与天地人纳入到一个整体的宇宙图式之中,建构起天人一体的宇宙秩序格局,而“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30]73。就道德之原初意义而言,绝非对人的约束,而是“开放人”“成全人”[30]70。劳思光认为,相对于西方文化重智,中国学问“自始就重德”[30]191,并且,中国文化以“圆教的形态”实现着生命的超越与内在的“通而为一”[30]202。董子既肯定了天之于人的根本性,同时又强调了人的主导性,“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汉书·董仲舒传》)天人“互相影响,互相决定”,“天人居于平等的地位”[3]370,从而“将人提升到天的高度,以天的神圣性来强调人的神圣性,是对天地人三才并立,以人为主体的深入论证。”[36]因此,董子天人关系依然映射着“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30]54之蕴涵。
“为生不能为人”,“人之为人本于天”,故“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为人者天》)。人本为存在与价值的双重统一,人之生命须在对天的守护中,才能回归到生命的价值系统或道体境界之中。一定意义上,对人生价值、生命之道的把握即是从天的高度对人当下存在的精神导引,这种导引正是以天道律令的精神方式植入人的内在观念甚至信仰层面,从而使其具有鲜明的实践精神。并且,天人因通仁而强化了实践基调。“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惟人道可以参天”(《王道通三》)。天人之际与同时生成着人天之相参,故人、天共通以仁。由是,仁德在人天互渗、相彰的程式中渐次敞开,实现着自天而人的缔造与化生。当然,仁德虽为“道德理性的观念”,但依然表现为生动的“实践”品格,因为德性观念只有与“生命问题”发生关联时才出现[30]。所以,“‘形上’之思与‘形下’之域”[37]在实践进路中使人于回归天道本体世界的过程中得以产生双重影响:于整体社会而言,型构着现实社会秩序;于个体自身而言,实现着个人的生命自由。
在张世英看来,从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个哲学问题角度而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既包含又超越“主客关系”[38]。这对应于原创马克思主义“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之“人的自由个性”阶段[39]。在此界域中,人为天地之心,人道即天道,故天道不是高高在上、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是人的主体活动的自然表达。而从文化角度而言,董子天人之际思想就是以对天道这个“绝对”世界的深层领悟而完成与天道的共在与统一,之所以如此,这“在本质上都植根于人类最深邃的自由本性”[10]。而圣者“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即由“天”追溯到“元”的层次,“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这就相当于启动了宇宙奇点,从而打开了一个“把过去、现在与未来作为可能性包含在自身之中的超越性视野”,也促成了“从整体的角度理解、追问自己与世界的存在,并因而进入了与“整体”共在”的宇宙谱系之中[10]。而此正是实现主体自由的必由之路。
四、结语
总之,董子以天人之际的宏观宇宙境域将人提升至天的形上世界,从而在理论上建构了“人类理性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通达自由境界的最高理想”[40],同时,又凭藉相应的“度制”重塑天道信仰、规范人伦秩序,以深切的人文情怀与朴素的天人框架隐寓了实现秩序自由的价值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