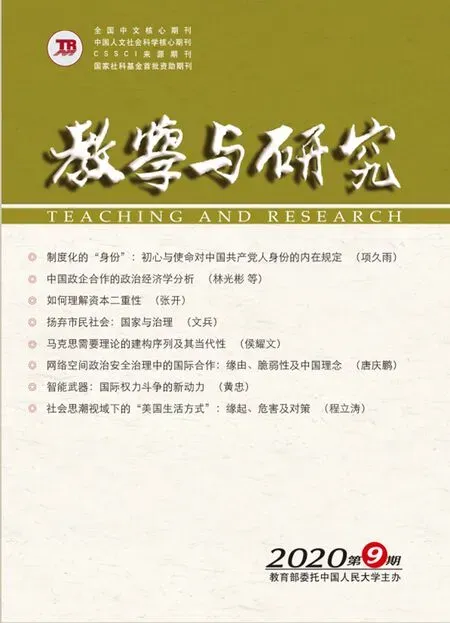如何理解资本二重性
——兼论新型政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张 开
一、关于“资本提法”的历史回顾和新定位
改革开放,是以我国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总的历史方位,并以所有制结构关系重构、资本化改革为主要内容。以“资本范畴”为切入点,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相关重要文件,我们可以总结如下重要提法的演进历程。
最初,在1993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一九九三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最早使用“国有资本金”这个提法:“通过界定产权,理顺企业的财产归属关系,核定企业的国有资本金,明确企业或控股公司作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应承担的资产责任,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的有效实现形式。”(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2、18-19页。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开始使用“公有资本”提法,而且主张“公有制实现形式”应该多样化发展:“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2、18-19页。在这里,明显是把“股份制”当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来使用的。在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使用了“国有资本”提法:“国有资本通过股份制可以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3)《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1999年9月27日。这里已经涉及两种资本形式,“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4)张开、崔晓雪、顾梦佳:《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3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这样一段文字:“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所有制结构来讲,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其重要实现形式,三大资本形式及其之间的结构关系则是混合所有制的本质内容。201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首次提出“新型政商关系”,并强调:“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6)《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3月5日。这是对非公资本提出的新要求。
综合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其主要内容则是各类资本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各类资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及其结构进行研究。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亲”和“清”新型政商关系,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命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命题。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含义,在于如何从理论上理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资本,如何从实践上更好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然而,国内理论界的现有研究,绝大多数是从政治学、社会学、统战工作、反腐倡廉、纪检监察、转变政府职能等视角进行研究,(7)例如,邓凌:《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症结与出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8期;杨卫敏:《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探析》,《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郑善文:《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若干问题研究》,《理论研究》2018年第5期;孙丽丽:《关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思考》,《经济问题》2016年第2期;杨典:《政商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等等。很少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理论研究和说明。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亲”和“清”新型政商关系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文总结和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劳动二重性”,重新界定“资本二重性”,尝试分析“资本二重性内在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努力给新型政商关系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或分析框架。
二、劳动二重性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出版后,马克思非常关注外界对这本著作的评价,他认为有“三个崭新因素”并没有引起足够的理论关注。1868年1月,马克思致信恩格斯:一是,“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做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6-467、467、467页。二是,“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6-467、467、467页。三是,“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6-467、467、467页。正是基于这“三个崭新因素”,使《资本论》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中,劳动二重性起着基础性、枢纽性地位和作用,这也是我们理解资本二重性的前提。
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马克思给出了两处经典文字:“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60、207、208、209、215、218、227、228页。以及,“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60、207、208、209、215、218、227、228页。
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如何贯穿始终的呢?
一个方面,“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60、207、208、209、215、218、227、228页。“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60、207、208、209、215、218、227、228页。“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60、207、208、209、215、218、227、228页。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统称为生产资料,劳动表现为生产劳动;然而,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得出的生产劳动定义,用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或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是“能力不足”的。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60、207、208、209、215、218、227、228页。一定意义上,劳动过程,更多强调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舍掉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过程,既包括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劳动过程,是抽象掉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生产过程;生产过程,是考虑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劳动过程。
另一个方面,劳动过程转化为商品生产过程,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马克思指出:“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60、207、208、209、215、218、227、228页。把商品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劳动过程的实质在于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60、207、208、209、215、218、227、228页。在价值形成过程中,上述这个“同一劳动过程只是表现出它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只是劳动操作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只是劳动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时间长度。”(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60、207、208、209、215、218、227、228页。由此可见,劳动具有二重性,商品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都具有二重性:首先,是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体现为生产过程本身;其次,是受交换价值或剩余价值控制的生产过程,体现为商品生产过程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于:“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9-230、384、385、417、421、422、493、690页。
资本主义管理也具有二重性。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9-230、384、385、417、421、422、493、690页。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9-230、384、385、417、421、422、493、690页。不能把由劳动过程的协作特性产生的管理职能(协作职能),和由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特性所产生的管理职能(榨取职能)混为一谈;后一重管理的目的,是为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
对于劳动过程逐渐隶属于资本、接受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控制,马克思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历史上依次呈现的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种形式,这也是劳动过程或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一方面有力推动了劳动过程的社会化结合程度,另一方面这些形式表现为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方法。相比简单协作,马克思指出工场手工业对工人的改造:“简单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彻底地发生了革命,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9-230、384、385、417、421、422、493、690页。一旦工场手工业“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9-230、384、385、417、421、422、493、690页。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一方面“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它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方法,“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并且“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9-230、384、385、417、421、422、493、690页。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在大工业中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9-230、384、385、417、421、422、493、690页。
对于资本的积累过程,马克思也是从二重性论述的:“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不仅都有简单再生产,而且都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虽然程度不同。生产和消费会累进地增加,因此,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产品也会累进地增加。但是,只要工人的生产资料,从而他的产品和生活资料,还没有以资本形式同他相对立,这个过程就不会表现为资本积累,因而也不会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9-230、384、385、417、421、422、493、690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二重性”理论,混淆了“储备的形式”和“储备本身”。例如,关于古代的农民经济,产品的绝大部分没有转化为商品,直接转化为备用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从而不形成商品储备,斯密认为“以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不存在储备”,显然他是“把储备的形式同储备本身混淆起来了,并且以为,社会历来就是干一天吃一天,或者等到明天去碰运气。这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误解。”(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8、157页。再如,对于“非生产费用”,马克思指出:“非生产费用在什么程度内,产生于一般商品生产和普遍绝对形式的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有性质;另一方面,又在什么程度内,为一切社会生产所共有,而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只是取得一种特殊的形态,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8、157页。
综上所述,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单层次理解”方式,马克思则是运用“双层次理解”或“二重性理解”;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和这种“二重性理解方法”密切联系。资产阶级经济学特有的拜物教性质,过多关注社会生产过程中“事物的自然属性”,而忽略“事物的经济社会属性”,诚如马克思所言:“这种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像被打上烙印一样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1页。
三、由劳动二重性派生的资本二重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没有像论述“劳动二重性”那样直接阐述“资本二重性”并给出定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资本二重性理论”。从《资本论》整个叙述逻辑来看,资本二重性不仅存在,而且是《资本论》主要内容。我们通常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精髓在于“剩余价值理论”,实际上,这主要是对“资本二重性”第二重属性的理论认识。
这里存在一个理论问题:能否脱离劳动二重性来理解资本二重性?
国内理论界有如下代表性理论观点:第一种观点,有学者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既是等价交换的商品生产,又是具有剥削性质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31)王峰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及其正义悖论》,《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实际上,这是将“商品生产形式”进行了“二重区分”,区分成“商品生产一般”和“商品生产特殊”(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种理解思路,其隐含前提是把“商品经济、商品生产”视作能够存在于若干不同社会形态之中,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同时,这也会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篇的研究对象,到底是某种“简单商品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定位问题。从历史来看,商品经济的确存在于许多社会形态之中,马克思就曾将原始共同体之间的“物物交换”视作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但是,商品生产作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取得支配地位,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成为现实,在其他社会形态下,商品经济只能算作一种主导社会历史形态的“杂质或附属形式”;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开篇之处,绝非“简单商品经济”或“商品生产一般”,而是只能理解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第二种观点,有学者立足张闻天的“生产关系两重性”来对“资本二重性”进行解释,这是一种限定在生产关系本身之内的“资本二重性”。(33)杨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公有资本的本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7页。与此不同,持有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在肯定“物质自然属性与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的资本二重性”基础上,进一步对社会生产关系本身进行“二次划分”,提出“资本社会生产关系的二重性”。(34)杨继瑞:《论资本经济实现形式的二重性》,《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这种理解的一个缺憾是,把马克思的“生产力”范畴仅仅理解成物质性、技术性、自然性,是一种“没有人在场的生产力范畴”。与生产力直接相关的劳动过程本身(即使用价值生产过程),马克思给出的定义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包含三个要素,其主观因素就是“人本身”;所以,“人的存在性”内含于马克思的“生产力范畴”。综合来讲,上述三种代表性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在于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层次区分;这种“二重区分”能够抽象出“商品生产一般”或“生产关系一般”,似乎能够给“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点”提供理论支撑。
然而,这里存在两个理论关键点需要探讨。第一,上述前两种观点,都没有对应马克思作为政治经济学“枢纽”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从《资本论》第1卷第3篇,真正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德文版第5章的标题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这在法文版中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3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9页。从逻辑上严格对应着劳动二重性,“使用价值的生产”对应着“具体劳动”(体现生产力属性),“剩余价值的生产”对应着“抽象劳动”(体现生产关系属性);如果我们把资本理解成运动,作为二重性的运动或过程,“资本二重性”就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的一个独特社会历史形式。我们通常认为,具体劳动是抽象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但是,作为具体劳动派生的使用价值生产过程,它的一个独特社会历史形式,则是作为抽象劳动派生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所以,劳动二重性和资本二重性之间具有严格的逻辑对应关系。《资本论》第3卷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可对资本二重性进行补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一般的一个历史地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6页。这段文字,对于研究资本二重性的文献来讲,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第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进行“二次划分”有无必要?张闻天把这种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的、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劳动分工协作关系称作“生产关系一般”,把那种在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所有关系”称作“生产关系特殊”;“生产关系一般”是内容,“生产关系特殊”是前者的形式;张闻天把通常理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内含并体现为”生产关系内部二重性之间的矛盾。(37)参见《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219-237页。我们完全可以提出相反的推论,为何不把通常理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内含并体现为”(即“植入”)生产力内部?然而,马克思《资本论》著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论述,是把“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4页。当作矛盾的两个方面,前者是生产力(人和生产资料的结合过程、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后者是生产关系(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并没有对生产关系进行“二次划分”;显然,马克思是把劳动的结合、社会化、协作特性等等,一并归入生产力范畴,并没有单列出来,作为所谓“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来讲。
四、资本二重性内在矛盾的创造性转化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其本质内容就是“资本二重性内在矛盾”。《资本论》第1卷第1篇,马克思凭借劳动二重性分析商品二因素,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体,使用价值只是商品生产者的手段,他的根本目的是占有商品的价值;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也是一个矛盾体;实际上,“资本二重性内在矛盾”是“商品二因素内在矛盾”的转化形式、发展形式。《资本论》第1卷第7篇中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既是第1卷的总结,也可视作马克思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历史结论,因而具有特殊重要性。对于这个矛盾,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4页。这里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对应的是生产力或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是主观因素劳动力和客观因素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过程,这个过程日益显示出社会化的特征;这里的“资本主义外壳”,对应的是生产关系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两者之间的矛盾,也体现为“手段”(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目的”(更多占有剩余价值或利润)之间的矛盾。处于资本主义激烈竞争中的单个资本家,竞相提高劳动生产力,其目的是使自己的商品更加便宜而占有市场,以期获得超额利润(相对剩余价值);这种最初对单个资本家有利的生产力进步,逐渐转变为一种对资本家阶级整体有害的社会行动,社会总资本中不变资本对于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表现为社会的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这“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7、237页。这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7、237页。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讲是致命伤害,资本离不开利润,就像鱼儿离不开水。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进行了集中阐述。在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反杜林论》,恩格斯对这个矛盾的阐述,译文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等等;(4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8页。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译文是“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等等。(4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9、408-409页。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理论界对“生产社会化”进行过热烈讨论,(44)朱延福:《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的社会化是同一概念吗?》,《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3年第5期;拱桥:《怎样认识生产的社会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4年第5期;陈耀庭:《“生产社会化”概念质疑》,《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5年第6期;吴敬琏:《“生产社会化”概念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观》,《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1期。都会涉及恩格斯此处对“生产社会化”的解释。恩格斯分析了人类社会三大发展阶段: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中世纪社会的个体小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更替。恩格斯认为《资本论》对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三个阶段的描述,分析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一是,“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7、397页。二是,“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7、397页。有学者认为,恩格斯这里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生产社会化”:生产资料的转变、生产本身(劳动)的转变、产品的转变;实际上,也可以理解成和马克思表述相对应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两个方面。至此,理论界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生产力方面,通常理解成“生产社会化”。然而,恩格斯在文中余下的论述,主要聚焦于“生产资料的集中”,凭借“生产资料的集中”来解释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劳动的社会化”则被淡化了。例如,恩格斯在讲到“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是指“生产资料的社会性”或“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等等。(4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9、408-409页。这和马克思的表述存在差异,恩格斯“生产社会化”(生产力范畴)的口径收窄了;当然,这种理解直接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第一个步骤——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是大有益处的。
国内理论界的讨论,通常将上述“生产社会化”理解成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的集中、生产规模的大型化;二是在生产资料集中的基础上,劳动的社会化或一体化。这两个方面,在马克思笔下是同一个过程,反映了1770—1830年那一次产业革命后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48)吴敬琏:《“生产社会化”概念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观》,《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1期。有学者针对那种以“生产规模大型化”来代替“生产社会化全部内容”的倾向,主张“生产规模大型化”不等于“生产社会化”;试图从理论上否定“一个国家一个工厂”或“社会辛迪加”的假定,进而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构建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将这次争论主要论点概括如下:一是“生产社会化”包含生产资料和劳动两个方面内容,决不应简单化理解成“生产资料的集中”一个方面;二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呈现出分散化,中小企业大量快速发展,生产过程的分散(即“生产资料的分散化”意义),显然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分工更专业化、协作更为紧密),最后提高了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三是“生产社会化”可以在生产过程分散的情况下实现。所以,脱离“劳动的社会化”,离开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特征,仅仅针对“生产资料的集中进行所有制升级”是存在问题的。这次争论的积极意义,在于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调整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构建了所有制主体多元化的“理论平台”;但是,并没有对这些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任何说明,这些多元主体之间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还是有“主导结构”(阿尔都塞用语)(49)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01页。统摄之下的复杂结构整体、紧凑的结构化整体?实际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在互联网新技术作用下,已有学者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关系演变”进行重新审视,努力批判那种“小就是美”(small is beautiful)的意识形态神话。例如,美国学者哈里森认为,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是一种“核心—外围生产网络”,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纳入由大企业领导的生产网络之中,美国制造业1977年以来雇佣人数减少的本质在于大企业的精简生产策略,通过外包、代工、外购等方式削减成本提高盈利能力,同时给中小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有趣的是,哈里森提出由大企业主导的生产网络是“没有集中的集中”(或译作“没有集中的积聚”;concentration without centralization),生产在全球的分散化,并不意味着大企业和小企业经济权力的均等化,员工在两种不同企业中的福利待遇是完全不同的;对于跨国公司自身来讲,在生产分散化的情况下,财务、配销等等权力仍然集中在母公司或公司总部手中。(50)Bennett Harrison,Lean and Mean: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Corporate Power in the Age of Flexibility,Basic Books, 1994, pp.8-34.中文译本参见班尼特·哈里森:《组织瘦身——二十一世纪跨国企业生产形态的蜕变》,李昭瑢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3—48页。哈里森的观点被有效吸收进“空间化学派”构建之中,参见Michael Wallace and David Brady, “The Next Long Swing: Spatialization, Technocratic Control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Work at the Turn of Century”, in Ivar Berg and Arne L.Kalleberg(eds.),Sourcebook of Labor Markets: Evolving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lenum Press, 2001, p.115.中文译稿参见迈克尔·华莱士、大卫·布雷迪:《下一个长期波动:世纪之交的空间化、技术官僚控制和工作重构》,顾梦佳译,张开校,《政治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2期;顾梦佳、张开:《空间化学派经济思想研究》,《经济纵横》2020年第1期。我们从“生产资料的集中”视角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微观主体的演变,这是一种新的集中形式,是通过分散而实现的集中,是“生产资料的集中”新的历史发展形式。
实际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呈现出具有“主导结构”多元主体的结构化整体特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恰恰体现并蕴含着“生产社会化”内容之一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内容。对这种所有制结构化整体的理解,我们可以借鉴马克思论述产业资本和其他资本类型之间结构关系的方法论。马克思指出:“产业资本是惟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业资本的存在,包含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存在。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那几种在产业资本以前,在已成过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会生产状态中就已出现的资本,不仅要从属于产业资本,并且要改变其职能机制来和产业资本相适应,而且只能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从而要和它们的这个基础同生死共存亡。”(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6页。这里的方法论,马克思也曾讲过:“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与“生产社会化”理论探索相伴而生,我国理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也进行了富有创见的探讨。(53)马原生:《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再认识》,《理论探索》1985年第4期;房良钧:《再谈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云惟经:《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现代哲学》1986年第2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表现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在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大工业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当代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生产方式主导之下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来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或“生产社会化”,其中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具有“以分散实现集中、有集中的分散”的历史特征,其中的“劳动的社会化”仍然要通过“分工专业化”和“协作紧密化”来实现,主客观两个方面的结合过程体现为我国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是具有“主导结构”多元主体的结构化整体形式,具体表现为作为形式的三大资本类型的结构化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类资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是马克思“资本二重性内在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造性转化形式”。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资本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资本形态”;“资本”存在,其自身固有的“资本二重性内在矛盾”就不会消失,但会发生上述历史转型。
五、结 论
马克思《资本论》开篇之处,就强调“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这个重大论断,并没有引起国内理论界研究“资本二重性”相关学者的足够重视。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对应着使用价值生产过程(生产力),抽象劳动对应着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生产关系)。本文认为,如果脱离“劳动二重性”来研究“资本二重性”,就会使得“资本二重性”建立在“理论沙滩之上”,陷入“理论空中楼阁”。那种延续张闻天的思路,单纯对“生产关系本身的二次划分”,进而对“资本二重性”进行理论解读,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其逻辑缺陷是:这种“生产关系二重性”基础之上的“资本二重性”,丢掉了“生产力”、丢掉了“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丢掉了“具体劳动”。其逻辑推理链条,存在明显“断裂”。
本文遵循“劳动二重性—资本二重性—资本二重性内在矛盾的创造性转化”的叙述逻辑,尝试给新型政商关系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或“政治经济学基础”,其本质就是立足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资本二重性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的“非公资本”,绝非是“中性的”,而是必然具有“二重性”;恰恰是“非公资本二重性”的存在,才谈得上构建“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对于“非公资本”的理解,一方面,我们若仅仅将其视作“中性的”,仅仅具有生产力属性,则会导致政商关系既不亲、也不清;另一方面,我们若仅仅将其视作“剥削”,仅仅具有生产关系属性,则会诱发“资本外逃”,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丧失活力。实际上,构建“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以及“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等等提法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就在于“非公资本的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