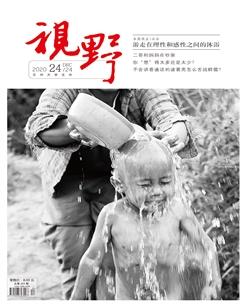做梦是自由的,说梦便不自由
文珍
我总是梦见在路上。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也时常出门旅行,只是似乎还嫌不够,还渴望在梦里走得更远,更远。经常梦见一个人走夜路,或者和人约好同去某地,却在车站错过,上车后一节节绿皮车厢寻过去,窗户敞着,大风把白色纱帘吹得老高,也就索性找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望向窗外更不可知的地界。还有一些梦里,我独自坐开往郊区的大巴去看望某个朋友(不知为何梦中朋友都住在郊外),下车后如同来到另一座城,会迷好一阵子路,但心里快乐异常。也梦见过开车驶入森林,或者沿着越南美奈无比漫长的海岸线,一直开到山顶。因为是在如深河一般的夜色里,当然山下什么都看不见。也有旅伴,却鲜少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在昏暗中回望旅伴的侧脸,在那黑白深灰的梦境中,如沉默忧伤的石像,见证我不知该驶往何处去的茫然。
有时候也梦见吃东西。五六岁时有一次冬天睡午觉,梦见妈妈给自己削一个梨子,汁水四溅,一看就很甜。怀着巨大的期待等她削完,眼看就要到嘴,突然被叫醒要去上学。醒后哭了许久许久,因为永远、永远都无法知道那个梨子到底有多甜了。妈妈说:梨离同音,这说明我们不会分离。这说法多少安慰了年幼的我,然而到现在还是没有忘记这个梦,因为那是第一次知道梦与现实的泾渭分明,而一個人又可以如此轻易地从美梦中被惊醒。
又过了一些年,上高中了。有一次梦到妈妈不见了,到处都找不着,心里无来由地一阵大恸,知道她多半遇到了危险,在梦里一直痛哭到醒来,立刻光脚下床去拍父母卧室的门。来开门的正好是妈妈。我一下子扑到她怀里放声大哭,又抽泣了半小时才重新睡着。反复寻思因果,大概是那段时间班上一个男生的母亲患癌去世,他的座位空了几天,问知缘由震惊之余,同情心迅速决堤,暗自发誓等这男生重新回校后一定要对他格外友善——我们原本几乎没说过话。结果过了几天男生回来上课,除胳膊上戴了黑纱,其余一切如常,甚至和前后同学若无其事地说笑。周末忍不住和来接我的妈妈说了这事,说着说着就角色代入,说如果是妈妈你……还没说完就觉得委实难以想象,眼泪夺眶而出,根本控制不住。当时公交车上人极多,妈妈不无窘迫地把我从人最多的上车口推到车窗边去。我就背对着人群一直默默流泪,一直到下车。之后不久就做了那个可怕的梦。
那年我十五岁,开始知道梦可以折射某种真实的恐惧。在梦里死过一次的人,也许就不会自杀了;在梦里永诀的人,醒后会否更珍惜彼此,我却不知道。因为妈妈只是一径搂着我说:傻瓜,梦死得生。梦死得生——这大概是中国人最原始的关于噩梦的麻醉剂了。
还有一个伤心的梦是关于猫。这时已毕业开始工作了。单位院子里有一只叫小黄的流浪猫,我每天都和几个爱猫的同事一起,给它喂食,陪它嬉耍,尤其是我,把它的相伴视为上班后最愉快的时光,数次动念要带回家……只是家里已经有两只猫了。后来小黄生了一窝猫仔,初长成后在单位后楼乱窜,惹恼了其他本来就厌猫的人,我和猫友只得设法寻好人家托养。不料费了许多功夫送走最后一只小猫,与我们相伴两年的小黄竟也在哀叫两日后不辞而别。因为内疚和牵挂的缘故,又或者只是单纯地难以忘记,时隔半年我又梦见了它。
小黄,我昨晚又梦见你了。
我梦见你死了,我大哭起来。你神奇地又在我的悲伤里活过来,变成了最初见你的模样。出生一个月不到的小黄猫,身上有老虎样的斑纹,小兔般的粉红小鼻,温顺如童的黑眼睛。我把你抱在怀里,你挣开,我作势欲走,再回头,你还和以前一样不停地跟着我,像阵风一样兴高采烈地冲来。我过了街,站在对面,也能看见你小小的身子在人群和车流空隙跑着,雀跃地,快活地。可是那条街好长,天好黑。你向我奔跑,却永远跑不到跟前。
小黄,天长地久,我一直在街道这边等你。你跑不过来。
除了2010年日记里记载的这个梦,关于小黄当然也有高兴一点的回忆。可是似乎通常快乐更容易被遗忘。其实即便是悲哀的梦,也有忘记的良方:心如刀绞地醒来,怔忡半日复又睡去,起身洗脸刷牙,就差不多忘了大半。在深深浅浅的梦之国度里,我们到底走过多少山长水短的幽明,见到如何若即若离的人,说过怎样真真假假的一些话。有时候也因为实在太像现实,也就不愿意记住。
我梦过故宫空旷处极苍白而辽远的太阳,我梦过一些幽暗宜于私语的房间,我梦过坐在冬天的草地上大笑,我也梦过绵延通往无尽的铁轨,胡同深处停放的旧自行车,暌违多年的儿时玩伴,越来越窄的林间小径,沙漠中心涌出的泉水,以及一直站在那里等我的鹿……我没有梦过得奖,没有梦过礼物,梦境几乎没有颜色,也少有连贯的声音。在一类时常重复的梦里,我心怀忐忑地等待考试,而且永远都是政治……从小学起,我就会梦见出门后才发现衣不蔽体,只能窘迫万分地藏在上学的路边,看众人谈笑风生地过去。无论梦多少次仍旧无法可想,最终只能一身大汗仓皇地醒来。
我还总是梦见一片大水,梦见我们在水上划船,而四顾都是大雾茫茫。这是我梦中出现过的最后一种交通工具,却也是最难忘记的,因为那雾随时可能吞噬你我。而桨握不好,也会随时掉入水中。
这就是关于梦我可以说的一切。你知道的,鲁迅先生说:做梦,是自由的,说梦,便不自由。
我好像也已说了太多。
余小洋摘自中信出版社《三四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