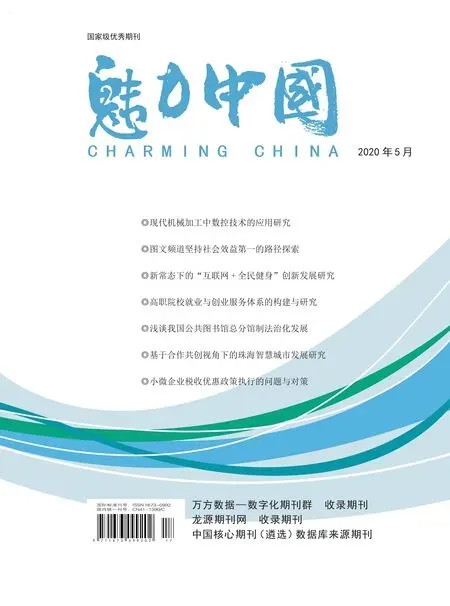汉语“心”字类词汇的认知转喻学新论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8)
一、引言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转喻本质上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手段和策略,Lakoff &Johnson(1980)将转喻定义为通过与其它事物的关系来概念化一个事物的过程,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和基本的思维方式。人们惯于用已知、熟稔的概念,来说明和解释未知、陌生的概念。一个词一经产生,语言使用者就会通过隐喻或转喻的认知分析,扩展和延伸其基本义,不断丰富该词的语义。
“心”本义指心脏这一人和高等动物体内主管血液循环的重要器官,具有维持生命的重要功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心是体验意识的中心或人的主体。因为心决定一个人的本性,是一个人真实自我的轨迹。当前学界对汉语“心”字类词汇的研究大多数是围绕认知隐喻来展开的,鲜有学者将其与认知转喻这一理论联系起来予以研究,针对这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本文立足于认知转喻这一新型理论基石,对汉语“心”字类词汇的认知转喻机制和认知理据予以深刻论述。
二、汉语“心”类词汇多义转喻框架建构
卢卫中(2003:25)指出,由于认知、思维和表达的需要,人类不仅将人体词投射于具体事物的描述,而且投射于抽象的概念表达。汉语“心”字类词汇主要将“心”这一器官投射于自我、情感、道德等抽象概念域。
(一)转喻自我
Yu(2007:27-47)指出,在传统意义上,中国人将心脏概念化为个体认知能力的中心,心除了是身体的一个重要的内部器官外,也是心灵的所在地。一方面,心被概念化为认知的主体,被认定是思想、智力、理性、意图、判断和意志的所在地,另一方面,心也被概念化为一个人内在自我的轨迹,相比一个人的外在自我,它包含着一个人最深刻的存在,或真实的自我和一个人的个人性格。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是体验意识的中心或人的主体,是内在自我所在。“心”是人的内心,贮藏着内心的想法和情绪,是人的性格特征所在,如:诚心、交心、粗心、口是心非、冷眼心热、赤胆忠心等;
(二)转喻情感
转喻倾向于用具体、关联的事物替代抽象的事物,情感范畴也位列其中。孙毅和杨秋红(2013)指出,人们根据自己的是非标准对外界刺激所引起的感觉产生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这种反应贯穿在整个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等过程中,这就是人们的情感。古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也理所当然地认定心是情感、情绪的发源地。由于情感是多种多样的,含“心”的词语也是五花八门的。“心”表示情感可以反映人的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汉语中表示“喜”和“乐”的词语如开心、可心、舒心、安心、宽心、欢心;表示“怒”和“恨”的词语如恶心、心头之恨、急火攻心等,表示“哀”和“愁”的词语如伤心、寒心、心死、心酸、心烦意乱、忧心如焚、心神不宁等。
(三)转喻道德
道德作为人类社会高级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约定俗成、共同遵守的既定行为准则与社会规范。转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现象,更是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借助转喻这一柄认知利剑,抽象而深邃的人类道德概念得以表达和理解。在汉语中,心表意念、愿望的意义进一步泛化,即可转喻为个体受制于公众舆论的对社会事件的看法和评价,即符合社会规范的想法或社会道德准则,如良心、爱心、好心、昧心、歹心、邪心、狠心、兽心、心黑、心狠等。
三、汉语“心”字类词汇多义框架的认知理据阐释
(一)体验哲学性
人是衡量周围万物的尺度和标准,原始人类在初识世界时,遵循“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以体认或体验的方式来直接认识世界。孙毅(2013:127)认为人体及其器官是人类认知的基础和出发点,人们随后又把对人体的认知结果投射到对其他物体、事物等概念的认知与理解上。人体是人类最熟悉的事物,人们惯于把人自身的结构及经验当作认知的源域,并将其映射到对其他事物概念的认知与理解上。人体及其器官是人类认知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人们常把对人体的认知结果投射到对其他物体、事物等概念的认知与理解上。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心”被看作具有认知和情感机能,被概念化为思维和行为以及储藏情感的器官。因此“心”是心智和认知、理解功能所在。
(二)民族文化性
转喻与文化之间相互诠释、相辅相成。由于民族区域和生态环境的区别、文化积累和传播方式的差别及社会生活形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差距,各民族文化亦会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不同民族的转喻概念体系既源于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又根植于具体的社会文化中。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的观察角度及对该事物不同侧面的关注程度不尽相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的思维方式、文化沉淀以及语言的发展演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观念提倡“身心统一观”,认为汉语 的“心”是情感和认知结构的核心,具有逻辑推理、道德意愿及审美感觉的能力,能够统一人的意愿、情感和思维。
四、结语
作为人们重要的认知方式,转喻对人们认识事物、事物概念的建构和语言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上通过对汉语“心”字类词汇的多义转喻框架进行详细的认知分析,一方面使得我们对汉语“心”字类词汇的语义认知更加全面和完整,另一方面有利于为汉语词汇理解和习得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实践路径。